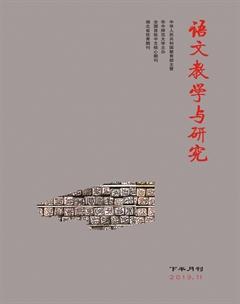浅析“犯”与“避”的艺术特色
“犯”与“避”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方法。“犯”,指让相同或类似的人物、环境、细节等在文章中多次重复出现。“避”,指避免人物、环境、细节等方面的雷同,使文章富于变化。“犯”和“避”的创作方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十分广泛,其時而出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让独特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与我们对话;时而出现在环境描写中,让情和景相互交融,创造出一种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时而出现在文章的细微之处,深深打动着读者的每一个神经感官。“犯”与“避”在文学创作中通过求同和存异的方式呈现出来,使读者领略到别样的艺术魅力。
一、人物形象塑造中的“犯”与“避”
“文学即人学,文学说到底是在研究人,只不过它是从文学这个角度去进行研究的。”人物是文学创作的灵魂,如何刻画出生动鲜活、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一直以来都是作家所追求的。“避”和“犯”常常用在人物语言、动作、外貌的描写上面,令人物形象“犯中有避”,表现更加丰满。
俗话说,“言为心声”,“犯”与“避”运用常常在人物语言的描写中得以体现。例如,在《孔乙己》中,“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一语出现四次,本是相“犯”,但次次表达的含义都有所不同。第一次出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这时尽管孔乙己已是落魄的书生,但自命不凡,妄想功名。第二次出现时,孔乙己已经沦落为讨饭的乞丐,但他“品行比别人都好,从来不拖欠”。可以看出,孔乙己最看重的除了功名之外,就是人格。然而残酷的生活使他失了最后的尊严,被打断腿的孔乙已,自知来日不多,于是只能“颓唐的仰面”。小说最后两次出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大概已经死了,可见孔乙己悲剧的根源——不会谋生,挣不到养活自己的钱。从“自命不凡”到“人格沦陷”,再到最终的“丧失生命”,只借助人物话语的重复,就将孔乙己的不幸、悲哀表现的淋漓尽致。鲁迅先生曾说:“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而在《孔乙己》中,透过掌柜的不断重复的话语,我们又何尝不能推断掌柜的形象:冷酷势利,麻木不仁。可见,“犯”与“避”在人物语言中的运用,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物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促进人物形象的生成。
“犯”与“避”在动作描写上的运用也很有魅力,能够帮助人物性格塑造的更加完整、生动。例如,《记念刘和珍君》中描写刘和珍和同伴被卫队杀害的片段,三人被杀本是相“犯”的,但鲁迅在选取动词时处处相“避”。刘和珍中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张静淑“中了四弹”“立扑”;杨德群“弹从左肩入”“穿右偏侧出”“在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立扑”。鲁迅选用“入”“仆”“穿”“击”等不同的动词,并且动词数量一次比一次多。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意图不是为了写杀害过程的残忍,而是意在指出凶手的残忍;写凶手残忍时,不是写凶手举起武器的如何恐怖凶残,而是省略了形容词,用动词(动作群)来堆砌,写凶手对刘和珍及其同伴下了多少次手,从而达到强调凶手残忍、人心冷漠的目的。“细微的差距使人物产生出性格内容的最独特最合适的形式”,《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的“三次摇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提辖对镇关西的“致命三拳”,都巧妙地在“犯”中融入了“避”,不仅令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更为情节增添了很多的趣味性。可见,“犯”的运用,并不是呆板机械的重复,而是重复中有变化,变化中又体现出一致。
“犯”与“避”在人物外貌描写上也有很多运用。例如,在《祝福》中,鲁迅三次描写祥林嫂的外貌,是为相“犯”,但三次外貌描写代表了其三种不同的人生状态。祥林嫂初到鲁镇时,“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她的生活虽是困苦的,但脸颊是红的,衣裳是规整的,可以看出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量,内心充满宁静和希望。当过了两年,她第二次“站在四叔家堂前”时,“她顺着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从她“没有神采的眼睛”里,我们不难发现,生活的重担,世俗的眼光已然让她的意志濒临崩溃,身心受到的巨大的创伤,失去了对生活、对未来的希望。第三次对祥林嫂的外貌进行描写,是“我”的视觉所见,所以描写的十分具体。祥林嫂在众人漠然的眼光里,只是“直着眼,和大家讲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从“顺着眼”到“直着眼”,从“黑发”到“花白”,从“周正”到“乞丐”,在对祥林嫂的三次外貌描写中,我们即可了解她的一生。可见,鲁迅功力之深厚,能犯中求避,抓住人物性格的变化,在人物外貌、气质、性情等方面,突出了“貌同而神异”的特点,做到同而不同,灵活多变。
二、环境描写中的“犯”与“避”
环境描写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避”与“犯”的完美结合在环境描写中多有体现,可以起到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外化人物情感的作用。
“渲染气氛”是环境描写最重要的功能,良好的环境气氛可以有效激发与读者的共鸣,而“犯”与“避”的运用可以帮助其展现出更丰富的情味和意蕴。例如,在《小狗包弟》中,将“犯避结合”的手法运用在环境描写里,营造了一种浓烈的“物是人非”的环境气氛。小狗包弟死后,“我”发现院子里的景色变了很多。“竹篱笆”变成了“砖墙”、“房屋”增添了“主人”、“墙壁上”多了“两扇窗”、“葡萄架”被“扫掉了”、右面角新增了“化粪池”……通过多次重复所形成的单调的节奏和平板的声调,描写了景物前后的“同而不同”,这样本是相“犯”,而“我”偏偏不厌其烦地将其一件件罗列出来,进行细致描绘,使我们感受到景物变化之“多”,从而暗示人物心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文章的主题进行揭示: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之久,但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机还没有完全恢复,公民的道德风尚也遭受了极大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漠和隔阂。因为“种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调,所以换成了“不开花的树”;人与人之间早已不是柔软温馨的“篱笆”,而变成了密不透风的“砖墙”。“我”放眼望去,处处都发生了变化,昔日的景色、欢愉早已不再。景物变化之多,实是“我”心中的痛苦之多,对时代的控诉、对亲人的思念,一处处叠加起来,导致“我”心中的愧疚、痛楚不止一丝。
“犯”与“避”的运用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点,反映其变化轨迹。例如,《边城》中对月光的两次描写:
“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若对溪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是太美丽了。”
……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在月光下變成一片黑色。”
小说中第一次描写的月光具有“洁白明亮”的特点,是朦胧的,是柔和的,是饱孕着生机的。正如这时的翠翠,正值青春韶华,初涉人世,单纯的心灵仿佛和外界隔了一层纱,充满着对爱情的羞涩和对未来的渴望。让翠翠心神荡漾,由此感叹:“若是有人唱歌,实在是太美丽了。”当翠翠听到妈妈的故事后,感到无比的悲伤和凄凉。妈妈的爱情是那样真挚和热烈,但自己却不能像她一样,让心中的爱情热烈勃发。就像那高高悬挂在天上的月亮,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人们只能远远地观赏,却不能触碰和拥有。因此,第二次所描写的月光具有“高寒清冷”的特点。从“洁白柔和”到“高寒清冷”,正如爱情对翠翠而言,曲曲折折,兄弟二人最终都离她而去,她终究没能得到理想中的纯洁爱情。从表面上看,两次对月光的描写似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由于人物心境不同,寓意有别,因而所体现的氛围、情感也有所差异。可见,“犯”与“避”是从表面的“同”中表现出深刻的“异”来。
“一切景语皆情语”,“犯”与“避”在景物描写中的运用,还可以帮助人物将内心的“情”,更加自然地渗透到外物之中。例如,汪曾祺在小说《八月骄阳》中描写老舍“坐在长椅,望着湖水”的情景: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赛着叫。整个太平湖全归了它们了。
……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蛐蛐、油葫芦叫成一片。还有金铃子。
小说三次描写老舍“望着湖水”的情景,本是相“犯”,但有三段景物描写穿插其中,这三段景物描写既表现了时间的不断推移,也将人物不同的内心活动展现出来。在第一处景物描写中:“柳树上的知了叫得非常欢实。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知了的叫声渲染出一种喧闹的气氛,这不仅是自然季节的反映,也暗示了时代的不平和喧嚣。在第二处景物描写中:“粉蝴蝶,黄蝴蝶。忽上,忽下。忽起,忽落。”蝴蝶自古就承担着多种表意功能,可以象征自由和美丽,也可暗示灵魂和死亡。在这里,飞舞的蝴蝶正是老舍内心活动的外化。他心中对时代的失望和报国无门的悲愤,化作漫天飞舞的蝴蝶,时时刻刻围绕在他身边,使他无法解脱。在第三处景物描写中,各种鱼虫生机勃勃,嘈杂热闹,而老舍先生只是静坐在湖边,仿佛世上万物都与他无关,可以看出他一心赴死的决绝。汪曾祺并没有描写老舍的思想挣扎,如何投湖,也没有呼天抢地的控诉,而是运用三处“同而不同”的环境描写,文字虽淡,情感甚浓,让我们通过外在的景物来观测到人物内心的真实情感。
三、细节描写中的“犯”与“避”
细节是构成艺术作品的细胞,鲜活生动的细节描写为文学作品增添了不朽的艺术魅力。“犯”与“避”在细节描写中的运用,对刻画人物形象、渲染环境气氛、推动情节发展都有很大帮助。
每一篇成功的作品中,必定会塑造出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犯”与“避”的运用能够帮助人物形象塑造的更加完整、生动。例如,在《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的“军大衣”像是一个“道具”,通过四次对其描写,不断对人物形象进行填充和丰富。当奥楚蔑洛夫穿着“军大衣”从广场威风凛凛的走过时,这时的“军大衣”是其身份的象征,仿佛穿着这大衣,就有了极大的权力。同时也暗示了时代背景:沙皇统治下官爵作威作福,对百姓凶横霸道。第二次描写“军大衣”时,奥楚蔑洛夫因为“判错了狗”而担心,但又碍于自己的面子,用“天气热”作掩饰要把军大衣脱下,足以看出其见风使舵,狡猾阴险的性格特征。第三次描写“军大衣”时,奥楚蔑洛夫认为“狗”确实是将军家的,他大惊失色,用“天气冷”做借口要再次穿上军大衣,他内心的胆怯暴露无遗,与外表的霸道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一次描写“军大衣”在小说结尾,当他确切知道这是将军家的狗,自己已出尽洋相时,他还力图保证自己的威风,故作镇定的“裹”上大衣,耀武扬威地走开了。通过奥楚蔑洛夫对军大衣的一“脱”一“穿”一“裹”,把其见风使舵、欺弱畏强的性格特点展露无遗。
除此之外,“犯”与“避”在细节上的运用还可以渲染气氛,通过气氛的渲染,达到揭示文章主旨的效果。例如,鲁迅的小说《示众》里,对胖孩子“叫卖声”的描写:
“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荷阿!馒头包子咧,热的……。”
“刚出屉的包子咧!荷阿,热的……。”
“热的包子咧!荷阿!……刚出屉的……。”
《示众》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只是描写日常的生活片段——熙熙攘攘的街上忽然来了巡警和犯人,众人一哄而上围观热闹,结束后又各自散去,恢复原样。全篇四次描写“胖孩子”的叫卖声,从其开始,又以其结束,本是相“犯”,但就是这简单的叫卖声中却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首先,小说开篇多次描写天气的炎热,“狗吐出舌头”,“鸟也张着嘴喘气”,万物都躁动难安。胖孩子的叫卖声单调乏味,又余韵悠绝,更为这炎热的气氛“添了一把火”,渲染了一种昏昏欲睡、百无聊赖的夏日气氛。就是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仍有众多“看客”围观止步,可见其无聊乏味的生活状态,和空虚麻木的内心世界。其次,“胖孩子”也是“看客”中的一员,尽管馒头已经凉透,他还在不停地叫卖着,仿佛只是在例行公事。祖国的下一代,仍处于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对于同胞被杀毫无所动,只一心想着赚钱。鲁迅反复提到“胖孩子”的叫卖声,意在表示“看客”的世界还将延续下去,祖国的未来看似渺无希望。
“犯”与“避”的运用还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两次描写偷听的细节,是为相“犯”,但两次描写详略有致,同而不同。一处是李小二妻子在酒店里“偷听”,陆谦等人做贼心虚,说话压低了声音,李小二妻子听得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但就是这场不大真切的“偷听”,才使李小二夫妻产生疑心,要是连半句也听不到,后续的故事便也无法开展。只有藏头露尾,模棱两可,才会让李小二夫妻意识到这伙人密谋的意图所在,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第二次偷听的主角是林冲,由于草料场被大雪压塌,林冲不得不到山神庙暂时歇息。而陆谦等人正处得意忘形之时,在山神庙中将所有计谋放肆说出,林冲听得一清二楚,意外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于是拔刀奋起,走上了梁山之路。“物类虽同,格韵不等”,两次描写偷听的场景,一清楚,一不清楚。前者略写,显得惜墨如金,恰到好处;后者详写,又泼墨如云,也恰如其分。由此可见,“犯”与“避”的写作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为小说写作带来了妙不可言的艺术效果。
“犯中有避”法,究其实质,是为了从同一中去寻求差别,从细微的变化处寻找深刻的蕴含。学生在阅读欣赏这类表现手法时要深入思考,发掘其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这样才能更好地感受到文章细腻精微处所体现出的作者的匠心,才能更好地领略文章的深长意味。
刘嘉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