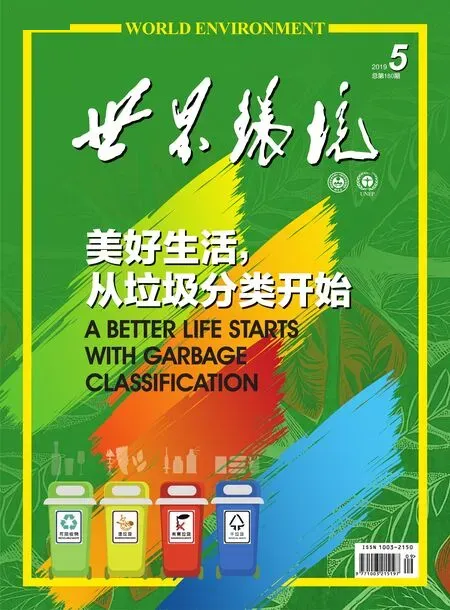垃圾分类将步入“强制”时代,长效机制还待完善
■文 / 李禾

2019年,被认为是中国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元年”。从7月1日开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开始步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随后,包括北京、广州、杭州、重庆、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也纷纷开始提速,将垃圾分类提到了城市管理的重要位置。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简称 《通知》),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生活垃圾分类曾呼吁和试点多年,但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此次上海强制要求生活垃圾“四分法”,如此分法是否太过复杂?该如何建立分类的长效机制?
垃圾围城和“邻避运动”的两难处境
部分大城市“垃圾围城”是难以回避的现实。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7年全国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2亿吨。其中,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北京市,产生量为901.8万吨,其次是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产生量分别为899.5万吨、737.7万吨、604万吨和541.3万吨。前10位城市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为5685.8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8.2%。
但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也成为“邻避运动”的主要领域,如2006年公众反对建设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2016年浙江海盐、海南万宁、江西赣州等地的垃圾填埋和焚烧项目又相继引发周边公众的抗议,生活垃圾减量和科学处理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短板在有害,难点在厨余收集
“本次上海的‘四分法’主要是根据《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国办发 〔2017〕26号)的分类标准、上海人的语言习惯,以及末端处理设备的能力和处理便捷性来确定的。”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说。
对于垃圾分类,曾有一种观点,“干湿”两分法比较好推行。也就是说,把菜叶、剩饭、骨头等厨余“湿垃圾”分出来,避免弄脏塑料、纸张等其他“干垃圾”,影响其回收再利用。号称世界上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日本,在实行垃圾分类初期,也仅将垃圾分为可燃烧、不可燃烧两类。
本次上海市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四类来分,但是让人费解的是,部分垃圾并非是按照干、湿的字面意思来分类,比如尿不湿属于干垃圾,干瓜子壳却属于湿垃圾,鸡骨头等属于湿垃圾,大骨头却属于干垃圾……杜欢政参与了上海垃圾分类相关政策研究的前期工作,他说,生活垃圾的特点是非标准化、成分极其复杂。比如按照粽叶属性,本应属于厨余湿垃圾,但粽叶的材质比较硬,后端处理时刀子很难切碎它,因此,只能作为干垃圾来焚烧处理;大骨头被分类到干垃圾,也是同样的道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显示,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其中,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同时参照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再选择确定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强制分类的类别。而未纳入分类的垃圾,按现行办法处理。
这是由于有害垃圾虽然产生量不大,但危害性比较大,这一类必须要强制分出来;可回收物,相对来讲资源价值高一些,当前市场上也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回收利用系统,将之纳入规范管理中,相对容易做到。如果用传统的填埋或焚烧方式处理有机、易腐烂的厨余垃圾,导致垃圾后端处理设施污染比较严重、效率相对较低等问题,因此,需要把厨余垃圾强制分类出来。
据统计,目前46个重点城市中,大部分城市对垃圾分类采取“四分法”: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其实,这也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虽然世界各国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方法不太一样,但大体上都是要将有害的、有用的垃圾分出来,其他垃圾进入规范的处理设施中。
“对比发达国家,我们当前生活垃圾分类的短板是有害垃圾收集,重点是可回收物,难点是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分类收集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体系,可回收物分类收集的问题是如何精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的问题是找到肥料出路。”如何破解这一连串难题,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看来,参与者的意愿和垃圾的出路是关键。
徐海云说,在惯用的“四分法”大前提下,进行垃圾分类的城市还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地区习惯和处理技术,去试着进行更精细的分类。
先有分类习惯还是先有处理设施?
垃圾分类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有机厨余湿垃圾分离出来。目前,中国生活垃圾总量中,厨余垃圾占比为36%-52%,占中国生活垃圾量的“半壁江山”。厨余垃圾中,水分、油脂和盐含量分别约为75%、16%和1.2%,因此,厨余垃圾是卫生填埋场里高浓度渗滤液的主要来源,也是填埋后腐烂产生沼气导致爆炸的主要风险源。
以前很多城市,居民在家把生活垃圾分类做好了,到了运输环节,所有垃圾又倒在一起混运到垃圾处理企业。那是由于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在全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而上海作为全国首个强制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市湿垃圾处理产能为3480吨/日,通过一系列的湿垃圾处理体系建设,目前,上海市湿垃圾处理产能已基本匹配产量。
后端比较适合厨余湿垃圾处理的是耗氧堆肥、厌氧发酵等生物处理,这也是当前一些大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重点。上海计划到2020年,湿垃圾处理能力达6300吨/日,并逐步降低干垃圾末端处理上限,计划到2020年降低到1.81万吨/日。
“但是在现阶段,分类后各种垃圾又混到一块运输、处理也是有可能出现的。”杜欢政说,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至少需要3-5年,到底是等居民养成分类习惯后再建设分类处理设施,还是等处理设施全部建成后再要求居民垃圾分类?“这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因此,先开始实施强制分类,再根据分类和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逐步调整和解决。”
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检测分析室主任刘欣艳说,随着垃圾总量的增加,后端处理压力颇大。2019年,北京垃圾处理总量预计突破1000万吨,厨余垃圾约占二分之一。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处理主要采用焚烧、填埋、堆肥等方式。具体来说,预计2019年北京垃圾填埋的处理能力不足200万吨,焚烧处理能力约600万吨,堆肥处理能力约200万吨,还有几座焚烧厂在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垃圾分类是一个从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完整链条,涉及产生垃圾的居民和单位,收集、运输和处理的企业,管理的政府,参与者众多。在一定阶段,分类又混运的情况难以避免。“现在需要做的是,大家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要相互推诿和指责,各负其责,把自己在链条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这件事情总会有解决的一天。”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可谓是“ 一枝独秀”。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的《“十三五”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2020年底,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其他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县城(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以上,建制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以上。
刘建国说,目前,中国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的基本结构是焚烧发电、卫生填埋并举,随着垃圾分类逐步推动,一批适合处理有机湿垃圾的生物处理设施在逐步建设中。“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成为中国垃圾处理整个技术格局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分类处理系统,将不同特性的垃圾放到适合的处理设施中去,达到整体绩效最优、污染最低。”
例如上海,在垃圾管理新规落地两个多月来,湿垃圾清运量显著增加,干垃圾明显减少。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底,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45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5倍;湿垃圾分出量约达到92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130%;干垃圾处置量控制在低于15500吨/日,比2018年底减少了26%。
怎么建成分类的长效机制?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垃圾曾被称为“ 放错地方的资源”,实质上,垃圾确实有资源的属性,但需要强调的是,生活垃圾首先是污染源,从环保角度看,是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一种物质;从经济学角度讲,是一种价值为负的商品。垃圾的首要属性是污染源而非资源,这样推行垃圾强制分类,不分类还要罚款才具有合理性。
为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多年来中国一直呼吁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并进行试点,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该如何建立分类的长效机制?
据悉,在2019年6月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在发言中认为,既然立法,应该有更强制性、更有约束力的规定,比如草案第38条提及的“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应该将“推行”改成“实行”,即实际执行法律确定的制度。
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主要是在培养公民意识、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其实是我们做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好的载体。我们每天都需要去做,它每天就在我们身边。这些事情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可以从做这个事情当中形成良好习惯和素质。”
从具体实施情况看,杜欢政说,分类投放不能“一刀切”。上海要求垃圾“定时定点”投入,投放点不能设的太远,投放时间也要跟小区居民协商。“比如小区居民工作时间多为996,设置早6点到晚8点为投放时间,很多人就无法扔垃圾了。必须‘一区一策’,‘一刀切’的政策最终是无法长期实施的。”
因此,目前上海按照“定点要坚持逐步推行,定时要灵活,撤桶要鼓励,破袋要引导”的思路,也在建议有条件的小区因地制宜适当延长垃圾箱房开放时间,同时大力推广“破袋神器”。对夏季湿垃圾容易腐烂发臭问题,还会督促相关单位,增加清运频次等。
在生态环境部2019年6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也表示,生态环境部正推进《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将垃圾分类制度及相关要求纳入修订内容;根据 《“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明确将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覆盖率、有害垃圾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生活垃圾填埋量等作为考核指标;将垃圾分类突出问题纳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