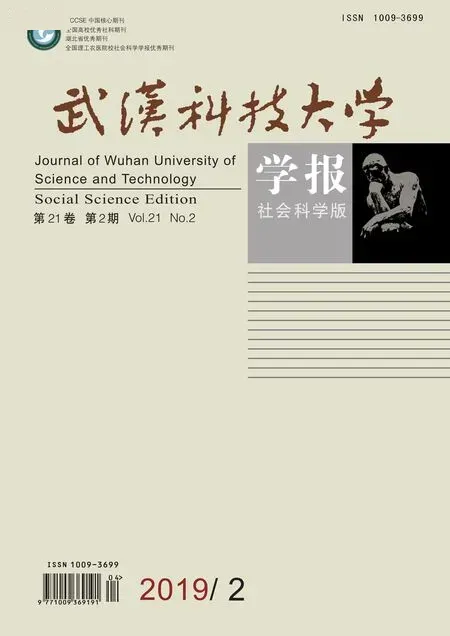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可能与限度
张 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
虽然我国某些特别法或司法解释对具体情形中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作出规定,但是仍无法指导这些具体情形以外的其他纯粹经济损失可否获赔问题的处理。结合域外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规则和我国法律体系,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规则的设定,可在两大领域展开,其一为合同法领域,其二为侵权法领域。在合同法领域,现行合同法对于某些类型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已经作出了规定,而其他尚未规定的类型,应否仍然放在合同法领域予以解决,即在合同法制度框架内设置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规则,还是说在侵权法领域内进行探讨,是设置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规则的前提性问题。
(一)合同责任扩张之非必要性
德国法上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规则并非《德国民法典》明定之内容,而是通过其后判例发展而来,其中最为重要的属第三人缔约过失和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但我国有无必要同样在合同法领域创设此种制度,以此扩张合同责任,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提供依据呢?
首先不应创设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合同相对性原则,但根据《合同法》第8条关于合同约束力的规定、第64条关于向第三人履行合同的规定、第65条约定第三人履行的规定以及第121条因第三人原因违约的规定,合同相对性原则仍然可得证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得到严格遵循和广泛适用①。《合同法》严格秉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存在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盖因在第三人受损情形中,由于第三人并未参与到合同缔结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对第三人不负有先合同义务,自然就不存在因义务违反而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此对缔约当事人课以第三人赔偿责任,难谓妥当。
德国判例之所以会引入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就是因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在合同成立之前或未成立之时无法为第三人提供保障。而我国现阶段尚未承认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在将来是否会创设此制度,仍有疑问,因此过早地创设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以“可预见性地”弥补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的缺陷,实属可疑。此外,即使是在创设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德国,其所依赖的案例诸如“香蕉皮案”(BGH NJW 1962,31)、“蔬菜叶案”(BGHZ 66,51)等,若发生在我国,均可根据侵权责任法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之侵权责任制度作出处理,无需创设一项新的合同制度。至于创设一项新的合同制度很可能会对现有法律规范体系造成负面影响,无需赘言。
其次也不应创设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曾指出,德国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存在前提有三:其一,法律允许合同相对性原则存在例外;其二,合同法将人身或财产等固有利益作为保护对象;其三,本应获得救济的损害无法得到侵权法的保护,而需由合同法进行补救[1]。虽然上述三前提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可以得到我国合同法的支持,如《合同法》第64条和第113条,但最为重要的第三项前提在我国法律制度上并不存在。德国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产生之初,是为弥补侵权法上雇主责任无过错免责制度的缺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了用人单位的无过错责任,因此不存在类似于德国侵权法上的缺陷。此外,德国法上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难以获得侵权法的保护,根本原因仍在于其侵权法上权利和利益区分保护,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我国未对权利和利益区分加以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合同法》应否引入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关键在于现行法律制度能否有效解决第三人保护问题[2]。由于《侵权责任法》能够有效解决第三人保护问题,因此无需在合同法领域创设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另外,若创设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为受有纯粹经济损失之第三人提供合同法上的救济,无疑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事实上,即使是在创设了此种制度的德国,关于此制度的适用条件在理论上还存在较大争议。甚至有学者指出,侵权法的缺陷引发的问题应当通过侵权法的完善来解决,通过创设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解决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是不必要的②。
(二)侵权法领域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之可行性
在司法实践中,有审理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并未明确排除当事人请求赔偿纯粹经济损失的权利,此项损失可得赔偿。也有审理法院从反面进行解释,认为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损害赔偿范围,因此不可获赔。另有审理法院认为纯粹经济损失并不在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财产权益范围内,甚至有审理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关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并不在《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调整范围内,还有审理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规定赔偿直接损失,而没有规定赔偿纯粹经济损失③。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担任着侵权责任一般规定的“角色”,该款所称“财产”和“人身”既包括权利,也囊括利益[3]。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之后,其第6条第1款用“权益”一词,将权利和利益均包含在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之内。那么纯粹经济损失作为财产利益受损之一种,自然可以包含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所言“权益”范围之内。有学者明确指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除了权利外,还包括纯粹经济损失等财产利益以及其他人身性法益[4]。也有学者指出,诸如某些尚未上升为权利的精神利益和纯粹经济利益,均包含在《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法益当中[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20条也明确,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权利,也包括应当受到保护的利益。
可见,不论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民法总则》第120条,还是《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均可以作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之法律依据。将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放在侵权责任领域予以解决,至少在制度层面上不存在障碍。另外,由于无需创设一项新的制度,因此不会对既定法律规范体系造成冲击。更为重要的是,侵权责任的成立要求侵权责任各构成要件一一具备,同时并非所有的纯粹经济损失均应赔偿,因此将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纳入侵权责任领域进行处理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判断某一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而筛选其是否应获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申言之,关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排除规则的那些法政策考量因素可以内化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判断中,从而在这些法政策的指导下,考虑具体的纯粹经济损失应否获赔。
不可否认的是,《合同法》中的部分条款涉及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这些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很可能也因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依据侵权责任法获赔,但这仅仅是请求权竞合问题。根据《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可见,对于请求权竞合的情况,受害人完全可以择一行使,无需因为可能存在竞合而拒绝在侵权责任领域处理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二、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法政策考量因素
(一)法经济学的分析
在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是否予以赔偿的各种考量因素中,法经济学的思考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尚未看到有审理法院根据法经济学理论对纯粹经济损失应否获赔进行论证,但这不妨碍本文从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在法经济学的视域中,社会损失与个人损失相区分,通过比较社会损失与个人损失之大小,决定应否对个人损失进行赔偿。例如一辆汽车被毁坏,此时整个社会的损失与汽车所有人的损失相等,那么侵权行为人所应负担的损害赔偿额相当于社会损失或个人损失[6]。但在纯粹经济损失中,个人损失与社会损失大小可能不一样④,很可能出现社会损失小于个人损失的情况,此时按照个人损失额要求行为人进行赔偿,会形成一项过度的预防机制⑤,受害者应当只能在社会损失额度内请求赔偿⑥。
之所以会出现社会损失和个人损失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存在外部性[7]。在存在正外部性的情形中,虽然受害人受有纯粹经济损失,但是第三人因此受益,因此出现了社会损失小于个人损失的结果,甚至是仅有受害人受损而社会整体福利得到增加。例如施工队伍因过失挖断通往A旅店的电缆线路导致A旅店无法正常经营,此时来当地旅游的旅客不得不选择与A旅店相邻但供电未受影响的B旅店投宿。此例中,虽然A旅店经营受损,招致纯粹经济损失,但B旅店却因此接待了更多旅客,营业收入大增。这里可能存在一个“零和博弈”,即A旅店之损失等于B旅店之获益,那么此时社会损失仅为电缆毁损的损失或者是为修复该电缆线路所支出的费用,而不包括A旅店所受到的纯粹经济损失。又如由于审计师A之事务导致B公司的价值被高估,C基于对审计报告的信赖高价收购了B公司,虽然C支付了过多的收购款遭受损失,但B公司之股东却因此获利,此时并不存在明显的社会损失。
然而法经济学的分析还是难以提供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何个人损失赔偿应当受限于社会福利之最大化。以牺牲个案中对受害人的正义来支撑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付规则,值得反思[8]。必须谨记,经济学家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社会效率,这注定在作出决策时,其关注的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非分配的公平与否[9]。法律关注的是个人得其应所得。受害人若因行为人之不当行为受损,且受害人在主观上具有可责性时,仅仅以个人损失小于社会损失或不存在社会损失为由,拒绝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完全赔付,实为不妥。
(二)水闸理论的思考
水闸理论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若允许受害人可就纯粹经济损失提出赔偿,将会引致以下两点难以接受的后果:第一,由于人的社会属性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使得其中一人受到影响必波及到相邻之其他主体,若允许其中之一就其所受纯粹经济损失获赔,则很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大量之其他主体要求赔偿,“闸门”的开放将会引起诉讼的泛滥,法院不堪重负而致司法系统的瘫痪;第二,从赔偿责任人的角度观之,大量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责任无疑会给行为人带来过重负担。正如有学者所言,这样做很可能让当事人的潜在责任与过错不匹配⑦。
首先应该承认,基于诉讼泛滥的考量而排除对造成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有其合理性。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审理法院在论证具体个案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应否赔偿时,就涉及对此理论的考量。行为人过失造成交通事故,他对受害人负有责任自不必言,但他并不需要因此对受害人的雇主,或是任何与受害人签订合同的人所受到的仅仅属于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承担责任。试想,甲公司的运输车侧翻而致一条城市道路无法通行,将可能出现众多的损失类型,如:附近集市无法营业导致营业收益的损失;行人及车辆因绕路而支出的额外的交通费用及上班、谈判等迟到而丧失的经济利益;其他法人因货物运输延迟而导致货物变质的损失以及违约责任,等等。甲公司在营业时并不能预见其正常的营业行为会造成如此多的损害,要求其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不确定的经济利益承担赔偿责任将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
然而,水闸理论从来就不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依据。如果受害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确有损害,为何仅仅因为法院将承担过重的工作量和被告将承担过重的责任就拒绝为其提供救济?William L.Prosser曾指出:法律救济值得被救济者,法院因工作过多而拒绝裁判,这只能说是其本身的无能罢了[10]。况且对纯粹经济损失采取宽泛性规定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并没有遭遇诉讼泛滥的困境。且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并非意味着受害人范围和损害不能确定,如“遗嘱无效案”“商品瑕疵案”等,由此可知水闸理论并无实践经验作为支撑,对法院将会不堪讼累的担心实无必要。学者所担心的“如洪水般泛滥”的诉讼究竟确有其事,抑或只是源于一种盲目的保守主义呢?
另外,允许某些纯粹经济损失获赔并不会导致行为人承担的负担过重。在一些案件中,纯粹经济损失的受害人是确定的。如律师因过失导致遗嘱无效时,可依遗嘱继承的财产权益是可以预见的,允许此情形中的专业服务人员应当就受害人的纯粹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并非对行为人课以与其过错程度不相符的责任。即使是在其他受有纯粹经济损失之当事人范围十分广泛而难以确定的情形中,允许部分受害人请求赔偿,也不会当然地造成行为人赔偿责任过重。因为应否赔偿并不是仅以当事人是否受到损失为充分条件,受到损失仅仅是可获赔偿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要结合其他要件,才能要求行为人赔偿。其中因果关系之判断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切断纯粹经济损失的链条,缩小赔偿范围。事实上,在Sparten Steel案中,从法院作出判决之日起就不断受到批评,首先是因为法院驳回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判决依据竟然是公共政策因素而非基于任何的法律原则,其次是法官对于无休止的诉讼的担忧从未被任何事实所证明是合理的和有理由的。也正是基于此,后来在Junior Books v. Veitchi案中法官认定纯粹经济损失亦是可救济的,从而否认了Spartan Steel案的判决⑧。
(三)价值序列的考量
价值序列常常作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排除规则的一项重要因素被探讨,其主要内容为: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法律不能为所有的利益提供同等的保护,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利益的价值大小对其进行排序,对于价值更大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纯粹经济损失是期待利益的丧失,归属于无形财产利益受损之情形。对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相对于人身权益和有形财产应当更为靠后⑨。然而以上论证仍然存在缺陷,无法支撑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付这一结论。
首先,这一论证的前提是司法资源有限。虽然司法资源稀缺是无法为所有利益提供保护的原因,但也仅仅是无法保护所有利益的原因,而不是价值序列中靠后的某一具体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的原因。申言之,司法资源稀缺导致价值序列中的部分具体利益可以得到保护,而剩下的一部分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由于未能明确指出司法资源稀缺程度,因此无法界定哪一部分利益可以得到保护而另外一部分利益无法得到保护,也就无法确定纯粹经济损失情形中受损的利益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其次,既然认为纯粹经济损失中受损的利益因为在价值序列中靠后而不应得到保护,那么为何又会出现故意致损与合同法上的纯粹经济损失可得赔偿呢?从价值序列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得而知。以上解释要想站得住脚,则需明确指出司法资源稀缺的具体程度,即司法资源稀缺到仅能保护因行为人故意而受到的纯粹经济上的不利益,而没有更多系司法资源可运用于保护过失导致的纯粹经济上的不利益。
再次,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无形财产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其重要性不一定就比有形财产利益要小。例如,因侵犯商业秘密所造成的财产利益损失很可能比实体财产损失大得多。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人身利益仍比财产利益更为重要,但已经很难对有体财产损害和经济损失之重要性作出区分。
(四)行为自由的指引
在搜集到的涉及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案件中,有审理法院认为不应获赔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行为自由。“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和扩大自由”。然而,侵权法的目标就是在“权益保护”(Gueterschutz)与“行为自由”(Handlungsfreiheit)之间寻求平衡。侵权法不仅是“权利救济法”,也是“自由保障法”。通过设立侵权责任赔偿规则为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提供法律保障自不待言,但从反面来看,也是通过划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之界限,从而划清自由的界限[11]。
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之所以在侵权责任领域“不受待见”,其原因就在于纯粹经济损失之范围十分广泛且极难确定,若允许其可获赔偿,虽然于受害人而言充分保障了其权益,但是于行为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向“权益保障”的过度倾斜必将严重侵蚀“行为自由”,使得行为人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之中。这可以说是对行为自由的不合理限制,行为人为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过重赔偿责任,其行为之积极性将大打折扣。从长远来看,甚至不利于社会整体发展。
但是在某些案例中,受有纯粹经济损失之当事人范围确定,也能为行为人所能预见,因此对这些受害人进行赔偿,并不会给行为人造成过重负担。对于这类案件,由于损害结果的可预见性,行为人可提前作出相应“谋划”,若仍“一意孤行”造成对方当事人纯粹经济上不利益的,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理所当然。理性人在从事某种行为时,能够认识到行为后果的,应当为行为后果负责[12]21,这与行为自由之保护并行不悖。
对纯粹经济损失之赔付问题,若一概承认纯粹经济损失可获赔偿,必然有损侵权法保障行为自由目的之实现,而一概否认纯粹经济损失可获赔偿,势难实现个案之公平。合理的处理方法应当是在行为自由的保障、权益的保护和救济的指引下,通过侵权责任之构成要件确认具体案件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应否赔偿。
三、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控制
虽然本节是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控制进行分析,但从反面来看,也是对何种纯粹经济损失可获赔偿的确认。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控制,实际上就是提供应否赔偿的认定标准,符合标准的就应当进行赔偿,否则不予赔付。
(一)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控制路径
上文已经说明,虽然《合同法》和其他特别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就各自领域内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可为相应类型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认定提供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规定仍不能涵盖现实中已经存在以及将来可能会存在的纯粹经济损失类型。对于未能涵盖的类型,如何认定应否赔偿,则完全可以在侵权责任领域予以解决,原因就在于《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认定提供了制度通道。这里的制度通道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可为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提供请求权基础,还体现在通过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判定过滤掉不应赔偿的纯粹经济损失类型从而筛选出可得赔偿的类型。因为仅仅存在纯粹经济损失并不是要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充分条件,还应具备其他诸如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等要件,而对这些要件的判断,则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侵权责任法关于权益保护和行为自由之价值目标,甚至还应考虑社会群体共同生活之情感等,综合予以判断。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将各种价值判断、政策考量内置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判断之中,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得出最优解。
(二)纯粹经济损失赔偿控制之展开
将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纳入侵权责任领域予以处理,而对其控制自然就是围绕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展开。关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问题,理论界主要争议点在于“违法性”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而在过错、损害、因果关系应当属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议,此即“三要件”和“四要件”之争[13]。实际上对于“违法性”是否属于我国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王利明曾多次发文论证我国侵权责任法排斥了违法性要件,采纳了“三要件”说。
1.损害
若不存在任何损害,则无赔偿之必要。损害事实的存在是成立赔偿责任的首要前提,这也是为何将损害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进行规范。例如在“重庆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重庆利佰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审理法院就明确指出,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但该项损失并非必然产生,且原告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财产损失,因此不予支持。
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只有具有可赔偿性损害的纯粹经济损失才可得赔偿[14]。可赔偿性损害应当具备两个要件:第一,损害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赔偿而得到补偿;第二,通过法律上的价值判断认定该赔偿责任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认定标准又可细分为损害是行为人侵害民事权益所致,以及该损害并非过于遥远以至于不应由行为人赔偿[12]217。理论上提出的这种可赔偿性损害的判断,实际上已经对损害应否由行为人赔偿作出了认定,即认定行为人应否承担赔偿的侵权责任,有“越俎代庖”之嫌。其中关于损害是否由行为人所致的判断属于因果关系认定的范畴,损害是否过于遥远的判断也和因果关系或主观过错的认定有关。因此,对于损害这一要件的认定,仅需判断是否存在损害事实即可,至于是否具有可赔偿性,则属于其他构成要件所要解决的问题。
2.过错
行动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15]。过错责任原则基本是所有国家涉及侵权法的基本归责原则,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826条[16];《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第1383条[17];《意大利民法典》第2043条[18];《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295条[19];《瑞士债务法》第41条[20];《日本民法典》第709条[21]。过错责任原则也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归责原则。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认定,自然应以过错为归责原则。首先,法律没有就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责任作出规定,也就谈不上将其规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次,纯粹经济损失是否赔付尚存在争议,将其规定为无过错责任更是难以让人接受。
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在纯粹经济损失情形中,若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其行为的可责性或非难性十分明显,要求故意之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毋庸置疑。例如在“刘军发与刘六妹、谭月华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审理法院明确指出,被上诉人明知毁损、阻碍公路的行为会给上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仍通过挖断、阻塞公路的行为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实属故意,应当赔偿给上诉人造成的养猪未成的纯粹经济损失。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是否有必要将行为人主观过错限定在故意范围内,以实现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进行控制的目的。实际上,行为人主观为过失的,在某些纯粹经济损失案件中仍应承担责任。这是因为,行为人有过失,其对他人权益的维护未能尽到相当的注意义务,未能对损害的避免采取合理措施,包括“为”或“不为”的一定行为,这种主观状态本身就有一定的可责性,尽管不如主观上为故意的可责性严重。此外,从各国司法实践的案件裁判情况来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认可。例如德国的修理行煤气表安装爆炸事故案、英国的White v. Jones遗嘱继承案以及我国的王保富诉三信律师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某些纯粹经济损失类型,行为人在主观上为过失的要承担赔偿责任,但另一些纯粹经济损失类型,行为人只有主观上为故意的,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第三人侵害债权导致的纯粹经济损失。至于哪些情形中应当要求行为人主观为故意,而哪些情形中过失即可,需要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就上文已经讨论的几种类型而言,过失履行专业服务、不当陈述、商品或建筑物瑕疵引起的纯粹经济损失、侵害第三人所有权或人身所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行为人主观上为过失即可。而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恶意诉讼、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则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公共资源利用不能和公共交通拥堵和延误类则需要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因为在专业服务、不当陈述和商品或建筑物瑕疵引起的纯粹经济损失中,法律已经对专业服务人员(如律师和会计师)、陈述义务人(如上市公司和新闻从业人员)、提供商品或交付建筑物之主体(如生产者和开发商),等等,明确规定了审慎义务、注意义务或保障商品无瑕疵之义务,行为人违反此义务的,即使主观上属于过失,仍应承担相应责任。而侵害第三人所有权或人身权造成纯粹经济损失的,盖因所有权和人身权本属绝对权,对其侵害即使为过失的也应担责,由此引发的纯粹经济损失,同样应当赔偿。但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恶意诉讼、第三人侵害债权中,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恶意诉讼本就是行为人主观上积极追求的结果,不存在过失的情形。
3.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仍然是行为人只对自己行为负责原则的要求。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解决的是可归因的损害赔偿问题,行为人对某一损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与损害之间存在联系[22]。侵权责任法中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两层意义:第一,过滤掉无关原因,贯彻自己责任原则;其二,截取因果关系链条,避免责任范围的无限扩大[12]220-221。
在我国,学者一般主张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23]。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法官在裁判时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进行认定[24]。在纯粹经济损失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中,同样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因为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包含两层意思,即“条件关系”的判断和“相当性”的判断,而“相当性”的判断是融入了政策考量的价值判断[25],因而具有了法律上的归责和责任限制的功能[26],从而实现纯粹经济损失赔偿中的权益保障和行为自由的平衡。
相当因果关系中的“条件关系”是指行为人之行为是损害结果的必要条件。“相当性”是指该行为通常足以导致该损害[27]。如何判断通常足以导致该损害,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其一是立法目的和法律政策,其二是过错[28]。在纯粹经济损失领域,由于侵权责任法并未专门对此予以规定,仅能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进行处理,因此从立法目的来看,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是权益保障,从法律政策的角度观之,则要考虑权益保障和行为自由的平衡。不可否认,此处提到的“考虑权益保障和行为自由的平衡”仍然“捉摸不定”,如何在裁判过程中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追求,有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一般来讲,可以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全面的权益保障自然是有损失即赔偿,但是这在现代社会是难以实现的,并且会阻碍社会进步,因此不予保障则是要求受害人承担一定之社会风险和生活成本。这就需要法官考虑将这种风险和成本划归给哪方当事人承担更为合适。其次,行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是否能够享有行为自决权,即能否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以及法律是否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从而在决定是否为某一行为前能够预先谋划。因此法官在认定相当因果关系时,可以从可预见性角度进行判断。例如在“陈丽丹诉周学刚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原告请求赔偿因交通事故导致其无法参加旅游而产生的旅游费用损失,并提供了旅游合同和发票进行证明,审理法院认为该旅游费用损失属于纯粹经济损失,由于该项损失无法预见,应予以限制,因此不予支持。
可预见性的判断标准有三种:①主观标准是依据行为人所知道的情事进行判断;②客观标准是依据一个合理人在事发之时所能认知的情事进行判断;③综合标准则是同时考虑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以上三种标准中,综合标准更为可取。第一,客观标准反映的是一般社会大众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所以据此作出的认定结果也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预期。第二,由于行为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具有的特殊性,其所知之情事对于行为结果可预见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专业人员从事专业服务时,其预见能力自然强于普通人,同时基于其专业技能,对其行为之要求自然也高于普通人。
四、结语
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并非简单的全有或全无的问题,而是根据一定之规则对其进行具体认定和控制。关于纯粹经济损失应否赔付在理论上所探讨的各种法政策考量因素,应当内化于这一规则当中,其中又以实现权益保护和行为自由之平衡为核心。认定和控制规则应围绕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展开,即从损害、过错和因果关系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标准,对“相当性”的认定,应根据行为人对损害的可预见性进行判断。
上述判断标准仍具有抽象性,这是因为经济联系的复杂性使得纯粹经济损失的形态各异,难以通过精确唯一的标准囊括千变万化的现实。为了给可能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预留必要的救济空间,同时不对行为自由构成不合理的限制,提供具有一定弹性和灵活性的规范模式和认定标准似乎才最为妥当。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在法政策考量因素的指引下,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作出价值判断,从而作出是否赔偿的判决。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不断充实这一抽象性的同时也具有弹性的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认定标准。学者根据实践中存在的纯粹经济损失事实模式,结合法官的判决,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问题进一步做理论上的探究,从另一个侧面对损失赔偿认定标准填充实质性内容。二者协力推动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规范的发展。正如毛罗·布萨尼等所言,侵权法不断展现其受解释的命运,即展现一种解释性的存在方式。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问题也逃脱不出这种命运[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