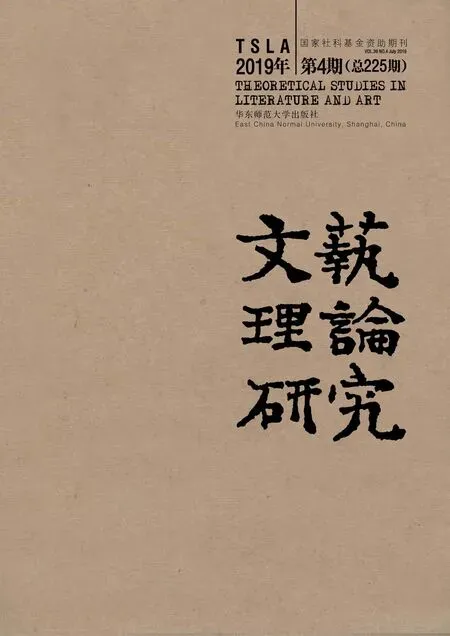从“像”到拟像 : 德里达论书写
董树宝
在解构主义中,书写(écriture)是德里达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与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的起点,也是他对“像”(image)、拟像与幻像、摹仿与再现进行研究的出发点,由之构成了与“解构”“延异”“替补”“痕迹”相互交织、相互辉映的解构主义,为我们研究和阐发“像”“拟像”提供了极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综观德里达的“像”论,他的早期著作《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
énom
ène
, 1967年)《书写与差异》(L
’écriture
et
la
diff
érence
, 1967年)和《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 1967年)集中阐述了西方思想自柏拉图以来的言语与书写的关系,其中《论文字学》主要以“柏拉图-卢梭-索绪尔”为主线批判了书写是古典意义上的言语之“像”(影像)的观念,呈现了一种鲜明的反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药》(Le
pharmacie
de
Platon
, 1968年)可以视作德里达实施解构主义批评策略的最佳范例,他不断变换着阐释视角,从不同的层面阐释了pharmakon,由此从宽泛意义上的“像”转向了拟像,打开了柏拉图尘封已久的文本空间,演绎了书写、药与拟像之间纵横交错、彼此延异的复杂关系,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拟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维度。一、 言语、“像”与书写

Cours
99;《普通语言学教程》102)。在此能指是指声音的影像,或者声音的能指是言语的影像,而作为视觉性的能指,书写(或文字)是声音的能指,是“能指的能指”,书写不过是言语的“形象表达”(figuration)。这种将书写归之于语言系统外部的构想也为书写的“僭越”埋下了祸端,书写不断地敲击着心灵的门扉,实施着破门而入的暴力。索绪尔强烈地感受到了卢梭提出的“书写僭越”问题,他不得不对书写进行谴责 :“首先,语词的书写影像犹如持久、稳固的对象一样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印象,它比声音更适合通过时间来构建语言的统一性。这种关系徒然是表面的,徒然制造了纯粹虚假的统一性;它远比声音的唯一真正的自然关系更容易把握”(Cours
46;《普通语言学教程》50)。书写作为言语之“像”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虽然被索绪尔谴责为“表面的”“虚假的”,但人们更偏爱明晰可见的、持久稳定的书写,也容易接受和把握作为不可见的言语或语音之“像”的、可见的文字或书写,由之书写篡夺了主导地位,言语或声音的价值和地位遭到了贬低。“在大多数个体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声音印象更清晰和更持久,因此他们更偏爱前者。最终书写影像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Cours
46—47;《普通语言学教程》50)显然索绪尔正是在“像”的维度上洞察到书写的篡权,洞察到书写的主导性地位,这致使书写与言语或声音的关系错综复杂,令人难以容忍,而又令人痴迷不已。“难以容忍而又引人入胜的恰恰是‘像’与事物、字符与声音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亲密,以至于通过反映、转换与倒置的效果,言语似乎反过来成了‘最终篡夺主导地位’的书写的窥镜。再现与其所再现的东西相互交织,以至于人们说话时就像书写一样,人们思考时,被再现的东西仿佛不过是再现物的影子或映像而已[……]映像、像、复影将其再复影的东西一分为二。思辨的本原变成了差异。能被反观的东西不是一,而且本原与其再现、事物与其影像的相加律就是一加一至少等于三。不过把‘像’置于现实控制之下的历史性僭越与理论性怪事被规定为对单一本原的遗忘。”(De
la
grammatologie
54—55;《论文字学》49—50)在这段论述中,文字或书写与言语或声音的关系通过映像、复影或影子的运动变化发生了逆转,两者在人类学习语言的自然关系中被颠倒了,“像”与物、本原与再现的关系也解体了本原的同一性,某种差异性的东西悄然而生。卢梭和索绪尔都承认这一点,卢梭和索绪尔谴责了人们被可见的文字或书写搞得眼花缭乱,被这种可见物冲昏了头脑,颠倒了意义通过书写向心灵呈现的自然性、原始性和直接性,使无意识的心灵突然遭遇了书写的暴力。本来一个人在学会写之前先学会说,也就是言语或声音先于文字或书写,但是文字或书写之于言语或声音的暴力却颠倒了这种自然关系,导致了对“影像-文字”(lettre-image)的反常崇拜,在索绪尔看来,这种对文字的迷信是一种偶像崇拜(idolatrie)的罪恶,导致了某种自然的偏离。不过,德里达不同意索绪尔的这种情绪化判断,他试图运用解构主义策略对这一点进行阐释 :“因此,解构这一传统并不在于颠倒书写的暴力,也不在于宣布书写无罪,而是在于表明书写的暴力为什么没有降临到无辜语言的头上。之所以存在书写的原始暴力,乃因为语言首先就是书写,并且这一点日益明显。‘僭越’早已开始。正当性的意义出现在轮回的神话效果之中。”(De
la
grammatologie
55;《论文字学》50)德里达通过不断地“清淤”与“解构”,发现索绪尔及其后继者错失了“语言学的完整的具体对象”(Cours
23;De
la
grammatologie
64;《论文字学》60)——书写,导致书写四处流浪、漂泊不定,之所以书写会出现这样的窘况,乃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导致的结果。“与表音-拼音文字相联系的语言系统是产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系统,而这种形而上学将存在的意义确定为在场。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充分言说的时代,始终给对文字的起源与地位的所有自由思考,给整个文字学加上括号,对它们存而不论,并因为一些根本原因对它们进行抑制,但文字学并非本身有赖于神话学和自然书写的隐喻的技术和技术史。”(De
la
grammatologie
64;《论文字学》59—60)逻各斯中心主义悬置了对文字或书写的起源与地位的自由思考,致使文字或书写遭到抑制与排斥,致使文字或书写成为言语或语音的影像或再现,成为那徘徊在语言学周围的漂泊者。“然而,将书写作为‘外在系统’排除在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书写要落在‘影像’‘再现’或‘形象表达’、语言实在的外在反映上。”(De
la
grammatologie
66;《论文字学》62)德里达认为从柏拉图至索绪尔的“书写是言语之像”(《斐德罗篇》276a)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于书写既不是言语的影像或记号,书写既不外在于言语,也不内在于言语,且言语本身也已经是书写,或者说一切人为的痕迹都是书写,由之德里达改变了书写与言语的自然关系,使书写进入了差异的游戏。二、 延异、拟像与替补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是自相矛盾的,存在着前后不一致性。一方面,他承继了柏拉图以来的语言理论,肯定了言语或语音之于文字或书写的优先地位与支配地位,由此肯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他认为,出于必要的和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理由,必须赋予言语以及维系符号和声音的一切联结物以特权。他也谈到思想和话语、意义与声音之间的‘自然联系’。他甚至谈到了‘思想-声音’。”(德里达,《多重立场》25)另一方面,索绪尔却肯定了符号的差异性原则,将语言界定为差异的符号系统。“语言中只有差异[……]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优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异和声音差异[……]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异和一系列观念差异。”(Cours
166;《普通语言学教程》167)概念和意义也只是符号的差异本身所产生的效果,并不诉诸语言之外的对象,这意味着书写不再是言语的影像,在场形而上学由之遭到否定。“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激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方面它堪称是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另一方面,它又毫不含糊地肯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间。德里达因此阐释了索绪尔的话语怎样解构了自身。但是他没有为此诋毁《教程》,相反,这一点不容忽视,《教程》的自我解构运动是其力度和韧度的根本所在。文本的价值和力量,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赖于它怎样解构同它相应的哲学。”(卡勒84)乔纳森·卡勒回应了不少研究者对德里达的质疑和“诋毁”,肯定了德里达正是基于《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解构运动所进行的阅读和阐释,从中发现文本自身的价值和力量,由此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强调了声音的差异,更准确的说是“音响影像”与“音响影像”之间的差异,他指出语言的能指“本质上决不是声音的,它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实体,而完全由把它的音响影像与其他音响影像分开的差异构成”(Cours
164;《普通语言学教程》165)。这一区分对索绪尔而言至关重要,但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一点是,“这种情况在另一个符号系统——文字——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拿来比较,借以阐明这整个问题”(Cours
164;《普通语言学教程》165),索绪尔已经将这种差异原则应用到了文字或书写,从整体上提出了“语言中只有差异”(Cours
166;《普通语言学教程》167)的观点。这一观点对德里达而言至关重要,《普通语言学教程》本身蕴含着自身解构的要素,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差异的游戏,德里达从中洞察到这种差异游戏,将这种差异原则彻底化,这成为他的“延异”(différance)思想的重要依据。德里达从《声音与现象》就开始探讨书写与“延异”的关系,逐渐发展出“痕迹”“替补”(supplément)“间隔”(spacing)“原书写”(arch-écriture)等“概念”(德里达,《声音与现象》85、104),从而将索绪尔的静态的“差异”变成了动态的“延异”。différance是德里达生造的一个词,读音在法语中与差异(différence)相同,但书写形式不同,这种以字母a取代e的书写形式显然不能通过声音来区分,沉默的a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含义,它是字母表的第一字母,象征着原初的和绝对的起源,它的大写字母A在视觉上像金字塔,象征暴君的死亡,开启了索绪尔所说的差异游戏。“索绪尔不得不召回的差异游戏,是任何符号的功能和可能性的条件,它本身是沉默的。恰恰两个音素之间的差异令人难以听见,这种差异仅仅容许它们如其所是地存在和运作。”(Derrida,Marges
5)différance的这种“音”同形“异”隐含着德里达对言语与书写的传统关系的质疑,隐含着书写之于差异的重要意义。虽然德里达赋予“延异”以丰富内涵,但“延异”具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 延迟与差异,也就是différance和différence的词源différer一词的双重含义,德里达从différer的现在分词différant借用了a,“延异中的a直接源于différer的现在分词différant”(Marges
8),因此也隐含了某种动态性。“这样一来,德里达就有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自柏拉图到黑格尔、海德格尔和索绪尔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同一与差异的关系的认识[……]德里达用différance来表示差异的动态性、过程性对改造传统形而上学具有革命性意义。”(汪堂家48)在德里达看来,延异是差异的根源,差异是延异的结果,是延迟着的差异,是正要到来的、正在发生着的差异。延异没有起源,不可定义,它完全超越了“什么是différance?”的问题模式,但德里达认为他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运用延异的词汇家族成员来描述différance的特征,这些成员有痕迹、替补、间隔、原-书写、原-痕迹等。“痕迹”与延异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德里达看来,没有痕迹就没有差异发挥作用,意义也就不会呈现,纯粹的痕迹就是延异,是感性丰富性的条件(De
la
grammatologie
2;《论文字学》89)。痕迹是指消逝了的东西所留下来的东西,可以是符号、文字、书写、踪迹,也可以指广义的声音。在延异的链条上,某种消逝的东西总是要留下痕迹,它本身也会被后继者“涂擦”,又会留下一道道痕迹,这种差异性的纯粹运动总是通过纯粹的延异得以持续。“在要素或系统之中,没有任何纯粹的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痕迹的痕迹遍布各处[……]延异是差异的系统游戏,是差异的痕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各种要素才发生了关系。”(Derrida,Positi
-ons
38;《多重立场》31)这种差异的游戏、差异的痕迹的游戏又被德里达称之为“原-书写”,痕迹更加古老、更具本源性,痕迹实际上是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本原(origine),是展示显像与意指活动的延异,也使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念陷入困境。“对痕迹的思考告诉我们,它不可能仅仅从属于关于本质的存在-现象学问题。痕迹就是虚无,它不是‘在者’(étant),超越了‘是什么’的问题,并且使之成为可能。人们可能再也不会相信原则与事实的对立,但这种对立一直是各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和先验的形式在‘是什么’的问题系统中发挥作用。”(De
la
grammatologie
110;《论文字学》107)在德里达看来,痕迹演绎着差异的游戏,呈现出差异的延异,而痕迹在显现差异的游戏时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席,痕迹最终成了在场的拟像。“痕迹由于不是在场,而是自身脱位、自身移位、自身指涉的在场的拟像,它本来就没有场所,涂擦属于痕迹的结构[……]这种结构性的悖论,以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产生如下效果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的颠倒 : 现在变成符号的符号、痕迹的痕迹。它不再是任何指涉在上一次诉求中所指涉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在普遍化的机构中的功能。它是痕迹,而且是痕迹的涂擦的痕迹。”(Marges
25)
三、 书写、药与拟像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基于“柏拉图-卢梭-索绪尔”的主线批驳了柏拉图以来的“书写是言语之像(image)”的观念,然而到了《柏拉图的药》,德里达对书写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书写不仅可以作为药,兼具“良药”与“毒药”之功能,而且书写开始作为“拟像”发挥作用。德里达以精妙独到的解构主义解读策略对parmakon的不同翻译进行层层剖析,他认为法语用remédie(良药)、poison(毒药)、drogue(药剂)、philtre(媚药或魔药)都无法传达pharmakon的丰富内涵,他通过分析《蒂迈欧篇》《斐德罗篇》《斐莱布篇》和《普罗泰戈拉篇》等对话来对作为pharmakon的书写进行区分,从善与恶、真与假、内与外、本质与表象等对立价值评价好的书写和坏的书写。尤其在《斐德罗篇》关于书写与言语的关系上,他批评了“书写是言语之‘像’(image)”的译法,赞成“书写是言语的拟像(simulacre)”的译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德里达对书写的问题从宽泛的“像”转向了拟像,书写与拟像在差异的运动中呈现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策略。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叙述了一则文字神话 : 文字之神Theuth向埃及国王Thamous展示他的各项发明,谈及文字时,Theuth说 :“大王,这项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 :“多才多艺的Theuth,能发明一种技术的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的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给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因为借助文字,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像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明智。”(《斐德罗篇》274c—275b;《文艺对话集》168—69)在这则神话中,文字作为礼物献给国王,国王的评判决定了文字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借助国王之口来攻击书写的含混效果 : 表面上,通过文字进行的书写似乎有助于记忆,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学到更多的知识,实际上,通过文字的书写却助长了人们健忘的恶习,不利于人们掌握真理。首先,从国王Thamous与Theuth的功能来看,国王是言语之神,是众神之王,他通过言说来创造世界,从不进行书写,因而书写毫无必要;而Theuth是书写之神,是附属之神,他希望通过书写来助人记忆,促人认识真理,因而书写有益于真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关系不就如同国王Thamous与Theuth的关系一样吗?苏格拉底是个述而不作的人,尼采曾言 :“苏格拉底,这个从不写作的人。”(《论文字学》7)而他的弟子柏拉图则是苏格拉底的记录者或“传声筒”,终生以记录恩师的言行为荣。Theuth把文字或书写比作灵丹妙药,有助于人的记忆;而国王却认为其效果适得其反,只会导致记忆力衰退,这两者的观点不就是pharmakon的含混效果吗?两种性质相反的功效置入同一个词中,呈现出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其次,从国王Thamus与Theuth的关系来看,国王就像父亲一样发挥作用,作为pharmakon的文字或书写呈献给父亲,惨遭父亲拒绝、贬斥,由之柏拉图主义的模式就在于把言语(逻各斯)的起源和权力分配给父亲的位置,与整个在场的形而上学密切相关,一旦失去了父亲,逻各斯也只不过是书写,因而书写与父亲的缺席息息相关,处于一种弃儿的地位,活生生的逻各斯与僵死的文字书写形成了鲜明对比。
通过谱系学的方法,德里达追溯文字神话的起源,发现这一神话与埃及、巴比伦、亚述的神话具有相似的结构,尤其在古埃及神话中,Theuth对应着图提(Thot),Thamous对应着太阳神阿蒙拉(Amon-Rê),两者存在着一种父子关系。阿蒙拉是万物之父,通过言说创造世界万物,他是一个“隐匿者”(le caché),是一个被隐匿的太阳。图提是阿蒙拉的长子,是神的代言人,他是一个被孕育的神,是一个反射太阳光辉的月亮。因而阿蒙拉与图提的关系隐含着彼此对立的二元结构 : 言语与书写、生命与死亡、父亲与儿子、主人与仆从、灵魂与身体、内与外、善与恶、严肃与游戏、白昼与黑夜、太阳与月亮等,意味着一种主从的附属关系。作为次级语言的神,图提把差异引入了语言,“他只有通过换喻性替代、历史性移位以及偶尔为之的暴力性颠覆才能变成创造性言语的神”(Derrida,La
diss
émination
100),德里达认为这一点如同《斐莱布篇》所描述的Theuth一样,他实际上是被诉诸于差异的作者,也就是语言中进行差分化的作者,也是将无限多样性引入语言的作者(《斐莱布篇》18b-c)。“这种替代就这样使图提取代了阿蒙拉,就如同月亮取代了太阳。书写神也由此变成了阿蒙拉的替补者,他在阿蒙拉缺席和基本上消失的时候补充和替代阿蒙拉。这就是月亮作为太阳的替补的起源,是黑暗之光作为白昼之光的替补的起源。书写,作为言语的替补。”(La
dissemination
100-101)作为阿蒙拉的替代者,图提就像反射太阳光的月亮一样,自身不发光,这种替补就像一种“痕迹“和“替补”的纯粹游戏一样运作,由之图提又悄然引入了重复,他变成了亡灵的记录者和复活神,他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更关注作为生命之重复的死亡与作为死亡之重复的生命、生命的复苏与死亡的重启,图提正是在这种替补的过程中重复一切,因此书写神也是医药神,他在“同”与“异”的游戏中进行替代行动,成为pharmakon的含混性呈现。因此,书写无论好坏,本身都不具有本质或价值,因为言语关系着生命、记忆、知识与真理,真理的运动意味着记忆逐渐展开,促使生命去认识真理;而书写连接着死亡、遗忘、无知与非真理,书写的展开意味着遗忘力量逐渐增加,扩大了死亡、无知与非真理的领域。书写在拟像(simulacre)中进行游戏,以痕迹来摹仿记忆、知识、真理等,因而书写的人在神看来不是有智慧的人(sophoi),而是伪装的或自吹自擂的智术师(doxosophoi),由此把哲人与智术师或者说把苏格拉底与吕西亚斯区分开来,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人是述而不作的言说者,以吕西亚斯为代表的智术师是伪装的书写者。这正是柏拉图从书写的角度对智术师们提出了控诉,“依赖书写的人吹嘘着书写向他提供保证的权力和知识,这个被Thamous揭穿的拟仿者(simulateur)具有智术师的全部特征 : 《智者篇》(268c)所说的‘有智慧的人的摹仿者’。”(La
dissemina
-tion
120)书写的人就像智术师们的孪生兄弟,从事着类似的活动 : 智术师们貌似多才多艺,卖弄着所谓的“真知灼见”,他们炫耀的不是记忆本身(mnèmè),而是档案、复制品、引文、笔记、传说、故事、族谱之类的遗迹(hypomnémata),是众多的回忆录,他们以此来满足贵族青年们的需求,赢得欢呼。智术师们假装知道一切,他们的“博学”也不过是假象而已,实际上他们远离了记忆与真理,走向了拟像世界。书写亦是如此,助长了记忆力衰退,而非是有生命的记忆,与知识、真理和辩证法相异。书写类似智术师们玩弄的把戏,是对知识和真理的摹仿。“这种语言的技艺是由追随信念的人,而不是由知道真理的人来展现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可笑的技艺,或者说它实际上根本不是技艺。”(《斐德罗篇》262c)德里达通过在书写、拟像与智术师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似关系来阐释书写的拟像性特点,当然他意不在“回归智术师”(retour-aux-sophistes),他也从智术师与哲人、诡辩学派与柏拉图主义的对立中洞察到智术师们也曾劝告世人要运用记忆,而不是依赖书写,苏格拉底盗用了智术师们的论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来攻击智术师们,在真理与书写之间竖起了柏拉图主义的层层围墙。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借用了智术师Isocrate或Alcidamas的论证来反对书写,攻击作为拟仿者的智者学派,为了恢复他们所摹仿的真理,柏拉图也拟仿这些摹仿者。“辩证学者实际上如何拟仿他谴责为拟仿者、拟像之人的人?一方面,智术师们像柏拉图一样劝告运用记忆。不过,如前所述,这是为了能够无知地进行言说、为了无判断地进行吟诵,无须担心真理,只是为了提供符号。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兜售它们。通过这种符号的经济,智术师们在他们自我辩护时就是书写的人。”(La
dissemination
128)在柏拉图看来,智术师们就像诵诗人伊安一样无知地进行言说,对他吟诵的《荷马史诗》毫无判断,他可以凭着他的吟诵技艺获得比赛头奖,但他只是提供语言符号,对真理和灵魂没有兴趣。智术师们以生动的修辞和活生生的言语感染听众和打动听众,柏拉图批评他们以花言巧语蛊惑青年,其实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笔下就是这样一幅智术师的形象,就是一名被指控蛊惑青年最终被判喝毒药而亡的“巫师”(pharmakeus);智术师们是进行书写的人,他们兜售符号,获得钱财,赢得尊敬;柏拉图虽然从事诱捕智术师的工作,但他实际上拟仿了智术师,他通过书写记录恩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必然要通过书写来唤起对善和真理的回忆。因而,德里达认为有两种pharmakon : 哲人的pharmakon,关系着理念、真理、辩证法和哲学,与之相对立的是智术师的pharmakon和对死亡的恐惧,由之pharmakon没有固定的本质和属性,也不具有同一性,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如若pharmakon是‘模棱两可的’,那恰恰为了构建对立项相互对立的中间地带,构建使彼此相互关联、相互颠倒、相互融入的运动和游戏(灵魂/身体、善/恶、内/外、记忆/遗忘、言语/书写等)。正是从这一游戏或运动,对立者或差异物才被柏拉图终止。pharmakon是差异的运动、场所和游戏(产物)。它是差异(différence)的延异(différance)。它在难以辨别的阴影和前夜中坚持保留着区别要切分开的差异物与不和。”(145—46)作为pharmakon的书写穿梭于柏拉图主义的二元对立之间,开启了相互关联、相互颠覆、相互逆转、相互游戏的差异运动,是差异的延异。
苏格拉底 : 此外是否还有另一种文章,和上述那种文章是兄弟而却是嫡出的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生出来的,以及它在本质和效力两方面比上述那种要强多少。
斐德罗 : 你说的是哪种文章?依你看,它是怎样生出来的?
苏格拉底 : 我说的是现在学习者心灵中的那种有理解的文章,它是有力保卫自己的,而且知道哪时益于说话,哪时益于缄默。

苏格拉底 : 对极了,我说的就是那种。(《斐德罗篇》 276a)
综上所述,书写在德里达的早期哲学中蕴含着一种从“像”到拟像的演变进程,他运用解构主义策略批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尤其他基于“柏拉图-卢梭-索绪尔”的主线批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书写是言语之像(image)”的观念,改变了书写与言语的自然关系,使书写在拟像中进行着差异的游戏,呈现出了鲜明的反柏拉图主义。不仅如此,德里达运用解构主义策略对作为pharmakon的书写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书写开始作为拟像发挥作用,最终书写变成漂泊不定的弃儿,书写也只不过是拟像而已,就像鬼魂一样飘忽不定,这为德里达的幽灵学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我们研究拟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注释[Notes]
① 在法语中,écriture含义较为丰富,既指“文字”,又指“书写”或“写作”,还有“笔迹”或“字迹”等含义,德里达显然是在这些含义的交叉维度上使用这一词汇,赋予这个词更加丰富的含义,不仅指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而且指与“文字”有关的书写。从《论文字学》开始,“文字”开始转化为“书写”(或写作),德里达开始探讨卢梭、马拉美和索莱尔斯的写作,还有各种非文学的书写,因而他的“文字学”应该译为“文字书写学”或“文迹学”更为合适,即包含着一切与“文字”有关或无关的书写,包括文学、哲学,也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关于这一点,汪堂家先生曾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德里达的用词策略 :“《论文字学》中的‘文字’则要从古典意义上理解,即,既把它理解为刻划痕迹的活动又把它理解为刻划下来的痕迹。《书写与差异》中‘书写’(l’écriture)既指‘写’,又指‘写下来的东西’;而‘差异’一词的原文(différence)既可表示‘差异’又可表示‘显示差异的活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区分。”(《汪堂家》25)朱刚也指出 :“écriture在法文中同时有‘文字、书写’两种意思,而德里达对该词的使用也恰恰是交替利用这两种意思。这两种意思很难单独在‘文字’或‘书写’中得到表达[……]它也有动作性的‘书写’之意。”(《文字与本原》218)另外,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首先是一种文本解读策略,他选取各种适合他进行“解构”的文本进行解读,之所以如此,与他对作为一种特殊书写的文学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一次访谈中,德里达曾指出 :“更确切地说是 : 书写是如何变成文学写作的?书写中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文学?”(《解构之旅》29)因而,écriture在德里达的哲学中有一个持续的意义增殖过程,“书写”一词的中文内涵更能含纳écriture的“文字”“笔迹”与“写作”等语义,由此écriture在本文主要译为“书写”,有时会根据具体语境译为“文字”“文字”或“书写”“写作”。

Tel
Quel
)杂志,后收入1972年出版的《播撒》。从其创作时间上,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的药》应该是对《文字学》中未竟的柏拉图主义进行深入阐述。④ 另参见《文艺对话集》 :“你说的是哲人的文章,既有生命,又有灵魂。而文字不过是它的影象,是不是?”(171);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二卷) :“你指的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话语,它是更加本原的,而书面文字只不过是它的影像”(199)。需要注意的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主要从“像”(image)的角度来阐述书写是言语之“像”,不过,到了《柏拉图的药》,他开始从拟像(simulacre)来谈论书写与言语的关系,这可能与他参照的《斐德罗篇》的法译本有直接关系,也与他对书写、言语与拟像关系的重新定位有关。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乔纳森·卡勒 : 《论解构》,陆扬译。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Culler, Jonathan.On
Deconstruction
. Trans. Lu Yang. Beijing :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Derrida, Jacques.De
la
grammatologie
.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7.- - -.La
dissemination
. Paris : Seuil, 1972.- -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雅克·德里达 : 《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 - -.Of
Grammatology
. Trans. Wang Tangjia. Shanghai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 -.Positions
.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 《多重立场》,佘碧平译。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 - -.Positions
. Trans. She Biping. Beijing :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04年。
[- - -.Speech
and
Phenomena
. Trans. Du Xiaozhen. Beijing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柏拉图 : 《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Plato.Literary
Dialogues
.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3.]—— : “斐德罗篇”,《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03年。
[- - -. “Phaedrus.”The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 Trans. Wang Xiaochao. Vol.2.Beijing :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斐莱布篇”,《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03年。
[- - -. “Philebus.”The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 Vol.3.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智者篇”,《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03年。
[- - -. “Sophist.”The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 Vol.3.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80年。
[Saussure, Ferdinand 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 Trans. Gao Mingkai. Beijing :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Cours
de
linguistique
g
én
érale
. Paris : Payot, 1983.汪堂家 : 《汪堂家讲德里达》。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Wang, Tangjia.Wang
Tangjia
’s
Lectures
on
Derrida
. Beijing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张宁 : 《解构之旅·中国印记——德里达专集》。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Zhang, Ning.A
Journey
of
Deconstruction
and
the
Impression
of
China
:A
Monograph
on
Derrida
. Nanjing :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朱刚 : 《文字与本原》。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Zhu, Gang.Language
and
the
Origin
. Shanghai :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