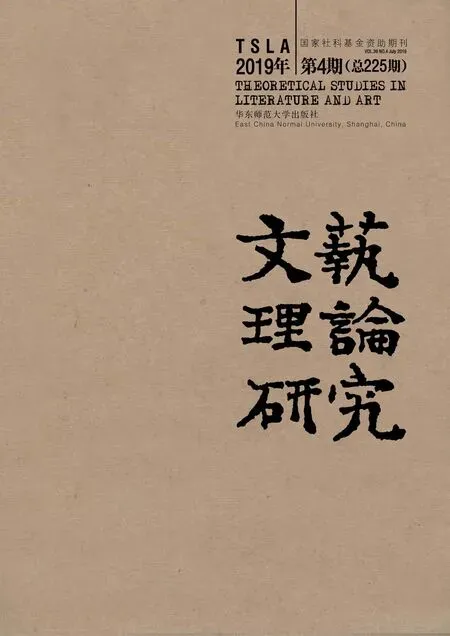从中性到他人 : 列维纳斯论布朗肖
王嘉军
列维纳斯的《论布朗肖》一书出版于1976年,该书最集中地表达了列维纳斯对他的世纪好友布朗肖及其作品和思想的评价,是我们研究二者思想关系的最佳入口。这本书实际上是由四个文本组成的,其中三个文本分别是列维纳斯对布朗肖的作品《文学空间》《等待,遗忘》和《白日的疯狂》的评论,另一个文本则是列维纳斯与安德烈·达尔玛(André Dalmas)1971年在《文学半月刊》上关于布朗肖的访谈。这四个文本分别发表于不同的媒体中,时间跨度将近20年,且除了与达尔玛的访谈算是综述性质之外,其它作品评论的都是布朗肖不同的文本。因此,尽管在列维纳斯对于布朗肖的评论中贯穿的总体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在诸文本之间也有诸多微妙的差异,而这恰是最值得注意的。
一、 文学空间与外部书写
《文学空间》写作于1955年,是布朗肖最重要的文学评论集之一,列维纳斯可谓这本书最早的评论者,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其评论文章《诗人的凝视》便发表了。列维纳斯首先指出了布朗肖的文学和思想所归属的历史语境,这是一种在诸神缺席之后兴起的无神论和非人主义。列维纳斯指出,在这一空间之中,诸神的缺席反倒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在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一种奇怪的虚无,它不保持静止而是‘虚无化’着”。列维纳斯同时也指出了布朗肖的文学理论所传承的思想谱系 : 黑格尔和晚期海德格尔,其中黑格尔是显性的,在布朗肖对于文学的运思中蕴含着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这尤其体现于白日和黑夜的划分及对二者关系的分析中,尽管布朗肖最终的目的恰恰是要打破这种辩证法之综合化的运作。在布朗肖那里,白日是那个黑格尔式地归属于政治、理性、权力和行动之调控和运作的世界,而黑夜则是对这一世界的排除,艺术正处在这一黑夜之中。晚期海德格尔对于艺术起源的思考,则隐性地影响了布朗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思索和定位。然而,在列维纳斯看来,不管是黑格尔的历史,还是海德格尔的世界,都暗含了一种总体化的暴力,因为它们把所有陌异之物都纳入了一种同一化的视域之中,陌异之物就此也就丧失了其陌异性,而这已经暗含了一种自我之主权和权力的运作。这样一来,如何让他者(l’Autre)“无权力的出显”(Lévinas,Sur
Maurice
Blanchot
14)对于布朗肖来说,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列维纳斯认为,对于布朗肖而言,这样一种出显的方式不能通过思想而实现,因为思想的运作本身就是同一化的,是一种把一切内部化的运作。因此,无权力的出显只能在“外部”实现,“它的存在方式,它的特质,就是由呈现而不被给予构成的,就是由不把自身交给权力构成的”(Sur
Maurice
Blanchot
14)。如此,这种出显和外部对于遵循权力之逻辑的思想和世界来说,就成了一种不可能之物。“外部”是布朗肖的标志性概念,不过对于这个概念,其实,列维纳斯早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就提出了。在该书中,列维纳斯指出,在艺术的异域感中呈现的“‘客体’处于外部,但这种外部却并不和一个‘内在’发生关联”(56),因此这是一种纯粹的外部,由于没有内部的关联,它也就跳脱出了内在化和同一化之权力的操控。笔者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表明布朗肖的“外部”概念直接来自列维纳斯,但无疑二者在这里对其的定义是大同小异的,在列维纳斯那里,外部与“il y a”和“不在场的在场”等概念在意指上也十分接近。
外部是对内部和世界的脱离,而布朗肖的文学追求的正是这一外部,于是“文学就让那最极端的非世界的东西言说并完成,[也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其消逝的在场”(Sur
Maurice
Blanchot
15)。因此,文学就是外部,就是世界之缺席,而书写的语言则变成了缺席的语言。这种语言并不是那种属于存在论的白日秩序的普遍理性之“连贯话语”,这种话语作为一种传递信息和知识的媒介,所基于的是可理解性,而书写作为一种“外部”,却恰恰是对可理解性,也即理性之连贯性的打破,它最终导向的是一种不可理解性,一种无意义的呓语的重复。这一语言,因其无人称而不再给予权力以任何支点——任何掌握权力的主格与主体,因此成为了对白日的否定。它的出现不基于任何一种主动性的推动,而是“如同黑夜在黑夜中的自身显现”(Sur
Maurice
Blanchot
16),或如福柯所说,“语言的存在随着主体的消失而自为地出现”(“外界思想”30),正是这成就了“无权力的出显”。在这个意义上,书写就是对于权力的解除,就是一种被动性,这是其与把捉客体的视觉和知识的不同之处,视觉和知识构成于它们对客体的权力和掌控,而书写则反过来,只能被那些它所遭遇的客体和词语所撞击、触摸、捕获。列维纳斯同时也指出,对于布朗肖而言,主权在这种书写中的散失,就如同在死亡中的散失一般,在那一作为“可能性的不可能”的死亡中,正如在书写中,正常的秩序颠倒了,在那里,权力通向了它无法确保的东西。书写,就像作为“终结的从不终结”(Sur Maurice Blanchot16)的死亡,在其中存在无尽地翻卷,不断地翻出自己的外部。这个外部与海德格尔那里为诗人提供庇护的大地相对,它不提供任何的庇护,“因为如果外部性向诗人提供了庇护,那么,它就会丧失它的陌异性本身”(Sur
Maurice
Blanchot
19),同样书写也不像海德格尔的艺术那样通向真理,它通向的是比真理更加永恒的“非真理”,或“存在的谬误”(l’erreur de l’être)。对于布朗肖而言,这才是文学所通达的本真性,这显然是对海德格尔艺术观的一种翻转。列维纳斯指出,虽然布朗肖认为艺术作品和诗歌允许我们去表达那种非现实的实现和缺席的在场,这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观念有高度的亲缘性,然而,二者之间的对立之处在于海德格尔最终赋予了真理以统率存在的至高地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被描述为真理,也即存在的去蔽。然而,对于布朗肖而言,艺术作品却不是真理的揭开,相反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绝对外部的黑暗”(Sur
Maurice
Blanchot
22)。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大地为人提供了一个栖居的空间的话,在绝对外部的黑暗中,有的却只是永无止境的游牧和流亡。列维纳斯同时也指出,尽管布朗肖和海德格尔一样,拒绝了对伦理学的关注,然而,在其逃离海德格尔式世界的构想中,已经暗含了伦理学的诉求。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存在对于存在者的优先性,使得探讨伦理学,亦即存在者与存在者之关系显得是一种低级的思索,它与存在之真理还隔着一段距离。然而,对列维纳斯而言,存在的这种优先性已经代表了一种主权,而对于这种主权的祛除,也即一种对于存在论之总体化视域的冲破,代表了“一种不让存在者成为我之对象的关系”的建构,而这“恰恰是正义”(Sur
Maurice
Blanchot
23)。这已经涉及到了列维纳斯对于布朗肖作品中之伦理的理解,我们将把其放在后面统一论述。二、 诗歌语言的潜能和限度
《女仆及其主人》解析的是布朗肖发表于1962年的作品《等待,遗忘》,该作品堪称布朗肖的最后一个叙事作品,但事实上叙事在这部小说中已经接近于其最低限度。故事在一个平常的旅馆房间中展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进行一场对话,他们似乎有所期待,又似乎想忘记什么,但一切都未发生,一些破碎、抽象、散漫的对谈几乎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在这部作品中,列维纳斯最为关注的就是小说的这种语言。他指出,这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语言,是一种永恒的在场的呢喃,而人在这本书中,也是一种同义反复,“仿佛人,由于同一,而变得双重[……]‘但一切保持不变’。他者只是同者的一种重复,另一种言语则只是最初言语的回声,而无视它的差异”(Sur
Maurice
Blanchot
31)。语言虽然被迫从它源出的地方,朝向外部运动,但却由于这种同一的重复,无法冲破自身,而永远地陷于瘫痪。这些试图冲破自身的同一性,却又以此方式囚禁于自身之中的同义反复,被列维纳斯称为一种“同一者的畸形”,而布朗肖的作品就试图解开这种“无-意义的双重扭结”(Sur
Maurice
Blanchot
31)。列维纳斯认为,在《等待,遗忘》一书中,人散失了对世界言说的能力,因为贯穿对话的同一反复的节奏封闭了交流的敞开。言谈和书写,本来是冲破这种同一的手段,然而,它们却依旧属于它们的话语所执行的存在论行为,而这一执行又使得话语本身囚禁于这一存在论行为中(Sur
Maurice
Blanchot
32)。不过,在布朗肖看来,诗歌的语言,却有可能是冲破这一存在论行为的出口。在这里,布朗肖把诗歌的语言和哲学的语言对立了起来,他挑战了哲学语言的权威 : 在哲学语言中,意义建基于语法上的某种命题顺序,它可以建构出一种逻辑的话语。这种语言清晰、直接,被视为一种可为共同体中的众人所共享的“客观”语言,并在西方思想中获得了至高的地位,以致被认作是意义的合法传递者而贯穿于意义之始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止是传递意义的语言,它本身就是意义生成的基础。但在布朗肖看来,还有另外一种可与其抗衡的语言,即诗歌的语言,这是一种爆炸的语言,其意义是由于语言的爆炸而迸发出来的碎片。这种语言之意义不依赖于任何其后的阐释而独立存在,或者说,其意义与这种由于阐释而得来的意义处于不同的层次。而这种阐释实际上使用的就是一种哲学语言,它力图让事物变得可以被归纳、整合和理解。因此,“《等待,遗忘》拒绝阐释的哲学语言(布朗肖作为文学批评家,却屈从于这种语言),它‘不间断的言谈’,拒绝其作为终极语言的尊严”(Sur
Maurice
Blanchot
33)。这种诗歌语言可以成为一个逃离同一性宰制的缺口,其词汇不具理性话语中的关联性,这同样也体现在时间上,它们不与过去和未来相关联,而是一种不断共时化和在场化的运动,“它们在表示(signification)上是共时的并且永远同时化的”(Sur
Maurice
Blanchot
36),这种瓦解词语,把词语还原成当下的运动,就是布朗肖所说的“等待,遗忘”。这是一种“与回忆相对的遗忘,一种不等待什么的等待。‘等待,等待是对等待什么的拒绝,一片逐渐被摊开的冷静的延展’。等待,遗忘,并置着,但没有任何的连接在结构中把它们结合起来”(36)。列维纳斯指出,这种遗忘首要的是对于自身的遗忘,有关自身的意识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中构成的,然而在这种取消了连续性的在场化运动中,自身由时间的连续性所建构起来的同一性解体了。在这种同一性解体之后,布朗肖最终在“这个放松了的自身中,在存在之外”,找到了“一个把平等、正义、关爱、共通和超越结合起来的表达[……]——‘一起,但还没有’”(38)。这一在列维纳斯看来十分精妙优美的表达,可以说相当恰当地传递出了布朗肖后来致力于阐发的共同体的真髓。换言之,同一性的解体不只是主体的解体,也是共同体的解体。在布朗肖的论域中,这一共同体是如巴塔耶所说的“没有共同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没有主权、不会固化且具有不断的自我解域能力的政治共同体构想,这一构想同时也欲对抗的是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以来愈演愈烈的总体化倾向,而文学和书写,作为一种哲学总体性难以包裹的异质存在,就成为了巴塔耶、布朗肖和南希等人构造他们的共同体思想时的重要参照。不过,对于布朗肖而言,这一思想的提出还有着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一共同体思想,以及布朗肖重新赋予其新义的共产主义(communism,共同体主义),更多地指涉的是68年的五月风暴,布朗肖认为,在其中,每个参与者与其他人都展开为一种不确定的关系。抗议者们无论无名或有名,年轻或年迈,贫穷或富裕而聚集在一起。他们拒绝权威,也拒绝将他们的拒绝转化成一种特殊形式的改革。他们所要寻求的不是一种解决,或者目标的满足。就像布朗肖的共产主义暗示的那样,他们所追求的是不能共同之物,是抽离于任何特殊团体的建构之物,它也指认了一种经验,这一经验脱离于任何主动的赋形之外(Iyer,“Preface” XI.)。正如在《情人的共同体》一文中,布朗肖所提到的 :
五月风暴已经表明,没有策划,没有密谋,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欢乐聚会里,犹如一场打破了人们公认并期待的社会规范的盛宴,爆炸性的共通可以把自己肯定为(这是一种超越一切肯定的惯常形式的肯定自身)一种敞开,允许每一个人,不管阶级、年龄、性别或文化的区别,与最初的到来者混在一起,仿佛与一位已经被爱上的存在者混在一起,因为他是未知的熟知者(unknown-familiar)。(“The Community”29-30)
关于这一共同体思想,布朗肖、南希和阿甘本等哲学家都有过直接的论述和互动,而德里达晚期阐发的友爱的政治学,显然也与此有密切关联。通常,这一共同体思想的源头都会被追溯到巴塔耶关于内在经验、爱和共同体的思考,不过列维纳斯关于他者、死亡和无限的观点无疑也对这一论题的阐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们为巴塔耶和布朗肖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补充和辩难。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会提到的,对于五月风暴这场代表法国战后政治共识崩溃的社会和知识革命,列维纳斯以其“保守主义”立场是一直持否定态度的,而布朗肖阐述的这种共通与列维纳斯论域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并非没有冲突。这种冲突也非常曲折晦涩地体现在了列维纳斯对布朗肖青睐的诗歌语言的评价上。一方面,列维纳斯认为布朗肖的这种诗歌语言,“做出示意,却不为任何东西而示意”,它“将诸词语、一个集合的诸指数、一个总体的诸时刻转换成了释放了的诸示意,它们冲破了内在性的墙壁,扰乱了秩序”(Sur
Maurice
Blanchot
39)。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接近于不会固化为“所说”(Le dit)的“言说”(Le dire)。此外,他指出在布朗肖的这种诗歌语言中,“言说松开了它所握住的东西。被给予的物——存在者——并不与等待相称,也不能与这种等待在存在之外的夸张意向相称,而主体性却要求自身在‘意识的意向性’能够承载的对象中被吸收”(Sur
Maurice
Blanchot
38)。因此,布朗肖“等待,遗忘”的诗歌语言,是一种不等待什么的等待,也即没有等待意向性的等待,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超出了以意向性来归化的主体意识。“言说是因可欲之物的临近而加剧、加深了的欲望,因此,在欲望中,可欲之物的临近也变得更加遥远。”(Sur
Maurice
Blanchot
38)这种诗歌语言已经与列维纳斯阐述的“亲近”相接近,那是一种“随着人们越来越走近,它倒越来越远的东西;好像一段越来越难以跨越的间距。这使得义务越来越增大,这是无限,这是一种荣耀”(《上帝》234)。然而,在列维纳斯的“亲近”中的亲近者实际上是他人,而亲近中“最近最远”的距离必须求诸主体内心中的责任感才能发生,这跟布朗肖的立场拉开了距离。在这句话最后的注释中,列维纳斯指出,在布朗肖那里,这种超越的形态中并不含道德元素,也并不是由他人带来的,而是“由于在场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构成的”(Sur Maurice Blanchot78)。而在列维纳斯看来,诗歌却不能仅是一个美学事件,也不能仅是一种语言的无政府主义式扰乱。它要成为一种真正的“言说”,还必须牵涉到伦理和他人 :“要为存在引入一种意义,就是要从同一迈向他者,从我(Moi)迈向他人;就是要给出示意,解开语言的结构”(39)。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布朗肖的诗歌语言,确乎为两个禁闭在屋子里的存在者,也即那两个小说中进行不是对话的对话的对话者,提供了一种找到出口的可能,然而,他们彼此却并不以列维纳斯意义上作为他人的他者而显现,毋宁说,在列维纳斯看来,他们只是自身的不同变式。他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列维纳斯意义上基于他人而脱离自身的伦理关系,而只是形成了一种自身与自身的新关系,他们“驱使自身与他人(Autrui)相遇,抛弃自身,重新融入自身,剥夺自身并向自身呈现自身——在自身和自身之间有多少崭新的关系”(Sur
Maurice
Blanchot
38)。因此,这种语言最终是一种 :
没有关联的纯粹超越的语言——就像无所等待也无所摧毁的等待——无对象的意识——纯粹的胡言乱语,一种从一种独一性走向另一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独一性的语言[……]一种没有词语的语言,其示意什么也不指示,一种纯粹共谋的语言,但那是一种无目的的共谋[……](Sur
Maurice
Blanchot
40-41)。从自身的伦理立场出发,列维纳斯对于布朗肖作品中这种变异的自身性,及那种企图自我超越的变异的语言,也即其诗歌语言及其背后暗示的“无目的的共谋”的政治思想,是持保留态度的,他最后也在结尾中隐晦地指出了这一点。列维纳斯指出,这种“不连续的语言”,随后即被跟随其踪迹并且不断述说的从属的词语所包围,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词语理解为阐释诗歌语言的语言,也即上面提到的哲学语言,存在者,甚至“存在者之存在”都栖身和伸展于其中。最终,这语言掌管了一切,我们最终的全部记忆、预见和永恒都只能以这种语言的形式,也即指意清晰的形式呈现于意识或历史之中。这种语言是连续性的逻辑化的语言,它不能容纳现实中的模棱两可,也不能容纳他人之“迷”。因此,这种哲学语言,也即言说真理的语言并没有真正被布朗肖的诗歌语言所打断,并没有消失。相反,它最终却享受着诗歌语言的服侍,因此列维纳斯称诗歌语言为女仆。这一作为哲学之女仆的诗歌语言,“从她所侍奉并监视的主人的失败、缺席和出走的叙述中获得胜利和在场。她清楚她不能打开的藏物处藏里的财产,她保管着毁坏的大门的钥匙。一个无可指责的管家,她控制着她所管辖的房子,并否认隐秘的锁闭之存在”(Sur
Maurice
Blanchot
42)。也就是说,这种诗歌语言对于哲学语言的挫败,反倒成了对哲学语言的确认,因为其打断连续性和反逻辑等方案都是相对于连续性和逻辑的哲学语言而言的,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它只是以一种同义重复的无意义对抗了基于意义的连续性,却没有真正打断这种连贯性的话语,要打断这种话语的连续性,需要一个他者的声音,需要一种“别样地(autrement)”超离。在其后期最重要的著作《别样于存在》中,列维纳斯也指出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只是一种更为接近存在的“所说”。这种诗歌语言却没有完全跳出哲学语言的逻辑,二者依旧处于同一平面,甚至同一辩证法的运作中。它朝向外部的运作,没有真正实现列维纳斯式的迈向他人的超越——迈向“存在之他者”,而反倒更像是完成一次土地测绘,它以其对于哲学语言的激进化偏离,而不断试探着哲学语言的边界,又以这样的方式,守护着这一边界。于是,列维纳斯说,它是一个无可指责、兢兢业业的管家,它的激进并没有走向对于其主人——哲学语言的背叛和超越,反倒是以这样的方式守护着他的边界,保管着他的财产,并否认在其中隐秘的锁闭。列维纳斯最后问道 :“管家或女主人?了不起的伪善者!因为她爱她一直守护着的疯狂”(Sur
Maurice
Blanchot
42),这疯狂正是白日的疯狂。三、 存在的封闭与理性的疯狂
这里的“白日”已不仅仅是作为劳作和理性控制的世界的白日,它代表的是“一股可怕的强力,通过它存在进入世界,并自我闪耀”(Blanchot, “La littérature”316),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光的在场。这是一种摆脱了时间限制的在场,一种被固定的当下的永恒在场,在其中没有什么得以延续,也没有什么会到来,只有相同的事物在不断重复。布朗肖指出 :“白日,在白日的进程中,白日允许我们逃离事物,它让我们理解事物,而在它允许我们理解事物的时候,它使事物变得透明,仿佛空无一物——但我们不能逃离白日”(318)。因此,白日接近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光,它奠基于西方历史上作为真理之隐喻的光照之中,一方面,它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事物、把捉事物,在这种理解中,它抹去了实在的晦暗和纹理,使其成为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使我们变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另一方面,它却也因此而宣告了自身的主宰和永恒的在场,而这种在场,又正是以那种使一切变得透明的白日之光的形式而存在的。它抹煞了事物的独一性和他异性,主体所能接触的只是一个普遍化的世界,它同时也抹煞了主体本身的“个体性”,主体也只是这一普遍化世界中的一个要素,最终,极致的普遍化就变成了透明,因为在透明之中,只有光的流溢,一切全无差别。在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看来,这是一种疯狂,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永恒的流荡,是“没有外部的运动,没有空无来接收其流散者的驱逐。[……]此刻的疯狂,白日的疯狂”(Sur
Maurice
Blanchot
60)。对于这一“白日的疯狂”,列维纳斯梳理出了几层含义,它既是一种在根本意义上的作为白日的理性的疯狂;同时也代表了对于这种理性的疯狂欲求;如果说这种理性的疯狂是通过将一切以光的形式“在场化”而实现的话,那这也是一种在场的疯狂,这种在场落实到时间上,就是“此刻的疯狂”,因为这种在场也就意味着要把一切共时化于“现在”,共时化于某种确定性,它甚至是我们在下文中会论述到的历史层面的“今日的疯狂”;列维纳斯还特别借用圣经指出,这一疯狂“尤其意味着,白日的疯狂和黑夜的疯狂或惊恐形成对照”(Sur
Maurice
Blanchot
58)。列维纳斯进而指出这一白日的疯狂的叙述,既不是为了抱怨与我们合乎理性的行为相伴随的无意义的举动,也并不是为了暴露人本主义者在面对存在之有限的时候,感到的惊讶和失望。简言之,这不是一种“人的疯狂”。这是一种更为基础的疯狂,它潜藏在“世界的稳固性——肯定性,它被置于一切的论题面前,停留在一切的骚乱和一切的欲望背后,支撑——或并入或包含——了所有的荒谬。一个甚至在论世界的荒谬性的句子中也在肯定自身的世界[……]一种支配着时间,并悬置其飞逝的稳固性”(Sur
Maurice
Blanchot
60-61)。这些论述看似抽象,然而,笔者则认为它们有着具体的所指,需要将其与列维纳斯当时所处的语境相关联。《白日的疯狂》写于1948年左右,而列维纳斯这篇评论文章则写成于1975年,其时,五月风暴余温犹存,列维纳斯指出,《白日的疯狂》虽然写于1948年,但在精神层面,却与1968年有着更多的相似(Sur
Maurice
Blanchot
59)。对于五月风暴,列维纳斯并不认同,他隐晦地指出其时学生们的游行是疯狂而浅薄的,并将其看做是“白日的疯狂”的一次爆发(72)。而在法国知识界,其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虽然已经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而走向没落,但依旧拥有强大的势力,对于结构主义思潮及其反人本主义倾向,列维纳斯也一直持批评态度。列维纳斯对于“白日的疯狂”对世界之稳固性的执迷的指责,也可以视作是对于结构主义,及其以新的形态所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虽然列维纳斯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的指责。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对知识的终极同一性和稳固性的追求,在欧洲的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无论它体现为柏拉图式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还是结构主义的“结构”。因此,欧洲也一直无法摆脱这白日的疯狂。“一切都是适恰的,这是欧洲!这是安全。这是不可转让者。‘我看见这个白日,在它之外,一无所有。谁能把我带离这儿?’”(Sur
Maurice
Blanchot
61)因此,和布朗肖的其它作品一样,这又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封闭”的故事。白日的疯狂是“同一者的循环往复” :(它)甚至不遵从一个长久的轮回。它是原地的旋转 : 幸福在其着魔般的永久之中,疯狂的爆发被封闭于疯狂之中,被封闭于压抑之中,被封闭于一种无法呼吸的没有外部的内部之中。疯狂是出路,或出路是疯狂吗?极端的意识似乎是对没有出路的意识,因此,它不是外部,而是关于外部的观念,以及执迷。一个在外部的不可能性当中被设想的外部,思想生产着对不可能之外部的欲望。(Sur
Maurice
Blanchot
63)在列维纳斯看来,真正的外部只能经由他人才能通达,他的代表作《总体与无限》的副标题即“论外部性”,在该书中,他用“面容”“享受”“生育”“爱欲”等“人化”的概念表达了对于内部性的出离和他人之于主体的绝对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使得存在的总体性或统一性(unity)破裂了,从而变得多元,而多元的存在才是伦理的存在。列维纳斯在此时使用的“外部”与布朗肖,包括后来的福柯和德勒兹等人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列维纳斯的外部是反空间的。正如德里达所说 : 列维纳斯想在《总体与无限》中表明“真正的外部性并非空间性的,存在着某种绝对的、无限的外部性,即大写他者的外部性,它不是空间性的,因为空间是大写同一的场域”(193)。因此,在布朗肖小说中的这种“非人”的“文学空间”的外部性,根据列维纳斯的标准,归根到底并不是外部性,而只是一种外部性的想法和执迷,它所代表的其实最终是一种外部的封闭,所谓的外部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深入,一种无路可出。一种对于观念或理性反其道而行之的抗拒,并不会真正超越出观念和理性,它只不过将自身变成了一种蜷缩在自身内部的“执迷”。如果说理性是封闭的话,那么,这种“非理性”也同样是封闭的。对此,将布朗肖视为“外部思想”之代表的福柯曾承认道 :“[……]我们永远处在内部之中。边缘是一个神话。外部言语是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驱逐的梦。”在列维纳斯看来,这种封闭是由欧洲的思想传统所决定的,它一直倾向于通过内部来占用他者,将其统摄于自身之中,如此也就堵塞了外部,“归根到底,我们的宏大的哲学传统,正是依据自我意识,来表达并包裹同他者的关系”(Sur
Maurice
Blanchot
69)。这种倾向在不断的滋长中,最终成为了一种疯狂,虽然,它一直自称是清醒、明晰的,是疯狂的反面。但其实,理性与非理性只有一线之隔,当理性成为一种独断和执迷,它就变成了非理性。就像绝对的光明也就是绝对的黑暗一样,因为眼睛在绝对的光亮中将一无所见,可能还会被刺瞎双眼。因此布朗肖在该小说中写道 :“光发疯了,光明失去了全部的理性 : 它疯狂地攻击我,失去控制,没有目的。”列维纳斯则将其放到了西方历史中进行解释 :“我们得自希腊的光,不是真正的明晰。我们的历史所赢得的自我意识,不是一种清醒。它总是一直醉着”(Sur
Maurice
Blanchot
67)。而正是这种理性,同时也是非理性的疯狂,导致了“奥斯维辛的疯狂”(60)。四、 布朗肖作品中的他者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在论《文学空间》时,列维纳斯认为布朗肖让文学所唤回的人的游牧本质中已经蕴含了伦理的要求。在这里,有一个视角的转换,布朗肖对于这种人的游牧本质的论述更多是从一种看待主体的视角出发的,他希望主体经由这种书写的游牧而不断逃逸出其同一性。然而,列维纳斯并不与这一游牧主体站在同一阵线,他不将其视为一种理想的自我,也并不以看待主体的视角来打量它,而是与之相隔了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他把这一游牧主体看作是他者,而且很快就将这一他者替换成了其伦理学中的他人,并进而将这一游牧的主体视为无根基的、流放的他人,因此需要我对其担负责任,并以这种方式终结了布朗肖的游牧主体中残留的浪漫主义和悲剧情怀。
简言之,在布朗肖笔下的“游牧”,之于列维纳斯却是一种“流亡”。早在其1948年的《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就已阐述过,他者,他人,是以一种极端贫乏,易受伤害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的,这种脆弱性向我发出了绝对的命令,使我对其负有无限的责任。由是,那个在布朗肖晦暗空洞的文学空间中孤独却执著的游牧作者,在列维纳斯那里,却以无家可归的他者的形象,开始以其贫乏和流浪来召唤主体的责任,这种召唤是以面容(visage)的显现来完成的。“在住所蜕下了其建筑之光彩的被诅咒的城市里,不仅诸神,就连天空本身,也缺席了。但在饥饿的咕咕作响中,在家园和事物回归了其物质功能的悲惨中,在一种没有视域的享乐内部,人的面容照射出来。”(Sur
Maurice
Blanchot
25)这个被诅咒的城市,不同于海德格尔那个因诸神的造访而获得慰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天地人神的四重性并不会赋予人与人的关系以优先性。这种关系反倒归属于这四重性的空间和几何之中,从而确保理解的绝对性。但如上所述,布朗肖那里作为外部的文学空间已经出离了这种可理解性的绝对性,而进入到了一块黑暗而不可理解的场域之中。对于列维纳斯而言,布朗肖的外部虽然还没有走向他人,但这种出离海德格尔之整全世界的努力,却已经走出了迈向他人之关键性的一步。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论《等待,遗忘》的时候,列维纳斯又明确指出布朗肖作品中的超越形态不含道德元素,布朗肖那种试图挑战存在论语言的诗歌语言,虽然确乎蕴含打破存在论语言之同一性和连续性的可能,然而,由于其中没有他人给出的示意以启动“言说”来超越“所说”,它就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同一性,由同一反复和无意义构成的同一性和连续性。而在其中呈现的他者,以列维纳斯“他人作为绝对他者”的标准,也不是真正的他者,而只是自我的变式。在分析《白日的疯狂》时,列维纳斯指出,其实该小说中暗含着他者-他人的维度,这体现在一个小细节之中 : 一个男人后退以让一辆婴儿车通过,“这是一个突然来临的事件——也就是说一种‘没有约定’的突然来临——在他者面前撤回的一己(l’un),为他者之一己”(Sur
Maurice
Blanchot
68)。但列维纳斯马上又指出,这只是一个虚伪的,或者似是而非的事件,这一事件旋即又被匿名性的晦暗和冰冷之运作所淹没了,被这一无限的空间之沉默所淹没,被大众之互相残杀所淹没。在这样的背景下,列维纳斯所倡导的伦理观 :“为他人受难”并不能实现,相反,这种利他主义的意识旋即又回归了自我,“为他人受难”变成了“他人使得我受难”。那个以其面容的特殊性呼唤我的他人,变成了一群无边无际的匿名的众他人,这一群他人成了夺走我快乐,我需要与其争斗,甚至将其谋杀的他人(Sur
Maurice
Blanchot
69)。如此一来,小说就又回到了自我中心主义之中,尽管这种回归是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形式实现的,但“自我否定(忘我)只是一种对于欧洲个人主义的回归和自我的加强”(Sur
Maurice
Blanchot
69)。在这种文学的自我主义中,一切他者,甚至上帝,都是以我所欲求的方式被包裹在文学之中的。然而,这是一种没有主体性和个体性的自我主义,主体性和个体性在列维纳斯那里意味着负责和担当,而这种想要包括一切的欲求却是总体性的,因为它想包括一切,包括个体性,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主体的意志也只不过是这一总体意志运作的一个节点,而不是主体。因为它已经不含“主体”,这种想把一切纳入“内部”的总体性在布朗肖作品中,就是以匿名的方式显现的。这种不可被理解的匿名性和内部性,在其不可接近的意义上,同时又是一种“外部”。因此,这是一种作为内部的外部,是不断内卷中的外翻,这种内在的外部性又被福柯和德勒兹称为褶子(le pli)。这种内在的外部性,这种匿名性如同蛛网般运作,而那只本应位于蛛网中心的蜘蛛(主体)却不存在,书写被叙述者还原成了形式主义——职业——存在论状态。对于这种书和书写而言,诠释无足轻重,它并不能对书和书写造成影响,也就是说不只书写中的作者死了,读者也死了。这个自在的文学空间中,“没有阅读、没有书写,没有表达。没有什么需要识破,没有内在性,没有深度。存在中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坚固。形式无尽地包裹着包裹”(Sur
Maurice
Blanchot
70),诠释在其中,只不过是没有所指地从概念跳转到概念,符号跳转到符号,完成一种“交换已知的筹码的游戏”(70)。在这种没有主体性的自我主义中,一切都被呈现给了外部,一切也都由外部来决定,而不求诸我的内部,这里的内部指的是列维纳斯定义的主体性,譬如我的伦理意识,我的责任心。但这里的“外部”并不同于列维纳斯的“外部”,后者所指涉的是“他人”,而前者指涉的是一个匿名而中性的空间,在其中没有主体的位置,也没有正义的位置,“正义完全地转向了外部,但那是一个没任何出路的外部。没什么逃避得了体系的关联性”(Sur
Maurice
Blanchot
71)。也就是说,对于正义的裁决被交给了一种体系的运作,一种中性、中立也因此貌似“公正”的外部的运作,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政治和法律的运作方式。但列维纳斯认为,这种中立的政治和法律的运作,如果不以伦理作为基础的话,对于解决正义的问题,解决对他人的迫害和不公是不够的。因为中性的政治和法律无法介入到我与他人之面对面的亲密关系,也就是伦理关系中,它们并不能让我充分注视到他人的独一性,“观念的辩护,司法的权力,法律的匿名话语,不能提供慰藉。法律并不进入对话的单独性之中”(Sur
Maurice
Blanchot
71)。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别样于存在或在本质化之外》中,列维纳斯也强调 :正义并不是管理着人类大众的合法性,从其中可以获得“社会平衡”的技巧,这种技巧能够调和各种对抗的力量。这种技巧证明那把自身交付给其必然性的国家是正当的。没有那个让它发现他处于亲近之中的人,正义是不可能的。他的功能不限于“判断的功能”,即把特殊的情形归在一般规则之下。法官并不处在冲突之外(置身事外),而法律位于亲近之中。正义、社会、国家及其机构、交换和工作,在亲近的基础上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意味着没有什么处于一个人对他人所负有的责任的控制之外。(Autrement
qu
’être
248)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列维纳斯认为布朗肖的小说以精妙的方式描写了中性的运作,以及其对伦理的回避和对他人的封闭。至于布朗肖对这种“存在之封闭”所持的态度,是一种执迷,还是暗含谴责,列维纳斯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当然,更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对此的评价。这也迫使我们再度认识到,列维纳斯对于布朗肖作品中他者和伦理的评价是复杂甚至矛盾的,一如他对于艺术作品的态度一般,而且其对布朗肖的评价还与所评论的不同的作品相关,也与他自己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相关。要对这种评价做出一种清晰的、线性的、统括的总结是困难的,甚至错误的,这很可能又会落入列维纳斯和布朗肖所批判的同一性陷阱之中。
结 语 文学与伦理的友谊
经过以上梳理之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列维纳斯和布朗肖的文论之共通和差异。二者的文论首先是一种深刻的结盟,这种结盟和两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艺术观的对抗密切相关。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艺术作品打开了一个敞开的空间,在这种敞开中,所有事情都不同于日常,它们在澄明中焕发出新异的光亮,而这就是本真性,真理的现身方式。然而对于列维纳斯和布朗肖而言,无论是认识之光还是这种存在之光,都蕴含了同一化的运作,它会抹杀物之独一性和陌生性,对于他们而言,艺术却恰恰是一种维持物之独一性和陌生性的方式,作为一种晦暗,它是使得物得以摆脱光线的手段。
不过,在引入伦理视角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开始变得微妙了。列维纳斯曾明确指出布朗肖的文学中不含道德元素,布朗肖在《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中也指出,文学应当拒绝道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道德缺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伦理的阙如。布朗肖之所以抗拒文学中的道德元素,在于它会干扰文学之中性的本质,从而使其成为一种说教、训诫甚至意识形态的附属,但这并不代表布朗肖就此也拒绝了伦理。这就牵出了“伦理”和“道德”之间的区分,这是一个至今仍争议不绝的问题。事实上,在古罗马人引进古希腊人的思想时,“道德(moralia)”正是“伦理(èthikè)”一词的翻译,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变得越来越规范化,“道德”越来越偏向于约定俗成的规范之意,而相较之下,“伦理”一词却还保持着其与生存状态相关的直接性。简而言之,“‘道德’应该属于继承而来的规范,‘伦理’则属于建构中的规范。”(德鲁瓦13)德鲁瓦甚至指出,未来伦理的新任务就是组织不同的道德共生(16)。列维纳斯也曾对道德和伦理作出过区分,他指出 :“道德指的是与社会行为和公民责任相连的一系列的规则,不过当道德通过社会-政治的组织规则运作,并提升我们的生存质量的时候,它的根基却建立在一种朝向他者的伦理责任上”(“Dialogue”29)。
在这个意义上,布朗肖与列维纳斯其实是共通的,布朗肖对于道德的排斥,同样不能视为是反伦理的。相反,在列维纳斯的影响下,布朗肖对于伦理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1940年代,布朗肖提出了一种“语言的非辩证经验”的诗歌理论,在其中,主体(诗人或作家,同时也包括读者)外在于作为观念的语言,这种写作发生在“交谈的外部”,“语言的外部”。布朗肖的这种写作被列维纳斯看作是一种绝对放逐的外部写作,这一放逐对于布朗肖来说就是伦理的。杰拉德·布伦斯(Gerald L. Bruns)认为,它甚至可与列维纳斯伦理学和诗学中的亲近类比。因为对于布朗肖而言,这种放逐是一种与晦暗和未知的联系,一种既非力量,也非认识,同时也不是启示的联系。在这里,诗歌意味着既要谈论未知,又要使其留于未知,而不用话语把捉它,使其同一化,而这就是一种语言的责任,语言的伦理,它只是在言说却不成为哲学的操演,而哲学的同一化运作中却包含了暴力。如此一来,它就使我得以与一种外在于我掌控之物真正亲近(Bruns224)。
不过,这种亲近与列维纳斯的定义是有出入的。在《语言与亲近》中,列维纳斯指出“原初语言”代表了一种语言与独一性的关联,这一独一性在语言之主题的外部,它不能被语言所主题化,而只能被语言所亲近。这一独一性被列维纳斯定义为一个个性化的他者 : 他人,或其面容,其“无防备的眼睛”构成了原初的语言(“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infinity”55)。而布朗肖则坚持“他人只是一个根本性的中立名称”(Bruns225)。他异性对于列维纳斯来说,一直是另一个人,然而,布朗肖却认为,如果只将人类视为他者,那同样也就给予了他者一种总体性的定义,或者至少是将其限定于一个范畴之内。比较起来,布朗肖更偏爱将他异性的非决定性或抽象性命名为“外部”“中性”“未知”——而不是像列维纳斯那样将其人格化为乞丐或老弱妇孺。易言之,布朗肖使他者留于无名,以保持其绝对的外部性。
可以说,列维纳斯与布朗肖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是将外部归属于他人,还是将他人归属于外部。对于列维纳斯而言,外部必须通过他人来设想,他人的外部性是最为根本、最为“外部”的外部性,因为他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被同一化,而其它“外部”,例如物质或元素则不然;而对于布朗肖而言,只有将他人事先归属于外部才能保证他人真正的他者性和不可规定性。换言之,要思考他人,必须以一个绝对外部作为必要的平面,这一绝对的外部就是“匿名”和“中性”,就是没有任何规定性,包括“他人”这一规定性。尽管他在后期也越来越承认他人的绝对陌异性,“唯有人绝对陌异于我。他就是未知者,他就是他者,在其中他在场 : 这就是人”(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59-60)。但这种陌异性,并没有如列维纳斯的伦理学那般激进地迈向对于他人的绝对责任、受制和替代。


总体而言,列维纳斯和布朗肖为我们展示了两种迥异而又共通的伦理学和文学,前者意图用伦理学来超越哲学的总体性,而最终却在深入到这种伦理学的语言表述的时候,找到了文学,从而使得伦理变得文学化;后者意图用文学来超越哲学的同一性,最终却在对于文学外部性和他者性的探索中,深入到了伦理学和他人的层面,从而使得文学变得伦理化。在这两种伦理学和文学中,充满着奇妙的交错,一如布朗肖笔下的友谊。这种友谊也应当存在于文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之中,这种友谊告诫我们 : 既不能使得伦理学过度文学化,也不能使得文学过度伦理化(这恰恰是我们将列维纳斯和布朗肖的哲学观点落实到具体的解释层面时最具风险的诱惑),而是应当使二者保持那种分离的联系,联系的分离,既亲密相通,又不相互占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 在这种友谊中,包含着对于他者或朋友的绝对尊重,对于他者之优先性的绝对承认,正是因此,列维纳斯和布朗肖才能在巨大的思想分歧中维持着毕生的友谊。
注释[Notes]
① Emmanuel Lévinas.Sur
Maurice
Blanchot
(Montpellier : Fata Morgana, 1975),10.笔者对该文本的翻译参考了lightwhite的翻译(诗翼阅读,2015-10-11, 〈https ://site.douban.com/wingreading/widget/notes/7547565/note/520163695/〉)。② 关于列维纳斯的哲学概念“il y a”与布朗肖文论的关系请参照拙作 :“il y a与文学空间 : 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文论互动”,《中国比较文学》2(2017) : 116—28。
③ 从布朗肖这种书写观中无疑也可以觅到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踪迹,布朗肖的挚友巴塔耶与超现实主义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联,在那个时代,许多法国文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④ 如果说死亡对于海德格尔是最为本己的事件,是作为“不可能性的可能性”,那么,对于列维纳斯和布朗肖来说,死亡却是最不本己的事件,是“可能性的不可能”,因为无人能够经历自己的死亡,死亡是一个永远延宕,不可触及的事件。
⑤ 针对海德格尔的异教真理观,布朗肖曾根据犹太教体验,反其道而提出“真理在游牧”。参见乌尔里希·哈泽,威廉·拉奇 : 《导读布朗肖》,潘梦阳译(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⑥ 列维纳斯在后期哲学中将语言区分为“言说”和“所说”,简单来说,“言说”指示的是原初的、直接朝向他者、将自身暴露给他者的伦理语言,而“所说”则是已经固化为一种传播载体的媒介语言,或不指向他者的存在论语言。
⑦ 转引自Judith Revel,Dictionnaire
Foucault
(Paris : Ellipses Marketing, 2008.)32.⑧ 转引自尉光吉 :“爱的三重奏——布朗肖的黑夜体验”,《文艺研究》2(2019) :29。
⑨ 关于布朗肖与浪漫主义文学之关系的梳理可参考刘文瑾 : 《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254—61。
⑩ 关于褶子这一概念,其实福柯早在1966年就已经在使用了,他指出这一概念是外部和内部之分的终结,因为它就是一种内部的外部。Cf. Judith Revel,Dictionnaire
Foucault
. (Paris : Ellipses Marketing, 2008)3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The
Unavowable
Community
. Trans. Pierre Joris. New York : Station Hill Press, 1988.29-53.- -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 Trans. Susan Hans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莫里斯·布朗肖 :“论友谊”,《福柯/布朗肖》,肖莎等译。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89—95。
[Blanchot, Maurice. “On Friendship.”Foucault
/Blanchot
. Trans. Xiao Sha, et al. Zhengzhou :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4.89-95.]Bruns, Gerald L. “The Concepts of Art and Poetry in Emmanuel Levinas’s Writing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vinas
. Eds. Simon Critchley and Robert Bernasconi.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06-33.雅克·德里达 :“暴力与形而上学”,《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年。188—276。
[Derrida, Jacques. “Violence and Metaphysics.”Writing
and
Difference
. Trans. Zhang Ning. Beijing : 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 2001.188-276.]罗热-保尔·德鲁瓦 : 《给我的孩子讲伦理》,姜丹丹译。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Droit, Roger-Pol.Ethics
Explained
to
Everyone
. Trans. Jiang Dandan. Chongqing :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米歇尔·福柯 :“外界思想”,《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8—46。
[Foucault, Michel. “The Thought of the Outside.”Michel
Foucault
:A
Reader
. Ed. Wang Min’an. Beijing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28-46.]Iyer, Lars.Blanchot
’s
Communism
:Art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al
.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 Trans. Alphonso Lingis. Dordrecht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47-60.- - -.Sur
Maurice
Blanchot
. Montpellier : Fata Morgana, 1975.Levinas, Emmanuel, and Richard Kearney. “Dialogue with Emmanuel Levinas.”Face
to
Face
with
Levinas
. Ed. Cohen R.A.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13-33.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 : 《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 :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Levinas, Emmanuel.From
Existence
to
Existent
. Trans. Wu Huiyi. Nanjing :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 - -.God
,Death
,and
Time
. Trans. Yu Zhongxian. Beijing : 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 1997.]Revel, Judith.Dictionnaire
Foucault
. Paris : Ellipses Marketing, 2008.弗朗茨·罗森茨威格 : 《救赎之星》,孙增霖等。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
[Rosenzweig, Franz.The
Star
of
Redemption
. Trans. Sun Zenglin, et al. Jinan :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