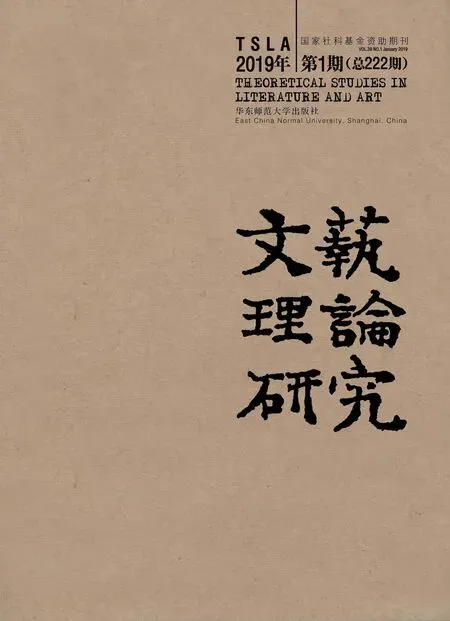苏轼的游寺诗及其禅悟的进阶
——兼论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三种类型
李舜臣 高 畅
Gao
Chang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n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of China (14BZW085), 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lassics Compilation Committee ([2014]097), and the Jiangxi Province Key Project of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佛寺,又称伽蓝、精舍、兰若,既是彰显宗教文化的重要场所,亦是迥异于俗世的“另类空间”。东晋以还,文人酷爱悠游佛寺,亲近禅侣,抒写禅悦风致,名篇秀句,郁起迭出,诗苑遂有“游寺诗”一门。爰至北宋,佛寺林立,文人公假尤多,自放闲适,游寺之风更显炽盛,游寺诗数量亦度越前朝。
赵德坤、周裕锴先生曾考察过北宋文人的游寺之风,探析了他们寺院书写的模式及其意义,不过他们研讨的对象是“散体之文”,未涉诗歌。事实上,文人佛寺文多因“僧人请托”而作,写作行为未免带有“他性”,而游寺诗则是诗人的主动书写,最直观地呈现出他们接受佛禅的心理和程度。北宋游寺诗的作者、数量相当繁复,稍具声名者几乎皆涉之。这其中尤以苏轼最为典型,据现存资料统计,他至少游历了140所寺院,游寺诗达266首,近其诗总数的十分之一。若仔细分析,苏轼游寺诗的创作明显存在阶段性: 他居汴京前后虽达八年之久,却只有20首;而外任凤翔、杭州,贬谪黄州、岭南之时,游寺最为频繁,游寺诗数量亦最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这四个时期的游寺诗不仅颇为鲜明地反映了苏轼习佛的进阶,而且基本涵括了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几种类型。
一、外任凤翔、杭州时期:从“不知禅味深”到“久参白足知禅味”
苏轼很早就与佛寺结有不解之缘,传说他少时即读书于连鳌山的栖云寺及实相寺、华藏寺。嘉祐初,苏洵携苏氏兄弟进京赶考,抵渑池,“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苏辙12)此或为苏轼的第一首游寺诗,可惜后来“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97)嘉祐五年二月,苏氏兄弟随父至京应制科考,于西冈赁一宅,常游临近精舍。苏辙《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忆及此事曰:“昔年旅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韂。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苏辙70—71)末两句表明他们只是寄食佛寺,尚不知玄远之禅味。
苏轼现存最早的游寺诗是他陪侍苏洵自蜀至荆州,途经峡州时所作《寄题清溪寺》和《留题峡州甘泉寺》。王十朋将二诗归为“寺观类”,然前诗评鬼谷子、苏秦、张仪的命运,后诗则凭吊姜诗之纯孝,纪昀还批评说“纠缠姜诗,牵强无味。”(纪昀1857)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游寺诗”,毋宁说是“咏史诗”。
嘉祐六年十二月,苏轼签判凤翔,至治平二年二月还朝。四年间,苏轼游历了11所寺院,作游寺诗18首。著名的《凤翔八观》,乃记凤翔“可观者八”,其中的“三观”即天柱寺维摩像、开元寺王维吴道子画、真兴寺阁。嘉祐七年二月,苏轼分往属县减决囚禁,数日间,游宝鸡龙宫寺,题诗于中兴寺、郿县横渠镇崇寿院;次年七月,祷雨磻溪,先宿僧舍僧阁,又宿青峰寺下院翠麓亭,再宿南山蟠龙寺。凤翔期间,苏轼对佛寺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嘉祐七年重阳节,他甚至不预府会而独自出游普门寺。因此,梁银林先生说:“叙写佛寺之作,成为他凤翔期间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些诗歌实际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像《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题画文殊、普贤》,着重描写寺中的壁画、雕塑,要旨则评赏二公之技艺,虽用了“双林”“祇园”等佛语,但皆是叙写佛像故事,别无深意。《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一诗,恰如查慎行所评“俱是祷雨之作”(《苏轼资料汇编》1771),其余游宿寺院之作,则皆只记游踪,甚至连寺院的景观都很少着墨,基本与佛教无关。因此,苏轼自称嘉祐末“予始未知佛法”(《文集》1965),应是如实之语。
熙宁四年六月,因政见不合,苏轼通判杭州。杭州佛寺林立,甲于天下,章衡撰于元祐三年的《敕赐杭州慧因教院记》中记杭州寺院多达532所。公务之余,苏轼常探幽揽胜,访僧寻寺,曾自言:“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诗集》644)倅杭三年,他共游历寺院41所,游寺诗凡79首,占此期诗歌总量的22.32%,并呈逐年递增之势: 熙宁四年十一、十二月5首,熙宁五年20首,熙宁六年33首,熙宁七年正月至八月18首。更为重要的是,他与佛禅的关系也随着时日增加而愈加密切。
初至杭州,苏轼游寺的初衷是“名寻道人实自娱”(《诗集》318),因此诗中皆描绘寺院清音、僧侣风致和内心体验。例如,写双竹湛师房:“羡师此室才方丈,一炷清香尽日留。”(《诗集》524)写与海月辩公“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文集》638)听僧昭素弹琴后,自觉“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诗集》576)等,似乎暂忘了尘烦热恼,觅得了自适平和的心境。苏轼甚至还体认到俗世与佛寺之间的巨大反差,并重新审视自我。“自知乐事年年减,难得高人日日闲”(474)、“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548)等诗句,皆意在凸显方内、方外之别,表达了他对此岸与彼岸意义的重新考量。
随着时日的增加,苏轼对佛禅的理解渐次深入,自言“久参白足知禅味。”(548)于山水清音,亦始“别具只眼”,故诗中每含禅味、禅境。例如,熙宁五年八月作《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云:“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380—81)首句即进入非有非无之境,复自称“幽人”,更添清幽之味;末句拈出“当空之月”,又具有空寂之感,故周紫芝《竹坡诗话》以“清绝过人”(周紫芝350)评之。作于熙宁七年的《游鹤林、招隐二首(其一)》,亦清腴拔俗,“古寺满修竹,深林闻杜鹃”二句,纪昀赞曰“不减‘曲径通幽’之句。”(纪昀1887)
自嘉祐末“喜佛书”至熙宁四年末,历时八年,佛禅文化潜移默化于苏轼的精神世界,他的游寺诗还常流露出“空观”“无常”之思。例如《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原是追怀建寺者钱镠,但并没有循着一般怀古诗的思路,而是用“佛家法眼”抒写了“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323)的旷达,用“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维摩诘经》36)的理论消解内心的执念。另如“废兴何足吊,万古一仰俯”(345)、“荣华坐销歇,阅世如邮传”(347)等诗句,皆是言说无常世事;而“入门空有无,云海浩茫茫”(577)、“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331)等诗句,则直接陈说“诸色皆空”的思想。需指出的是,苏轼在演绎这些佛教思想时,多出之以概念、术语,明显未臻至圆融无迹之境。
苏轼此期的游寺诗还略具禅偈之风。例如《游灵隐寺戏赠开轩李居士》:“推倒垣墙也不难,一轩复作两轩看。若教从此成千里,巧历如今也被谩。”(2525)该诗仿偈颂体,出以粗浅、直白之语,故纪昀评有“禅偈气”(纪昀1883)。又如著名的《书焦山纶长老壁》,以长鬣人为喻,言心无所住之理,纪昀评曰:“直作禅偈”(纪昀1887),赵翼《瓯北诗话》亦曰:“绝似《法华经》、《楞严经》偈语。”(赵翼1147)不过,这类仿偈颂体的诗歌仍显得比较生硬,模仿之迹明显,因此赵翼批评道:“摹仿佛经,掉弄禅语,以之入诗,殊觉可厌[……]此等本非诗体,而以之说禅理,亦如撮空,不过仿禅家语录机锋,以见其旁涉耳。”(赵翼1146—47)
综上可见,苏轼倅杭时期的游寺诗渐有禅味,屡用佛典,兼及佛理,甚至略具“禅偈味”,但总体未臻圆融之境,更像是应特定场域而作。这反映出他与佛禅的关系仍处于认知的阶段。熙宁六年,苏轼循行富阳,作《自普照游二庵》中云:“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434)表明了他仍眷恋红尘,难耐孤寂。这是以典型的文人“用舍行藏”的处世方式对待佛教,佛寺于其意义只是暂时的遁世之所。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去杭,历任密州、徐州、湖州。五年中,因客观环境、个人境遇之变,游寺诗的数量急剧减少,仅有29首,所占比例约为6.97%,游历寺院11所。他在密州、徐州创作的诗歌总量与倅杭大致相当,但游寺诗却从79首下降至14首。此中原因,乃在于密州等地佛教不昌、寺院稀疏之故,而且兹地临近邹鲁,诗礼簪缨,儒家的济世思想占据其心。这些游寺诗总体更接近凤翔期间,无太多佛禅色彩。元丰二年,苏轼致信久上人说:“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矣”(《文集》2530),体现出他在密州、徐州期间与佛禅的疏离。后赴湖州,相伴者乃旧友、高僧,苏轼游寺诗创作热情高涨,占此时期诗歌总量为20.27%,内容上也出现某种程度的回归。例如“虚明中有色,清净自生香”(944)言说佛教色空理论;一些诗作亦富有禅机,如“清风偶与山阿曲,明月聊随屋角方”(943)、“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985—86)等等,暗含着佛家随缘任运的思想。无论从内容还是格调看,与倅杭时期颇为接近。
二、黄州时期: 洗心归佛,以求安心
元丰二年八月,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数月“魂惊汤火命如鸡”的牢狱生涯,不仅使其备受摧残,更增添了内心的“无常”、“幻灭”之感,从而促发了他重新省思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抵黄州后,他常杜门却扫,反躬自省,“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文集》392)从此觅得锄其本、耘其末的自新之方——归诚佛教,并自号“东坡居士”,且“常着衲衣”(惠洪2204),开始了“如实修行”的习禅生涯。
苏轼因文字而坐狱,至黄州后仍如惊弓之鸟,忧谗惧祸,“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文集》1752)又为待罪之人,不便随意行游,“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文集》1567)因此,黄州四年诗歌数量仅184首,游寺诗17首,分别为元丰三年13首,四年3首,七年1首。
元丰三年的13首游寺诗,有8首为初至黄州所作,呈现出苍凉、悲寂的格调。这些诗歌写景的笔墨明显减少,寄怀抒慨的成分增加,即便是寺中赏花,寄寓的也是身世感慨:“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1035)、“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1037)。但苏轼绝非自我沉沦者,为摆脱内心的困顿,他归诚佛教,涤除是非,安顿身心。作于赴黄州途中的《游净居寺》,他反复陈说归佛之愿:“稽首两足尊,举头双涕挥”(1025)、“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1026)。他甚至叹闻道之晚:“嗟我晚闻道,款启如孙休”(1018),“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1170)。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归诚佛教的初衷并非为解脱生死,而是期获静达之心,他在《答毕仲举二首》中言:“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文集》1672)因此,他“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1108),着眼于佛教“安心”之用。
如果说倅杭时期,苏轼游寺诗中表达的“空观”“无常”思想多指向他者或外物,那么黄州时期则是慰藉心灵,指向自我。例如,《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其二)》曰:“寒泉比吉士,清浊在其源。不食我心恻,于泉非所患。嗟我本何有,虚名空自缠。”(1045)以“寒泉”自比,用《易经》“井渫不食,为我心恻”谓寒泉本自清净,而我本空无,何以自缚于虚名?用“诸色皆空”之理,劝诫自我。又如《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一诗,先写孙郎石、陶公柳皆如飘渺云水,消散于历史时空之中,弥漫着浓厚的空幻意识;继而转向自我:“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所须修竹林,深处安井臼。”(1050)相比于倅杭时期,他的归隐之志也更为坚决,所言佛理也更注重于自我心灵境界的构建。
黄州时期的苏轼对佛禅义理的参悟,较以往也更进一层。例如,他的游寺诗多次写到寺院澡浴,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意趣。熙宁五年七月的《宿临安净土寺》云:“晚凉沐浴罢,衰发稀可数。”(345)只写沐浴的行为,无关佛理。熙宁六年八月的《宿海会寺》曰:“杉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497)用《维摩诘经》“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维摩诘经》155)之意,言澡浴兼具洗身、洗心之功用。而元丰三年所作《安国寺浴》云: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烟雾蒙汤谷。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1034)
苏轼由“洗身”而悟出的“洗心”之法,实际就是洗去“净秽”、“荣辱”之念。然身垢易洗,心垢难除。“心困”两句用《维摩诘经》“唯置一床,以疾而卧”(97)典故,阐明“洗心”之法应心无所住,彻悟色空不二、无待至乐之理。此诗之意,恰如同年所作《胜相院经藏记》云:“愿我今世,作是偈已,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文集》389)这三首游寺澡浴诗,随着时间、境遇的变化,阐发的意趣明显不同,从洗身之垢到洗心之垢,再到洗净垢、荣辱之执,这种变化体现了苏轼对于佛教义理渐次深入的事实。
黄州游寺诗虽仅有3首诗援引佛典,但侧重于佛教义理的阐说,且较多用事典,更显精确、圆融。例如,《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云:“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1085)纪昀评曰“竟是偈颂。”(纪昀1917)“何处”句实脱化于《楞严经》卷五:“月光童子[……]我有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236)是借月光童子修习水观之事,言己谪黄而得清净之心。“四方”句则契合《楞严经》“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236)之“水天”,不着痕迹。
黄州时期,苏轼运用佛禅文化来反观自省,用是身如幻、一切皆空的理论来洗心,以求心不染物,断除妄念。安国寺五年的暮旦往还,似乎使他终获“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文集》392)的心境。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言:“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文集》1671),他的游寺诗也反映了内心“杂草”旋去旋生的事实。例如,作于元丰七年的《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一诗,先写“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1190),继而发出“平生所向无一遂,兹游何事天不阻”(1190)的哀叹。苏轼虽努力忘净秽、洗荣辱,欲臻至无心之境,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黄州之后,元祐之前,一年之多,苏轼辗转多地,诗作共计204首,游寺诗26首,游览寺院16所。游寺诗关涉佛禅虽不多,但明显更显圆融、成熟。例如《赠东林总长老》,“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1218—19)首二句,用《法华经》:“世尊[……]现大神力,出广长舌”(《法华经》442)中的意象,阐述佛教义理无所不在,暗合“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之意。“八万四千偈”出自《楞严经》:“八万四千烁迦罗首[……]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八万四千清净宝目。”(260)言佛家法轮日月运转,浩荡无垠。再如《题西林壁》,亦是书写游寺之悟,纪昀评:“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尚不取厌。”(纪昀1924)相对于此前的禅偈诗而言,这两首诗从借佛语说理,转化成以禅悟达理,更富理趣。
元祐时期的八年内,苏轼作诗570首,游寺诗30首,所占比例为5.26%,游历寺院15所。游寺诗数量急剧下降,而实际当时汴京的寺院并不少。究其原因,苏轼此期“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文集》699),王事鞅掌,无心游寺,自言“老病不复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于外。”(《文集》1870)因而所作之诗主要以应酬、唱和、赠答为主,“交际性的诗歌占其此时期作品总数的80%以上”。(“诗可以群”131)此期的游寺诗亦多唱和之作,较少涉及佛禅,甚至在杭州一年余,所作仅10首,也基本属于游玩赏物之作,其中最具佛禅色彩的《观台》一诗,则被纪昀讥为“五六九僧一派。”(纪昀1945)无论是数量还是与佛禅的融摄程度,都远不及倅杭时期。正如苏轼自云:“经年不闻法音,径术荒涩,无与锄治。”(《文集》1870)苏轼与佛禅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凤翔时期,但实质上更表明了他的禅悟进阶充满着法缘与俗缘的反复纠葛,顺、逆之境深刻地影响着他与佛禅的距离。
三、岭海时期: 即心即佛,无思之思
绍圣元年,苏轼谪知英州军州事,后累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已近耳顺之年的苏轼,再贬至“九死南荒”之地,对佛禅又有了新的领悟,游寺诗的创作亦呈现出新的特征。
绍圣元年八九月间,苏轼过大庾岭龙泉寺,题诗于寺钟曰:“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2057)一念顿悟,本性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正,这是南宗禅倡导的“佛性即自性”的诗意呈现。黄州时期,苏轼执着于觅求“安心法”,实则为“逃世之机”,而此时他“身世永相忘”,已无是非之想。不久,苏轼再入曹溪,礼六祖惠能真身,作《南华寺》诗云: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2061)
首二句点明礼佛之意在于“识本来面”;次用《坛经》“惠明求法”(27—30)《楞严经》“指月眩目”(63)典,言己了知万法,不为外物所迷;“我本”以下诸句,触境寄感,既抒写了笃实修行的宏大誓愿,又表达“今是昨非”之恨。全诗情真意切,表明他的习佛进阶已逐渐从洗净秽、去荣辱,上升到对“本来面目”的觅求。绍圣元年十月在惠州嘉祐寺,苏轼立有“思无邪斋”,且作《思无邪斋铭》,其并叙曰:
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文集》575)
所谓“有思而无所思”,即“无思之思”,心无外物,是一种抛去功利、拟议、作用、语言之思。这与沩山灵祐开示门人之语:“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普济527)之意,颇相契合。沩山灵祐认为,“思无思”可返观自我之“灵焰”,识得本心,从而达到理事不二的真如境界。次年,苏轼又作《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云:“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文集》390)究其实,“无思”乃佛家“无念”之意,即去除妄念,摆脱相念之执,性相一体,圆融无碍。
苏轼觅得以“无思之思”之法来探寻“本来面目”,游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岭南蛮荒,九死一生,但他的游寺诗却极少悲愁、孤寂之象,反而呈现出怡然自得、随缘任运的情调:“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2112)、“我行无迟速,摄衣步孱颜[……]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2063—64)他俯仰人生、天地、宇宙,无不以一种“无思”“无待”的态度视之:“嬉游趁时节,俯仰了此世”(2099),“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2195—96)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苏轼的寺院书写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29首中有近20首纯写游赏之乐。他不再刻意使用佛经语汇和经教义理,而是将佛教的思想经义内化为一种生活情调、价值取向,将佛理融摄于诗中,书写“无思之思”的精神状态,表达主体的精神自足。表面上看,这与凤翔时期写景记游的游寺诗很相近,但实有本质之別,是他“即心即佛”后的大彻大悟,寺院纯为客体景观,不着半点主观色彩,这颇类于青原惟信“见山是山”的第三重境界。
绍圣四年苏轼再谪儋州,三年中诗作共133首,但游寺诗仅《入寺》1首。揆其原因,盖儋州地区寺院较少之故。据刘正刚先生考察,宋代海南佛寺凡26所,而儋州仅开元寺、光孝寺、凌霄庵3所。不过,这首《入寺》亦值得注意:
曳杖入寺门,辑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多生宿业尽,一气中夜存。旦随老鸦起,饥食扶桑暾。光圆摩尼珠,照耀玻璃盆。来从佛印可,稍觉魔忙奔。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2283)
首四句,先述入寺礼佛,转言自己为“玉堂仙”,流露出道家思想。次四句,返观自照,从佛教角度言己宿业已尽,习以道家养生之法。“光圆”以下四句,王文诰案“谓光明透彻,无所不了也”,言己参透佛禅,心魔消散。末四句,写自我心境,无欲无求。此诗融摄佛道,以道家养生之法而达无思无欲的佛禅境界,可谓“仙山佛国本同归”(2267)。
绍圣四年七八月间,苏轼至儋州,“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名曰“桄榔庵”,并摘叶书作《桄榔庵铭并叙》。在这篇铭文中,苏轼澄怀观道,“神尻以游”,跳脱“百柱屃屭,万瓦披敷”草庵之缚累,无顾于“海氛瘴雾”“蝮蛇魑魅”之侵凌,俯仰宇宙,“以动寓止,以实托虚”,不仅抒写了豁然旷达的情怀,更表达了识得“本来面目”的体验:“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文集》570)苏轼用了禅家常用的“非非”句式,破除了对名实、动止、虚实、欠余的知解执著,认识到万事万物皆平等如一,从而达到心不住相,永息诸念,回归到最初真如佛性之状态,由“即心即佛”而达到“非心非佛”的境地。
元符三年五月,苏轼再移廉州安置,后北归,作诗94首,游寺诗16首。此期的游寺诗很明显的表征是频用佛典,占此期游寺诗比例的75%。所用佛典多出僧传、灯史,其中《景德传灯录》8次,《五灯会元》3次,涉及禅宗公案多达13处。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苏轼对灯录、佛经了熟于心,信手拈来;另一方面这些诗歌多为与僧人、习佛之士的赠答、戏和之作,故常用佛典以切合赠答对象。例如《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除“道人有句借宣扬”外,其余7句皆引佛典,广涉《景德传灯录》中诸多禅宗公案,如鹫岭善本禅师“水浴无垢”(道原1286),古灵神赞“蝇子投窗”、“佛放光”(道原591),石霜庆诸“遍界不曾藏”(道原1085),南泉禅师“寸丝不挂”等公案(道原494),以及《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子说圆通偈一事(《楞严经》264—69),跋陀婆罗并同伴十六开士于浴堂忽悟水因,于熏笼焙浴具,得大安乐之典。(《诗集》2448—49)皆信手拈来,足见其对僧传、语录的谙熟程度。苏轼前期的游寺诗援引佛典多为言说佛法,而此期或为戏赠他人,或抒写自我心境,或延及万事万物,这可谓游戏圆通,左右逢源,故查慎行评曰:“尽用禅家语形容,可谓善于游戏者也。”(《苏诗补注》1360)
岭海时期,实质也是苏轼人生历程的最后阶段。数十年的游寺、参禅、悟道,不仅使他获得了精神慰藉,炼明心志,更使他能以一种“无思之思”如实修行,彻见“本来面目”,对佛教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认同。这种认同首先体现在身份上的认同。苏轼“前世为僧”之说,始于元丰七年。是年,他赴筠州省弟,与云庵禅师、聪禅师说梦,“自是常衣衲衣。”(惠洪2204—2205)绍圣元年谪英州,苏轼遣书佛印,中云“戒和尚又错脱也”(惠洪2202),视己为戒和尚。绍圣二年,于惠州作《答周循州》曰:“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2151)绍圣三年,《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四)》中言己:“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2208)后再贬琼州,又称自我是“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苦行僧”(《文集》1841)。北归游灵峰寺,“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2401),以得道高僧德云自比。后复官,监玉局观,作偈曰:“却着衲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惠洪2202)尽管都是述说自我是僧,但皆随苏轼对佛禅的体悟程度而变化,从最初的自疑为僧,着衲衣,进而认定为“卢行者”“行脚僧”“苦行僧”,最后自比为得道高僧“德云”,“自疑身是五通仙”,可见苏轼佛禅境界的渐次上升。
四、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类型
综上所述,苏轼对佛禅的接受、领悟的进阶,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他的游寺诗之中: 凤翔时期,因“不知禅味深”,游寺诗基本未涉佛禅;倅杭期间,因彼地浓郁的佛禅氛围以及文人禅悦之风的兴盛,苏轼积极地访僧寻寺,所作之诗开始营构禅境,演绎佛理,甚至带有“禅偈气”;贬谪黄州,因身心俱创,终日宴坐佛寺,归诚佛教,游寺诗处处言禅;岭海时期,苏轼已逾耳顺之年,转而内求本来面目,游寺诗常以“无思之思”书写自我对佛禅的感悟,最终完成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
苏轼思想融摄儒、道、释三家,历来被视为北宋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作诗文最能凸显彼时的文化风尚。他的游寺诗不仅直接反映了熙宁、元祐间文人极盛的禅悦之风,更饶有兴味的是,其不同阶段的游寺诗亦基本代表了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风貌。根据诗人的创作心态及诗歌自身的特质,综括言之,北宋游寺诗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 纪实绘景型
此种类型与苏轼凤翔时期的游寺诗颇为相类,寺院往往纯为文人游赏的客观场域,宗教意涵非常薄弱。这是游寺诗最基本的创作类型,贯穿于北宋各个时期,尤以北宋初期最为突出。
宋初文人尽管身份殊异、思想有别,但他们的游寺诗除了极少数书写羁旅之情、寺院历史、集会宴饮外,绝大多数以摹绘景物为主,率皆等同于通常的山水游览诗,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特征: 首联一般叙写行程,中二联着力绘景,末联言归隐、恋景之意。例如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云:“底处凭阑思眇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全宋诗》1213)所写茂林、良田、孤鸟、夕阳、寒烟诸景,皆寓目所见,真实可感,但与佛禅并无直接关联,诗题中的“孤山寺”,完全可以置换为某个亭台、楼观,而诗意、诗境不会有太大变化。再如,田锡《题天竺寺》、潘阆《秋日题琅琊山寺》、赵湘《题国清寺》、寇准《游花岩寺》诸作,亦皆如此。尽管有的文人如潘阆、赵湘等,诗中之景颇含空寂、幽静之味,但究其实,这并非因之于佛教精神的影响,而是山水清音洗郁的结果。
宋初文人游寺诗的这种风貌,直接反映了他们与佛禅的关系。“会昌法难”,像教陵夷,唐末五代虽逐渐走上复苏,但宋初奉佛文人并不普遍。清人彭绍昇《居士传》仅辑有杨亿、李遵勖晁迥、王随四位宋初居士,而且他们亦未认真思考诗与禅的相通机制,诗与禅实际仍处于一种疏离状态。杨亿堪称宋初最著名的佛教居士,曾刊定了《景德传灯录》等禅门文献,深悟禅观,《五灯会元》甚至将他列于广慧元琏禅师法嗣。但读他仅有的4首游寺诗,像《留题南源院》《留题黄山院》《题显道人壁》皆无关佛理,而《大中塔》则纯为绘景,舂容典贍,犹未脱台阁之气。其余像徐铉、钱惟演、张咏等诗人的游寺诗,更与佛禅精神相距甚远。此正如周裕锴先生所言:“直到北宋文化发展到鼎盛,出现文化整合思潮时,诗歌和禅宗相融的潜在可能性才变为现实性,诗人才真正从参禅活动中受益。”(《文字禅》48)
这种“以寺院作为客观场域”的创作类型,主要是出自受佛禅浸染不深的诗人之手,在北宋中、后期仍比较普遍,例如曾巩、欧阳修、范纯仁、毕仲游等人的游寺诗。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寺院除供奉三宝、安禅弘法等宗教功能之外,因其遍布于通都大邑、山林爽垲,还兼具避难、读书、客宿、雅集等功能,这些功能大大地拉近了它与世俗之间的距离。文人游寺或为消除劳顿,或因读书修业,或是奔赴雅集,寺院的宗教功能反而被遮蔽,他们的游寺诗关注的焦点自然不会是宗教本身。
(二) 阐理写心型
庆历年间,儒学复古思潮兴起,文人皆倡道统,辟佛老。契嵩作《原教》、《辅教编》等文,明儒释之道一贯,护法辅教,厥功至伟。尝诋佛教为“夷教”的欧阳修亦尊礼之,并在居讷中敏的循诱下,最终潜心向佛,自号“六一居士”。欧阳修前后态度的变化,意味着宋代居士佛教发展的重要转向。自此之后,儒释互渗互融的局面渐开,文人耽于释典,禅悦之风大盛。寺院的宗教意义逐渐突显,游寺诗的书写亦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方面是以禅入诗,阐发佛理;另一方面是书写游寺参禅的内心体悟,有两种表现途径,一是通过营构禅境,表现禅悦之思;二是书写参禅后的心境及以佛安心的愿望。这种特征,与苏轼在杭州、黄州时期的游寺诗创作比较接近。
宋初的游寺诗基本不涉佛典。但至北宋中后期,禅门语录、僧传、灯史频出,“文字禅”渐盛,文人们谙熟于各种佛教典籍,在游寺诗中援引佛典、公案的现象就显得比较普遍,甚至一诗中用多个佛典,像秦观《圆通院白衣阁(其一)》、李廌《少林寺诗》、黄庭坚《题吉州承天院清凉轩》、苏轼《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等诗。这些文人对于佛典的运用,还不止停留泛化的层面,而逐趋深层次地诗禅一体,形式上也非常接近禅偈。像黄庭坚《戏题葆真阁》:“真常自在如来性,肯綮修持祗益劳。十二因缘无妙果,三千世界起秋毫。有心便醉声闻酒,空手须磨般若刀。截断众流寻一句,不离兔角与龟毛。”(黄庭坚1636)此诗句句用佛语、佛典,涉及《传灯录》《楞严经》《法华经》《长阿含经》《维摩诘经》诸经,于语言文字中,游戏三昧,横说竖说,不可纯以诗格绳之。此外,王安石《题半山寺壁二首》、李复《题大圆庵二首》、彭汝砺《云盖寺谈空亭》《法轮院》等,亦皆通篇用佛典明理,弥漫禅偈之气,充满禅机禅趣。
除了表达禅学见解外,文人们还经常书写游寺时的感悟。一种表现即在诗中营构禅境,表达法喜禅悦。这类诗歌表面上看与“纪实绘景型”相类似,旨趣却不尽然。“纪实绘景型”的游寺诗歌重点是表现“自然”,乐景闲适;而此类诗歌虽通篇绘景,但实为“写心”。这些诗歌多出于那些虔诚向佛的文人之手,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王安石。王安石早年为官时,即频游寺庙,广交禅僧;晚则退居金陵,遍游钟山诸寺,且舍宅为寺,注《楞严经》、《华严经》等经,深通禅理。其晚年所作游寺诗常藉景抒怀,营构清幽、空寂之境,书写禅悦的风致。例如《定林院》:“漱甘凉病齿,坐旷息烦襟。因脱水边屦,就敷岩上衾。但留云对宿,仍值月相寻。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王安石517)诗中既描写了寺中清景,“枕石漱流”之中,更表现出诗人物我两忘游憩之乐和旷达的胸襟。再如《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其二)》云:“独寻飞鸟外,时度乱流间。坐石偶成歇,看云相与还。”(王安石579)似有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禅境。另如王安石《游草堂寺》《台城寺侧独行》、文同《吉祥院》、张耒《寺西闲步》等诗,皆寓禅味于自然景物之中。另一种表现则是抒发游寺参禅后内心的超脱及以佛法安顿身心的愿望。例如,郭祥正《游鹿苑寺》“烦心沃醍醐,顿悟超十地”(《全宋诗》8847),李复《周巨寺》“金篦刮病膜,清冰沃烦肠”(《全宋诗》12413)等,都肯定了游寺参禅涤除心垢的功用。正如张方平《游琅邪山寺》所云“俗游殊不意,僧话粗宽心”(《全宋诗》3856),文人们游寺不再是“俗游”,而是一种“精神之游”,期望通过参禅问道来澡雪精神,清净内心。然而,这种希冀从高僧言语中开悟的安心之法,仍是以佛为用,向外觅求,此正如《五灯会元》卷十二守芝禅师所言:“向言中取则,句里明机,也似迷头认影”(普济708),终非第一义谛。
(三) 明心见性型
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游寺诗书写识得本来面目后的自适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领悟,类似于苏轼岭海时期的游寺诗。表面上看,寺院在诗中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诗人游寺的目的既非礼佛赏景,亦非借佛洗心,而是返诸自我,省察内心。例如,“鹿门居士”米芾的《登米老庵呈天启学士》云:“我居为江山,亦不为像法。劫火色相空,未觉眼界乏。屹然留西庵,使我老境惬”(《全宋诗》12261),米芾参悟了“万法皆空”“像法”亦空,故所求惟自性之惬意,而非佛法。其游润州甘露寺,作《净名二首(其一)》云:“依静家如寺,游频寺是家。何须傅大士,芰制著袈裟。”(《全宋诗》12251)禅家常以“家”比喻“自性”,此处“家”亦象征“自性”,“寺”则指代佛法,米芾以为只要“自性清净”,家即是寺,寺即是家,非家非寺,这与苏轼在《桄榔铭》所说的“无作无止,无欠无余”是同一层意思。
北宋中后期的居士文人参悟佛法日益精深,一些游寺诗开始书写彻见真如本心的体悟,非常接近禅家的悟道偈。例如李之仪《浴南寺园头求诗》曰:“一重洗尽一重生,尘垢昏人不自醒。会得栽茄种瓜意,始知松竹本来青。”(《全宋诗》11198)前两句是针对神秀禅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而言(《坛经》10),否定向外求法,渐悟成佛的可能;后两句中的“栽茄种瓜”则隐含“触类是道而任心”之意,“松竹本青”则暗喻人自性清净。此诗之意即向外求佛实是逐物迷己,应向内明心见性。

游寺诗书写明心见性的感悟多集中于北宋后期,这一方面是他们涉佛之深的体现;另一方面,此一时段党争愈发激烈,促使文人转向对自我命运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理学蓬勃发展,与佛禅互渗互融,与传统儒学相比更注重道德、心性的内省来澄明生命的意义,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文人对自我心性的省察,这种种机缘,促进了文人对真如本性的体认,也从整体上提升了北宋游寺诗的品格。
总之,从时段上看,北宋文人游寺诗大体经历了这三种类型的发展过程: 即宋初以“纪实绘景型”见多,中后期则以“阐理写心型”为主,同时也出现了“明心见型”。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种类型发展仅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并非严格的线性发展。就具体的诗人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就像苏轼一样,随着其习佛进阶的提升,这几种类型可能皆涵括在他的创作之中。
余 论
寺院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大抵相当于西方社会中的“教堂”,都是导人信仰、传播教义的“宗教场域”。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寺院还兼具读书、客宿、雅集、游赏、救济等功能,实为连结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公共场域”。处身于这种“场域”之中,不管是宗教徒,还是非宗教徒,因受宗教力量的感召,都会或多或少获得一种不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和境界。他们常将这种情调、境界诉之于诗歌,表达自我对宗教精神的认知和体悟。本文通过梳理苏轼不同时期创作的游寺诗,不仅可以窥见其禅悟的进阶,而且表明游寺诗的创作风貌实质取决于诗人对佛禅体悟的程度。可以说,游寺诗是探讨个体文人甚至某个时段的文人奉佛的绝佳视角,其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重视。
注释[Notes]
① “游寺诗”一词,最早见于释皎然《诗议》:“如游寺诗,鹫岭鸡岑,东林彼岸。”《文镜秘府论》南卷引释皎然《诗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44—45。目前学界尚无对“游寺诗”的统一界定。我们认为,诗题中凡出现“止宿”“游览”“过”寺院、僧舍、招提、精舍者;诗题中有“访僧”“题寺壁”等字眼者;诗题虽未出现以上字眼,但明显写寺院风物者,皆可视为游寺诗。
② 赵德坤、周裕锴“济世与修心: 北宋文人的寺院书写”,《文艺研究》8(2010): 63—69。目前关于苏轼游寺诗的论文有: 施淑婷“苏轼参访寺院之因缘”,《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1(2009): 31—66,主要探讨苏轼游寺之因缘;贾晓峰“苏轼黄州寺院诗的新变”,《内蒙古大学学报》5(2016): 100—105,将黄州寺院诗与前期寺院诗对比,探究苏轼黄州寺院诗在内容上、情感强度上及意象营构上的变化。
③ 本文数据统计以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2年)为蓝本,除去卷四十六帖子词口号65首。
④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传尝读书连鳌山栖云寺及三峰山、实相寺、华藏寺”(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40。
⑤ 梁银林《苏轼与佛学》,2005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
⑥ 李翥纂辑《慧因寺志》卷六,白化文、张智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第56册(扬州: 广陵书社,2011年)69。
⑦ 此诗在外集编卷四倅杭诗中,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皆从之。王文诰注本删去不收,底本补编于卷四十七。王文诰删此诗并无根据,本文据外集、查注、冯注移至倅杭时期。
⑧ 黄启江《北宋汴京之寺院与佛教》一文考察后认为:“宋室南渡之前,汴京寺院约有九十所”,载《北宋佛教史论稿》(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100。
⑨ 刘正刚“宋明海南佛寺与佛教世俗化研究”,《古代文明》3(2017): 97—108。
⑩ 袁衷等录,钱晓汀: 《庭帏杂录》卷下。(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1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道原: 《景德传灯录译注》,顾宏义译注。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Daoyuan.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Tran. Gu Hongy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0.]傅璇琮等编: 《全宋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Fu, Xuancong, et al., eds. Complete Poetry from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黄庭坚: 《黄庭坚诗集注》,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北京: 中华书局,2003年。
[Huang, Tingjian.An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Huang
Tingjian
’s
Poetry
. Eds. Ren Yuan, Liu Shangrong,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惠洪: 《冷斋夜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Huihong.Night
Talks
of
the
Cold
Studio
.General
Views
o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Literary
Sketches
. Ed.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纪昀: 《苏文忠公诗集》,《苏轼资料汇编》,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北京: 中华书局,1994年。
[Ji, Yun.Collected
Poetry
of
Su
Shi
.A
Sourcebook
of
Su
Shi
. Ed. Sichuan University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Research Depart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孔凡礼: 《苏轼年谱》,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
[Kong, Fanli.A
Biographical
Chronicle
of
Su
Shi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普济: 《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4年。
[Puji.A
Compendium
of
the
Five
Lamps
. Ed. Su Yuanle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苏轼: 《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2年。
[Su, Shi.Collected
Poetry
of
Su
Shi
. Eds. Wang Wengao and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苏轼: 《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Su, Shi.Collected
Essays
of
Su
Shi
. Ed.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苏辙: 《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校点。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
[Su, Zhe.Collected
Works
of
Su
Zhe
. Eds. Chen Hongtian and Gao Xiuf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坛经》,赖永海主编,尚荣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
[The
Platform
Sutra
. Eds. Lai Yonghai and Shang R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法华经》,赖永海主编,王彬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
[The
Sutra
of
Saddharmapundarika
. Eds. Lai Yonghai and Wang B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楞严经》,赖永海主编,刘鹿鸣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
[The
Sutra
of
Surangama
. Eds. Lai Yonghai and Liu Lum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维摩诘经》,赖永海主编,高永旺、张仲娟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
[The
Sutra
of
Vimalakirti
. Eds. Lai Yonghai, Gao Yongwang,and Zhang Zhongj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王安石: 《王荆文公诗笺注》,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Wang, Anshi.An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Wang
Anshi
’s
Poetry
. Eds. Li Bi and Gao Keqi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赵翼: 《瓯北诗话》,《清诗话续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Zhao, Yi.Poetry
Commentaries
of
Oubei
.A
Sequel
to
Qing
Dynasty
Commentaries
on
Poetry
. Eds. Guo Shaoyu and Fu Shous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查慎行: 《初白庵诗评》,《苏轼资料汇编》,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北京: 中华书局,1994年。
[Zha, Shenxing.Poetry
Commentaries
in
Chubai
’s
Hut
.A
Sourcebook
of
Su
Shi
. Ed.Sichuan University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Research Depart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 《苏诗补注》,王友胜校点。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3年。
[- -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to
Su
Shi
’s
Poetry
. Ed. Wang Yousheng.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3.]周裕锴:“诗可以群: 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5(2001): 129—34。
[Zhou, Yukai. “Poems Teach the Art of Sociability: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Yuanyou-style Poem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 (2001): 129—34.]——: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 - -.Literary
Zen
and
the
Poe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7.]周紫芝: 《竹坡诗话》,《历代诗话》,何文焕辑。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
[Zhou, Zizhi.Poetry
Commentaries
of
Zhupo
.The
Poetry
Commentaries
Through
Ages
.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附表一: 苏轼游寺诗数据统计

时间诗歌总量游寺诗数量寺院数量游寺诗所占比例援引佛典诗歌数量援引佛典诗作数量占游寺诗比例凤翔前期78222.56%00凤翔时期138181113.04%316.67%凤翔后杭州前1900000杭州时期354794122.32%1417.72%密州时期142553.52%00徐州时期205914.39%111.11%湖州时期7415520.27%640%黄州时期1841769.24%317.65%黄州后元祐前204261612.75%415.38%元祐时期57030155.26%516.67%惠州时期199291314.57%517.24%儋州时期133110.75%00北归至金陵94161217.02%1275%补编、辑佚、他集互见36419125.22%15.26%诗歌总量27582661409.64%5420.3%
(注: 本文以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为蓝本。诗歌总量除去卷四十六帖子词口号65首。据《苏轼年谱》,《苏轼诗集》补编、辑佚、他集互见部分移动情况: 《题李景元画》、《游灵隐寺戏赠开轩李居士》、《题双竹堂壁》、《会双竹席上,奉答开祖长官》均移至倅杭时期;《宿资福院》移至黄州后元祐前;《惠州灵隐院,壁间画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隐峦所作,题诗于其下》移至惠州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