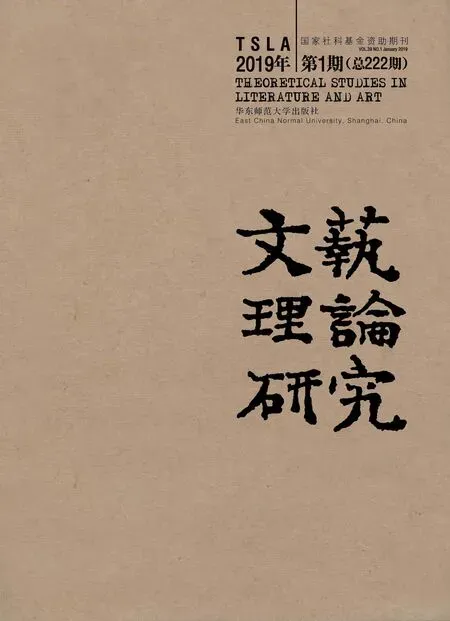从诗史名实说到叙事传统
董乃斌
一、辨“诗史”名实
笔者近年研究中国诗歌叙事传统,拟以“抒叙两大传统贯穿文学史”之观点破解“抒情传统唯一”的说法,补正其偏颇,因而自然关注到诗史问题的讨论——归根到底,“诗史”的核心乃是与抒情“对垒”的叙事,诗史传统实即与抒情传统共生并存的叙事传统。既如此,论说叙事传统又怎能离得了“诗史”?
关于“诗史”的言说,在中国诗歌史和诗学史上,可谓触目皆是。直至今日,相关言说和歧议仍然非常之多。在众多歧说中,劈面遇到的便是“诗史”的名实问题,故不能不先来稍加辨析。
诗史二字组联成词,习惯的说法是起于晚唐孟棨的《本事诗》,或更早一点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事实是否如此?我以为不妨打个问号。
按常识,任何事物总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诗史”一名亦当在诗史的事实存在且逐渐被人认识之后才会产生。今知“诗史”常用之义有二,一是诗歌史的简称,一是对具有史性特征之诗歌作品(或诗人)的指称。前者事实清楚,名实相符,没有争议,故得通用。后者则须先有了颇具史性而堪称“诗史”的诗篇,从而显示出诗歌与历史的密切关系,才会使人的意识逐渐产生“诗史”的观念,并逐渐凝聚为“诗史”概念和名词,再后来这观念和名词才会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认识和实际应用常处变动之中,情况复杂,导致“诗史”之实与名的契合难以稳定,更无从统一,而表现为对“诗史”解释之见仁见智、歧见纷纭,甚至于或拥护或否定乃至批判的状态。
沈约书中的“诗史”是诗与史的并列,可以勿论;孟棨其实也不是“诗史”概念的真正创造者。作为某些学人奉为“诗史”出处的《本事诗·高逸第三》之首条,大段讲述的是李白的高逸行为,多次引录的是李白的诗篇,在铺叙了七百多字之后,才终于提及杜甫的“赠李白二十韵”,但仍未引其文,仅云“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孟棨14)。这之后,才是我们在前面注文中所引那句含有“诗史”二字的话,总共不到三十个字。这个表述清晰显示了孟棨整个叙述的主次,显示他几乎只是顺便地提及、转述了“当时”对杜甫诗歌的议论。当然,虽是简单一笔,却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此种无心栽柳柳成荫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在学术史上,并不罕见。但由此可知诗史的事实早已存在,诗与史的密切关系早为人们所关注,“诗史”概念早在潜滋暗长,“诗史”之名早晚要出现。这是一种必然性,至于它究竟见于今日留存的哪个文献,却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这偶然性在杜甫身上得以落实,却又有深刻的必然之理。
《本事诗》对杜甫诗史的阐说反映了孟棨对当时已存在的“诗史”概念之理解,正如我们今日谈论“诗史”,所谈的也只是我们的理解而已。谁的理解也不能成为“诗史”的标准定义,更不存在一个经典的不可违拗的所谓“本义”。事实上,“诗史”之名虽然产生,但在文学批评的运用中,“诗史”的含义又是在人们的理解中继续生成并演变着的。“诗史”概念具有某种开放性,“诗史”的实际运用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又有相当的随机性。同时,“诗史”既可以是对诗歌事实的指称,也能够成为诗人自觉期许的目标,因此既可以是他称,也可以是自称。杜甫的许多诗篇无疑够格称为“诗史”,但也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是“诗史”,当然“诗史”亦非杜甫一人的专利。文学史和批评史实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窃以为既不能把“诗史”名称的发明权归诸孟棨,也不必奉孟棨《本事诗》为经典,而应实事求是地将《高逸第三》之首条看作一位唐人对“诗史”的理解,亦即“诗史理解史”上的一个环节。然后立足文学史实,斟酌古今,因应时变,参与到对“诗史理解史”的延续运动中去,探索今日能为更多人理解接受和运用的诗史概念,努力把研究推向深入。
说到“诗史”之名产生的必然性,当然首先应该注意到中国诗歌的历史事实,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也是研究的正路。我们只要认真阅读留存至今的古代诗歌原典,比如《诗经》,便不难发现许多诗篇的叙事性,发现它们的叙述咏叹与历史(历史事件和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篇,《小雅》中的《六月》《采芑》《出车》《节南山》《十月之交》等篇,国风中《新台》《载驰》《硕人》《清人》《南山》《黄鸟》《株林》等篇,古人早已反复证实其叙事内容的实在性、历史性,今人也认为它们与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有关。说这些作品具有某种“史性”,堪称“诗史”,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如其不然,试问又该如何切合其内容的性质给它一个简洁准确的名称呢?倘若我们能够不因曾将西方的epic译为“史诗”,就非得以西方的epic奉为史诗的唯一标准,那么甚至不妨称它们为“史诗”也无不可。这些作品的存在就是“诗史”概念和名称产生的真正根源和依据。后人,特别是汉人对《诗经》作品的研究理路,如《毛诗》小序大序和许多汉唐人的注疏直至今人的注释所显示的,也充分表明他们确信诗歌与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
再进一步说,原来,在中国,从我们的人文初始时期,诗与史还曾有过一个浑融一体的阶段。那时文字尚未成熟,应用很费劲而不普遍,人的认识水平低下,史识犹浅,有诗心而缺史德,以致诗、史皆已萌生滋长而却彼此不分,可以互代。诗(文)和史由浑沌不分到明确分开,是人类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发生的事。而且,即使到有人认识到文史应该分家,并从各方面努力使它们得以分开之时,却仍很难彻底割断二者的关系。甚至直到今天,文史早已俨然为分庭抗礼的两大学科,然文(也包括诗)史在某些方面依旧浑然难分,从而被认为是学术上的一个大问题。文与史似乎总有一部分是兼体的。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所谓文和史,都是人类智力创造物,又都离不开文字的表述传达,二者本有许多内在的同一性。所以文史难分很可能是一个将要伴随人类存在之始终、人类自身所不可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既然诗与史有过一段浑然不分的经历,“诗史”或“史诗”便是人类实践的一种产物,也就是一种历史事实,一种客观存在,一种无法漠视的现象,那就早晚会在人的思维、语言和文字中反映和表现出来。“诗史”这个词迟早是一定会在中国出现的,只不过在现存哪个朝代的文献中发现这个词,却有些偶然性而已。
中国人确实很早就发现并论说了诗史关系的密切——因为,在上古,文字产生并成熟之前,它们一度曾是二位一体的混沌存在。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战国后期)的《孟子》,其《离娄下》有云:
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之矣。”(孟轲 192)
这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对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王者之迹”指什么?何谓“王者之迹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应怎样理解?句中的“诗”字,是泛指的诗,还是作为专名的《诗》?“诗亡”又该如何解释?等等,都有不同说法。但无论怎样理解,这句话涉及古人对于诗与史存在密切关系的看法,应该是清楚的。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做些思考,引出几点认识:
第一,孟子所言涉及了我们所关注的诗史关系。他的意思似乎是“诗亡”之后,“史”才全面、正式地出现(没说此前是否有“史”,但事实上是有的)。这里的“诗”指《诗三百》的可能性较大,此前的诗歌肯定还有,但缺少可靠的文本依据。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诗史”,谈诗与史的关系,谈诗歌叙事传统,为此提出实证,如果鉴于种种困难暂不再向前追溯,那么,起码也应从《诗经》开始。
第二,孟子虽没有明说“诗亡”之前的诗是“诗史”或诗中有史,但从这话的语气来看,实乃隐含这层意思。即以为《诗三百》(应该还包括《诗》成书时被删落以至后来逐步被遗忘的那些诗)都曾经是一种史述或至少含有史述的意味。在那时,虽然列国已有自己的史官、史记,但这些诗也是被当作“史”的一部分。其时,诗与史的区别主要不在其内容,而在其形式与表达。诗记政治大事,也记生活琐事,诗的语言(文字)允许夸张隐喻,还可有比兴手法,史文则更强调直笔和朴实(虽实难避免形容和虚饰),“其文则史”,这个“文”是和诗同时而相对地存在着的。诗与史,无论作为文体还是学科,在后世是被分开了,但“诗史”一词却仍把二者联为一体。这时“诗史”则是指文学性的诗歌与历史性的史述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体存在着密切关系,“诗史”也好,“史诗”也好,其词的重心都是在于“诗”,主要是指那种具有浓厚史性质地的诗歌(或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诗史或史诗都是指文学作品(而非历史著作);而所谓“史性”,其内涵与实质,无非是以接近实录的态度和直笔的手法表现和记叙现实、时事、新闻——从社会的一般日常生活、各行各业、人际琐事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直至改朝换代、政权更替那样的重大事件等——经时间的淘洗而堪与史述相印证、媲美者。
第三,当《诗经》尚未成书之前,各国就已经存在“史”,晋有《乘》,楚有《梼杌》,鲁有《春秋》。那时诗、史一家,二者并无严格区分。那时的诗也便是史,是史记、史料的一种,所以那时不需要“诗史”这个名称,而已存在“诗史”的现象或曰事实。既有其实,则“诗史”之名,便随时可以出现,至于究竟何时出现,何时被记录于文字,记录下来会丢失还是会流传等等,则有偶然性。今日我们在《本事诗》中初见“诗史”,焉知将来不会有新的发现?
第四,《诗三百》有比兴隐喻、美刺讽谏,与之同时存在的各国春秋“其文则史”,似乎在表述上还没有“诗”那么多花样而比较质朴简陋。孔子的贡献是把诗的表现手法借用到史的写作中,使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成了著作史书的“大义”,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诗与史分家的种子,也在一开始就埋下了;诗与史从最初的混沌不分到渐渐各显特色,有所区分,到基本分开了却又藕断丝连,保持难分难解的状态,在新的背景和不同层次上出现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景,这个漫长而几乎无止境的过程,也就启动了。而所谓“诗史”,其含义也就不仅是记录史事,还包括了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赞美或批判乃至鞭挞),包括了对历史经验教训和规律的总结,对历史学的探索研讨等等。“诗史”在发展中至少涉及了史述、史论、史学三个层次,故对“诗史”实亦不可一概而论。
要说明当孔孟之时,诗史不分实为一家,不须远求,就在《孟子》书中,便可以看到他把《诗》之原文当作史料运用的例证。
《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和梁惠王关于“贤者之乐”的对话。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问孟子曰:“贤者亦乐此乎?”(孟轲 5)。孟子巧妙地将话题引到贤不贤不在于是否因拥有池沼鸿雁而乐或不乐,关键是能否与民同乐。他指出,能够与民同乐,那么即使役使百姓修建池沼,百姓也会乐意,君王也才快乐;如果相反,百姓就会诅咒反对,君王拥有池沼鸿雁也不可能得到快乐。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孟子引用了正反两条史料。正面的是《诗经·大雅·灵台》的“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孟轲5)。用周文王修灵囿百姓踊跃从事的例子来阐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轲5)的道理。反面例子则是夏桀,引用《尚书·汤誓》“时日害(曷)丧,予与女偕亡!”发出“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轲5)的警告。孟子在这里,完全是把《灵台》诗的描述当作史实看待的。在他看来,《灵台》就是《诗》亡而《春秋》作之前的历史记述。所以此节引用的文字较多,是十二句,四十八字,而不像在其他地方引《诗》往往仅是两句八个字而已。
这样的例子,《孟子》书中还有多处。如与梁惠王谈到“文王之勇”,引用《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孟轲31),这是《皇矣》篇描写“密人不恭,敢距大邦”(31),周文王兴师问罪的一节。又如在回答齐宣王自称“好货”“好色”时,引用《大雅·公刘》和《绵》,说明只要是“与百姓同之”,好货好色都不成问题:
昔者公刘好货,《(公刘)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橐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36)
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绵)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美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37)
这显然是把《公刘》和《绵》的诗文当作了叙述先王事迹的历史记载来使用的。
再如《滕文公上》记述滕文公向孟子问“为国”,孟子引《邠风·七月》“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榖”(117)教以“民事不可缓”(117)之理,接着引《小雅·大田》论历代田税制度的不同与优劣,最后引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18)(《大雅·文王》)的话,鼓励滕文公以周文王为榜样既继承传统不违旧制,又努力创造新气象。
《孟子》又一处用《诗经》史料为借鉴论述现实政治的例子,是引用《大雅·文王》篇“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168)来阐释服从天命与实施仁政的关系。《文王》的诗意是时运一过,殷商后代即使优秀也只能臣服于周。无论大国小国,只有实施仁政才能获得天佑,而不实施仁政,就犹如《大雅·桑柔》所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大热天却偏不肯冲凉”(168),完全是悖时而行,必然事与愿违。

二、“诗史”的现代义涵
诗史一词流传下来,历代学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今天也同样。对追溯梳理其演变过程,做学术史研究自有其必要与意义。但也不妨提出今人的看法,参与到学术的增进与变革中去。
在这里,我觉得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一文中对“诗史”的理解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对上古时代“《诗》即是史”的阐释,特别是他对诗歌史系统梳理中提出的几个主要观点,值得重视,不宜被轻易否定。






其次,从字词之源入手探讨,难道就那么要不得吗?王国维不是也用此法、善用此法吗?比如他的《释史》一文,开篇即引《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王国维27)以下一路从甲骨文说到金石之文,从《尚书》《周礼》追溯到殷和殷前之“史”,将古文字与古文献联系、对照着分析解说“史”之古义。似尚未见有人说他是“字源谬见”。当然,考察字源只是论证之一途,远非全部。闻先生认为“志”字原含记忆、记录、怀抱三义,举例甚夥,推论亦不失严谨。但他在文末还是说:“在上文我们大体上是凭着一两字的训诂,试测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我们知道《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191),对字源考证的有效性持清醒的态度,没有宣布唯我独对,而是特意说明其文是在试测、试述上古诗歌史。今天我们即使完全不用这种方法,仍然能够充分论证“上古诗史曾经混而不分”的观点。我们钦佩闻先生,却没有闻先生的学力,只好不用字源考证之法,却并不认为此法一无是处,甚至一涉此法便堕“谬见”。
说过感想,仍回正题。
闻先生讲得很清楚,他所说的“诗即史、史即诗”,那是遥远的古代之事,而且在那时二者也只是性质相通并非完全同一,否则哪还需要二名?人类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变化。今日大家还在言说的“诗史”,早已不是“诗即史、史即诗”之意,也不是“诗即以史为本质”之意,而是在诗、史二分之后,有些诗歌作品中所叙述描写的生活之“事”、现实之“事”,在人们看来具备了一定的“史性”,可以印证、比照乃至丰富历史记载的某些方面,甚至触及某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或某种历史规律,从而使这作品具有了史述(或史论、史学)的某些意味。“诗史”是诗歌(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诗歌(文学)的一个品种或类别,而在文学批评中,则不过是一种评语或概念而已。
闻先生的论证,在我们看来,还可以导出如下的观点: 当歌、诗尚在二分的时候,歌主抒情,诗主叙事,但抒情叙事是表现手法的不同,并不决然对立,甚且相互渗透,因而诗歌早晚是要合流的,抒情与叙事的对垒性也就早晚要化合为诗歌特质的统一性。而且进一步从根本上讲,诗歌中不会有毫无感情色彩的叙事,也不会有绝对无事、无来由的抒情,抒情叙事虽可分剖解析,有不同的侧重,却实难截然割裂。既然如此,一部诗歌史当然只能从头就由抒情和叙事来贯穿,从而形成并发展出抒叙对垒互动、融渗互竞的传统,而不可能是任何单一传统的贯穿史。
果然,闻先生在第三节中作出了更精彩的论述:
诗与歌的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乃是《三百篇》的诞生。一部最脍炙人口的《国风》与《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一种如《氓》《谷风》等,以一个故事为蓝本,叙述方法也多少保持着故事的时间连续性,可说是史传的手法,一种如《斯干》《小戎》《大田》《无羊》等,平面式的纪物,与《顾命》《考工记》《内则》等性质相近,这些都是“诗”从它老家(史)带来的贡献。然而很明显的,上述各诗并非史传或史志,因为其中的“事”是经过“情”的泡制然后再写下来的。这情的部分便是“歌”的贡献。由《击鼓》《绿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显而隐,“情”的韵味由短而长。那正象征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递增。再进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胀,而“事”则暗淡到不合再称为“事”,只可称为“境”,那便到达《十九首》以后的阶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样,在相反的方向,《孔雀东南飞》也与《三百篇》不同,因为这里只忙着讲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诗的第二阶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处。总之,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是诗第三阶段的进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质。(190)

闻先生重视诗的史性,但也没有忘记诗歌的抒情性审美性。他认为,“诗言志”“诗传意”“诗缘情”,志、意、情实是一回事,而“‘诗言志’的定义,无论以志为意或为情,这观念只有歌与诗合流才能产生”(191)。“《三百篇》时代的诗,[……]是志情事并重的”(191),后来人的观念中却“把事完全排出诗外”以至“诗后来专在《十九首》式的‘羌无故实’空空洞洞的抒情诗道上发展,而叙事诗几乎完全绝迹了,这定义(指‘诗言志’)恐怕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191)。闻先生把《诗三百》视为抒叙良好结合的典范,又认为出现《十九首》式的抒情诗,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在诗中排除“事”而过偏地强调情志意(“诗言志”理解的狭隘化)的缘故。这个说法非常符合中国诗歌史的实际,而又极具启发性,对我们研究诗歌叙事传统,用抒叙两大传统贯穿全部诗歌史文学史,极具指导意义。


三、“诗史”的核心是叙事,诗史传统在叙事传统中

的确,诗史言说虽然纷繁,但在众多说法中,最有价值、能对诸说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正是叙事说。
史的本质和核心要义是事与记录事实,简言之即叙事。“史”从诞生伊始,无论是指人还是指此人之行为、活动或其产物,皆与书策记叙之事相关。王国维《释史》引《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引《书·顾命》“大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引《周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女史掌内令”等,谓“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王国维28—32)。而史官所作、所读、所藏之书,则皆与记叙史事、史言有关。史与事的关系不仅可从字源追寻,尤其应以事实证明,亦可从道理阐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397)圣人如此,何况我辈?史既如此,诗又何尝不如此?“诗史”当然更不能不如此。叙事遂成为“诗史”与“史”发生关联的根本基础。
不过,“诗史”毕竟是诗而不是史,即使是具有史性的诗歌,也不能丢失抒情、言志和表意的功能。于是两相融和,则凡具“史性”之诗,即“诗史”,其本质特征便该是富于感情色彩地叙述评说历史之人与事,此类诗之叙事成分必然较重,且所叙之事又当多与国族命运遭际相关,否则不够称“史”,但也须不乏感情(包括议论)色彩和感人力量,如若质木无文味同嚼蜡,也就不足称“诗”。所谓“诗史”其义大抵如此,并无其他特异神秘之处。
再看得通达些,所谓历史乃是往日之现实,而今日之生活,过后也就成为历史。“诗史”也者,就内容言,号称反映或表现历史,换言之则是记述昔日现实生活点滴而已。而就艺术手法言之,“诗史”的写作是在抒情、叙事二法中,偏于叙事,而不废抒情,但多用客观素材,多关注与观察体会他人事迹境遇和心态情绪,甚至干脆化身为角色,代他人(尤其是向来极少话语权的人)发声,而不是仅仅以诗人自我为中心抒发一己感情。因而一般说来,“诗史”中摄入的具体生活事实乃至故事、画面、人物动态等比一般抒情诗皆较多较富,作者感情往往寓于叙事之中,较少直白呼喊,故艺术风格也往往较为沉实而不空泛虚浮。前人总结创作经验,有云:“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馀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魏泰322)大概“诗史”就有这种好处。被称为“诗史”的作品,至少不会如闻一多先生批评的那样“羌无故实,空空洞洞”。
诗史须具“史性”,也应具有诗性,已如上述。也许后者还须再作强调。“诗史”是诗,毕竟与规范的史书不同,它带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但记什么不记什么、何事用浓墨何事用淡笔甚至略去,都是带着感情有意选择的,而且其表述(选词择字造句修辞等)必有倾向,往往在一字半句之微中透露爱憎,寓含褒贬,显示美刺,表达方式往往含蓄用晦,变化莫测,时而直赋,时而比兴,隐喻有之,影射有之,皮里阳秋有之,嬉笑怒骂有之。这就是史诗或诗史作者从主观出发的叙事干预,是其文学性之妙用和所在,也是其审美意味之所由来。“诗史”是史性、文学性和审美趣味的精巧结合或深度融合。后世人们重视“诗史”,就是因为“诗史”犹如合金钢,兼有二者的优长,形成了更高的思想强度和美学价值。通过诗史的文学性去探索其隐含的史性,可以在尽享审美乐趣的同时收获认识价值,启发更深广的思考。

鉴于题旨,这里我们着重围绕诗歌叙事传统来谈。自《诗经》之后,历代堪称诗史的作品,乃是由《诗经》史诗孳乳而生。楚辞,汉诗,汉乐府,魏晋文人诗,南北朝乐府诗与文人诗,乃至唐宋元明清和近现代的文人诗和民间诗歌中,都有堪称史诗和诗史的好作品。直至今日,“诗史精神”仍是许多诗人作家自觉秉承和追求的良好传统。杜甫则是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尤其是在“诗史”之发展演变史上,杜甫因其创作特色与成就,因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而居于独特的高峰地位。“诗史”虽非由杜甫开创,非其独家专利,也不能说杜甫的任何一首诗都是“诗史”,但杜甫作品中堪称“诗史”者确多,且创作成就特高,“诗圣”之誉与“诗史”之名相得益彰,相互增价,杜甫成为中国“诗史”的首席代表。若就这一点而言,孟棨《本事诗》倒是功不可没。

杜甫的功绩正在于以优异的创作实绩抗衡了这个语境,扭转了积习甚深的诗坛风气,从而使诗歌重新回到抒情与叙事双线交融并进的健康道路上去。具体来说,是在安史之乱造成的国破家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其一系列史性和文学性都很强的作品,使诗歌的叙事功能,诗歌的史性内涵,得到全面的发扬和提升,显示出巨大的思想力和美学能量,使诗歌关怀现实、记录历史的职能重新获得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使数百年来几乎渐被遗忘的《诗经》史诗叙事传统,重新成为人们关注和热爱的对象,不但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而且在当时就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元稹白居易李绅诸人为代表的新乐府创作在中唐兴起绝非偶然,而杜甫的正面影响则更贯穿一千多年,至今未衰。杜甫所接续和弘扬的《诗经》史诗和乐府民歌的精神,也就是中国诗歌抒情和叙事并存互动的优秀传统。
以杜甫为典范和代表的叙事传统,其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多方面研究阐述。许多研究杜甫的论著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于此,可谓成果累累。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内涵要义,试作概说如下:
一、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往往更为关注历史,也更关注现实生活,把创作的视线和笔触更多地超越个人而投向客观世界: 他人、社会(甚至底层)和国族之事,表现出对时事、政局、新闻、街谈巷议、民情风俗等的兴趣,且善于将其摄入笔下,作出多样的载录。而在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往往能以国族的安危利害作为关切的首要问题和判断是非、采取写作策略的根本依据。


传统的这个内涵也限制了“诗史”之称的运用范围。前文论到“诗史”之本质实即诗与生活的关系,故“诗史”既有其崇高性,又并非神秘稀奇得高不可攀。那时留下一个漏洞: 那么是不是任何反映一点儿生活内容的诗都能称为“诗史”?“诗史”概念岂不过于宽泛?阐明了叙事传统的这一内涵,当可避免这个误解,等于打了一个补丁。
二、叙事传统不废以个人为中心的抒情咏怀,但强调将家庭的悲欢离合、个人的喜怒哀乐与国族安危大事紧密结合,把小家的聚散苦乐放在大家乃至国家安危存亡的背景之下,形成崇高而感人的家国情怀。
杜甫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脍炙人口的作品亦多,如五古《北征》《羌村三首》,五律《春望》,又如被誉为“生平第一首快诗”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均是史性很强的叙事与写怀言志的抒情和谐融合,标志着被称为“诗史”的杜甫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能够登临怎样的高峰,也标志着诗歌叙事传统具有怎样的亲和力和情感容量,更标志着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虽有各自的侧重和专长,却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三、叙事传统强调明确的彰善瘅恶意识,爱憎鲜明,褒贬有力,赞美英雄仁人,讽刺丑恶宵小。或以为这是受到“史”的影响所致,其实正好相反,孟子那句名言引孔子说:“其义则丘窃之矣”(孟轲192)。这个“义”即指《诗三百》所寓含的褒善贬恶之义。诗具美刺,曾对史述产生过重要影响。孔子《春秋》能使乱臣贼子惧怕的“一字褒贬”法,就是从《诗经》的比兴美刺学过去的。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史学宗旨和撰写原则又长期反哺诗人,使中国诗歌,特别是那些贯彻了诗史意识和诗教精神的叙事性诗歌,大多是有为而作,有的放矢,对培育民族正气和儒家伦理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表述朴实简洁,但不废反复咏唱,也不废议论抒情。史述对文字的要求是简洁,刘知几《史通》从史家立场出发,对史述的叙事提出了明确要求,那就是信实简要,文约事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如何才能简要?他提出了省句、省字、点烦、用晦等法(152—71),并亲自做了“点烦”趋简的示范。一方面是这种理论的影响,一方面也是诗歌文体自身的要求,诗歌自然不能像文章那样细致状写、任意挥洒,而必须用有限的语词(律诗还须合律)来描述历史事件或概括历史现象,而这种简约的叙述还必须蕴含作者想诉说或想宣泄的深意。应该说,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这一要求相当高而苛刻,也正是这种要求造就了中国诗歌内涵的深刻和艺术的优美,但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诗歌叙事、描写的舒展纵放。
五、风格温柔敦厚,符合“诗教”的原则,具体而言,是美刺褒贬均须合度有节,而不过分。这不但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也是儒家社会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实际上全面渗透贯彻在古今中国人的生活和理念、品格之中。这里不仅有掌握“度”的难题,实际上还存在着深刻的自相矛盾。刘知几主张史必实录、痛恶曲笔,同时却又认可“避讳”:“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183)显然,当求真与避讳冲突时,让步的便只能是求真,否则便违背了诗教。上面提到刘知几提倡史述含蓄用晦,也与此有关。
除上述外,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即诗史传统、诗史精神,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内容,只是这五点似乎比较明显而重要。
仅就此五点而言,这个传统自有许多值得肯定和继承的正面精神,如热爱国族而勇于奉献、甚至勇于舍弃个人的精神,其基本面无疑值得发扬光大,而且只要中华民族存在,这种精神就不能也不会泯灭。然而,即使正面之中亦不是不含负面,如因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官府吏员的凶残暴行有所容忍,便是正面中所含的负面因素,而且明知其为负面因素,要在正面行为中剔除和避免之却还相当困难。至于诗风的温柔敦厚,固是中国诗歌的美学特征之一,也是中国人素质和品格的一种优美之点,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应结合历史和时代背景对之做具体分析,充分看到其负面作用和影响。这种矛盾现象既规定了中国诗歌的特点,也造成了它的弱点和缺陷。如果说掌握分寸、褒贬合度是必要的应该的,那么为尊者和亲者讳却必然使诗歌的史性和思想锐利深刻的程度大打折扣。而当其在国势孱弱的情景下,就更易于虚伪软弱、自欺欺人甚至与对强敌的奴颜媚骨相混,成为戕害和背叛国族的毒药。
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就是这样有其优秀卓越的一面,也有其不良落后的一面。我们实事求是地揭示它,为的是继承发扬前者而努力克服后者。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诗歌传统可以而且应该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探讨总结。从艺术表现方法的不同入手,将其概括为抒情叙事两大传统,不过是许多角度中的一个而已。“诗史”固然可以是评价好诗的一个标准,但好诗并不一定非得“诗史”不可。文学是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世界,任何“唯一”“独尊”的念头都是要不得也行不通的。
注释[Notes]
① 历代与当代言及“诗史”或讨论“诗史”问题的论著,包括博硕士论文数量繁多。英年早逝的学者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北京: 三联书店,2012年)对此作了系统梳理。此书之后,有关论文仍多。本文涉及某些论文,将在后面相应处注出,这里就不罗列了。
② 据陈尚君考证,《本事诗》作者孟棨,应作孟启。我相信陈先生的考证,这里只为读者习惯,暂用旧名。
③ 请参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引言及第一章。孟棨《本事诗》:“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又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史臣曰:“至于先士茂制[……]并直举胸臆,非傍诗史。”或谓“诗史”指《诗》《史》二事,然王世贞则据此曰“然则少陵以前,人固有‘诗史’之称矣。”参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三,《历代诗话续编》(中),丁福保辑(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991页。
④ 杜集作《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浦起龙云:“前十韵叙其才名宠渥,以及去官之后,文酒相从。后十韵,伤其蒙污被放。为之力雪其诬,诉天称枉。”见《读杜心解》卷五之二(北京: 中华书局,2015年)第718页。
⑤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北京: 三联书店,1986年)认为孟棨《本事诗》所记“诗史”“这种话本是当时流俗随便称赞的话,不足为典要。”(188)既是流俗之语,早就存在的可能是存在的。
⑥ 参看彭敏:“诗史: 源起与流变”,《求索》1(2016): 152—56。此文认为“诗史”观念的实践从先秦至明清一脉相承,诗史之实远早于其名,并概略而系统地论述了宋前“诗史”传统的流变。笔者赞赏其观点。
⑦ 请参[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著《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⑨ 讨论孟子这段话含意的论文,至今不断,见解各有侧重,均有参考价值,这里不能一一引用。其中如刘怀荣:“孟子‘迹熄《诗》亡’说学术价值重诂”,《齐鲁学刊》1(1996): 63—65;马银琴:“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3(2002): 74—79;魏衍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发微”,《理论学刊》4(2010): 105—108;蔡英俊:“‘诗史’概念再界定——兼论中国古典诗中‘叙事’的问题”,《语言与意义》(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3—83页,等,对此皆有专论,观点基本与杨伯峻《孟子译注》一致。杨氏此节译文:“孟子说: 圣王采诗的事情废止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孔子便创作了《春秋》。(各国都有叫做〈春秋〉的史书)晋国的又叫做《乘》,楚国的又叫做《梼杌》,鲁国的仍叫做《春秋》,都是一样的。所记载的事情不过如齐桓公、晋文公之类,所用的笔法不过一般史书的笔法(至于孔子的《春秋》就不然)。他说:‘《诗》三百篇上寓褒善贬恶的大义,我在《春秋》上便借用了。’”(卷八193)录以备考。
⑩ 即使仅引用二句八字,也是在运用史料,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引得多,史料意义更明显。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杜甫: 《读杜心解》,浦起龙撰。北京: 中华书局,2015年。
[Du, Fu.A
Kernel
Interpretation
of
Du
Fu
’s
Poems
. Ed. Pu, Qil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孟轲: 《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
[Meng, Ke.Note
on
Mengzi
. Ed.Yang Bo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孟棨: 《本事诗》,《历代诗话续编》(上),丁福保辑。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
[Meng, Qi.Benshishi
.A
Sequel
to
Poetry
Notes
across
Dynasties
. Ed. Ding Fub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刘知几: 《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Liu, Zhiji.Note
on
Shi
Tong
. Ed.Pu Qilo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王国维: 《王国维集》第四册,周锡山编校。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Wang, Guowei.Col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 Vol.4. Ed. Zhou Xish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魏泰: 《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上),何文焕辑。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
[Wei, Tai.Poem
Theory
of
Lin
Han
Yin
Ju
.Poetic
Remarks
in
Past
Dynasties
.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第1册。北京: 三联书店,1982年。
[Wen, Yiduo.Collected
Works
of
Wen
Yiduo
. Vol.1.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萧统编选: 《文选》,《四部丛刊》影宋六臣注《文选》本。
[Xiao, Tong, ed.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The
Four
Categories
of
Books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上)。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
[Yong, Rong, et al..Complete
List
of
Si
Ku
Quan
Shu
Collection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张晖: 《中国“诗史”传统》。北京: 三联书店,2012年。
[Zhang, Hui.Poetry
as
History
:A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