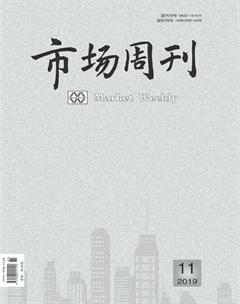个人信息权的二元立法保护模式之证成
摘 要: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是性质、内容迥异的两种不同权利,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制度理念、客体、权利内容及保护方式等方面。美国法律中的隐私权相比于其他国家,是一个扩张解释的结果,而我国的隐私权相关理论则不能涵盖个人信息权。同时,法院的判决也证明,隐私权的保护模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个人信息权权利人的权利主张。就联系而言,本文对比了“一元论”和“二元论”模式,并认为“一元论”模式下,隐私范围广,甚至包括姓名、名誉等人格权内容。有学者认为美国隐私权理论实际上是一锅“大杂烩”,其包括但又不限于个人信息。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二元论”的立法模式。
关键词:隐私权;个人信息权;被遗忘权;一元论;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9)11-0163-03
一、 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问题
从个人信息权理论的起源、发展和现代转型等角度来看,其常常与隐私权纠缠在一起,因此,理论上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即“一元论”和“二元论”。这两种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隐私是否可以包含信息?立法上坚持“一元论”的国家(美国、日本等)认为信息是包含在隐私之中的;而在我国,无论是学理上还是立法上,都坚持“二元论”。但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对于隐私权,往往采取的都是“框架性权利”定义。
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立法层面,司法实践层面亦是如此,实务界也同样缺乏对个人信息性质、地位的准确认识。从比较法角度,当今世界两大法系对个人信息的认识就不一致。概括而言,主要为以欧盟为代表的“渐进式发展”和美国为代表的“隐私权保护”两种不同路径。
二、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区别
无论内涵、外延,还是价值、功能,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都存在着较大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制度理念上的差别。随着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个人信息开始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值也日益凸显。因此,构建个人信息权的核心理念,应为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一点在近年来各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所体现。比如,日本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修订中,重新定义了其立法目的,即更加强调信息对信息产业的促进作用。与之不同的是,隐私权的立法理念则一直强调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与自由,这主要是出于隐私的私密性特点。隐私权侧重于保护人格尊严,而非财产利益,并将其作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
其次,客体不同。隐私权的权利是权利主体不愿意公开的任何隐私。相反,个人信息权的客体是一切信息,且这种信息不以私密性为限制。比如,自然人的电话号码,在现代社会很难将其定义为隐私。在王景素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等隐私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王景素曾租住王涛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某房屋。在向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申请办理该房屋宽带业务时,留下王景素139XXXXXXXX手机号码作为该房屋宽带业务的联系方式,登记的客户姓名为业主王涛。上述宽带合约终止后,该手机号一直作为王涛的联系方式保存在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系统中。2016年6月26日,王涛向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提出变更联系方式申请,申请将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系统中王景素的该手机号码更正为自己的电话号码。办理后,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为王涛出具了编号为100235520706号的业务登记单。王涛将该业务登记单拍照片发给了王景素。王景素同年8月初仍然接到了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客服电话。王景素认为自己隐私权受到侵犯,自己遭受精神上的侵害,对方应当对其损害进行赔偿。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认为王涛申请变更的是登记资料,所以系统账户信息中仍能显示出该电话号码。王涛认为其当时申请的就是要求彻底变更删除,不知道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为何删除不彻底。进而,一审法院认定在该案中,王景素主张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侵犯其隐私权,但并未就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王涛存在侵犯其个人隐私的上述行为进行举证,故其要求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赔偿11500元并由王涛承担全部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但需要强调的是,公民的手机号码属于个人信息,无论该个人信息是否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任何公民都有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的权利。关于王景素在本案中要求判令与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之间没有宽带合约关系的诉讼请求,虽然王景素与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自始并未建立合同关系,但该主张不属于隐私权纠纷。原告王景素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認为在本案中,难以认定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和王涛存在侵犯王景素隐私权的主观故意,且将王景素电话留在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的行为以及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根据信息库的数据给王景素拨打电话催收费用的行为,亦难以认定系侵犯王景素隐私权的侵权行为。
再次,内容不同。隐私权的权利内容表明它并非是一项积极的权利,更多地表现为消极性,即仅在其遭受或可能遭受他人的非法干涉和不当揭露时,权利人才能够行使该权利,即无侵权,无权利。在非侵权领域,隐私权更像是一种虚置的权利。与之相反,个人信息权是一项积极性的权利,这就赋予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人对其权利拥有完整的且独立的权利,与物权等绝对权完全一样,权利人可以在任何场合行使这种权利。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人可以像物权人一样,通过其所享有的个人信息权积极地对抗一切不法行为人,而作为义务人的其他人要尊重权利人的此项权利,即除了不被侵害的权利,还应包括权利人对其所掌握信息的控制权。这一点已得到许多国家立法确认,其表现就是被遗忘权、删除权和知情权的创设。其中,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是指权利人享有的清除、限制、分解(delink)、删除和修正个人网上信息的权利,这个互联网信息通常是令人产生误解的、不相关的和过时的,而且这一点日益为美国和欧盟所重视。被遗忘权近期受到欧洲民众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其在欧洲框架下的蓬勃发展之势。这也带来两项相关的争议:第一,所谓的被遗忘权依然是一项抽象的权利,给予权利人删除过去记录的权利。第二,欧盟立法者所通过的法律。随着欧洲联盟法院在2014年的判决中接受了被遗忘权,许多人认为相似的表达在美国不仅是不受欢迎的还是违反宪法的。尽管如此,许多联邦和州的法院在近期的判决中使用了近似的表达。
最后,保护方式上的差别。就个人信息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而言,当今世界主要存在美国和欧盟两大立法模式。相比较而言,美国法律所采取的是经营者自律的模式,该模式将其与美国已有的体系庞杂、包罗万象的隐私权理论相结合。与其相反,欧盟则针对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一方面通过欧盟层面的立法,另一方面又注重成员国的国内立法。这种欧盟同一立法与成员国立法相结合的模式主要是由欧盟独特的结构所决定的。为了更好地促进人员、资金、数据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就要求欧盟的立法一方面要兼顾共同体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结合各国的法律传统,对欧盟法进行本土化的续造。不幸的是,我国现在不仅没有建立起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甚至连隐私权保护的理论也未全面确立,这就导致了我国在有关领域常常处于一种于法无据的状态。这就使得制定一部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变得有必要和必须,通过制定这样一部法律,不仅可以使立法次序完整,还可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规范和界定。
在现代立法环境和制度下,立法工作首要考量的便是利益衡量。在信息时代,以“个人信息”资源为中心,周围主要分布着三类利益相关人,即国家、互联网从业者与权利人。只有真正了解法律所调整各种利益(既可能是个人利益也可能是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才能够将其中的平衡规则抽象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理论的基础。而通过以往的概念,比如个人敏感型的隐私信息则难以实现新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要实现“三方平衡”就需要通过立法来强化个人一般信息的利用。
总之,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是性质、内容迥异的两种不同权利。美国法律中的隐私相比于其他国家,是一个扩张解释的结果,而我国的隐私权相关理论则不能涵盖个人信息权。同时,法院的判决也证明,隐私权的保护模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个人信息权权利人的权利主张。
三、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联系
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存在一定的重合。在“一元论”模式下,信息是隐私的一部分,因此隐私权的概念外延就很大。“隐私权”的概念源于美国,这一点学界的观点高度一致。无论美国的学术界还是美国司法界,都对隐私和个人信息采取“一元论”模式。在该模式下,隐私的范围广,甚至包括姓名、名誉等人格权内容。有学者就认为美国的隐私权理论实际上是一锅“大杂烩”,其包括但又不限于个人信息。但也有英美法系的专家、学者认为这种定义方式非常糟糕,过于宽泛、模糊甚至无边界,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概念。为了消除此种概念上的模糊性,有美国法官就将其概括为“不被打扰的权利”。这一表述后来经常被美国学者、法官、当事人所引用,因为它道出了隐私权所反映的核心价值取向,即公民的私生活“不受打扰”。后来,有学者就隐私权的诉因类型和范围做出探讨,他们分析认为根据与隐私权有关的诉因,其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类型的纠纷:对原告独自相处和独自居住状态的非法侵入;公开披露他人信息,且这些信息是令其难堪的(embarrassing);被告为了自身的利益,未经原告授权,对原告的肖像和姓名予以盗用。此外,还有学者将美国的隐私权概括为以下四种:原告享有独自相处,而不被人打扰的权利;信息控制权;对他人信息的有限可获悉性;权利人对身份性私密控制和自我管理。早期的日本完全借鉴美国的隐私权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个人信息和隐私,进而发展“二分法”理论与“三分法”理论。受美国法和日本法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践也采取“一元化”的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显然,在我国台湾地区,隐私权包含私人秘密和个人信息自由。
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陆学者都一致认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模式应当区分,不应该套用隐私权的保护模式对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张新宝教授曾在文章中指出,隐私权的权利指向是权利人的私生活,只要权利人的私生活不受到他人的不当干扰,此种权利就是一种虚置的权利。但是,个人信息却不同,权利人可以主动要求相关的义务人不得非法采集、非法使用和非法公开权,否则即侵犯了权利人的个人信息权。王利明教授也曾细致比较了隐私与信息的关系,他认为两者存在共同点,即权利主体相同,均为自然人;均反映了权利人对其私生活的自由决定权,但同时两者又是不同的权利。信息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隐私权是被动型权利,等等。
四、 隐私权保护之局限
受《论隐私权》这一著名文献影响,隐私权这一概念在美国法中不断地发酵、发展,不论在宪法层面还是在侵权法层面,都有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发展的趋势,就权利保护而言,隐私权保护模式的局限性很大,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权利范围上,隐私权范围具有不确定性。由于隐私权概念界定不清,司法实践中对应当纳入隐私保护范畴的个人信息认定也不一致,就可能导致应当受到保护的个人信息被排除在隐私权保护范围之外。隐私权现在是一项体系庞杂的权利,其包含的对象和行为模式很多,但在其存在之处,其范围有限。与之直接关联的,是与权利人的私生活或者是私人有关的事务,比如女性的怀孕、生产情况、避孕(包括避孕方式和时间)和堕胎(时间和地点)等。但是,以隐私权来包括日益发展的个人信息权是不妥当的。个人信息权的外延不断延伸,已经覆盖了之前法律不曾到达的范围和领域。电子商务已昂首迈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当前无论个人信息权还是隐私权,对于这些新兴领域的立法都存在不足,我们的立法仍处在前人工智能时代。
其次,在举证责任上,权利人负担的责任过重。在隐私权侵权行为认定过程中,其采取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这就意味着需要权利人证明信息控制人存在侵权行为。但是,在个人信息权诉讼中,权利人与控制人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应采取过错推定原则。隐私权不仅不能包括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个人信息权范围,而且在举证责任方面对权利人不利。
最后,对各方权益的维护上,个人隐私权无法像个人信息权一样起到平衡的作用。除了互联网、大数据以外,个人信息保护另外一项动力是商业信息的维护。电子商务经营者通过收集、分析个人信息,可以精确获悉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进而针对性地发布广告,继而享受高额的经济回报。随着信息资源逐步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化与全球化相互作用促成了电子商务的全球化。也正是因为这种电子商务的全球化,逐步使得产业分工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产業结构大升级。这种升级和调整对个人信息的启示和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抓住转型期的机遇。因为前述的升级和发展对全球产业模式的重塑作用,使得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去重新组合产业结构和产品生产。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和升级也要求我们通过制定更为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来规范和控制我们的个人信息。如此,才能实现商业大繁荣。
参考文献:
[1]《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2]Michael J.Kelly and David Satola.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J].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2017(1):16-23.
[3]Cesare Bartolini and Lawrence Siry.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Light of the Consent of the Data Subject[J].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16 (2):218-237.
[4]Amy Gajda.Privacy,Press,and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United States[J].Washinton Law Review,2018(1):201-264.
[5]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中国法学,2015(3).
[6]石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63.
[7]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
[8]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J].现代法学,2013(4):62-72.
[9]李永军.论《民法总则》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二元制”保护及请求权基础[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3).
作者简介:
周亚柳,男,安徽寿县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徽大学法学院2017级非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