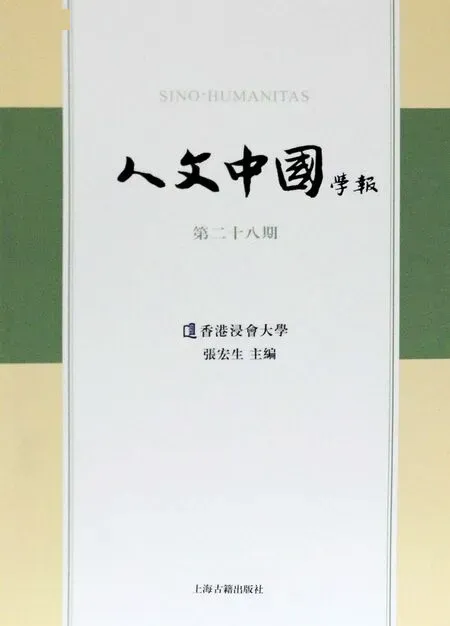卿憐及相關作品考論
趙杏根
提 要
關鍵詞: 清代詩文 和珅 梅村體 陳文述 腐敗官員
引 言
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中,有乾隆帝、和珅與罪臣王亶望的“義女”蘇卿憐之間的風流情節。這些情節,當然出于虛構,但也不是全無所本。
據清代嘉慶初年以下的記載,卿憐確有其人,其詩歌曾經頗爲流傳,甚至還有名爲《分香》的詩集。以卿憐爲題材的詩文和詩話、筆記之類,也有不少。這些作品,儘管體裁不同,但情節却大致相同: 吳地美貌的才女卿憐,嫁給浙江巡撫王亶望作小妾,得到寵愛並且享受榮華富貴。王亶望因貪污而敗後,卿憐被人送給和珅,又得到寵幸。和珅敗後,卿憐作詩感嘆。于是,當時和後來不少作家,以此爲題材,寫作詩文、筆記、詩話等。
對卿憐及其相關史實、詩文等的研究,有助于我們認識當時官場和文壇的生態,以及此類文學現象後面的規律。《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3年第一期高洪鈞《吳卿憐外傳》,[注]高洪鈞: 《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3年第1期,頁90—92。對憐卿其人其詩作了研究,惜高先生掌握的材料不够充分,對某些材料的解讀有重要錯訛和不足,結論也未盡當,故筆者擬對此課題重新作一番研究。
一、 從王伏到卿憐
從王伏到卿憐的轉變,應該是我們要研究的女主角在王亶望那裏完成的。
關于王亶望其人,世人還不大熟悉,爲了論述的方便,有必要先略作介紹。王亶望(?—1781),字渭璜,一字誕鳳,山西省臨汾縣人,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舉人。臨汾古屬平陽府,故王亶望出事後,人們多稱他爲“平陽”或“平陽中丞”。其父親王師,字貞甫,一字良輔,號莪園,官至江蘇巡撫,爲官既清廉又能幹。王師去世後,王亶望進入官場,不斷升遷。乾隆三十九年三月,朝廷批准陝甘總督勒爾謹關于在甘肅開捐監生、以報捐監生所捐糧食用于賑灾的計劃,並調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取代“謹厚有餘”而魄力不足的原甘肅布政使尹嘉銓,以加强對此事的領導。王亶望到任後,夥同當地各級官員,把捐監者應該繳納的糧食折合成銀子收取,又用僞造賑灾事實等手段,大肆侵吞本該用于賑灾的款項。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遷浙江巡撫後,仍然在任上大肆貪污。繼他擔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開始還想糾正甘肅官場的貪污之風,但不久就同流合污了。到乾隆四十六年案發,這幾年中,在甘肅捐監生者多達二十七萬四千多名,按照朝廷規定,每名捐四十三石糧食,但甘肅不僅用于賑灾的倉庫空虛,連常規收取的糧食,也嚴重虧損。此案中,受到各種處罰的涉案官員超過200人,包括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等高官在内的58人被處死。這就是著名的“甘肅冒賑案”。可以想象,這在當時的官場、知識界乃至整個社會,所引起的震動有多大。卿憐就是此案主犯王亶望的一個侍妾。
在關于卿憐的傳說中,出現較晚但最爲完整的,是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七《吳卿憐小傳》。關于卿憐是如何嫁給王亶望的,此文云:
卿憐,吳姓,蘇郡小家子也。眉目妍媚。數歲,教之歌,便能爲新聲。及長,韶秀出衆,且嫻近體詩句。時有虞山某中丞者,方爲浙東監司,諂事制府王亶望,遂進之,果得制府歡。床帷供具華縟,世莫與比。監司尤曲意下之,每燕見,輒詣小夫人,再揖而後敢語。數年之間,薦至方伯。或曰卿憐力也。[注]朱駿聲: 《傳經室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25。
這段文字,起碼有兩個錯誤。其一,甘肅冒賑案發生之前,王亶望確實在浙江做過官,但擔任的職務,先是布政使,後是巡撫,而沒有擔任過浙江總督或閩浙總督。巡撫是“中丞”,而總督才稱“制府”。終其一生,王亶望也沒有擔任過總督的職務。其二,在王亶望擔任浙江巡撫期間,擔任浙東監司,後來“數年之間”晋升爲布政使、巡撫的常熟籍官員,完全是虛構的,因爲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人。清代去今未遠,布政使、巡撫這樣的高官,是容易查到的。有清一代,儘管常熟籍官員衆多,但做到布政使、巡撫的,在乾隆年間,也沒有幾個人。筆者通過《清代職官年表》等文獻仔細查核,乾嘉間根本沒有符合這些條件的常熟籍官員。儘管朱駿聲也是蘇州人,但王亶望被殺的時候,他還沒有出生,和珅垮臺的時候,他也不過虛齡十一歲而已。因此,他的記載,明顯得之于流傳了幾十年的傳聞,錯訛是難免的。至于有些錯訛的産生原因,下文我們還會探討。
其實,卿憐本來不叫卿憐,也不姓吳,而是姓王,乳名伏。鄭光祖《一斑録》之《雜述二》云:
乾隆間有某中丞,好内,廣置姬妾,猶以爲温柔鄉中尚無尤物。由京赴浙,道過金閶,諒吳下必多殊色,而遍選竟無當意。聞虞山靈秀,潜來咨訪,亦猝不易得。因以便服閑步城隍廟,前見有婦携女進香者,其女麗質天成,不言生媚。中丞驚爲國色。從者覘其旋入石梅尼庵,爲訪,知是邑東鄉張墅王姓女,乳名伏。父訓蒙,爲學究。家係淸貧,應可貨取。卽謀于尼。尼善爲說合,以成其事。旋知女家亦係山西籍,不無同姓之嫌,然已定情,待之有加禮而已。及入浙署,寵冠諸姬女。[注]鄭光祖: 《一斑録》(臺北: 文海出版社,2003年),頁40。
這似乎是通俗小說和戲劇中輕佻書生、豪門公子、流氓無賴跟踪乃至强娶民女的情節,作者把這樣的情節按到堂堂巡撫大人的頭上,是否符合事實?是否合理?不過,細節方面,或有出入,但常熟某姑娘嫁給浙江巡撫王亶望,則還是可信的。這“某中丞”,明顯是王亶望。王亶望屬于風流才子一類的官員,非常好色,姬妾成群。乾隆四十六年,他被殺的時候,除了三個兒子已經成年外,尚有八個兒子,俱在六歲以下,這可以作爲明證。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赴浙江巡撫任,經過以多美女著稱的吳地,順便物色,也在情理之中。清代官員,不能在其所管轄的地方娶妻妾,常熟儘管和浙江毗鄰,但屬于江蘇省,王亶望娶王伏,幷不違反這樣的規定。鄭光祖是常熟人,儘管王亶望被殺的時候,他還只有6歲,嘉慶三年(1798),和珅還沒有垮臺的時候,他已經23歲,就開始寫作《一斑録》幷且不斷增删修改,這工作持續到他80歲。我們無法斷定他關于王亶望娶王伏的記載,是何年所寫,但是,在現存的關于卿憐的記載中,就記載者的年輩先後而言,他是比較靠前的。更爲重要的是,繼王亶望娶王伏事後,鄭光祖還有如下一段記載:
春暮百花競放,中丞喜人有花容,花如人面,開盛筵賞之。諸姬稱美吳饌,女獨無言。詰之,曰: 欲似我張墅毛厨所治,恐未逮也。中丞問其詳,曰: 妾家住江鄉,春初魨美,秋暮鷄肥。毛厨名榮,字聚奎,烹飪獨絕。張墅與附近之梅林鎭,重筵席者必致之。……中丞奇之,立將榮物色到浙。榮一時名震西湖。後中丞不久坐法,榮歸,名又重于鄉里。竊思與榮同事者不少,其人多年習熟,所治應無大異,乃一經假手,知味者必立辨爲非出榮手,則榮之藝真有不可及者。後榮不久下世。其侄孫毛觀大,隨先君到滇,藝遠不逮,惟遺榮食譜一册,流落余箱,今檢出視之,法制紛繁,皆人所共知。余欲著名厨之佳制,翻閲全册,無可著意。[注]同上。
鄭光祖家和毛家關係如此,其關于毛榮到王亶望處烹飪因緣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王伏的家鄉常熟東鄉張墅,就是現在常熟的東張鎮,和常熟另外一個叫“西張”的鎮相對。要之,常熟姑娘王某嫁給王亶望的說法,是可信的。
可是,王伏和卿憐之間,又有什麽關係呢?“卿憐”這個名字,就不似良家女子的名字,倒天生就像姬妾乃至青樓女子的名字,讀書人根本不會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爲“卿憐”。陳文述《西泠閨咏》卷十四《玉蕊軒吊吳卿憐詩》有“誰向花前贈小名”之句,[注]陳文述: 《西泠閨咏》(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頁582。即使是小名,也是姬妾的小名。這大約有兩種可能。一是此女嫁給王亶望以後改或被改的,二是後人根據相關的故事而稱她爲“卿憐”的。
關于王亶望寵愛卿憐,多篇作品中,寫到“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的對聯。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云:“制府抄籍時,聞有見其綉床榜聯‘卿須憐我’之句,予思之,殆爲卿憐發也。”[注]朱駿聲: 《傳經室文集》,頁425。黄鈞宰《金壺七墨》之《金壺浪墨》卷七《吳卿憐》云:“卿憐,吳人,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按: 指王亶望)得之,寵幸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爲吳賦也。”[注]黄鈞宰: 《金壺七墨》(臺北: 新興書局,1987年),頁3981。其實,這樣的情節和對聯,鄭光祖《一斑録》中早已有之,但這是王亶望寵愛王伏的事情,沒有提到卿憐:
(王伏)及入浙署,寵冠諸姬。女本多才,善《心經》,通文翰。偶綉句于幃幔,曰‘色即是空空是色’,要中丞對,效蘇小妹三難新郞故事也。中丞緩之,同夢中語中丞曰:‘胡不對“卿須憐我我憐卿”也?’中丞狂喜,令幷綉于幔。[注]鄭光祖: 《一斑録》,頁40。
王亶望和他的兩個姬妾分別有這樣的故事,這不大可能。因此,王伏就是卿憐,卿憐就是王伏。至于“卿憐”這個名字,是何人給她所取?是否和這一風流韵事有關?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知道。我們只能知道,在她和王亶望故事的有些記載裏,王伏就被人稱爲“卿憐”了。
這兩句工整的對聯,又見之于梁章鉅《楹聯續話》卷四,但又和王亶望、卿憐無關了,云:“邗上徽商某,荒于色。嘗制一床,備極華麗。床柱上懸一小聯,摘‘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榜諸其門,曰有能屬者予千金。或以‘色即是空空是色’對之,立攫其金以去。按此語不但工切,兼寓箴規之義。千金,非幸得也。”[注]梁章鉅: 《楹聯續話》(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70。“色即是空空是色”,乃化自《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句,而“卿須憐我我憐卿”,則本自明代人記載中錢塘名妓馮小青的詩歌。馮小青嘗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見萬時華《溉園集》初集卷二、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一、張岱《西湖夢尋》卷四、張潮《虞初新志》卷一等所載馮小青故事中。這兩句詩,也爲後來某些小說或戲曲所引用,例如曹雪芹《紅樓夢》第八十九回、佚名《永慶升平》卷八等,移用或者化用後面一句的通俗作品和詩詞,也有一些,例如獨逸窩退士《笑笑録》卷六《京官詩聯》中所引用紀昀的詩,黄景仁《兩當軒全集》卷十八詩餘中的《風流子·江上遇舊》,陳端生《再生緣全傳》卷二十等。因此,這樣的對聯,是通俗文學中的材料,才子佳人的俗套而已。王亶望和他的侍妾文藝女青年王伏用之,也在情理之中。
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的行政區劃中,常熟都是屬于蘇州管轄。陶梁《國朝畿輔詩傳》卷五十四所載李燧《卿憐曲》“姑蘇臺畔如花女,初嫁王昌年十五”之句,[注]陶梁: 《國朝畿輔詩傳》(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686。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卷二《卿憐曲》“當年生小橫塘住”之句,[注]孔昭虔: 《鏡虹吟室詩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89。都說卿憐的家鄉是蘇州,解恕《蘧亭筆記》,[注]高洪鈞: 《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1期(2003年1月),頁90。張汝杰、楊俊明編《清代野史》第四輯佚名《檮杌近志》[注]張汝杰、楊俊明: 《清代野史》(成都: 巴蜀書社,1987年),輯4,頁121。和鄧之誠《五石齋小品》[注]鄧之誠: 《五石齋小品》(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8年)頁155。所載吳卿憐詩歌自序,都說卿憐姓吳,是蘇州人。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七《吳卿憐小傳》云卿憐家鄉爲“蘇郡”,也就是蘇州。這些說法,都不錯。陳文述《卿憐曲》明確卿憐的家鄉是屬于吳地的常熟,“卿憐本是琴河女,生小玲瓏花解語”,[注]陳文述: 《頤道堂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5。常熟古稱“琴川”,所以“琴河”指常熟。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也明確說卿憐是常熟人。他們兩人這樣的說法,和鄭光祖所記載,是完全一致的。陳文述後來長期當常熟縣的知縣,和當地的士大夫,包括孫原湘等文壇前輩,都非常熟悉,他後來有可能在常熟聽說過卿憐和王亶望的故事。至于在不少記載中,卿憐姓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改“王”爲“吳”,乃是避免和王亶望同姓,傳統上“同姓不婚”,《左傳》中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之說。二是常熟屬于吳地。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十六孔昭虔部分,稱卿憐爲“濮氏女”,[注]徐世昌: 《晚晴簃詩匯》(北京: 中國書店,1988年),頁259。則不知何據。
二、 卿憐之進入和珅家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 後來給和珅當侍妾的那個卿憐,和王亶望那個常熟籍的侍妾王伏,也就是卿憐,是不是同一個人?如果是同一個人,那麽,她是如何進入和珅家的?
李燧《卿憐曲》云:
“王昌”,明顯指王亶望。“何郎”,三國時何晏,字平叔。此人雖爲男子,但以柔美婉麗著稱。《世說新語·容止》云:“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注]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册下,頁333。“芳信”二句,言卿憐以“鴆鳥媒”,見到和珅,通過相貌等的檢驗,其美確然,而進入和珅家。可是,這“鴆鳥媒”是誰呢?孔昭虔《卿憐曲》云:
單衫二月艶春陽,恰遇琅琊大道王。十斛量珠暫買笑,一宵倚玉便專房。此生自分歸金屋,地久天長歌未足。繫爪春調大喜筝,折花夜按秋娘曲。按曲調筝枉斷魂,教成歌舞爲他人。無端驚破文鴛夢,緹騎飛來已到門。喬松吹墮罡風劫,女蘿花早隨飛蝶。又向誰家舞柘枝,翻憐當日迎桃葉。權門有客慕程松,買得名花進相公。[注]孔昭虔: 《鏡虹吟室詩集》,頁589。
“琅琊大道王”,顯然指王亶望,切其姓氏。此詩云王亶望敗後,“買得名花”卿憐,進貢給和珅的,是和珅的門客“程松”。“程松”,南宋朝錢塘縣知縣,因很久沒有得到提拔,乃獻一妾給當時專擅朝政的韓侂胄,取名“松壽”,侂胄因此妾名字竟然用程松之名“松”而驚訝,程松回答,“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此後,程松果然得到迅速提拔,官同知樞密院事。可是,這作爲和珅門客的“程松”是誰呢?陳文述的《卿憐曲》,爲我們提供了重要綫索:“卿憐本是琴河女,生小玲瓏花解語。十三嬌小怨琵琶,苦向平陽學歌舞。平陽歌舞醒繁華,移岀雕闌白玉花。幸免罡風吹墮溷,從今不願五侯家。侍郞華望殷勤顧,移入侯門最深處。欲使微名達相公,從今却被東風誤。”[注]陳文述: 《頤道堂集》,頁25。“平陽”,指王亶望。此云把卿憐送給和珅的,是一個侍郎。此侍郎給和珅送女子的目的,當然也是以此巴結和珅,故次句云云,也是用“程松”的典故。
陳文述《西泠閨咏》卷十四《玉蕊軒吊吳卿憐》文云:“卿憐吳人,中丞某公侍兒。中丞敗,爲琴河侍郎購獻相國。相國籍沒,卿憐賦詩自悼,聊落以死。余在都下爲賦《卿憐曲》也。”[注]陳文述: 《西泠閨咏》,頁582。既然稱“琴河侍郎”,那麽,這侍郎應當是常熟人。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和珅姬妾》云,此侍郎爲常熟蔣錫。[注]小橫香室主人: 《清朝野史大觀》(臺北: 新興書局,1987年),頁37。按清代常熟並無侍郎蔣錫其人。
李燧是河間(今屬于河北省)人,其父李棠,乾隆七年進士,在江南爲官期間,和袁枚等交往密切。李燧本人,也和袁枚曾經有較多的交往。嘉慶四年和珅垮臺的時候,李燧擔任浙江龍山鶴砂鹽課大使,年四十七歲。其《卿憐曲》的寫作時間無考,但就他的家世和經歷而言,該詩所寫,當有所據。陳文述《卿憐曲》,載《頤道堂集》之《詩選》卷一,[注]陳文述: 《頤道堂集》,頁25。沒有編年。但此詩之前,是《都下呈王蘭泉司寇昶》五律二首。可見當時他和王昶都在京城。王昶在乾隆年間就已經退休,回到家鄉青浦居住,當時陳文述怎麽會在京師向王昶呈詩?其一有“龍去鼎湖澄,攀髯恨不勝。烟波別圓泖,風雨拜橋陵”云云,可知乾隆帝去世後,王昶特意從家鄉到京師,參加乾隆帝的喪禮,因此,陳文述正好遇見他。當時的陳文述,才19歲而已。乾隆帝去世不久,和珅就垮臺了。陳文述的《卿憐曲》,應該就作于此時,所寫也必有所據。再者,他就是浙江人,因此,關于王亶望和卿憐的傳聞,也應該不是陌生的。後來,陳文述長期在常熟當知縣,和那裏許多士大夫非常熟悉,因此,關于卿憐、關于“琴河侍郎”的事情,他有可能後來在常熟還會聽到。如果《卿憐曲》中有誤,他會在後來編詩集的時候改正的。
筆者能找到的關于卿憐的記載,包括本文所涉及的,除了《一斑録》未云卿憐爲和珅侍妾外,皆云卿憐先是爲王亶望侍妾,後爲和珅侍妾,僅僅是大多表達委婉而已。筆者沒有發現和這矛盾的記載,可見這應該是事實。至于把卿憐送給和珅的,據陳文述的記載,是卿憐也就是王伏的常熟同鄉某侍郎。
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解决的是,這個爲了嚮和珅獻媚而把卿憐送給和珅的常熟籍侍郎到底是誰?馬星翼《東泉詩話》卷八,在敍述中亦僅云卿憐歸和珅,然又録卿憐在和珅伏法後所作詩云:“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紫燕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馬星翼云:“戟門,蔣姓,購送和處者。”[注]馬星翼: 《東泉詩話》(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頁1007。這就和陳文述所說完全符合了。蔣戟門,就是蔣賜棨!蔣賜棨,字戟門,常熟人。門第清華,其祖父蔣延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和張廷玉等齊名,謚號文肅。其父親蔣溥,官至東閣大學士,謚號文恪。其叔父蔣洲,官至山西布政使。其兄蔣檙,官兵部左侍郎。其本人長期擔任倉場侍郎和戶部侍郎等高官。蔣家這些人物,《清史列傳》中都有傳的。不僅如此,蔣賜棨在文化界也有較高的聲望,常和錢載、翁方綱、紀昀等名家一起詩酒風流。紀昀《紀文達公遺集》詩集卷十二《三十六亭詩》中,有《戊午二月八日同人小集》詩,參與小集的,就有當時已經六十五歲的“蔣戟門少司農”。[注]紀昀: 《紀文達公遺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72。據《清代職官年表》,蔣賜棨卒于嘉慶七年,則其生卒年當分別爲1732年(雍正十年)和1802年。
蔣賜棨與和珅的關係如何呢?他正是諂事和珅的幾個大臣之一!嘉慶四年,皇帝求直言之士,洪亮吉上《極言時政啟》,揭露朝廷和地方官員負國者多人。洪亮吉以此險遭不測,被流放新疆,雖百日後獲賜環,但仕宦生涯到此結束。他所上《極言時政啟》,見洪亮吉《卷施閣集》文甲集卷十續,[注]洪亮吉: 《卷施閣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847。但顯然是經過修改的。其他史料,保存了某些被删除的内容。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一引嘉慶四年八月癸亥上諭,云洪亮吉在此文“所稱諂事和珅諸人”中,“吳省欽則業經罷斥,蔣賜棨、韓鑅,雖尚列朝籍,亦不復向用”,“春間將和珅定讞時已明降諭旨,凡依附和珅者,概不必株連”。[注]平步青: 《霞外攈屑》(臺北: 新興書局,1987年),頁9。陳康祺《壬癸藏札記》卷六也有類似的記載。[注]陳康祺: 《壬癸藏札記》(臺北: 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694。可見,蔣賜棨之“諂事和珅”,是皇帝、朝臣們所共知的,官場和知識界當然也是知道的,更何况還有上諭在。又洪亮吉《卷施閣集》詩卷二十《單車北上集》之《書事》,即寫和珅垮臺,其中有云:“屈指承恩盼,南頭一侍郞。只緣新歲近,催送侍姬忙。粉墨乖淸議,銀黄奪舊章。浪傳收騎過,失足墮匡床。”[注]洪亮吉: 《卷施閣集》,頁804。這“南頭一侍郞”,應該就是蔣賜棨。“失足墮匡床”是“浪傳”,未知真假,但有這樣的傳言。至于“催送侍姬忙”,則應該是有過“送侍姬”的事實,才能作這樣的諷刺。要知道,洪亮吉寫這些詩歌的時候,蔣賜棨儘管因爲諂事和珅而由戶部侍郎降職爲光禄寺卿,但他仍然是朝官,仍然是知識界的人物,知識界仍有許多朋友,如果洪亮吉所寫不是事實,那麽,他和他的朋友,也還是可以發言反駁的。再說,洪亮吉畢竟是著名人物,他也犯不上造謠以吸引眼球。因此,給和珅送美女之類的事情,蔣賜棨是幹過的。
那麽,蔣賜棨是否有必要諂事和珅呢?他是在大約什麽時候,把卿憐送給和珅的呢?我們可以通過《清代職官年表》,看他當京官的仕曆,也許可以得到大致的答案。乾隆三十四年,蔣賜棨由山東運使入京,官倉場侍郎,次年,晋升戶部右侍郎,三十九年被革職,次年授順天府尹。四十二年,遷倉場侍郎,直到五十二年正月,才由倉場侍郎改爲戶部侍郎。此後,他一直擔任戶部侍郎,直到和珅垮臺後,他才被降爲光禄寺卿。可見他連續擔任倉場侍郎達十年之久,而沒有得到升遷,後又連續當了近十年戶部侍郎。清代地方、軍隊等的所有財政收支,都要經過戶部核銷,因此,儘管戶部侍郎才二品官,但權力非常大。蔣賜棨在這個官位近十年,沒有强有力的奧援,似乎難以如此。最有可能給他奧援的人,就是和珅。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由戶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到四十九年改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但仍然管理戶部,此後他的職務屢有升遷,但仍然長期管戶部。即使就工作關係而言,和珅和蔣賜棨也是非常密切的。和珅垮臺後,世傳卿憐所作十絕句,其八云:“白雲何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温。”[注]高洪鈞: 《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1期,(2003年1月)頁92。從嘉慶四年上推十五年,是乾隆四十九年。王亶望垮臺後,卿憐可能回到家鄉,和父母生活。乾隆四十九年,她被蔣賜棨物色到,送給和珅。到嘉慶四年,她和父母已經分別十五年。因此,蔣賜棨把卿憐送給和珅的時間段,應該在乾隆四十六年王亶望被殺之後,到五十二年他當上戶部侍郎之前,而最有可能的,是乾隆四十九年。當然,這僅僅是根據情理推測而已。至于卿憐被送給和珅的確切時間,現在很難考證明白了。
要給和珅送“侍姬”,也不是容易的事。選擇什麽樣的女子呢?除了年輕漂亮外,還要出身清白,才藝出色,氣質高華,見多識廣,能够應付大場面。此外,該女子還必須和蔣賜棨有一定的淵源,以確保她能够真心幫助蔣賜棨。蔣賜棨畢竟還是讀書人,畢竟還是滿門仕宦的官宦世家,還沒有無耻到把自己的姬妾送給和珅的程度。于是,前浙江巡撫王亶望的侍妾、蔣賜棨的小同鄉卿憐,就成了最佳人選了。
這裏,要對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中的“虞山浙東監司”再作一些探討。該文云:“時有虞山某中丞者,方爲浙東監司,諂事制府王亶望,遂進之,果得制府歡。”[注]朱駿聲: 《傳經室文集》,頁425。意思是說,是這位“浙東監司”,先把卿憐送給王亶望,王亶望被殺後,又是他,將卿憐送給了和珅。上文已經說過,在清代常熟籍官員中,沒有在浙江當過監司且後來官至巡撫者。不過,朱駿聲此說,是如何來的呢?這位“浙東監司”,也是由蔣賜棨致誤而來。
王亶望和蔣賜棨,確實是有過交集的,但不是在浙江,而是在山東。乾隆三十四年四月,王亶望由甘肅肅州道遷山東按察使,次年十一月,遷浙江布政使。蔣賜棨在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由山東運使遷倉場侍郎。因此,他們在山東有七個月的交集。此後,他們兩人,再也沒有交集了。按察使的品級,儘管略高于運使,但運使不歸按察使管轄,故他們在職務事務上,幷沒有聯繫。蔣賜棨完全沒有諂事王亶望的必要,考慮到他的門第背景,更是如此。後來,蔣賜棨的品級,長期在王亶望之上,且蔣是京官,王是地方官,也沒有統屬關係,蔣就更加沒有必要諂事王了。再說,如果在山東的時候,蔣賜棨就把卿憐送給王亶望了,這和古籍中所載卿憐的年紀,也相差不少。不過,“運使”這個官職,也稱爲“監司”。朱駿聲說把卿憐送給王亶望的是“虞山浙東監司”,而蔣賜棨在山東和王亶望共事期間是確確實實的“虞山山東監司”。或許,王亶望在常熟娶王伏也就是卿憐的過程中,咨詢過前同事蔣賜棨,或者得到過蔣賜棨的一些幫助,這也是有可能的,因爲蔣賜棨是常熟人,但蔣賜棨把王伏送給王亶望,我們看不出有這樣的必要。
總之,王亶望被殺後,其侍妾卿憐,當了和珅的侍妾。相關詩文、筆記、詩話中所寫,都是如此。把卿憐送給和珅的,是卿憐的同鄉、侍郎蔣賜棨。
這裏,順便交待古籍所載卿憐的結局。孔昭虔《卿憐曲》云和珅敗後,卿憐“又搖雙槳渡江歸,歸舟重過西陵渡。記得當時歌舞處,燕子都非舊日梁”,[注]孔昭虔: 《鏡虹吟室詩集》,頁589。可見她是歸江南故鄉的。陳文述《卿憐曲》中,有“將軍西第凝紅泪,阿母南樓夢白雲”、“昨日才歌相府蓮,今朝已嘆旗亭柳”等句,[注]陳文述: 《頤道堂集》,頁25。她似乎流落江湖,似乎回到故鄉,以娛樂業生活。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三十《題卿憐小像並序》云:“或云效綠珠之節,而錢唐陳文述《卿憐曲》,又似仍還故鄉者。”[注]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31。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云:“資産籍沒,相國賜盡。諸附相國者咸得遷謫。卿憐煢煢無依,于是席捲私槖,遁歸吳閶陸宅巷,將求蒲團禮佛,自懺夙孽。會某太守慕其姿,仍挾之去。”[注]朱駿聲: 《傳經室文集》,頁425。沈濤《匏廬詩話》卷下云:“仁廟親政,相國籍沒。卿憐流落人間,爲怨詩若干首,時年二十九矣。嗣後不知所終。”[注]沈濤: 《匏廬詩話》(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頁128。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十六亦云其“流落民間”。[注]徐世昌: 《晚晴簃詩匯》,頁259。雷瑨、雷瑊編《閨秀詩話》卷十四引《紅葉山房詩話》,則云其遁入空門。所載卿憐《興感》詩有“擬擇江南清雅地,一尊綉佛證前因”之句,[注]雷瑨、雷瑊編: 《閨秀詩話》(上海: 掃葉山房,1922年),第7頁。可爲之證。諸說不同如此,但似乎都是合理的,有這樣的可能。然鄧之誠《五石齋小品》之《掌故》又說她在和珅敗後作詩多首,“詩成後,投繯自盡”,此說和卿憐所作詩歌和其他的記載相矛盾,且就情理論之,不大可能。
三、 卿憐所作詩歌
卿憐所作詩歌,和珅敗後,就流傳于世。馬星翼《東泉詩話》卷八云:“吳卿憐絕句詩十首,自嘉慶己未有人傳之,並注甚詳,但不知何人筆也。”録其詩云:“曉妝驚落玉搔頭,宛在湖邊十二樓。魂定暗傷樓外境,湖邊無水不東流。”[注]馬星翼: 《東泉詩話》,頁1007。“嘉慶己未”爲嘉慶四年,正是和珅敗之年。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云:“相國既敗,卿憐爲《感世詩》廿四首,傳播人世云。”[注]朱駿聲: 《傳經室文集》,頁425。黄鈞宰《金壺七墨》之《金壺浪墨》卷七《吳卿憐》云:“頃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注]黄鈞宰: 《金壺七墨》,頁3981。沈濤《匏廬詩話》卷下云:“余嘗載其詩《續婦人集》中。”[注]沈濤: 《匏廬詩話》,頁128。
乾嘉間人解恕《蘧亭隨筆》所載最多,爲十首七絕,且有較爲詳細的自注。可惜此書僅有稿本,未嘗流傳于世,筆者無緣寓目。幸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研究員高洪鈞先生《吳卿憐外傳》中,盡録該書所載卿憐所作詩歌及自注,我們可以得而論之。[注]高洪鈞: 《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1期,(2003年1月)頁90—92。解恕《蘧亭隨筆》所載卿憐七絕十首,第一首即是馬星翼《東泉詩話》卷八所載“曉妝驚落玉搔頭”云云。《閨秀詩話》卷十四引《紅葉山房詩話》,云吳卿憐有《分香集》,並録其《自述》《志慨》《遇事》《興感》《即景》等絕句或斷句。其中《志慨》就是《蘧亭隨筆》所載卿憐十首詩中的第六首。鄧之誠《五石齋小品》所載卿憐《泪詩》十首,和《蘧亭隨筆》所載卿憐諸詩,次序和詞句只是稍有不同而已。此高洪鈞《吳卿憐外傳》已作詳細比勘。
這些詩歌,是否卿憐本人所作?此頗爲難言。清代詩話筆記等所載女子詩詞,爲他人假托者,並非罕見。如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三第七五條云:“明季用兵時,有女子劉素素者,被掠,題詩店壁云:‘天明吹角數聲殘,將士傳呼上玉鞍。恰憶當時閨閣裏,曉妝猶怯露桃寒。’”[注]袁枚《隨園詩話》(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册上,頁462。劉素素虎丘題壁的故事和這些題壁詩,其實都是出之于吳兆騫之手,見其《秋笳前集》卷五《虎丘題壁二十絕句》,“天明吹角”云云,正是其第一首。[注]吳兆騫《秋笳前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86。關于雍正間女詞人賀雙卿,是否實有其人,學術界有過不同意見,經人考證,似乎實有其人,但是,世傳由她創作的作品,是否都出于她之手?亦難以定論。托名康熙間江蘇巡撫侍妾劉碧鬟的詩歌,其實都是出于他人之手。[注]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南京: 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769。鄭光祖《一斑録》明確記載,王伏(也就是卿憐)的父親是“訓蒙學究”,因此,她很可能有一定的文化修養。王亶望是一個才子型的官員,卿憐嫁給他以後,也有很大的可能受到他的影響甚至教育和培養。因此,卿憐能够寫詩,應該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她真的能詩,且有作品傳世,當時,在江南地區大力扶持女詩人的袁枚、王文治等,爲何都沒有提到卿憐?常熟和卿憐同時代的女詩人衆多,且幾乎都是袁枚的弟子,爲何他們的詩文等,從來沒有提到卿憐?我們今天缺乏可靠的史料,無法確定這些作品是否出于卿憐之手,只能就相關詩歌的内容論之,且以情理推測。
《閨秀詩話》卷十四引《紅葉山房詩話》所載卿憐事,云吳卿憐有《分香集》,此詩集的名字,乃是用曹操臨終處理姬妾時“分香”給她們,並囑咐她們此後編織鞋子“賣履”爲生的典故,卿憐用以名其詩集,用以紀念和珅,表達對和珅深厚的感情,這是可通的。
有些詩歌,看似和事實不符,但還是可以說得通的。黄鈞宰《金壺七墨》之《金壺浪墨》卷七《吳卿憐》云:
(吳卿憐)《感遇詩》卽咏和事。顧其中有‘馬上王嬙’、‘玉笋敲殘’等語,和雖籍沒,眷屬未嘗流徙。當時薩彬圖承命查辦,請鞫使女,朝廷降旨切責,初無刑及婦女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泪沾衣,意固何所指耶?[注]黄鈞宰: 《金壺七墨》,頁3981。
確實,這些詩歌所咏,與和珅事不合,不過,此《感遇詩》,不僅感和珅事也,也可感王亶望事。阿桂《蘭州紀略》卷十七云,王亶望被殺後,其已經成年的三個兒子王裘、王棨、王焯,“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充當苦差”,尚有八個兒子,俱在六歲以下,則留在其家鄉山西,由地方官員管束,“待年至十二歲時,再行遵照前旨,陸續發遣伊犁”。[注]阿桂: 《蘭州紀略》(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43。王裘等流放伊犁,家屬當有隨行者,這正和“馬上王嬙”、“玉笋敲殘”相合,未必指卿憐自己,顯然,她是不能自比“玉笋”的。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十三《灤陽雜咏》有云:“鷄竿高建晃朝暾,盡遣流人返玉門。不獨夜臺思結草,旁觀也代感君恩。”自注云:“王亶望、雅爾哈善子孫久在戍所,有旨宥之。凡在此類,皆得援赦。”[注]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頁230。時爲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可見王亶望的子孫,確實是被流放的。
但解恕《蘧亭隨筆》載卿憐十首詩及其自注,大多未必出于卿憐之手。這些詩歌,以言和珅、王亶望及其家庭驕奢淫逸而導致垮臺爲大宗。如其一云:“曉妝驚落玉搔頭,宛在湖邊十二樓。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自注云:“己未正月八日曉起理妝,適聞和事。平陽王處遇事時,亦清曉,情景宛然在目。又王撫浙時,起樓飾以寶玉,人傳爲迷樓。和處池館,皆仿照上。王、和禍福,如出一轍。天道之常,有如流水。”其二云:“香稻入唇驚吐日,海珍列鼎厭常時。蛾眉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自注云:“和處查封日,有早餐者,因驚吐哺。王處查封時,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然。人每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嘩然,大嚼,謂之蘿蔔絲。”其中如“起樓飾以寶玉,人傳爲迷樓”,以及王亶望家人厭吃燕窩之類,有濃厚的誇張和傳說的色彩。其三云:“緩歌曼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綉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自注云:“和素有腿疾,然亦有愈時。仍是倩人扶入内廷,若爲相度者然。”和珅裝模作樣,自端架子,以顯示其朝廷重臣的地位,此非僅其家人所知,却非宜其家人所道者。其四云:“相公冠蓋列星辰,幽室傳聞盡貴臣。今日門前何寂寂,可知人語未曾真。”這分明是指責和珅拉幫結派、和位高權重的顯貴密室謀事,有不可告人的陰謀活動在,這正是皇帝的大忌!和珅本人,反正已經死了,但諂事和珅的朝臣例如蔣賜棨等,還在官場,讀來能不心驚肉跳!其九云:“一朝能悔即君才,項羽雄心月夜臺。流水落花春去也,伊周事業枉徘徊。”自注云:“和有‘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之句。”和珅如此自負其才,又是“項羽”,又是“伊周”,他到底想幹什麽?欲置皇帝和其他朝廷大員于何地?
這些詩歌中,和珅與王亶望的形象,都是負面的,他們被處死,罪有應得!其中的警示意味,是很明顯的。王亶望與和珅,對卿憐可謂不薄,卿憐對和珅的感情尤其深厚,至以“分香”名其詩集,但是,這些詩歌中,却充滿了對王亶望、和珅揭露、抨擊的内容。又,一個姬妾,對官場、對朝政,乃至對世事,理解得如此深刻,也很難使人信服。此外,這些詩中,作者分別稱呼和珅、王亶望爲“和”、“王”,都是如此,這明顯不是侍妾的口吻,何况以“分香”名其詩集,對和珅感情如此之深,豈有直稱其“和”的道理?
這些詩歌中,有五首是自悲自嘆。但其中所涉及的年齡或年份,也頗費猜測。如其五云:“蓮開並蒂豈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空是個中人。”其七云:“村姬歡笑不知貧,長袖輕裾翠黛顰。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還是淺嘗人。”其八云:“白雲何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温。夢裏輕舟無近遠,一聲欸乃到吳門。”當時是嘉慶四年,卿憐如果是廿九歲,十五年前是乾隆四十九年,卿憐僅僅十四歲,被送給和珅,不大可能,且王亶望在乾隆四十五年因丁艱離開浙江巡撫任,次年“甘肅冒賑案”發,他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巡撫任上以年幼的卿憐爲姬妾。當時卿憐如果是三十六歲,有可能在王亶望擔任浙江巡撫的時候嫁給他,也和其他記載中她在十五歲那年嫁給王亶望之說基本相合,但是,“廿九春”又作如何解釋呢?
其中有兩首詩尤其耐人尋味。其六云:“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紫燕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卿憐不怨恨和珅,却怨恨把她送給和珅的蔣賜棨,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其十云:“冷夜痴兒掩泪題,他年應化杜鵑啼。啼時莫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栖。”自注云:“分香何人?賣履何人?空梁落燕泥,如助妾之悲悼。”這仍然是表現她對和珅的感情之深。自注中所云,有譴責和珅的其他姬妾的意思在。此詩用曹操臨終前“分香”給姬妾、囑咐姬妾編履出售以謀生的典故,體現和珅臨終前對姬妾們的關懷和希望,可是,和珅死後,姬妾們都跑光了。其實,嘉慶帝只將和珅賜死,並未逮捕其家人,他的兒子豐紳殷德仍然世襲爵位,仍然是駙馬,見《清史列傳》等,故孔昭虔《卿憐曲》云:“幸免收孥輸織室”,陳文述《卿憐曲》亦云:“天恩高厚真難戴,族誅終貸房遺愛。已免厨車載屈氂,只勞廷尉收元載。”和珅的姬妾即使有跑掉的,其家也不會至于“空梁落燕泥”的境地。如果真的這樣,那麽,卿憐確實應該是殉節的了,至少也會在和珅家守節,如果回到家鄉,那麽,和那些各奔前程的姬妾,有什麽區別?更加不用說再嫁給別的男子了。
這兩首詩歌中,或許有某種寄托在。和珅在朝數十年,正如《清史列傳》之《和珅傳》所云,他“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下,逢迎饋賂,皆所不免”,[注]清國史館臣: 《清史列傳》(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册9,頁2700。這是嘉慶帝上諭所說。這些官員,包括那些諂事和珅的官員,受到和珅恩惠的,肯定不少。諂事和珅,這自然不是好名聲,是耻辱,相關官員,肯定不免愧悔的。但是,我國向來就普遍奉行“受恩必報”的道德觀念,和珅于他們有恩,他們自然要感激的。有愧悔,他們不能恨、也不會恨和珅,而只好恨給他們諂事和珅牽綫搭橋的“戟門”一類的人物,如果沒有此類人物,他們很可能免于這樣的耻辱。有感激,他們當然就“不怨”和珅,儘管和珅在當時是十惡不赦的人物。于是,“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害殺兒家是戟門”云云,就是此類人物心理的寫照。“分香”的典故,似乎暗喻和珅曾經給很多官員恩惠。和珅垮臺後,這些官員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當然不會選擇爲和珅“殉葬”或者“守節”。因此,“冷夜痴兒掩泪題”云云,或有對這些官員的諷刺在。
總之,古籍中所載所謂卿憐所作詩歌,即使其中有若干首确實爲卿憐所作,但全部出于卿憐之手,則幾乎不可能的,當有其他人托名卿憐寫的詩歌在。此類詩歌,大多對王亶望、和珅及其黨羽加以揭露、抨擊和諷刺,既是在和珅垮臺後一種社會情緒的委婉表達,也是對當時官場生態的一種警示。
四、 以卿憐故事爲題材的詩文
以卿憐故事爲題材的詩文,都是作于嘉慶四年和珅垮臺以後,甚至更晚一些,而作者大多是乾嘉之間人。那麽,王亶望被逮,在乾隆四十六年,距和珅垮臺,尚有十八年之久,可是,這十八年中,就現存古籍所載,很少有關于王亶望的詩文等記載,却在十八年後被人家編排故事,寫作詩文,這又是爲什麽呢?僅僅是因爲他的侍妾卿憐,後來成了和珅的侍妾?顯然沒有那麽簡單。
我們可以推測其中的原因。首先,王亶望爲人豪爽,能詩能文,書法尤其出色,是才子型的人物。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十一言其“行書筆力雄健,龍蛇飛舞”。[注]葉昌熾: 《緣督廬日記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669。其學問也不錯。他在浙江布政使任上,和三寶一起編《蓮華峰古迹考略》一卷。儘管現存的當時詩文作家的詩文集中,很難找到他寫的詩文,以及他出席詩文活動的記載,但間接的材料,還是有的。幾乎可以肯定,他和當時的許多詩文作家之間有來往。儲大文《存硯樓二集》卷十三《謝問疾啟》云,山西“平陽渭璜喬子,風調諧暢,天章之儔匹也。不遠數百里來視疾,其比《世說》煎藥真長之高誼,復何减焉?謹草此以志謝”。[注]儲大文: 《存硯樓二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36。當時,儲大文在山西。此“平陽渭璜喬子”,當是王亶望。“喬子”者,“王子”之假托也。周靈王太子王晋,字子喬,傳說後爲神仙,以“王子喬”名于世,不少王氏宗族,奉之爲遠祖。王亶望出事後,用其真實姓名,有所不便,故儲大文如此略使狡獪,以“喬”暗指“王”。不遠數百里來視疾,這還是王亶望早年的事情。可以推想,他當大官後,對文壇上的朋友,肯定也是不錯的,也會參加詩文等的活動。因此,“甘肅冒賑案”發生後,人們除了删除關于王亶望的詩文等記載外,也很少有人寫詩文等抨擊他,或有所不忍也。即使本文引用到的和卿憐相關的詩文、詩話和筆記等中,寫到王亶望,也幾乎都很委婉,極少直呼其名。其次,“甘肅冒賑案”之形成及審理,過程頗爲複雜,因素繁多。受到懲罰的直接涉案者200多人中,清廉、正直者亦有之,其中也有不少詩文作家,如和袁枚等關係密切的宋樹谷、楊芳燦等就是。非直接涉案的大員,也有多人受到懲罰,例如文壇領袖、陝西巡撫畢沅,就被連降三級。如果人們寫相關詩文,即使僅僅抨擊王亶望,但是,這對那些多少受到委屈的人來說,也是一種刺激,畢竟,他們是同案人物,或者是有關聯的人物。故王亶望身後十八年中,關于他的詩文等記載極少。
和珅就不同了。儘管也有如吳省欽、吳省蘭兄弟,以及蔣賜棨等若干漢族高官諂事他,但更多的漢族士大夫,對他是沒有好感的,甚至與他有所鬥爭,如錢灃、謝振定、管世銘等人即是。此類事迹,後來尤其爲人津津樂道。和珅垮臺,當時許多人作詩,反映其事,當然,寫得隱晦婉轉,也在情理之中。也許因爲“甘肅冒賑案”之重大,與和珅案相當,故人們在寫和珅案的時候,爲了加强警世效果,就把二者聯繫起來,而卿憐就是二者之間的紐帶。某些假托卿憐的詩文是如此,關于卿憐的詩文等也是如此。這些作者的筆鋒所向,不是卿憐,也不是王亶望,而是和珅。就筆者所見關于卿憐的詩文或記載,其作者幾乎都是我國東南人士,或者在東南部擔任過職務,而東南是有清一代受當局控制最爲嚴厲的地方。這是令人深思的。
在以卿憐故事爲題材的詩歌中,最爲突出的是分別由李燧、陳文述和孔昭虔分別寫的三首梅村體同名長詩《卿憐曲》。李燧(1753—1825),字東生,號青墅,河北河間人。歷官浙江下砂頭場大使,有《青墅詩稿》十卷。袁枚《隨園詩話》之《補遺》卷七第五十六條云:
余集中有《佳兒歌》,爲同年李竹溪棠之子燧作也。三十餘年,問消息不得。今年在杭州,遇李婿陳鴻舉,爲仙居令,誦其近日句云:“體因慣病翻忘藥,人不工詩亦自窮。”嗚呼!才則猶是也,而近狀可想矣。[注]袁枚: 《隨園詩話》,頁757。
李燧《卿憐曲》,見陶梁《國朝畿輔詩傳》卷五十四,其詩集《青墅詩稿》未收,是集外詩。此三人中,其年輩爲最長。陳文述(1771—1843)爲著名詩人,嘉慶五年舉人。孔昭虔(1775—1835),字元敬,號荃溪,山東曲阜人。嘉慶六年進士,歷官貴州布政使,有《鏡虹吟室遺集》。他們這三首詩,都沒有明確的編年,應該是在嘉慶四年以後不久所作,上文已言之,此不贅。
這三首詩,充分發揮了梅村體適合鋪敍的長處,鋪敍竭盡豪奢的“色”和幻滅蕭條的“空”,都酣暢淋漓,而抒情效果,以此得到了加强。其重點都是寫和珅,而不是王亶望。卿憐和王亶望的故事,僅僅是這些詩中類似于“引子”的部分,且都很委婉。此上文考卿憐之被送入和珅家的部分已引用之,此不贅。就情理而言,卿憐如果沒有在王亶望那裏的歷練,也難以適應在和珅家的生活,甚至就沒有資本被蔣賜棨選中,作爲送給和珅的禮物。
以濃墨重彩鋪敍和珅的驕奢淫逸,不僅是此三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重點所在。不過,具體内容及其表達,此三詩又有不同在。李燧多寫和珅之奢侈,而多以卿憐所見所歷出之:
綺閣連雲夾道斜,武安甲第逞豪華。拚將壯歲調羹手,妝點中朝宰相家。風光到眼仍如故,雕闌步障重重護。錦佩光搖明月珠,玉階穩稱蓮花步。……相公才思孰能儔,領袖鵷班第一流。歌扇舞裙爭獻媚,銅山金穴鎮持籌。錦屏十二雲鬟簇,華筵夜夜燒高燭。擬把良宵有限歡,盡消人世無窮福。[注]陶梁: 《國朝畿輔詩傳》,頁686。
孔昭虔則多寫和珅耽于淫樂:“相公家世擅奢豪,司隸威嚴戚里驕。門外弓刀傳赤幘,屏前環佩列紅綃。朝回日日耽歌燕,曲房行樂無人見。五夜分熏侍女香,三春頻起催花宴。新妝各自媚春華,誰是平泉第一花。”[注]孔昭虔: 《鏡虹吟室詩集》,頁589。陳文述則重在渲染和珅之權勢地位,以第三者的視角敍述:
相公早歲直龍樓,炙手熏天第一流。襄邑金多頻起宅,高安年少已封侯。富貴功名古來少,美麗金貂都道好。十庫珍逾内府充,九州貢比公家早。許降同昌是國恩,春風油壁月華門。戟門別起汾陽里,粉碓頻頒沁水園。不疑原是梁家弟,棠棣碑前恩禮異。瀚海河源幾度行,居然功業齊驃騎。廿年樞府秉鈞衡,靑犢西南正阻兵。餉運半從私室飽,軍書例有副封呈。相公此日權難謝,奉御曾無休沐暇。騎馬常從禁殿行,肩輿直到宮門下。……相公此際太猖狂,絕席軍容敢雁行。九列公卿稱弟子,頭行厮養傲侯王。[注]陳文述: 《頤道堂集》,頁25。
相比之下,陳文述所敍,揭露的力度最大。
至于寫和珅之垮臺,三詩亦有不同。李燧還是從卿憐的角度鋪敍:
一聲驚落玉搔頭,舉室倉皇泣楚囚。離魂舊冷烏衣巷,斜日新關燕子樓。封侯頓醒黄粱夢,也知負罪丘山重。執法寧嫌瓜蔓抄,鳴岡爭賀朝陽鳳。西曹咫尺路迢迢,零亂殘魂不可招。那許痴情分賣履,枉拋心計積胡椒。可憐寂寞春宵永,猶認熏香侍早朝。[注]陶梁: 《國朝畿輔詩傳》,頁686。
孔昭虔則從第三者的角度予以敍述:“不信冰山一旦傾,連宵貫索度台星。中樞密敕收元載,御史交章劾竇嬰。九卿執法原難免,八議殊恩從末减。絕命哀吟枉費辭,牦纓盤水猶寬典。”[注]孔昭虔: 《鏡虹吟室詩集》,頁589。陳文述則從和珅的視角鋪敍:“御史彈章何待諷,側耳東厢短轅鞚。到此方知獄吏尊,他生枉作河神夢。太息墻高不見春,圜扉冷月照孤臣。《唐書》盧李應同傳,不作神仙誤此身。”[注]陳文述: 《頤道堂集》,頁25。至于和珅敗後其府邸的凄凉,三詩也都是盡情渲染,而多以卿憐出之。
就此三詩中所寫看,李燧他們都是讀過卿憐或托名卿憐寫的那些詩歌的。李燧所云“鄉關迷望更牽情,綿綿絮語愁中句”,[注]陶梁: 《國朝畿輔詩傳》,頁686。似乎還不那麽明確,那麽,其餘二位則很明確了。孔昭虔云:“燃脂自寫浮生夢,樂府雙聲唱《懊儂》。妝台獨曲翻囉嗊,荷珠風蕩不成圓。”[注]孔昭虔: 《鏡虹吟室詩集》,頁589。陳文述云:“獨有紅閨絕代人,網絲塵迹吊殘春。將軍西第凝紅泪,阿母南樓夢白雲。哀詞宛轉吟香口,珠啼玉泣嗟誰某。昨日才歌相府蓮,今朝已嘆旗亭柳。辛苦何人作鴆媒,杜秋娘曲不勝哀。”[注]陳文述: 《頤道堂集》,頁25。所謂“鴆媒”云云,就是卿憐詩中所云“害殺兒家是戟門”者也。可見在他們寫《卿憐曲》的時候,卿憐或者托名卿憐的詩歌,就已經流傳了。
以卿憐故事爲題材的詩歌,除了以上三首梅村體外,還有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三十《題卿憐小像並序》三首絕句,編年在嘉慶十九年。小序也提到了陳文述的《卿憐曲》。其一云:“省識春風只畫圖,似聞慧業比人殊;舊時響屧廊邊住,嫁婿端應西子湖。”此云卿憐爲吳門女子,嫁給當浙江巡撫的王亶望。其二云:“笙歌葛嶺幾朝昏,量盡明珠價莫論。無奈楊花易漂泊,又隨風去墮朱門。”此云卿憐大受王亶望寵愛,享受無度,無奈王敗,而歸和珅。其三云:“十首吟成薄命詞,死生踪迹費猜疑。可憐碧玉年猶小,兩見瀛波淸淺時。”[注]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頁431。此云年輕的卿憐,身歷了兩次如夢富貴的破滅。
那麽,人們爲什麽樂于傳播或寫作卿憐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在當時有什麽樣的社會意義呢?從表面上看,是人們樂于聽聞、傳播貪官污吏的緋聞情事,或以此進一步在道德上打擊他們,體驗自己的道德優越感,或以此欣賞他們的此類經歷,或以此進一步領會世事無常之類的“色空”哲理,或以此滿足探秘富貴者私生活的心理,或以此欣賞才情辭藻,因爲此類作品,最適宜展現作者的才情辭藻。就作者而言,或以此炫耀其才情辭藻,或以滿足社會心理需求而獲得被肯定、實現自身價值的感覺,或用以行所謂的教化,正如朱駿聲《卿憐小傳》中,作者警告世人:“顧獨疑處高位者,溺于聲色,鮮克令終。懷安縱欲于内,罔上營私于外,自作之孽,彼媚灶以求福而得禍者,又何心哉!”[注]朱駿聲: 《傳經室文集》,頁425。除了以上所云外,此類作品,似乎還有更加深層的意義在。
卿憐被作爲性賄賂送給達官貴人,但是,這些作品,幾乎都忽略了這樣的性質,僅僅是以此作爲故事的引子或者紅綫而已。這些作品的重點,還是在于才貌雙全的卿憐先後和王亶望、和珅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所鋪敍的驕奢淫逸。就這些詩文等記載中看,卿憐先後深受王亶望和和珅的寵愛,獲得奢侈的生活,儘管還沒有到“出賣風雲雷電”的地步,但有的記載中,她也以丈夫的權勢爲人爲己謀取私利。朱駿聲《卿憐小傳》云:“卿憐既專制府寵,又倚監司爲外援,寖至黷貨。冬日織孔雀毛爲被,實以香屑。又嘗爲西湖游,侍婢數十人,各曳霧縠,望之如神仙然。”又云:“值二十初度,相國預告門下士,外自督撫下,每有厚獻,而尚書、侍郞素附相國者,且親至,爲吳夫人捧卮。有自平明至日昃,鵠立俟者數輩,股爲之疲,而卒不可見者。”儘管其中明顯有不實之處,但卿憐先後靠王亶望、和珅過奢侈的生活,則是肯定的。這樣說來,王亶望、和珅,都有恩于卿憐,而“卿憐兩負之。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信矣。抑申公巫臣所謂不祥人也。”[注]朱駿聲: 《傳經室文集》,頁425。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三十《題卿憐小像幷序》中,說卿憐在和珅敗後,“或云效綠珠之節”。[注]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頁431。綠珠爲石崇侍妾,石崇敗,綠珠跳樓自殺以殉。這似乎是對卿憐的美化,但其中也有作者乃至社會的觀念在,這就是,受恩的卿憐,應該爲施恩者殉節。沈濤《匏廬詩話》卷下云,他尤愛世傳卿憐所作的兩句詩:“‘金谷輸人傳墜粉,他家夫婿是英雄’,不减豫讓‘衆人’、‘國士’之論。”[注]沈濤: 《匏廬詩話》,頁128。意思是說,王亶望也好,和珅也罷,都不是英雄,都不值得她爲他們殉節。這又是另外一種觀點。他們確實不是英雄,是罪犯,都不值得她爲他們殉節,可是,寄食于罪犯,靠罪犯過奢侈生活,乃至倚仗罪犯作威作福,又作如何說法?
此類作品,實際上,在當時還有一種隱喻在。王亶望、和珅權勢顯赫的時候,他們的下屬、幕僚以及其他各色人等中,有多少人用種種方法攀附他們,從他們的種種非法所得或者違法活動中得到過好處?這些人,就是朱駿聲所云“彼媚灶以求福”者。王亶望或者和珅垮臺後,那些人失去的,僅僅是一兩座靠山而已!那些人,還可以繼續尋找新的靠山,一如王亶望垮臺後卿憐嫁給和珅,繼續過驕奢淫逸的生活,再不濟,也是歸老林下而已!一如在和珅垮臺後,卿憐歸老家鄉或者隱居江湖間。卿憐,就是這些人的一種隱喻。“金谷輸人傳墜粉,他家夫婿是英雄”之類的詩歌,正是對這些人的辛辣嘲諷!卿憐題材作品、卿憐的作品乃至那些托名卿憐的詩歌的流傳,也體現了人們對這些人的態度和感情這些社會情緒。
結 語
吳地常熟女子王伏,嫁給浙江巡撫王亶望作侍妾,以卿憐名。乾隆四十六年,王亶望因在甘肅布政使任上所犯“冒賑案”被殺後,卿憐被其常熟同鄉、和珅黨羽、侍郎蔣賜棨送給和珅爲侍妾。嘉慶四年,和珅垮臺。卿憐所作或托名卿憐所作幷且以她的經歷和情感爲題材的詩歌,開始流傳。以其故事爲題材的詩文、詩話、筆記等廣爲流傳,其中不乏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是當時官場生態和文化生態的體現,除了娛樂化的因素外,其意主要在抨擊貪官、警示世人,諷刺那些當初攀附貪官、受到貪官恩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