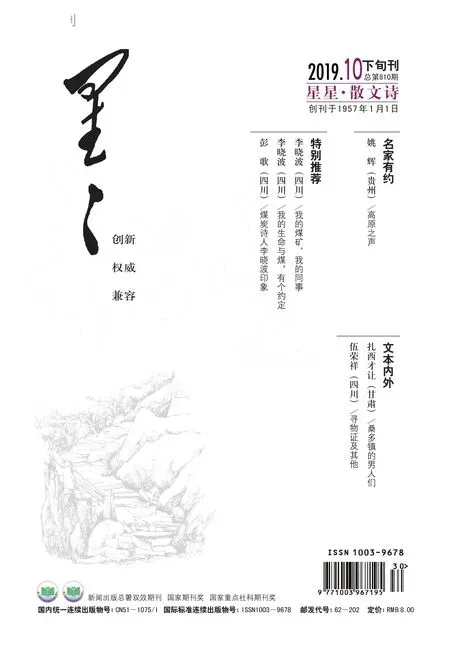历史册页(组章)
永济普救寺
峨眉塬上的风吹了千年,还在吹。吹薄历史沉甸甸的夹页,却没吹走一叶小小的梨花。
一座寺庙,用它浩淼的佛光,普度众生。
一座寺庙,用它的包容,接纳一个纤弱小女子的月光和琴声。
我在纤纤修竹之上,打量,唐朝一个叫元稹的诗人,最初折起的那一页初恋的红叶。
我在桃花灼灼的春光里,捡拾,元代王实甫丢在时空里那一响彻云霄的呐喊,绝唱。
其实,对于普救寺,我只是以一种简单的邂逅,便越过它历经七十二磨难的台阶。
只是让梦来了一次千年的飞翔,就让自己跌落进那场溶溶的月色。
走进,是一种单刀直入的触摸。
在一个叫张生逾墙的豁口处,一曲蒲剧,和正统的历史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
从此,天下有情人,才终于得以正儿八经地抛头露面。
红娘传简,是一颗少女的心,触痛了另一颗少女的心。
拷红,是历史对历史的问责,也是历史对历史最后的袒护。而一个弱女子卑微的胸口,此时,正燃烧着一股烈火。
这火,一下,就映红一座千年古刹。
仿佛一只美丽的蝴蝶,轻描淡写,风轻云淡,便飞入那爱情的花丛。
而,峨眉塬上的风还在吹。
它要吹散黄河里一簇浪花吗?
它要吹散莺莺塔前那清越的蛙鸣吗?
但一直吹的风,却没有吹散普救寺大钟楼上,一位书生眺望远方和爱情的绵绵思绪。
更没吹散千年之后,曹雪芹笔下那滴晶莹的泪。还有,戴望舒《雨巷》里那滴丁香一样的雨。
鹳雀楼
当历史与我打个照面,不偏不正,我也与一只鹳影撞个满怀。
站在鹳雀楼前的空场上,我伸手,触摸。想摸到什么呢?
是一座军事戍楼的威仪,还是朝代与朝代更迭的星转斗移?
而最后,我摸到的却是一个人被风撩起又被风放下的薄薄的青衫。
鹳雀楼,是一座现代仿唐建筑,气势不减当年。油漆彩画,古典风雅。
拾阶而上,步华夏上下五千年,历河东风流才俊数十人。期间,一手握着唐朝的紫气,一手握着剪纸年画。
极顶:再揽河山入怀,自然有怡情云上之慨叹!
依楼西南角上,是一座唐朝诗人王之涣的铜像。
仿佛,在时间深处,织布机吱吱作响的声音,揉黄土叠涌,依然还显得那么苍茫;
仿佛,在岁月之上,酿酒工人的号子声,和黄河涛韵,依然还显得那么低哑而厚重。
鹳雀楼,因诗而名的鹳雀楼哦。
鹳雀楼,因一种文化标识,耸立在历史肩头的鹳雀楼哦。
登高,摸到的应该只是诗人博大的胸襟和情怀。
而下来,就一定会摸到庶民曾经沧海桑田的悠悠呼吸和命运!
万荣秋风楼
汉天子的威仪,还和一座巍峨的楼一起,站着。
一千年,两千年,秋风还在吹。吹薄了厚厚的历史,吹薄了远处的河山。但,却没有吹薄一曲词赋,和兰菊悠悠的芬芳。
汾河之上,谁在泛舟?
峨眉台上,谁在鼓瑟?
歌以迥远,楼以高耸。
水含秦晋,惠泽四方。
上有皇天兮,皇天渺渺。
下有后土兮,后土绵绵。
秋风楼,用四周之回廊,行草历史;
秋风楼,用飞檐和斗拱,挑着苍茫的诗经。
之后,又是谁,使劲吹旺一炷香火,像吹旺头上的三尺神灵,像吹旺我们骨头里的火焰。
以祭祀的形式,与秋风共舞?
在秋风楼上,我一站,就让自己站了二十个世纪。
在秋风楼上,我一回头一转身,就错过了大汉和隋唐明清。
但,我还是没有错过
——汾阴睢地的远处,那场浩浩荡荡而又气吞山河的秋风!
运城盐池
众神在上。阳光。风。
四千年的水,以一种生命的质地,摇曳。
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白和纯,翻晾着人类的进程,和文化。
深度的掘进,骨子里的咸或甜。硬和直,一路伸张;即是弯曲,也如弓的秉性。
我在寻求,那些拉纤的汉子。他们黝黑的梦。
我在探寻,古盐道一匹马日行千里的张力,和它目光里燃烧的火焰。
九州十八府,方圆天地间。
古老的河东,用璀璨的星光,点盐成金。
一张《南岸采盐图说》,是一幅画卷。肩着、持着、拽着、导着,如同时间深处的一次朝圣。
采盐人,他们用地道的方言,还原历史。
采盐人,他们用纯正的乡俗,镌刻睿智。
艺术是一种夸张,而真实往往只存在于一种灵魂里的记忆。
鸣条之侧,南风薰兮。远古的祖先在上。
白花花的盐,白花花的骨头。
我相信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书简和史册里的记述。
我相信一种文化,它只存在于浩瀚的时空里。一直的,一直的,都在那里。像一种点缀,更像一种经久不息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