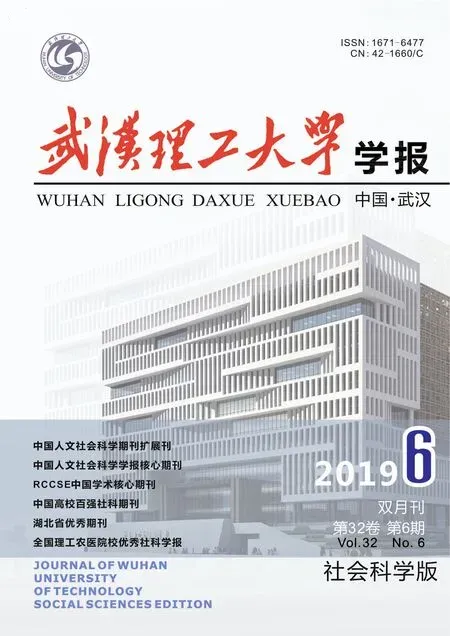论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
李红文
(湖南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
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过度关注义务的道德底线或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超常义务和道德理想。一些当代有影响力的伦理学家,都对道德生活中的崇高理想持怀疑态度,认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必定会与生活中的其他目标和责任相冲突,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其他值得关注的事情,如个人计划、家庭关系、友谊等[1]。我们承认,道德理想只是人们生活的考虑因素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它并不比个人爱好、娱乐等其他个人追求更有价值。然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使得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道德理想的地位:一是道德理想是值得追求的,道德卓越的典范是值得效仿的,它有助于指导和激励我们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二是它可以扩展现代伦理学的视野,不再是仅仅关注规范伦理的抽象原则、规则、义务等理论体系,而是将道德美德、道德理想纳入到伦理学理论的综合框架之中。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意味着,除了道德原则之外,追求令人赞美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抱负在道德生活中应该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 道德理想及其类型
道德理想在通常的意义上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崇高的道德目标,这种目标需要个人独特的道德意志力和持久不断的行动才能予以实现。比如,雷锋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所表现出来的崇高道德品德,是通过多年持久的无私奉献的行动来实现的,哪怕是这些行动是举手之劳的一桩小事,它也能通过长久的努力与坚持内化凝练成一种个人的崇高品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树立起来的各种道德楷模,他们无一不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不懈地做着平凡不同的小事,怀着一种敬业之心将它做到完美与极致。
那么,哲学家们所指的道德理想究竟是什么?弗兰克纳(Frankena)明确地说,拥有道德理想意味着想要成为具备某些特定道德品格特征的人,比如道德勇气、人格完整性[2]。当然,除此之外,像慷慨、行善、正直、忠诚、诚实等都属于道德品格的范畴。很显然,弗兰克纳是通过道德美德来定义道德理想的。这种定义虽然抓住了道德理想的核心本质,但是它没有区分道德理想和道德美德,甚至是有点将道德理性与道德美德混为一谈了。
道德理想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理想或目标,而不单纯地指个人性的道德品格。不可否认,道德品格或美德可以成为特定个人的理想或目标,并且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值得敬仰的道德模范都是这么去做的。道德理想之为理想,就在于它超越了个人当前的现实情境,它要求个人克服重重困难,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去达到或完成。这种超越性意味着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少数人才能做到,普通大众、芸芸众生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到。理想之为理想,就在于它的超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当下、指向未来的特定目标。道德理想也是如此,它是将当下还无法实现的某种未来的伦理目标作为个人、社会或国家的奋斗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理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或层次,即个人道德理想、社会道德理想和国家道德理想。很显然,这种区分是根据道德主体的层次性、结构性来划分的。个人道德理想是指向特定个人的,属于个体层次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设定适合自身情况的道德理想,只要这种理想不违背社会国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底线。个人道德理想往往是和自身职业紧密相关的,由于社会分工与职业发展的不同,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体往往秉持不一样的道德理想,例如一个学者与医生的道德理想是不同的,学者以追求真理、探索知识、实事求是为最高伦理价值目标,而医生则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职业最终之理想归宿。
社会道德理想和国家道德理想超越了个人道德理想的个体性,从而进入到某种超个体性的宏大话语体系之中。社会层面的道德理想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也可能是由官方意识形态来确定的,而国家层面的道德理想则毫无疑问是由国家权力来确定或号召的,从而起到一种价值引导性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内容,在个人层面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道德规范,在社会层面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美好社会目标,在国家层面提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囊括了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它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确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的产生虽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党意志,但其内容却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基本内容。
二、 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
道德理想能否构成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它是否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或者部分地去遵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负有实现道德义务的责任,这牵涉到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通过仔细地研究考察,对此我们提炼出三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主体无论何时都有义务去实现或达到道德理想,或者至少要朝着这个理想的目标去努力。持有这种观点的有功利主义哲学家布兰德(Brandt)和斯洛特(Slote),他们认为我们有持续不断的义务去实现某种特定的道德理想。一些神学家追随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所能够完成的作品不可能超出上帝的律令要求之外,但每个人都应该在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中追求至善的理想。康德伦理学在本质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完全服从于义务的行为才是可称之为道德的行为,那些不属于义务的行为不能说是道德的行为,对道德的追求不可能超出义务之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道德理想超出了道德义务之外,属于一种份外行善或超义务行为(supererogatory)。弗兰克纳和彼彻姆(Beauchamp)持有这种观点[3]。在他们看来,完成道德理想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没有实现道德理想的行为既不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也没有违反道德义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多,道德理想确实如此,它的超越性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如果一种道德行为的要求对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那么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去遵守它呢?基于现实主义和人性弱点的考虑,人们在道德生活中都会做出妥协,而只有那些有真正的坚定的道德信仰之人才能够做到。
第三种观点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它认为有时候道德主体有义务去实现道德理想,有时候实现道德理想属于份外行善,而有时候实现道德理想既不属于道德义务,也不属于份外行善[4]。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一种中间路线,既不认为道德理想是绝对的道德义务,也不认为它仅仅是超道德义务,而是主张根据具体的案例情景来分析它的属性,不能下一个绝对的判断。基于对道德事实复杂性的考虑,行为主体究竟是否承担某种道德理想的责任,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么,这三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道德理想的属性究竟该如何界定?对此,我们要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不得不说,前两种观点都有很明显的弱点。
第一种观点对道德行为的要求显得过于苛刻。要求道德行动者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去实现道德理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道德理想来行事,这估计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拜耳(Baier)幽默地指出,普通人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之后,回到家里听听音乐、喝喝小酒、放松放松,我们不能据此就谴责他没有完成更大的理想目标,没有为世界创造更大的善[5]。这种谴责显然是不公平的,普通人只要没有违背基本的社会道德原则,完全有自由过自己想要的、值得一过的生活。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医生都按照白求恩的道德标准去行事,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像雷锋一样永远做好事而不求任何回报。当然我们可以号召人们向这些道德模范人物学习,并且我们确实发自内心地赞美、讴歌这些人物,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人们做不到他们那样的高度而谴责之,任何一个人的平凡生活都是值得过的。
与第一种观点相反,第二种观点不是显得过于苛刻,而是对道德行为的要求显得过于宽松。始终将道德理想定义为义务之外的行为,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严格的理由去追求它,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理想并不在个人责任范围之内,它只是某些道德卓越之人的可选择性行为。这种观点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然而大多数人的想法和信念并非始终是对的。在人的一生中只做那些属于自己的分内之事,绝不做一丁点超越义务的任何事情,这虽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是不怎么完满的。一个始终坚持道德标准最低纲领的人,我们只能说他不是一个坏人,但也称不上一个“好人”或“德性完满的人”。总之,终其一生不做任何一点属于道德理想的事情,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看是有缺陷的。
如果前面两种观点都不合适,那么第三种观点是否就能站得住脚呢?道德理想在什么情景下算是一种道德义务或超义务行为呢?又或者既不是道德义务又不是超义务行为呢?如果道德理想是一种道德义务,那么就对人的行为构成了基本约束;如果不是义务,那么它就失去了这种约束力。毫无疑问,道德理想在大多数时候的确是超义务行为,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某种形式的道德义务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我们对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的深入分析和理解。
有些哲学家认为,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并不总是分外行为、义务之外的行为,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是一些人的分内之事。例如,诚实(veracity,sincerity)是一种做人的美德,也是一种道德理想,很多人经常会有撒谎或欺骗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不说谎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医生而言,其职业角色要求他有讲真话的义务,至少在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场合都必须讲真话,即便是面对一些患有癌症而又心理脆弱的病人,医生也应该对病人的家属诚实。
三、 超常行为与分外行善
道德理想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如何确定道德标准。按照通常的理解,道德标准有两个基本的层次:常规道德标准和超常道德标准。前者就是适用于每个人的公共道德(common morality),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底线,包括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则所规定的义务,如不伤害他人的基本义务。后者是道德主体可以自行选择的道德目标,它并不要求每个人都不偏不倚地去做到,因为它超越了常规的道德标准,比道德底线的要求更多。
据此,我们可以把人类的道德行为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正确的和义务性的行为(如讲真话);二是错误的和被禁止的行为(如杀人);三是选择性的和道德中立的行为,它既不是错误的也不是义务性的;四是选择性的但具有道德价值、值得赞扬的行为[6]。前面两种行为在我们的日常道德生活中很常见,其中正确的、义务性的行为属于积极正面的道德行为,而错误的、禁止性的行为则属于负面的行为。而后两种行为属于选择性的道德行为,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其中,第三种行为讨论得较少,而第四种就是符合超常道德标准的行为,人们一般把这类行为称之为道德理想。
超常行为,从字面或词源学的意义上是指它超出了一定范围或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一种行为要成为超常行为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它是选择性的,非选择性的行为属于不得不去做的义务行为;第二,超常行为超出了公共道德的期望或要求,超常意味着超出常规;第三,超常行为是行为者有意识去实施的且有利于他人的行为,行为者主观上知晓做这件事对他人或社会有好处;第四,从道德评价来说,超常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它对他人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把道德理想理解为超常行为,且把超常行为界定为超义务行为,那么很显然,道德理想就是超义务行为。但是,超常行为就一定是超义务行为吗?在此,“超常”可以有两种理解:超越常人和超越义务。如果道德理想仅仅只是超越了常人的行为,还不能算作是超义务行为,因为常人的道德水平可能会低于一般的道德底线,在这种情况下的超常行为可能只是满足了道德义务的要求而已。例如,在一个大部分人都作恶的群体中,有一个人凭良心选择了不作恶,那么他的行为虽然属于超常行为(不同流合污可能面临着同伴们的很大压力),但也只是一种义务性行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要求;在一个医德医风败坏的医院中,当大部分医生都收受红包贿赂,而只有一个医生坚持拒绝收红包,他的行为属于超常行为,但绝不是超义务行为,而只是一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而已,尽管我们会因他的行为难能可贵而赞扬、钦佩(他居然能在如此恶劣的风气中坚持医生的基本操守)。由此看来,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评价是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
如果我们将“超常”理解为“超越常规义务标准”,那么道德理想就是一种超义务行为。对于超常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它要求该行为是选择性的,但是许多英雄和圣人在做出道德理性行为时,通常会使用“应当、责任”等词来描述他们的行为,“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毫无选择”、“这是我的责任”。这意味着英雄和圣人的道德责任感要超越于常人或者是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他们的义务是个人性的、自我赋予的。例如,医生在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竭尽全力,将自己的生命置身于巨大的疾病风险之中。在正常的灾难或风险面前(如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地震),人类需要某些人勇敢地站出来做出牺牲,而那些英雄人物通常会把挺身而出看作是自己必须做的,觉得不这么做就会感到内疚。
超义务行为并非总是格外艰难、代价高昂或有巨大风险的。那些在艰难环境中挺身而出的人当然是道德英雄和楷模,是值得高度赞扬的行为。但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并不需要我们成为英雄或圣人才能做到的,而是作为普通人就能去做的事情。生活中的很多“举手之劳”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多,就能够完成超义务行为。例如,搀扶老人过马路、给地震受灾群众捐款捐物、自愿献血、在空闲时间从事志愿服务、原谅他人的错误等,这些都在个人能力范围之内,且不要付出过高的代价(如生命代价)。这样一些超越义务的行为通常被视为分外行善,这里所谓的“分外”就是指在个人职责和常规义务之外。
如何确定义务与超义务行为的边界,这在具体的案例情景中并不是那么明确。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根据一个人的角色、工作职责来判定义务的范围,但这并不那么绝对。例如,一个护士照看临终的绝望病人的角色义务是什么?是每周花40个小时的时间照看病人?还是帮助病人克服困难和挑战?如果以工作时间来确定,那么每天8小时工作之外的付出就算是超义务行为。即便是8小时之内的工作,医生也需要格外的耐心、韧性和友善,医生职业精神要求他们以积极审慎的态度投入到临床诊治活动之中,但这种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也并非是毫无边界的。在一些特殊的人际关系中,比如人情债、近亲,一些原本属于选择性的行为也往往会变成义务性的行为,人们感到不得不去还别人的人情,不得不去为了近亲去做一些特殊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如果换作是没有亲戚关系的陌生人就不必去做的。
从严格义务到最高的道德理想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性的谱系。这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1)严格义务;(2)弱义务;(3)一般的超出义务的理想;(4)圣人般的、英雄般的理想。其中,严格义务属于公共道德的核心要求,通常被理解为道德的底线或最低要求;弱义务则处于公共道德要求的边界上,相比严格的义务来说并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然后从弱义务过渡到一般性的、较低层次的超义务行为,如帮助迷路的人;再到谱系的顶端就是较高层次的超义务行为,如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这是一条从义务行为到选择行为的全景谱系。
然而,人类的道德生活十分复杂,有些医疗人员的许多有利行为横跨了“义务”和“超义务”两个领域,特别是在弱义务和一般性的超义务行为之间。比如,医生的角色义务是“救死扶伤”,这一职责的范围并不明确,边界模糊。希望医生和护士鼓励与安慰病人,这似乎是职业义务,但它却没有写进职业准则。如果医生放下自我利益、冒着风险照护病人(如冒着感染病毒的危险救治SARS病人),这究竟是职业义务还是属于超义务行为呢?如果一个医生没有表现出审慎的美德,没有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那么似乎也只能评价说他不是一个“好医生”。在很多人心目中,一个“好医生”的标准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合格医生,也就是说从合格到优秀与卓越,这中间还有相当庞大的地带。
四、 道德美德与道德卓越
追求道德理想的人通常都表现出令人赞赏的美德,它是人类身上展现出来的优秀道德品质和人格特质,如勇敢、智慧、耐心、好客、节制等。美德就像技能一样,是需要不断培养和训练的,需要持久的努力和投入,因此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一个个有美德的人不是按照义务来行事,而是按照自己一贯的道德品质来行动,对其行为的评价不是看是否符合某条道德义务的标准,而是看他在优秀道德品质上的投入、坚持和坚韧的程度,道德品格发展的深度。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个人今天做一件好事,明天做一件好事,还不能说他是有美德的,而只有当他将某种优秀的品质变成其性格中内在的稳定要素时才算是有美德的。
道德美德具有自我教育和激励的功能,当一个人自觉地去追求某种道德品格,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道德义务对他的约束,从而能够采取不一样的行动,取得不同于道德水平较低的人所期望取得的成就,他的行为因而更值得承认、赞扬和钦佩。道德美德、道德理想的激励作用是基本义务不具备的,它为我们道德生活的进步与提升指明了道路。这种分析说明了在美德伦理学(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不是义务原则,而是道德理想和美德。美德是为那些具有道德理想的人准备的,而不是为那些只想知道社会基本义务的人准备的。追求美德者与纯粹的义务论者在动机结构上有根本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我要成为一个道德上优秀或卓越的人”,后者的目标是“我要采取符合道德义务的行动”;前者以行动者为中心,而后者是以行动为中心的。
一个人要想成为道德卓越(moral excellence)之人,需要超越社会基本义务的要求,进入到美德培养、提升与完善的征程之中。纵观人类历史上那些道德模范人物,可以总结出道德卓越的四个评判标准:第一,始终坚持不懈地忠于道德理想和价值信念,即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状况下也不会放弃;第二,为追求道德理想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毫无保留地为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贡献自己的能力;第三,具有超常的道德品格,能够驱使自己在超常的层次上做出超常的道德行为;第四,在道德上完全地诚实,不会被个人欲望和迷惑人心的利益引诱所压倒[7]。例如,一个医生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医院待遇优厚的工作,选择到偏远贫穷的小山村行医,怀着一颗为村民身心健康服务的理想,在年复一年地照护村民和行医过程中,他变得格外有爱心、奉献精神、良知和耐心,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个人的需求和回报,村民们对他也十分地信任和赞赏。这样一名普通的医生虽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卓越的要求,并且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追求私利的平庸生活。
道德英雄和道德圣人表现出最高程度的卓越道德品质,他们远远超越了上述关于道德卓越的四个条件。道德英雄通常能够极其勇敢地面对大多数人避而远之的风险,抵制住了内心的恐惧和自我保全的欲望,往往是通过一次超常行为甚至是自我牺牲的行为就成为了道德英雄。那些不顾个人安危而见义勇为的人,就是道德英雄的典型例子,比如在危急情景下救助落水儿童、与歹徒勇敢搏斗、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的医生或科学家(比如将试验性的艾滋病疫苗注射到自己身上)、为扑灭山火而英勇牺牲(赖宁)、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来炸掉敌人的碉堡(董存瑞)、为把战友推出塌方的窑洞而牺牲自己(张思德)。
道德圣人比道德英雄的行为标准更高、条件更苛刻。它要求长年累月地坚持道德理想,始终不渝地从事利他主义的行动,这些是大多数人由于自私自利的欲望而不能实现的。做出一次英勇的行为就可以成为道德英雄,而只有在一生中持续不断地行善才能成为道德圣人。并且只有当一个人死后,我们才能对他的道德圣性进行最终的评价。雷锋、白求恩、特蕾莎修女是道德圣人的典范。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道德圣人的行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表现出纯粹的美德品质,成为道德上极其高尚的人。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英雄、圣人,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够做到道德上的卓越已经非常不容易,能够成为道德英雄、道德圣人更是少之又少。
从道德卓越到道德英雄、道德圣人(moral saints)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从合格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其间需要跨越很多的障碍。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否仅仅停留在道德的合格水平上,满足于严格义务的最低道德标准?以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人的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看,终其一生从不做出任何行善举动的人,他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密尔认为,要求每个人时时时刻都按照道德美德来行动,这无疑是过高的要求;但是,只要有机会来临,人们就应该去做特定的行善行为,在一生漫长的时间里,至少是一些暂时偶然的场合下应该做出举手之劳的助人为乐,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完善义务”(imperfect duties)[8]。
对人类的道德生活进行考察便会发现,人们经常为自己不能做到超义务的道德卓越行为而寻找各种理由,这往往会成为人们道德懒惰(moral laziness)的借口。特诺斯盖(Trianosky)指出,当我们的行为受到他人的质疑时,有些人会一笑了之,有些人会感到情感上的不舒服或者羞耻,还有人会做出理性的辩解,即“我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行善是迫于无奈的选择”[9]。一个人不能做到分外行善,这虽然不能导致否定的义务判断(negative deontic judgments),但可能导致否定的德性判断(negative aretaic judgments)。当一个人有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他人时,却表现出十足的冷漠,这无疑是一种缺乏美德的道德冷漠行为,它表明行动者在意志或情感上的恶性,要么是性格懦弱,要么是缺乏关爱与同情心,要么是自私自利之心很重。当然,道德冷漠与面对他人的无助时表现出遗憾悔恨的情感(feelings of regret)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心灵的非美德状态,后者出自于一个人内心真诚的良知[10]。
总之,道德理想和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比常人所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而微妙。从美德伦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行动者毫无道德理想,从不做出任何超义务行为和分外行善之举,即便是没有违背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义务,他的道德动机和品格仍然是有缺陷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