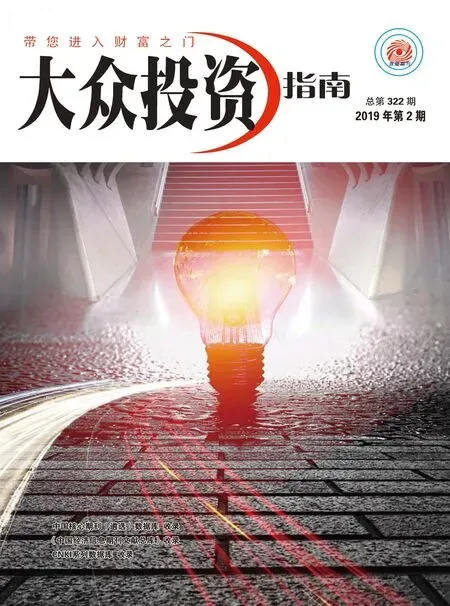浅谈粉丝应援下的集资“陷阱”
李青南
(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一、粉丝集资乱象横生
(一)乱象产生背景及原因
在百度百科中粉丝经济被颇为学术地泛指为架构在粉丝和被关注者关系之上的经营性创收行为, 是一种通过提升用户黏性并以口碑营销形式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商业运作模式。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在其著作《名流》中提道:“随着上帝的远去和教堂的衰败,人们寻求救赎的圣典道具被破坏了。名人和奇观填补了空虚,进而造就了娱乐崇拜,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娱乐崇拜是粉丝经济的精神内核的话,那么互联网无疑将其无限发扬光大了,毫不夸张地说,粉丝作为一种带有特别标签的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放异彩”。粉丝的壮大伴随着商机,而只要涉及交易自然少不了法律的“掺和”,但是“粉丝集资”却出人意料地游走在灰色地带。因此笔者不会在本文中对粉丝经济的发展多着笔墨,而将着重关注其背后的集资乱象。
(二)乱象具体表现及危害
1、乱象表现
毫无疑问,近年来粉丝集资还是个新鲜词汇,在众多学术论文和书籍中鲜有学者对其专门研究,仅有少许媒体登载过诸如“粉丝集资无人监管游走灰色边缘”“数千万应援偶像的集资款谁来监管”“粉丝集资得算个明白账”等等标题的文章,颇有“蹭热度”之嫌,但研究少不代表影响小。前几年某著名张姓歌手曾被曝“捐款门”,其背后便有粉丝集资的操作;前几月出自某“造星”节目的女艺人的粉丝被爆集资“喜提海景房”闹得沸沸扬扬,还带火了“喜提”二字;前几日某男星粉丝集资九万为偶像买烧饼也让人哭笑不得....由此可见,粉丝集资不仅早有苗头,而且规模甚大。有人或许会疑问:粉丝出于个人崇拜给偶像出资不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吗?话虽如此,但粉丝集资乱就乱在无人监管、不成体系、“粉头”职业化、粉丝低龄化、涉资巨大化、伴随风险大。
2、危害及研究意义
乱象必然伴随着危害,这也是笔者研究它的意义。首先粉丝集资无疑是对众多粉丝的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粉头”打着为偶像集资的幌子为自己敛财的不在少数,而且粉丝多低龄化,绝大多数经济尚未独立,甚至心智尚未成熟。早有新闻爆出,粉丝群体内部大都有“绑架”性质的规则,例如某选秀出道的女歌手的粉丝群内要求每月至少“捐资”两次,若未达标准将被踢出群,某组合出道的歌手生日会集资群内也有这种规定,而粉丝们出于“好面子”“组织认同感”或是单纯的个人崇拜大都会出手阔绰;其次粉丝集资对偶像而言也并非好事,沸沸扬扬的“捐款门”不仅坏了该张姓歌手的名声,还把粉丝集资推上了风口浪尖,当然,类似《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这类的明着集资的综艺节目暂且不论,更多演员、有资历的歌手是极其反对集资的,例如某胡姓演员多次提出反对其粉丝集资而被认为是优质偶像的代表;最后粉丝集资是对法律的挑战,虽说游走在灰色地带,暂未触及法律,但集资渠道如何?集资款项去向?集资风险多少?社会影响如何?等等问题都将随着粉丝经济的发展愈演愈烈。
二、定性
目前,关于粉丝集资行为的定性众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对此行为的定性是极为重要的,是否触碰法律?触碰何种法律?如何才能管制?等等问题都源于对粉丝集资行为的定性结果。
(一)赠与行为
1、个人捐赠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力认为粉丝基于为偶像拉人气、提升影响力而自愿出资的行为属于自愿捐赠,同时也带有委托代理的法律特征。法律并为相关禁止性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粉丝集资自然未触碰法律。同时他也表示由于粉丝集资往往具有盲目性与冲动性,且涉及人数众多、资金容量巨大,这其中潜藏着诸多道德风险。捐赠在民法上的概念体现为自愿性、无偿性,这与粉丝们的应援行为契合,但是这是把粉丝作为参与者来讲的。如果是“粉头”或娱乐公司方牵头就应另当别论了。粉头和利益相关的公司以应援、募捐等名义集资能看作是捐赠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募捐只能用于公益事业,粉丝如果以募捐的名义集资,是否合法还有待商榷。
2、委托赠予
首先下定义,委托赠予是指委托人通过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委托他人将自己有权处分的财产赠予第三人的有法律意义的民事法律行为。此中,涉及三方主体,即委托人---粉丝,被委托人——“粉头”以及受益人---偶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其中,在代理权限内活动不仅是兼顾内外利益的关键,更是判断被代理人法律责任的标准。因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将粉丝应援集资定性为此,将有效规范粉头的行为责任,亦可规避粉丝的民事风险。
(二)买卖行为
1、以专业平台为介参与应援集资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粉丝经济的愈发流行,专业的集资平台也更加多样。通过平台,公司以提供应援服务为包装,集资摇身一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但此商品既不完全归属于服务范畴,归于虚拟财产亦有些牵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买卖必须有标的,而“打榜”、投票、“提热度”等很难将其直接认定为标的,而法律亦并未有所涉及。因此,将此种通过商业平台应援的行为定性为买卖行为略显肤浅。
2、以非平台手段参与应援集资
此定性否定了粉丝集资中的无偿性,其认为粉丝集资的目的是为了交易。例如某偶像生日,粉丝集资数千万为其在时代广场大屏幕上宣传造势,《创造101》女艺人的后援会集资为其买热搜、买宣传资源和投票。此种定性将粉丝比作买方、将资源持有方比作卖方,将偶像比作受益第三人,整体而言,在此种关系下粉丝需要承担买方义务和风险,而偶像的义务和风险降到最小了。
三、所涉风险
粉丝集资涉及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法律风险还是道德风险都需要及时研究并未雨绸缪。本文将法律风险分为刑事和民事,是从粉丝集资的不同阶段讨论的,同时道德风险其实早“初见端倪”。同时,笔者认为在粉丝集资的环节中,不同主体所涉风险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刑事风险通常只与粉头以及集资发起公司密切相关,而民事风险与道德风险是每个主体都可能涉及的,同时当粉头与娱乐公司涉嫌刑事犯罪时,必然导致粉丝的财产损失,此中逻辑关系,不必赘述。因此下文仅结合上文对此行为的定性,针对粉丝的受众群体浅谈应援集资下的法律陷阱。
(一)法律风险
1、成为刑事案件受害人
若说粉丝集资与刑法最可能的关联,首要提及的应当是非法集资。在《刑法》上非法集资并非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多个行为表达。《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将集资诈骗罪定性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粉丝集资属于非法集资,但是某些个案中显示出来的特征已与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相符。当粉丝后援会组织者贪污逃跑的情况发生时,组织者的行为应根据其主观目的来界定,如果组织者在集资之前已经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虚构事实,欺骗粉丝出资,则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
除了涉及非法集资,侵占也是一个与之联系紧密的法律问题。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占有自己管理的他人财产如果组织者是在集资之后,擅自对已经募集来的集资款进行挪用,甚至占为己有,则可能构成刑法上的侵占罪。
以《创造101》的集资“盛况”为例,截至节目决赛当日,集资款项已达4000万之多,同时其中亦频频有“粉头”携款“潜逃”、个别粉丝接受采访无奈追讨之新闻,只不过仅引发了社会短时间的关注。庞大资金链指向何处?粉丝们或许无法得到答案。当然,触犯刑法的风险多是针对所谓粉头、娱乐公司而言的,由此可见,众多粉丝很容易成为非法集资案件中的受害者。
2、产生民事纠纷
若将粉丝应援集资定性为委托赠与行为,此中的民事纠纷主体则为委托人和受被委托人,即粉丝和粉头。此时的民商纠纷形成原因即围绕委托赠与行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展开。被委托人应当在委托权限内履行义务大可根据《民法总则》之规定,追究其超越权限或不履行委托义务的责任。结合众筹来看,粉丝集资同样不具有利诱性,但都同时存在“骗捐”之可能,责任人自然是粉头与牵头公司。此类民事纠纷,一是无委托合同可证明,二是维权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有粉丝愿意用法律途径解决,也给了对方可乘之机。
若将粉丝集资定性为买卖行为,此中的民事纠纷主体则为买方和卖方,即粉丝群体和持有资源的商家,此类买卖合同纠纷往往涉及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粉丝维权成本大于投入资金或者缺乏牵头人而不了了之。
(二)道德风险
此处的道德风险显然是针对社会而言的,粉丝应援集资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现象,其中风险也更像“温水煮青蛙”,隐隐有爆发之势。从金钱至上之风到娱乐化社会,随处可见粉丝应援集资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粉丝群体多以青少年为主,无疑是对青年一代教育和文化的腐蚀。
四、粉丝维权的方案设想
粉丝维权不仅需要粉丝积极参与、更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政府、平台、粉头、偶像等不能做旁观者,应该做引导者。现行经济和制度下,并无专业和完善的渠道以供粉丝维权,导致的社会后果虽鲜有新闻大篇幅地报道,但其潜在危害却是无穷的。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法律层面,粉丝都应该有维权的社会意识,有维权的专业渠道。
(一)粉丝协会制度
虽然粉丝与粉头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但其中的权益保护被动性、信息单向性却有相似之处,因此,仿照工会或者其他行业协会,粉丝可以建立粉丝协会予以一定监管。按照笔者的设想,粉丝协会的设立应以网络为载体和基地,以官方微博或公众号等形式,其拥有的权利为粉丝团体登记注册、监管各粉丝团体内部的风气及资金、制定粉丝协会规章制度、对违反者予以通报批评等,其运行资金来源为政府和注册登记的粉丝团体缴纳会费,同时登记注册的粉丝团体将拥有官方颁发的许可证书、涉及资金的应援方案应在协会备案。但是粉丝群体,不同于行业的纪律性和严肃性,而且受众广、分布杂,只能以有一定组织的团体为单位予以监管。粉丝协会在性质上仅勉强算是社会团体法人,不能拥有罚款等带有明显行政性质的执法权力,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只有粉丝经济以及社会舆论,要使众多粉丝团体心甘情愿被纳入协会监管之下,唯政府和社会舆论双管齐下才可实现。因此,此方案或许仅能作为设想,其可行性且在所不论了。
(二)专业维权平台
粉丝维权专业平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结合上文的粉丝协会制度,将维权平台作为粉丝协会的下属平台,由粉丝协会通过初步调查,情况属实的可选择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二是结合集资平台的现成资源,由平台方开辟专门维权通道,联系当下众多众筹平台的公众监督手段,其中平台主要起材料形式审查作用,对发起众筹人的现实状况并无真实了解,虚假众筹情况亦不在少数。而笔者认为,此类粉丝应援集资平台与众筹平台有根本性差别,即发起人是否是平台方。毫无疑问,诸多专供粉丝应援的集资平台背后是娱乐公司的操控,因此类平台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仅仅是监管与信息公示。以买卖行为定性而论,平台需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此时提供维权通道亦应包含于买卖合同的约定当中,作为卖方义务呈现。
五、结语
粉丝应援集资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更是蕴藏着潜在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笔者着重从法律角度粗浅谈论了当下粉丝应援集资的“陷阱”,之所以谓之陷阱,是因为目前的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此为违法,正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灰色地带往往暗藏着巨大的“商机”和风险。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娱乐法团队合伙人纪玉峰律师就曾表示:粉丝在互联网平台众筹实质上是一种集资消费,并不存在向粉丝承诺保本付息的情况,没有利诱性,因此没有引发金融系统风险的可能。同时,笔者在探讨时有意回避了一个重要主体,即偶像,其在粉丝应援中的法律地位是如何?法律权利与义务又是如何?如何规避?如何防御?是留给众多粉丝的问卷,也是留给社会的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