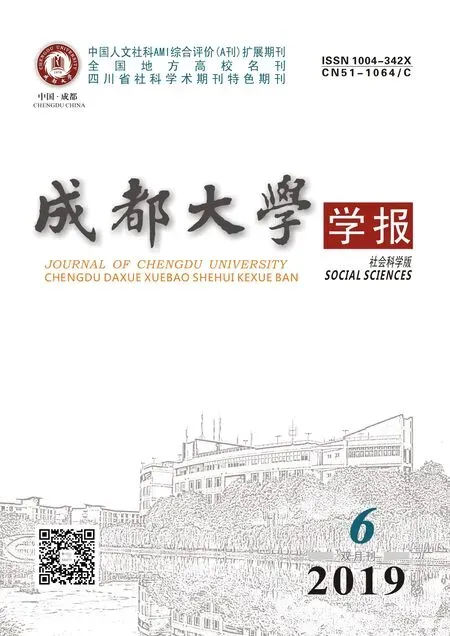弱者情结与文学中的苦儿主题探析*
冯和一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16)
作为经典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苦儿”是一种比个人的命运更具有意义的典型形象。从先秦时代,“苦儿”就已经被创作者纳入文学视野,成为各种体裁记录、反映、关怀、演绎的对象。“苦儿”不仅是我们文学欣赏的对象,也逐渐成为我们那难以解脱的自身,心理学视野下久挥不去的“弱者情结”的载体。
苦儿文学的诞生、演绎、发展离不开创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也离不开接受者对自身生存世界的认知,离不开过去、现在及未来具有特定心理需求、行为意识、情感想象、文化积淀的个体或集体的“人”。鉴于心理学、人类学与文学的亲密联系,尤其是苦儿文学所具有的极强的弱者情结感染力和震撼力,让我们难以漠视苦儿文学的诞生、演绎、发展的心理学与人类学注解。就像《解构与建构》所言:“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形式,文学总是以它独特的方式,编织着人类美丽的童话,构建着一个‘人’的神话。”[1]
一、弱者情结
从某种程度上,心理学相关成果具有阐释苦儿文学深层创作动机的可能。譬如,世上的弃儿有很多,但人们对后稷、令尹子文、褒姒、后羿等更感兴趣;世上的奴隶有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往往是那些曾经具有高贵血统或者最终赢得辉煌地位的伊尹、傅说、百里奚、越石父、勾践等,稍次的灵辄、虞公等人,虽然也偶有提及,但已经远不为人们所熟悉,至于收养伊尹的有氏女子、教导伊尹的人,则更是连姓名也没有人知道,或者说也没有意识去记忆。那么,是怎样的力量,促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具有双重命运的人物故事,而对于更普遍的社会苦难却宁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在无意识中给予忽略、在大脑中形成一种漠视、 整体遗忘。我认为能解释的这些现象的也只有心理学视野下的“情结”了。
(一)情结
情结(complex)本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一种被压抑或被忽略的情绪性的观念或意念,“一种潜意识内挟有情感力量的观念集团”[2]。它以一种充满情绪色彩、特殊的、固着的形式,存于人的潜意识境界并影响着人的思想、感觉和生活。心理学的“情结”研究,始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立及其对“潜意识”“力比多”主题研究的引入。基于精神分析学对人的性本能分析,弗洛伊德提出了“恋母情结”(Oedipuscomplex)、“恋父情结”(Electracomplex)、“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等概念。之后,阿德勒系统地发展了“自卑感”观点。按照阿德勒理论,自卑感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也是正常现象,它是行为产生与发展的最原始的决定力量[3]192。这种因自卑感(意识的)而转变至内在(潜意识)的心理倾向,被阿德勒称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荣格则通过“词语联想测验”(Word Association Test),发现了潜意识中依赖个人经验、反映个人经历的个人“情结”,并提出其“情结心理学”(complex psychology)理论。相对于荣格的“个人情结”,还有一种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超越个人生活领域的“非个人内容的情结”,它对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并具有时间的无限性;它隐藏在人类潜意识之中,以更为难以觉察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譬如“原型”(archetype)。无数非个人情结原型、种族性的经验和记忆,在无穷无尽的重复中,留在我们的精神构造、人格构造中,最终组成了“心灵的基本结构”所携带的“远古心里的痕迹”[3]272——集体潜意识(collect unconscious),这大概也是相同、相近的民族,面对类似情景时,都会不自觉地以类似的方法做出反应的重要原因。
(二)“情结”的补偿与文学对“情结”的创造性转化
“情结”的表现,时常通过未被意识到的微妙形式来显现。譬如一位倾心奉献的母亲因身体不好反过来要受到家人的照顾和迁就,对应着“权力情结”而且不受责难;有人大喊反对某物但却隐藏了他对某物的强烈兴趣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文学”,借助文艺的手段,补偿和转化内心深处的“情结”。反映在创作上,“情结”在补偿和转化中成为一种艺术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学接受上,这种补偿和转化也会影响着一个读者对特定作品的深深迷恋和文学性再创造。
阿德勒曾通过“自卑情结”“补偿”等概念及其对“优越感”的阐释,提出“文学创造性的想象总是遵循梦境形成的原理,不仅实际的身体缺陷和损伤会引起自卑感,主观感受到的心理或社会的无能也会引起自卑感,有了自卑感就有了‘补偿’的需要,自卑感不是变态的迹象,而是大多数人之所以进步的原因。”[3]191正因为有“补偿”的需要,所以才会促使文学创作与接受者不断地从“自卑情结”中释放出来,在寻求创造性的想象和创作共鸣中得到解脱。
荣格认为“情结”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行为,而且能成为艺术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艺术家之所以对创作具有强烈的激情,往往是因为某一种强有力的“情结”促使他这么做:“对艺术家做实际分析,不仅显示出来无意识的创作冲动,而且也显示出这种冲动乖戾蛮横的特征。我们只要翻翻大艺术家们的传记,就能找到有关创作欲对他们影响的丰富例证;它常常是那样的专横,竟然吸收了人身上所有的冲动,驱使一切为其服务,甚至损害了人体健康,破坏了常人应有的幸福。”[4]83对于接受者,凡是牵涉到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情结”的文艺作品,也总是会引起意外和无法估量的文学影响或传播效应。因为“情结可以变得如此难以抑制以至于他同化了更多的联想,并常把自我纳入其支配之下。”在艺术的创作与鉴赏过程中,“不适合‘情结’的东西都一掠而过,……只有适合‘情结’的东西才产生感情,并被精神所同化。”[5]
荣格还提出了原型理论:“与原型的所有联系,无论是通过经验,还是仅仅靠口头上说,都是‘激动人心’的,十分感人的,它所唤起的声音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加宏亮。……他使个人的命运成为人类的命运,因而唤起一切曾使人类在千难万险中得到救援并度过漫漫长夜的行善力量。这就是动人艺术的秘密所在。”[4]92“原型”的力量正是“情结”凝聚和释放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我国民族心理积淀下的“弱者情结”
本文涉及到的“弱者情结”,近似于阿德勒“自卑情结”,但又不完全一致。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能力有限、社会生活环境复杂、各种社会势力的压制、人常常会因自己的目的、期待难以实现而自感渺小无力;因长期忍受这种卑微之感,人的自尊心难免受到伤害,从而产生人格裂变,阿德勒称此为“自卑情结”[3]196。“自卑情结”对个人不能或不愿奋斗而形成的纹饰作用只会加深个人的自卑感。“弱者情结”则是以“弱者”“弱势”为核心,由潜意识中的弱者认同、欲望和情感组成的系列复杂心理。首先,“弱者”是一个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群体概念,这既是一个历时性群体,也是一个共时性群体;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相对性。其次,“弱者情结”的形成虽然具有个人情结“卑微”体验的成分,但更多的呈现为个人或民族对“弱势”情形的理性认识和感性体验的综合记忆。“弱者情结”的释放,往往与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奋斗史相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非个人情结”相联。“弱者情结”对个人或民族的精神文化起到的作用往往会混合着苦难、道德、拯救的责任与期待。
在我国民族心理情结积淀中,“弱者情结”的发生几乎是与民族的起源、人类的意识发生同时。与今天的狂妄自尊不同,远古人类在万物中的地位曾十分脆弱、卑微,卑微到似乎世界万物精灵都可以征服他、践踏他、毁灭他。比如《蛙蛇之谜》云:“三四十亿年前……和其它动物比起来,人还得屈尊在‘晚辈’地位。”[6]112换句话说,曾几何时,人类的名字叫“弱者”。那时的人类面对自然界不得不被动迁就,对动植物甚至非生物也虔诚崇拜。故弗勒贝尼乌斯曾说:“在这里不妨叫做人类动物说,处在这个时代的人类认为自己不过是与自然界同格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想到人相对于非理性的动物而言更有理性,而且具有更完善而非凡的能力。”[7]其实岂止是崇拜动物,宇宙间能见不能见的万物(精灵、动物、植物甚至石头土块等等)都似乎具有造福于人类、毁灭人类的能力。
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对人类自身能力的极端不自信,最终使中国古神话中的人类创造者往往呈现为非人非物又具有变形能力的图腾“怪物”。从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8]389,到盘古投凡“化成一物,团圆如一蟠桃样,内有核如孩形,于天地中滚来滚去”[9],无不如此。而且人们相信,人与万物是可以互化的。于是,他们或者纹了皮肤,或者披上图腾的外皮,把自己装点成精怪,实现人与动物同体,实现人与植物互变。故闻一多曾指出:“我所疑心创造人首蛇身型的始祖的蓝本,便是断发文身的野蛮人自身,当初人要根据图腾的模样来改造自己,那是我们所谓的‘人的拟兽化’。”[10]
人与万物同体互化的观念,也悄然酝酿着人与精怪鬼神恋爱、结婚的可能,随之出现的就是看似荣耀却又无比悲催的异类婚——人们把美丽的女儿嫁给异类(或称为神灵、异类英雄等),或者某男子娶回一位或者几位神不可测的异类女子(或称神女)。传说中盘瓠娶帝喾小公主、穷男苦儿与天上飞的天鹅、麻雀,水里游的田螺、蟾蜍,或者陆地上跑的狐狸、猴子所幻化之女子邂逅成婚,便为此类。文学对异类婚神话的反复演绎,无不从某个层面上说明:即使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生物界的主宰,但那种面对强大的异类、面对无法预知的灾难时所伴随的弱者情绪,却划过漫长的原始蛮荒时代,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成为心理底层的一道稍触即发的心理疤痕——弱者情结。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似乎只有符合了、触动了人们对感受弱者记忆的那种期待,才能让其在文学的真实性和诱惑力中获得一种情结释放的舒服和酣畅。所以鲁迅说,我们的文学,“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方法。”[11]
二、“弱者情结”在我国文学中的若干呈现
我们的祖先从几十万年前走来,历经无数灾难的降临,饱受无穷濒临死亡的现实,最终他们开始了伟大的思考,他们要在苦难的生存世界,为“弱者”生存寻找一切可能的契机。在这个世界里,人是“智慧”与“弱者”的统一体,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他们必须付出永不休止的努力和探索。这些努力和探索,不仅早已载入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也保存于我们的文学创作中。
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用他的顶天立地拓展着人们狭小的生存空间。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用她的造化天地的技能,保卫着人们得以生存的宇宙环境。燧人钻石取火,用法自然的大道使人们脱离了腥臊恶臭的原始生活。神农尝尽百草,用屡屡垂亡的用药体验为人们带来病体“复活”的希望。至于嫘祖养蚕制衣、后稷播撒百谷、大禹疏通河海……最终使人类脱离了原始的野蛮和荒野的无助。我们的祖先用人类特有的大爱与智慧,应对自然界的洪难与酷暑、丛林野兽的攻击与侵犯,锻炼着人自身与自然界、生物界抗争的本事与能耐。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得不用抗争去面对血腥杀戮的现实——刑天舞干戚,精卫填东海,共工撞天柱,鲧死复生禹;后羿射九日,蚩尢夺九隅,炎黄战阪泉,大禹灭三危——杀戮、反抗、复仇、征战、兴起、灭亡、流徙,在秩序的不断被扰乱、恢复与重建中,人们的心里,也时时充满着对生存能力的极大不自信,蕴藏着对和谐安定生活的无限渴盼和憧憬。

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复活”。不言而喻,人类与自然界万物一样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但在先民视野里,人类却具有复活或者再生的本领。在古老传说中,流传着许多人、神、动植物再生与蜕变的故事。如果说“人”“神”的复活只是传说,但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现象令我们对先民的“复活”意义充满幻想,譬如低等动物所具有的惊人的再生能力[6]30-91。试想,我们的先人是否也曾有这样的“历史”,或者说他们曾经设想过自己的种族本来拥有这样的“历史”?
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刑天”就是这种具有再生能力的形象,至于民间流传的那些被刀剑劈开的肉团里蹦出的人类男女,似乎也具有危险境遇中杀而不死的生命再生能力。如《布依族民间文学·迪进迪颖造人烟》[14]讲:妹妹生下一个肉团团,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也没有嘴巴,两兄妹怄气,就把它砍成了一百多块儿,撒往四面八方,第二天早上,四面八方九冒起了烟子,据说人烟就这样造出来了。苗族《神母狗父》[15]277-285故事说,神农将公主嫁给狗翼洛,两年后生下一个大血球,神农一听很生气,一剑把它剖开,从里面跳出七个男的代兄代王,七个女的代茶代来。彝族撒尼人《阿霹刹、洪水和人的祖先》[15]212-214说:两兄妹结婚了三年,妹妹怀孕生下来一团血肉,他们把一团血肉剁成好多块儿,挂在树上,过了几天,再去一看,都变成了青年男女,成双成对,有说有笑,在树上吃果子。侗族民间故事《捉雷公引起的故事》[16]说:姜良姜妹成婚三年生下一个肉团,无头无脑像个冬瓜。瑶族《伏羲兄妹》[17]说:两兄妹成婚,妹生下一个像冬瓜般的肉团;瑶族《日月成婚》[18]又说:日月成婚,月亮生出一个大冬瓜,将冬瓜籽洒在房前屋后,就都成了人了。
这种能在危险的生存境遇中再生的能力想象,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恐惧与改善生存法则的渴望;但逃过一时的危险而意外地生存,终究无法让人体会到永生的安心。死亡,无论你是强大或是弱小,无论你是丑陋或是美丽,无论你是英雄或者凡夫,终究无法摆脱。当一个人由健壮渐渐羸弱,当一个人由美丽渐渐衰老,当一个人气息奄奄,难以自主,人们又为自己找到了安慰——在人类面对灾难、死亡的恐惧、抗争中,在人类对永生、永恒的复活渴望中,在人类意识到自身渺小而又不断寻找拯救和获得拯救的行动中,文学中的沐浴物化、浴火重生、返老还童的复活神话也诞生了,也就是“浴神话”。这在《山海经》里有很多记录,如“十日所浴”[8]308、“舜之所浴”[8]422、“昆吾之师所浴”[8]434、“浴月”[8]463、“颛顼所浴”[8]478等,先民之所以一再重复讲到“浴”,很大的原因是想强调它的神圣性,即“化”“生”的神异。太阳会落山,月亮会蚀食,于是能够赋予宇宙重生的伟大女神——浴女便出现了,浴日的羲和、浴月的常仪就是用“浴”的手段定期对日月施以“浴”术并使这些天体“吞生化育”“恢复机能”。又有织女神话,也是典型的浴女神话,天河织女定期到天池沐浴,七夕鹊桥定期搭建和消泯,无不将人、水、鸟与宇宙的消耗损坏与幻化再生建构在一起。当然,无论采用怎样的方式去寻觅、创造、再造生存空间,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必然或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人的生命极其脆弱——伟大的盘古在生存空间的拓展中死去,始祖女娲在炼石补天的伟大事业中消亡,精卫填海千古流传但大海至今波澜壮阔,后羿已埋骨历史而天空依然阳光灿烂。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祖先与我们一样,不会真的成为自然界中丧失自身存在价值的玩偶,也不会真的成为被“司命”随意拨弄的宠物;他们在精神上不仅逃避着灾难与死亡的困惑,在心理上也积淀着强者与弱者的抗争与冲突;他们在困惑中建筑了耸入天堂的幽都昆仑,在恐惧与拯救的抉择中,掩盖着对生命永恒撕心裂肺的渴求;他们遥望璀璨的星河云汉,祭祀着不平凡的祖先;他们手舞足蹈、结绳画字,记载诠释着生命最初的渊源;他们创造了鱼蛙鸟兽血拼共存的神话世界,也创造了引领人类的灵魂飞升的文学殿堂。当有人在“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哲学课题中难以解脱之时,那个由我们的祖先创设的神话世界就是一个存在着永恒价值与意义的异域天堂,随时诱惑着“弱者情结”影响下的无数迷茫的灵魂向她靠拢、获得愉悦。
三、中国苦儿故事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弱者情结”的情感释放
将我们民族“弱者情结”演绎得最为充分的,就是文学中的苦儿故事,或者说苦儿文学。何谓“苦儿”?翻阅古今文献,也许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已有的界定。缘于苦儿文学研究的需要,笔者在梳理我国古代“苦儿”诗赋、“苦儿”传说、“苦儿”剧、“苦儿”故事、“苦儿”歌谣以及相关的论著时发现,“苦儿”及苦儿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如下几种特征。
第一,“苦儿”是在人类社会特定阶段对社会“人”群中生存于特殊家庭结构、特殊物质与精神状态下的一类弱势群体的特定称谓。脱离了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物质、精神模式,苦儿就不再是苦儿。这种特殊家庭结构、特殊物质与精神状态涵盖了“苦”“孤”“弱”等基本内涵,在这一称谓下的“苦儿”往往是一群弱年丧父,或幼龄失母,或者失去双亲,或失去亲人,无人照料、遭人虐待、生存状态极端孤苦、期待“神”“异”佑护的“人之子”。那些以塑造“苦儿”或“苦儿化”形象,复写或描绘苦儿悲惨生活、苦厄命运、非常事迹、神异事件,传达特定人群对真善美生活的诉求与愿望,反映文学作品对民族弱者情结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青睐,表达某种特定的思想情感等为要件或创作追求的故事,我们都称之为苦儿故事。
苦儿故事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令接受者自愿放弃形式审美的巨大精神能量。可以说,从先秦时代至隋唐,“苦儿”的典型形象就已经成为各种体裁文学作品记录、反映、关怀、演绎的对象。譬如《孤儿行》中孤儿对坟头父母的哭诉:“父母在时,乘高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23]这首诗,至今犹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就是因为它总是能触动和激活人们心中、经验中不断沉淀的、挥之不去的一个遥远的惊悸、回忆和期待救赎的弱者情怀。这种促动,就契合了荣格所阐释的艺术创作要心理的、经验的高度的奥秘,将作品的内容带回到一种个人与集体“神秘共享”的状态中,这样,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就“比他个人的命运更具有意义”[24],更能激起接受者的关注和情感的震动。所以,“苦儿”在我国文学中往往毫无例外地成为幼者弱者的代表而受到更多作者读者的关爱与恻隐。譬如《孤儿行》中,孤儿的痛苦不仅召唤着人最初的良知与恻隐,孤儿对“天”的诉求,也无限地触及了人们的苦难情结与渊源久长的弱者经验。
第二,现实的民俗生活以及俗文学作品中的“苦儿”,往往围绕“苦”“孤”“弱”这三个基本内涵而发生的延展和变异,无论是民间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的“苦儿”形象,往往都会具有一种“苦难”“道德”与“拯救”的象征性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苦儿”的家庭状态往往是孤儿寡母,但又并非只有孤儿寡母。具有破损意义的(扩大的)核心家庭、破损意义(扩大的)主干家庭、破损意义单身家庭、类单身家庭等,即“无父(母)”“无夫(妻)”“无子女”等有破损或者不完整意义的家庭,往往都是苦儿家庭结构的典型特征。只是,孤儿状态是“苦儿”典型中的主体。其次,在年龄界限上,“弱”,通常被强化为一种年龄上的“幼”,比如幼年,即未成年、未婚或者新婚阶段等;但一些民俗仪式对“苦儿”的界定以及“苦儿”通天的传说中,也往往会超越“幼”的范畴,即便是成年甚至老年的男女,面对“天”“神”或“祖先”,也经常被赋予通天“苦儿”的内涵。只是呈现在特定的文学中,创作者往往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成年苦儿“弱龄化”“幼龄化”,并由此演绎出更丰富的苦人故事。从这个层面来讲,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苦儿”被人们等同于“苦人”,但人们更倾向于将“苦儿”的“弱”指向“幼年”。比如子胥故事,《史记》记载并不存在子胥来不及迎娶已“就礼”的妻子便独自到梁国远游出仕的情节。事实上,伍奢作为太子太傅,家里出现这样不合常理的事情也实在令人疑惑。但作为文学作品,后来的敦煌文献《伍子胥变文》则已经超越了历史现实进入到敦煌的当下,对子胥的逃亡之途付诸了充分的想象,借助打纱女、阿姊、细辛、渔人的角色的塑造,弱化子胥的年龄,赋予子胥经历苦难的成长过程。子胥与细辛未婚情节的插入,不仅从感觉上弱化了我们对子胥年龄的注意,而且强化了子胥连正常的婚配还没有完成这一背景。这分明就是想将一个介于中年的苦人刻画成类似未成年或者说新婚不久的“苦儿”,只不过这一蜕变只是半成品。
另外,文学创作对“苦”的理解,越是往后发展,越发强调多苦并存、极端之苦。譬如晚唐五代,敦煌文献苦儿故事对“苦儿”形象的关注,不仅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敦煌苦儿群”,而且他们塑造的苦儿之“苦”,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苦并存”的,这里不仅活跃着具有“孤”“苦”“弱”的孤儿丧子、弃儿殇魂、乞儿残女、复仇之子、前男苦女等“苦儿”形象,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多苦并存”的苦儿化特征、家庭结构多样化破损、呼唤社会“良知”与“担当”、包含“感天”与“励志”价值的“复合型苦儿”形象。这里的“苦儿”故事,更多地借助对多重身份的苦人弱龄化、失依化、苦儿化演绎以及对其家庭结构的破损或不完整的强调,逐步将作品主人公“多苦并存”的孤苦处境推向无以复加的极端,在主人公失父丧母、遭受遗弃、饱尝饥饿伤痛、生离死别,在感天动地、得逢神异的过程中,为“苦儿”赠赐一个理想的圆满或苦难后的辉煌,从而完成一种比唐前苦儿故事更具有“励志”叙事价值、更强调线索叙事与思想指向、更注重多重情节整合的恢弘故事模式。仍以《伍子胥变文》为例,在这篇作品中,创造性运用“线索”和“苦儿群”多重组合的方法,不仅强化了“苦儿”主题和“励志”文学的戏剧性作用,也赋予了故事“苦难”“道德”“拯救”的意义,强调了更高的民心向背意识与社会价值期许,反映了域外宗教文学、敦煌俗文学创作与敦煌大众视野在“苦儿故事”创作方面一致的心理期冀与文化联系。又譬如《韩朋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将“苦子游学丧命”“孤女嫁而失夫”“苦子死后连理枝”等具有“苦+神异”意义的故事整合在一起,单一的苦儿形象逐渐演绎成为具有多重悲苦身份、经验多苦并存生活的复合型苦儿。《王昭君变文》融合敦煌地域文化色彩的构思,对自幼孤苦的“宫中薄命妾”“塞外断肠人”“为国岂辞死”“时向紫亭魂”的昭君塑造,既传承了苦女远嫁异邦异类的悲情模式强大的心理冲击力,又通过昭君美丽才情与多变人生的反差吸引着人们的多重解读和文学想象;“不那夫妻义重”的单于形象也被赋予一种“弱龄化”的“孤苦”特征,暗含着敦煌俗众对苦儿题材的特殊青睐。另外“目连救母”故事等对孤儿目连一波三折、上天入地的“寻母”“救母”故事不仅传达着苦难、佛教道德与拯救的意义,而且对中土“苦儿”故事寻母传说中母亲形象的影响及其对传统母神信仰的也造成强烈冲击。
第三,“苦儿”可与天相沟通的“感应”意识,往往成为苦儿故事情节“变”“异”的媒介。
首先,“苦儿”的出现,面对的是现实社会,期待的是人的恻隐。“苦儿”,作为一类社会存在,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诉求、命运遭际、伦理观念,戏剧性地强化着社会的普遍生活状态与道德价值判断。文学中的“苦儿”,则又总是以其特别震撼人心的形象魅力,召唤着人类心理底层最初的良知与恻隐。在人类追求关爱与幸福的理想中,从相反的方向昭示着人们生活的苦难和人性的真实。在人类追求生命的永恒与价值的期待中,用单纯辛酸的故事穿透人们的凄苦寒栗的内心;诞生、抛弃、挣扎、生存,历经考验;他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在人性的善与恶之间,饱尝饥饿、伤痛、生离、死别。即便是带有奇幻色彩的美好结局,也无不展示着世人对现实苦难的不满,对非和谐秩序的否定,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事实上,在祖先崇拜盛行的华夏,“天人相通”的信念从来就没有断绝过,“苦儿”能与天相互沟通,更是在“祖先信仰”“天人感应”信念与“弱者情结”千年激荡下必然产生的一种执着的联想。譬如人们对《幽冥录·王志》中“王志还魂”以及董永故事中“至孝感天”的诠释。《幽冥录·王志》中,王志夫妇丧亡,孤儿尚小,作为亡魂,王志为孤儿忧心流涕,祈求鬼王允许还魂以抚养孤儿,鬼王为之动容,便许之还魂三年(即人间三十年)。为什么许之还魂呢?因为留在世上的“孤儿”正是黄土之下(或者叫做天堂)的“亲人”甚至“鬼王”都怜悯牵挂和要照应的对象。董永“至孝感天”的故事中,董永也具有“沟通天神”的身份——苦儿身份,他对死去亲人的至孝,感动了上天,身处苦难的董永于是获得天的怜悯,娶了织女星。事实上,织女星曾被视为祖源世界的神,是天女孙、天女、天子女,她的存在与人间至孝感应关系非常密切,“王者至孝于神明”,织女星“三星俱明”,否则,三星“暗而微”“天下女工废”[25]卷27-1311。“织女”与“孝亲”“孝神”的感应联系正是董永故事的不断演绎的基础,而“董永至孝”的行为也从某种意义上承继了古人——作为脆弱的生灵——对先辈神灵的祭祀与礼拜,隐含了先民对祖神回顾幼儿甚至降临人间救苦救难、守护孤弱的期待。因为我国传统的祖先信仰中,养老送终、守墓祭祀的“大孝”“至孝”,不仅仅是出于对父母的感恩,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天”,取得具有血缘关系的祖神或者称之为“天”的佑护。“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怜,便为鱼肉。”[26]卷65-2142
又如民间流传的苦女求雨民俗。笔者故乡汝南就流传有“苦女扫天晴”与“苦女求雨”习俗性仪式。这种仪式的主持者皆由苦女(往往是女性孤儿、有时可能是寡女、女性乞儿、以各种原因丧失生活依靠的女性等,更确切地说是具有极端之“苦”的灵媒素质者)来承担。仪式中,苦女手执“扫天晴”(一支捻去高粱米的穗杆),“扫天晴”只要在雨中左右挥动,上天就可以知道雨下多了。而苦女如果拿着九支这样的穗杆,到干涸的河里扫几下,上天就会知道人间大旱了。通过苦女拿着那么几根高粱杆,就能够将民情上达天听,从而达到祈雨抗旱的目的,起作用的当然不仅仅是高粱杆,而更是苦女。
古代传说中的那些能够将民情上达天听的、能够连通天地的“大巫师”,也通常是由苦儿担任。譬如后羿,传说他被父母抛弃山林,是受山间泉涧养育的弃儿,甚至连教授他射箭的弧父也是如此。但是“昆仑之虚,……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8]344-345,大海之内又只有后羿具有“与天相通”的能力。“天”或者“昆仑”,是我国远古幽都的代名词,在弱者的心里,“天”这里既是强者汇聚的象征,又是弱者冲出苦难的依赖,“天”这里聚集着无数牵挂人间的祖先鬼神,它们具有着“人”所不具备的一切超越常人的能力和智慧。这种超于常人的能力和智慧,不仅为我们的苦儿故事带来神异色彩,而且在文学心理学视野下,也充分满足了无数具有弱者情结、拯救意识的接受者的期待和诉求。“苦儿”愿望的达成带来的刹那快意,不仅是对心理上“弱者”的拯救,也是创作者与接受者由此获得“期望阈”满足的载体。就像英国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之战》所云,通过这一载体,“我们可以在这之上的一个十分快乐的超越时刻,把怪异表现手法统统悬置起来,然后回过头在一个基本属于人类的平台上相遇。”[27]
当然,这并不是说,苦儿故事只要传达弱者情怀,或者达成附加愿望,就可以实现感染世人的效果。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基础。如果苦儿故事的创作总是一成不变,那么它最终会丧失最佳的文学感染力。因为人类天生具有“求同记异”“求异”的心理倾向,而且每一个时代对“强者”“弱者”总会有各自的界定与诠释、信仰传承与文化的更新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公众期待,就像《文学理论的向度研究》说的,“那些完全符合读者期望阈的作品并不值得重视,因为它们没有创新;那些与读者期望阈全然相反的作品也不一定有太大的价值,因为读者可能因读不懂其中的意思而无法获得明显的‘接受效果’。”[28]这大概也是历代创作者一边传承着原滋原味的苦儿故事,一边又放开“狂放的绚烂的幻想力”,呕心沥血编织着“变化无穷的”苦儿世界,它们的笔触像“五色缤纷的彩线伸到整个大地,用美丽得惊人的言辞的地毯把大地覆盖起来。”[29]
三、结语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13]299当人们过多地食用酸甜辣咸之味引发疾病的时候,苦味的药成为人类纠正人体五味之偏、治疗疾病的良药。如果说“苦药”就是冥冥之中大自然对人体五味失衡的一种纠正,那么生活中的“苦难”与苦难感受,就犹如药草,调剂着人类的生活,延续着人类对生存的渴望。“苦儿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普救人类沉沦苦难的“药草”。在诸多类型的苦儿形象中,那些被聚焦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苦儿”形象,似乎都曾经毫无例外地被作为幼者、弱者的代表,或者成为诠释人类悲剧命运、忧患意识、抗争精神、拯救精神的载体。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曾经或者依然受到无数的创作者、表演者、观赏者、聆听者、阅读者的恻隐与垂爱。他们的苦难对文学的接受者所造成的情感震撼也往往具有比他个人的命运更具有意义。按照心理学的解释,那就是这些“苦儿”的命运总是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历史经验中所积淀下的,挥之不去的遥远记忆,总是具有触动人们对远古生存苦难产生无数惊悸的魔力,总是具有将以往所经历的痛苦、悲哀、失望、绝望的情绪进行美化、升华的魄力,他们能够释放人们拥有的期待救赎的“弱者”情怀,并令他们为之而苦苦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