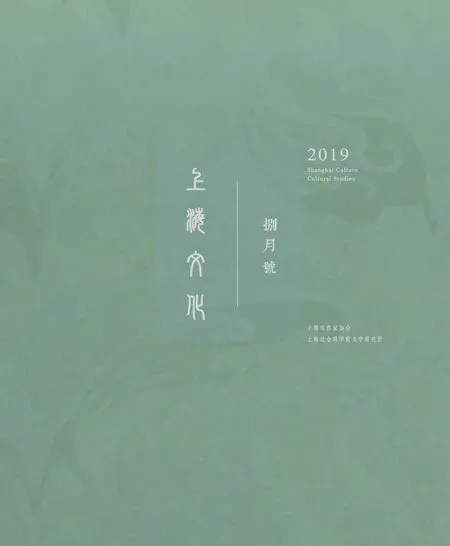金庸小说的文化解读与文化人格的建构
汤哲声
金庸小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武侠小说如何经典化的问题上。这是运用精英文学的批评标准分析金庸小说。①李以建:《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紧张与体系构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金庸先生去世之后,对其研究有了很多新成果,有些研究者注意到金庸小说的价值还是要到“中国武侠小说”的空间里思考,用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标准分析金庸小说的文类的贡献和价值。这确实是金庸小说乃至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科学而合理的批评路径。②代表论文有韩云波:《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论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该文对金庸小说的文类功能、文类历史和文类品位的改造做了分析,肯定了金庸对武侠小说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的贡献。我认为除了以上3个层面之外,金庸小说还有另一个贡献:文化武侠。我认为金庸小说除了在文类功能、文类历史和文类品位等方面对中国武侠小说主流化进行创造性转换之外,文类文化的提升更为重要。文类只是一具“形体”,文化才是“形体”的“精气神”。武侠小说是类型小说。争霸、复仇、夺宝、行侠、情变……无论武侠小说的文类功能、历史、品位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武侠小说情节的基本套路。作为武侠小说的金庸小说同样是这些情节套路的演绎。为什么具有同样情节套路的金庸小说就能读出不同的感觉呢?在情节套路中表现文化内涵是根本的原因。值得探讨的是金庸小说吸取的是什么文化,以及这些文化给武侠小说带来的什么样的“精气神”。从文化分析入手,自然就能分析金庸小说对中国武侠小说乃至中国小说美学所做出的贡献。
写小说都离不开文化,武侠小说更是儒家文化的最好演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可以演绎为练武、门派、平地、扬天下。事实上,这就是中国武侠小说传统。《水浒传》以及近现代中国大多数武侠小说均是儒家文化的阐释。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时也是这样的思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小说均为儒家文化的张扬。金庸的贡献在于,他将惯于运用儒家文化思维的中国武侠小说带到了新的文化空间,给中国武侠小说带来新的内涵,从而使武侠小说充满了生机。
一、墨学、佛学:金庸小说传统文化阐释新拓展
《射雕英雄传》是一部阐释墨家文化的武侠小说。墨家本是细民、流民之团体,兼爱、非攻是墨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兼爱是要爱天下所有的人,而非亲亲为大,“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①《孟子·尽心上》。非攻是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那些打着各种正义口号的侵略战争,看起来是夺取了几座城池,伤害的却是平民百姓。小说第37回,郭靖率军打下了撒麻尔罕。他向成吉思汗提出的要求是放了这城里数十万百姓的性命。②金庸:《射雕英雄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352、1450、99、435页。听到这样的请求,成吉思汗先是一楞,然后就是愤怒,因为蒙古兵从来是打下城池就杀人抢物的。他根本就想不到,郭靖有这样的请求。小说结尾的时候,郭靖与成吉思汗论英雄。成吉思汗当然认为自己是英雄。
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说:“难道我一生就没有做过什么好事?”郭靖说:“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过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③金庸:《射雕英雄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352、1450、99、435页。
听了这话,成吉思汗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上。成吉思汗临死之前还在念叨着“英雄”。儒家讲门第、崇品格,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目标。为达到目标,可以牺牲自我的一切,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墨家讲天下大爱,反对战争,郭靖将墨家的思想糅合在侠义精神的挥洒之中。
郭靖没有陈家洛身上的英气和灵气,却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认死理”,绝不投机取巧。他第一次获得铁木真好感就是“认死理”。当别人逼着他说出哲别的藏身之处,他可以说,我不知道。但是,他却这样说:“我不说,我不说。”②金庸:《射雕英雄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352、1450、99、435页。我不知道,是与此事无关。我不说,是明明知道而就是不说。洪七公开始并不喜欢他,说他笨,但是后来答应教他武功了,当然有黄蓉的功劳,也与他“认死理”有关。面对洪七公要他发誓不外传武功给黄蓉,他自觉做不到,就回答说:“那我就不学了。”洪七公在惊奇他这样的回答的同时,倒也很佩服他,说:“傻小子心眼不错,当真说一是一。”④金庸:《射雕英雄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352、1450、99、435页。当然,他这样“认死理”也有吃亏的时候。在归云庄,黄药师因为不满郭靖杀了自己的徒弟,要杀了他。黄蓉当然拼死保他。但是黄药师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杀可以,教训是少不了的。一掌下去,郭靖如果机灵一点,就干脆跌个鼻青脸肿倒也罢了,谁知他就是不会装假,他不但不跌,还站稳了脚跟。结果黄药师的面子下不来,又是一掌,这下吃了大苦,膀子给打得脱臼了。1人们喜欢郭靖这个形象,首先喜欢的是他的本性,然后才会佩服他侠客本色。郭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踏实践行。他一旦认准的道理,立刻付诸实践,而且一旦实践,绝不投机取巧。他四处奔走,消弭蒙汉两族的恩怨,抵御金国侵宋。他学武功招式,一天学不会,就两天;两天学不会就三天,直到学会为止。即使是爱情,一旦倾心于黄蓉,绝不改变。陈家洛与郭靖的形象之别同样是儒家与墨家之侠的差别。“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②《庄子·天下》。墨者的形象与儒者的长衫、长扇有着明显的差别。“赴汤蹈刃,死不旋踵”,③《淮南子·泰族训》。墨者就是“认死理”,而且一旦确认,绝不回头。墨者的风采在郭靖身上得到了精彩的演绎。注重实践的墨家,发展到后期逐步对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产生了兴趣,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金庸将墨家这些机巧之学也纳入了小说的描述中。黄老邪和黄蓉是代表人物。
《天龙八部》实际上是从因果关系出发,写出的一部小说,正如金庸的好朋友陈世骧所评论的那样,这本小说:无人不冤,有情皆孽。④金庸:《天龙八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975页。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因果推演而构成。大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萧峰,核心事件是寻找自己的身份。第一个小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段誉,核心事件是寻找自己的爱情。第二个小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虚竹,核心事件是怎样从一个小和尚变成了一个武林高手。第三个小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段延庆,核心事件是他为什么成为了第一大恶人。第四个小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慕容复,核心事件是他为什么发疯了。《天龙八部》中的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情势造成的。情势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由人造成的,人—事—人—事,各为因果,这又造成了因果链。既然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它就会依据自己的规律发展,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空的,最后的结果早已注定,而这样的结果却是当事人所想不到的:萧峰、段誉、虚竹、段延庆、慕容复,还有那个带头大哥少林方丈玄慈等,他们的人生结果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更是命中注定。既然是命中注定,却拼命索取,自然就会带来痛苦。在佛家看来“人生皆苦”,“一切皆苦”。生老病死,这些人间自然规律的苦自不必说,无法避免。在人世间真正苦的是那些人为的苦,是“求不得苦”。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追求,但是都求不到,只能是自寻痛苦,表现得最突出的当然是慕容复了。
《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扫地、烧火、干粗活的老僧在点化萧远山和慕容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须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弛,相互牵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①金庸:《天龙八部》,第1684页。这段话提出了一个人生的境界问题。武功代表着功利,代表着贪念。要消除功利和贪念,靠儒家和道家都不行,无论是儒家的“有为”,还是道家的“无为”,都没有否定武功,他们还只是关注怎样利用武功。利用武功还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天龙八部》不是说武功怎么使用,而是说武功根本就不需要,要去除,这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了。怎样达到这个境界呢?只有多学佛法。所以说,《天龙八部》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用佛法来指点人生的一部武侠小说。
侠客本是墨家演化而来,然而,纵观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却很难找到一部完全演绎墨家文化的武侠小说(当然,武侠小说中的墨家人物并不少见)。《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整地阐释墨家文化的武侠小说。佛家讲究的是放下,是消弭,是平和,这样的思想本来与武侠小说相克,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将佛学与侠义结合在一起的武侠小说几乎不见,金庸却能将佛学演绎成武侠小说,确实难得,所以说《天龙八部》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②对《天龙八部》中佛家思想的详细解读,可参见汤哲声:《梵音: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佛学叙事解码与史学地位》,《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二、政治、社会:金庸小说文化阐释的自有境界
《天龙八部》之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进入了自由自在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将自己的世俗文化思想在侠义的精神中随意挥洒。最有说服力的是《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笑傲江湖》有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小说写作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热闹的时候,因此,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说它是政治小说也不为过。二是这部小说的历史感不强,我们无法判定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什么朝代。因此,这里面没有什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江湖小说。这两个特别点,也是我们分析令狐冲的两个视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纷繁的江湖争斗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姿态呢?应该是率性而为、个性为本。这就是令狐冲的形象意义。
在金庸的笔下,政治有两重意义,那就是掌握权力的终极性和耍阴谋诡计的过程性。令狐冲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领袖欲和为人坦荡。小说写了三次争霸,一次是任我行与东方不败争夺日月教教主,二是五大门派争夺五岳门派的掌门人,三是日月教和五岳门派争夺一统江湖的领袖。这三次争斗令狐冲都是主要参与者,他都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但是他都不要。因为他从心里就反感为当领袖而做的阿谀奉承的事情和当了领袖接受那些阿谀奉承的事情。小说是这样说他的:“他本性便随遇而安,甚么事都不认真,入教也罢,不入教也罢,原也算不上甚么大事。但是要他口中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不由得大起反感,心想倘若我入教之后,也须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当真枉自为人,大丈夫生死有命,偷生乞怜之事,令狐冲可决计不干。”①金庸:《笑傲江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540页。当听到那些教徒们恭贺任我行当了教主的谄媚之声,他心中有说不出的厌恶。要说耍阴谋诡计,他则是个受害者,是个受冤屈者。他一出场人们就将他与采花大盗田伯光相提并论,后来被他师傅认定是偷《紫霞秘籍》的贼,再后来又被他的师傅认定是偷《辟邪剑谱》的贼。如果说第一个冤屈有证人可以帮助澄清,后两个冤屈不但没有证人,而且是师傅说的,也许就成为千古奇冤,无法翻身了。面对这些阴谋和所受的冤屈,令狐冲不是喋喋不休地到处伸冤,更不是设计报复,而是胸襟坦荡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那些阴谋和冤屈都自行暴露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作弊者必自毙,作贼者必被捉。在令狐冲率性坦荡的身形中说明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个人崇拜之坏,人们都知道。《笑傲江湖》的深刻性在于写出个人崇拜就是一种毒品。没有吃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但是吃了以后就上瘾,上瘾之后就戒不掉。小说生动地写出了任我行对个人崇拜的上瘾过程:反感—劝说—舒适—惯例。他上瘾了,以后再想戒也戒不掉了。追求舒服是人的本性,毒品就是看准了人的这个本性趁虚而入,结果是掏空了你的身体,掏空了你的金钱。个人崇拜也是看准了人的这个本性趁虚而入,结果一定是掏空了你的意志,掏空了你的原则。所以当任我行接受一批批参拜者的时候,令狐冲悄悄地退出大殿,再远远地看任我行,形象有些模糊,心中居然分不清坐在教主位置上的人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了。
如果要问金庸小说哪一部写的门派最多,那一定是《笑傲江湖》,加上那些草莽黑道上的人物,小说中门派不下20多个,即使是一个门派里的人还要再分派,例如华山派中再分剑宗、气宗。有意味的是,这些派别明明斗得头破血流,却还把对方说成邪派,而且正邪分明,绝不混淆。令狐冲小的时候也是以正派自居,也是自信正邪不两立,可是后来他发现左冷禅这些以正派自居的人,起奸诈凶险处,比之魔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再看看东方不败和任我行也是用阴谋诡计互相陷害,一旦得志就唯我独尊。于是他就没有什么正邪之分,只有意气和不意气之分。他可以与采花贼田伯光成为朋友,可以和魔教长老向问天结为兄弟,可以将桃谷六怪收在手下,可以娶小魔女任盈盈为妻。交朋友要的是义气,娶老婆要的是性情。所谓的正派高手刘正风和邪派高手曲洋合撰的曲谱《笑傲江湖》交在他的手上有着深刻的含义。音乐没有正邪,没有贵贱,它来自于天上,是人性的结晶,令狐冲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正邪、没有贵贱的人性结合体。率性而为、个性为本是令狐冲的人生观。这个形象令人感动,还在于他是一个有情有意的男人。他被师傅赶出了师门,却始终以重回师门为目标,这是忠义;他践行一切允诺的事情,甚至是保护林平之,因为他向岳灵珊承诺过,这是责任。他做了恒山派掌门,面对那些女尼守如君子,这是品质。令狐冲是一个君子素质的浪子。
《鹿鼎记》是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韦小宝的生动和内涵在于他是一个文化人物。我认为他应该与康熙看成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两张面孔和双重性格。韦小宝在皇宫中的那些处世为人以及各种手段全是妓院里的那一套。金庸每一次写韦小宝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说他如何受到妓院工作的启发。再想想康熙,他身上具有典型的“韦小宝性格”。康熙最能体现本性的地方就是与韦小宝打架的时候,这个时候韦小宝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他们两人都是真情流露,互相争斗,又互相倚赖,互相以对方作为争斗的依据。康熙的一生中擒鳌拜、平三藩、定台湾,算是他的丰功伟绩,可是哪一次不是险胜,哪一次不是运用了赌徒心理。康熙功于心计,下手狠毒,既有胸怀全局的的气概,也有争强斗胜的小鸡肚肠;既有知人善用的才能,也有傲才自负、狂妄无知之处。但是,他也讲义气。他在大婚之际召韦小宝回宫吃喜酒的密诏说:“我就要大婚啦,你不来喝喜酒,老子实在不快活。”倒是真话。小说的最后康熙南下寻找韦小宝也是费尽了心机。令人回味的地方是,为什么满身世俗气息的韦小宝能够在皇宫里如鱼得水呢?为什么身为皇帝的康熙能与满身流气的韦小宝成为朋友呢?只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韦小宝和康熙本来就是一个人。
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韦小宝和康熙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就更有意思了。韦小宝代表的是草根文化,康熙代表的是庙堂文化。韦小宝这个人物告诉我们世俗文化本来就是和庙堂文化相通的。在世俗社会中吃得开同样需要上流社会的气质,在上流社会中混得转同样需要下三滥的举动和碰运气的“赌”。世俗社会和上流社会只是生存的环境不同,其生存法则是相同的,它们是中华民族这个大文化圈的两个侧面而已。
韦小宝是整个中国国民性的代表。问题还在于他的这样的国民性还要延续下去,你看他身边的7个老婆,她们是康熙的妹妹,李自成的女儿,云南沐王府的公主,明末遗民送来的丫头,神龙岛的少夫人等等,几乎通领了当时中国的各方势力,谁有这样的力量能够通领中华大地?只有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韦小宝不仅有了这代表着各方势力的7个夫人,还与俄罗斯的女王索菲娅来了那么一手,是不是表示着中华民族的国际交往呢?可以意会。韦小宝的7个老婆中有3个夫人怀孕了,她们是公主、珂珂和苏荃,这可是当时中华大地上最有力量的三股势力:当朝、在野和江湖,韦小宝都给她们下了种,她们生下的孩子应该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韦小宝形象中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是中国侠文化的叛逆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所遵守的原则,也是金庸相当长的时期内写大侠的形象标准,陈家洛、郭靖、萧峰等人都是这样的大侠。但是这样的标准在《鹿鼎记》中却受到了怀疑。陈近南如此辛劳,却显得心胸狭窄,在大陆与台岛之间,他根本就没有辨清楚谁是国,谁是藩;他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实质上是愚忠于一个国姓爷。他收韦小宝为徒是为了便于他接近皇宫,其动机并不纯。至于顾炎武等人,心胸更为狭窄,他们竟然推举韦小宝做皇帝!韦小宝能做皇帝吗?韦小宝做了皇帝能治理国家么?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么?顾炎武等人似乎都不顾忌,他们只要有一个穿着汉族服装的皇帝就行了。为国为民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口号,但是常常被个人的利益和狭隘的民族利益所污染,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其历史内涵实际上有时是很难说清楚的,金庸在《鹿鼎记》中看来是放弃了这个标准了。大侠们当然更不是那些武功高超者。小说中具有高超武功者如陈近男、洪教主、海老公等人无一人称得上是英雄,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狂妄自大、心地阴毒之人。什么是侠文化,小说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义”字,其余的都不是。韦小宝当然称不上大侠,但是,他“义”字当先,就不得不承认他的身上有侠气。在这一问题上,那些自称大侠的人倒是显得小气了。
《笑傲江湖》中的文化阐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生态有着强烈的影射性。《鹿鼎记》再将政治文化延伸到国民文化,对中国国民的世俗性有着深刻的反思。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精神切合。《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还是传统文化框架内的新拓展,《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不再是运用传统文化写武侠小说,而是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框架,在更深广的时政、社会层面思考问题,赋予中国武侠小说全新的面孔。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收放自如的自有境界。
三、文化人格:现代章回小说美学新价值
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能否写出“人的文学”来,张恨水已经用《啼笑因缘》等小说实践做了圆满的回答。①有关张恨水对“人的文学”做出的贡献的评析可参见汤哲声:《被遮蔽的路径: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现代化之旅——张恨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赏析》,《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章回小说写“人的文学”,既有精彩的故事,也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果说张恨水小说还是一种尝试,金庸小说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人的成长为中心,说故事、写人物。更有价值的是,怎样在章回小说的文体模式中写“人的文学”,金庸有着不同于张恨水等人的独特贡献。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小说中的人性张扬是将人物置于与传统文化的对抗中完成,写人性的多面性和人生的困顿,要求的是人性的发展和创造,是外国的人道主义观念的张扬,受到的是当时文坛新文学的影响。金庸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阐释人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中阐释政治文化与国民文化,写人性的规范性的光彩和对人生规律性的思考,金庸小说中的“人性”更具有中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写“人的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既然是以文化思考人性,金庸小说也就塑造出了一系列的文化人格。要论儒家人格,可以推陈家洛和袁承志;要论墨家人格,应该是郭靖和黄蓉;要论佛家人物,最精彩的当然是段誉、虚竹、慕容复;要论政治人格,是任我行、林平之、岳不群,浪子令狐冲也应该属于政治人物,只不过是另一种形态;要论到国民人格,自然是韦小宝。只要讲到哪个人物,马上就能与某种文化特性联系起来。令人称道的是,这些文化人格几乎每一个都很鲜活,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新文学中的文化人格是写人的压抑和人的反抗,压抑的重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世俗社会,反抗对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世俗社会,例如鲁迅小说中孔乙己人格、祥林嫂人格等。金庸小说中的文化人格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写人的出彩,在现实的世俗社会中写人的生动。金庸小说告诉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中和现实世俗生活的书写中同样可以写出鲜活的文化人格。传统文化体系和民族世俗性场域对人性和人生来说就是一种设定,一种规范。按照现有的文学理论,人道主义的人性、人生的形象构造是塑造人物的路径,而在设定、规范体系中塑造出的只能是模式化的类型人物。这样的分类看似不错,既然是设定和规范,人物形象的塑造只能是类型化。问题是,类型人物是否也能创造出鲜活的文化人格呢?金庸小说给出了肯定回答。
值得思考的是,金庸是怎样写出那些鲜活的文化人格的呢?这与金庸小说创作的开放式思维有很大关系。
家学渊源使得金庸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之本,文化教育和学识成长又使得金庸接受了现代文化的滋养,并成为了他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视角。传统世俗文化是根基、是守定,现代文化是视角、是方式,传统世俗文化给他的小说带来了厚重,现代文化视角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活力。这样的创作思维在金庸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很突出。传统世俗文化是恒定的规范,现代文化视角却是多面与灵活。在我看来,金庸小说的现代文化视角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西方文学艺术。例如在韦小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宫廷戏中的弄臣形象的影子。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那些复仇小说、侠士小说对金庸小说也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些外国小说的人物也还是类型人物,但是异样的影响给金庸小说人物带来了异样的色彩。
二是电影艺术。金庸小说中有着众多的电影镜头,举两例说明。《天龙八部》中段誉碰到的第一个女孩子是木婉清。木婉清始终蒙着一张面纱,她的那张脸不能给人看,谁要是看到她那张脸,她就要嫁给谁。她那张藏在面纱后面的脸是什么样子,就是小说中一个“关目”。怎么解这个“关目”呢?金庸用的就是电影特写镜头。段誉用双手捧着一掬清水走到木婉清的面前,叫她喝水。木婉清受了伤,流了很多血,口渴得厉害,迟疑了一下,终于揭开面纱的一角,露出嘴来。木婉清的脸是什么样子呢?金庸写了一个画面:“其时日方正中,明亮的阳光照在她下半张脸上。段誉见她下颌尖尖,脸色白腻,一如其背,光滑晶莹,连半一粒小麻子也没有,一张樱桃小口灵巧端正,嘴唇甚薄,两排细细的牙齿便如碎玉一般,不由得心中一动:她实在是个绝色美女啊!这时溪水已从手指缝中不住流下,溅得木婉清半边脸上都是水点,有如玉承明珠,花凝晓露。”①金庸:《天龙八部》,第126页。用一个镜头来解决读者心中的疑问,木婉清的脸是什么样子,读者自己去看吧。电影的特写镜头突出的是画面感,在金庸小说中比比皆是,稍微回味一下,那些画面就会在你的脑海中停留,挥之不去。
三是接受中国鲁迅等人的新小说的影响。鲁迅等人的新小说善于用细节刻画性格、塑造形象,金庸小说同样做得相当到位。我这里介绍几个人物出场的情况:
“持白子的是个青年公子,身穿白色长衫,脸如冠玉,似是个贵介子弟。”②金庸:《书剑恩仇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75页。这是陈家洛的出场,突出了一个“雅”字,金庸抓住了几个细节,一是白色长杉,这是个读书人;二是面如冠玉,长得英俊;三是下围棋,有贵族气息。在中国围棋和象棋是有区分的,围棋透着雅气,象棋只能算是大众娱乐。陈家洛的性格和形象一出场就已经展现。
“就在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左手提着一只公鸡,口中唱着俚曲,跳跳跃跃地过来,见窑洞前有人,叫道:‘喂,你们到我家里来干么?’走到李莫愁和郭芙之前,侧头向两人瞧瞧,笑道:‘啧啧,大美人儿好美貌,小美人儿也挺秀气,两位姑娘是来找我的吗?姓杨的可没这般美人儿朋友啊。’”①金庸:《神雕侠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41页。这是杨过的出场。脸上贼忒嘻嘻,说话油腔滑调。这是个小乞丐的形象,估计他抓来那只公鸡也是偷的。杨过的性格和形象在这里有了个初步交代,无拘无束,无所畏惧,插科打诨,一副自由自在的样子。
再看一个人物出场:“蓦地里大堂旁钻出一个十二三的男孩,大声骂道:‘你敢打我妈!你这死乌龟、烂王八,你出门便给天打雷劈,你手背手掌上马上便生烂疔疮,烂穿你手,烂穿舌头,脓血吞下肚去,烂断你肚肠。’”②金庸:《鹿鼎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45页。不用我多说,韦小宝出场了。
形成金庸小说创作开放式思维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社会身份。金庸是武侠小说家,同时也是个报人和出版家,还参加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具有很强的政治思维能力。他除了写小说,还写了大量的社论、时评、世评,翻译过外国小说、随笔,写过学术论文。李以建曾任金庸的秘书,他这样评说:“如果说,金庸小说是浮现在海面上冰山的雄伟壮丽的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部分,二者是无法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③李以建:《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新华文摘》2019年第2期。确实如此,金庸相当关注时事大事、社会变化,并不断地通过社评等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等文章,他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每天同时写着两种文体。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中思考问题,社评等政论文体中的逻辑思维必然再通过小说中的形象思维表达出来,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阐释。令人钦佩的是,金庸能够将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中的批判思维与小说的形象思维圆融地糅合在一起,非大手笔不能完成。这也许正是金庸在中国武侠小说创作中能够“一览众生”的最重要的原因。④2018年11月13日社会各界人士送别金庸先生,金庸的灵堂中写着“一览众生”的横联。“一览众生”有着禅意,是说金庸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看穿、看透。“一览众生”是从“一览众山”化境而来,是说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座难以比肩的高峰。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其作家、作品多如星斗,金庸小说备受推崇,就在于其光亮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