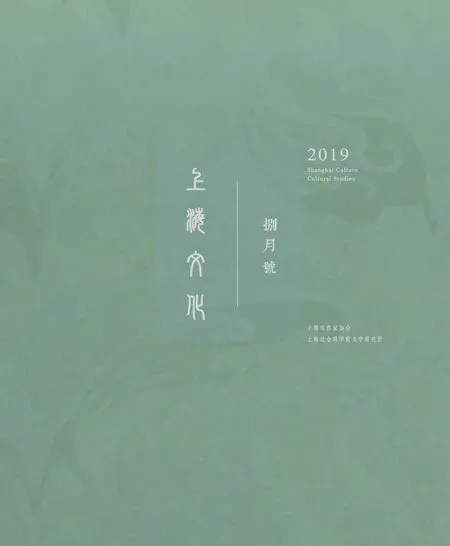金鲁贤早期(1926—1946年)著述文献整理与研究
李 强
金鲁贤(1916—2013年)是当代中国天主教的著名人物,被中国天主教界和学界公认为是杰出的天主教领袖,也是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推动者。①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纪念金鲁贤主教》,《中国宗教》2013年第5期;徐宏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推动者:纪念金鲁贤主教诞辰百年》,《中国宗教》2016年第7期;朱晓红:《论金鲁贤主教关于社会服务的思想》,《中国天主教》2016年第4期;房兴耀:《爱国爱教荣主益人——纪念金鲁贤主教诞辰100周年》,《中国天主教》2016年第4期;周太良:《“福音应民族化、本地化、中国化”——深切缅怀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中国天主教》2016年第4期。国外新闻媒体和学术界有关金鲁贤的报道和研究亦较丰富,如美国记者艾明德(Adam Minter)在《大西洋周刊》(The Atlantic)上的两篇文章,以及美国学者柯学斌(Anthony E. Clark)在《天主教世界报道》(The Catholic World Report)上的文章。
鉴于金鲁贤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时期在当代中国天主教发展进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中外学界对他个人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其人生的后半段,或是考察特定时期他的相关活动,或是从他的“牧职”实践中探究其对中国天主教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而少有研究者关注作为个体的金鲁贤的早年时期生活及相关著述活动。即便是金鲁贤自己的回忆录对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也是略微提及,也未在他生前编订的文集中收录彼一时期的相关著述。②金鲁贤主教著述主要见于金鲁贤:《引玉集》,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金鲁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金鲁贤主教牧函集》,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12年;《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
而金鲁贤的早期著述文献,无疑是进一步认识其早期个人经历的重要依据。同时,通过这些文献并结合他个人及相关中国天主教群体的思想表述,以及民国时期的时代因素,也可反观彼时中国天主教的相关本地化思潮。因而,本文写作的目的既在于认识金鲁贤的早期经历,也在于进一步认识他所处时代的中国天主教,进而理解金鲁贤“爱国爱教”思想对当代中国天主教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源头。
一、徐汇公学读书期间(1926—1932年)的刊物习作文章
金鲁贤1916年6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现属黄浦区),圣名类思,法文名“Louis”。其父金望德,生于1885年;其母张云贞,生于1884年。金家早年世居浦东金家巷,世代信奉天主教。①《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5-8页。在金鲁贤之前,作为天主教重要社群的金家巷仅有金若瑟、金文祺两位传教神父成为教区神职。金若瑟,名轼,字品三,1858年生,1872年入修院,1884年晋铎,1926年去世于江苏泰州,曾被江南教区派往意大利学习;金文祺,1901年生,1920年入小修院,1931年在徐家汇圣依纳爵堂“晋铎”,后传教于横沙、张家楼、徐州等地,1934年调至太仓张泾,1937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金鲁贤为该“会口”第三位神父,第一位耶稣会士(1938年入会)。到读书年龄,金鲁贤与很多上海周边地区信仰天主教的少年一般,选择进入徐汇公学(1933年改为徐汇中学)②关于徐汇公学的历史演变,参见马学强:《“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近代上海徐汇公学研究》,《史林》2010年第6期;庄小凤、马学强主编:《西学东渐第一校——从徐汇公学到徐汇中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熊月之:《徐汇中学百年名校》,《千江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9-83页。学习。金鲁贤于1926年9月6日进入徐汇公学小学部,1932年毕业于该校高中部。他在回忆录中只是简要地记录了学习生活的大概,特别提及对阅读各种中外文学作品的热爱。他回忆说,尽管徐汇公学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式教育”,但“无论如何,我学会了法文,高中毕业时我已经能看原版的法文小说”。③《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22、17-18页。
在该校读书期间,金鲁贤的家庭发生了一连串重大变故。1927年其母亲即因病去世,其父亲的生意也受挫,家境逐渐衰落。1931年其父因肺炎去世。金鲁贤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们姐弟3人成为孤儿后,亲戚们的各种“狠心”行为。④《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22、17-18页。在徐汇公学读书期间少年金鲁贤经历的诸多家庭重大变故,也影响了他个人性情的发展。
徐汇公学的毕业生去向,或是升入大学,或是回乡服务,也有不少人走向修道之路。如1926年金鲁贤刚入学时,应届32名毕业生中,有唐致中等8人于1926年9月4日进入小修道院(也即教区修道院系统下的耶稣圣心修院)。⑤潘振华:《送同学入圣心修院记》,《汇学杂志·乙种》1926年第3期。
1932年高中毕业后,金鲁贤面临未来出路的问题。他虽已考取了震旦大学,但在毕业避静时,选择了“弃家修道”进入教区小修道院,准备成为一名教区神父。这一选择必然也与他的家庭状况、个人宗教情感等因素息息相关。
历史地来看,“弃家修道”也是徐汇公学中具有天主教信仰学生的传统。该校自1850年成立以后,即成为重要的天主教传教人员的摇篮。1926年金鲁贤入学当年的10月28日,正值罗马教廷祝圣6位华人主教,其中的海门教区第一任主教朱开敏早年虽不是徐汇公学的学生,但在加入耶稣会后,曾担任徐汇公学的监学和教员。⑥据综合教区修院和耶稣会的档案资料,朱开敏,名铭德,字季球,原籍青浦诸巷,后世居董家渡,1868年生,1882年入修院,1888年入耶稣会,1898年“晋铎”,1903年2月2日发耶稣会的“显愿”。他在彼时也成为整个中国天主教的光荣,特别激励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教区的中国天主教徒,增强了他们发展本地教会的主动意识。①参见沈润卿编:《诸巷会修道人表·叙》,陶飞亚主编:《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第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而就在此种环境下,刚入学不久的金鲁贤,也遇到朱开敏回徐汇公学演讲的重要时机。朱开敏向徐汇公学内的天主教学生训示说:“罗玛教宗特简我华人为主教,成属鸿恩殊遇。惟主教之职綦重,亟需信友之辅助。故学生时代,即宜品学兼修,俾他日能成完善之教友。诸生之特蒙主召者,更宜善备为将来之好司铎也。”并说“将来涉世,于社会交际场中,苟德学俱著,必能受教外人之重视;既重视斯能听从,既听从斯能同化矣”,勉励学生“努力于学问道德,必能成有为之人,为国家效力,为圣教会效力。苟如是,非仅为一身之荣,一家之荣,亦全国之荣,教会之荣”。②李则曾:《欢迎朱主教略记》,《汇学杂志》1926年第9期。
朱开敏的鼓励,无疑激发了更多中国天主教青年走向“圣召”的主动意愿。1932年9月3日徐汇公学毕业生中共有18人进小修院,“弃家修道”者如此之多,实属罕见,其中就包括金鲁贤;1933年9月4日则有6人。③1932年徐汇公学入小修院的毕业生有:卞国玉、傅鹤洲、倪林祥、金鲁贤(Kien Lou-yé)、邱岑生、戈锡基、张孝松、张良贤、邹福生、朱福仁、诸宏玉、黄道生、黄金芳、陈天保、陈天祥、钱志元、钱益生、杜锡恩;入震旦学法政科有:陆景龙、张尚德;数理科有:沈耀庭、徐裕昆;医学科:金爱德、周渭良、蒋鸿仪。参见《一九三二年毕业生的升任》,《汇学杂志》1933年第15期。
金鲁贤在就读徐汇公学期间,也在该校《汇学杂志》上发表若干篇短文。这些文章是了解其青少年时期思想状况的难得史料。以下按照这些文章的主旨分而述之。
(一)个人生活情感的表达
对金鲁贤个人而言,“命苦”是他青少年时期最大的人生经验。如他所言,“我丧父、失母、亡姐,弟死未见尸骨,接二连三的打击,我的命真苦”。④《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27页。这种生活的痛苦之感,也表露在金鲁贤早期个人情感文章的字里行间,特别是他1930年在徐汇公学读书时所写的《黄纸条》一文:
呀的一声,散心场的门开了,看门房的人走进来,手里拿了一叠黄纸条交给监学;同学顿时饥民抢米票似的,蜂到监学身边,好一等到监学叫到自己的名字,就立刻可以接了纸条,到校长处去盖印。
我杂在这一群饥民争食似的同学们中,等我的黄纸条。
监学手中的纸条,一些少一些,同学也差不多走了一大半,我尚没听得叫到我的名字。
这时我的小心,跳的速度,比平日加快了一倍。“他们没有接到我的信么?”“不会的。”“他们忘了么?”“不会的。”“那么为什么不来叫我呢?”好似有呓语病的我,这样的想。
监学手中的纸条发完了,我金鲁贤三字,却没有从监学的口中出来过。那时监学的身边,只有可怜的我一人立在;监学用手一拍,拿了他的大日课经,向我说:“金鲁贤你没有呀!”说罢就独自念他的日课经去了。
那辈在校长处打印回来的同学,都满脸推着笑容,好比在战场上凯旋回来的兵士。
我呢!在操场上垂头丧气踱来踱去;看同学们越跑越稀,眼中的泪,几几乎滴点下来了。①金鲁贤:《复活瞻礼放假三天·黄纸条》,《汇学杂志》1930年第9期。
这篇记叙文蕴含了很深的情感,特别是一种青少年特有的思亲之感跃然纸上。而彼时的金鲁贤却没有收到代表有家信来的“黄纸条”。从此篇短小的抒情文中,可以看出少年求学时的金鲁贤因家境变化,在心理上颇为敏感,缺少家人的探望和问候,也在其年幼的心中留下了伤痛。
此种凄惨境遇,也使得少年金鲁贤看透了世事的炎凉。“人生经历虽然痛苦,但也让人看清很多东西”,促使他的宗教情感进一步加深:“我深深感到,小时穷,青年时遭挫折、多磨难、过贫穷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天主的降福,使我有同情心,心里能想着穷人,也想着为穷人做一点儿事,想交一些穷朋友。”②《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27页。这种“同情心”,无疑是修道人所必备的。这或许也是促使金鲁贤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修道院的内在情感原因之一。
此一时期,金鲁贤也尝试翻译一些宗教文学作品,抒发宗教情感,如他和同学卞国玉一起节译的描绘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祈祷景象的《墓畔祈祷》一文。③卞国玉、金鲁贤:《墓畔祈祷》,《汇学杂志·乙种本》1931年第7期。可以说,这也为他以后从事宗教文学作品的翻译奠定了基础。
(二)“爱国心”与民族意识的体现
金鲁贤早期文章也含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表达,体现了他和其他中国天主教青年的“爱国心”。这种“爱国心”在这个群体中间早已有之,并有其延续性,而徐汇公学的教育无疑促进了这种情感的延续。
金鲁贤入读徐汇公学时,张家树神父担任舍监,后来成为徐汇公学的校长。④张家树(1893—1988年,Aloysius Tsang),又名端六,字庭桂,1893年6月30日生,毕业于徐汇公学后赴英留学,1911年在欧洲入耶稣会。1918年回国,在徐汇公学任教两年后,又至欧洲学习,并在法国负责华侨教务。1925年回沪,长期负责徐汇公学教务。1960年在上海市天主教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被选举为上海教区的正权主教。1988年去世于徐家汇天主堂。参见《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第215期(1925年10月10日)第1版;宗怀德:《怀念张家树主教》,《中国天主教》1988年第1期;付克勇:《爱国爱教的楷模:张家树主教》,《中国宗教》1996年第1期;张多默:《我的伯父张家树主教》,《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3期;沈保智:《张家树主教受命于艰辛之时》,《上海文史资料选辑》2002年第4期;龚国伟:《我所知道的张家树主教》,《世纪》2010年第4期;等等。张家树早年也是徐汇公学的学生,青少年时期即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张家树早年的“课艺”(徐汇公学考试作品)也多透露出这些意识和情感。
张家树在徐汇公学读书期间,长于写作,发表在该校《汇学杂志》的文章计有:《申江观剧记》《论日俄盟战之机关》《扶植民气说》《不倒翁传》《百步桥旅行记》《江湾观飞行艇记》《仲由喜闻过论》7篇及学期考试算学解题。⑤《汇学杂志》1912年第1期(庚戌下辛亥上学期合刊),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2年。对于这些“汇学课艺”中的优秀作品,徐汇公学的中文老师常在文末给予评语。如张家树《申江观剧记》的主旨在于讽刺当时政治人物的“表演”不如“优界之剧”之更新和改良,获评语为“借题托讽,挥写自如”。①《汇学杂志》1912年第1期(庚戌下辛亥上学期合刊)。
而“汇学课艺”能够反映徐汇公学针对中国学生设置的国文教学的宗旨和目标。统观张家树及其同学在徐汇公学时期的文章,大多关注时事,论说古今,表现了该校学生的国家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情结。如张家树《论日俄盟战之机关》一文,关注日俄之间的国际关系,开篇即言:“蒿目日俄之忽战忽盟,殊令神州酣睡之狮,今后不能一日安枕矣。”整篇论说揭露俄日对华侵略之历史和意图,通篇展示了他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担忧,获评语为“洞彻外情,隐忧祖国,目光四照,具有深心,极沉郁顿挫之妙”。②《汇学杂志》1912年第1期(庚戌下辛亥上学期合刊)。
整体而言,通过中文教学,徐汇公学的学生与其他具有进步意识的中国青少年一样,逐渐萌生了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③按:如张家树同学黄子鹤即有《爱国说》一篇,论曰:“况君我父母,民我同胞,一国之忧危困难,吾得充耳不闻乎?是以上之则尽我之忠爱,下之则尽吾之亲爱,犹己溺而己饥,夫然后方可谓有爱国心,而身家之爱,亦庶几赖以全矣。”参见《汇学杂志》1912年第1期(庚戌下辛亥上学期合刊)。这种教育宗旨和综合性教育内容的设置,也普遍影响到每个个体以后的人生选择。
张家树在任职徐汇公学期间,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虽然由于掌权的是外籍耶稣会士,相关行为也受到压制,而他的《扶植民气说》等文章表露的爱国思想还是在中国学生中间得到延续。④1993年金鲁贤在纪念张家树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提及张家树《扶植民气说》一文。参见宗怀德、金鲁贤:《爱国爱教的楷模——纪念张家树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天主教》1993年第5期。
金鲁贤在徐汇公学读书期间,正遇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脚步。中国天主教的代表人物马相伯等人也极力提倡中国天主教信众发挥自徐光启以来的爱国思想。⑤参见《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徐景贤编录笔记,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按:金鲁贤也曾提及他17岁时曾拜访过马相伯。参见《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1页。
金鲁贤也在一篇早期记叙文中表露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1932年3月10日,金鲁贤和同学周渭良等高中三年级学生一起,在徐汇公学圣母会值会司铎徐宗海神父⑥徐宗海,常被称为“徐味增”神父,因其圣名为味增爵(Vincentius Zi),字朝伯,1886年生,1906年入耶稣会。的带领下,前往震旦大学、仁爱会、广慈医院等天主教附属机构慰问受伤的将士,并将经过详细记录下来,以《慰问受伤将士记》为题发表在《汇学杂志》上。该文通过所见所闻,以及对受伤士兵的采访,显示了这些青少年对“国难”的关注,对保家卫国将士的敬佩。
金鲁贤等人并没有借此发出长篇议论,而是以记叙文的笔触将因保家卫国而受伤将士们的医疗状况呈现给读者,作者的爱国意识也随之隐含其间。
(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抒发
金鲁贤在徐汇公学具体的成绩如何,尚没有直接材料来予以佐证。但在毕业后能直接进入小修院,也说明了他品学兼优,是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也正因为如此,金鲁贤在毕业之际代表毕业生发表演说。
金鲁贤的《毕业生演说辞》在内容上抒发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他对毕业生同学说:“诸位同学自今日起,在形式上各走各路,但是在精神上我还盼望一德一心……我就用仁义礼智来勉励同学。我们将仁义礼智当做立身的基本,那就是一生用不尽的教训了。”金鲁贤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仁义礼智”是每一个个体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他进而说:“现在天灾人祸,国难临头,我们在上海安乐窝里,不知别处同胞,多在水深火热之中,若我们有些心肝,决不放两支脚跨进游戏场……我所希望的,就是各人善尽其职。从小事体上操练起来,忠信勤恳廉洁,不拘大小职司,都要有个责任心……同学如能将此责任普及全国民众,则上下一致,便可像水门汀一般团结坚硬起来,就可不受别人蹧蹋了。”①金鲁贤:《毕业生演说辞》,《汇学杂志》1931年第14期。金鲁贤在结语处并引曾子“一日三省”的警语,勉励徐汇公学的学生们实践“仁义礼智”。
可以说,金鲁贤的演说与张家树在20余年前的论说文有相通之处,因它们都饱含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着对解决彼时中国社会的时代性问题的思考。此外,金鲁贤的演说也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识和内化,且通篇未见对天主教教义的引申,而是从中国传统伦理观和“修齐治平”的方法上呼吁每一个个体责任心的实践。再者,在他成为主教后的“牧函”中,金鲁贤也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问题,并提出他所代表的天主教会的观点,引导信众融入当代中国的社会潮流。②参见金鲁贤:《兄弟共处,乐也融融,吾乐之缘,为我等祈——与教友浅谈构建和谐社会》,《金鲁贤主教牧函集》,第134-142页。
简而言之,青年金鲁贤的演说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也是他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这种社会责任感,也延伸至他在当代中国的“牧职”实践。
二、进入教区修院后(1932—1937年)的宗教文学译著
在圣心修院(小修院,1932—1935年)和圣母修院(大修院1935—1937年)修道期间,金鲁贤除了学习拉丁语、神修功课、中国古典文学、教会史、教会礼仪、教会音乐(小修院)、神哲学(大修院)外,还有1年(1937—1938年)在徐汇中学的出试。③参见《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25-31页。
(一)早期宗教文学翻译活动及成果
1. 译著《天上英儿》与《天上珠儿》
金鲁贤第一部宗教文学译著的全名为《天上英儿——琪特丰笳郎》,1935年由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出版。该书法文原名为“Guy de Fontgalland”,原作者碧禄(Henry Perroy)。
《天上英儿》主要描述了法国小孩琪特丰笳郎天真活泼的个性,诚实不欺的品格,以及敬爱“圣母”“小耶稣”的宗教虔诚行为。金鲁贤翻译此书的用意在于引导天主教儿童“志行纯洁,作事专诚,肯听命,耐劳苦”,④《书报介绍:〈天上英儿——琪特丰笳郎〉Guy de Fontgalland》,《磐石杂志》1935年第5期。增加该群体的宗教虔信度,强化宗教教化。
第二部题名为《天上珠儿》。该书原作者是方济各会的戴尔华(Victorin Delvoie)神父。《天上珠儿》也可看作是名叫亚纳的一位法国小女孩(1911—1922年)的传记。戴尔华集合了其他亚纳传记的精华,以演讲体的形式重新创作,成书名曰“Anne de Guigné”。该书于1931年出版,1936年即由金鲁贤译出,亦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
亚纳1911年4月25日出生于名叫“Annecy-le-Vieux”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1922年1月14日在戛纳(Cannes)离世。亚纳是其父母4个孩子中的大女儿。其父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中受伤去世,此后亚纳性情大变。原本暴躁、倔强、固执、嫉妒、骄傲的亚纳转而听从母亲教导,行为举止端庄淑雅,热心于宗教生活,但于1922年即因病去世。
《天上英儿》与《天上珠儿》都是“圣体军小丛书”之一种,而“圣体军小丛书”又是“公教学生文库”下的一种丛书。很明显,该丛书面向的读者是具有天主教信仰的中小学生,而金鲁贤的翻译是天主教会赞助和支持的集体翻译活动的组成部分。
2. 宗教文学译著的读者意识
天主教圣人传记文学的“读者意识”主要体现在借助圣人的德行加强信众的宗教虔诚度。《天上珠儿》也就起到了向儿童少年讲道的作用,要他们如亚纳般多领圣体,勤望弥撒,刻苦努力,为人谦逊,听从长上之命,善待他人等,也即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宗教实践。金鲁贤翻译此类传记文学作品的目的在于训导天主教青少年“天天改毛病,天天修德行”。①戴尔华:《天上珠儿》,金鲁贤译,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6年,第43、13页。
金鲁贤的翻译明显带有宗教教化的目的指向,这一翻译动机和目的在他的《天上珠儿》译序中也有清楚的表达:“(此书)事约而赅,词简而显,诚为儿童阅览之佳本……则此编岂但为儿童读品,亦为父母师长教养儿童之标本,修德作圣之模范也。”②金鲁贤:《天上珠儿·序》,戴尔华:《天上珠儿》,第1页。
彼时作为神职人员后备的修院修生,金鲁贤通过翻译天主教信德模范的文学传记承担了向教众进行宗教教化的责任。这种宗教教化的信仰目的在于让普通信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宗教道德和伦理观念。
这也要求金鲁贤要把译书时的“读者意识”放在中国天主教儿童身上,采用他们易于理解的语言。比如在叙述亚纳在其父去世后,遵从母亲教导,事事顺从的“孝行”时,金鲁贤引用了中国俗语“百行孝为先”来与读者对话,劝他们效法“小亚纳从孝上开首修德”,并告诫读者“你们要父母喜悦,小耶稣欢爱,也该如此”。③戴尔华:《天上珠儿》,金鲁贤译,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6年,第43、13页。
《天上珠儿》的译文实际上可以等同于金鲁贤自己的讲道文,而且内化外行于他日后的神职牧灵实践中。即便时光过去近90年,我们在金鲁贤作为主教时的讲道中,仍能看到类似的表述模式。如讲道文《致公教家庭——耶稣显圣容瞻礼儿童感恩祭中的讲道辞》在论及父母在家庭中要树立好的榜样时,金鲁贤说:“古人云:‘有其父必有其子’,父母怎样,子女也怎样。”④金鲁贤:《引玉集》,第181页。按:在同一篇讲道文中,金鲁贤主教在述及教师的教育时,引用了另一句俗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来强调“提倡全社会尊爱师长的风气”。可见,金鲁贤从中国俗语中引申出天主教家庭进行宗教教化的重要方式是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而父母言传身教的重要内容又在于“爱国爱教”,如金鲁贤所说:“将来我要是能在天堂上,看到今天许多的青少年中,有的能作到修女、神父、主教,都能做一个好公民,那是最令人欣慰的了。”①金鲁贤:《引玉集》,第184页。金鲁贤在此时强调的宗教教化,是要求天主教家庭在“爱国”和“爱教”两个方面引导青少年的道德成长。
(二)作为“公教学者”的金鲁贤
如何理解金鲁贤在早期译作以及后来讲道文中一以贯之地引用中国俗语呢?答案非常简单且显而易见:因其是一名中国神职人员,面向的听众(或者说宗教教化对象)是中国天主教信众。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但对于理解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宗教文学的本地化进程却又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我们还要注意到彼时“修生”金鲁贤的“公教学者”身份。
“圣体军小丛书”借助一批“公教学者”(也即“天主教知识分子”②“天主教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是接受修院教育的神职人员群体。)为青少年编著一批侧重于宗教教化的读物,目的在于“为了便利儿童读物和帮助之时训导一般公教青年,使他容易得到基本的公教智识起见”而创办发行。“圣体军小丛书”编著文本涵盖的文体和主题较为广泛,包括“经史、圣传、神修、圣召、伦理、指导、小说、剧本、诗歌”等类,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系统性的天主教汉语文献创作活动,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天上英儿》即是这一工程的产物之一,作为修士的金鲁贤也即彼时的“公教学者”之一。
回到金鲁贤翻译《天上英儿》《天上珠儿》的20世纪30年代,“本地神职”的培育和发展是彼时中国天主教会讨论的要题。出于满足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内在需要以及对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兴起的时代要求的回应,中国天主教界已经意识到培育“本地神职班”的重要性,并公开讨论此议题。
彼时的中国天主教界对“本地神职班”的重要性有以下共识:一是本地神职的培养,在天主教的宗徒时代以降,有其可遵循的历史轨迹;二是本地神职“在自己民族中,更能得到国人的信仰”;三是本地神职“更熟悉本地语言,风俗,习惯,与民族性”。③刘宇声:《本地神职班与传教事业》,《磐石杂志》1936年第10期。再者,鉴于彼时基督宗教被看作是“文化侵略”④相关研究参见陶飞亚:《“文化侵略”源流考》,《文史哲》2003年第5期。的工具,且在事实上存在中国公众难以了解和谅解之处,“本地神职”的培育有助于消除这种“误解”。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本地神职”如何作为,才能具体地体现他们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性和适应性?1936年发表在《磐石杂志》上的《本地神职班与传教事业》一文,给出了具有强烈“中国化”色彩的回答:(1)宣传工作;(2)社会事业;(3)文化事业;(4)国产修会;(5)传教区艺术问题;(6)传教工作的互动。⑤刘宇声:《本地神职班与传教事业》,《磐石杂志》1936年第10期。这些措施都是彼时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对“中国化”议题的思考与探索。
而彼时的中国天主教会对“公教学者”也提出了知识创造的要求,“哲理书”“教理书”“修养书”即成为“公教学者”应当着力贡献其知识准备和学术能力的方向。其中“修养书”主要是通过文学文本来作为主要表达方式。在他们看来,文学“虽不应纯以载道,然载道亦无害于文学。寓教训于文学内,实较直接施教,收效良多。有趣味之小品文,可助人改过;悲剧,可引起人之同情;小说及公教圣人传记等,皆可用作指导青年修养之工具”,因而有天主教知识分子呼吁天主教教内学者“群策群力,翻译著述”。①继高:《向公教学者请求一件事》,《磐石杂志》1937年第1期。
呼吁“公教学者”加强本国文字书籍创作的文章,在天主教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响应。1937年的《磐石杂志》上对此进行了讨论。一位名为周连墀的天主教中国神父认为“本国文字中无此良好的书籍”要归罪于“本地神职班”,也即指中国神职人员应当担负起天主教中文文献创作的主要责任,缺少此类文献是“本地神职班的耻辱”;他进一步认为“本地神职班”不应当在此事业上作旁观者,“每位司铎固然不能尽做到公教学者,但公教学者总该出自神职班,二千位司铎中总该有些公教学者”。②周连墀:《读继高君〈向公教学者请求一件事〉后》,《磐石杂志》1937年第3期。周连墀最后总结说:“每位司铎,该有做学者的决心,埋头苦读,成绩我们不用去管,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把‘传教不忘读书,读书不忘传教’,当做我们的座右铭。在上者提倡扶助,在下者努力苦干,我国公教学术,或有独立之一天;不然拖延疏懒,百年之后,仍恐不能满一般公青之要求。”③周连墀:《读继高君〈向公教学者请求一件事〉后》,《磐石杂志》1937年第3期。周连墀的回应和呼吁体现出中国神职群体在汉语天主教文献创作上的主动意识,是民国时期天主教神职人员本地化思想的一种表达。
翻译宗教性儿童文学,也即彼时金鲁贤“公教学者”身份的体现。
(三)从其译著反观民国天主教“儿童文学”的本地化
金鲁贤的宗教文学译著,可以归为“文化事业”一类。更进一步而言,是面向天主教内部的“文化传教事业”,也即通过文学化的信德模范传记来增强对天主教青少年的宗教教化。前文已述,金鲁贤所译两种宗教儿童文学作品可大致归类为故事性质的传记。在其译著出版的同一时期,中国天主教文坛也在讨论与“文化传教”相关的儿童文学的创作问题。
较早提出天主教“儿童文学”议题的有在徐汇师范学校学习的邹文华,他于该校校刊《我们的教育》上刊发了《建设公教儿童文学》一文。邹文华在文章中首先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儿童文学”④与民国时期“儿童文学”讨论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心科:《民国儿童文学教育文论辑笺》,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朱利民:《严既澄与现代儿童文学》,《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的定义问题,他先是罗列了彼时中国文学界各家对“儿童文学”的定义,⑤邹文华列举的文学名家有严既澄、戴渭清、周作人、周邦道、陈学佳、郭沫若等人。参见邹文华:《建设公教儿童文学》,《我们的教育:徐汇师范校刊》1932年第4期。随后给出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儿童文学”是“美善的,适合儿童心理生理的文学”。⑥邹文华:《建设公教儿童文学》,《我们的教育:徐汇师范校刊》1932年第4期。
邹文华呼吁天主教界应注重“儿童文学”,一是源自对同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回应;二是表达对天主教“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他进一步梳理了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并进而对“儿童文学”进行了分类,并就“怎样去建设公教儿童文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是“对于儿童的心理有切实的研究”;二是“对于儿童文学有详细的研究”;三是“自己常常住在婴孩世界,保存儿童的面目”。①邹文华:《建设公教儿童文学》,《我们的教育:徐汇师范校刊》1932年第4期。
金鲁贤的这两部译著可以说是邹文华以上倡议的翻译实践。“公教学者”的身份,使金鲁贤承担了此种“文化传教事业”的任务。
而实际上,这种实践也反映了彼时中国天主教知识界在宗教文学创作上的本地化思潮。如另一位天主教教育家黎正甫②黎正甫,福建人,曾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生卒信息不详。曾任天主教中文期刊《公教学校》主编,出版有:《儿童教育概论》(北平: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1936年)、《历代皇帝谥讳生卒年及葬地列表》(出版信息不详)、《雨后残蕾》(北平:传信印书局,1935年)、《宗教与人生》(北平:传信印书局,1936年)等。《儿童教育概论》一书第15章则专论“儿童读物”。在讨论“公教儿童文学”时说:进行相关创作时的宗旨是“指导公教儿童的正当生活,矫正儿童的误谬行为,灌输儿童以高尚思想,启发儿童以真理知识”;而在内容编选上,则注重“取材于公教的史实,祝圣人的传记、教理诸书,还可根据圣教会里的传说、故事而编述;或根据社会道德及教义教规,而作寓言童话”。另外,再论及翻译外国名著以作为创作的基础时,他强调翻译时“必须具有普遍性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而地方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最好不带一点地方色彩)著作为佳。译笔不宜过巧,行文造句,更应脱去外国语的强调”。③黎正甫:《编制公教儿童文学读物的商榷》,《磐石杂志》1934年第4期。
黎正甫关于中国天主教“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的见解,表达了比较明确的本地化思想。可以说,金鲁贤的译著活动实践了这种本地化思想。
三、在徐汇中学初试及加入耶稣会期间(1937—1946年)的文章
1937年至1938年,金鲁贤被分配到徐汇中学出试,也即在此实习,教授初二年级的法文,并负责训导初一、初二年级天主教学生的宗教生活。在此期间,金鲁贤进一步接触了耶稣会的管理方式和修会宗旨,萌生加入耶稣会的意愿,如他所言“绝意进一步把自己献给天主,进一步弃绝自己,有了进修会发三愿的念头”。④《金鲁贤回忆录上:绝处逢生1916—1982》,第31页。
金鲁贤1938年加入耶稣会后,先经历两年初学,又先后进入耶稣会文学院(1940—1941年)、哲学院(1941—1942年)、神学院(1942—1946年)。在此期间,金鲁贤自己逐渐受训成为一名耶稣会士,也承担了更多耶稣会的宗教教化活动,其中即包括撰写诸多有关天主教宗教信仰的讲道文和论说文。
(一)讲道文中的宗教教化与社会认同塑造
1937年金鲁贤已在修院5年之久,同时负责面向青少年平信徒团体的训导工作,也因此常借助教会刊物发表类似“讲道”的文章。这些文章也离不开对现实议题的关注。如《非常时期的圣体军人》一文,即关注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如何发挥天主教青少年信众的“爱国心”:
小朋友,你们念过圣经吗?路加经第十九章第四一节记着:“耶稣看了日路撒冷痛哭。”原来耶稣爱国心切,当时预见自己的京城,不久要遭大难,就不禁流泪了。小朋友,现在我们可爱的国家,正遭着空前大难,凶暴的敌人来侵略我们的土地,残杀我们的同胞,焚毁我们的房屋;我们,耶稣的勇兵,怎可不表示一些爱国心吗?①金鲁贤:《非常时期的圣体军人》,《圣体军月刊》1937年第3卷第2期。
金鲁贤认为,在“国难”时期,普通信众可以从“善行祈祷”“多做献祭”“勤领圣体”“勉为宗徒”4个方面的宗教性实践和活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心”。
毕竟,宗教神职对信众的引导作用不仅体现在纯粹的信仰层面,也体现在信仰的实践如何与社会的需要、时代的环境相结合的世俗层面。这篇“讲道文”可以说很适宜地在特殊环境中将加强宗教教化与塑造社会认同结合在了一起。
(二)耶稣会国际性的习得:与徐汇公学“圣母会”有关的两篇文章
由于在徐汇中学实习的缘故,金鲁贤在此时期也写有两篇关于“圣母会”(Congrégation de la Ste Vierge,中文全称为“圣母始胎会”)的文章。“圣母会”是耶稣会成立后在其所属学校、各种宗教单位中为平信徒成立的宗教性团体。徐汇公学的“圣母会”成立于1853年10月10日,其成员多是公学中的优秀分子,而且很大部分成员都走向了加入耶稣会或进入教区修院的“齐家修道”之路。②据1903年时的统计,该会在1853年成立之后的50年间共有会友477人,其中40人成为神父,耶稣会读书修士5人,辅理修士10人,天主母会修士5人,大小修院修生各15、17人,有秀才(生员)功名者38人。参见《圣母会五十年大庆》,《圣心报》1903年第199期。毕竟,“圣母会”的一大宗教功能即促进所属成员信仰的内在化。③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目前尚未看到金鲁贤在读书期间加入“圣母会”的直接资料。但考虑到他是徐汇公学优秀毕业生的代表,也应是该团体的分子之一。1939年在“国难”时期,徐汇中学“圣母会”的《慈音》还在坚持出版。该刊物1939年第1-2期刊发的《慰年》一文鼓励会员按照《圣经》的训言祈求“天地大主”“要为吾中国祝祷,为中国的圣教会祝祷,为吾每一个同胞祝祷”。④张士泉:《慰年》,《慈音》1939年第1、2期。
金鲁贤编译的《圣母会的光荣史》一文,也发表在同一期《慈音》上。金鲁贤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圣母会”的体认。他认为,“圣母会好似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这家庭的家属”。⑤金鲁贤:《圣母会的光荣史》,《慈音》1939年第1、2期。
随后,金鲁贤按照日历顺序向该会会员介绍了“圣母会”历史上30位被列为“圣人”的会员。这30位“圣人”虽然有宗教阶层和世俗出身的差异,但有一个相通的共同点就是:都不是中国人。因而,金鲁贤在文章结尾发出如下期望:“圣教传到了中华,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母校圣母会成立到现在,也已八十五年了,但是这名单上,寻不到一位同胞的芳名。为此,我再祝望,后来若有人向诸位报告圣母会的光荣史时,能够加上一位或数位新圣人,说道:某某某,中国,上海,徐家汇,依纳爵公学的圣母会会友。”①金鲁贤:《圣母会的光荣史》,《慈音》1939年第1、2期。
作为国际性天主教修会耶稣会附属宗教性团体的“圣母会”,在宗教信仰层面,共享了耶稣会的国际性。徐汇公学的“圣母会”会友,也与全球“圣母会”相“通功”,进而在信仰层面寻找到模范和榜样。但是,本地“圣人”的出现更能强化信仰的虔诚度。因而,金鲁贤鼓励徐汇公学“圣母会”会员“成圣”,也就蕴含了一定的信仰本地化意识。
此外,金鲁贤另一篇与“圣母会”相关的文章刊发于1944年,题名《徐汇中学圣母会九旬纪念主教训词》,乃翻译自1943年11月26日上海教区主教恵济良(Auguste Haouisée)为庆祝徐汇公学“圣母会”成立90周年所发的训词。该训词强调增强会员们的“超性生活”。②惠济良:《徐汇中学圣母会九旬纪念主教训词》,金鲁贤译,《慈音》1944年第1、2期。
除了以上两篇与“圣母会”相关的文章外,耶稣会士金鲁贤在此期间还有多篇“论道”文,注意于强化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教化,提升宗教“热心”,这也与他的宗教身份相符合。③这些文章集中于《圣心报》《圣体军月刊》等天主教宗教性刊物,如《达尼老与克己》《圣诞瞻礼与圣体军人》《主日上拜圣体》《奉献经》等。
综上所述,通过整理和研究金鲁贤早期(1926—1946年)著述文献,既可丰富学界关于金鲁贤个人人生经历的认知,也可在天主教中国化的学术视野下考察他的具体实践和相关思想。此一时期的青少年金鲁贤在特定阶段有着明显的人生转折痕迹,且在天主教的培育体系下逐步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并参与了相关宗教教化活动。但在大的时代环境中,他与其他受教育的中国青少年一样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担当,这一点我们既可从张家树的早期著述中体会到一种时代性,也可在金鲁贤晚年作为中国天主教重要人物的言行著述中得以窥见某种延续性。
总的来说,金鲁贤宗教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他早期相关著述的侧重点。不过,具体到天主教中国化的视域,考察金鲁贤早期著述文献的主要意义在于发掘他作为一名典型中国天主教宗教人物的相关思想及对当代的启示。
——国际化大型社区徐汇苑管理特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