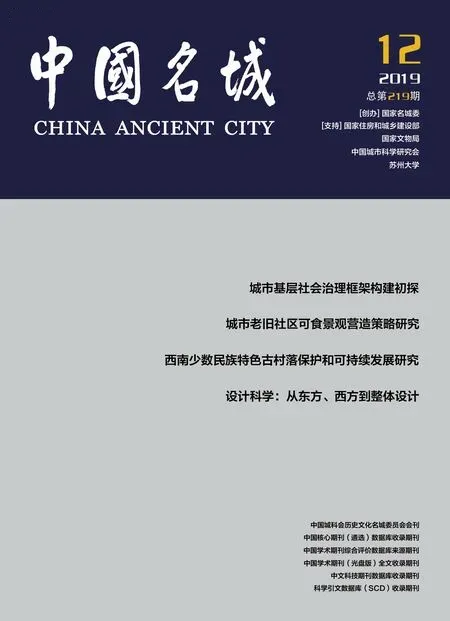传统聚落文化记忆对公共空间形态的构建特征研究*
——以贵州安顺雷屯为例
周 红 王梦妮
20世纪末,德国学者扬·阿斯曼首次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1];“文化记忆包括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分享的有关政治身份的传统,相关的人群借助它确定和确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和与众不同之处。”[2]简单来说,文化记忆在经过一些矛盾与冲突之后,具有选择性和倾向性。经过时间累积的不断开放以及不断重建循环之后由集体的记忆提炼下来,它代表着区域内集体所有成员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兼顾所有人的情感和利益,具有最高的约束力;区域内全体成员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强化一个具象的身份,并能在集体性事件上保持一致的意见并且能够采取统一的行动。
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在西方学术上采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曾叙述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即各种自发的公众集会场所和机构的总称[3]。二十世纪以来,在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下,研究与关注“公共空间”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当一定的社会组织形态与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具有了某种公共性,并在物质空间中相对固定下来时,就形成了公共空间[4]。它是居民可自由出入的,进行日常社交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社会生活的主要的场所,容纳与承载村民公共生活及邻里交往的物质空间。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构建反映了基层乡村居民的公共娱乐精神状态,能为新时期美丽乡村公共空间和文化娱乐生活的建设的研究带来思路。综上所述,村落公共空间形态,它不仅是公共空间的外在表现形式、分布特征以及公共空间的形体环境。同时,它具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反映出了社会生活与场所精神的环境与秩序。
贵州省安顺市雷屯的公共空间的分类可分为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两类。物质公共空间是指在相对固定的某个特定的物质空间而展开的村民思想交流的场所,这类交往空间通常是具体的、有形的[5]。根据开放程度分为开放型公共空间、半开放型公共空间。如果更全面来理解,聚落内的公共空间还包括庭院、门檐下等一些半私密性公共空间,而本文对屯堡公共空间的探讨则基于一个开放的层面。非物质空间是指传统村落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约定俗成的活动形式,这类空间的空间形态是抽象的、无形的,且是不固定的,它因民俗活动而生[2]。如跳地戏的场坝空间、唱山歌的山头、红白喜事仪式等等。
1 安顺雷屯概况
雷屯的地理区位是贵州省安顺市黔中地区的七眼桥镇,东经 106°10′,北纬 26°21′,北临水洞口村,南接小山村,处在以屯军山与麒麟山为主的山地环抱的盆地内。安顺雷屯位于中国华南喀斯特地貌核心部位,气候一年四季温和舒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有丰富的地下水源。它处在发育最集中、最成熟、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带。全村行政区面积12.0Km2,村域总面积为1.8Km2,其中,传统村落重点保护面积为0.056Km2,现有住户大约823户。雷屯目前还是一个未完全被现代化发展同化的古村落,主要依靠着原始农业为生,是安顺地区众多保存完善的特色屯堡之一(当地的方言“堡”字的发音念做pu,上声)(图1)。
贵州安顺雷屯建于明洪武年间,是贵州军事防御的重要战地之一,大量南方地区移民随调北征南政策来到安顺雷屯,并在严厉的军籍制度下筑城安居。贵州历代俗称“山地之国”,在元朝以前,贵州地区未被完全开化,一直被称为 “蛮夷”之地,发展缓慢且生产落后。明朝统治后,其并没有完全控制西南地区,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贵州的稳定关系到云南边防的巩固和西南政局的稳定,于是开始派重兵防守,并且实行的强制的调北征南政策,及军籍管理制度,沿线修整驿道,设立卫所。当地的喀斯特地形地貌使得石头材料随处可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营建思想造就了雷屯建筑的石质建造风格技艺,延绵不断的石头建筑构成了一道颇为壮观的亮丽的风景线。在空间装饰中,如铺地,建筑雕花,龙、凤、鱼、兽则运用于各家各户,妇女服饰“凤阳汉装”的头饰、耳饰乃至腰带、挂饰、鞋子都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非物质遗产。在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雷屯军民一心,逐渐沉淀出了雷屯固有的文化记忆,并影响了雷屯一代又一代人。
2 雷屯的文化记忆解读
2.1 “平衡共生”的喀斯特地貌记忆
贵州约13万平方公里都是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是我国喀斯特区域最为集中及典型省份。雷屯就建立在贵州喀斯特地形之上,地形与地质条件决定下的生存困境,使雷屯居民必须要在聚落选址意识、构筑物空间的适应性、构筑物结构与材料的应对等方面去寻求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特征是地势陡峭,地形破碎,覆土层薄,平坦的地面在喀斯特山区非常稀少,尽管降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但土质稀薄调蓄功能差,水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存在一定的旱涝灾害。恶劣封闭的环境使得他们安贫守旧,形成一种低层次的人地共生平衡关系。喀斯特文化是喀斯特地区的人们智慧对环境的适应、利用与改造的结果,脆弱的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紧紧依附于自然,衍生出对自然的崇敬、崇拜,形成信仰及图腾。
2.2 “征南平边”的军事防御记忆
雷屯源于明洪武年间的征南部队,明朝平定中原后派30余万大军铲除前朝残余势力以拓展疆土,经贵州一路南下,扫平云南;后命征南部队沿湖湘至云南的驿道上就地驻扎,昔日人烟荒芜的喀斯特地貌地区瞬间集聚了大量军士,各自分成各个屯兵点进行驻守,而雷屯是当时八大核心屯军点之一。初期雷屯因此形成,其军事防御记忆是其村建立的前提,他们具有强烈的家国荣誉感,是强大且光荣的军事胜利者。他们及其后裔在身份、权力和文化上都较之于当时的贵州的原居民先进,显示出强弱之分,华夷之分、文野之分。军营式管理使得雷屯聚落的整体风貌充满的很强的防御性风格。村落中地戏文化大部分都是古代征战故事,从另一方面也是在宣传和暗示自身祖先的光辉战绩给自己一个强大的背景记忆,不仅在本村落,而是在各个村落都互相传承。祖先“王朝武士”的将军身份永远成为他们记忆的源头和族群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
2.3 “江南祖地”的儒家礼制记忆
由于明朝初年为了稳定西南地区局势以拓展疆土而实行的调北征南政策,大批江南地区移民随政策迁入贵州安顺雷屯,明朝实行军籍制度,及行军打仗时,军人家属随军出征,亦随军家属随驻军屯驻,其带有原籍地的浓厚文化记忆,促进了西南边陲的稳定和发展。在对雷屯的调研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祖籍是明代“调北征南”时从老家江南移民来的,在祖辈口耳相传中很明显的感受到提及入黔祖先是军人身份的自豪感。他们随政策来到“蛮荒”之地要依靠自身携带的先进文化生存,而当时的江南是经济富庶之地和文化繁荣之区,也是明初政治中心,展现出了一种落差和对故乡江南的思念,也使他们固化了对祖源地的地域认同。即便至清代康熙年间卫所制度解体,屯堡内军人身份转为农民,并与后来的汉族移民相比逐渐边缘化,但他们仍“不忘初心”,执着地保留着对“江南”的记忆。
2.4 “军事信仰”的民俗文化记忆
在雷屯公共空间的职能中民俗活动和宗教仪式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的节庆活动。雷屯有非常多的祭祀活动和寺庙建筑。寺庙祭拜对象不仅仅局限神灵,还有许多崇敬、崇拜的军事人物。另外,每家每户中基本有祠堂、神龛,上面写有“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儒家礼制文化的思想。其二,每个月都有佛事,由已婚女子参加。民俗活动重点体现在地戏文化。地戏又称“跳神”,不仅在安顺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盛行,还包括布依、仡佬、苗等少数民族中流行。地戏的题材大多为古代战争类型,内容基本上为精忠报国的英雄故事。村民通过对正史类人物“忠、义、勇”的主题精神的描刻与演绎来传达本村落的历史和信仰。雷屯地戏除十年动乱外,从未间断。还有著名的“抬汪公”仪式类活动,基本在吉昌屯举行。还有其他的一些如跳花节、四月八、六月六等节庆活动[5]。
3 文化记忆对雷屯公共空间形态构建特征分析
“文化记忆有其固定点,它的范围并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固定点是过去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其记忆是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和庆典)维持的,我们称之为‘印迹形象’(figures of memory)。”[6]这里所指的印迹形象是文化记忆的具象表达,我们能够清晰的理解文化记忆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头交流或是书本记载,而是由潜意识中的具体象征载体传承,其象征载体在整体上按照一定的结构秩序和空间布局共同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文化记忆公共空间。通过公共空间的各种文化记忆活动达到对传统村落结构和精神意义上的整合,从而到达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文化记忆对雷屯公共空间形态的构建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3.1 围合式空间场地特征
“场景的围合是造成到访者具有场所感的关键,进而也是塑造文化记忆的关键。”[7]传统雷屯村落公共空间形态是围合式的,客观上与喀斯特地貌文化记忆的适应性有关,精神上又与移民军事化文化记忆的防御性有关。屯堡的选址尤为重要,一般遵循“靠山不据山,傍水不进水”的风水法则,符合围合式的空间场地特征,雷屯把麒麟山、屯军山、三岔河等喀斯特地貌环境要素作为村落边界条件加以利用,形成自然围合边界。然后加以非连续性的村口、迎星门、石桥等人造的象征性围合边界,作为村落边界的标识入口空间,它们与民居的建、构筑物有不同的形式与体量,共同暗示与界定了村落的领域,形成边界的场所性、多样性和层次感。主街是屯堡聚落最重要的中心性公共空间,其中场坝与主街后半部分重合,呈一个围合空间,是早期居民进行军事演练、社会交往、文化娱乐、宗教祭祀等的主要活动场地。还有一些停留性公共空间,如树下、水井旁、道路节点等利用树荫、周围构筑物的围合自行构成一小块范围,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频繁,容易停留于此进行闲适的交流。
3.2 中心性空间序列组织特征
多山、起伏的喀斯特地形地貌文化记忆与依山而建的村落宏观格局塑造了因地制宜、与地势协调发展的公共空间形态,军事管理的卫所空间组织特征与儒家正统文化记忆造就了雷屯村落半封闭式的核心性公共空间与单中心块状街巷组织。雷屯的场坝核心位置——一种标志性的、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和在重要民俗庆典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公共空间类型[8]——以中心放大空间向周围有序发散,有且只有一个中心圈。单中心性场坝公共空间是雷屯空间序列的始发点,使村落在整体上或者局部呈现出了一种内聚的形式,是雷屯的公共生活的汇聚点和精神凝聚的核心,让人们通过场坝空间来把握雷屯的布局、结构与秩序。雷屯场坝处于主街北向末端,空间宽敞与主街重叠,主要道路通向寨门,以辐射的方式与支巷垂直相连,街巷以及建筑肌理密致均匀有序化排列分成一块一块状,强调上下级主次秩序的维护,这是军事驻军屯的显著特点之一。中心重要性公共建筑布置宽敞,巷道内民居建筑布置紧凑密集,有条不紊,军事化安驻营既是征战时的大本营,又是防御组织的战营(图2)。
3.3 防御式街巷空间形态特征
“征南平边”的军事防御记忆使得雷屯从建屯初始就以确保防御的需求来进行整体规划与构建的,巧妙地利用当地复杂的喀斯特地形,通过街巷组织的联合性以及封闭性,利用主次街巷形式设防、巷道交叉节点设防、尺度造成的精神设防。雷屯由入口进入主街直通场坝空间,地形平坦开阔,在主街上中下设有3座古箭门楼,门楼上设有瞭望台,可观每个角落动向,户户相连巷巷相通,首尾相顾视线一览无余,侵入者无处可藏,突然的行踪暴露也给与了一定的精神压力。主街与场坝连接各个支巷,与宽阔的主街大尺度有所不同,雷屯支巷面宽通常最多两人并行,两边建筑高约2-4米不等,是急剧收窄的狭隘小尺度空间,两边建筑不开窗或开高窗,窗洞很小,墙面隐蔽处布置有枪眼,压抑的尺度给人一种警惕、危险的心理信号,人们往往不会在这里长时间逗留。支巷中还分布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防御式交叉节点,其中还有大量的节点空地,形成瓮城,给人以迷惑性,大多最终为尽端路或者通向后山的逃生路。内部道路如同迷宫纵横交错蜿蜒曲绕,节节相扣,又能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严谨的易守难攻的战略防御建筑体系。
3.4 轴线式公共构筑物布局特征
在“江南祖地”的儒家礼制记忆与军事管理的卫所空间组织特征双重影响下,相较于大部分南方其他村落自由曲折的街巷布局,具有规整对称的轴线式街巷布局与是雷屯的典型特征,团状是喀斯特传统乡村最主要的形态[9]。雷屯的主街布置在全村中心的主要中轴线上,主街末端通向永丰寺,长约100米,上宽约13米,下宽约7米。良好的尺度保证了居民能容纳全村村民举行大规模的公共娱乐活动,宽阔的视野给人热闹,愉快的场所感受,人们愿意长时间逗留,聚集人气。主街的长度又能保证村民井然有序的进行祭祀仪式类活动,宽阔延长的场所空间能给人庄严、肃静的场所感受。与两侧各支巷垂直相连且道路等级明确且构成尺度差异明确、层次分明的主次街巷体系,主街比较宽、次街道比较窄,整体街巷形态结构清晰有序,巷道串联村内各个院落。街巷布局各种主要建筑如永丰寺和戏台沿主街布置坐落在主轴线上,坐北朝南,并紧邻场坝。反映出雷屯军事卫所式的结构严整、主次分明、层层围护,进一步强化烘托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度与等级观念。永丰寺一寺之内同时供奉三教神像,前殿供关羽,二进院落中的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二殿正殿供如来与观音,后殿内供玉皇大帝,是一个释道儒三教合一集功能及意义的复合性综合体典型庙宇,其空间意义是多层次多功能的,反映了雷屯村民祭祀对象的适用性和混杂性特征(图3)。
3.5 空间尺度收放自如的喀斯特地形适应特征
雷屯的公共空间形态为适应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而变化,而军屯的属性又决定了雷屯空间尺度的收放不仅具备了交通性能,还有防御和活动的多功能属性。结合这些功能需求,首先,会选择合适的开阔地形建立场坝空间,并连接主街,其次再布置合理的街巷系统。空间的收与放主要体现在主街与支巷的形态上。由雷屯屯门进入呈一个“收”的空间,南北走向的主街近二分之一三岔路口处局部放大,宽度近扩大一倍 ,是雷屯最重要的场所之一,是“放”的空间,为居民民俗活动所用,受外围建筑层层包裹的状态下,具有聚集人气和安全意识的作用。支巷空间收与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适应山地空间的高差变化,以及防御性功能。另外,与主街的功能一样,每一个支巷的入口和岔道都是防御的重点,因而均为收的空间。有些支巷在顺应地形的情况下,在岔路的局部布置中加一个“放”的空间,形成瓮城防守进攻,也用于迷惑闯入的敌人。总而言之,在地形狭窄处收,地形宽阔处放,在高差错落的地面收,地形平坦宽阔的地面放,在转角的地面收,直行的地面放,在有军事防御的节点收,有民俗活动的场所放等(图4)。
4 结语
文化记忆不是静止的,在不同时空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可能面临入侵与遗失,一方面这些文化记忆影响了屯堡居民对公共空间的构建,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又反向地强化了他们对文化记忆的理解,在“城市化”进程大背景之下,新农村建设的脚步加快,越来越多的村庄受其模式化影响,丧失其自身文化记忆,最终显现出“千村一面”的情况。而公共空间是一个村庄乡村风貌、地域特色的外在体现,也是传承村庄文化记忆、延续人们乡愁记忆,找寻身份认同的内在部分。研究一个地域的文化记忆对公共空间形态构建的影响对我国新农村公共空间的营造与设计是十分必要的。村落居民与环境之间的联系的确立,安全感的产生,对村落内涵体验的深度和强度,对场所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新农村建设富有个人标签,均是通过文化记忆的营造实现的。
——以福建省儿童医院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