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黄、山趣与盛宴
青 黄
在村子没粮的日子里,一从床上爬起来,就听大人说:“又快没米下锅了,晚饭米又得找村里人借去。”这句话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我们一家人的心里,弄得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使得一家人小心翼翼,生怕掉了一粒饭。如果吃饭时掉了一粒饭,父亲就会一耳光扇来。哭声加上父亲母亲的叹息声,连同早上的阳光也变得如同黑夜一样阴沉。
夜晚来临后,无米下锅的母亲就坐在火堆旁等着父亲借米回来下锅。我们三姐妹也坐在火堆旁等着,等得肚子叫爹叫娘,还不见父亲回来,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映红了母亲流汗的脸。姐姐不断地叼唠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妹妹也开始叫饿了。外面一片黑暗,只有火塘里的火在不断地闪。还有鼎中的水,在火的烧烤下,不断发出哭泣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的肚子饿了,又感到困,困得连睡觉的力气也没有。正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母亲在没力气打哈欠的时候,才听到门“哐”的一声响,父亲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高举的一个火把下,他背上用一根棍子挑了一袋东西,他把火把扔到地上,把肩上的袋子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如同放下一个脆弱的生命,接着他朝母亲大声叫道:“做饭!”母亲站起来,我们的姊妹,全都站了起来,去看那一小袋东西,父亲一屁股坐下来擦着脸上的汗说:“这是我跑了全村,一家一家地借,最后才在我一个干亲爹那儿借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有这么一个干爹,住在离我村一个很远的村子里,是一个黑得如铁的老头。
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母亲淘米,姐姐帮忙举着火把。把米淘好后,把饭煮上,我添柴烧火,母亲又开始切菜,姐姐一边举着火,一边抹汗。
一会儿饭米水开始泛出来了,我赶快打开饭鼎盖,生怕饭米水泛了出来。父母亲说过,饭米水是最有营养的。
饭熟了,又开始炒菜。刚架上锅,母亲放了油,父亲又认为油放多了,又舀了些油放回油壶里,嘴里骂道:“真是败家子,这家就是你这样粗吃大用败光的。”母亲没有争辩什么,沉默如一块木头,炒着菜。妹妹被父亲那个凶样吓得哇哇大哭。姐姐把只有三岁的小妹妹抱着说:“不哭了,不哭了,呆会儿就有饭吃了。”妹妹真的不哭了。
菜做好后,父亲一手举着火把,一手用筷子吃着饭。我端着碗,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吃着,生怕掉了一粒饭,招来父亲沉重的耳光。
吃后,还想吃的我,见饭鼎已像舔过一样那样干净了,我只有失望地放下碗,就听见村里的鸡在打鸣了。
姐姐领着我和妹妹在一张床上七仰八叉地睡了过去。醒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姐姐与妹妹还在沉沉的打呼。只听见父亲在说:“还熬几天,还熬几天,就收稻子了,家里人就不再挨饿了。”
可是过了几天,还不见收稻子,村里成群的青壮年挑着箩筐开始四处借粮去了。村里只剩下我们这些孩子与老太婆们。我们三姊妹只有饿着肚子,坐在家门口盼着父母亲回来。日子长得不可救药,我们朝村外那条路望着,望着。越望天越黑,直望到星星出来,狗在不停地叫。狗叫得再也不想叫了,才见通向村外的那条路上有了一点火光。一见那火光,村里的老太婆全从家里举着火把出来,孩子们跟在她们后面。我也跟在她们后面,站在村口。可那火光还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一闪一闪的。直到老太婆手上的火把燃尽,腿都站得酸了,还没见那火光闪到眼前来。
我依着姐姐,不知不觉睡了过去。我被姐姐叫醒的时候,只见母亲举着火把,父亲挑着一担粮食满面流汗,满脸笑容地朝我们走来。父亲对姐姐吼着嗓子说:“快去生火。”姐姐领着我们进了厨房那屋,母亲也举着火把跟了进来。姐姐问母亲:“借到粮了。”父亲说:“借到了,应该能熬到秋收了。”
火马上生了起来,一家人围着火,眼盯着火上的饭鼎,全在期待着它发出欢快的开水声,可饭鼎里的水只是发出嘤嘤的歌唱。我不知这支歌唱了多久,饭鼎里才发出哗哗的鼓掌声……
山 趣
叫“反季嚷”的知了叫开的时候,池塘边的木瓜树上爬满了叫“凤凰”的甲壳虫。它们笨笨的,有时在田埂的蜡树上吃树浆。用手去抓它们时,它们为了贪食也不知道飞。它们的颜色很多,在阳光下五光十色的。有花的,一般是甲壳有呈绿黄色的,有呈金黄色的,也有呈黑红色的。对于我们它们身上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秘感。木瓜树与蜡树就是它们的家。只要去这两种树上一定能找到它们。它们飞起来时发出“嗡嗡”的叫声,在孩子们听来是最美的音乐。孩子们一般抓它们回去,用线绑住它们的一只大腿,然后让它们飞;它们飞的时候,知道有线系住了,它们就会围着我们的头转着圈儿飞。我们如同拥有了百万财富那样幸福。玩着它们,有时忘了摘木瓜树上的木瓜。大人们有时把木瓜摘下切成片,晒干,当菜吃。那木瓜给我的口感,就是一个又酸又涩的味道。
玩腻了“凤凰”,我们就玩大人说的“炮筒”。“炮筒”就是细竹的一节,用一头有节的一段,然后把有节的那头,用刀或小锯子切成半寸长的样子,另一头没节的一般有四五寸的样子。把有节的半寸长的那段叫做“炮筒帽”,在“炮筒帽”里对一根与“炮筒眼”一样大小的由竹筷子削成的又圆又直的竹棍子,竹棍子的长度只比“炮筒”本身短1厘米的样子。竹棍子的大小能在“炮筒眼”里自由推送就好。而“炮筒子”一般由樟木子、“飛花柴子”或浸了水的纸充当即可。开始由戴了“炮筒帽”的“炮筒棍”把一粒“炮筒子”从“炮筒口”送到“炮筒尾”,再从“炮筒口”塞一粒“炮筒子”进去,我们用力用“炮筒棍”一推“炮筒子”,另一粒“炮筒尾”的“炮筒子”就“叭”的一声飞出老远。如果在有限的射程内,能打伤一只小鸟。
我们玩“炮筒子”每年直玩到夏秋季过去,就玩弹弓,弹弓只要找一个“茶树”的树丫,在树丫成“丫”形的两根木的尖端用铁丝或铜线固定有弹性的橡皮条,再在这橡皮条中间固定一块包石子或其它子的弹子的皮,就可以玩啦。我们一般用弹弓来发石子出去往水上“打飘”。有时我们直接用石子在鱼塘上打大人说的“水飘”。有些大人见我们在“打水飘”,就喊:“使劲扔啊,不错,不错,你们能干。”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的热情老被大人们唤起。有一次打伤了一条鱼,鱼浮上了水面,大人们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跑来先把我按在他腿上打得我大哭为止,然后才解气地把鱼捞回家放木桶里养着,那晚叫母亲煮给我们吃了。那味道就是大人们说的“恬静”。在那年年底,我们村里放塘分鱼的时候,我家里少分了一条。
秋收忙完后,晒完稻谷,就开始晒茶子。茶子,不是喝茶的茶叶树结的那种茶子,而是用来榨油的。那树呈黄色,春季里开白色的茶花。那白色的茶花一开,好日子就来了。我们用一种空心草的草棍子,大清早就爬到茶树上去跟采蜜的蜜蜂们争抢茶花心的“糖浆”。把那茶花心的“糖浆”吸进嘴里。茶树开完茶花被我们吸完“糖浆”后,又结大人们说的“茶泡”。“茶泡”没脱皮前是红色的,脱皮后就是白色的了,吃起来又涩又甜。更有好吃的是茶树春天开出的嫩树禾叶子能变成大人们说的“茶板”,“茶板”也相当于“茶泡”,只是呈叶形,不脱皮时也是红色的,脱皮后就是白色的,朝天空的一面是红色的,吃起来味道与“茶泡”一样。贪食的我们总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片一片的茶树林里找这些好吃的东西。可惜如今一片又一片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茶树林被毁成一块一块板栗林与竹林或杉木林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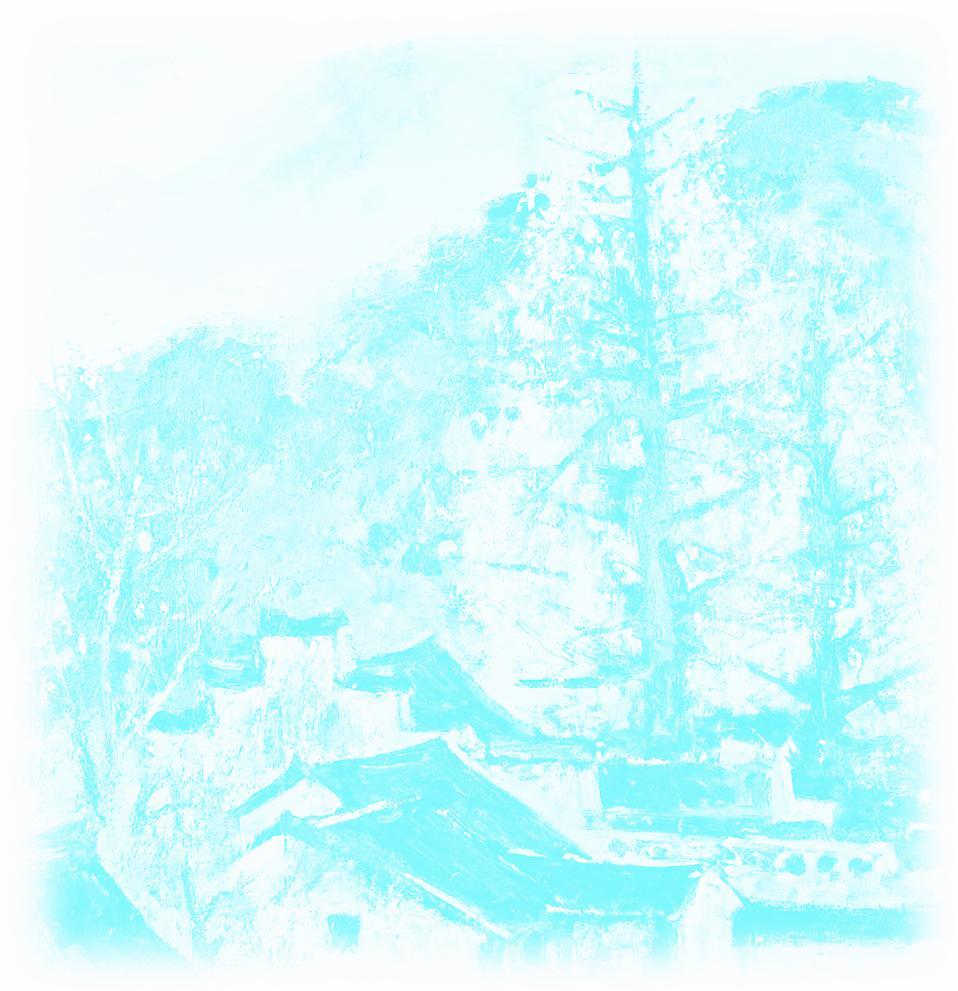
茶树结完“茶泡”到初秋就结满了能榨油的茶子,茶子的皮被晒裂后,只见又硬又厚的茶子壳内,里面的茶籽一般有圆的,有半圆的。几个太阳晒下来,在大人说的“烂垫扇”的竹晒席上,大人们用一块大人说的圆木橔板,在橔板上用小锤敲掉“茶籽壳”,弄出茶籽,再用竹筛子或簸箕分开茶籽壳与茶籽后,用石磨将茶籽磨成粉装进木桶里,大人们就带着我们去一个叫牛古田的纸厂榨油。
榨油前先将“油籽粉”放在一个大人叫的“木蒸”里。“木蒸”就是一个木制的圆桶,离桶底半尺上有镰刀月形孔的圆隔板,隔板上放些能透热气的稻草或棕树衣,再把“油籽粉”放在上面,盖好,再把它放进一口架在土与石子或土砖砌的火灶上放了水的大敞口的铁锅里,盖上盖子,直到铁锅里的水不断开不断缩水,大人们不断添水,待闻到飘出的香味,“油籽粉”就算熟了。再用一个一头用绳子扎死的一把稻草,置在一个事先备好的篾箍上,把“油籽粉”倒进这把稻草心,“油籽粉”加满一个篾箍,再加一个篾箍,最多加到两个篾箍,再将“油籽粉”夯紧,稻草开口这一头扎死后,置在一个圆形的大木桩上一个凸出的大小与扎“油籽粉”篾箍相等的小圆木桩上。小圆木桩下有一圆槽线,圆槽线朝置油桶的前方通了一节空心小竹棍。把用稻草与篾箍箍紧的“油籽粉”放在小圆木桩上后,再在小圆木桩的“油籽粉”上放一个与大圆木桩相等的短筒子圆木,木筒子上置一根大压木,压木两头套两根嫩竹皮浸水发黑后编织的又大又粗的竹皮绳子。竹皮绳子缠在一个两端固定在两根大木柱子之间钻有四个方向不同分别能放进一根大粗圆木大孔的“滚木”上,几个大人们分别把大木头捅进“滚木”的大孔,一使劲,套在大压木上的竹皮绳子就会不断缩短,压木压圆筒木,圆筒木压篾箍与稻草内的“油籽粉”,发亮的油就哗哗地被挤出,从小圆木桩上流到底下大圆木桩的圆槽子里,再沿着那根通向油桶的竹管流出来,在大人们的“嘿嘿”的踩木声里与竹皮绳子发出的“嘎嘎”声中,油哗哗地流了出来。顿时整个纸厂内充满了茶油香。待油流尽了,再松开滚木,竹皮绳也自然松了。移去压木与木筒子,取下篾箍与稻草包的“油籽粉”,去掉篾箍后,里面的“油籽粉”成了一块呈棕黑色的大人叫的“油壳饼”了。这“油壳饼”一到阳光天,可以用刀剁碎,对上开水,洒到田里,可以“药”到整块水田里的泥鳅与大人们嘴里说的“黄鳝”。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油壳饼”水一泼到水田里,那些泥鳅就会自己从泥里出来“找死”。一吸了这香香的“油壳水”,一下就“翻白”了,大人们又有好的下酒菜了。
榨完油,无事的大人们,把夏日里用石灰“咬”在“料塘里”的,曾经在竹笋刚长到与老竹一样高没发叶的嫩竹砍倒,用削刀削去竹皮,浸在这石灰水塘里,几个月后快烂得不行了的造纸浆原料才被大人们一担一担挑到纸厂,放纸厂外的石槽里用脚踩烂如泥了,再放到一个木制的四方大水槽里,水槽里再放些用樟木熬制的大人们叫“滑”的成丝的汁液,跟纸浆一搅,再用“造纸”用时大人叫的“粘子”,也就是一张草纸大小的簾子,朝水里一挽后,将沾满了一层薄薄纸浆的簾子翻过来往一个垫有一张黄草纸上的木板上一贴,再揭去簾子,那层薄薄的纸浆就不见了。大人们嘴里的“操纸佬”就是这样用簾子挽一张,贴一张,挽一阵,贴一阵,再把槽子里放了纸浆与“滑”的水搅一阵,一叠又厚又流水的纸就堆在那了。待那水流干后,在上面加块簾子,加块木板,木板上再压块大小相同的木板或两块起平衡作用的木条压条压干水后,再用一个竹做分纸的夹子,把纸一张一张的“体”开,往“烘纸炉”的“焙”上一贴,用棕刷子刷平展了,直到纸在“焙”上自行干脱。
而这个“焙”就是造在一个大屋内倒过来的“V”形状,两边先是用竹片制成架,上安一横木梁,然后在上面涂踩熟的无一粒石子和了石灰与纸浆的黄泥,涂平后,再在表面涂上一层桐油,让对风的一头开口烧火,另一头封死,只留开一个朝天的烟囱冒烟,这样呈倒“V”形的两边就很热了,把“水纸”一贴上,不一會儿就成了干纸,就成了我们村里人用毛笔写字的黄草纸,与打纸钱祭祖宗送神的草纸。通常分为一刀一刀的。一刀大的有100张,小的一刀有30张50张60张的。“操纸”的过程最难的技术就是熬“滑”。
纸“操”好后,多余的就由大人们挑去,一担一担地挑去村外挨家挨户地叫卖到卖完为止。
盛 宴
三月花满山开了,我们摘三月花吃的时候,才想起山外人把它叫映山红。我们到山林里去砍柴,觉得饿的时候,就随便摘几朵花塞进嘴里,让它的味道酸到我们的心里去。
去山里砍柴的除了小孩还有大人,都喜欢成群结队的。有了我们这一群,三月花与山里的柴就遭殃了。我们砍的柴一般有叫“杨果柴”的、“粑粑柴”的、“白柆嵇”的这几种。捆柴禾的树叫“条子”,“条子”在夏秋日结出“红色小圆粒”的果实,我们叫“条子仔”。有的甜,有的涩苦,吃到嘴里,舌头与舌角都会发红。当然也有“毛栗禾”柴,也是我们小孩爱砍的。另外就是爬到又高又大的杉树与松树上去剁它们的枝当柴,我们叫“杉树杠”“松树杠”。

小孩大人一到山里砍柴,就会听见从这个山头上飘出山歌,那个山坡上的人就会回应。有时跟我们去砍柴的婆娘,唱着唱着就不见了。一下子那边山头上的歌声也歇了,通常一个时辰后,才见那婆娘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地回来。接着这个山坡与那个山坡上的歌声又会响起。一般是唱有关风流的歌。什么“郎想妹啊,妹想郎,两人想得脸发黄”之类的,或是什么“这个坡来那个坡,想亲妹妹脸窝窝”这些山外认为有伤风化的东西,在我们这村子里自然不过了。就连我们小孩也会唱两句:“岩山高岩山低,岩山底下好脱衣。”有时无聊,我们会对着那些对面山上砍柴的骚婆娘喊道:“来脱衣哎!”她们一听我们是小孩,开始会哈哈笑一阵,便大声问道:“什么时候来脱哎!”我们就喊道:“现在就来脱吧!”她们就大笑一阵。我们接着就笑成一堆。就听到对面没反应了。我们小孩子就开始自己说村里哪家的媳妇脸蛋蛋俊,哪家的婆娘屁股翘翘的。正瞎说着,只见一群婆娘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把我们一个个逮住搂在怀里,夹在他们两腿之间,撕的被撕嘴巴,捏的被捏脸,脱的被脱裤子。婆娘在对我们干这些时,一边嘴里骂:“我叫你们嘴里窝屎窝尿。”“我叫你们不学好。”她们把我们欢乐地胡整了一顿,然后看着我们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在四处寻找被她们扔远的裤子,有的在揉被撕痛的嘴角与捏痛捏红的脸,或揉被恶毒婆娘们咬出的牙印。有大胆的小孩,见她们望着我们恶毒地笑,就说道:“我长大后,我要一个个把你们在这山里脱光……”她们就说道:“怎么了,脱光了想把我们怎么了,说呀,有种的今天就来,我躺在这里,你敢吗?”有几个真的躺在地上,用手挑逗我们说:“来呀来呀……”总之是山外人认为不堪入耳的话,我们这里就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会被她们吓得背着柴禾就往村子里跑,她们在后面就会哈哈大笑。还唱歌为我们送行。一般唱的是什么“细细竹子不开花,细细伢子没办法,鲜花虽开山野里,好色伢子不摘花。”
我们一回到村子里,大人们见我们的样子就忍不住笑。知道我们被婆娘们调戏了。我们跟一些和蔼的大人们诉苦,他们只说:“男子汉都会经过这一天,等你们长大了再去调戏她们。”大人们这样一说,那些恶婆娘们回村子里与人笑谈我们几天之后,又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天气一热,大人们就开始用锄头锄去田埂傍水的那一边再用“脚耙”拖上细泥抚上,我们这里的大人叫“耙田基”。所以我们这里的田埂我们都叫“田基”。
夏季与秋收后,大人们一有空就开始上山采我们那叫“柆嵇柴”树上的“柆子”,有的地方叫槠子,通称栗子。“柆子”一般是椭圆形的,与树连接的一端生有一个朝天张的像刚盛着“柆子”的圆盘子,我们叫“柆子帽”。而“柆子”在夏天呈青色,朝天一端生有一根针一样小2毫米左右长的尖刺。如果我们去掉“柆子帽”,就会看见正中有一个能越过外壳插棍子的小孔,我们通常喜欢从这能插棍子的小孔插上棍子后,放在平坦的地上或石板上用两个手指捏着一旋,“柆子”就会在石板或地上旋转如飞。我们小孩子们常聚在一起,互相旋着自己的“柆子”比一比谁的“柆子”旋转得最久。而大人们背着白麻布缝成的袋子在不停地摘或在地上捡。“柆子”到秋天就由夏天的青绿色呈青黄色了。大人摘回“柆子”后,再放在竹篾织成的“晒席”上晒,再用石磨磨碎,将磨碎的“柆子”粉装进白布麻袋,放在一个装有水的圆形木制的“大黄桶”里不停揉挤一阵,再放在搭在“大黄桶”口上用几根细篾丝连成的几块青竹片的“蔑搭上”挤干水,再用木盖子把“大黄桶”盖上,待过一夜黄桶里的水清了以后,只见黄桶底沉了厚厚的一层粉,大人把黄桶底上面的水用黄桶底上离粉的面高半厘米开的孔放掉,剩下的就是还含水的“柆子”细粉,把这些含水的“柆子”细粉再放一口大锅里一煮,就成了一块又厚又大的呈棕白色的“豆腐”了。我们这叫“柆子豆腐”。细心的大人们再用刀子分成一方块一方块,吃时,取一方块切成一片一片的,放上油盐剁辣椒新姜大蒜,就成了一道我们渴望的美食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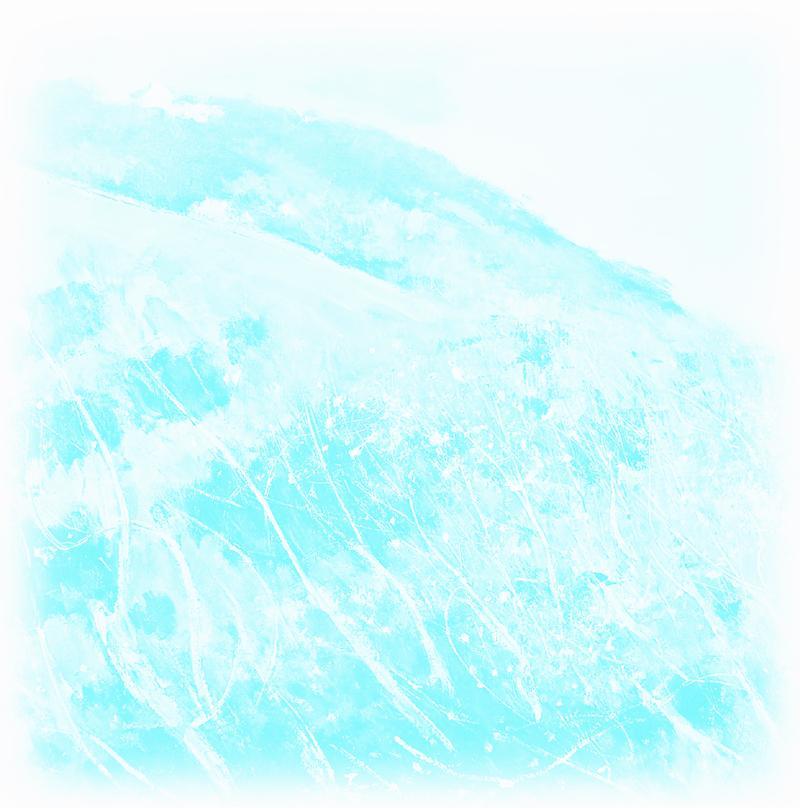
做了“柆子”豆腐的大人们,吃了这个还不过瘾似的,就成群结队去山里挖蕨根,挖蕨根要找有黄土的地方挖,在黄土里长的蕨根才出“蕨粑”。我们这叫“打蕨粑”。大人们把成捆的蕨根挑回来后,就在一个只有一个“对”竹管的孔出水的石槽里把“蕨根”用一个“对”着两片厚竹片柄的长有一米的木筒棰子将蕨根棰烂,或直接用两米长打糍粑用的大木筒子我们叫“粑粑棰”的木棰子扎烂,扎烂后再用一竹管或竹简引清水进石槽冲洗蕨根。冲洗蕨根的浊水再沿着一根通向连接大黄桶的一个口子的竹管进入“黄桶”,待冲洗的蕨根渣再也冲洗不出浊水后,就撤去引水进石槽的竹简,也撤去进那连接石槽与“大黄桶”的竹管,盖上黄桶盖子。一夜之后,取掉离黄桶底半寸以上的塞子,放出清水,黃桶底剩下的就是约两毫米水下的白蕨粉。把白蕨粉取出,装在放了白纱布的簸箕里,放在太阳下晒干,就会干成板状结构,想吃时取一块,放进放了油盐的锅里一“焺”,白色的粉末马上变成了乌亮色,蕨粑就做成了。大人们通常用春天捡回枯了的笋衣包好,就可当去深山里劳动的午餐食用了。那种又糯又沾口软绵的味道,至今也如一股乡土的味道,久久在我的记忆深山里萦绕。
村里人除了拿蕨粑当午餐,也拿糍粑当午餐。一到过年前打糍粑,先将糯米用水浸上几天,再将装满了糯米,在有镰月形孔的底端上放有透水汽的白纱布或棕衣的木“蒸”放在灶上一口放了水的锅里,再生火烧热锅里的水,这样将糯米蒸熟。把蒸熟的糯米放入一根大木挖了个椭圆形槽子的槽子里,我们大人叫“粑粑框”的东西里。“粑粑框”两端呈U形,如对着两边的叉子。打“粑粑”的大人各站在“粑粑框”的两端,脚踩着U形着地的一边,手持“圆珠木”做的两头呈大圆形状,中间从两头逐渐缩小便于手握的呈小圆形状的又重又大的木筒子,我们这里叫“粑粑棰”的东西。两个大人你朝槽里的“糯饭”夯一下,我夯一下,你捣一下,我捣一下,你打一下,我打一下,一般是两个大人都互相交叉捣打,先捣打槽子两头的“糯饭”,再捣打中间的,直“捣打”到“糯饭”成了能拉成又细又长的白条条了,就算把“糯饭”打成“粑粑”了。再用一个木盆装满温清水来,用竹饭瓢沾水刮尽沾在“粑粑棰”上的“粑粑”,大人们再用两手涂满热油与事先在水里煮熟的鸡蛋黄以便防粘。就在槽子里取一坨“粑粑”,再放在已撒满白米粉的簸箕里,用拇指与食指夹一小坨“粑粑”,一个又圆又白的“粑粑”小圆坨坨就从大人的拇指食指缝里生蛋似地掉出来,一个个“叭叭”地落到白粉上。我们小孩子就滚动这些从大人指缝里下的“蛋粑粑”,直到它们全粘上了白米粉,再把它们一个个成排摆在一块木板上,摆满了一块木板,再在粑粑上面压一块木板,又在这块木板上摆粑粑,就这样一层一层摆上去,摆到极限了,再放又大又重的压木,压一夜,第二天早晨粑粑蛋全成了又硬又圆又扁的好看的“糍粑”了。我们把它们从木板上一层层取下,放到“塔子里”盖上盖子,为防漏气,再在“塔子盖”沿加上水,就这样封存到忙月,再开“塔子盖”,大人把“粑粑”带在身上口袋里,在山里劳动饿了,再生一堆火,把粑粑放在火烧过后的火子上,待一个扁扁平平的粑粑长出了白白的奶头香气飘飘时,就可以张口大吃了。
【作者简介】唐国明,男,汉族,现居长沙,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