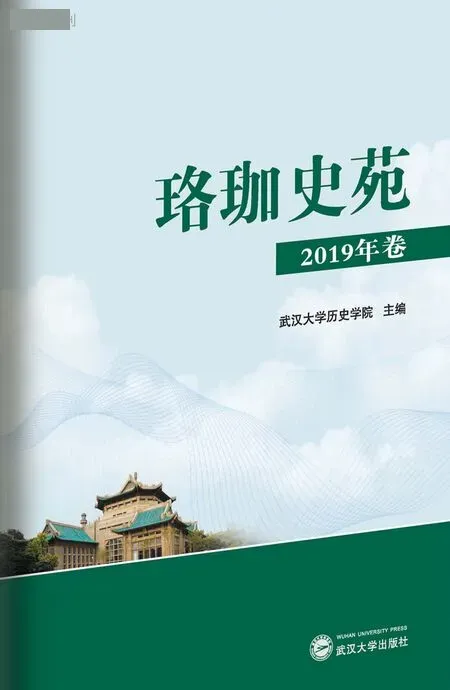裴炎之死与嗣圣年间的政局研究
达 锬
公元684年①684年,中宗年号为“嗣圣”,睿宗即位后为“文明”,10月又改 “光宅”。本文取“嗣圣”年号代称。,在不同政治势力互相勾连、对抗下,唐朝发生了中宗退位、裴炎被杀等非正常的权力更迭事件。作为高宗末期重臣,裴炎被杀是高宗死后政局中各类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诛杀裴炎时,徐敬业在扬州发动兵变。对于两件事的联系,前人虽有论述,但没有纳入嗣圣年间政局进行深入探讨,许多认识并不清晰。笔者以整体性、全局性视角,围绕裴炎之死,试图从史料中找到嗣圣年间政局的发展变化,加深对嗣圣年间政局的理解。
一、联裴反武?——扬州兵变发动起因再研究
«资治通鉴»载,及李敬业举兵……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太后问计于炎,对曰:“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监察御史蓝田崔詧闻之,上言:“炎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太后命左肃政大夫金城骞味道、侍御史栎阳鱼承晔鞫之,收炎下狱。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5页。
«新唐书»«旧唐书»记载皆同。武后对诛杀裴炎的解释是,裴炎在扬州兵变期间意图谋反。前代学者认为:徐敬业是山东大族反抗武氏的代表,兵变本质上是大族对武氏打压的不满和反抗。宰相裴炎支持甚至暗中煽动了兵变。②张先昌:«试论徐敬业起兵的性质»,«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第38~41页。这种论断默认裴炎涉及兵变之说。但在武后公布裴炎罪名时,重臣胡元范、刘齐贤公开反对此说法。如果裴炎真的参加谋反,朝臣不可能替他求情。史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裴炎谋反的具体过程,种种细节似暗示此说存疑。裴炎是否涉及兵变,还需要深入探讨。
兵变平定后,朝野之间出现了一种舆论,描述裴炎与兵变联系的种种细节,«朝野佥载»记载:
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女妓骏马,亦不语。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歘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杨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惟有青鹅人阙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③张鷟:«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页。
«朝野佥载»的记载极为可疑:裴炎当时位极人臣,地位极高;徐敬业出生名门,但祖父徐世勣已逝世多年,家族远离政坛中心多年。敬业本人被贬前也仅是眉州刺史,二人地位悬殊已大,更何况徐敬业特使骆宾王贬官前仅为长安主簿,如何进行如此亲密的对话。徐敬业到扬州是七月,贬谪应在五月以前。如果裴徐关系亲密,以裴炎的地位,徐敬业断不会贬谪柳州,眉州刺史之职也不至陷于中央政争中。«资治通鉴»没有直接收录这条史料,而是放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可见史家态度。
裴炎的态度,除了野史笔记记录以外,比较明确的是这条:“徐敬业兵兴,后议讨之,炎曰:‘天子年长矣,不豫政,故竖子有辞。今若复子明辟,贼不讨而解。’”①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248页。从中可见,裴炎确实没有积极讨伐之意,而是劝说武后归政睿宗。归政的问题容后文讨论,这里先解释裴炎为什么采取消极态度。据«资治通鉴»,兵变范围只限淮扬镇,维持了40余天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7页。,算上朝廷部署动员,实际平叛不超过一个月(算上李孝逸观望的时间)。再结合这三地的人口,扬州兵变的规模和人数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大,实质是区域性的武装暴动。更何况与裴炎商讨时,润州还未攻下。由于兵变的实际影响有限,裴炎的不以为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们也可以假设,如果裴炎真的组织发动兵变,规模应不止于此。徐敬业到达扬州是在7月,裴炎下狱是在9月。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居然没有裴炎策划、参与政变活动的记载,这也难以解释。
山东大族支持兵变则更站不住脚。兵变中,徐敬业始终坚持“反武拥李”。李武在打压大族的政策是延续的,拥李对于山东大族没有煽动性。在整个兵变中,除扬州本地和楚州司马李崇元外,并无其他势力的呼应支持。尤其是徐敬业叔父李思文亦反对起兵,说明徐氏内部对起兵之事尚存分歧,何况其他大族。考虑到与李贤过从甚密的苏州刺史曹王李明在此地盘踞多年,长孙无忌的余党也多曾在扬州任官。徐联络的应该是保留在江南地区的李唐宗室和反武势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徐开始打出李显的旗号,之后又打出李贤的旗号。根本上是为了煽动更多的江南地区支持李氏的势力。需要强调的是,徐敬业不是没有考虑借助山东大族的关系;徐置兵楚州,就是出于号召全国反武的想法。只是此时武后与宗室朝臣间矛盾并未爆发,兵变无法一呼百应。李孝逸在平叛时多次犹豫,也在观望扬州以外是否出现不宁。
裴炎对扬州兵变的真实态度,可以从润州司马刘延嗣身上反映出:
延嗣与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业执延嗣,邀之令降。辞曰:延嗣世蒙国恩,当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负朝廷。终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岂以一身之故为千载之辱?今日之事,得死为幸!敬业大怒,将斩之。其党魏思温救之获免,乃囚之于江都狱。俄而,贼败,竟以裴炎近亲不得。①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79页。
有史籍载,徐敬业的亲信薛璋是裴炎外甥,不过此为孤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都难以佐证。润州司马刘延嗣在兵变后因裴炎之故,仕途有所阻碍,可见确与裴炎有亲。刘延嗣在润州时积极抵抗,被俘后激烈反对兵变,并担心“以累宗族”。这态度是真实的,构建裴炎参与兵变的解释体系时,并没有拿刘延嗣说事;刘本人在之后也没有遭遇严重的迫害,可见其反对兵变是公认的。如果裴炎真的勾结兵变,刘延嗣不应该有如此表现。综上可见,裴炎等人参与扬州兵变,应属子虚乌有。
兵变后,社会上开始制造和流传串联徐敬业的种种细节。如裴炎交好,几乎同时被杀的程务挺也有类似的传言:“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以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谮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8页。«骆宾王集»收录多篇给程的赠诗,暗示程和兵变策划者往来密切。不过程在七月已开赴突厥前线,距离扬州四千多里,无法及时有效策应。«资治通鉴»不相信程参与共谋,称之为“谮”。武则天对于骆宾王的态度也值得玩味:一方面,武则天非常重视骆宾王的才华,“素重其文,遣使求之”①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7页。,花费大力气编纂«骆宾王集»;另一方面,勾结徐敬业此时仍然是武后朝肃清重臣的重要罪名,依然在以扬州兵变为罪名追究朝臣。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是否证明武则天有意利用整理的机会制造某些历史?笔者认为:武则天在兵变后,有意制造裴炎、程务挺和扬州兵变的联系,将扬州兵变的性质由地方军事反抗性质上升为朝廷内外勾结,从而为诛杀裴炎和利用扬州兵变清除异己建立合法性。须知,直到武后登基前,都有重臣因私通扬州兵变的罪名下狱被杀,这距兵变爆发已过去六年。«骆宾王集»的相关内容与«朝野佥载»的记载,应都是这种细节的保留。因此,裴炎被杀与扬州兵变并无内在联系,裴炎被杀的原因必须结合嗣圣年间证据进行分析。
二、裴炎的权力扩张与嗣圣之变
上元之变后,李武矛盾愈发激烈。②韩昇:«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史林»2003年第6期,第40~52页。高宗晚年与尚书左丞冯元常的对话,可以反映这种紧张的政治局势:
“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5页。
需指出:冯元常的“不能用”,是高宗无法直接“抑损”武则天,并不是政治上完全没有行动。永淳后,高宗先立皇太孙,擢拔皇孙李重福,多次让太子临朝主政,重用了一批大臣加强太子权势,都是高宗加强太子权力、抑制武后的部署。高宗遗诏言:“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6页。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后的政治参与,与前面扩大中宗的权力一脉相承。高宗留下的政治设计是形成帝、辅政大臣共同挟制武后的局面。辅政大臣以裴炎为核心。裴炎曾任侍中,深受高宗信任,此时改任中书令,更是炙手可热。这一点,可从裴炎迁政事堂一事看出:
甲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以刘景先为侍中。
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徵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6页。
唐代政事堂为三省长官商议政务之地,裴炎迁政事堂提升了中书省的地位。郎洁博士考证迁政事堂应该在683年年末或684年一月,即高宗死后嗣圣政变前,并认为此举将宰相议事制变成了宰相裁决制。③郎洁:«论唐初裴炎迁政事堂»,«社科纵横»2012年第10期,第114~117页。笔者进一步引申:宰相裁决制的结果是裴炎同时把持中书门下,掌握决策执行权,从而减弱了门下省“封驳权”的制约,且尚书省刘仁轨久居长安,不参与中枢政事,无法制约裴炎。
嗣圣之变便发生在裴炎权力扩张时期,围绕的问题是宰相任命,本质是中宗和裴炎间发生了矛盾:
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与乳母子五品,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炎惧,乃与则天定策废立。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报曰:“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废中宗为卢陵王,立豫王旦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东县侯。①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43页。
高宗非常规提拔培植外戚以巩固皇权,中宗即位,便“擢后父玄贞自普州参军为豫州刺史”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9页。。此时又任其侍中,企图让岳父掌握门下省之权,可看作其对“迁政事堂”行为的反制。中宗不接受高宗的政治设计,对裴炎总揽三省之权心存顾忌,希望强化自身和门下省权力来限制裴炎的权力。这可以理解,“裴炎惧”以及在韦玄贞问题上裴炎的阻挠力度大于武则天的原因。裴炎选择先发制人,主动提出废帝,制衡武后力量发生了分裂。
分裂的后果,是裴炎与正在观望的武后建立了联盟关系。武则天政治地位在中宗即位后比较微妙。高宗在时,武后可以丈夫风疾为由秉政,高宗死后便失去政治参与的合法性,政治上有所冷落。在侍中人选的问题上,中宗先和裴炎商议,而不是知会武后。这种举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则天不能直接过问朝政;二是中宗和裴炎赞成后,武则天必须赞同。无论哪条,都是高宗“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意志的体现。对于武则天而言,只有帝相制衡的局面改变,才可以稳定朝政为由重返政坛。因此,支持政变符合武后的利益。
嗣圣之变起因是亟待掌权的中宗与权力扩张的裴炎间的矛盾,本质是裴炎和寻求复出的武则天联手合作的军事政变。政变后,权力相互制约的局面被打破。武后势力迅速扩张。此时,武后和裴炎的博弈逐渐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
三、嗣圣政变后武后和裴炎的矛盾
嗣圣之变后,睿宗是唯一合适的接班人。这在政变谋划时已现端倪。除裴炎外,中书侍郎刘祎之、将领程务挺、张虔勖参加逼宫。刘祎之曾任豫王司马,是睿宗亲信,可见裴炎谋划政变时已经拉拢了睿宗及其左右。当时武则天在世儿子还有李贤,但早为武氏废黜,裴炎参与了整肃李贤的过程,不可能让其即位。嗣圣政变后,李贤很快被丘神勣逼令自杀。郭沫若提出,此举是裴炎主使。①郭沫若:«郭沫若剧作全集•卷三•我怎样写武则天»,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笔者认为,武后也默许了这个行为。因为事后丘神勣仅遭流放并很快复职,此时裴炎已经被杀。杀李贤应该是武后和裴炎共同的希望。
政变后裴炎依然坚持高宗晚年的政策,将扶植皇权作为第一要务。对于裴炎而言,联合皇权制衡武后,强化中书省权力是其能继续发挥政治能量的最优选择。而武则天所希望的,则是改换或是颠覆现有李唐王朝的格局。武后在临朝初,谋划杀李唐宗室即可看出这一点。这种差异导致了裴炎与武后关系破裂。
据史载,二者的决裂是由于立武氏七庙。如果仔细梳理史料,双方矛盾已逐步激化。矛盾的表现在于宰相的任命和变更。睿宗即位后,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任侍中,刘祎之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属于破格提拔,按高宗武后朝例,中书侍郎初次拜相应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再升“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初次拜相便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是高宗武后朝的唯一一例。此举除表彰其功外,也为了强化睿宗势力,共同制衡武氏。武后也在宰相中培植势力,令武承嗣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但到了八月,武承嗣突然免职。此时武则天仍受裴炎掣肘,没有实现政局中的“清一色”,绝不会自废手足。武承嗣的罢相应是迫于裴炎等人压力的权宜之计。此时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武氏立七庙的争论,不过是将矛盾公开化。总之,裴炎希望睿宗发挥制衡作用,但睿宗的实力远不及其兄长,以至于即位后成为傀儡。②有史料指出,武后临朝时,睿宗退位称太子。这涉及睿宗上台前后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嗣圣政变后,睿宗的政治能量有限,至于是否退位,则是有限程度的体现,故本文暂不探讨。裴炎只能站到前台制衡武氏,这是武、裴产生矛盾的关键。
在九月,武后在扬州兵变改年号和官名,可以看出武后已经在政局中占有先机:
九月,甲寅……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1页。
武后临朝后,官制出现女性化的“凤阁”“鸾台”,在朝内外昭示武则天的权力,对裴炎必然有所刺激。对裴炎而言,恢复高宗晚年留下的政治格局,于公于私都比扬州兵变更重要。如前文所述,扬州兵变的范围和规模并不大。裴炎最关心的是武后临朝后高宗政治设计濒临破产,自然无暇顾忌此事。我们便理解裴炎忽视兵变处理,而责令武后归政的原因了。
裴炎与军队关系,以及发动政变的能力,也成为武氏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原因。按«资治通鉴»:“(弘道元年)十一月戊戌,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阿史那骨笃禄等。”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5页。程务挺出发次月高宗驾崩,但程在嗣圣政变时已回到长安城内。即程回长安应在嗣圣元年一月前后,紧接着便参与政变,命其返回的应是裴炎。裴炎下狱后,程还专门上疏力挺。二者应为政治同盟关系。«新唐书»载:“豫王虽为帝,未尝省天下事。炎谋乘太后出游龙门,以兵执之,还政天子。会久雨,太后不出而止。”③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248页。现有材料无法确认此事真实与否,但以裴、程的能力,再组织一场针对武后的政变并非不可能。这是武氏对二人斩草除根的根本原因,因此,武后不愿程留在京师。“秋七月,突厥骨咄禄、元珍寇朔州,命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拒之。”④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6页。“(九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1页。有故意不让程返京的嫌疑。或许,武后此时已经准备处理二人。“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①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147页。也为了防止意外。
武则天临朝后,裴炎成为阻碍和隐患,必须诛杀。而扬州兵变是现成的理由。于是“凤阁舍人李景谌证炎必反”。裴炎下狱被杀。
在诛杀裴炎的过程中,武则天获得被裴炎排挤的重臣支持。高宗留下的辅政大臣并非铁板一块,没有全部团结在裴炎周围,不能笼统归于一个集团和群体中。裴炎等人控制中书门下,平时专行独断,必然排挤了其他朝臣。在嗣圣政变中,许多朝臣甚至宰相没有直接参与,对裴炎的跋扈未尝没有怨言。清除裴炎时,远离政坛的大臣参与了反击,这从宰相刘仁轨的表现即可看出:
郎将姜嗣宗以使来,因语炎事,且曰:“炎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知邪?”曰:“知。”及还,表嗣宗知炎反状不告。武后怒,拉杀之。②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85页。
刘仁轨是开国元老,此时久居长安,除老迈外,也是裴炎有意排挤打压的结果。武后在嗣圣之变多次拉拢刘仁轨,不仅原谅了刘仁轨对武后临朝的指责,还派出心腹武承嗣到长安看望刘,并加封了刘仁轨爵位。刘用姜嗣宗之事向朝野坐实裴炎造反的罪名,明确表示对武后的支持,向洛阳中枢的大臣发出了政治信号。
李唐宗室对于诛杀裴炎持观望态度。«旧唐书»载:“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贵绝宗室之望。刘祎之、韦仁约并怀畏惮,唯唯无言。炎独固争,以为不可。”③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44页。前人根据以上史料,认为裴炎是李唐宗室的代言人。笔者认为,裴炎反对诛杀韩王鲁王,不能证明裴炎支持和维护李唐宗室。武则天希望联合裴炎等人清除李唐宗室,于是与裴炎等商议。作为嗣圣之变的延续。“刘祎之、韦仁约无言”,因为杀宗室只有利武氏,不利睿宗执政;但明确拒绝,等于失去与武则天的同盟,矛头便会先对准自己。此时,宗室存在一定实力,武氏无法同时清除宗室朝臣的势力。向朝臣征询诛灭韩王的行为,便是武氏顾忌二者的表现。684年,除诛杀废太子李贤外,武后基本上没有与宗室发生直接冲突,诛韩王仅是腹案,对不放心的藩王仅仅是迁徙封地。对于诸王而言,裴炎先后参与废杀章怀太子、废立中宗,绝不会与之联合。对于武、裴斗争,宗室也是隔山观虎斗。裴炎的据理力争只能两头不落好,却又无可奈何。
诛杀裴炎对政局影响深远。其一,诛杀裴炎彻底打破了高宗晚年留下的政治平衡,武则天权力的扩张除去了重要阻碍。裴炎死后,辅政大臣群龙无首,政事堂改由三省轮流秉笔,本已集中的相权分散到三省之中。没有人存在干涉和制衡武则天的政治能量。睿宗的政治影响迅速淡化,武三思、武承嗣等人先后拜相,武氏集团迅速壮大。其二,诛杀裴炎后,武则天加速了清除辅政大臣和李唐宗室的过程。这一段时间宰相名单变动迅速,武则天大肆抓捕和清除朝臣。高宗留下的辅政大臣难以善终,韩王元嘉等一批李唐宗室被整肃殆尽。
中宗上台后猜忌和打压裴炎,致使高宗晚年设计的帝相联手制衡武后的局面破产。武后和裴炎形成联盟,发动嗣圣政变,逼迫中宗下台。政变后,二人从联盟转为对立。裴炎坚持皇权为主的决策以及在军中的影响,使得武后不得不将其清除之。因此,武后利用扬州政变并借口杀死裴炎是必然中的偶然。从长远看,清除裴炎是武氏取得最高权力的必然,扬州兵变成为整肃的绝佳借口。在诛裴炎后,武后的权力得到了巩固,开始大规模清除朝臣和宗室力量,培植亲信。可以说,诛杀裴炎是武后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从此开启了女主称帝的历史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