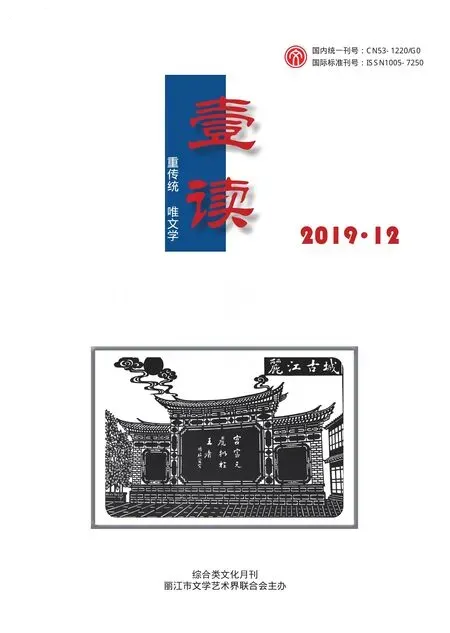斯那尼玛和藏族骑兵队
◆ 杨增适
斯那尼玛(1936-2000),汉名杨炎后,男,云南德钦县升平镇人,12岁后跟随商家马帮进藏,当马脚子。1948年3月,在丽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任地下交通员。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边纵七支队三十一团骑兵队队长,十四军直属骑兵大队大队长,先后荣获军、师战斗英雄称号。1951年3月,调北京学习后留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并任全国学联副主席。期间,多次受到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接见,曾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席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1957年回迪庆工作,任首届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76年至1982年底,先后任迪庆州民政局长、州政协副主席。1983年1月,调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当选为云南省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援藏基金会理事长。2000年1月20日病逝,享年75岁。
1999年6月,迪庆高原阳光和煦,满目春色。德钦首届弦子节如期举办。我应邀随云南电视台的朋友到现场拍摄专题片。在开幕式上,见到从昆明赶回家乡参加活动的斯那尼玛同志。他自然成为我们的“特邀嘉宾”,参与临时安排的“敬酒舞”的演出。斯那尼玛和他的家人踏着优雅的弦子舞步,唱着德钦传统的敬酒歌,为远方的客人敬上一杯醇香的青稞酒。大方热情的表演,赢得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部队文工团出身的张兴科导演感叹道:“想不到战场上纵马驰骋的老英雄,还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艺术家哩!”
可是谁能料到德钦山城的这次欢聚,竟是他和故乡亲人与朋友的匆匆诀别。斯那尼玛在电视荧屏上留下的音容笑貌,从此定格了他75年的人生经历,成了他留给世人最后的纪念。半年后,在参加省政协会议的途中心脏病突发,不幸与世长辞。每当看到当年拍下的录像,总会引起我对英雄无尽的思念。他向我们讲述藏族骑兵队走过的光辉历程时所表达出的那种对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感激和热爱之情,如今仍深深的感染着我,并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拍电视,空闲下来交谈的话题也多与电视有关。斯那尼玛讲到这样一件事:前些年有些人以骑兵队和他本人为题材写成一部电视剧,到省民委向他“征求意见”,剧中把他和他的战友写成一帮乌合之众,后来被共产党“收编”才走上革命道路。他看了剧本非常气愤,当即表示自古以来藏区地方武装多如牛毛,土司上层更是没有不拿枪的。藏族骑兵队与这些武装本质的区别在于它是一支共产党组织和带领的人民军队。他还说,最初的领导人李烈三、鲍品良、孙志和等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藏族娃子和穷苦百姓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这批积极分子后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少战功,怎么是收编来的呢?剧组人员向他解释:“电视剧是艺术作品,允许艺术加工。”斯那尼玛回答:艺术加工也不能脱离实际嘛!笔者无意于对该剧妄加评说,但编导先生们若知晓“文革”时期斯那尼玛为抵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泼在骑兵队员头上的脏水被打成重伤的往事,就不会不理解这位老革命为啥不同意他们“高于生活”的创作态度。斯那尼玛把骑兵队看得比生命都还重要,他不能容忍别人任意涂改。在云南解放战争史上,藏族骑兵队毕竟没有出现过第二支,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斯那尼玛还向我们讲过一些骑兵队的战斗故事。后来,我在查阅“边纵”的资料中,发现有关这支队伍成长的历史与他谈的情况完全一致。似乎骑兵队是为了埋葬蒋家王朝而出现的,因此它的成长史几乎全由惊险动人的战斗故事组成。有些人总会把骑兵队与旧社会的帮派组织混淆在一起,还有人甚至误认为它的前身就是中甸土司骑兵,这是十分错误的。我明白了斯那尼玛之所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他不懂文艺作品可以虚构的创作手法,实在是他对骑兵队爱得太深了,不忍心别人随意改变它的形象。联想到斯那尼玛为人处世的一贯作风,更加敬佩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
1943年,因国币贬值,人民生活困苦,民变武装四起,为了货物运输的安全,长年奔波在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永兴号“立记”老板李烈三与鹤庆“庆成”商号老板鲍品良等出资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组织了一支“保商队”随马帮出入藏区。李鲍二人一向扶人危困,与手下伙计情同手足,组成保商队后更成为藏区商界知名人士。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僵持阶段,日寇封锁了我东南沿海各大交通口岸及运输路线,滇缅公路亦被切断。一时之间,茶马古道成为大后方重要物资补给线。大批货物从印度经拉萨源源不断运到丽江,再从丽江运往内地。丽江古城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变成了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每年来往的骡马多达二三万匹,吞吐货物上千吨。
且说由滇入藏的驿路旧时多作茶马交易,故称“茶马古道”。由于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崎岖又无驿站马店,货物运输非藏族马帮莫属。藏族赶马人藏语称“腊都”,他们适应高原气候环境,善于骑射,还习惯在山野露宿。由于抗战时期商业狂潮刺激,商家大量招募藏族“腊都”,以扩充马帮。来自迪庆及周边藏区乃至青海的藏族青年,成了这条商道运输的主力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场萧条,各地商家纷纷从丽江撤走,一大批藏族赶马人丢了衣食饭碗无力返回家乡。由于民不堪虐、社会更加动乱,丽江工商界人士以“抑强扶弱、互帮互济、出入相友、困难相助”为宗旨,拉人马、搞武装,竖起四个“堂口”,即文峰社、雪山社、崇新宫、蜀康云。其中雪山社实力最为强大,入社者不再局限于工商界而遍及乡镇。如前所述,雪山社主帅李烈三、副帅鲍品良在藏区深得人心,还有被中甸人称为“阿五达”的后代孙致和在藏民中有一定号召力,因此在4 万多雪山社成员中,藏族占的比例不少,甚至在巴塘、察隅等藏族地区都有社员。但是,不能把雪山社与骑兵队划上等号。雪山社的藏族社员并非个个都参加骑兵队,骑兵队中也有不少人是后来从德钦、中甸等地自愿入伍的。例如:李阿土、甘玛白久等18 人骑是从德钦燕门赶到维西投军的。还有阿森、七林培楚等一批藏族青年,是自带武器和乘骑到鹤庆参军的。又如:丽江地下党员公曲卫曾(郭有才,西藏昌都人)奉命组建的第三支队直属骑兵队中有不少纳西族,他们从未入过任何社团。还有五人原籍四川、青海。至于雪山社,在《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史料选编》中有记载,“虽然部分上层多为权势之辈,下层却是农、工、商、学、兵、职员,名为帮会组织,行动上严格与国民党当局保持距离。”因此不应该把他与旧社会“青红帮” 完全联系在一起。
由于帮派之间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动用步枪、冲锋枪相互攻击,弄得人心惶惶,恐惧不安。李烈三感到长此下去对地方百姓不利,于1948年6、7月间,偕鲍品良等人以“经商”为名,先后到广州、香港、成都等地“找共产党寻求出路。”后来通过旧友何其昌介绍,见到云南地下党负责人,他们表示要求参加革命的决心。省委为他们接通了滇西工委的关系。经过慎重审查,1949年3月滇西工委吸收孙致和入党。同年4月李烈三、鲍品良二人亦加入党组织。
此时,人民解放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滇西北地区革命形势发展迅速。4月2日,地下党成功组织了剑川武装暴动。7月,丽江、鹤庆、剑川三县先后建立人民政权,滇西北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宣告成立,下设三个支队,计3000 余人,开展了对国民党保安团、“共革盟”等反动武装的斗争。9月,人民自卫军奉滇西工委的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南至大理、西至腾冲、龙陵的大片土地几乎都建立了人民政权。
再说1949年3月,永胜出现了以罗瑛为“司令”的“民主联盟军”数千人的反动武装,伺机进犯毗邻各县。国民党丽江县长代专员习自成下令由文峰社、雪山社、崇新宫组成三个大队,分守各路要口,以阻止罗匪窜犯。雪山社(称丽江联防二大队)负责守护关坡。为了加强兵力临时从中甸分社调来汪区批的藏兵40 余人骑。5月,罗匪上关失利后窜逃鹤庆,13日清晨洗劫鹤庆后仓皇溃退。二大队由一名姓和的中队长率领声言追击罗瑛从关坡赶往鹤庆,其中的一些士兵不听指挥做了恶行。鲍品良率领斯那尼玛、农布、马载武、汪如江等藏族警卫,从剑川回到鹤庆,土司兵的恶行才有所收敛。滇西工委指示鹤庆县工委对二大队进行整编,并纳入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建制。为遣散汪区批骑兵,孙致和从自己商号拿出资金,发给每人卡机布2 丈、砣茶1 筒、银元2 元,把他们打发回中甸。鲍品良准备着手组建自己的骑兵队,令斯那尼玛带领藏族骑兵到南区收缴了镇公所的枪支。其时,还介绍何其昌、刘汉勋一批来自中甸的仁人志士加入党组织。6月,丽江习自诚弃暗投明,丽江工委及时派干部参与联防二大队的整编工作。整编后,二大队驻防鹤庆,称“人民自卫军直属大队”,大队长李烈三(因留丽江后勤部未到职)、副大队长鲍品良,孙致和任办公室(政治部)主任。斯那尼玛等几位藏族同志被派往丽江,动员来一批藏族马娃子、帮工穷汉,与原有9 名藏族战士组成直属大队骑兵队。队长斯那尼玛、指导员李世昌(鹤庆藏族)共40余人骑——这才是藏族骑兵队的前身。骑兵队成立当天,在鹤庆中学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队员们身着整齐的藏装,在军旗下举手宣誓:“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革命、为人民、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也要同时战死!”会后,骑兵队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骑马跨枪上街游行,以肃清土匪在当地造成的恶劣影响。
7月底,骑兵队奉调剑川,后编入第一支队。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十分关心、重视这支由少数民族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他们更新装备:每人一匹战马、一支外国造马枪、一把马刀、弹药不加限制,穿上清一色的藏族服装。还作了“一般战斗不准调用骑兵队”“不准干涉骑兵念经、背佛盒的习俗”“骑兵参战前不准饮酒”“若有伤亡按藏族习俗办”等四条规定。
骑兵队转战洱源、剑川、丽江、腾冲等地,由于马队行动快捷,战士们作战勇敢,弹不虚发,打得国民党保安团鬼哭狼嚎、闻风丧胆。在战斗中6 名队员献出宝贵生命,9 名队员负过重伤。在骑兵队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今保存在剑川档案馆的《沙溪战役阵亡烈士纪念专辑》(油印本)中,记载着“骑射英雄”五金(中甸人)的事迹。在剑川甸南剑湖畔白族老人们还记得一位叫立称(即陈宏发,中甸尼西人)的骑兵战士曾在他们船上养伤,妇女们每天轮流为他送饭、洗伤口……当然,藏民族生就乐观豁达的性格,骑兵战士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正如研究党史的藏族学者张史七林所言:“骑兵队不仅有战火纷飞、追敌杀敌的斗争生活,而且有赛马、比武、唱情歌、说唱格萨尔、跳锅庄弦子的欢乐日子。”(难怪几十年后斯那尼玛仍然舞步潇洒歌声感人!)出生大中甸的副大队长柯森与白族女战士赵应珠在腾冲举办的“火线婚礼”,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8月,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组建了以李阿土为队长的骑兵队。接着,第三支队也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队。队长公曲卫曾(郭有才),指导员洛桑嘉参(钟秀生)。
为了对付藏族骑兵队,国民党“滇西剿匪司令部”总指挥官、新编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慌忙电告卢汉,要求组织骑兵“对付古宗马队”,还指令汪学鼎搜罗一支门户兵到游击区参战(汪手下也有骑兵),但余建勋施展的伎俩却无济于事,蒋家王朝如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汪匪被打得狼狈撤退,余建勋后来也成了反动势力的殉葬品。
9月,人民自卫军改编为“边纵”第七支队,下属三个团部保留了骑兵队的连级编制。据统计,他们先后参战39 次,足迹遍布滇西广大游击区,远至四川盐边、盐源等地。
1950年1月,三支骑兵队在保山汇合,编为“边纵”七支队骑兵大队。大队长斯那尼玛,副大队长柯森、李阿土,参谋长公曲卫曾,教导员洛桑嘉参。同年4月18日,骑兵大队改编为十四军骑兵大队,集中大理整训,在十四军和四十一师英模大会上,斯那尼玛、柯森、农布、李阿土、甘玛白久等5人分别荣获“人民铁骑”锻带和“战斗英雄”称号,木林被评为十四军“战斗英雄”,苗五斤被评为十四军“特级爱民模范”。
云南解放后,骑兵队部分指战员随军进藏,有的转业地方工作。那些复员回乡的队员安贫乐道,从不向党伸手要钱要官,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本色。对于不足三年的队伍,有关资料有如下评价:
“滇西北人民特别拥戴藏族骑兵队,大部分藏族骑兵虽然不懂汉、白、纳西语言,生活习惯又不相同,丢下父母和兄弟姐妹,远离家乡作战,但他们直爽、豪放、勇敢、斗争坚决、讲究纪律、爱护人民,战斗间隙就帮助人民群众抬水、扫地、推磨、砍柴、驮柴、劈柴、挖地、锄草、收种(庄稼),用实际行动洗刷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痕迹,表现了藏族人民固有的勤劳、朴实、善良、心地宽豁的美德。”
斯那尼玛平时不善言辞,讲起战友们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却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可是他从来不讲自己,他的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我是从他的战友口中听来的。比如,他化装成乞丐混进戒备森严的鹤庆县城侦察敌情,并成功转移了藏在鲍品良家中的武器。又如,他率领7 名藏族骑兵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南区镇公所提取枪支,抓捕了地霸杨桂芬等人。还有骑兵队初战保安团,他身先士卒,冲入敌阵,杀得敌人四散溃逃。尔后,在沙溪山口,在朗宋河畔,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就出现他跃马飞刀的英姿。此时的斯那尼玛,还只是个20 多岁的小青年。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一个从梅里雪山深处走出来的藏族赶马人,成长为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1951年3月,斯那尼玛被选送到北京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实习队队长,政治系班主任,后任学生会主席、院党委委员、并任全国学联副主席,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到柏林、布加勒斯特参加世界联欢节。
1953年2月14日,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模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此后,他有幸多次见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和他亲切握手的照片,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藏族同胞的关怀、爱护,在藏区,被人们视为珍宝,被高高悬挂在神龛上。更让斯那尼玛感到荣幸的是他再次见到毛主席时,老人家还能叫出他“斯那尼玛”的藏名。
寒来暑往,逝者如斯。当年驰骋疆场的骑兵战士中,如今已有不少人作古。转眼,斯那尼玛也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一代英雄远去,他们并没有带走什么,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漫漫征途上,当年骑兵队勇往直前团结拼搏的战斗作风,战士们在军旗下立下的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铮铮誓言和优良作风,将昭示后人永远向前,奋斗不息,牢记使命,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