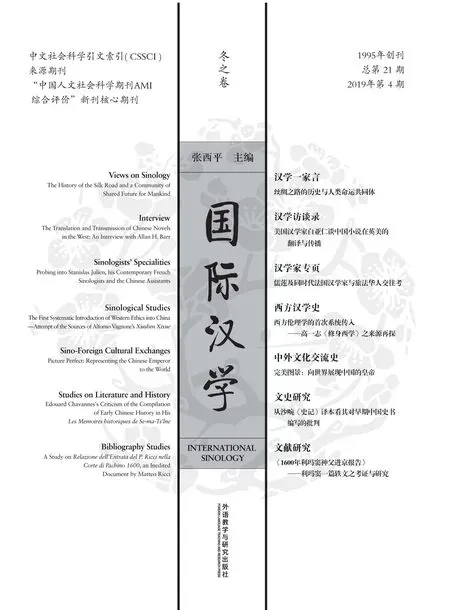《红楼梦》盖尔纳法译本对宗教词汇的翻译策略*
□ 张 粲
一、《红楼梦》里的中国宗教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①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皆出自(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对18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宗教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从主张“色空”、宣扬因果观念的佛教义理,到寻求解脱、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信仰,再到劳苦大众的民间崇拜(如花神、痘神、火神崇拜);从理想化的神仙及佛道人物(如警幻仙姑、癞头和尚、跛足道人),到世俗僧道(如张道士、马道婆、净虚);从宁荣二府公子小姐的佛道修养,到下层民众(如刘姥姥)的宗教信仰;从隆重的宗教活动(如秦可卿丧事、清虚观打醮),到符咒巫术(如马道婆施魇魔邪术),无不体现了独特的中国宗教文化。“宗教思想观念影响《红楼梦》的各个方面,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生活习俗、叙事方式乃至批评视野,都洋溢着宗教气氛”②吴志达:《〈红楼梦〉与宗教·序一》,载李根亮《〈红楼梦〉与宗教》,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序言第4页。。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将人类文化分为五类,分别为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及语言文化。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俗。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集儒、释、道三教于一体。而在西方,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经过与希腊罗马文化的摩擦与融合,最终成为西方宗教的主流。中西宗教的异质性势必造成宗教词汇外译中的文化缺省。《红楼梦》的宗教描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因此,如何翻译《红楼梦》的宗教词汇、向国外读者传递中国宗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红楼梦》译本的成败。
二、《红楼梦》盖尔纳法译本
迄今为止,在国外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红楼梦》法语译本有两种,一是阿梅尔·盖尔纳于1957年、1964年出版的上下册节译本(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下称“盖译本”),二是华裔翻译家李治华(Li Tche-houa,1915—2015)和其法籍妻子雅克琳娜·阿雷扎艺(Jacqueline Alézaïs,1919—2009)于 1981 年完成的法语全译本。盖尔纳的节译本是第一个较完整的法文译本,共42回,转译自德国汉学家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于1932年出版的德译本。库恩德译本意思确切、文字朴实,“迄今在欧美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红楼梦》译本,英、法、意、荷、匈等多种欧洲文字,都曾据此转译”①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7页。,“它的译文今天仍然应该受到称赞,因为它传达了原作抒情和细腻的特点”②同上,第27页。。由此转译而来的盖尔纳节译本亦受到好评,如德国学者梅薏华(Eva Müller)在1974年库恩德译本后记中便称赞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法译本”③同上,第28页。。盖尔纳重视《红楼梦》的宗教因素,他在其法语译本的序言中说:“一部杰作,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黄色人种或白色人种也好,红色人种或黑色人种也好),都必然是带有宗教感情的。”④同上,第200页。基于评论界对盖尔纳法译本的高度评价以及译者对《红楼梦》宗教因素的重视,本文拟考察盖尔纳法译本中的《红楼梦》宗教词汇翻译策略,以尤金·奈达的翻译对等原则为指导理论,分析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原则在翻译中的导向作用,考察各种翻译方法的利弊得失,以期得出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外译有所助益的启示。
三、《红楼梦》盖尔纳法译本对宗教词汇的翻译策略
奈达的翻译对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二是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形式对等主要以形式为导向,关注“诗与诗、句与句、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对应”,“接受语的信息应该尽可能地和源语文化中的各种因素分别对应”,以使读者“感受到原文文献使用本土文化因素传达意义的方式”。动态对等则以“等效原则”为基础,“以表达方式的完全自然为目标,而且尝试将接受者与他自己文化语境中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⑤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42页。在翻译《红楼梦》的宗教词汇时,盖尔纳法译本的翻译策略或以形式对等、动态对等为导向,或兼顾二者并灵活变通,其中不乏成功案例,但也存在某些局限。
1.以形式对等为导向
这样的翻译以原文为中心,尽可能地复制原文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包括原文的语法单位、词语用法的连贯性等。这要求译者保留原文形式,不拆分或调整语法单位。对此,盖尔纳法译本主要有直译和音译两种方法。
1)直译法
直译法是保持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翻译方法,它要求译者全面阐明原文含义,不随意增删原文的思想,同时保持原文的风格。例如:
原文:“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红楼梦》第1回)
译文:“Nous y trouverons peut-être occasion de réussir la délivrance de quelques âmes, ce qui serait une œuvre méritoire.”(盖译本上册⑥Armel Guerne tran.,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Paris: Guy le Prat, 1957.文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便于对比。第12页)
“功德”是佛教名词,指做善事、得福报。佛教宣扬因果报应,善因者得善果,恶因者得恶果。法语名词œuvre意为“道德行为,作为”,形容词méritoire由同族名词mérite(功绩)派生而来,其宗教含义为“功德”⑦《新法汉词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22页。文中所有法语词的含义均出自该词典。,因此méritoire则意为“有功德的”;œuvre méritoire回译为“有功德的行为”,属于对应原文的直译,成功地实现了原文和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统一。再如:
原文: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红楼梦》第16回回目)
译文:Le jeune Tsin Chung fait prématurément le grand voyage aux Sources Jaunes.(盖译本上册第191页)
《红楼梦》第16回讲述了秦钟少年早夭、并有阴间鬼判索其魂魄之事。“黄泉”,在中国民间宗教中指人死后居住的地方。人们打井至深时可见地下水呈黄色,又因旧时中国人死后多埋于地下,故而古人认为人死后居住的地下世界即为黄泉地带,又称“阴曹地府”;人死后到阴曹地府报到时所走的路即为“黄泉路”。死亡是全人类的共同现象,世界上各种宗教无一例外都对人的死亡表达出终极关怀,也对人死后的去处有着各种设想。法语中表达“死亡”的词语最常用的有mourir(死),décéder(去世),也有不少出自《圣经》或希腊罗马神话的短语,如retourner dans la poussière(归于尘土),sommeil éternel(长睡不醒),dans le sein d’Abraham(在亚伯拉罕的怀里),aller chez Hadès(去见冥王)。但盖尔纳并未采用现存的法语词汇来翻译“黄泉”,而是直译为“黄色的泉”(Sources Jaunes),译文绝对忠实于原文,保留了原文的异域情调,激发了译文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这种直译法的局限性:由于该词孤立地出现在《红楼梦》的回目中,缺少关联语境,若读者对中国民间信仰一无所知,那么读者便很难将“黄色的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无从领会原文含义。
2)音译法
音译法是指将原文语词用译语中与它发音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表示出来。由于形式对等翻译往往要求复制词语用法的连贯性,故而译者常常将源语中的一个特定措辞译为接受语中的一个对应措辞。音译法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妈咪(mummy)、披头士(Beatles)等,但若用之不当则可能词不达意。例如:
原文: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红楼梦》第57回)
译文:A-mi-to-fo! fit Pao Yu avec un accent de ferveur.Puisse-t-elle se guérir enfin!(盖译本下册①Armel Guerne tran.,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Paris: Guy le Prat, 1964.第87页)
“阿弥陀佛”是梵文Amita-buddha的音译。中国佛教宗派净土宗认为“阿弥陀佛”四字名号包含万德,只要念佛名号,即可往生净土。由于这种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因此五代以后净土宗逐渐普及于佛门,“阿弥陀佛”名号亦深入民间,成为人们常用的感叹词和口头禅。贾宝玉平日最喜毁僧谤道,却也在听闻林黛玉病情有所好转之后无意识地念起佛来。盖尔纳将之音译为A-mi-tofo,这四个字母从读音和形式上都与“阿弥陀佛”严格对应,极具节奏感和音韵感,但它们对于法语读者而言仅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拉丁字母,读者对其宗教内涵依然一无所知,亦无法具有与原文读者相近的认知反应。
从上文可知,以形式对等为导向的翻译有利于保留原文的异域情调,但某些情况下亦可能呈现给译语读者以毫无意义的字母符号。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常常存在着形式和内容、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对立和冲突。在不能兼顾二者的情况下,过于拘泥于字面和形式的译文极易抹杀原文的精髓。因此,译者在面对形式和内容对等时,越来越重视动态对等的导向作用,优先考虑内容对等和读者反应。这在盖尔纳的《红楼梦》法译本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2.以动态对等为导向
这种翻译重视译语读者的反应,指向读者反应的等值而非译文与原文形式上的等值。这要求翻译打破原文语法结构,尽量适应接受语言和译语文化的语境。而要取得自然的翻译,则要求译文在词汇、语法、文化语境等多个层面进行调整。中国宗教在信仰、教义等各方面均与西方宗教相去甚远。翻译《红楼梦》的宗教词汇,如若过多地注重原文形式,势必造成译语读者的认知障碍。盖尔纳的《红楼梦》法译本采取了意译法、解释法、综合法、替代法等多种方法,体现了动态对等的原则,其效果亦有利有弊,需要具体分析。
1)意译法
与直译法严格遵照原文形式不同,意译法不拘泥于原文的措辞,而是保留原文的精髓,追求流畅自然的译文。当直译法行之无效时,译者可采取意译法打破原文的表层结构和字面意义。例如:
原文:“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红楼梦》第1回)
译文:“Dans trois cycles, je t’attendrai au cimetière que tu sais, sur le coteau de Peh mang,près de Loh yang.”(盖译本上册第 14—15 页)
“劫”是佛教名词,是梵文kalpa的音译,意为极为久远的时节。佛教认为世界有周期性的生灭过程,它经过若干万年后,就要毁灭一次,重新开始,此周期称为“劫”。②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178页。对于这一佛教词汇,李治华的法译本、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的英译本等均音译为kalpa,保留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而盖尔纳则取“劫”的“周期性”之义将“三劫”意译为“三个轮回”(trois cycles),较之音译的kalpa而言难免淡化了原文的佛教色彩,却阐释了佛教的“六道轮回”教义,也不失为合理的翻译方式。
2)解释法
解释性翻译是指对所译内容做出解释性说明,它通常是对语言意义的解释和文化背景的补充说明。虽然它往往会增删译文的字数,并造成译文和原文之间语法、形式、内容上的不对等,但却可以在译文中融入某些缺失的信息,在原文和译文读者之间架起一座跨越文化鸿沟的桥梁。例如:
原文: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红楼梦》第2回)
译文:Car celui-là versa dans les errements du taoïsme et s’adonna à l’alchimie, ne s’occupant plus que de sublimations et autres distillations de l’élixir de vie, cuissons et réductions de pilules de cinabre.(盖译本上册第32页)
“烧丹炼汞”为道教炼丹方术,“丹”指朱砂,“汞”指水银。道教炼丹“讲究服食炼养之法,以朱砂(丹)、水银(汞)等烧炼‘仙药’服之,以此妄求飞升成仙,长生不死。”①《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第181页。因此道教往往与古代医学、化学、矿物学产生联系,道教炼丹术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为近代实验化学的前导”②李刚:《中国道教文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如何让译语读者理解中国独有的道教炼丹术呢?对此,盖尔纳并未直译“烧丹炼汞”,而是在译文中增添了一系列解释性的词语:用cinabre(朱砂)解释炼丹所需原料,用alchimie(化学)、sublimation(化学升华)、distillation(蒸馏)、cuisson(焙烧)、réduction(化学还原)解释丹药的制作过程,再用élixir de vie(长生不老药)、pilule(丸药)解释出道教“仙丹”的所谓功能及形态。通过上述解释性词语,译语读者能较好地理解道教炼丹术的原理和方法以及道教的长生不老信仰。
3)综合运用意译法、解释法、省译法
对《红楼梦》里的某些宗教词汇,一方面由于词汇本身过于晦涩,一方面由于省译或不译这些词汇并不影响读者的整体理解,因此,盖尔纳在必要的情况下综合使用了意译法、解释法、省译法。例如:
原文:宝玉……遂提笔占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红楼梦》第22回)
译文:Pao Yu…exprima sa détresse en un double vers désabusé, qui puisait aux sources du renoncement au monde et du détachement de la philosophie bouddhique.(盖译本上册第248页)“偈”乃佛教术语,是梵文gāthā的音译,佛经的一种体裁,又名“偈诗”,通常以四句为一偈。僧人或文人们常用这种四句韵文来阐发佛理或哲理。佛教是东方宗教,西方语言中并不存在与“偈”对应的概念,因此盖尔纳首先将“偈”意译为“对称的诗句”(double vers),这译出了“偈”的形式特征,随后使用形容词désabusé(醒悟了的,看穿了的,不抱幻想的),传递了佛教的“了悟”等内涵;继而又增添了“弃世”(renoncement au monde)、“超脱”(détachement)、“佛教哲学”(philosophie bouddhique)等解释性词语,进一步向读者说明宝玉所作的偈与佛教关于出世和超脱的思想有关。但盖尔纳仅翻译了“偈”的概念,却将这一参禅偈的内容省略不译。这是可以理解的:佛教哲理玄妙深奥,如若缺少佛学修养,即使是汉文化圈的人士也未必能领会其中要义,何况宗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西方读者。事实上,在译者对“偈”已做出详细解释的前提下,如此省译亦无伤大雅,并不妨碍读者在总体上理解佛教思想。
4)替代法
中西宗教的迥异使得《红楼梦》的宗教词汇在外译过程中经常出现文化缺省。替代法将原文术语(往往是文化空缺词)替换为译语术语,是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变通手段。该法能使译文符合读者的文化背景,但要求译者精心挑选替代词。盖尔纳处于以犹太—基督教为主流宗教的西方文化之中,常用西方宗教术语解释中国宗教。例如:
原文:“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红楼梦》第3回)
译 文:“cette nouvelle cousine comme un ange!”(盖译本上册第55页)
“神仙”是道教名词,指“道教信徒所理想的修炼得道、神通广大、变化无方、长生不死的人”①黄海德、李刚:《简明道教辞典》,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7页。。作者讲述宝玉初见黛玉便赞其好似神仙,一语道出了黛玉超凡脱俗的美貌气质,也暗示了林黛玉乃仙草转世。盖尔纳将“神仙”译为“天使”(ange),后者在《圣经》中指“在天国工作,奉天国之命,来到人间的使者”②代彭康、陈邦俊:《圣经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页。。该词还有“纯洁”“完美无缺”之意,亦可作爱称使用,如法语中常用mon ange(我的天使)称呼爱人。盖尔纳将道教的“神仙”替换为基督教的“天使”,看似与原文相去甚远,但却正好符合西方人对神灵的想象,效果可谓一石二鸟:一则,它向读者暗示了宝黛之间纯真的爱情;二则,林黛玉(绛珠仙草)何尝不是由天上来到人间向贾宝玉(神瑛侍者)偿还灌溉之恩的呢?
再如:
原文:“南无解冤孽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颠倾,或逢凶险,或中邪祟者,我们善能医治。”(《红楼梦》第25回)
译文:“Au nom des puissances salutaires du Midi, nous possédons l’infaillible remède qui chasse les démons et libère les possédés! Au nom du Sauveur Méridional!”(盖译本上册第274页)
马道婆施魇魔之法陷害宝玉和凤姐,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赶来相救。盖尔纳将“南无解冤孽菩萨”译为“南方的洁净大能天神”(puissances salutaires du Midi)、“南方的救世主”(Sauveur Méridional)。首先,此处 puissances和 Sauveur值得注意。puissance(权力,力量)作复数puissances时,专指基督教的“大能天神”,即“九品天神”中的第六品;sauveur(救星,救命恩人)大写为Sauveur时专指基督教的“救世主”,即耶稣基督。其次,“邪祟”指邪恶而作祟的事物,尤指害人的鬼怪;盖尔纳用chasse les démons et libère les possédés(驱除魔鬼、解救被鬼附身的人)来解释“善能医治中邪祟者”。démon是《圣经》中的“魔鬼”,常附于人身;possédé(s)指“被魔鬼附身的人”,他们常有好斗、企图自毁、丧失视听能力等异常表现,这在《马太福音》中多有描写。“福音书”里屡屡记述耶稣为人医病、驱鬼(chasser les démons)的神迹。宝玉、凤姐中魇后的异常举动与《圣经》所描述的“被鬼附身之人”有很大的可比性,因此,盖尔纳将佛教的“菩萨”替换为基督教的天神和救世主,将中了魇魔之法的宝玉和凤姐比作被魔鬼附身的人,将“医治中邪祟者”通过耶稣赶鬼的故事来解释,均为成功的替代,这是基于中西宗教乃至世界各宗教的共性,即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它们可能是作祟害人的鬼魂,也可能是至德良善的“神”。
但盖尔纳的替代翻译并非都是成功的。使用替代翻译时,选择精准的替换词至为关键,否则会导致译文缺乏准确性,甚至造成荒谬的后果。例如:
原文:……俱是各家路祭。(《红楼梦》第14回)
译文:...en offrant à l’esprit de la morte, pour son voyage, des sacrifices propitiatoires...(盖译本上册第173页)
《红楼梦》第14回对秦可卿的丧事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路祭”又称“道祭”“路奠”,指旧时亲友在亡者的灵柩赴陵途中设供品香烛祭奠亡灵,对亡者表达崇高之敬意。译文中,sacrifice指“祭品、供品”,而propitiatoire作名词时指“(古犹太教)约柜上的金板”③《新法汉词典》(修订本),第811页。,也有《圣经》中译本(如和合本)译作“施恩座”。《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上帝耶和华曾在西奈山晓谕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进献礼物,并明确地规定了如何制造“施恩座”。propitiatoire作形容词时意为“赎罪的”,sacrifice propitiatoire则意为“赎罪的牺牲”①《新法汉词典》(修订本),第480页。,或“用以赎罪的祭品”。犹太—基督教宣称人生来即有原罪,因此人必须向上帝忏悔以获得救赎,此即西方“罪感文化”的来源。但原文中“路祭”本是贾府亲友为秦可卿的亡灵所设,秦可卿身份固然尊贵,但此处译为“赎罪的牺牲”,虽然译出了路祭的庄严肃穆和宁国府的奢侈排场,却误将秦可卿亡灵的地位拔高到犹太人和西方人心目中的唯一神和最高神“上帝”的位置,包含了过于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完全抹杀了中西宗教的差异,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因此是不成功的替代翻译。
再如:
原文:“这物……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红楼梦》第12回)
译文:“Ce miroir...a pour vertu cardinale la purification des âmes, qu’il débarrasse des mauvaises pensées et des désirs charnels obsédants.”(盖译本上册第 154 页)
《红楼梦》第12回写贾瑞因中了王熙凤所设的相思局,在寒冬里挨饿受冻,又遭贾蓉和贾蔷的勒索惊吓及祖父的责罚鞭笞,种种折磨使之病势加重、奄奄一息,忽有跛足道人来化斋,借出“风月宝鉴”,称它有“济世保生之功”。译文中purification(洁净)一词在《圣经》中屡屡出现,《圣经》“旧约”对“洁净”及“不洁净”的禁忌有着明确且名目繁多的规定。盖尔纳用purification des âmes(洁净灵魂)这一极具犹太教风俗色彩的语词来阐释“风月宝鉴”的作用,大致符合跛足道人关于“风月宝鉴”的反面能断人邪念之说,是谓成功的替换;译者继而将“济世保生之功”译为vertu cardinale,此为天主教信徒的勇、义、智、节“四枢德”。天主教宣称这“四枢德”扮演着枢纽的角色,信徒的其他一切德行均环绕着这四德而组合在一起。这原是天主教对信徒的道德要求,却被盖尔纳用来解释“风月宝鉴”的奇功,与原文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3.兼顾形式对等、动态对等
虽然盖尔纳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了动态对等的原则,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翻译并非截然对立。为了最大限度地传递中国宗教文化,译者也会“多管齐下”,综合运用音译法、直译法、解释法、注译法等多种翻译方法。例如:
原文:过了一日,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进荣国府来请安。(《红楼梦》第25回)
译文:On eut, le jour suivant, la visite au palais Yung kuo de Mère Ma, ou Ma taopo, la magicienne taoïste dont les charmes, les exorcismes et les cures miraculeuses avaient assuré la réputation comme guérisseuse mystique.Elle avait servi de marraine à la naissance de Pao Yu, qui l’honorait en retour du titre appréciable de mère adoptive.(盖译本上册第265页)
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对中国人的民俗、心理及人生礼仪影响极大。旧时中国人希望孩子健康长寿,为了避免半途夭折,常将婴孩送到道观佛寺,请道士、和尚给孩子取名,此即“寄名”。由于人们认为道观佛寺属于神圣所在,因此在礼仪和象征的基础上将孩子托付给道观或佛寺,寄名神佛,缔结一种宗教和世俗的亲属关系,如此,婴孩名义上便是僧庙道观的成员,有佛祖道神保佑,可以逢凶化吉。明清时“寄名”风俗已经相当普遍,如《金瓶梅》第39回“寄法名官哥穿道服”便对“寄名”仪式有着完整的描写。《红楼梦》中马道婆便是宝玉的寄名干娘。西方并无“寄名”风俗,故而盖尔纳并未将之单独译出,而是通过解释“道婆”的身份以及“干娘”这一称谓来达到翻译的目的。
先看“马道婆”的翻译。盖尔纳首先译为Ma tao-po,此乃音译,但这些字母对于读者而言毫无意义,故而译者又通过解释法多管齐下地解释旧时“道婆”的身份:从称谓上看,她是道教徒,因此,盖尔纳首先将她定义为taoïste(道教徒),这是符合原文的。紧接着,盖尔纳解释了道士和道婆的主要活动:一是驱鬼,二是治病。道士和道婆驱鬼时要作法术、念咒语、画符箓,这通过“道教的女巫师”(magicienne taoïste)、“魔法”(charme)、“驱魔”(exorcisme)等词汇得以解释;同时,道士多通晓医药,民间常有“十道九医”的说法;道士的治病途径通常有“符水驱邪”“医药偏方”“法术”等,因此译文中“神奇的治疗”(cure miraculeuse)、“神秘的医者”(guérisseuse mystique)较准确地解释了马道婆的职业活动。而guérisseuse一词最妙,它通常指“没有正式资格的行医者”①《新法汉词典》(修订本),第480页。,一语道破了道士的行医途径不为正统医学所承认的事实。
再看“干娘”的翻译。盖尔纳首先直译为Mère Ma(姓马的母亲),继而替代为“教母”(marraine),该词与基督教的洗礼有关:在西方国家,基督徒追求天国属灵的幸福,基督教家庭出生的孩童要接受洗礼以涤清原罪,在洗礼仪式上,家长在亲戚朋友中选定一位“教父”(parrain)和“教母”(marraine)对孩子进行宗教教育。然而,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爱好“此生命和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②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91页。,因此中国的“寄名”风俗并不是真让孩童皈依佛道、遁入空门,它仅是旧时家长为儿孙祈福的心理体现;同样,“寄名干娘”马道婆并未对宝玉进行任何宗教教育,她除了游说贾母布施财物外,还设计魇魔之法陷害宝玉。由于西方社会并无“寄名”的风俗或“寄名干娘”的称谓,因此在无法找到完全对应概念的情况下,用西方宗教术语“教母”来替代“寄名干娘”可谓是最贴近原文、也是相当成功的翻译方法了。
结语
宗教以其独特的方式渗透于人类社会,在使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同时,又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造成了种种障碍。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古典名著中无处不在,因此准确地传递中国的宗教文化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地道的中国文化,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盖尔纳为法语世界的读者奉献了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红楼梦》法译本,并在译介中国宗教文化和古典文学方面做出了宝贵的尝试。总的来说,盖尔纳较好地传递了《红楼梦》所描绘的中国宗教文化,虽然其译本中也存在少许未能忠实于原文、抹杀了中西宗教差异的译文。事实上,处于西方宗教语境下的译者经常面临类似的困惑而无所适从,盖尔纳的翻译尝试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首先,以形式对等为导向的翻译有利于保留原文风格和异域情调,激发译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因此,若译文的音律、节奏、形式、内容具有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译者应首先考虑形式对等的翻译。其次,中外文化的异质性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鸿沟,面临文化空缺词,译者应侧重于译文和原文的动态对等,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可适当借助译语文化术语来解释原文的术语,但需严格注意术语的选择。再次,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并非完全割裂或不可调和,在某些情况下,译者可以综合两种原则,运用多种翻译方法,既能保留原文风貌,又能使译文准确向读者表达原文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