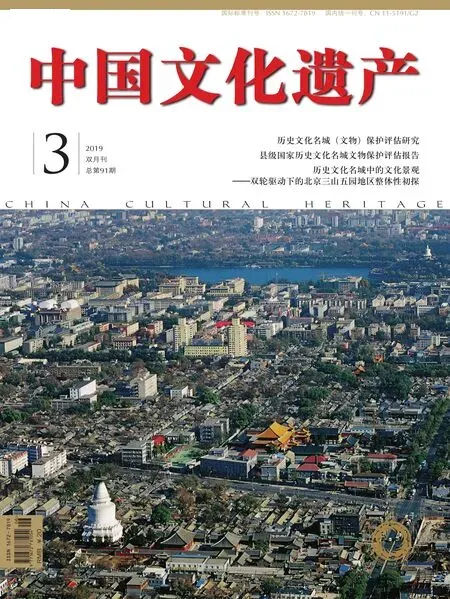论聚落遗产与价值体系的建构①
张 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 100084)
引言
尽管遗产一词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法语和拉丁语中,但历史遗产保护却是一个近现代概念。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领域”的意识,遗产不再单单是私人拥有的财产,而是全社会共同拥有的。18世纪后期,法国首次将文化遗产纳入国家政府的管控。到19世纪中叶,保护古老的文化物品和不可移动的古建筑和景观开始与保护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世纪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国家对遗产的管理不断加强。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签署将遗产保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四十年来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遗产数量激增,初步建立了与国情相适应的法规体系。
随着遗产数量的增加,如何划定遗产、阐释遗产的价值也成为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将针对遗产划定的一般标准、遗产范畴的演变、遗产价值的建构等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社会参与、以时间为主要标准划定遗产对象是基础
我们知道,价值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灵魂所在,一个项目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但从各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实践看,确认标准普遍采取以时间为主要依据。这也很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当然要在时间维度上有一定的“历史”。
1837年法国成立了历史建筑委员会(Commiss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根据建筑的建成年代、建筑风格及相关的历史事件划定要保护的建筑。当时该委员会划定的主要是中世纪的古建筑。这种方法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划定标准均产生了影响。1870年代,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英国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2]。将一些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划入保护名录,是为了在当时工业革命城市大发展的背景下对它们加以保护,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的公共财产。从那时开始,历史建筑保护就一直在对抗大规模的拆除、损害中艰难地发展着,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签署正是因为“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197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对它们的任何严重的损坏都是悲剧。其中那些最重要的、无价的遗产构成了文化、自然遗产的本体,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对全世界人民都具有突出普遍价值”[3]。
作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英国遗产保护的历程可以很好地说明以历史时间为划定标准的发展历程。英国的建筑遗产主要分为四种类型:(1)在册古迹(scheduled ancient monument)、(2)登录建筑(listed building)、(3)保护区(conservation area)、(4)注册历史公园与园林(registered historic parks and gardens)。
“在册古迹”是英国最早被列入保护的对象,对其立法保护始于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Ancient Monuments Acts),英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立法来源于民间团体的推动。为了抢救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消失的大量古迹,威廉·莫里斯于1877年创立了英国第一个民间建筑保护组织——“古建筑保护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推动了民间保护运动的发展,促使英国政府在1882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古迹保护法》。
“登录建筑”的主要构成是那些年代不那么久远、但在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历史建筑。1930年代是英国工业城市快速扩张的年代,城市环境、乡村景观都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1932年的《规划法》提出了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并授权地方政府划定历史建筑予以保护。1947年的《规划法》奠定了战后的城市规划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提出了规划许可制度。正是在这部规划法中,英国建立了历史建筑的登录制度。超过50万宗建筑遗产被列入保护名单。
登录建筑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5个方面:1)随着古老程度与罕见程度,越晚近的标准越严格;2)著名建筑师的作品;3)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4)与著名历史人物、事件相关的建筑;5)具有群体价值。在英格兰历史建筑的标准中,所有1700年之前的建筑都包括在内;对1700—1840年间的建筑绝大部分予以登录。19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建筑由于量大,采取选取重点的原则。1840—1945年间建筑的入选标准进一步严格。最后,1945年以后的建筑需严格挑选。在苏格兰的标准中,1840年以前的与英格兰相同,但将1840年以后的时期又分为:1840—1914、1914—1945,以及1945年以后。这样的时间划分与历史时期划分相吻合[4]。
英国的登录建筑分为3级。Ⅰ级为拥有罕见独特价值的重要建筑,Ⅱ*级为拥有非常独特价值的重要建筑,Ⅱ级则是具有特殊价值、值得尽力保护的历史建筑。Ⅰ、Ⅱ*、Ⅱ级分别占总量的2.5%、5.5%、92%[5]。由此可见,建造年代越早,建筑登录的等级越高,1700年之前的建筑即使仅留存部分轮廓也可被登录为Ⅰ类。而时间越晚近的建筑,选择标准则更严格。但同时,大量Ⅱ类建筑绝大多数为住宅,而且成为保护区整体性的“本底”。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二战”期间被认为可以拆除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到1980年很多都成为保护的对象。除此之外,在英国还有大量的登录项目是有地方制定的,它们主要是通过公众征询确立名单,而且主要与地方特色相关,标准与国家的登录体系不同[6]。
“保护区”是1967年在市民托拉斯(Civic Trust)的倡议下形成的《城市宜居法》(Civic Amenities Act)中正式提出的。战后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历史城市的拆除达到了空前规模,造成社会的强烈反弹。1958年英格兰历史建筑委员会(Historic Buildings Council for England)针对一些小城市和村落景观明确提出了群体价值(Group Value)的概念。1959年发生的伦敦圣·詹姆斯广场(St.James’Square)事件诱发了保护区制度的诞生。另一方面,新的考古发现也促进了保护理念向群体的发展[7][8]。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1967年颁布的《城市宜居法》明确提出了“保护区”的概念,对具有群体特色价值的历史建筑群予以整体保护,这标志着英国的建筑遗产保护立法从单体走向整体,该法后纳入1968年的《城乡规划法》。在这个时期,英国还对4座历史悠久、较为完整的历史城市——约克、彻斯特、齐齐斯特、巴斯提出了保护要求。其中针对这4座古城的保护研究报告都系统梳理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街巷、建筑景观等,但不包括后来在世界遗产中强调的“价值”研究与分析的内容[9]。到1980年代,文化景观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设立了“注册历史公园与园林”制度,以保护那些具有历史价值或景观价值的公园与园林,要求建造年限在30年以上。目前,英格兰地区有1500多个注册历史公园和园林[10]。
1983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国家遗产法》(National Heritage Act)首次在法律中提出了遗产的概念,它将历史建筑、保护区和古迹与各类博物馆、军工厂、皇家园林一同纳入遗产的范畴,并提出为这些遗产设立管理机构[11]。目前,仅在英格兰就有近10000个保护区,包括历史城镇、村落、两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的住宅区、老工业区、交通网络、历史公园和园林等[12]。
同样,时间或遗产的历史维度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的考虑因素。譬如,1987版《操作指南》中,在“文化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中,第一次专门讨论了有关“仍有人居住”的历史城市保护与列入的问题,指出原则上不将20世纪新城列入名录,因为“对20世纪新城的质量作出评价是困难的,历史将会说明其中哪个可以成为当代城市规划的代表。这样的城市的申请应该不予考虑,除非所有代表人类脆弱遗产的、传统的历史城镇都已经全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3]。
我国的遗产保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符合国情的遗产保护体系,其中保护对象的划定也主要是考虑时间因素。我国在1960年代初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多是像故宫这样的重要历史建、构筑物。1980年初代在一批老专家的动议下,国务院确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开启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保护的新局面。1990年代中期城市改造大规模展开,历史城市面临严重冲击,当时的住建部及时强调了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城市化的进展开始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广大农村地区的众多遗产,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国家于2003、2012年先后设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公布制度。近年来,信息工业部、中国文物学会又分别推出了“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各省还按照自身特点公布了省级名城、名镇名村、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等,有的城市设立了风貌保护区等。与此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对超过50年的老建筑也建立起相应的保护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76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31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487个、中国传统村落6799个(包括第五批公示2646个)、国家工业遗产名单53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298处。除此之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在以上名录②各类遗产数量为笔者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建筑学会等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保护名录批次予以叠加统计。中,聚落与建筑遗产总量已相当可观,为我国遗产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我国遗产名录建立历程可以看出,越早划入名录的项目,历史越悠久,总体保护状况也更好。当然,后来的工业遗产名录则主要涉及了20世纪以后的工业建筑及其环境,这与我国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有关。
二、遗产范畴随历史观念的发展而扩展
现代历史遗产保护是社会参与的一种国家行为,必然与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密不可分。
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过去记忆的学科,各民族用不同方式叙述自己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发生着变化,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到17、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兴起,开始探讨历史、文化、文明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受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盛行,但随着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开始萌芽,历史的主、客观如何结合成为历史学的重大课题。法语中的历史是指“经历过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思想活动”[14]。在德语中,历史一词既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即相关的历史叙述[15]。
可以看出,历史一词同时涉及主、客观两个方面。中国治史传统悠久,很早就有专门的史官,历史著述之丰,堪称世界之最。中文的“史”字,本为记事之意,历史就是要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然后再把它们编辑在一起[16]。虽然中国古代史家秉承“春秋”如实记录、不做评论的原则,但“以史为鉴”的大义贯穿始终,其中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
历史观念的演变与后来的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在线性时间观念影响下,“进步”的乐观主义史观逐步形成,当时人们对过去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那是落后的。18世纪随着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萌发,人们开始将历史传统与国家的起源等联系起来,遗产也逐渐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19世纪和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酝酿和出现,欧洲和北美国家开始将历史保护视为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到20世纪初,在西方,遗产已成为文化或知识界一个重要的议题[17][18]。
历史叙述,无论是传统的以事件为主的历史,还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都是以排斥记忆为基础的,认为记忆是主观的、不可靠的。诺拉指出,从中世纪到当代,“在历史深处,活跃着一种对自发的记忆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批判精神……一个完全在历史影响下生活的社会,已不再是传统社会,它不认识记忆赖以根植的场域”[19]。正是由于“历史”将记忆放逐,在日益变动布局的现代社会,社会记忆与历史之间出现巨大的裂隙。
历史试图寻找一种“普遍性”,而记忆则与生活息息相关,总是由当代具体的群体所承载,而且可以适时发出火花。所以,诺拉指出,我们有一种记忆“是整体性的、支配性的……永远伴随着遗产”,它属于过去,但没有过去的记忆。而另一种记忆则是“我们的记忆,它仅仅是历史,或曰经过挑选后的痕迹”[20]。在西方国家造成“两种记忆”离析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消失。所以,建构历史与记忆的融合成为当代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法国的遗产保护历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早在1830年代,面对当时工业革命和社会动荡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法国成立了历史古迹检查机构,由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普罗斯佩·梅里美负责。当时该机构保护历史建筑的动机是将其“看作是有待研究、有待加固、需要挽救的物体”[21]。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国遗产从最初的国家与民族记忆拓展到了社会心态记忆,而且遗产所涉及的历史越来越近,从而使遗产与更广泛的民众联系起来。19世纪时,梅里美(1803-1870)提出了四项历史悠久的遗产保护议题,其中包括法国南部的罗马人建造的水渠加尔加桥。1970年代后,遗产保护的社会意识凸显,从1975到1980年五年的时间内,国家与地方确立的遗产项目数量剧增。数量的增加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保护观念的变化与视野的拓展。1980年代,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的雅克·朗格配合密特朗总统的文化政策,相应地提出了新的“四个遗产”的概念,其中包括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张照片和一个19世纪外省的老式马桶等(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雅克·朗格是想借保护那些能够唤起普通人对过去日常生活记忆的东西,拓展遗产的内涵与外延[22][23]。在法国,民众对于集体记忆的需求不仅拓展了遗产对象的外延与内涵,还极大地推动了各种博物馆的出现。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拉对此总结说:“遗产从历史时代……过度到了记忆时代”[24]。世界各国的遗产保护很多都是在拆除与保护的斗争中确立下来的,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记忆与情感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三、价值提炼是对既有遗产的选择与重组的过程
1977版《操作指南》指出:《世界遗产名录》的提出,是与对各成员国保护遗产的工作相互补充,而非竞争[25]。这种互补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价值提炼是对既有遗产再认知而非普遍的保护标准
绝大多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在成员国都经历了较长的保护历程,譬如保护项目在国家法律、法规中遗产地位的确立,长期的专业保护和管控都是历史遗产必备的条件,否则它们就不可能达到《操作指南》要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也不能满足管理规划的要求。《世界遗产公约》在1972年才签署,但绝大多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远早于这一时间。各国在不同时期、在社会的推动下,以时间为主要标准建立的遗产保护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在“突出普遍价值”框架下的保护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换言之,“突出普遍价值”与各国长期建立起来的“一般评价体系”是一种互补,而不是排斥。
如英国约克、彻斯特、齐齐斯特、巴斯四座主要的历史城市,早在1967年就被列为英国重要的历史城市保护起来,并做了系统的保护工作,但巴斯古城1987年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样,近年来约克古城也在申报,但至今尚未被列入名录。中国的情况也相同,如故宫、长城、颐和园、曲阜“三孔”等,也都是在国家长期保护的基础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列入名录需要梳理历史脉络,提炼突出普遍价值。但可以清楚地看出,对绝大多数遗产来说,按照《世界遗产名录》列入条件的要求对价值进行的挖掘与长期保护之间的关系与顺序。
此外,很多国家包括我国的很多城市,都提出了5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不得随意拆除的规定,我国上海市最近又提出了“永不拓宽的马路”[26]。这类遗产保护政策的提出,主要是社会对历史记忆的需求,而不是高深遗产价值提炼的结果。这些都反映出保护历史遗存与价值阐述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多没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保护对象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保护价值,其价值往往会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才被确认。
最后,社会记忆的沉淀可以将相关的遗存或场所塑造成遗产,法国的“环法记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03年7月,法国《汽车报》为了促进报纸发行量,并为自行车做广告,发起了环法自行车赛事。由于成功的路线和内容设计,它很快成为欧洲重要的赛事,并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法国一项重要国家记忆遗产。诺拉对此解释道:“环法所交织的,是关乎一片土地的回忆……赛事塑造着一份遗产的想象”“环法车赛并不仅仅展示着国家的界限与统一,也让人们邂逅关乎国家的记忆”[27]。环法线路串联了法国最美丽的地方,展现了它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加强了法国人的归属感,为人民所热爱。一代又一代法国人对赛事“朦胧”记忆的沉淀,塑造了这个赛事及其串联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整个国家人民中的记忆。显然,这里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人为的价值提炼将一些既有的场所塑造成遗产。
(二)主题建构与遗产要素重组
关联性是世界文化遗产系列遗产项目类型的重要特征。一项系列遗产各组成要素之间必须在同一主题下,共同支撑项目所表达的突出普遍价值。这就涉及到历史学中的选择性问题。这种选择性可以分为:a)因果关系链条选择性,b)对同一历史对象的不同问题、不同方向的选择性,c)历史叙述自身的选择性。下面我们有必要将这三个方面的相关理论逐一加以讨论。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其历史哲学名著《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一种过程。”他引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话说,“历史是一个选择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就像历史学家从浩瀚的事实海洋中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换言之,一些没能纳入因果关系的事实可能被认为是“偶然事件”,在既有的选择体系中不具备“历史意义”,而被忽视。卡尔进一步指出,“历史解释总与价值判断交缠在一起,因此,因果关系也与解释交缠在一起。”如果没有价值的引导,人们就无法在历史中寻找因果关系[28]。
有时为了对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或年代作出解释,历史学家会给它找到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概念”以便将各部分联合为某种整体。例如,历史学家把18世纪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解释为“革命”。“革命”这个“整体”就是历史学家对这个历史时期主要事件的概括与解释。但是,这样的统一的概念并不能遮盖一个真实的历史时期的复杂与多面性。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指出:即使对同一历史时期、同一历史事实,不同的历史学家所感兴趣或研究的问题也是不同的。譬如,海斯在《唯物主义的一代》一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面的19世纪的最后25年,兰格对此作了如下的概括:“这是欧洲的和平年代,是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是进步的时期,是逐步宽容并迅速传播自由主义的时期……然而,从历史上看,从批评的角度来考察,19世纪末叶毋宁表现为唯物主义时代,表现为自命不凡和盲目自信的时代”[29]。其实多面性正是历史社会的本来面目。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19世纪这样评价道:“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蠢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春天,那是黑暗的冬天;那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登天堂,我们全都直奔相反的方向”[30]。威廉·德雷认为:“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他所划进来的内容。这个问题是在他选择了研究主题之后提出的,不仅在选题时需要选择,在他研究过程中也需要选择。”作者认为,如果不同的历史学家选择了不同的题材而作出自己的解释,那么不应该说其中一个是错误的解释,而应该把他们视为是相互补充的[31]。现代史学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专门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譬如与世界史相平行,我们还看到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文明史、技术史、军事史、艺术史、女性史,城市史、建筑史,等等。
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将19世纪的历史著作呈现出的概念化分成五种,它们是:编年史、故事、情节化的模式、论证的模式以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他把“编年史”和“故事”视为历史记述中的“原始要素”,因为“二者都表现了’材料从未被加工的历史文献中被选择出来并进行排列的过程”[32]。也就是说,历史叙述需要像讲故事那样,有一个开始、中间和结局。海登·怀特还指出:“严格地说,编年史没有结局;原则上,它们没有序幕,只有在编年史家开始记录事件时“开始”。它们也没有高潮和结局,而能够无静止的继续下去。故事则不然,它有一种可辨识的形式(即使那形式是一种混沌状态的情景),使得包含在其中的事件能与其他同时期内所有编年史中涵盖的事件区分开来”[33]。所以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历史的叙述也是对过往的历史素材的一种选择和排序。
价值的提炼就是一个有始终的“故事”,它需要从广泛的、类似“编年史”史料的既有遗产中选择出符合支撑申报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的那些要素。而这些要素绝大多数是在一般判断标准下被长期保护的。某个要素是否被选入,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项目“突出普遍价值”所涉及的主题,并且在相应的因果链条中起到有力的说明作用。最后,世界遗产作为一种国际社会共同的事业,涉及行政管理、政治与外交等因素,必然影响着名录的类型、文化背景、国家背景等因素的构成。譬如,世界遗产委员提出了的鼓励文化多样性的政策、遗产项目类型数量的均衡政策,各地区、国家遗产数量的平衡政策等,这些都会影响成员国对申报遗产项目的主题、类型等的选择。
四、构筑基于三个历史时间尺度的 聚落遗产保护体系
黑格尔指出,“进步”或一种特殊的变化是历史的原动力[34]。一个变化过于缓慢的社会难以产生真正的历史感;同样,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人们的历史感也会变得浅薄。在当下这个强调创新的时代,对过去的关注、对身份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思考是每个社会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当代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对快速发展的世界的镜像与反思。要处理好“应保尽保”与选择性的价值提炼的关系,我们需将一个合理的历史观念并与遗产保护的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从18世纪的孟德斯鸠开始探求历史发展规律以后,现代史学研究都试图通过发现历史事件的因果及其内在的支配性规律。但这种这做法带来的常见问题是“简化答案、在混乱中寻求秩序的一致性”[35]。从国内外遗产保护名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遗产保护的评判标准变得越来越包容,它涵盖了纪念性的单一的建构筑物、活态的城市、聚落、文化景观等遗产类型,涉及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它们共同构筑起了保护与传承国家、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记忆载体的立体网络。
法国的年鉴学派从“总体史”的视角提出了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历史的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历史中的结构、局势、事件。早期年鉴学派特别强调长时段历史的深层作用,忽略后两者[36]。1970年代的史学界意识到这样的观念意味着将历史与当下脱离。诺拉的“记忆之场”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
从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六条标准看,它们其实涵盖了三个历史时段的遗产类型,如有的项目反映了一种重要的文化、文明,这指的是长时段的历史;与重要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技术、军事等)的代表则反映了中时段的历史;最后,代表性杰作、重大的历史事件等则反映了短时段的历史。
世间万物有不同的生命周期,有的瞬息则逝,甚至不能为人类所察觉;有的则超过百年、千年,或更长,或被人类视为永恒。年鉴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中,由于不同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的历史事物也存在着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时间尺度。其中,人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互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属于长时段的历史,而经济模式、社会制度等属于中时段的历史,而人一生中的各种经历则为短时段的历史[37]。
依照年鉴学派的理论,作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如文化景观、建筑、街区、城市、村镇等,都是相对稳定的空间因素,一般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或类似的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的叠加而成的。它们反映的历史信息是多元且不完整的,难以用一个体系或价值概念加以概括——尤其是对城市结构、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及其构成的文化景观而言,它们是在长期过程中形成并起作用的,但其中发生的人与社会活动的变化与更迭则要相对快得多。而正是这种变化赋予这些相对不变的建成要素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集体和个人记忆的载体。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建筑或场所,由于特殊的功能和属性,其中发生的活动相对单一(如北京紫禁城),更可能由于它们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相关(如北京与绍兴的鲁迅故居)而变为博物馆等,这样它们会承载一种绝对主导性的历史价值或集体记忆。但绝大多数历史建筑和城市会承担着多层次的历史记忆,具有多维度的遗产价值。譬如《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其核心价值与特色提炼为九个方面,包括: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古迹”;二、“丰富的岭南文化和重要的文化地位”;三、“辉煌的港口历史和著名的贸易口岸”;四、“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众多的革命史迹”;五、“独特的岭南山水和优美的水乡田园”;六、“千年的商业发展和多样的商业街”;七、“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八、“全国著名的华侨城市”;九、“文化多元、风貌多样的活态遗产城市”[38]。
遗产保护与展示是用一个主题线索对不同历史遗存的全部或部分信息的串联与提贯。同一个遗存的不同信息被组合在不同遗存的集合体中,可以支撑起不同的历史叙述;这是遗产展示的主题线索与遗存本体信息的差别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就涉及两个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北京故宫和天坛,这就是一个以不同遗存信息的不同组合,反映不同遗产主题的突出案例。所以,处理好以时间为主要标准划定的文化遗产与特定主题为线索的遗产价值提炼与重构是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39]。不可否认,主题性价值的提炼可以深化人们对遗产内涵的认识,并使一些存在内在关联的散的遗产要素成为一个清晰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化的前提是,那些被纳入的散的要素已经被主动保护起来或“无意间”幸免于灭失。
如果我们接受卡尔“历史是一个选择体系”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遗产自身并不是“历史”,它是与过去人类的“活动事迹”相关的遗迹[40],它们曾经是(或者依旧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和平台。这些遗迹的保存是集体意志的体现,要将它们转变成“历史”还需批判性的研究和思考[41]。但是,在当代它们构成一种“记忆之场”。跟档案馆、图书馆等其他的“记忆之场”一样,它们为缺乏仪式感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仪式感,可以唤起社会的回忆[42]。
黑格尔指出,没有国家就没历史或历史意识[43]。国务院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中,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提出了“老城不能再拆……做到应保尽保”的要求[44]。这是我国从国家政治的高度指明了北京乃至全国历史遗产保护的方向,因为它是我们社会“乡愁”的载体,为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历史遗迹的信息可以唤起一个国家、民族、社会乃至个体深层的记忆,并具有广泛的影响。“乡愁”既与个人的经历有关,也与人们在成长、经历过程中接受的历史知识与教化有关[45]。它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一个民族、社会群体和个体的精神境界——“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是“应保尽保”遗产保护理念的根本所在。
结语
从我国聚落遗产名录的发展,我们亦可看出以下几点。
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一开始就注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强调历史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整体风貌的保护。根据《文物保护法》,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名城制度的设立,注重了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文物单位保护在方法上的区别。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内涵。《条例》第七条规定:“(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三)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四)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体系具有巨大包容性。它涵盖了国家、民族、社会不同时期的丰富的遗产。尤其是近年来公布的工业遗产名录、20世纪遗产建筑等,则更重点关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新近历史与集体记忆,而它们与今天的国人依旧有着真切的情感联系。
三、我国多样的城市历史街区和传统镇村遗产反映了我国丰富的地方历史与文化特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复杂的地理条件与历史背景使不同地域的聚落及其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央政权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遗产既是各民族统一融合的见证,也是未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源泉。
最后,《文物保护法》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强调:名城、名镇、名村的条件是:“文物特别丰富”。这一方面突出了重要历史遗存在聚落遗产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反映出它们在历史主题、线索、主体等方面的多元和丰富性,为未来不断挖掘遗存的历史信息及其价值留下了广阔空间。对历史遗存的意义与价值挖掘,要以过去、现在、未来前后相续统一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分析遗产信息及其所反映的史实,思考对当下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启示。我们必须看到,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随着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理论发展必然促进人们对不同保护对象的价值的认识的深化,会出现新的遗产类型。
我们应该在三个时段历史框架下,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的记忆,促进社会文化与精神的发展。中国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尤其是城镇与乡村聚落遗产,以其相对稳定的载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画卷和文化传统,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最为珍贵的生动素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中国式叙事的精髓。我们要保护好真实的遗产,通过合理的整合,使之成为文化回忆的空间,并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做到“润物细无声”[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