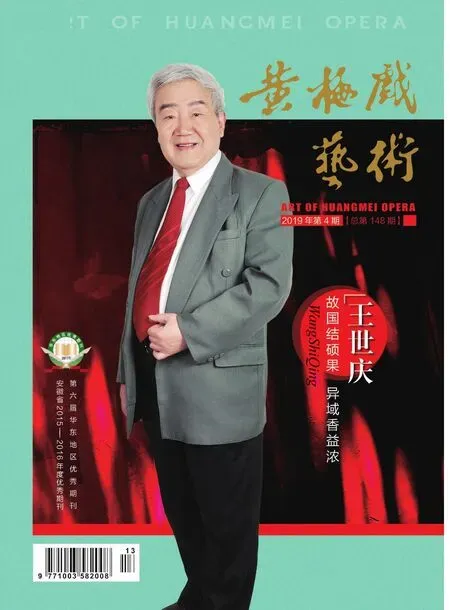摭取花旦“俏”之内涵—— 谈《卖水》及其他
□ 张 丽
1、谈到戏曲表演艺术花旦的“俏”,似乎打翻了心中的五味瓶,有一股子酸甜苦辣麻的感觉。在安徽黄梅戏学校学习之初,老师根据我的外形,在行当上就予以定位——花旦。这种一厢情愿的“归行”,于我真实的内心、个性十分抵触,因为我的性格趋于沉稳、内向,似乎属于“青衣”型的。但这一切,也是我在成长和成熟为“社会人”之后才明白的。因此,行当定位,让我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创作之路。
《卖水》一剧,由李梅青老师教授,由于该剧为我初习表演打下了基础,因此在若干年里,我坚持寻觅与《卖水》相关的资料,以充实自己的创作素材。
2、京剧《卖水》,是刘长瑜老师的看家戏,自从有了录像,该剧红遍全国。它是根据蒲州梆子《火焰驹·卖水》一折改编而成。剧中小丫环在大戏中纯属配角,而在此折中,俨然担纲为地道的主角。该剧与《女驸马》部分情节相似:礼部尚书黄璋,非但不容女婿(未过门)李彦贵的求助,反而趁机撕毁婚约,逼得李以卖水为生。小姐黄桂英思念夫婿(约定相见),主仆二人在后花园等候未果,梅英只得以点报十二月花名来拖延时间,缓解小姐急切心境。
梅英在表现这段唱腔时,极尽唱、做、念、舞之能事,淋漓尽致地数落着一年四季不同的花名。京剧艺术对唱念有严格的要求:“演唱的最高境界,如同说话一样自然;念白,则如同唱一样赋有旋律之美。”这不就是老师们常说的“唱如念,念如唱”的解读吗?梅英看似在为小姐解闷,实际她内心又是何等的着急,其间贯穿着一句潜台词:“小姐你莫急,听我报花名啊!”
梅英(唱)行行走,走行行,
信步儿来在凤凰亭。
这一年四季十二月,
听我表表十月花名。
由此从正月、二月、三月、四月……“这个李彦贵死到哪里去了?”梅英气得装模作样地跺跺脚,眼盯着花墙,耳听着园门外,仍然杳无动静,不得不继续唱道:
五月五正端阳,
石榴花……
刘长瑜老师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她在编演该剧中,配以“不太正宗的荀派”那独特的诠释功力。正如她曾经演过的李铁梅、春草、尤三姐、乐昌公主等不同旦行角色,在她的重新创作下现代、古代一个个美丽的女神鲜活起来。
正宗的荀派戏《红娘》,我也曾认真看过、学过,刘长瑜老师并不完全拘泥于流派的规范,而是从人物出发去剖析“这一个”,每个皆具韵味,每个都是这唯一一个。
3、有位老师,曾经为鼓励我深研花旦——闺门旦一行(我也演过《女驸马》公主、《西楼会》方秀英、《葡萄渡》沈秀英等闺门旦,赠我一首词:
眼儿媚 花旦
灵动鲜活率直娇,
双目下低瞧。
松驰带巧,
嗲羞透媚,
慎小魂飘。
指柔步碎清纯女,
飞凰欲还巢。
一颦一笑,
一沉一燥,
只有妖娆。
词的上阕,融于花旦的“娇、活、直”特点和闺门旦的“目下瞧”特征。道破花旦的“俏”之核心:娇——娇嗔、娇媚、娇嗲;活——灵活、灵动、灵巧;直——率直、爽朗、松驰。下阕涵盖了花旦——闺门旦的基本表演风格。每当接受一个新的角色,不由得述念着老师这首词对我的提示,力争从中挖掘戏曲艺术的真谛。
由于《卖水》的梅香打开了我日后表现角色的神秘之门,《夫妻观灯》中小六妻,我注重表现农村少妇手疾眼快,迷于观灯的喜悦情境;《小辞店》中的柳凤英,倾向于热情如炽,迎来送往的“扎干”的老板娘形态和伴以传统“摇旦”的表演元素。
4、近年,我在现代戏《老支书》中扮演“八姨”一角。安庆的父老乡亲闻说“七大姑八大姨”那心直口快,热肠暖心的中年妇女形象便活脱脱跃然于眼前。我们四个女演员,于剧中七嘴八舌、手舞足蹈,确为该剧起着调味品的点缀作用。但四个妇女,各有特色,“八姨”时有忧郁、自私、短视的另一面,已经融入到我对角色深层次解读之中。
回首已往,我所工花旦一行,与我个性相悖,却连闯数关,虽然有苦涩,很艰难,但也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