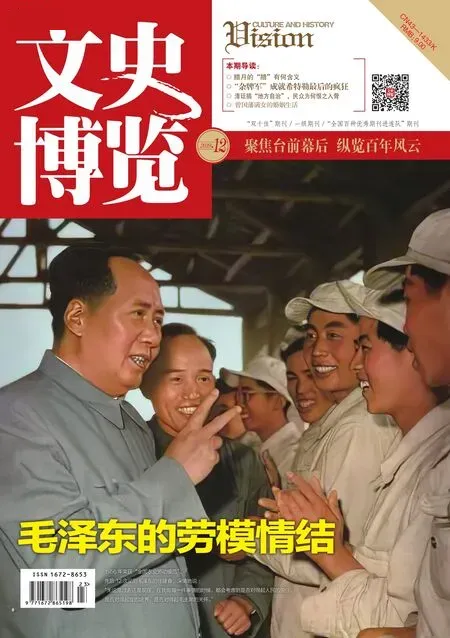70年前的高小生活
1949年9月,我初小毕业后,升入了离家三四里路远的湖南益阳县(即今天的益阳市赫山区)一个校址叫行宫坛的箴言一校。
“行宫坛”这个古怪的名字,我年长后才略识其义:“行宫”是为古代帝王外出巡行所建宫殿,“坛”是供祭祀用的土石砌成的台。
在我稀薄的记忆里,“行宫”建在一座小山前,旁有小溪汩汩流淌,它占地仅几十亩,但建筑却颇为讲究,殿内有七八间大小不一的房子,中堂神龛上供奉几尊神像。“坛”建在宫右首一块宽敞的高坪上。在旧社会,“行宫”是益阳县瑶华乡政府的所在地,解放后被用来办学,“坛”作升国旗的台。
我入行宫坛箴言一校学习时,湖南刚和平解放,未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天翻地覆,给我们所在的穷山村带来了崭新气象,也滋生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据我所知,在旧中国,我们这上百户的道子坪村(旧时属一个“保”),除地主子弟外,是从未有人进过高等小学的,因此,“高小生”成为乡间十分羡慕向往的称号,就像老一辈人对清朝“相公”(秀才之俗称)的向往一样。
在行宫坛箴言一校,我只学习了半年,但它却是开启我智慧之窗的重要契机和经受人生历炼的开始。回忆半年的学生生活,感触颇多,记得我入学后,曾遇到几个难题:
一是行路难。当时,山村的孩子上学是从来没有大人陪送的,山村没有修公路,我们一天来回要走七八里,而且道路多泥泞,特别是路过一个大塅时,倘遇隆冬季节,路上结冰,最容易出事。有次我一人经过大塅,就被凛冽的寒风吹倒,摔入稻田,油纸伞吹得不知去处,书包被水浸得透湿,引得我大哭一场。
二是吃饭难。当时学校未开餐,无法搭伙。我家穷,多是早餐后略带点供中午充饥的干粮,到放晚学时,已是饥肠辘辘。幸好满姑住在学校附近一个破祠堂里,她常要儿子喊我去她家吃点中饭。但满姑赤贫,有时还外出乞讨,我不便常打扰她。
三是听课难。当时多是大班上课,一个大堂里,满满当当地坐上六七十个学生。我因个子高,常被安排在后排,而我患过耳疾,左耳有些重听,故听起课来颇为吃力。
虽遇“三难”,但学校的一些新鲜事却像磁石般吸引着我,渐渐地,我就不把困难当回事了。
入校后,我遇到的头一件事,是学校更名和领导换人。原“瑶华小学”更名“箴言一校”(这“一”字很重要,说明它在小学中是居首位的)或“箴言完小”,原校长谢亚成(据了解他原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被解除职务,校长由原语文教师张赛迁(后改名张志远,升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担任。听人说,箴言一校于1949年5月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党员有七八个人,多是本校职工。令人惊异的是,谢亚成之子谢某与父同校,也是共产党员,这种“红”与“黑”的对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箴言一校是中共益阳县工委的一个重要据点,故常有身穿灰色军装、头戴五角星的人出入。记得有次我在校门口歇凉时,看到一个骑黑色大马、身材魁梧的大汉由一名勤务兵跟随,来校办事。旁边有位知情者对我们说,这是新任县长董早冬。听人说,他是南下干部,文化程度不高,批示文件多由秘书代劳,但他性格豪爽、办事果断。这是我出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位“高官”。由此,我想起乡间一些人说的话:“共产党来了,黑脚杆子会真正掌印把子了。”
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骑“眼镜车”(自行车之俗称)的中年妇女来校找张书记。这位中年妇女蓄短发,身着列宁装,脚穿草鞋,胸前插支钢笔,一副乡镇干部的模样。旁边有人称她“肖主任”,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新社会“半边天”的妇女真的翻身了,但更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年,这位“肖主任”竟成了益阳县的县长,而且连任五届,历时十余年。
在箴言一校,我开始学习到一些新课程、新教材,如语文课,头一篇是《开国大典》,书中还有胡绳的短论《“想”和“做”》、何其芳的诗《生活是多么广阔》、叶圣陶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等,这些作品都被列为精读课文,它在我稚嫩的心中埋下了追求美好志趣和情操的种子。除语文外,学校还开设了“自然”“体育”“音乐”等课程。
“自然”对于我来说是一门崭新的课,由这门课,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有五(七)大洲四大洋,有南极、北极,气温有温带、热带、寒带,还有为区分地球表面东西南北距离而设的经线、纬线等。这使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稀奇事。老师讲雷电一节时,我听得格外细心,因为乡间向有“雷公电母”的传闻,特别是把人遭雷击说成是对坏人最厉害的惩罚。而此时,恰遇我满姑的一位邻居某日下午上山砍柴时遭雷击。据满姑说,死者是一个50来岁的农民,忠厚、老实,从未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显然,他绝非恶贯满盈的坏人,却为何遭此惨死?我学了雷电知识后,略知电荷、正负电、电流等原理,知道“火花放电”等现象,由此而知,这位农民是遭遇强电流致死。从此,我再不相信“雷公电母”的胡话了。
学校的体育课,除练习体操外,大多是教学生打篮球,担任教学的何奇锋老师可真是名如其人。这位人高马大的老师,打球时多充任中锋,他左旋右转,动作灵活,奔跑似风驰电掣,令人称羡。由此,我成了一个“篮球迷”,而对原来喜爱踢的小橡皮球则不屑一顾了。
音乐课上课不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附近育才中学的学生来校的一次表演。他们演出的均是延安时期的一些优秀节目,如秧歌剧《小放牛》《王二小放牛》《夫妻识字》和歌曲《南泥湾》《信天游》《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作品与我过去在木偶、皮影戏中常看到的哪吒闹海、八仙过海等大不相同,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演员们淳美的歌喉,曼妙的舞姿,带有泥土气息的表演,常引来满堂喝彩。
箴言一校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新招。如算术教师在破解难题时,总是先由他讲解原理,作些解题的启发,然后要学生举手作答。当时,有个叫张润春的男同学,人很机灵,是我们班的数学尖子。每次老师列出难题要学生回答时,他都是率先举手,自告奋勇,登台用粉笔演算,并作说明。老师称赞他是“鬼才”。
对学生的文化成绩,学校于期末公布一次大榜,以学期积分多少排列名次。这方法是否妥当,或有副作用,见仁见智。但从我个人来说,受了一次刺激,还是获益多多的。记得我们年级有同学一百二三十人,我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看这张大榜,看见自己排在第三十七名,虽有点失落感,但仍坦然。
接着,我又着重查看榜上前五名的名字,记得前三名是朱萼华、陈百千、卜才英,第四名已记不清了,第五名是张润春。
这几名年级高材生,自我从箴言一校与他们相别后,风流云散,各在一方,未有来往,但多年来,我总系念着他们。经反复打听,我得知朱萼华曾考入华中某大学,毕业后分在湖南省水电厅工作,是位高级研究员,曾率团去美国参观、访问;陈百千背着父亲有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经艰苦奋斗,在武汉某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名校益阳一中任教,是位资深的中学教师骨干;卜才英因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她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后与当地一个乡干部结婚。不过最近听乡人说,卜才英、陈百千因过度操劳和乡间医疗条件欠佳,前些年先后病故了;张润春出身中农家庭,可能是家庭景况不好,未能升学,回乡后他在生产队当过会计、队长,虽工作称职,但终因儿女太多,家累甚重,只60来岁就病故了。
由此,我还联想到我在蜚英中学时同班的女同学邓菊莲,菊莲是位作文高手,她的习作每次都被老师作范文评讲,不知什么原因,在二年级时,她突然休学了,以后的事情不得而知。
想到这几位中、小学时的精英的不同命运,我感慨不已。古代有“飘茵落溷”的典故,其意谓人之富贵贫贱实出自偶然,而非命定,我不知道这解释是否适合我曾敬佩的这几位朋友,或有其他更合理的诠释。
离开行宫坛已是70年了,物换星移,虽然作为历史的陈迹来说,它已空无一物,但我却始终系念着它。往事历历,每当我记起它时,那黄墙碧瓦的屋舍,那红得似火的丹枫,那像天使一般活泼蹦跳的莘莘学子,那学舍里琅琅的读书声,总浮现在我脑海,就如同昨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