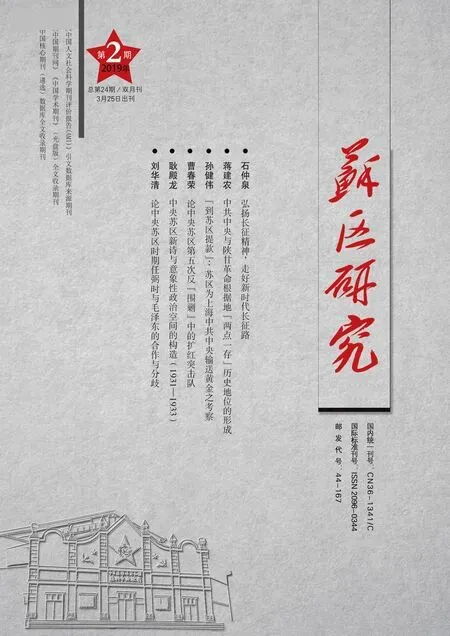中央苏区新诗与意象性政治空间的构造(1931-1933)
提要: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来阅读1931年到1933年的中央苏区新诗文本,可以看到在世界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拥护苏联”等观念涂抹的苏区空间里新诗作者所持的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立场,并进而探究出在国共两党的对抗性空间里,中央苏区新诗“反帝国主义国民党”核心主旨出现的原因,加深对中央苏区新诗文本中“祖国”“红旗”“鲜血”等意象及黑暗和光明截然不同的精神所指的产生之认识。反过来,中央苏区新诗营造的这种精神与意象也再生并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治空间的革命色彩,让苏区空间带有鲜明的中共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特点。
在当今的新诗研究领域,苏区新诗受关注的程度相对较低,这不仅因为苏区新诗在整个苏区文艺中所占的比重小,而且因为苏区新诗在今天看来艺术成就不高,口号化、标语化、歌谣化倾向明显,同时影响力较之于同时期上海中国诗歌会的普罗诗歌,显然更逊一筹,因此有些诗评家在研究三十年代新诗时对苏区新诗着墨很少,甚至忽略。就拿2017年新出版的一部《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来说,偌大的集子,专门研究中央苏区新诗的文章仅有一篇[注]邓家琪:《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道路——谈谈苏区新诗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23页。,而且诸如此类的研究主要关注苏区新诗的题材、内容、艺术特色以及政治宣传、教育民众功能等,整体看来大多侧重从文学角度研究,而从历史角度对其某些意象和精神产生之原因的透析却相对较弱。其实,关于中央苏区新诗,我们不但可以从文学艺术角度去观察诗歌的特色或者进行诗歌发展脉络和主义的探源,还可以应用某些新理论、新方法如采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去挖掘其某些历史特点,对其进行更有力的历史考察。
作为20世纪初最先关注空间理论的学者,列斐伏尔打破对空间既定的地理方面的认识,创造性地认为空间是容纳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场域。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三种形式:“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注]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 Blackwell Press,1991.p.42.,空间实践指的是空间的物质特性之产生,空间表征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想象空间之营造,而表征空间则是前两者的完美结合。同时,列斐伏尔还指出“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注]Lefebvre·H.“Spatial Planning: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in Richard Peet(ed.) Radical Geography: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Chicago:Maaroufa,1977.p.341.。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学者援引其理论进行各个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反观中央苏区,我们也可以应用此理论,而且中央苏区空间和列斐伏尔的上述理论内涵非常契合,实则一种物质和精神结合的双重空间,在其中的中央苏区新诗一方面受其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影响产生特定的精神主旨和意象,同时这种精神主旨和意象又加强了苏区空间的意识形态色彩。由此,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引入中央苏区新诗研究,我们会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的历史发现。
一、“世界革命”的政治性空间指向
十月革命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以及退出一战等原因,苏俄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新生政权面临威胁,因此,反帝成为苏俄的头等任务。一战结束后鉴于欧洲国家的革命形势,苏俄幻想苏维埃革命可以遍布欧洲从而保卫自身新生政权安全,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即是体现苏俄进行这种权力想象的工具式机构,苏俄借以同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下的“国际联盟”对抗,积极向外输出苏维埃式的革命。“为了推动各国革命,苏俄新政权不顾历经战乱的俄国民众仍在严重饥饿之中的困难局面,倾尽国力,甚至不惜秘密变卖沙皇及俄国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以筹集援助他国革命党人的巨额经费”[注]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帮助其他国家组建共产党进而推动革命。但一战后,欧洲带有无产阶级色彩的革命如匈牙利革命等很快被资产阶级镇压或和平演变,而这时,列宁注意到亚洲的革命浪潮,如朝鲜、中国等,尤其是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因此,在欧洲革命无望后,苏俄试图通过支援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推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保障新生苏维埃政权安全,很快,苏俄开始派驻共产国际成员携经费来中国帮助激进的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7月23日,由共产国际成员马林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
然而中共成立之初,苏俄(联)考虑到中共力量很弱等因素,不适合立即建立苏维埃,于是积极指导国共合作,希望借此帮助中共发展力量并把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由于阶级立场差异、党内合作的诸多弊端、农民运动的分歧以及孙中山乃至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拒绝接受苏联意识形态等原因,[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国民大革命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下最终失败。之后,苏联为了摆脱责任把革命失败罪责归咎于陈独秀,“在失败中维持其一贯正确的外表”[注][美]本杰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并试图利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时机挽回面子,但事实是这些以进攻中心城市、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暴动都失败了,接下来苏联不得不调整政策,将目光投向农村苏维埃运动。1928年初,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在乡村之中也要建立苏维埃”,进而提出“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政权”。[注]《附: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1928年3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随后的几年,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经过发展,力量逐渐壮大,加上不断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声名大噪,为后来在此建立中央苏区政府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它的成立进而“标志着中央苏区正式建立”[注]梅黎明:《伟大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与此同时,伴随着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环境日益凶险,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开辟的中央苏区显得愈发重要,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
这样一来,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的重点关注与援助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以例为证——1933年8、9月份,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转交给中共的经费就包括“24.56万法郎、6.1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注]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1-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且不说这笔费用能不能真正到达苏区,单看经费的庞大数目就足以看出苏联对中央苏区的支持。其实,在苏联给我们倾尽全力支持中共革命印象的背后,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一直在发挥着指导作用。在列宁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要想保全革命成果,必须进行反帝的“世界革命”,以此推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战胜帝国主义,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我们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提及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不得不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没有祖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页。观念,两者紧密相连。何谓“工人没有祖国”?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看来,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这种利益是超越民族或国家的,那就是无产阶级利益,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靠消灭国家才能实现,所以,无产阶级只能讲国际主义,不应该讲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达到世界革命的目标。用列宁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8页。
为了实施该理论,苏俄不间断的对中国进行政治权力渗透,而且大力宣传列宁的反帝主张,从帮助建立中共,再到促成中央苏区的建立,都是苏俄(联)进行自保和输出意识形态的体现。在当时反帝也是中国人民的核心任务,尤其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之后,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随之破灭,从而引发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各种欺压行为日益加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书写的“各种帝国主义侵华史连篇累牍”的出现,“数量之多,令人震惊”[注]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打倒帝国主义”成为爱国民众的重要口号。这样的情况为苏俄反帝的“世界革命”理论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土壤,而作为苏俄直接领导下的中共,自然更积极地实践这种理论,贯彻这种意识(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共“自恃与世界革命的直接联系,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自始即甚明显”[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55页。,不断与国民党进行革命话语权的争夺;而在1920年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中共也曾一度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依归”[注]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3页。,主张外蒙古“民族自决”)。
当这种理论变成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进入中央苏区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的马恩像、列宁勋章以及以无产阶级领袖命名的物质性政治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实践”)的产生,同时伴有弥漫着世界革命意识、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观念协同无产阶级反帝立场的精神性政治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言的“表征空间”)的出现,而这两个空间在中央苏区新诗里都得到了展示:
把红旗插在全中国的地面上,
使我们劳动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那时候我们的胸坎上,
要挂上光荣的列宁勋章![注]时英:《纪念三八》,《红色中华》1933年3月23日,副刊(三八特刊),第1版。时英,原名不详,苏区新诗诗人。
你看红色中华,
我看青年实话,
他跑来笑哈哈!
列宁室真好呀![注]洪水:《在列宁室》,《青年实话》1933年3月19日,第2卷第1版。洪水,原名武元博,越南人,1926年加入中共,苏区时期任红军学校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工农剧社社长。
建设苏维埃,
工农来专政,
实行共产制,
人类庆大同,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的成功![注]《工农暴动歌》,《石叟资料》(陈诚文库)影印件,第6卷0409号。
前两节诗中“列宁勋章”和“列宁室”两个意象的出现,说明在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央苏区物质性政治空间的产生。作为世界革命理论的坚持者和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的地位毋庸置疑,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支部,中共理所当然把这位世界革命理论者奉为偶像,而且用偶像驯化群众——“最好要尽可能的挂起马克思列宁的像,使群众在非常喜欢和快乐的时候,还可以不时看到革命领袖的形象,而不致一时会把革命忘掉”;此外,中央苏区陆续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小学”“列宁俱乐部”“列宁室”[注]周平远:《从苏区文艺到延安文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40页。等等,这些政治、宣传乃至教育机构也无不透露出领袖崇拜意识和仪式色彩,其实这些机构名称的出现本身也都是世界革命理论和意识的变形产物。反过来,第三节歌谣体新诗中出现的“人类庆大同”字样,实则是世界革命终将成功的意识在物化的氛围影响下得到升华、认同与再生后的想象空间,物化与精神两者相结合,就出现了列斐伏尔所讲的空间最高形式——“表征空间”。
不仅如此,让我们再看第一节诗中的“红旗”意象,这个带有鲜明无产阶级特色的物质性旗帜也很好地体现了和苏联红旗、红军的联系以及浓厚的“世界革命”色彩,而单说“红”这个字,自从十月革命开始就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性颜色,无论苏俄还是后来的中共,在旗帜、军队、荣誉乃至身份上都用“红”表示,以示和其他政治力量区分,成为政治身份的标配颜色。以致于后来“一些红色之物”“如用红布、红纸、红字等”做成的标语都被国民党当做“赤化的象征而禁用”[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55页。,足见红色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革命的影响力。
按照如上理解,我们是否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苏区的新诗也是一种融合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双重空间,在诗歌里,诗人一面建构精神上的世界革命意识,同时又亲身感受着苏联光环影响下的中央苏区物质性空间的魅力,二者在诗人的心里达到完美的融合呢?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们看下面这节诗:
十四年前的今日,
苏维埃联邦在西方诞生,
今年的今日,
苏维埃中国又在东方降临:
这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信号,
这是中俄工农(阶级)头颅热血的结晶!
看啊!世界的无产阶级者被压迫的人民,
哪个不在那里庆祝它的诞生,
因为它呀,将把恶魔们束缚我们的锁链捣碎,
因为它呀,将把敌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毁灭干净![注]黄克诚:《庆祝我们的生活》,《武库》1932年10月,纪念十月革命专号。黄克诚,苏区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
诗中“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世界的无产阶级”相互照应,“恶魔们束缚我们的锁链”和“中俄工农头颅热血”构成因果关系,歌颂“苏维埃中国的诞生”目的是最终要“把敌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毁灭干净”,从这节诗可以看出,在高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央苏区空间里,苏区新诗诗人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立场,而这种立场又恰恰指明了世界革命的方向和诗人自身对其的理解。无独有偶,下面两节诗,同样的无产阶级国际立场一目了然:
世界革命激昂地歌着
帝国主义入墓曲;
繁荣着社会主义的工人祖国,
正奏着凯旋的交响乐;
苏维埃红军的洪流
将泛滥到全中华。
今年的“五一”
更急剧地击撞着
帝国主义的丧钟,
万国劳动者围绕着
“五一”的赤焰,
高呼:“解放万岁!”[注]思凡:《到处是赤焰——纪念今年的“五一”》,《红色中华》1933年4月23日,副刊(红中文艺副刊“五一”纪念专号),第1版。思凡,原名不详,苏区新诗诗人。
一八八四年的“五一”,
美国芝加哥工人大团结。
举行示威向资本家斗争!
牺牲了无限的生命,
流了不少的工人的血液,
这一天终于变成了——
世界工人共同的劳动纪念节!
一九三三年的“五一”,
世界工人团结起,
拥护祖国——苏联和中国革命,
同资本家作坚决的拼死斗争,
反抗帝国主义血腥的屠杀和压迫![注]斯顿:《红色“五一”》,《红色中华》1933年4月29日,第2版。斯顿,原名不详,苏区新诗诗人。
前一节诗开头即点出用“世界革命”埋葬“帝国主义”,继而“万国劳动者”实现“解放”,后一节诗借助回忆1884年的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来衬托1933年的五一劳动节,这不仅是在讲述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及发展,而且在集中表达对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渴望,两节诗都站在和黄克诚诗一样的立场——无产阶级国际立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一起反对帝国主义。诗人在此将物化的无产阶级红色旗帜、革命火焰、红军洪流转移到苏区空间内,而本身这些物化的空间自身又是诗人在精神层面构造的想象空间,于是,世界革命的政治性空间指向便明确了。
不过,此处稍有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变化,那就是在这首新诗中无产阶级居然有了祖国——“苏联”,这个论断来自于“繁荣着社会主义的工人祖国”和“拥护祖国——苏联和中国革命”两句诗,前一句稍稍琢磨,可猜想此处社会主义工人祖国指的是苏联,而后一句直接点明了这个猜测。这让我们不禁诧异起来,在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不是没有祖国吗?为何此处有了呢?既然无产阶级有了祖国,那还算不算无产阶级国际立场呢?
二、苏联作为“工人祖国”的空间意象
按照世界革命理论,苏俄在列宁时期不间断的对中国进行物资援助和政治权力渗透,从亲自指导中国建立共产党,再到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从共产国际源源不断地给予中共中央活动经费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热情地培养中共干部,这些都是苏俄进行自保和输出革命的体现。然而,这种“世界革命”方式在列宁逝世、斯大林上台后开始逐渐变得以苏联为核心,不再像列宁时期那样不顾国家利益。尤其是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伴随着斯大林逐渐改变列宁新经济政策而试图通过计划经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单一公有制方式把苏联拉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苏联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在民族领袖领导下的民族国家,它自身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来了”,“不可能像列宁时代的苏俄政权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了”[注]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23页。。不但如此,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在苏联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苏联的存在才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保障,而不是其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是苏联存在的保障,如此说来,也就不难理解当李立三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际妄图“以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注][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而被苏联抛弃的原因。
事实证明,机敏务实的斯大林确实有自己的高明之处,他以自己的方式印证了斯大林模式的可行和强大威力。1932年,苏联成功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但成了工业先进国,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紧接着,1933年苏联又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但没有危机,而且猛烈的向前发展,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注]柯华:《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404、302页。鉴于苏联高速的工业化成就,斯大林威望快速提升,紧接着,斯大林开始了大清洗,原来在打击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处于同一战壕的布哈林就是在此时因对富农及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而被斯大林打压下去。斯大林政治权力的巩固在文学领域也有表现,那就是原来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被压制,高尔基重新被抬举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取代了“唯物辩证法”,成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后被周扬介绍到中国来,深深影响了左联文艺。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逐渐改变了列宁的“世界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里面的部分内容,在提高自身经济实力的前提下,让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团结起来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斗争,另一方面让各国无产阶级认同“无产阶级有祖国”,那就是通过五年计划而很快实现工业化的“苏联”(笔者查阅了从1929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很多宣传文件,发现1929年到1931年底很多文件最后结束语都以“世界革命万岁”口号为终,但1931年底以后便不再明确出现该口号,而“武装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或者“武装拥护苏联”数量明显多起来[注]柯华:《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第245-370页。)。此时,苏联建立起了认同自己的国际立场,并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影响使得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随之生成相应的认同苏联为无产阶级祖国的想象空间,于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就变成了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上面讲到的黄克诚那首新诗在1933年出现“工人阶级祖国苏联”的原因了,同样的,再看下面这首诗:
墨索里尼
东奔西走,
组织四强会议,
把欧洲反动势力团结一起,
为了挽救动摇崩溃的资本主义,
更像疯狗般向苏联乱咬乱吠,
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都准备好武装保卫工人祖国;
他们说:
滚开,法西斯蒂!
不准你
侵犯苏联一寸土地![注]许雷:《滚开,法西斯蒂》,《红色中华》1933年5月5日,第4版。许雷,苏区新诗诗人。
通过苏区诗人许雷这首《滚开,法西斯蒂》,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在经济大危机时期,在法西斯主义崛起并将矛头指向苏联的时候,世界无产阶级对保卫祖国“苏联”的一种急切的心情,接下来这首诗强化而且印证了这种心情:
我歌颂啊,五年计划!
我把这首诗献给全世界的劳苦人民。
我要用这首诗激励他们,向他们招呼——
为得守卫你们的祖国苏联,你们都准备好了么?[注](德)培赫尔:《我歌颂五年计划》,《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4日,第7版。培赫尔,无产阶级诗人。
借助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培赫尔的诗,祖国苏联再一次得到认同,这从侧面烘托了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心情,这不是改变了“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而是在认同通过工业化建设强盛起来的苏联为祖国的前提下,烘托世界革命,烘托“全世界劳苦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苏联,仍然是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立场。在此,民族国家立场让位于国际立场,无论是中央苏区的诗,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诗人的诗,都分明指向这样一种国际立场,这也是开头列宁所讲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说,斯大林并没有从精神主旨上改变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观念,而是在加强苏联民族国家的前提下进行了政治权力渗透与影响,再生了“工人祖国是苏联”的政治性空间。
除了上述新诗,苏区各种文艺形式里那些明确的“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注]《“八一”纪念的口号》,《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等标语口号等也是对这种政治性空间构造的很好证明。总之,1931年底以后的中央苏区受苏联影响,世界革命理论仍然继续,但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已经置换成了“无产阶级有祖国——苏联”,同时“祖国”正在成为中央苏区新诗中建构的重要意象,这一想象的空间意象从侧面烘托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权力渗透。
三、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对抗性空间表述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而且毫无疑问,“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注]高峰:《空间的社会意义: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探讨》,《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第45页。,这个解释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最合适不过了。作为俄式苏维埃革命的试验场,中央苏区实践了苏俄革命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因为中心城市暴动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中国苏维埃只能在农村开展,这和俄国有别;同时在建立红军方面,俄国是先全国暴动后建立红军,而中国则是先建立红军,而后试图实现全国暴动成功;另外,苏俄苏维埃运动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工人运动”[注]周平远:《从苏区文艺到延安文艺》,第5页。,而中国苏维埃运动却沾染了浓厚的农民气质,虽然二者都有工农联盟),并使中共带有目的性的在中央苏区这块根据地上构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空间。
在这种空间里,中共以农村作为根据地,以红军作为政治权力根基,以农民作为强大的后盾,承继并夯实中共二大提出的“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主张,进而对中央苏区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培养阶级认同感。在苏联“世界革命”、“保卫苏联”等观念的影响以及1929年到1933年国民党依靠德、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围剿苏区而中共“左”倾路线又在不断重演的情况下,中共自然会将国民党等同于帝国主义,进而将“反帝国主义国民党”作为这种想象空间的核心精神主旨,并为此大加渲染,甚至在“东北少壮派军阀张学良试图占有中东铁路事件”上也坚决支持苏联而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猛烈抨击国民党,抨击帝国主义,结果受到陈独秀的批评。[注](美)本杰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版),第118、119页。不但如此,在“肃反”和“打AB团”中,中共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有无产阶级国际立场起作用,让中共理所当然的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成同伙,反帝就得反国民党,反帝反国民党就是保卫苏联、保卫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有关这一点,苏区新诗中有鲜明的胎记:
可是我们也要准备开赴前方,
着上全副威武的武装,
去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
把红旗插在全中国的地面上,
使我们劳动妇女得到彻底解放。[注]时英:《纪念“三八”》,《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副刊(三八特刊),第1版。
帝国主义,国民党狗,
呸,残酷的野蛮的恶兽!
你们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注]小雅:《不怕你,刽子手!》,《红色中华》1933年5月14日,第4版。小雅,原名不详,苏区新诗诗人。
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我们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
我们是四万万人群中工农的总指挥。
数万万民众紧密的团结在我们周围,
全世界工人弟兄愿意做我们的前卫。
那帝国主义国民党——
就是我们唯一的阶级敌对![注]爱伦:《先锋队》,《红色中华》1933年7月2日,第4版。爱伦,原名不详,苏区新诗诗人。
在这三节诗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并列在一起,是因在当时国共对立的大背景下,中共受到了苏联反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把国民党当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当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但实际上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不能算作完全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且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时候,蒋介石政府还是力主抗日的,因此,不应简单将蒋介石直接归入帝国主义行列。
但从另一方面看,蒋介石在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面,暗中和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和解,然后毅然和苏联断交,间接促成国民大革命失败,这一点让中共付出了血的代价,再加上受到苏联反资本主义及“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中共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并列在一起便水到渠成。而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世界革命的火焰逐渐高涨,这再一次加剧了中共的不安,尤其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年轻的留苏派中共中央逐渐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他们对苏联的盲目追随,也造成了这种认识上的左倾。比如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对于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抗日,中共斥责其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是“沽名钓誉、图利谋财”,甚至认为“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注]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72页。,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共是把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一起作为反对对象来看待的。
其实,考虑到当时蒋介石对苏区的疯狂围剿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公开政策宣传,中共高度紧张有其原因,这种紧张背后彰显的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苏区的武力渗透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央苏区想象空间中不安的氛围,以致于苏区进行空间再造时,统治者有意制造出更多的象征符号,来进行对人们精神的控制,进而破解这种不安的氛围,更好鼓动民众,而这种由象征符号所构成的空间无疑就是列斐伏尔所认为的“再现性空间”[注]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述评》,《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1页。。
何谓“再现性空间”?起初,在中共控制下,苏区出现了由各种宣传战斗口号、苏联文化、马列画像以及俄式土地制度、商品买卖关系等所改造的苏区建筑、设施、田地、合作社等构成的物化空间,耳濡目染之下,苏区民众对这些物化空间产生了各种想象和经验,并且逐渐将一些实体的空间演变为脑海中的符号,比如看到马克思列宁像,就会产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等表征性的符号,而这时再进行宣传时,民众就会自然投入其中,由人们受物化空间影响而产生的与之密切联系的经验与符号化空间就是所谓的“再现性空间”(其实,再现性空间仍然是空间表征,只不过和空间表征稍有不同,空间表征的想象范围更大,它和物化空间的对应性没有再现性空间和物化空间的对应性强),它无疑加强了中共在苏区的意识形态领导。
拿新诗来说,将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一同划为敌人即是这种再现性空间下的产物,同样,苏区新诗中的语言暴力、歌谣对话及黑暗光明对立之图景也多半产生于这种再现性空间:
呵,数不清的一个个,
在你们刀下滚着的人头,
你们的嘴一口又一口,
喝着我们工农的鲜血,
不眨眼儿不叫腥臭![注]小雅:《不怕你,刽子手!》,《红色中华》1933年5月14日,第4版。
永远忘不了的红军胜利的故事:
活捉张辉瓒割下了那狗头,
沿着赣江漂流到各个口岸;[注]许雷:《回南昌——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六周年纪念》,《红色中华》1933年8月1日,第6版。
“人头”“鲜血”两个意象穿梭在恐怖语言中成为苏区诗人一方面反国民党、另一方面赞美红军胜利的极端表达方式,血腥的画面让人毛骨悚然,不过“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和“活捉张辉瓒”“割下头颅”[注][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确实照应了当时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再现性空间来自于当时的物化空间,针对性、再现感增强。
与上述血腥、恐怖画面相对的,苏区新诗里的“红旗”“赤焰”意象则代表光明:
小同志,
你们都是劳动的孩子。
敲着琴鼓,擎着红旗;
大家走得脚步整齐;
一面还吹着号声达达啼。[注]明:《欢迎小同志——给全苏区的共产儿童们》,《红色中华》1933年4月2日,第4版。明,原名不详,苏区新诗诗人。
去哟!去哟!坚决的当红军去哟!
一切都不要顾虑!
前面展现辉煌夺目镰刀斧头式的红旗。
是代表工农劳苦群众的标帜。[注]霭民:《快当红军去》,《红星》1931年12月30日,第4期,第1版。霭民,原名不详,苏区新诗诗人。
这已经不是一小颗火星,
一点子曙光,
这是满山遍野。
势如燎原,
到处都是的赤焰![注]思凡:《到处是赤焰——纪念今年的“五一”》,《红色中华》1933年4月23日,副刊(红中文艺副刊“五一”纪念专号),第1版。
第一节诗用一首儿童诗的形式赞美了革命后继有人,里面的“红旗”意象和第二节诗中的“红旗”意象一样都代表中共苏维埃政权,代表革命的种子和工农群众的理想;第三节诗用“赤焰”意象代表苏维埃革命,代表中共政治权力的扩张,是人们对未来憧憬的一种经验性想象,是对儿童活动、对参军景象真实物化空间的再现,光明色彩一览无余。由此看来,在中央苏区的再现性空间里,诗人们用严格的黑白分明、正邪两立的经验想象之方式宣传国民党之反革命,歌颂苏维埃革命和中共红军,其间伴随着言语暴力,以及代表敌人残暴屠杀工农的“鲜血”红色意象和中共革命正义的“赤焰”红色意象,虽然都是红色符号系统,但意象所指却截然不同,由此所造成的批判和歌颂的精神所指也就大相径庭。通过这样一种反差强烈的手法,苏区想象空间里所强调的苏维埃意识形态便有了附着,立场也就更加坚定,语言鲜活明白,散发着浓烈的阶级斗争气息。
“红军是工农自己人,
帮助红军是千该万该应;
那就得先耕红军公田,
优待红军家庭!”
他和她的壮丽歌音,
兴奋了远近弯着背儿的同志们,
大家便同声合唱一曲,
“赶紧插秧,增加生产二成!”[注]思凡:《插秧曲》,《红色中华》1933年4月29日,第4版。
你要知道:
战争不取得胜利,
终身要受苦恼——
地主要来收回你的田地。[注]加伦:《莫逃跑》,《青年实话》1933年2月26日,第2卷第1版。加伦,原名彭加伦,红二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
以上两节诗同样是苏区再现性空间在诗人文本中的投影,诗中对于耕作、土地关系等方面的描写用看似轻松愉快的口吻实则勾勒出了中共背后艰难的苏区开拓史和严肃的意识形态宣传,同时,民众对苏维埃土地革命的认识也在中共营造的物化空间里上升为再现性空间,成为诗人头脑中对“地主”“插秧”“红军”“田地”等具有总结性、经验性的认识,并将人们抽象出来的感情色彩,变成人们耳熟能详的山歌、口语形式,并借此警醒民众:拥护红军才能赢得光明,否则会两次跌入受敌人压迫的黑暗之中。
虽然于今天看来,这样的诗歌写作方式看似浅显易懂,没有多少艺术含量,但却最能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而且适合民众的欣赏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致,避免了艺术和人认识水平的分离,可谓苏区新诗具有自身特色的体现,这在后来的延安新诗中有更好的体现。
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不难发现,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下,中央苏区变得不再是单纯物质的、静止的地理区域,而变成了由苏联和中共主导的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性空间,这空间充斥着“世界革命”理论下的大量物化意象,如红旗、勋章、伟人像等等,同时又弥漫着诸如“祖国”“鲜血”“洪流”“插秧”等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色彩的精神性空间乃至和物化空间更具针对性的再现性空间,两者在中央苏区新诗中达到完美的结合。从1931年到1933年,伴随着苏联经济实力和斯大林政治权力的加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观念逐渐被置换成了“保卫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苏联”观念,随之而来的,是对反苏联的一切帝国主义的敌视,这其中就包含着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新诗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经常被关联在一起,“反帝国主义国民党”成为中央苏区新诗的精神主旨,背后则夹杂着苏区诗人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立场,在所有涉及到苏区和苏联的地方,光明扑面而来,而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着墨处,黑暗接踵而至,一正一反,明暗截然对立。
结合空间理论和历史背景,苏区新诗的立场、精神主旨、意象等得到了很好的揭示,这些因素出现的原因也在这些空间中找到了答案,由此,中央苏区的政治性空间在中央苏区新诗中得到了新生式的体现和移植。相对比于同时期中国新诗阵营里的其他派别,诸如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人群体,中央苏区新诗以其特有的口号化的、带有国际特色和斗争性特征意象的政治性叙述而独具一格,它和上海左联的中国诗歌会遥相呼应,但比中国诗歌会更加政治化,而且军事题材、生产题材、农村题材的意象明显区分于上海左翼诗歌中的城市意象、革命浪漫意象和工人意象。随着中共丢失苏区逐渐退往陕北并在延安落脚后,这一特色将延续,只不过,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崛起以及正确性的逐渐被证明,延安新诗将逐渐减少“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这一观念,减少国际化的苏联特色,而加强对本民族国家、中共政权及农村革命的歌颂与拥护,届时延安新诗将容纳苏区诗人、左联诗人乃至从国统区进入的自由派诗人(如卞之琳、何其芳等),而且将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以全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出现,洋溢中共的意识形态色彩,建构着代表中共对民族解放命运关注的政治性空间。
如此说来,作为体现中共在农村建立政权尝试的中央苏区新诗,其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对中央苏区新诗的研究将对于我们洞悉中共苏维埃历史、探析苏联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之关系、比较延安在左翼时期与苏区时期中共文化的异同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