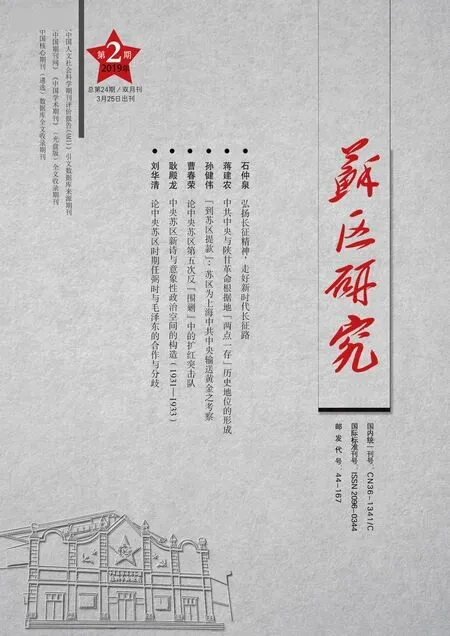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发生历程与社会价值
提要:中央苏区红色戏剧创作及民间普及,经历了直面传统、走出传统、形成具有独特革命特质和民族品格的乡村新戏的过程。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创作与上演,抑制了军民纯粹娱乐化的消遣倾向,动员了大家的参战热情;在同旧戏的博弈和苏区社会民众的互动中,演绎着革命文艺的价值参照,最终生成了一批剧情易懂又寓意鲜明,既结合乡村生活又深入民心的优秀戏剧作品。
武装斗争的“武仗”和发动群众的“文仗”是苏区革命发生和政权巩固的两个拳头。在中央苏区,为唤起军民的军事斗争热情和政权建设信心,改变苏区传统落后的、甚至是阻碍革命的封建观念,文艺战线上动员和传播功效相对显著的戏剧从红军队伍中发生并逐步走向乡土社会,成为宣传工作体系的重要一环。苏区红色戏剧[注]文中提及化装表演、活报剧、话剧、改编的传统戏剧、新戏、文明戏、革命戏剧,在这里同指“红色戏剧”。的研究启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以剧团或剧人为中心展开。[注]如汪木兰:《活跃在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和《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最大的戏剧团体——工农剧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汤家庆:《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教建设的贡献》(《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第2期)等,形成了较早一批研究苏区戏剧的文章。新世纪以来,学界进一步启开苏区戏剧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内容涉及红色戏剧的成因、特征、影响、启示及剧人的贡献、剧团的发展等。[注]王亚菲:《论苏区戏剧运动对当代戏剧形态多向度发展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钟俊昆:《论中央苏区文艺的创作主体与服务对象》(《嘉应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郑紫苑:《苏区戏剧教育功能:大众化与化大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江明明、刘魁:《新与旧:中共与民众对苏区戏剧的取舍研究》(《党史文苑》2015年第22期),刘魁、江明明:《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修辞学、传播学、图像学、社会学、文学等角度来剖析红色戏剧的审美内涵及发展轨迹,或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红色戏剧的乡村建构。[注]如吴超昭:《中央苏区文艺体制研究》(南昌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陶运宗:《革命与景观——苏区图像文化研究》(南昌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郑斐:《传播学视角下的苏区戏剧》(南昌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永华:《苏区戏剧与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互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郑紫苑:《从娱乐到革命:论中央苏区时期乡村戏剧的“政治化”实践》(《戏剧之家》2018年第1期)等。不难发现,从历史视域分析中国共产党建构新戏的政治场域以及红色戏剧同乡土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却相对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旧戏的解构、红色戏剧与封建旧戏的角逐、革命新戏建构的发展历程做一些学理性的研究尝试,以期再现红色戏剧与苏区社会的互动样态。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伴随红色革命的发生,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苏区乡村中新文化尤其是红色文化逐步兴起。革命化的红色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因其声形并茂、直观易懂的特点,短时间内就能达到吸引人感染人的效果,成为传递政治意图、鼓舞和动员群众、改造群众思想观念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苏区革命中的红色戏剧扎根乡村生活,结合革命场景和政治需要,对传统戏剧进行有益解构和重新建构,实现了从剧本改造到创作的蝶变,形成了话剧、小歌舞剧、活报剧、快板、双簧、相声等多种艺术形态。在此过程中,苏区戏剧的红色呈现及思想表达,也曾游离于革命及社会动员的历史主题之外,出现了意识形态功能娱乐化的偏移。随着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对偏移的纠正,红色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最终还是迈上了革命前行的台阶,成为苏区社会红色变革的合力之一,成为既具有高度革命和政治意识,又具有乡土生活和质朴情感的艺术作品和精神画卷。
一、直面传统:中央苏区戏剧的红色觉醒
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战争若要成功,需要拿枪的军队,更需要有文化的军队和人民大众的追随。随着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兴起,革命文化在战火中创生,适合革命战争需要的、形式多样的文明戏和改编的传统戏剧在同封建糟粕的较量中逐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接受,并在乡村社会中崭露头角。
(一)红色戏剧创生源自革命的现实需要
中央苏区农村被崇山峻岭包围,远离都市,“地权的分散、公田的发达,工商业的落后及相对闭塞的环境,都显示出赣南、闽西与外部社会的距离”[注]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这一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偏于保守封闭,“有些地方(宁冈的茅坪,遂川的黄坳水井等)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有些地方更还是杵臼时代,如山上的农民还是用手臼打米”[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洋货的冲击也使得赣南闽西地区工商业日渐凋零,大量工农失业,“迫而当兵做匪,做匪尤其容易,因此闽西就成了土匪世界”[注]《中共福建省委关于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1929年3月8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龙岩地区印刷厂1982年版,第37页。,这里可谓“匪军遍地,暴敛横生,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注]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加之地方势力独霸一方,剥削异常严重,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很难接触和产生进步的思想。鉴于此,发动广大百姓支持和参加革命,成为一件重要且亟需解决的事情。
早在1929年初,中共中央就已下发通告明确了争取群众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团结,如果没有广大群众斗争力量,尤其是广大群众还没有推翻统治阶级的决心和勇气的时候,就是反动统治阶级已经极易动摇,还是没有办法打倒他,还是不能有革命的爆发。”[注]《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1929年1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南下赣南闽西途中,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及张贴的标语,表明了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革命自觉。5月闽西第一个新剧团——新声剧团就演出了《弓铁缘》《武松打店》《薛仁贵投军》《打铁》等一批歌颂古代英雄的传统剧目,编演了《放高利贷》《逼债》《大秤入小秤出》《少年先锋歌》《妇女解放歌》《送郎当红军》等文明小戏,宣传土地革命斗争和红军革命事迹。红四军通过战斗实践,逐步建立起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范围的革命政权,进一步证明了“群众中的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注]《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66页。8月,福建省委给永定县委的信中特别强调要“扩大我们闽西土地革命的胜利到全省去,然就要注意宣传工作”[注]《中共福建省委给永定县委并转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最近的政治情形、省委对闽西各县工作的指示》(1929年8月7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168页。。在此背景下,鉴于戏剧的视觉效果、宣传对象的知识水准,简易的化装宣传在红军队伍中很快兴起。《古田会议决议》有关红军宣传工作部分指出:“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群众的化装宣传。”[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摘自《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29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地方上,负责戏剧排演的俱乐部、新剧团在闽西各区乡也逐渐建立,各种形式的剧目不断上演。12月底,龙岩县龙池区第十乡新剧团自编自演了《打倒帝国主义》《打破迷信》《无良心者》等新剧目。长汀县红坊区苏维埃剧团编演了《扩大红军》《老兵归队》等节目。
(二)左翼文化陶染了艺术与革命的结合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的迅速发展,国统区的左翼文化界受到很大鼓舞。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联合左翼文化界形成一条战线,进行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左联”是一个兼具政治性、文艺性的社团组织,提出了“文艺应该配合革命,紧跟革命,促进革命,做革命的武器和工具,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方面军”[注]王永华:《苏区戏剧与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互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第50页。的纲领。作为引领“左联”发展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于1934年2月到达红都瑞金,对苏区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戏剧组织的发展和戏剧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开创性的安排。他秉承“左联”的文艺政策,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他还指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为此他将蓝衫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学校里除普通班,还设立红军班和地方班。为使文艺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实现戏剧运动的正规化建设,瞿秋白主持制定了《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从而保证了戏剧运动的群众化、正规化、革命化,大大推动了红色戏剧运动的发展。同时,他还亲自选校与编辑话剧《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等,并亲自写序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使苏区戏剧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除瞿秋白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左联”作家也进入中央苏区,如吴亮平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财经部长,李一氓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潘汉年1933年5月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冯雪峰1933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长和副校长。这些作家汇聚中央苏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央苏区戏剧的快速发展。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部分戏剧家的回国等,也助推了苏区戏剧的革命化发展。在革命文艺大力发展的趋势下,1931年1月“剧联”成立,选举产生了以田汉为首的执行委员会。“剧联”的战斗任务是在“白色区域”中开展工人、学生、市民和农民的革命演剧运动,注意从基层中挖掘革命的作品。1931年,李伯钊从闽西转战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曾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李伯钊,最早把苏联的活报剧这一艺术形式介绍到苏区。她排演的歌剧《战斗的夏天》、话剧《最后的晚餐》《黑人吁天录》等作品,结合了当时的战斗情景,主题鲜明、生动活泼,受到苏区群众欢迎。沙可夫于1932年到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等职务,积极从事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他创作的剧本《北宁路上的退兵》《我——红军》《我们自己的事》等,有力配合了地方工农的武装暴动,成为中央苏区早期红色戏剧中的杰出作品。
这些承载着时代使命的苏区红色戏剧,深受左翼文化的陶染,冲破了传统束缚,“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样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注][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6页。,形成了革命战争情景中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风格。
二、迈向交锋:中央苏区戏剧的光荣使命
中央苏区乡村革命发生之际,受阶级觉悟所限,普通红军战士和一般民众关注的仅仅是戏剧的纯粹娱乐性。而中国共产党因革命和政权建设的需要,注重把革命和进步文化元素注入对旧戏的改造之中,进行新戏创作和宣传动员。由于观众和红色戏剧创作者之间的相互心理需求无法在短期内达成默契,尽管文明戏不断创作和上演,但是封建旧戏依然屡禁不止,文明戏与旧戏之间的博弈一直存在。出于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对旧戏剧进行有目的的改造,“她一面输入无产阶级的意识,一面却猛力的打破群众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注]《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节录)》(1929年12月26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18页。,在革命进程中建构苏区戏剧的生活样态。
(一)新戏进村入户与旧戏屡禁不止
“由于苏区从一开始起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的规模上扩大革命”,并夺取革命的思想高地,打破一切束缚人们思维的陈规陋习,形成适合苏区发展需要的先进思想。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之际,就“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注][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374页。。《古田会议决议》之后,中共的宣传工作发生了巨大转变,红色革命中心区域内“每逢纪念节的文明新剧、革命小调都普遍的有”,“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注]《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55-356页。。新戏剧的演出与宣传无疑收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凡是带有封建性、剥削性,有悖于战争动员,不利于革命战士精神风貌、思想境界、革命信念和革命斗志提升的娱乐性节目都被苏区政府禁止演出。
实际上,对这种政治功能突出的戏剧表演,军民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接受过程。潘振武回忆:“红四军最初演戏纯粹是一种娱乐形式,最流行的是花鼓戏,一丑一旦扭扭捏捏登场,演唱的内容不外乎‘情歌’‘情妹’之类平庸低下的陈词滥调,以后逐渐发展为文明戏。”[注]潘振武:《战歌春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到1930年下半年,红四军战士的娱乐节目中依然有一些带有封建性质的花鼓戏。由于封建传统根深蒂固,革命新戏在一些民众心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痕,那些被群众熟知的封建旧戏总是无法完全禁绝,有时还甚嚣尘上。
作为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和政治认知的革命团体——苏区俱乐部,在发挥革命动员、纠正戏剧纯粹娱乐化问题上的作用也是有局限的。“在乡村,大部分的俱乐部,偏重在娱乐,忽视政治及其他文化工作,具体的表现是俱乐部只有中乐及改良的旧戏,甚至就演封建式的旧戏。”[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1933年6月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1页。俱乐部的晚会,很多时候“只做老戏、打花鼓、唱京调、跳舞(中国式的),真正有革命意义的新剧和歌曲很少表演,更谈不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形编些活报表演”[注]《怎样去领导俱乐部列宁室工作》(1933年7月12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4页。。“在赣南、闽西农村地区,活跃着台阁戏、花朝戏、采茶戏、东河戏、木偶戏以及香火龙等传统剧目形式。这里戏台遍布,演戏之风盛行。”[注]王永华:《苏区戏剧与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互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第51页。纵使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逼近,“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已摆在党的面前,放到党的工作日程上了”的危机关头,封建旧戏在红色戏剧的浪潮中依然时有发生,从“1933年9月到10月,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有瑞金北郊上中乡第二村、于都县段屋区段屋乡胡公庙、西江县宽田区令泉乡等几个地方上演封建旧戏”[注]王予霞、汤家庆、蔡佳伍:《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可见,解决新旧戏的冲突,推出更多的红色戏剧,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融入到革命实际和民众生活中去,一直是中共和苏维埃政府文化宣传的一项重任。
(二)政策推动和理论认知上的新旧博弈
直面传统的苏区红色戏剧创作进程中,地方党和苏维埃政府加紧破除迷信及废除旧礼教的宣传,文明戏在扩大宣传范围、建立健全宣传组织、完善政策法规、强化理论指导等方面,逐渐改变着苏区民众对旧戏的情感依赖,并在革命实践中与旧戏展开实战。
首先是建立相应的戏剧组织和制定法规推动新戏创作。早在1927年7月,江西省委通告就指出,“在农村中应尽可能的组织新剧团”[注]《中共江西省委通告(第二十五号)——为什么要发动秋收斗争和如何发动秋收斗争》(1929年7月12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版,第39页。。1929年7月,上杭县才溪乡暴动成功,即组织俱乐部,新剧团有三十多人,在俱乐部内演出花鼓新戏、白话剧。1929年12月底,龙岩县龙池区第十乡成立新剧团,组织新戏演出。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中特别强调“各县要组织新剧团,表演新剧本”。1930年9月,龙岩县成立了革命剧社,下设化装、歌舞等八个股。此后,上杭县、永定县、连南县等都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各地文化建设的决议,要求区、乡建立大规模的新剧团、俱乐部,使之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的阵地。到1930年底,闽西的新剧团、俱乐部遍地开花。1932年初,以开展戏剧活动卓有成效的红军学校俱乐部为基础,经过统一整合,在瑞金成立了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红军学校——八一剧团。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下,同年9月,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建立工农剧社总社,并在各地建立分社和支社。为提高苏区剧团的演剧水平和培养戏剧人才,工农剧社总社于1933年4月成立蓝衫剧团(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前身)。同时期,蓝衫团训练班改名为蓝衫团学校,同年4月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团长和校长均为李伯钊担任。截至1933年5月,工农剧社分社“计有汀州,叶坪,红校,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等六处,约会员六七百人”[注]《工农剧社成立各地分社》,《红色中华》1933年5月20日,第4版。。关于剧团、剧校及俱乐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也相继出台,如《区乡村俱乐部组织系统与工作任务》(1933年4月23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教育部编)、《俱乐部纲要》(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工农剧社剧章》(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苏维埃剧团组织法》(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1934年3、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等,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对戏剧宣传工作进行提纲挈领的规划,保证了戏剧宣传正常化、高效化运作。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较多者建立俱乐部,人员较少者建立列宁室。红军中则以师为单位设立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1934年初,仅“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2391个乡中,有俱乐部1656个”[注]王予霞、汤家庆、蔡佳伍:《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第58页。。工农剧社与各地俱乐部、列宁室通力配合,积极开展苏区的戏剧运动。
其次是强化政策保障和理论指导。中共的各项决议的出台对苏区文艺宣传工作发展的指导作用较为突出。从中央层面看,1931年《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就强烈批评在立三路线的指引下忽视革命宣传、放弃革命宣传的状况,并主张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和游艺会晚会,在俱乐部下应该设立演剧组等。有关赤色工会的宣传工作,《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节录)》中提出要建立工会宣传队、俱乐部等,扮演新剧、化装演讲以扩大宣传;农业工人工会的戏剧宣传工作方面,《中国农业工人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决议案(节录)》中强调建立农业工人俱乐部,尤其是流动剧团、化装演讲等,1933年5月24日,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提出了要关注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的戏剧宣传工作。从地方上看,《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节录)》中指出,要尽可能组织新剧团文艺团体开展宣传工作。《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节录)》,对俱乐部及戏剧宣传也给予相应的指导。在理论指导上,张闻天着重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批评宣传形式的单一性,提出宣传要打破传统的藩篱,利用戏剧等新颖的方式,改变宣传内容过于呆板的形式,强调把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注]张闻天:《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932年11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51页。杨尚昆同样提出,“宣传鼓动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并从宣传组织、宣传内容、宣传方式三个方面查找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他还认为化装讲演、活报、“蓝衫团”、戏剧都应该充分地发展起来。[注]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2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56页。1934年,一篇署名阿伪的《关于宣传鼓动员》的文章特别强调戏剧、活报、化装讲演等,这一切有效的方法都应该用在动员亿万的青年武装上前线。[注]阿伪:《关于宣传鼓动员》(1934年5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99页。
最后是开展同旧戏的斗争。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封建斗争,如共青团“在俱乐部内组织‘不信神教同盟’,经常进行反宗教的宣传与解释工作”[注]《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节录)》(1932年1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7页。。为了把有革命和政治动员性的新戏剧同军队的当前任务相结合,反对封建思想,红军学校举行盛大晚会,开展反宗教迷信斗争,《破除迷信》的上演引发群众的反宗教热情。禁演花鼓淫戏以及一切宣传迷信和帝王英雄思想的旧戏成为了苏区的常态。为打破乡村旧戏一贯持有的“菩萨是有灵的,能保人口平安”落后盲从逻辑,作为苏维埃政权舌喉的《红色中华》也连续不断刊载批判封建旧戏的文章。1933年9月27日,《红色中华》刊发了《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反对瑞金演封建戏》一文,提出“应该努力创造工农自己的艺术,动员群众来彻底消灭封建残余!”1933年10月6日刊登《开展反宗教迷信斗争》、12月5日刊登《艺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展开反对封建旧戏的斗争》、1934年1月10日刊登《开展反对封建迷信斗争!云集区列宁小学教员拜老爷!封建旧戏大演特表演》等系列文章,表明了苏区党组织对戏剧界阶级斗争的重视。除此之外,《红色中华》文艺副刊《赤焰》在表明创刊宗旨的《写在前面》中明确表示:“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的。”《赤焰》还全文刊登话剧《我们自己的事》,反映工人拥护红军,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的事迹。
(三)不断创作和改造中的苏区新戏
为提升戏剧表演的革命性、宣传的时效性和艺术的审美性,苏维埃各级党组织对戏剧的演出内容进行设计,对剧本进行审查,对戏剧的娱乐效果的提升进行预设。如1930年1月28日,中共闽西特委对纪念“二七”惨案的新剧内容进行框架式的规定。[注]《中共闽西特委通告二十八号——关于纪念“二七”工作大纲》(1930年1月28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43页。1930年3月25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指出,新剧剧本须经区以上之政治审查方得表演。1933年3月工农剧社还成立编审委员会,加大对剧本的审查。“审查各地俱乐部现有剧本与歌剧,以便甄别好坏、决定取舍。”[注]《工农剧社启事》(1933年3月12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60页。审查明确要求,剧词必须具有政治斗争性,带封建性的剧词是绝对禁止的。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对俱乐部的戏剧演出也做了相应规定:“a、注意布置和化妆(装),表演出职业、阶级、性别、时空的差异需要化妆(装)和舞台布置的辅助;b、要拿实际的材料做基础,更便于一般人表演,并以材料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主题,对于戏剧的中心,不能平铺直叙,要注意穿插使剧情具有波动性;c、演出要有动作的配合,如果缺乏动作,就变成了报告;d、二人以上的谈话多于一个人独自叙述;e、戏剧必须具备结构性。”[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102页。瞿秋白也强烈要求:“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注]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00页。新戏创作通过化装宣传、活报剧、话剧、歌舞剧、双簧等不同形式传播开来。
为了赢得老百姓对革命戏剧的青睐,逐步扭转其对旧戏的精神依赖,赣南闽西一带的戏剧宣传还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形式,进行旧戏新编。“有的套用家喻户晓的唱段,有的模仿妇孺皆知的情节,如《打鼓骂郭》,即是京剧《打鼓骂曹》的翻版。”“上杭县樟树乡俱乐部主任邱必书率先带领木偶班‘福胜堂’全体艺人编演了《扩大红军》《打土豪》《婚姻自主》《不识字的痛苦》《团结一致》《大小争风》《老少配》《借衣劝友》等十余个旧调新词的文明小调。”[注]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值得提及的是,剧本《蹂躏》《无论如何要胜利》打破一贯剧情是拼命的、结局一定是胜利的、大团圆的剧情编演模式,以更多悲剧的成分来宣传革命主题,尝试不同的戏剧表演方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政治审查越来越严,但剧作家的创作热情并没有受此影响。根据汤家庆的研究,“当时中央苏区创作的剧目有120个之多,从已收集到的79个剧本来看,‘一苏大会’以前的作品只有11个,85%的作品是‘一苏大会’以后创作的,内容题材广泛,形式活泼多样”[注]汤家庆:《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化装讲演、新剧、活报构成了苏区戏剧运动的三大体系。
三、获得新生:苏区戏剧的人民情怀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一苏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央苏区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赣南闽西的戏剧艺术也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冲刷和锻造,获得了新生,形成了很多军民喜闻乐见的戏剧表演形式,譬如形式简单、对比鲜明的化装宣传,演员化装成帝国主义牵着军阀杀工农,乡村妇女上台演说,“以对话、形体动作和舞台布景为基本形式,吸取了古代民间传统的口头文学优点和以故事连贯性的叙述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了适合群众情趣的话剧表演艺术形式”[注]刘国清:《中央苏区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0页。。活报剧以及改编的地方戏曲等不同形式的戏剧表演有效地发挥着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作用,彰显了苏区戏剧的人民情怀,如“长汀的河田区,在晚会上表演了欢送逃兵归队的新剧,当场就有青年报名归队,又在二拨乡表演了新剧,当场鼓动了二十七人加入红军”[注]《艺术战线上的动员》(1934年),《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186页。。在赣南闽西,苏区戏剧不再是文人墨客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融入群众生活、伴随革命发展的战斗剧,有着具有革命特质、人民情怀、地域风格的历史表达。
(一)剧情易懂寓意鲜明的戏剧风格
简洁明了、直抒胸臆是苏区戏剧的一个突出特征。为动员广大工农积极应对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首次“围剿”,话剧《空室清野》突出地表现出敌人的狼狈窘境,其以闹剧的表现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白军在根据地里搜不到粮食,寻不到水,到处碰壁、丑态百出,陷入四面楚歌的狼狈境地。当演到一个白匪士兵从水缸里拎出一个臭马桶时,全场笑语不绝。《蒋介石自叹》产生于第二次反“围剿”以后,唱词简单凝练,以清唱的形式揭露了蒋介石悲惨的境况和他迫害军民的罪状,极容易让闭塞保守的老百姓分辨敌友。部分唱词如下:
南京城打罢了二更鼓净
提起那张辉瓒好不伤情
他为我蒋介石江山坐定
他为我蒋介石东打西定
到龙岗打红军一仗交锋
只杀的张辉瓒一命归阴
提起来那红军心惊胆战
一声声要夺我锦绣龙庭
他说我是美帝忠实走狗
他说我杀工农保护豪绅
他说我苛捐税剥削民众
他说我夺地盘连年战争
……
这就是我军阀最后末路
急的我蒋介石如那万箭穿心[注]潘振武:《战歌春秋》,第76-77页。
为赢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鼓舞士气,杜绝士兵开小差的现象,话剧《反对开小差》[注]陈少卿(开小差者):我以前是个怕死鬼,我现在坚决改正过来。马上到前线去,不彻底打垮国民党匪军,誓不回来。乡主席:这就对了。陈妻:这才是我的好丈夫。陈弟、陈妹:这是我的好哥哥。汪木兰、邓家琪编:《中央苏区戏剧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从舆论、家庭的角度表明为革命奋斗的光荣与伟大。
中央苏区建立之初,赣南闽西不识字群众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文化教育普及成为根据地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加强军民对接受文化教育的认识,苏维埃各级党组织不仅大办各种类型的识字班,而且还进行形象化的戏剧宣传。《不识字的害处》就讲述了一个农民因为不识字,急忙找人给家里写信,结果信中错将“忙”写成“亡”,将“帐”写成“葬”,害得家人悲伤至极,准备给他办葬礼,这一啼笑皆非的闹剧有力地揭示了识字学习的重要性,深刻地教育了人民群众。
为庆祝前线红色战士的胜利,《工作在箱子里》及《滚出去》等更是特点鲜明。有一军团表演令观众捧腹的《工作在箱子里》讽刺剧,有三军团火线剧社表演的新剧《东洋人照相》,有五军团新鲜且含有政治鼓励性的活报剧,有直属队别开生面的反帝拥苏大鼓词及滑稽而含有深意的《滚出去》话剧,博得了观众如雷掌声。《松鼠》描写了白军为了消灭“共匪”,而派一部分经专门训练的白军特务打入红军内部;同时列宁室的主任也打入了白军内部,通过一系列的智斗,向白军士兵揭露了其长官的丑恶嘴脸。有从红军队伍里逃脱的奸细报告白军说“三班班长是红军奸细”,但是列宁室主任沉着应对并策反了众多白军将士,一起脱离了白军的魔掌。剧作以滑稽搞怪的语言风格和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二)紧密结合乡村生活的戏剧场景
为应对敌人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1933年,党和政府开展了春耕运动。随之,《春耕战线》和《春耕突击队》等反映和宣传苏区群众努力春耕、发展苏区经济、改善工农生活的戏剧就不断上演,动员宣传效果显著。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全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提出了“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注]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7页。出于现实的需要,《战斗的夏天》就是在这种情景下产生的。剧作描写了在查田运动中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分子造谣生事,毒害耕牛,企图谋杀乡苏维埃主席,结果群众和上级派来的“轻骑队”发现并揭破了敌人的阴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剧作塑造了农村中各阶层人物鲜明生动的形象,有乡苏维埃主席钟文连、团支部书记钟福娣、伪装贫农的地主苏庆云、漏划的富农陈阿富,还有钟三嫂、陈大嫂、谢陈氏等普通农村妇女。这一剧作在熟悉的情景演练中宣传了革命主题(众呼,加紧查田工作,深入土地革命)。这些戏剧对于推动查田工作,在经济上赞助革命和政治上助推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制定的《俱乐部纲要》规定:“戏剧及一切表演的内容必须具体化,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当地的群众的生活材料,不但要一般的宣传红军革命战争,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暗示妇女解放,家庭及生活条件的革新,揭破宗教迷信的荒谬,提倡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和战斗精神。”[注]《俱乐部纲要》(1934年4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21页。诸如产生于赣南闽西的《惰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富农婆压迫和毒打童养媳》《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及揭示反革命欺骗群众反水的《上了他们的当》等戏剧,都是根据现实生活改编而成,赢得群众的一致好评,“他们一面吃喝,一面笑着说,‘同志嫂,你们的戏扮演的蛮好,有头有尾,连我们妇女子都能懂’”[注]戈丽:《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1934年4月26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04页。。正是由于红色戏剧的大众化和化大众的独特性,红色戏剧才能实现它宣传动员的效果。
(三)深入群众走进民心的戏剧情感
苏区红色戏剧剧本以火热的革命现实为题材,反映大众的日常生活。“闭门造车是决不能创造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瞿秋白指出,“剧团演出剧本的主题和内容,是根据当前的方针政策和主要任务而创作的,剧情是来自生活,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汲取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真人真事,加以艺术提炼,自编自排自演,惟妙惟肖地再现在舞台上,因而很受群众的欢迎。”[注]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49页。关于剧本的台词,瞿秋白认为:“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注]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74页。除了专业戏剧人才以外,苏区戏剧题材的构思也有军民共同参与,往往形成一些集体创作的优秀作品。
演出更是如此,戏剧表演中军民的共同参与,打造着独具地域特色和革命风格的艺术逻辑。在戏剧《庐山之雪》中,红一军团长林彪扮演红军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扮演红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扮演红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则扮演蒋介石。在正式演出前,《庐山之雪》只有一个剧本大纲,具体的台词演员临场发挥。“当戏剧表演到蒋介石被红军俘虏时,扮演红军司令员的林彪脱离即定剧情,竟然问‘蒋介石’:‘你为什么这么瘦?’罗瑞卿一怔,急忙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信口开河,越说越带劲。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发挥:‘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烧肉拉白水,无药可救’。”[注]何立波:《红军将领与苏区戏剧运动》,《党史纵横》2012年第12期,第20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剧团化妆(装)以木炭代墨,以红纸泡水代胭脂,‘松光’代汽灯,幕布不够代以被单”[注]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02页。。没有正规舞台,红军就临时搭建草台,利用露天的剧场,观演之间全无障碍。即便如此,戏剧演出也是深受群众喜爱。从村镇小圩到前线慰问演出,苏区戏剧努力实现着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历史使命。从苏维埃春耕巡回演出的效果可以看出,戏剧受群众欢迎的程度不言而喻。“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晚上打着火把,小的替老的搬凳子,成群结队的来看,最远的有路隔十五里或二十里的。”[注]戈丽:《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1934年4月26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03页。正如傅钟所言,“文艺不论思想内容也好,技巧也好,真正提高的道路唯有深入到群众实际斗争生活中去”[注]傅钟:《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在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第31页。,才能赢取并征服广大老百姓。
结语
直面传统、迈向交锋、走向新生,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发生、发展历程高度吻合了新生事物的生长逻辑。红色戏剧的成长历程,不仅体现着革命在乡土间的历史进程,同样反映出民众对革命的认知与认同过程。不难发现,针对红色戏剧的乡土认知,民众的戏剧想象总是与革命发生相互交织。在中央苏区,传统戏剧的娱乐性和封建教化功能一直干扰着新戏的创作、演出和传播,因此,消除纯粹的娱乐化,改造旧戏和创作新戏,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完成政治目标的重要使命。随着革命不断向前推进,在新旧戏曲的较量中,传统戏剧从被注入红色基因到红色改造,再到出现赋予推动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民众置身其间,在耳染目睹中得以改造思想和深化认识。
当然,乡土间普通民众看戏追求娱乐效果,纵使在中央苏区,很多乡村民众更多注重戏剧的声色之美,这同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诉求必然发生冲突,这也促使了红色新戏在革命的洪流中被逐步强化和放大。苏区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主动对落后的、封建的、阻碍革命发展的传统戏剧进行重新改造,旧戏在新戏的裹挟下走出传统的逗趣、情哥、情妹的庸俗之圈,践行文艺战线上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神圣使命,由此产生了很多适合普罗大众的文艺作品,彰显了苏区戏剧的革命和人民情怀,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苏区戏剧的通俗化、大众化,成就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战线的业绩,也奠定了革命文化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脉络。当下,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向国际社会更全面地展示中国风貌、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更加需要文艺战线上的鼎力相助。传承红色戏剧的革命精神和价值立场,发扬文艺的时代引领作用,创造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优秀作品,传递新时代的精神风貌,“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前行的路还很漫长,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仍需很大的耐力和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