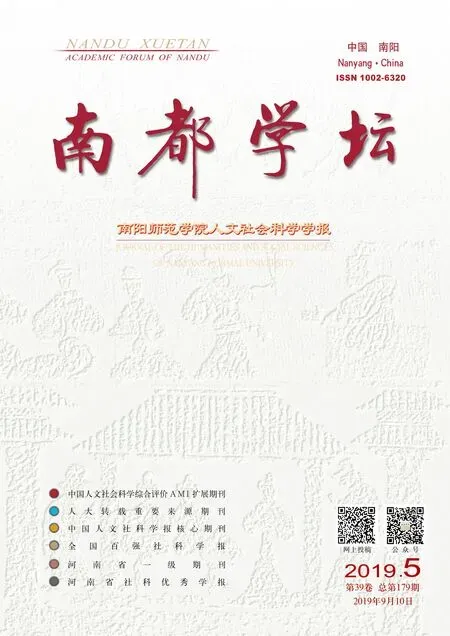《小团圆》中悖谬的母女关系解读
李 法 惠
(南阳师范学院 期刊部,河南 南阳 473061)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无私的爱,古今中外有数不清的作家都对母亲进行过讴歌,唐诗宋词中歌颂母亲的诗词比比皆是,现当代文人墨客更是创作了数不清的作品来歌颂母亲,比如老舍的《我的母亲》、沈从文的《我的母亲》、杨绛的《回忆我的母亲》、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肖复兴的《母亲》、梁晓声的《母亲》、孙犁的《母亲的回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陈建功的《妈妈在山岗上》、宗璞的《我的母亲是春天》、贾平凹的《写给母亲》等,这些作品中母亲形象都是高大圣洁、无私善良、勤劳美丽的。可是,研读张爱玲的作品,我发现其作为女性,却把母亲写得非常不堪,塑造的母亲形象大部分都庸俗、冷漠自私、变态,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花雕》中的郑太太、《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这些女性,心灵异化、感情扭曲,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母亲形象的认识,尤其是她在《小团圆》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更是特立独行,通过对九莉形象的塑造,解构了人们对传统母女关系的书写,把至纯至亲的母女关系写得僵硬、冰冷、无情,母不慈子不孝。本文试图结合张爱玲的生平对这种悖谬的母女关系进行解读,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颠倒的母女称呼书写
《小团圆》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在创作的过程中,张爱玲反复与她的好友邝文美、宋淇夫妻商讨修改。1976年4月4日她写给好友邝文美、宋淇的书信中说道:“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分明。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1]5-6确实如作者所说,在《小团圆》中,她写了“祖父母或母亲的事”。小说除了述说女主角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纠葛外,重点是描写了九莉的母亲。
(一)人物对应关系
小说女主人公盛九莉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贵之家,有个弟弟。她4岁时母亲与三姑楚娣一起出国留学,9岁时母亲返回与父亲离婚,她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后父亲再婚。因遭继母和父亲打骂,九莉逃往留学回来的母亲处,可惜好景不长,母亲不久又出国了。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九莉失去了在香港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只好返回上海,与姑姑租住在外边的公寓,靠写作卖文为生,在此期间认识了汉奸邵之雍,与之结为夫妻,后来战争结束,邵之雍逃亡,又与其他女子同居,九莉与之断绝关系,只身去往美国,后与美国作家结婚,终身未要孩子。盛九莉这种人生经历实际上就是张爱玲的真实人生写照。《小团圆》中人物几乎都可以一一找到对应关系:盛九莉——张爱玲;邵之雍——胡兰成;蕊秋——张爱玲生母黄逸梵,文中九莉叫二婶;楚娣——张爱玲姑母张茂渊,文中九莉叫三姑;九林——张爱玲弟弟张子静;乃德——张爱玲生父张志沂;后妈——耿十一小姐(翠华)——张爱玲后妈孙用蕃;大爷——张爱玲大伯;大妈——张爱玲大伯母……
《小团圆》中张爱玲借助他人之口说九莉“是只有她母亲和之雍给她受过罪”[1]241,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遭遇也确实如此。张爱玲1920年出生,母亲黄逸梵1924年就出国了;1928年母亲返回中国,1930年父母离婚,张爱玲与父亲生活在一起;1932年母亲去往法国;1934年父亲再婚,1936年母亲返回国内;1938年因与后母发生冲突,张爱玲遭父亲毒打软禁,逃往母亲家;1939年母亲到南洋;1947年母亲返沪,一年后母亲出国到马来西亚,之后移居英国;1957年母亲病逝于英国。从黄逸梵的人生经历看,张爱玲出生后,她就不断出国,只有1920—1923年、1928—1931年、1936—1938年、1947年,共计12年在国内,并且这12年中,张爱玲仅有1920—1923年、1938年,1947年,共计6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从张爱玲1920年出生到黄逸梵1957年去世,这37年间,母女相处时间太短。张爱玲4岁之前与母亲生活的印象,因年幼应该是模糊的,长大后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又太短。张爱玲说她母亲给她受过罪,应该是指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对她照顾不到、关心不够,让她童年失去母爱、花钱没着落、居住无定所、遭受后母虐待、受很大委屈这些罪。
(二)母亲角色的错位
这种因母亲角色的长期缺位而对张爱玲造成的心理创伤,张爱玲是借助盛九莉周边几个母亲角色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盛九莉的一生中承担她母亲角色的有4人:生母、后母、伯母、姑母。在法律上九莉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亲妈蕊秋,她喊作二婶,这个是与九莉有血缘关系的妈,是九莉心目中最在意的妈,也是九莉又爱又恨的妈。父母离婚后,九莉判给爸爸,所以九莉也不能指望她给自己太多照顾,花妈妈的钱总觉得亏欠了她。另一个是她的后妈翠华,小说中说给乃德(二叔)做媒的两个堂妹议定让九莉、九林叫她为“娘”,这个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妈,也是张爱玲与之生活10多年的后母的化身。除了上面法律意义的两个妈妈外,她还有两个妈:一个是九莉自小就过继过去的大伯母,《小团圆》中说“她因为伯父没有女儿,口头上算是过继给大房,所以叫二叔二婶,从小觉得潇洒大方,连她弟弟背后也跟着叫二叔二婶,她又跟着他称伯父母为大爷大妈,不叫爸爸妈妈”[1]22,“后来因二婶三姑出国的事与大伯家闹翻了,然后就不再提过继的事了”[1]83,关于大伯母小说没做过多交代,想必没有给九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吧;另一个就是她的三姑,也就是张爱玲姑姑张茂渊的化身,张爱玲1938—1952年都与姑姑住在一起,所以小说中的三姑更像是九莉的母亲。
总结这几位交织出场的履行母亲职责的母亲,就像九莉对她们的称呼一样,颠倒错乱:亲妈非妈是二婶,不能全面履行妈的职责;后妈是妈且是娘,但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妈,她不关心九莉,只盼她早点出嫁,还挑拨九莉的父女关系;大伯母九莉称其大妈仅是名义上的妈;姑妈像妈又非妈,但代替了亲妈,又确实不是妈。一个豪门千金,一个别人眼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这些妈的角色,哪个都是妈,哪个都不像妈,都不能完全符合那个真正的“妈”的称号,小姑娘时而在这个妈家,时而在那个妈家,时而遭受白眼,时而接受责骂,时而还要装作低眉顺眼。就像三姑问她喜欢谁,她知道自己心里是喜欢二婶的,但是嘴里却说喜欢三姑,她知道自己与二婶有特殊关系而与三姑远些,要让三姑开心。如果得罪了三姑,让三姑不开心,三姑随时就会不照顾她。
梳理一下九莉的童年、少年生活轨迹,可以发现就养育关系的确立上来说就出现了许多悖谬。九莉父母都是出身豪门,家里有钱有洋房有仆人,只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刚好组成一个传统家庭渴望的“好”字,九莉聪明伶俐招人喜欢,还是长女,他们应该能养得起她,可是父母却因伯母没女儿把她过继给父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家,让九莉做他们的继女,让她把不是自己爹妈的人认作爹妈,而把亲爹妈喊作二叔二婶。爹妈就在眼前,但九莉名义上已是别人家的女儿,人为地在他们之间设道墙。亲生母亲二婶本来可以把九莉带在身边,把她教育培养成自己心目中的名媛,让女儿正常读书、社交、打扮,但是她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不管自己女儿死活,满世界旅行去了。如果说九莉被送给她人做继女是形式上的被抛弃,那么母亲二婶远走他乡,是九莉真正意义上的被抛弃。父母有悖常情的做法和豪门千金无家可归的遭遇,在九莉心中绾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二、残缺的母女情感倾诉
有评论家说,看完《小团圆》才发现伤害张爱玲最深的是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和胡兰成[2]。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
(一)母爱的缺失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写到的女性形象众多,但是写得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九莉的亲妈蕊秋,让人最惋惜的还是九莉与母亲蕊秋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九莉喜欢和母亲在一起,又害怕母亲,希望得到母亲的关爱,又不喜欢母亲唠唠叨叨的说教。
从九莉成长过程来说,母亲不能守护她。《小团圆》中写到九莉与回国后的母亲的几次短暂相聚,时间脉络不是太清晰,出国次数也不明了,感觉就是来去匆匆忙忙,只能从黄逸梵的出国时间、出国次数来印证蕊秋的出国时间、出国次数。张爱玲的生命中,只有4岁前、17岁、26岁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小说中九莉也是如此,母亲不断出国旅行,楚娣说她像个流浪的犹太人。她去的地方有法国、英国、瑞士、爪哇、埃及、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而九莉生活的地点也在天津、上海、香港及美国等地变换。母女俩聚少离多,从小九莉由老妈子带大, 老妈子相互攀比,带弟弟的老妈子自认为比带九莉的老妈子地位高,九莉挨打时抱着韩妈痛哭,才知道自己不过是韩妈的事业,谁也不能保护她。九莉挨打后离家与二婶三姑住在一起,但是九莉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家,事事小心翼翼,回来晚了拿钥匙开门都要特别小心,来客人了自己要赶紧躲在阳台上,从家里到学习的地方很远,但是她宁可走着去,也不愿意问母亲要七毛钱的车费,免得母亲数落她,说她给自己带来负担,影响自己前途。九莉的童年,母亲就是那个墙上的照片。一天她母亲告诉她,做梦梦见了九莉,九莉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怎么会误入禁地。言外之意,就是母亲不关心自己,母亲的心里从来没有自己,自己走不进母亲的内心。
长期不见母亲,母女之间缺乏亲密的感情交流,产生了严重的隔阂。蕊秋关心的是九莉是否具备淑女风范、是否成才,而九莉渴求的是母亲对自己的理解。9岁那年,九莉第一次与母亲一起上街过马路,“母亲正说‘跟着我走;要当心,两头都看了没车子——’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那一刹那的内心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1]80。作者说“她也有点恶心”,这个“也”字,说明不仅是母亲蕊秋感到恶心,女儿九莉也感到恶心,可见母女心理距离之远。母亲的许多话也深深刺痛九莉的心,九莉17岁时病了,母亲竟然责骂嫌弃地说“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1]130,言语恶毒,哪像一位可爱的母亲在女儿病中说的话。九莉在港大读书时,母亲来看她,顺便看看九莉的宿舍,九莉听见母亲给亨利嬷嬷说自己住在香港最贵的浅水湾饭店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九莉当时非常穷,暑假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一个夏天都住在免费的修道院,而母亲说是来看她,竟然没问问她有没有钱,需要什么帮助。
作为母亲,蕊秋不仅不能满足九莉精神上的需求,也不能满足九莉的物质需求。女孩子都喜欢穿新衣服,但是二婶给她做衣裳总是“旧的改的”[1]181。有一次,父亲乃德的下堂妾爱老三做衣服,顺便给九莉也做了一套,然后故意问九莉喜欢谁,九莉违心地说喜欢爱老三。九莉喜欢穿新衣服,后妈翠华给九莉一堆旧衣服,九莉烦死了,觉得一件又一件永远穿不完,使她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很没面子,姑姑说等她18岁了,给她做点新衣服,但是九莉觉得18岁太遥远,像隔座大山,过不去,看不见,满足一个女孩子的基本愿望就那么难。
(二)恨母情结
“在生命的最初阶段,不论男孩和女孩都与母亲维持着一个密切的关系,在生物学上称之为‘共生’现象,‘共生’是孩子成长初期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它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由于母亲是女孩成长的摹本,所以女孩与母亲的共生阶段要长于男孩,所以对女孩来说,母女之间的‘共生’尤为重要。”[3]因为九莉与母亲的“共生”关系在九莉童年时就时断时续,所以九莉强烈地渴望母爱,并且由爱不得而生怨,最终生恨。《小团圆》的末尾说九莉“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分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1]283。蕊秋虽然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但也不是一点儿不关心女儿。她离婚时还专门把女儿受教育写在离婚协议书里,要求乃德必须让女儿上学,她从国外给孩子们邮寄玩具,她还专门去香港看望女儿,在女儿挨打逃出来后收留女儿,在女儿生病时还照顾她,有时甚至还梳妆打扮女儿,在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为女儿聘请专职教师,教女儿学钢琴、英文,特别是最后一次出国前,还给女儿留了一对翡翠耳环。为什么九莉说生了小孩害怕他来替她母亲报仇呢?这应该是反映了九莉的心理,她恨母亲不了解自己,害怕自己生个小孩将来也像自己一样恨母亲。在港大读书时,她申请奖学金没有成功,老师安竹斯先生鉴于她的成绩给了她800港币,资助她上学,被母亲知道了,首先怀疑她与安竹斯有不正当关系,然后打牌一下午把这800港币输个净光。九莉得知后感叹:“如果有上帝的话,也就像‘造化小儿’一样,‘造化弄人’,使人哭笑不得。一回过味来,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1]28
九莉怨恨母亲,每一次从母亲那里拿钱都觉得很不自在,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有一天不花母亲的钱,有朝一日能还了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有一天看母亲心情不错,“九莉乘机取出那二两金子来递了过去,低声笑道 :‘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蕊秋流下泪来。‘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她并没想到蕊秋以为她还钱是要跟她断绝关系”[1]251,252。母亲没要她的钱,她心里说,“不拿也就这样,别的没有了”,“时间是站在她这边,胜之不武”[1]253,她对自己说“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1]253。她母亲临终在欧洲写信对她说:“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她也没去。九莉母亲去世后,拍卖行拍卖遗物清还了债务,清单给她寄来,看到有一对玉瓶值钱,九莉联想到从前帮母亲整理出国带的行李,从来没见过这对玉瓶,她还在怨恨母亲没让自己开开眼界,防自己女儿像防贼似的。
三、另类的母女形象塑造
母爱缺失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国外研究母爱缺失更多的是把它与儿童教育成长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认为:“童年的赤子之心与作家的真诚之心是相同或相通的”,“一个作家的观看世界的艺术的眼睛是母亲给予的”,“如果作家在幼年就失去母亲……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那么就会对作家的童年造成精神创伤,这种情况也会内化为心理定式,使她用另一种病态的眼光看世界,并从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来”[4]。张爱玲看世界的眼睛也是她母亲给予她的,她创作中表现出的病态的眼光也是童年不幸生活给她打上的烙印,她通过九莉的眼睛和九莉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塑造了一对不一样的母女形象。
(一)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颠覆
在九莉的眼中,母亲蕊秋是一个新潮、叛逆、勇敢的女性。她对不务正业、吸大烟、赌博、纳妾、逛窑子的丈夫非常不满,敢于主动提出与丈夫离婚,“蕊秋逼着乃德进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方才提出离婚”[1]81,她勇敢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不依赖自己的丈夫;她虽然裹了脚,但到处旅行,像一个旅行家或犹太人一样居无定所,九莉说“她们母女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永远是在理行李,因为是环球旅行家,当然总是整装待发的时候多……她母亲传授给她的唯一一项本领也就是理箱子”[1]254。蕊秋结婚后还出国学绘画、雕塑、滑雪,这都迥异于20世纪初在家相夫教子的女性形象。
在九莉心目中,蕊秋又是一个身世凄凉的风流罪人。和蕊秋有暧昧关系或肉体接触的人有一大堆:她深爱的简炜,离婚也主要是因为他,还为他打过胎;在新加坡等她被炸死的商人劳以德;毕大使;随她到香港浅水湾九莉看到的年轻的英国人;教九莉唱歌有可能是九林生父的意大利人;英俊矮胖的法国军官;劝她母亲钱不要花给九莉,自己留着用的马寿;诚大侄侄;为九莉治病的范斯坦医生;给蕊秋塞钱的雷克医生;法科学生菲力;等等。和蕊秋一起留学的楚娣曾亲口告诉九莉“二婶不知道打过多少胎”,这种混乱的男女关系,“真实地展现了一名颠覆了传统注重贞操、从一而终的母亲形象”[5]。
蕊秋满世界跑,欧洲、南洋不断变化,也曾做过尼赫鲁两个姊妹的社交秘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她停下作为避风的港湾,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作为她的终生依靠。她每次出国都带着祖上留下的古董,需要钱时就变卖,用九莉弟弟九林的话说就是二婶永远有卖不完的古董。她离婚后虽然经济条件不是多好,能养得起九莉,可在钱的问题上,她总是斤斤计较,九莉不小心打碎了母亲一只茶壶,还赶紧自己花钱去买一个,然后二婶也没阻止。在九莉要不要留学问题上蕊秋总是患得患失,犹豫要不要送九莉出去留学,时常把九莉当作累赘。九莉母亲做事新潮,也许这样做是为了锻炼九莉的独立生活能力,但是,“在金钱问题上的过于理智却导致了九莉以金钱衡量她的付出”,“过于理性也表现为冷漠、刻薄、寡情”[6]。母女战后在香港重逢,母亲自己住着高档酒店,让女儿在修道院蹭吃蹭喝,还打牌输掉女儿辛苦得来的奖学金,在离开香港之前,蕊秋给九莉交代,有事找那个雷克先生(也是蕊秋的情人),如果雷克问起她们的关系,让九莉谎称蕊秋是她阿姨。蕊秋的自私、拜金、对女儿的冷漠由此可见一斑,这与传统的善良、慈祥、贤惠的母亲形象差异甚大。
(二)女儿的冷酷无情及对母爱的呼喊
“《小团圆》中的九莉与蕊秋创造了一种空前的母女关系和情感形态,一种依存与拒斥同在、并且都是连生死都无法将之切断和抚平的状态,它真切而勇敢地指认了某种完全没有可能和解的矛盾体是存在的,张爱玲以自已的方式诠释了它,但始终得不到拯救。”[7]在《小团圆》中,张爱玲通过九莉的回忆,把母女亲情的寡淡、世俗、冷漠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九莉的回忆中,母亲除了在意美丽漂亮,自己好像做什么事,都不讨她欢心。母亲教育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到了九莉眼中,就变成了嫌弃。她认为母亲总是把她的事想到最坏里去,实际上她也总是把母亲的事想到最坏里去。蕊秋见有时候说教也不管用,便不再纠正九莉的举止,她就认为母亲是对她彻底死了心了。小说没说九莉是怎么到美国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从未想过去与她母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邵之雍出逃、她食不甘味、每天靠喝西柚汁度日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想到去找她的母亲。
小说是以九莉的眼光来看母亲的,如果换成张爱玲的眼光来看她的母亲黄逸梵,这应该也是一一对应的,这是“张看”。张爱玲母亲1957年就去世了,1975年张爱玲才开始写《小团圆》,那时候张爱玲已经50多岁,是写30多年前发生的事,回首往事,也许她早就原谅了母亲,所以在小说中,她借九莉之口说不要小孩,“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1]155。《小团圆》中有九莉在美国打胎的情节描写。这是张爱玲之前的小说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毕直的欹立在白磁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1]157这段关于打胎情节的描述,真是惊悚,让人不寒而栗。九莉坚决、果断、绝情地抛弃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像当年母亲无情地抛弃她一样。作家张爱玲一辈子没有生孩子,九莉的遭遇正是张爱玲的遭遇,张爱玲在纽约打胎的事曾告诉过她的朋友邝文美[1]5。九莉为什么不要小孩呢?她自己说是担心他来替妈妈报仇,我认为还有其他隐情,是不是她认为要孩子没用,就像自己一样是家人的负担,不能报答妈妈,或是后悔自己当初对妈妈不好,没有珍惜母女相处的时光,伤了妈妈的心,辜负了妈妈的期望。因为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九莉把母亲留给她的一对玉耳环卖掉后的一段心理活动,“其实那时候并不等钱用,但是那副耳环总使她想起她母亲她弟弟,觉得难受”[1]260,楚娣说卖了个好价钱,这时候九莉想道:“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想卖。”[1]260这是母亲留给她的念想,睹物思人,空留想念在心中。 九莉在看写她祖辈的历史小说《清夜录》时说“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1]106。
四、总结
九莉的遭遇也正是张爱玲的遭遇,研究九莉与二婶蕊秋的关系就是研究张爱玲与其母亲黄逸梵的关系。九莉与母亲的关系、二婶在九莉心目中的形象、九莉与二婶形象的塑造,充分说明童年生活遭遇对张爱玲性格形成和创作的影响。张爱玲勤奋好学、追求自由、追求经济独立、不顾一切追求爱情、追求所谓的新生活、追求金钱,都是来自于她母亲的榜样。她在作品中塑造的母亲形象和九莉形象,就是自己揭自己的伤疤,自己对自己的鞭笞,她说有些地方总是自己揭发的好。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2月22日刊发了一篇林方伟撰写的《传奇的传奇——张爱玲之母最后的南洋岁月》,写到张爱玲的母亲在英国的生活很苦,租住在一间阴冷的地下室,黄逸梵生前与她的朋友邢广生有5封通信,邢广生今年94岁,比黄逸梵小28岁,现在还完好保存了这5封信。其中,黄逸梵在1957年3月6日写给邢广生的信中提道:“说爱玲的话,我是很喜欢她结了婚……又免了我一件心愿。如果说希望她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你要知道现在是20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8]1957年10月11日黄逸梵在英国孤独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卖完的古董被运往美国,张爱玲见到母亲的遗物大病一场。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孤独病逝,死后一周才被人发现。母女结局何其相似。只有这样的母亲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女儿,正是童年这复杂的母女关系和不幸遭遇,才使张爱玲形成了多愁善感、敏感猜疑、孤僻冷傲的性格特征,一篇苍凉悲怆、闪烁着泪光的《小团圆》,展现了非同寻常、爱恨交加的母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