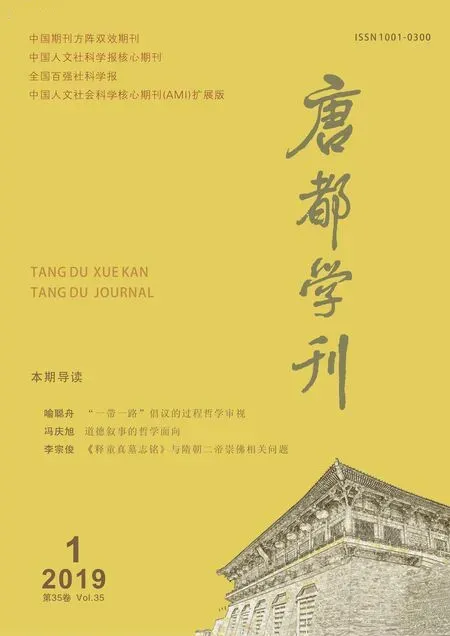试析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与当代祛魅
沈宝钢,王有凭
(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南京 211100)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传统节日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与瑰宝,几乎每个民族都在历史长河中孕育出属于自身的独特节日。诚如钟敬文先生所言:“节日,是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创造物和传承物。它是由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完善和变更的。”[1]风格各异的传统节日既有着丰富的物质形式,如春节的张贴春联、清明节的祭祖扫墓、端午节的包粽子、划龙舟等。同时,传统节日也内藏了深厚的伦理情感与伦理意蕴,如春节、中秋节表征着“阖家团圆”、清明节和重阳节蕴涵着“慎终追远”等。近年来,学界对传统节日伦理意蕴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如董志芯将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概括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忠存孝的家国理念、崇和内聚的价值追求”[2],王央央则概括为“宇宙意识、感恩意识、家庭意识、祈禳意识与娱乐功能”[3],唐凯兴将壮族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概括为“热爱家国、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热爱生活、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勤劳勇敢、坚毅顽强的优秀品质;尊老敬祖、慎终追远的伦常孝道;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生态伦理”[4]。上述研究成果都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传统节日背后蕴藏的伦理意蕴,并由此突出传统节日对于中国人生活与生命的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局限于生活层面的经验探索,使得传统节日的众多伦理意涵犹如智力拼图般的显现过于“支离”,难以呈现出传统节日本身的伦理生命与伦理魅力。象山先生曾云:“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对此,本文拟另辟蹊径,试图从精神哲学的“简易功夫”入手,挖掘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并据此揭示当今传统节日祛魅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一、传统节日的伦理重任
通常意义上,我们将传统节日看作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复杂的起源,如先人古老的图腾崇拜、固定的祭祀活动、对岁时的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等等。但是,当我们跳脱具体的生活层面,试图从文明史的全景鸟瞰时,必然会产生如下追问:古老的传统节日何以成为传统、绵延千秋?对此,我们必须回溯到人类文明的起点去寻觅答案。
当人类从鸿蒙时代走出并进入文明时代,其最大的进步便在于“伦理启蒙”。当人类处于“前伦理时代”时,人类所有行为都是由本能(动物性)驱使的,相互性的生活也是直接而无序的。当伦理意识诞生后,人类便开始意识到公共本质的重要意义,家族、部落、氏族的意识在人的精神世界逐渐清晰。伦理在古希腊语中译为“Ethics”,意思是“灵长类动物的长期栖居地”。由此可见,伦理是人类原初生命的安顿之所。人类之所以需要伦理的根本缘由在于人有“终极关怀”或对无限、永恒之期盼。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在物质世界中人类的有限性是毋庸多言的[注]《荀子·王制》曾深刻地指出人类在生理上的有限性,“(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可参见方勇等《荀子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7页)。,显而易见的莫过于生命的有限。因此,为了获得无限性,人类只能求解于精神世界。西方文明给出的回答是“宗教”,即我们可以在肉身死后,灵魂进入天国、得以永生。西方文明中的终极实体(或终极性的公共本质)是上帝,人类匍匐在上帝脚边,分享着共同的身份——上帝的子民。当我们虔诚地信仰上帝时,我们便完满地履行了“人(个体)——伦(上帝)”义务,人类借此可以摆脱原罪、获得拯救。相对的,中国文明给出的回答是“伦理”,即我们可以在伦理中获得永生。我们将个体精神融入现世的伦理秩序中,从而在“伦理流”中获得延续与传承。在文明的演进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会时刻感受到伦理感的存在危机。原因在于,人类需要伦理,可是人类又在本能上排斥伦理。因为伦理的本质是人伦关系的内在规律与规则,而这本身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束缚。伦理是人的自为状态,这与人的自然状态之间存在着先天矛盾,而这一矛盾的直接产物便是——“伦”的先天危机与内在紧张。“伦”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以至于我们很难将其恰如其分地译成英文。“伦”集中表达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终极存在。“伦”指向的是实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存在。“伦”有着多重形态:家庭之“伦”、社会之“伦”、国家之“伦”乃至天下之“伦”。人类需要“伦”,又在本能上排斥“伦”。故人类需要主动地营造伦理感,以一次次地将“伦”的意识在现世中唤醒、复苏,而传统节日的最大意义便在于在人的精神世界一次次地营造伦理感。比如,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起源于古代吴越民族的“龙”崇拜,而人们年年过端午节便是一次次地将“龙子”(公共本质)的意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唤醒。
对于“伦理感”,樊浩先生曾言:“伦理感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感、实体感、精神感。”[5]这一概括对传统节日的精神意义解读有较大借鉴意义。为了准确地把握上述“三感”,我们不妨以黑格尔所言的自然伦理实体——家庭为例进行论证。首先,统一感是指“人伦”之感,即个体与实体“在一起”[注]樊浩教授曾指出:“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参见樊浩《“我们”,如何在一起?》,载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观点受樊浩教授开设的《伦理》课程的重要影响,在此表示感谢!之感。个体是指人的单一性,而实体则是指人的普遍性,个体与实体的“在一起”便是指作为单一性的个人获得了普遍性的公共本质,获得了普遍承认。家庭中的伦理关系并非人际关系,而是人伦关系。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伦”(人的公共本质)的感觉是否在场,“伦”的感觉即精神上共融的“在一起”之感。家庭的魅力不仅在于家庭成员共处同一生活场所——“庭”,而且在于家庭成员分享着普遍的公共本质——“家”。正如黑格尔所言:“我必须把伦理设定为个别的家庭成员对其作为实体的家庭整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个别家庭成员的行动和现实才能以家庭为其目的和内容。”[6]8-9《说文》曰:“庭,宫中也”[7]308,“庭”是具象的物质存在,其本意为“宫室的中央”。而“家”则是抽象的精神存在,表征着家庭的根本属性与精神特质——“在一起”。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可以通过思维能力将“家”具象为客观实体加以把握,比如苏东坡在密州思念其弟苏辙时,便将“家”具象为天空中的一轮圆月,“共”婵娟的实质便是共“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次,家庭成员的伦理行为充实着实体感,而实体感是伦理感的核心,“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6]9实体并非是个体的集合并列组合,而是将个体纳入其中、作为普遍性的个体,即作为普遍物的公共本质。最后,精神感是伦理感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黑格尔说:“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8]我们在把握伦理感时,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的主观情感或主观情绪(如喜、怒、哀、乐等),而应将其理解为个体精神超越单一性并与实体“在一起”的客观之感。个体是经验性存在,而实体是精神性存在。家庭的诞生需要我们在精神世界中构造个体的公共本质——“家”,并在生活世界中为“公共本质”找到物质托载——“庭”。
综上所述,在面对“伦”的先天危机时,先人自然而自觉地担负起寻找可以营造伦理感的精神载体的历史重任。当这一精神载体上升为一种民族习惯,并在具体的时空中具备了外在物质形式时,传统节日便诞生了。换言之,我们可以将传统节日看做是伦理感或“伦”意识的集中登场。伦理感的诗意表达是个体精神的“在一起”之感,由于伦理感具有超越性,因此,传统节日便具备了双重伦理意蕴——超越时间“在一起”与超越空间“在一起”。
二、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
(一)超越时间“在一起”
伦理感的第一种哲学形态是超越时间的“在一起”,而传统节日的第一重伦理意蕴便是通过传统节日,个体与他者可以超越时间“在一起”。对此,我们需要追问:时间存在有何意义?孔子的回答是充满智慧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9]时间有如流水般稍瞬即“逝”,其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够让所有人不同时“在场”。正是因为时间存在,我们不能永生、注定死亡,以便给后人留下生存空间。但是,问题随即而至。人是个体性的存在,个体对实体(“伦”)的眷念就如同外出闯荡的游子对“长之育之”的家乡那样难以割舍,黑格尔称其为“悲怆情愫”。《说文》曰:“伦,辈也。”[7]260可是,先辈已逝,人类精神又该如何构建完整之“伦”呢?这势必需要人类精神跨越时间的“无情”限制,与先人重新在一起,清明节便是对此“精神努力”的最佳诠释。
清明节最早只是一个服务农事生产的重要节气,后来随着历史发展,到了元朝以后,清明节融合了上巳、寒食两节,成为一个全国性节日。今日清明节的主要活动便是家人来到祖先墓前扫墓祭祀。扫墓往往有着复杂流程,据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注]刘侗《帝京景物略·春场篇》:“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多四方客未归者,祭扫日感念出游。”参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如今,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进步,人们的祭祖仪式愈发多元化。但不管如何,清明节始终是国人祭奠祖先的重要时刻且具重要意义。第一,清明节存在的个体意义在于以祭祖仪式呼唤家庭的“伦”意识。随着时间流逝,家庭中的一部分家庭成员必然会面临死亡。死亡是重要的“伦理事件”,而不仅仅是没有呼吸、心跳停止这样的生理事件,正如黑格尔所言:“死亡是个体的完成,是个体作为个体所能为共体(或社会)进行的最高劳动。”[6]12死亡成就了“身”与“心”的完全隔离。当祖先死亡后,其“身”不复存在,而其“心”(或精神)却在“家”(伦理实体)中永久存活,由后世子孙延绵存续。可是,后世子孙毕竟“身”在此岸,现世纷繁的物质生活总会使人淡忘精神之乡,自然也会淡忘祖先的精神存在,由家庭(或家族)成员共同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存在——“伦”也会被逐渐淡忘。因此,我们需要唤醒精神深处的伦理记忆,需要从物质生活中暂时抽拔出来,将精神重新回到“伦”中与祖先重逢,清明节的个体意义便在于此。第二,清明节存在的民族意义在于以祭祖仪式呼唤民族的“伦”意识。斯大林曾给“民族”下过一经典定义:“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33。简言之,斯大林将民族看做是“共同体”。“共同体”多见于社会学视域,而在精神哲学视域中,“共同体”便指向伦理实体。“民”之所以能够“族”,除了需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习俗等现象载体外,还需要民族精神这样的精神载体,而民族精神只有在脱离具体时空的“场”[注]“场”,物理学话语,原指某种空间区域,这里指“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域。或“伦”中,方能形成民族牢固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而成为真正的共同体。清明节的意义不仅在于家庭成员能够与其祖先在精神上“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能够与民族祖先在民族精神上“在一起”。正如刘魁立教授所言:“要祭祖,祭三代宗亲。此时此刻,天神地祇、列祖列宗来到人间,天地人沟通汇集、协调合作,共同对付邪祟,共同维护人间的幸福安康,共同营造美好的未来,这些成为节庆活动的信仰层面的最重要的内容。”[11]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在于“伦”的永生与民族精神的不灭。因此,我们需要以隆重的仪式呼唤民族的“伦”意识,清明节的民族意义便在于此。
总之,当家人以相同的仪式祭祀祖先,当族人以相同的语言祈祷祝福,家庭的“伦”意识与民族的“伦”意识便超越时间在个体精神中“在场”了。同样的,在除夕、重阳、中元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中,我们也会祭奠祖先与民族的道德楷模,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伦”(家庭、民族、国家等)意识的集中登场。通过这些节日,我们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与先人“在一起”了。
(二)超越空间“在一起”
伦理感的第二种哲学形态是超越空间的“在一起”,而传统节日的第二重伦理意蕴便是通过传统节日,个体与他者可以超越空间“在一起”。空间与时间不同,时间的特质在于“流逝性”,而空间的特质在于“无限性”。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超越空间限制的能力也在逐渐提高。古人车慢、马也慢,今人可以通过高铁、动车、飞机轻松跨过千山万水;古人无法听到远方亲人的乡音,今人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候寒暄;古人无法看到远方亲人的面容,今人可以通过视频软件轻松“会面”等等。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类都需要直接的感官接触。因此,当久隔两地的亲人因各自工作无法在一起时,我们便需要传统节日的巨大文化作用,让人们超越空间“在一起”,春节便是此“身体努力”的最佳诠释。
春节,俗称过年。春节源于上古时期的腊祭,中国人庆祝春节已经有四千余年的历史。进入腊月以来,人们便会做一些事情来迎接春节,俗语称:“二十三,祭灶神;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烀猪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帖倒酉;三十夜,守一宿。”正月初一过去后,人们还“意犹未尽”,仍然会有一些特别的行为(或禁忌),如“正月一,忌扫地;正月二,迎婿日;正月三,赤狗日;正月四,祭财神;正月五,赶五穷;正月六,挹肥日;正月七,人口日”。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其意义重大。第一,春节存在的个体意义在于为游子重温家庭之“伦”提供契机。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成员进入市民社会是对家庭无可奈何的背离。当我们在外求学或工作时,不仅在身体上远离“庭”,更是在精神上远离“家”。换言之,我们的身体离开了“庭”这一生活场所,个体精神也离“家”(作为普遍物的公共本质)愈来愈远。身体的离开并不会让我们从“伦”中完全抽离,而只会慢慢“失去”“伦”的“温度”,即身体上的久久离乡必然会带来精神生活中“伦”的缺场与祛魅。因此,我们需要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来让游子“还乡”:身体的回乡团聚与精神的重温伦理。每逢春节前夕,我们都会看到一场巨大的人口迁徙——春运。春运表征的不仅是人口的大迁徙,更是中国人精神还乡(“伦”)的集体登场。第二,春节的民族意义在于为重温国家之“伦”提供契机。在新春佳节之际,许多海外游子会回到祖国。由此可见,对于小家来说,春节可以让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共庆佳节;对于大家来说,春节则可以让中国人民聚在一起,共同享受沉浸于国家之“伦”的精神酣畅。中国人过春节有着共同的仪式,比如放鞭炮、贴春联、看春晚等等,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生活于同一个国家、呼吸于同一片天空。“国家”于我们,不仅是物质呈现(如疆域国土、GDP、科学技术等),更应是精神呈现。每一个国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精神的铸造者,也都是国之“伦”的拥有者与分享者。
总之,当家人与国人以相同的形式庆祝春节时,家庭的“伦”意识与国家的“伦”意识便超越空间在个体精神中“在场”了。同样的,在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中,我们同样会跨越千山万水与家人、国人在一起,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伦”意识的集中登场。
三、传统节日的当代祛魅
在厘清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蕴后,我们不妨回归到当代生活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愈发感受到传统节日的祛魅与失落。对此,我们通常会给出以下三点原因:其一,传统文化的式微。从戊戌变法的“天下移风”到“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传统文化与传统习俗被一股脑地当成时代“赘疣”加以无情鞭挞。对此,金耀基先生曾说:“五四的知识分子是不惜去掉中国文化以救中华民族的。”[12]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是巨大的,传统民俗被一概划为“四旧”加以剿灭,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层。其二,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多元化、全球化文化背景下,西方的文化产品与价值观大量输入中国,并为年轻人所热捧,洋节受欢迎与传统节日受冷落便是其直接体现。当我们对传统文化不再青睐,而将欧风美雨看作珍宝时,传统节日的失落便在所难免了。其三,传统节日的形式缺乏创新。传统节日经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逐渐形成了复杂甚至繁冗的外在形式,正如上文所说,过春节就有着繁复的“流程”。相对地,在社会竞争益发激烈、生活节奏日趋加快的现代生活中,如此繁复的形式可能会被现代人所厌烦甚至鄙弃,故更多人将传统节日看作是难得的休息日。在此,笔者旨在提出传统节日当代祛魅的另一重原因:伦理感的失落。
我们不妨以春节“年味儿”的缺场为例。冯骥才先生说:“所谓年味就是过年的意味,过年的方式则是这种意味的载体。”[13]在21世纪的今天,春节的传统气息已经慢慢散去,而经济气息却愈发浓厚。沿街叫唤的是商场折扣而不是春节“小调”;高谈阔论的是收入攀比而不是嘘寒问暖等。可见,春节的“假日化”现象愈发明显。春节作为传统节日,本应有着浓厚的伦理感,即参与主体精神上“在一起”的感觉,而假日仅仅是为了给人们放松身心提供一个随意性契机而已,如假日旅游、假日狂欢、假日party等。反观现在的春节,虽然走亲访友、拜年祝福等传统形式仍然存在,但也有人选择宅在家里睡觉上网、聚众娱乐。春节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经过历史洗练后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其原因在于春节体现了“家”的理念在国人心中的至高位置。春节体现的是家庭伦理对个体强大的召唤“力”与吸引“力”,而这种“力”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难以拔除也不能拔除。通过春节这个载体,家人不仅在身体层面上“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在一起”,以获得归属感与还乡感。过春节的传统形式是经过中国文明的发展而留下的精华,它们深刻地将“伦理”包裹其中,有着浓浓的伦理感。比如,“以拜年为例,方式虽不同——晚辈给长辈拜年、亲戚之间往来拜年、朋友之间团聚拜年,但顺序有讲究——先家内、后家外,先同宗、后街坊,先邻里、后亲戚。”[14]传统的拜年仪式深刻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尊、亲亲”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观念与秩序理念。反之,今天的我们更习惯“一次性”地给所有亲朋好友群发短信与微信来“完成”拜年。尽管方便又快捷,但久而久之,这种拜年祝福便会流于一种“形式”或“任务”。不可否认,时代的进步必然会带来过节方式的变化,一味地守旧只会被时代所遗弃,但如果这些新兴方式“越俎代庖”,遮蔽甚至取代传统过节方式,那么必然是使伦理感的失落——“年味”的缺场。
综上所述,传统节日承担着重要的文明重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营造“伦理感”。由于伦理感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精神特质,传统节日便具备了双重伦理意蕴——超越时间“在一起”与超越空间“在一起”。“伦”是人的公共本质与精神家园,我们时刻需要在“伦”中获得公共承认,如家庭承认、民族承认与国家承认。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利益追求远比精神世界的伦理追求显得更加强势,“伦”意识的缺场愈益明显,传统节日呼唤“伦”意识的出场。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发挥传统节日的重要文化作用,在扬弃传统节日风俗仪式的基础上,认真体悟传统节日内在的伦理意蕴与精神气质:超越时间、空间而“在一起”。只有这样,传统节日才能真正发挥其文化意义以及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