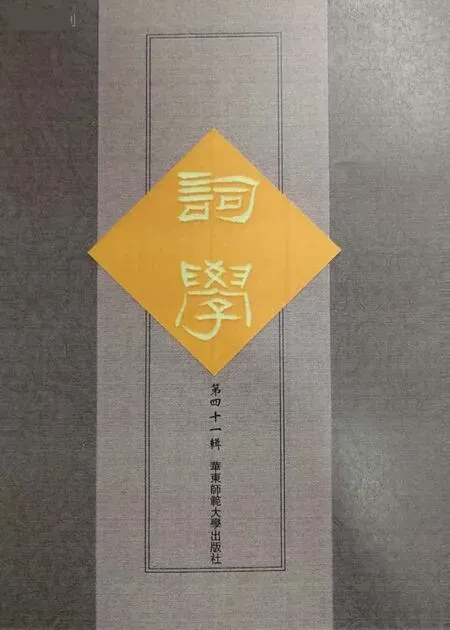《舊時月色齋詞談》輯佚
陳匪石撰 戴伊璇輯録
陳匪石(一八八四—一九五九),本名陳世宜,字小樹,號倦鶴,江蘇江寧(即今南京市)人。主要詞學著作有《宋詞舉》、《聲執》、《舊時月色齋詞譚》等。其中《舊時月色齋詞譚》一種,最初發表於《華僑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一期與第二期上,之後又分三次重新登載於《民權素》一九一五年第一三期、一九一六年第一五、一七期上。二〇〇二年出版的陳匪石詞論合集《宋詞舉(外三種)》中所收録的《舊時月色齋詞譚》就是這兩份雜誌上所刊登的内容。此後的各類詞話叢書中也曾多次收録,或名《舊時月色齋詞談》,内容都是一樣的。
據筆者搜索整理,陳匪石的《舊時月色齋詞譚》曾於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起,以連載的形式重新發表於《生活日報》,直到一九一四年五月二日。並從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起,改連載詞話的名字爲《舊時月色齋詞談》,内容也和之前不同,以談《樂府指迷》一書爲主,這一部分内容尚未有前人整理點校,筆者因爲之輯録,凡得約三十則,以供學者參考。
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
碧山之詞品,其在夢窗、白石之間乎?幽眇之思,綿密之詞,與夢窗爲近,而流利之筆,疏宕之氣,則雅近白石。玉田與碧山近,與夢窗遠,故專取白石一家也。然吾以爲,與其學玉田,無寧學碧山。
玉田所以膾炙人口者,以字句打磨易於爲力,初學者易尋途徑,吾已言之。若以境言,則淺於碧山,弱於白石,薄於夢窗。
選詞之事難矣。《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詞林萬選》、《草堂詩餘》,雜之一字,皆不能免。然而存人存詞,其功自不可没。
詞之選本以一家宗派爲限,古人蓋多有之,草窗之《絶妙好詞》,其初祖也。他不必論,即觀其於於湖、幼安、龍州、龍川諸人去取之間,可以概見。竹垞之《詞綜》,守玉田家風,茗柯之《詞選》,守碧山門徑,即近世復堂之《篋中詞》所選清人之作,亦堅守常州派家法,一絲不紊,故清初之迦陵一派,選入較少。此皆所謂一家言也。
選本之無價值者,昔以夏氏《清綺軒詞選》爲最,今則推《藝蘅館詞選》矣。漚尹先生爲之題字,吾嘗尤之。蓋此書撰擇之不精,已爲大雅所笑,且其所取材,又不過從朱氏《詞綜》、王氏《明詞綜》及《國朝詞綜》、張氏《詞選》、周氏《四家詞選》、譚氏《篋中詞》雜抄而成,而再益以近世三數人之專集,千古有只見人人所有之數種書而即可操選政者乎?此不足論詞,只可與乃父之不明四段活用而譯東文、稗販日人講義以論國學同一以腐鼠視之耳。
止庵《四家詞選》,其於領袖與附庸之間,配置或有失當,以此種選法較其他選法爲難,吾雖偶有不滿之語,然未嘗不轉服其眼光之巨,體裁之當也。蓋選詞原爲啟迪後學而設,必使有門徑可尋,方爲善本。然詞與詩文一例,千塗萬轍,而所衍之家數即各有不同,株守一先生言,既不足以盡其變,且學者之心思才力,亦未免爲之束縛。在宋本無宗派之説,而止庵擇其塗徑之相近者,各類比而列之,此中消息,亦可以令人潛心默會,而知倚聲正變之淵源。降至有清,則門徑顯然判矣。吾以爲有清一代之詞,尚無完全之選本,頗欲輯一《清代詞選》,而體裁則以止庵爲法。蓋自清初以迄乾嘉,迦陵一派趨蘇辛,而梁汾、電發諸人屬之;竹垞一派趨玉田,而樊榭、頻伽諸人屬之;茗柯繼起,標揭碧山,而如黄仲則、莊中白、蔣鹿潭、譚復堂諸人,皆爲碧山之一派。此三者略可以居其大部分,而清末之時,白石、夢窗又以鄭叔問、王半塘、朱漚尹諸先生之提倡,各成爲一派,爲一朝之殿焉。特兹事體大,甄採既恐有掛漏,鑑别又慮有未精,故久懷此志,而不敢必以成書也。
一九一四年五月九日
沈時齋(義府)與夢窗同時,夢窗詞中多有次伯時韻者,即時齋也。惜其詞不傳,而所著《樂府指迷》二十八條,議論精闢,允爲填詞家軌範,其價值足與玉田《詞源》並稱。然只見於《花草粹編》中,無單行之本。吴江翁氏據文瀾閣本刊之《晚翠樓叢書》中,而世亦不多見,惟况夔笙校本,刊之四印齋所刻詞中。巢南近覓得翁氏刊本,又從吴癯庵處得一癯庵手抄况氏校本。今巢南方刻《笠澤詞徵》,擬與陸輔之《詞旨》同附卷末,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兹録之以實我詞話,間附按語,則一得之愚,欲有所引申者也。
余自幼好吟詩。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癸卯,識夢窗。暇日相與倡酬,率多填詞,因講論作詞之法。然後知詞之作難於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則知所以爲難。子侄輩往往求其法於余,姑以得之所聞,條列下方。觀於此,則思過半矣。(陳去病按;靜翁當是翁處靜。)
愚按,時齋學於夢窗,時齋論詞之法,即夢窗作詞之法也。下字之雅而不露,發意之不可過高,皆夢窗詞之法度,學吴詞者,執此義以衡之,庶免於半塘所謂「但學蘭亭面」之誚也。
凡作詞當以清真爲主。蓋清真最爲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
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絶也。學者看詞,當以《周詞集解》爲冠。
愚按,夢窗之詞,下字運意,全從清真脱胎而來,時齋學於夢窗,故亦揭櫫清真也。然清真集詞學之大成,世人久有定論,不獨南宋諸家皆得清真之一體,即以北宋論,亦至清真而始有百川匯海之觀,有耆卿之沖和而無其俚,有山谷之奥折而無其硬,有東坡之高遠而無其麤,比於淮海、小山,又加以博大高渾之氣,此清真所以爲大宗也。至其善運化古人詩句,不用生硬字,此世人所皆知,今讀《樂府指迷》,乃知時齋實首發之也。
又按,《周詞集解》一書,當是宋時周詞通行之本,今只見元巾箱本之《清真詞》(四印齋曾仿刻),汲古閣刻之《片玉詞》(《西泠詞萃》即據此本),而《集解》已不可考矣。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日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
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
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使人不可曉。
愚按,時齋從夢窗遊,而論夢窗者如此,此夢窗詞所由受晦澀之譏也。夫夢窗爲詞,用事下語,頗有昌黎古文「陳言務去」之概,故其過也,偶或失之晦,有非細心讀之不能知其所隸何事者。蓋其運典煉字之法,每有所用爲此典,而其字面則另於他典求之者,只隸一事,而常有數事奔赴腕下,轉化去故實之面目,使他人之所有者,變爲我之所獨有。其晦因此,而其前無古人别開生面者亦在此。此實啟發後人不少,不可以間有晦處,遂以夢窗造句煉字之法爲非也。
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聲無舛誤。讀唐詩多,故語雅澹。間有些俗氣,蓋亦漸染教坊之習故也。亦有起句不緊切處。
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句,可惜。
愚按,伯時於兩宋人詞,有鄙俗語俗氣市井句者,特爲拈出,此南宋人之詞説也。昔人謂詞至南宋,遂爲文人之詞,蓋北宋爲珠玉、六一、屯田、東坡、少游、美成諸人之作,大半當筵命筆,曲成即付歌喉,非如南宋人視爲著作之業,數日而易一字,一字又改竄數次也。故《樂章集》中,率多俚語,亦常不免。蓋爲便於當時歌唱,但求合拍,不暇推敲。且流傳教坊,亦不能盡歸於雅正,蓋猶不得與温飛卿之《菩薩蠻》比,以飛卿乃受令狐網之囑,預撰以進,與當筵作曲者不同耳。南宋人去北宋未遠,故雖漸流爲文人之詞,,於字句力求雅正,然而流風未沫,則北宋俚俗之弊,必有承之者,此不得爲梅川、花翁咎也。然既爲文人之詞,則俚俗語市井語,必不可有。藉口北宋以自飾,遂以淺陋者爲正音,伯時蓋深戒之矣。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
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之意,以景結情最好。如清真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又「掩重關,遍城鐘鼓」之類是也。或以情結尾亦好。往往輕而露,如清真之「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又云:「夢魂凝想鴛侣」之類,便無意思,亦是詞家病,卻不可學也。
愚按,一詞之中,緊要關節,不過三處,即起過結是也。起處宜迤邐而來,如沿路看山,漸行漸近,其取勢雖不妨稍遠,而貴在不黏不脱,不即不離。蓋去題過遠,抛卻主意,則不知所詠何事,且一時不易着題,實齋之論是也。但若泥定題意,將全意説足,則層次將不能分,而布局必如出師之無律。故一篇之全局,當由淺而深,由景而情,由實境而入寄托。比興之體固然,即賦體亦無不如此。而起首一句,總以虚籠爲佳,即古人詞中,亦有先見喻意或正意者,然不可爲常軌也。閲實齋此條,切勿誤會其意,以爲當一口喝破而不顧以後轉折之當如何。雖體認一「見」字,亦不可作實見解也。過變處亦全篇緊要關鍵,周止庵所謂「或藕斷絲連,或奇峰突起」者,實爲扼要之論。蓋此處爲上下段之樞紐,必開下段而又不可離上一段,須以和婉之氣,而又具跳脱之筆,則上下兩段詞,自然成一關連,所謂「常山蛇擊中則首尾皆應」也。自敘固多,而另起一意者亦不少,然但以趨入寄託之本旨或所感的之意爲要。時齋不可走了元意之説,至切當矣。結處之竅要,「有餘不盡」四字,千古不能易其説。蓋天下説煞之語,都無餘味,有何妙處?可見煞而不煞,而言外之意可由甜吟密詠以求之,嫋嫋餘音,繞梁不絶,「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此實行文之極致,亦作詞之要義矣。情入於景,自比專言情者佳,北宋人多寓情於景中,妙處不可言喻,伯時拈出之,吾人當深味斯言。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如詠物,須時時提調,覺不分曉,須用一兩件事印證方可。如清真詠梨花《水龍吟》,第三第四句,引用「樊川」、「靈關」事,又「深閉門」及「一枝帶雨」事,覺後段太寬,又用「玉容」事,方表得梨花。若全篇只説花白,則是凡白花皆可用,如何見得是梨花?
愚按,詞中詠物體裁,運典一事,最關緊要。不可過疏,亦不可過密。過疏則流於蹈空之弊,而不能切題;若過密則餖飣堆砌,又成爲兎園册子,成爲書袋,而不能成爲詞。二窗固以典實著者,然試靜觀之,有《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之流弊否耶?蓋疏密相間,乃運典之布置法,前後兩段,必須相稱,而不可有所偏。伯時舉清真《水龍吟》以起例,誠哉運典之不二法門也。然而有宜加意者,則不可太泥。
要求字面好,當看温飛卿、李長吉、李商隱及唐人諸家詩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採摘用之。即如《花間集》小詞,亦多好句。
鍊句下語,最爲緊要。如説桃,不可直説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如説柳,不可直説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又詠書,如曰「銀鉤空滿」,便是「書」字了,不必更説「書」字。「玉筯雙垂」,便是淚了,不必更説淚。如「緑雲繚繞」,隱然髻髮;「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曉,如教初學小兒,説破這是甚物事,方見妙處。往往淺學俗流,多不曉此妙用,指爲不分曉,乃欲直截説破,卻是賺人與耍曲矣。如説情,不可太露。
愚按,詞中用物之法,當力避庸熟,而運新穎之典以代之,然不可生澀。此在夢窗,最得驪珠,而草窗次之,美成即不免有熟俗處矣。且熟俗二字,亦無一定,如前人用得太多,用得過濫,則本不熟不俗者亦變爲熟俗,此倚聲家所不可不知也。夫熟俗且不可,況説破乎。《四庫全書提要》謂伯時此條力避鄙俗,而不免失之塗飾。此何言歟?塗飾之弊乃絶無意思,而徒飾門面以爲美者,苟有意,即非塗飾,況力求新穎者,固無新意不足以驅遺乎!揆厥由來,則清當乾嘉以前,蘇辛之派,流爲詞論,姜張一派,又專取清空,而其病乃在直率,在空虚,而與烹鍊興實之説格格不相入,非正論也。吾謂伯時之言,庸有未備,而不得以塗飾目之。蓋露骨之弊,無論言物言景言情,皆不可犯,「渾化」二字爲上上乘,學者當從事於此。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遇兩句可作對,便須對。短句須剪裁齊整。遇長句須放婉曲,不可生硬。
愚按,一首詞不過數十字,多則百餘字耳,而千迴百轉,不在虚字之掉弄,專在於句中。常有一句之中,而意思轉折至數層者,若一句一意,即嫌淺率矣。長句之放婉曲,即此之故。婉則詞意和美,曲則具有迴折之波瀾,此造句之要訣也。若以生硬出之,則非特不能有清和朗潤之致,且流於直率矣。
押韻不必盡有出處,但不可杜撰。若只用出處押韻,卻恐窒塞。
愚按,押韻之妙用,與下語用事同。固不可有一字無來歷,亦不可使事而反爲事使。蓋反爲事使者,非生硬即餖飣,而詞機爲之不暢,即伯時所謂窒塞也。
腔律豈必人人皆能按簫填譜,但看句中用去聲字,是爲緊要。然後更將古知音人曲,一腔三四隻參訂,如都用去聲,亦必用去聲。其次如平聲,卻用得入聲字替。上聲字最不可用去聲字替。不可以上、去、入盡道是側聲便用得,更須調停參訂用之。古曲亦有拗者,蓋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牽,今歌者亦以爲礙。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當用去聲字。如《絳園春》之用「遊人月下歸來」,(原按,此夢窗《絳都春》句,或當時亦名《絳園春》,他本未見。)「遊人」(原按,人當作字)
合用去聲字之類是也。
愚按,宋人言詞多言五宫,鮮言四聲者,以四聲爲言,其自伯時始矣。《四庫提要》謂此一條「剖析微芒,最爲精核」。萬樹《詞律》實祖其説。蓋平仄聲之中,上去入各有一定,而去聲字尤關音節。如清真《六醜》、《浪淘沙慢》,夢窗《鶯啼序》諸詞中,去聲字有一定,且上字亦間有一定,而《齊天樂》結句之「上平平去入」,尤爲著明,此非多看各名家詞而細辨之不可也。(輯録者按,《齊天樂》的結句應爲「上平平去上」,疑爲筆誤。)至調停參訂之説,參訂是互參同調之詞,調停則上去間分配之法。周止庵所謂上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宜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即伯時調停之法也。今人填詞,什九不知音律,欲求四聲之不誤,當深奉伯時之言爲指南針。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協律腔,所以無人唱。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市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詠月卻説雨,詠春卻説秋。如《花心動》一詞,人目之爲一年景。又一詞之中,顛倒重複,如《曲遊春》云:「臉薄難藏淚。」過云:「哭得渾無氣力。」結又云:「滿袖啼紅。」如此甚多,乃大病也。
愚按,詞中運意之法,其開門見山語則忌鑿枘,忌重複。鑿枘則於境不合,即於理不通,重複則意無轉换,詞屬敷衍。不獨詞然,即爲文爲詩,亦必加一紅勒帛也。若以詞言,無意不必填,意少不必填。瞻園師曾諄諄詔我,天下固無勉强完篇之佳文,而勉强完篇亦直不得以文論。伯時此條,深中奥竅,蓋教坊樂工之所爲,律腔容勝我輩,而下語用字,絶不能及,此古今確論。且微特樂工教坊,即令詞家當筵製曲,倉猝成篇,亦未必盡能純粹。六一之《臨江仙》,東坡之《賀新郎》,不可語於尋常人也。愚謂此病,固應引爲大戒,然輕律腔而重字句,則伯時實首創之。兩宋名家,工於律者無不工於詞,若以一二鑿枘重複者謂爲重律之過,則其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引人以偭規錯矩,其罪又當加等矣。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七日
作詞與詩不同,縱是花卉之類,亦須略用情意,或要入閨房之意。然多流淫艷之語,當自斟酌。如只直詠花卉,而不著些艷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所以爲難。又有直爲情賦曲者,尤宜宛轉回互可也。
如「怎」字、「恁」字、「奈」字、「這」字、「你」字之類,雖是詞家語,亦不可多用,亦宜斟酌,不得已而用之。
愚按,詞稱綺語蓋離騷樂府之遺本爲道兒女事者。後人用以詠物,其體一變。然美人香草自是詞家本面目。故情意不可忽也。伯時謂須用情意,而不可流入淫艷,此雅奏正音,而一洗靡靡之習。實X宋人作詞方法。北宋不同之點,讀詞者可深味而得之也。而「怎」、「恁」、「奈」、「這」、「你」等字之不可多用,亦是此意。
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虚字,如「嗟」字、「奈」字、「況」字、「更」字、「又」字、「料」字、「極」(輯録者按,《樂府指迷》原文作「想」。)字、「正」字、「甚」字,用之不妨。如一詞中兩三次用之,便不好,謂之空頭字。不若徑用一靜字,頂上道下來,句法又健,然不可多用。
近時詞人,多不詳看古曲下句命意處,但隨俗念過便了。如柳詞《木蘭花慢》云:「拆桐花爛漫。」此正是第一句,不用空頭字在上,故用「拆」字,言開了桐花爛漫也。有人不曉此意,乃云:此花名爲「拆桐」,於詞中云「開到拆桐花」,開了又拆,此何意也?
愚按,詞中虚字,一名軟字;靜字,一名硬字。用軟字一取曲折,用硬字取峭拔。軟字過多嫌空,且易犯複;硬字過多,又每流於直。此中大宜斟酌,伯時之言是也。但詞之曲折,在意不在字,故硬字苟能用好,則亦無妨。夢窗詞靜字多於空頭字,而於其潛氣内轉絶無妨害,可以見之。伯時之論靜字,恰是覺翁家法。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然放處未嘗不葉律也。如東坡之《哨遍》、楊花《水龍吟》,稼軒之《摸魚兒》之類,則知諸賢非不能也。
愚按,此條乃爲偭規錯矩而藉口蘇辛者説法。蓋南宋自稼軒、龍洲以後,豪放儼成一派,而人之學之者,乃流於粗,流於直,而音律格調亦多不厝意,伯時箴之是也。夫東坡即席賦詞,如「乳燕飛華屋」之類,未嘗非立付歌喉,如不葉律,何以能此?稼軒之作亦然。則二公固先通曉音律,而後可以豪放。然其偶不經意以致格律不嚴之處,世人猶病之。余嘗與人論蘇辛,謂當如馬伏波語,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即伯時之旨也。伯時所舉《哨遍》《水龍吟》《摸魚兒》諸詞,蓋穠麗微婉,與豪放不同者。他如東坡之《卜算子》「缺月掛疏桐」,稼軒之《祝英臺近》「寶釵分」之類,亦爲詞家正軌,。又爲陳龍川之《水龍吟》「鬧花深處層樓」一闋,亦極旑旎風華,則豪放固非專長,明明可見矣。不能穠麗微婉,而徒以豪放不羈爲歸,而反藉口蘇辛,使東坡、稼軒爲人受過,此後人之累蘇辛,非蘇辛之誤人也。
壽曲最難作,切宜戒「壽酒」、「壽香」、「老人星」、「千春百歲」之類。須打破舊曲規模,只形容其人事業才能,隱然有祝頌之意方好。
愚按,詞中之壽曲,與壽文壽詩同爲酬應文字,托體甚卑,古人之不主張有此文字者,已數數見。然不得已而爲之,亦必以脱去俗套爲長。蓋題即甚俗,詞復不雅,當成何詞耶?伯時「只形容其人事業才能」之説,極爲得體,蓋必切定其人,只當作贈詞做,不當作壽詞做,而壽之之意,即從其事業才能中着想,既切題,又不落套。觀夢窗甲稿,壽曲頗多,然多從其人之本身落筆,即不俗不泛。吾人能不爲壽曲最妙,倘至不能不作時,當守定伯時此義,再參看夢窗詞之壽曲,即免於惡趣矣。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詞中用事,使人姓名,須委曲,得不用出最好。清真詞多要兩人名對使,亦不可學也。如《宴清都》云:「庾信愁多,江淹恨極。」《西平樂》云:「東陵晦跡,彭澤歸來。」《大酺》云:「蘭成憔悴,衛玠清羸。」《過秦樓》云:「才減江淹,情傷荀倩」之類是也。
愚按,詞中不欲用出人姓名,嫌其硬也,不欲兩人名對使,惡其板也。一首詞有幾多字?字字皆須從千錘百錬中出來,人名已嫌占地位,況直書人名,無從用運化之法,意亦未免嫌淺乎?《四庫提要》謂伯時此條,不免於拘,吾謂寧爲伯時之拘,不可以不拘而生流弊也。
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諸家目前好腔爲先可也。
愚按,此條所言,即所謂襯字也。《四庫提要》謂觀此云云,「乃知宋詞亦不盡協律,歌者不免增減。而萬樹《詞律》所謂『曲有襯字,詞無襯字』之説,尚爲未盡其變。」蓋宋人詞中之有襯字,昔人鮮言及者,伯時宋人,言之當屬確鑿,惜實例無從考證耳。至以句法之參差,歸諸教師之改换,嘌唱之增添,則正與曲中之襯字同一淵源,而襯字之不足爲訓,可以概見矣。
詞中多有句中韻,人多不曉。不惟讀之可聽,而歌時最要葉韻應拍,不可以爲閒字而不押。如《木蘭花》云:「傾城。盡尋勝去。」「城」字是韻。又如《滿庭芳》過處「年年,如社燕」,「年」字是韻。不可不察也。其他皆可類曉。又如《西江月》起頭押平聲韻,第二第四就平聲切去,押側聲韻。如平聲押「東」字,側聲須押「董」字、「凍」字韻方可。有人隨意押入他韻,尤可笑。
愚按,《西江月》詞第二句起平韻,第三句葉平,第四句葉仄,前後段均同。今曰「第二第四就平聲切去,押側聲韻」,疑刊本有誤,待考。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詞腔謂之均,均即韻也。
作大詞,先須立間架,將事與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間只鋪敘,過處要清新。最緊是末句,須是有一好出場方妙。作小詞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遠,卻易得古人句,同亦要鍊句。
愚按,此論作長調小令之異同。長調可以鋪敘,短調極須遒錬,此人所共知也。
初賦詞,且先將熟腔易唱者填了,卻逐一點勘,替去生硬及平側不順之字。久久自熟,便覺拗者少,全在推敲吟嚼之功也。
愚按,熟腔則參考者多,易唱則較少拗句拗字,平側之不順,即可少見,生硬字替去,亦易從事。此初學所易爲力也。憶予初學時,漚尹先生嘗語予,當取玉田詞仿其調仿其題而賦之,參互比較之下,易有進境。猶伯時意也耳。
詠物詞,最忌説出題字。如清真梨花及柳,何曾説出一個梨柳字?梅川不免犯此戒,如「月上海棠詠月出」,兩個月字,便覺淺露。他如周草窗諸人,多有此病,宜戒之。
愚按,此條之意,與前論桃柳等字不可直説破者同,蓋力避鄙率淺俗之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