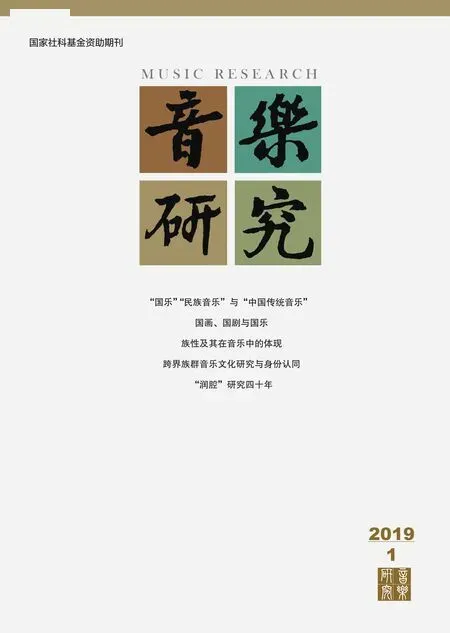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
——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
文◎赵书峰
传统音乐的形成与建构是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间“濡化”“涵化”的结果。任何原生性传统的形成过程决不是一源的,而是多元文化融合、互动而成的产物,其中包含对传统文化的发明、改造与借用,尤其是前者在传统文化的延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发明与改造,不但为了适应其所处时代社会、历史、民俗、审美语境的需求,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延续音乐的传统。只有成功实现对传统音乐的发明与改造,才能在其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完成本土音乐文化传统的重建过程。当然,这是基于族群文化间互动、交融过程中建立彼此身份认同基础上的文化重建。本土音乐文化在其长期地发展历史语境中出现的持续性身份重建过程,也不断促使对传统文化进行不断地发明与改造。“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率先提出的。他认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①〔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第一章导论:发明传统),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本文运用民族音乐学、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史学等相关理论,针对“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展开跨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正如霍氏所言:“对于传统的发明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它是一个将历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研究者联系在一起的研究领域,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研究就无法进行。”②同注①,第17页。
一、文化涵化与本土音乐文化重建
族群传统文化的涵化过程最终导致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并随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以及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即传统的“发明”),也就实现了传统音乐的重建过程,并预示其文化身份认同的变迁。传统音乐的涵化是指两种或多种传统音乐文化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音乐文本的互文特性。文化涵化的前提是指族群传统音乐文化之间彼此建立相互的认同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其音乐身份的重建提供更多地可能。同时也是在受到他文化影响下的对自我传统音乐的改造或发明。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它逐渐被“文化持有者”的民间艺人、审美受众、地方文化部门等充分认同以后,作为一种新的本土音乐文化传统进行保护与传承。传统音乐的形成轨迹,决不是一源,而是多源文化互动交融而形成的。在传统音乐文化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背景中,只有源源不断的新鲜活水注入进来,才能为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与流变提供更多新的内在驱动力,进而为本土音乐文化身份的持续性创建过程带来更多的可能。比如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很多乐种就是基于汉文化影响下的一种持续性地重建过程(如西南少数民族的戏曲、曲艺)。尤其受到当下全球化、现代化、流行化趋势影响下,一些少数民族音乐的演唱形式、乐器编配、表演语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导致其音乐身份认同的变迁。这种被发明的新的表演文本,在经历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逐步培养成一种新的较为固定的文化认同,从而也就实现了本土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比如,“侗戏音乐是在侗族民歌,如琵琶歌、叙事歌、大歌和山歌等的基础上,吸收汉族戏曲剧种(特别是阳戏)的音乐逐渐发展形成的。唱腔为曲牌体(自然形态的民歌)和板腔体(板式变化尚未有一定程式)并用的综合体结构。”③吴宗泽《谈侗戏音乐》,《民族艺术》1987年第2期,第192页。侗戏音乐其实就是侗、汉传统音乐文化的复合型文本。它是侗族传统文化的“濡化”(侗族民歌)与“涵化”(汉族传统戏曲)互动交融下的身份重建产物。因此,上述跨族群文化间互动交流的结局导致一种新的文化“传统”的发明与形成。
发明的“传统”首先是先前文化“传承主题”“时间链”“变体链”三者的互融、互构的结局。那么何谓“传统”呢?有学者认为,传统是“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的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④〔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译序),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从上述对“传统”概念的界定中包含的“传承主题”“时间链”“变异”(或者称“变体链”)三个关键词足以看出,任何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建构都是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中“濡化”“涵化”的现代结局。另外,它证明了传统的形成必将是基于自身文化母体作为传承主题,在与他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形成的一种“变异”“变迁”,这种所谓传统的新发明在经受其长期的社会历史积淀中,逐渐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化认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正如有学者对“民俗”概念的界定一样:
民俗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它是一国民族或一地群体民众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它呈现为一地社会民众里特有的风行的不成文(法)的程式化的规矩或文化心理模式,其间,它经过了反复的积淀过程,一旦形成,就依其定势,如射线状地发展,并不经意地包孕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器物用具、观念言行中。所以,民俗本身就是与一定人群生存密切相关的人俗,一种联系历史、展示现在、遥望将来的独特文化。⑤陈勤建《文化旅游:摈除伪民俗,开掘真民俗》,《民俗研究 》2002 年第 2期,第6页。
由此,让我们拓展到对“传统音乐”概念的审思,笔者认为,“传统”是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短时段内,其本质内核可能是很难看到其变化的,然而,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内回看其音乐文化的本质特征,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动态的、持续性的建构过程,而且是被周围文化影响下的一种持续性地重建过程,其结局就是传统的“发明”。当然这种“发明”的传统必须是与其文化母体保持密切的连续性。因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⑥同注①,第2页。因为,“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⑦同注④,第2页。比如,某些少数民族乐种多是在其传统基础上的与其他族群传统文化互动、交融后衍生出的一种新的乐种。比如蒙古族的“二人台”音乐、侗戏、布依族的小打音乐等,这些都是文化的“流”,而不是“源”,都是基于政治、军事、战争、贸易、移民等背景下导致的文化传播与涵化之结局。这些新的少数民族乐种的产生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形成地方性的区域音乐文化认同,进而建构成一种被发明的文化传统。因为,“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必然如此地留给后人的,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使用传统的材料,进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传统。作为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杂语言( 亦即福柯意义上的话语) ,传统一定是经由后人不断‘发明’而生产出来的。传统对今天的意义,就是根据当下的现实需要来建构一套复杂的话语和程序。”⑧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123页。另参见注①,第1—17页。如苗剧产生的社会背景,⑨杨鸽《苗汉文化撞击整合的产物——苗剧源流发展的一种解释推断》,《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6—130页。在历史的短时段内,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少数民族乐种,但不是一种纯粹的传统文化,因为它不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只是被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地方民间艺人进行的一种文化创造,但是它一旦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沉淀,这种新的剧种被当地的文化受众逐渐认同之后,才能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即少数民族戏曲——苗剧。正如历史学家彭刚认为:“霍布斯鲍姆所谓的“传统的发明”,就揭示了在各种现代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中,既包含了对于过往真实存在过的事件或传统成分的重新利用和诠释,又包含了对于并非过去真实出现过的要素的创造。”⑩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9页。笔者在2016年10月、2017年2月分别两次考察四川阿坝州茂县、理县羌族传统音乐文化,尤其针对羌族“夬儒节”(每年二月初二举办)中的“释比戏”表演与仪式的重建问题进行了跟踪与关注。羌族释比戏的重构与“非遗”项目的申报与茂县文化馆的韩树康先生的努力密不可分,他具有传承人、羌族文化研究者以及表演者(韩树康是一位舞蹈专业出身的羌族演员)三重文化身份。羌族释比戏的重构其实就是他根据《四川傩戏志》《羌族释比经典》文献中记录的关于羌戏书面文本,并根据羌族民间艺人采风资料,运用当下传承的羌族传统乐舞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化处理等基础上实现的“羌族传统文化的发明与释比戏表演的重建”过程。
传统的“发明”是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思维语境下的文化产物。因为任何传统文本的发展与传承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会在历史的长时段与短时段中经历与周围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上述结局无形中会造成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结构系统发生从解构到重构的历史性过程,此种文化变异现象将会最终导致族群传统文化的身份认同发生变迁。比如,西南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就是西方后殖民语境下音乐文化变迁的产物。换言之,它是受西化背景影响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身份(认同)重构的结局。因为,西方基督教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景颇族等)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本土文化的元素(如唱腔与经文的在地化)。所以,这种经历过20世纪初半殖民地语境下的西方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传播背景,为西南少数传统音乐文化的重建营造了前提,但是随着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重新审视这种西方宗教音乐在少数民族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历史与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当下的西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已经发展成为,被这些族群的“文化持有者”、基督教信众、地方文化部门乃至学界共同认为的、是这个区域内族群传统系统中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这个历史的认知过程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文化的身份重建轨迹(如贵州石门坎苗族基督教音乐)。总之,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话语霸权以及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受西方基督教音乐文化的影响下,致使其民间宗教文化系统发生变化,由此导致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仰系统发生解构性的改变。比如傈僳族、独龙族、布朗族等族群的传统音乐文化系统中融入了更多基督教音乐文化元素,并在基于少数民族语言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中西交融特性的新的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系统。杨民康认为,西方基督教音乐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基本上抛弃了本民族原存的传统音乐及其祭祀诵经风格。⑪杨民康《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笔者认为,这种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现象多是建立在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话语霸权基础上,通过多种文化(西方基督教音乐、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汉族传统文化等)之间的采借、吸收后产生的一种文化适融局面,形成一种“本土化”与“现代性”的互文本,即实现了少数民族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过程,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的习惯认知系统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发明的传统”。
总之,结合西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我们看出,“因为跨文化交流使得‘本源’的文化面目发生了改变,……但在被改变的过程中,被压迫者文化也对压迫者文化进行了‘改写’,并在与压迫者的空间竞争中言说自己,界定自己,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⑫查日新《空间转向、文化协商与身份重构——霍米 ·巴巴后殖民文化批评思想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第80页。还如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身份无非是‘集体经验’的聚结和建构,其方式就是通过建构对立面和他者;自我或‘他者’的身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仔细加工过的历史、社会、思想及政治过程;身份的建构,要依每个社会中权势的分配而定,它不仅是不自然、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被硬造出来的。”⑬转引自王宁等《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183页。
二、族群间彼此的文化认同是本土音乐身份重建的重要前提
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的前提是:族群文化之间彼此建立相互的音乐认同或相互妥协(或“文化协商”)。这是形成音乐文化涵化的一种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最终实现本土音乐文化身份走向从解构到重构,从而形成音乐的在地化过程。音乐的“在地化”过程就是外来音乐与本土音乐文化之间互动与交流后形成的音乐文本的一种重建过程。当然实现上述过程还是要基于传统音乐文化间的强势与弱势的对比情况而定。历史上当汉族传统音乐文化流播到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后者为了自身的保护与传承以及生存与发展,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主流文化认同,不得不在文化之间的博弈上进行妥协,这种结局就会导致传统音乐发生涵化现象。比如宋代熙宁年间(1072)中原王朝“开梅山”之后,在汉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下,苗、瑶族群为代表的“梅山蛮”的传统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了解构性的变化。如瑶族传统仪式音乐中加入了道教文化的元素(比如仪式用乐结构),以及瑶族因为无文字早期便以“刻木为契”⑭(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6页。作为信息交流载体,后来在汉族语言文字表述系统的影响下,瑶族传统文化中的书面信息交流开始采借汉字的表述方式(其中瑶族传统仪式经书中加入了很多新创造的“文字”)。瑶族先民的文化认知思维中形成一种接受过程,其最终结局就是实现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身份转换或变迁过程,或者说是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系统的重构。王铭铭认为:“……国家和文明产生,族群之间,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成为变迁的重要动力之一。古代帝国之间的冲突和征服使一种权力体系取代另一种体系成为可能,并曾引起大规模的文化取代和改造。”⑮王铭铭《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第3页。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山地的族群特征和认同不仅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而且也包含了他们与国家权威之间相对关系的密码。”⑯〔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8—39页。
族群之间彼此的音乐认同的结局会导致文化的互文现象。如蒙古族漫瀚调的形成,以及侗戏、白剧等少数戏剧音乐形成都与汉族传统音乐在少数民族区域内流播后文化涵化的现代结局。历史上以西南历史官道为文化带的“古苗疆”⑰此概念由贵州大学的杨志强教授提出。走廊的形成,是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向西南渗透、流播的征战之道、商业之道、多族群文化互动之道。尤其是明王朝设立的卫所建制背景下形成的军户移民文化,为西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重构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比如以瑶族、苗族、土家族、白族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吸收了大量的汉族传统音乐元素,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互文现象。又如目前流播在少数民族音乐中的传统器乐曲牌【朝天子】 【大开门】 【小开门】(如广西贺州过山瑶婚俗音乐中的唢呐曲牌⑱赵书峰《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历史与变迁》,《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2期,第20页。)等,虽然彼此之间的旋律音调发生较大改变,但是明显看出是受到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因为,这种鲜明的文化杂糅现象是对汉族主流文化认同的接受甚至是妥协的文化产物,因此,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少数民族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重构)现象。结合霍米·巴巴等人的后殖民理论来看,这是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动态‘协商’的结果,差异文化迫使进入者对自身进行了某些改变或“变形”⑲同注⑫,第77页。,如“明朝在元代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儒学,到处立孔庙、设学校、开科举。明王朝还用中原汉文经典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取代在大理长期流行的密宗。儒学的广泛推行,使云南文化与中原趋于一致 ”。⑳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3期,第111页。彭兆荣在研究瑶族文化认同问题中认为:“民族迁徙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域空间转移到另一个地域空间,更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族群所发生的互动关系。瑶族之所以有那么多支系,相互间的文化差别如此之大,民族认同如此复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长时间的‘小单位’移动中与其他族群产生‘临界’的互动作用,以致于在有些情况下,某一个民族的‘小单位’(如支系)虽在某一个符号下作‘名分’上的认同,而在文化的某些‘质’上却作了更接过于另一个族群的认同。”㉑彭兆荣《民族认同的语境变迁与多极化发展——从一个瑶族个案说起》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年第1期,第33页。因此,本土音乐文化重建的前提是彼此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达成一致,彼此协商与妥协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认同。
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影响力大小,完全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主导者所建构的“大传统”有关系。比如汉族传统音乐文化、西方古典音乐文化带来的强大的文化话语权,并在全球化、殖民主义、城市化进程的驱动下,对“小传统”之间的影响与改造,会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人口迁徙等手段建构而成。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之后,为了更好地达到与迁入地传统音乐文化的融适作用,必须结合其音乐的历史传统中的一部分作为核心元素进行改造,并与迁入地的传统音乐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区域音乐文化认同,同时也是更好地延续自我传统音乐文化集体的历史记忆。贵州“喇叭苗”的传统音乐就是移民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多元互融后的文化产物。有学者认为,“喇叭苗”族群构成相当复杂,有明初洪武时期前后进入的湖广土军和官军,更有弘治年间平定“米鲁之乱”后留下来的湖广土兵或官军,还有明中期自湖湘雇佣来黔的卫所卫戍军士中的游离者;籍贯有湘西、湘西南、湘中南的不同地域之分。“喇叭苗”群体及其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异源合流”。㉒叶成勇《贵州“喇叭苗”家族史调查与相关问题探析——以晴隆县长流乡为个案》,《地方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第26页。“许多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的输出,通常要经过形式、功能甚至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接受者一方文化的特殊要求。比如汉族道教进入黔东南,常以变化了的形式、功能和当地各族的传统信仰相结合;又比如汉族的戏剧传入侗族地区演变成侗戏,其中一些剧目从语言、形式到内容都发生许多变化,以适合侗族文化的要求。”㉓龚佩华《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1期,第89页。还如,西南少数民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系统内的西南少数民族道教音乐文化是湖南湘中梅山文化的深刻影响下的结果。它是道教文化在中国南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播扩散后,与各族群的传统信仰,传统音乐涵化后的文化产物。傩戏研究学者庹修明认为,贵州安顺地戏是中原民间传承的民间傩,随南征军和移民进入贵州,并与当地民情、民俗结合而形成的。㉔孙婕《贵州布依族小打音乐组成及文化探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31页。贵州布依族小打音乐是丝竹乐在流变过程中的产物,是从江浙一带汉族地区逐渐传入少数民族地区,经当地少数民族艺人加工之后,形成少数民族的丝竹乐品种。㉕同注⑫,第78页。因此,正如有学者认为:
凡是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社群相遇,就必然产生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 。交流发生的位置就在彼此交接的疆界区域,这个疆界不仅是两个异质的文化体相互区隔的界限, 更是一个“间隙”空间,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因素不断进入这个空间,彼此交织、碰撞,结果产生新的文化意义,它不是原来的任何一方,而是经“协商”后形成的全新的东西。 ……这种“协商”不仅可能产生两种文化传统的播撒,导致两个文化群体从它们各自文化的源头移位;而且可能带来一种共同身份,一种在杂交中产生的新身份,一种非此非彼的身份。这种交互影响的状态类似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每一个文本都对其他文本开放,因此文本间的交互影响改变文本原来的意义并不断产生新的意义。同理,不同文化之间的“杂交”也在不断地生成意义,这个过程是无止尽的 。㉖庹修明《中国军傩——贵州地戏》,《民族艺术研究》2001年第4期,第4页。
三、传统的“发明”是多维度权利与知识互动语境下的主观话语建构
传统的“发明”是国家行政权力、地方性知识、学者、民间艺人等多维度互动的主观话语建构。我们知道,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建构决不是自我文化的一种本真性的纵向传承过程,而是与周围族群文化互动交融后的产物。这种过程既是文化间自然选择的结果,同时又是受国家在场作用下的一种主观话语建构。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为例,若从当下反观历史发展语境,某些传统音乐文化的原生性、本真性问题却很难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任何传统文化在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都是多种文化间涵化的产物,即文化互文的结果。葛剑雄认为:
在南方,随着汉族聚集区向山区和边远地方的扩张,当地原有民族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但除了少数人迁离原地,向更南更深的山区转移外,多数人选择了与汉族人共同生活的方式。由于南方的非汉民族基本也都从事农业或半农半其他产业(如采集、狩猎、养殖等),因而比较容易与汉人结为一体。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先进地位和统治者必然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在取得了与汉族大致相同的经济地位之后,采用了更改民族身份的方法来摆脱受歧视的处境。他们往往编造出并不存在的汉族世系,证明自己的汉族身份。实际上,历史上曾经在南方占优势的越、蛮、夷等族系人口,大多并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而是融入了汉族人口之中。㉗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相反,在南方与少数民族混居的汉族为了逃避赋税,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与生活习性,逐渐改变自己的族群文化认同,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身份。据清代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傜人》(卷7)记载:“诸傜率盘姓,有三种: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岁七月十四拜年,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傜。”㉘(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傜人》(卷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费孝通认为:“有些汉人迁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汉族的特点,但是不明确自己是不是汉人,以附近少数民族称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而被视为少数民族。”㉙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页。所以看出,“有两种对于文化身份的理解。一种是本质主义的,认为文化身份一旦确立,就不容易变更;一种是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文化身份总是时刻被塑造着的、永远没有完成的流动着的东西,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着的未完成状态。”㉚苏勇《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中的文化主体性》,《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第94页。同时证明:“事实上身份是关于使用变化过程中的而不是存在过程中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那在我们有可能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㉛〔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编著,庞璃译《文化身份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如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认同的变迁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中为了不断地适应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与文化冲击,以及为了实现自我传统音乐文化的长期发展与传承而选择的一种应对策略,这种做法就是文化自觉地表达。比如,土家族哭嫁仪式音乐,由于现代化、城镇化、流行化语境的广泛影响,其原生性生存语境被现代化的信息与交通,以及民俗旅游经济的过度开发造成的仪式用乐环境的变化,其文化的原生性在逐渐消失。同时由于土家族哭嫁仪式音乐的传承环链被现代化文化语境逐渐地解构,土家族女孩在结婚之前很少有机会学习哭嫁歌的唱法,导致其传承环链与传承语境发生变迁,因此,在土家族的某些地方的婚俗仪式中,虽然有哭嫁行为,但是其音乐中已经加入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如贵州沿河土家族哭嫁音乐中用流行歌曲《妈妈的吻》来替代),这些哭嫁仪式音乐结构的改变,也就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过程,同时这种结局来自于内部的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用乐语境的逐渐消失,以及外部的现代化、流行化、城镇化进程对土家族本土音乐的强烈冲击影响下的文化产物。
以当前的“非遗”项目的族性界定为例,某些文化官员、研究者、地方民间艺人仍带有鲜明的本质主义思考。他们在对族群传统音乐的“非遗”项目的族性界定时仍固守传统的学术思维,没有针对其民族识别存在的问题展开反本质主义思考。比如,满族“吵子会”音乐,若以后现代主义思维观照它其实就是跨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交互文本,是国家在场语境下跨族群文化间彼此妥协形成的一种区域音乐乐种。因为我们很难界定“吵子会”到底属于哪些族群的“传统音乐”,因为,从其用乐人身份、乐器构成、传统曲牌看与汉族传统音乐没有区别,但是当下其用乐人的身份分别属于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可以看出,这种乐种的族群边界随流播而移动(汉族——满族——蒙古族),进而实现了音乐在跨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区域音乐认同的形成)。所以,这在某种情况下为其族性界定带来困惑。但是,据笔者调查,该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选取某村的这个乐种作为“非遗”项目进行申报,不但是由于该村乐人的演奏技术相对较好,而且还可以把它作为该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进行推广,并没有真正考虑这种音乐原本的族性特征。所以,当下的“非遗”是国家政治文化权力与地方性知识相互作用下的一种主观的话语建构,是文化部门、学者、民间艺人等多方“共谋”的文化产物。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的共谋所决定的话语。㉜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 年第1期,第125页。如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文化自觉,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运用地方文化资源,建构地方的文化身份认同。然而,必须认识到并保持警觉的是,地方在发掘原生态文化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展示,同时也是在表述,是为了使他们所构想的认同能够被更大的世界所承认。在这一文化创造的过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为他人生产自我,还是为自己生产自我。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原生态文化发掘中,更多地表现为前者。㉝刘晓春《谁的原生态? 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7—158页。
笔者认为,当下的“非遗”问题,就是为了在发展地方民俗旅游经济文化中,在基于本土音乐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他人生产自我”。比如将原生态的土家族哭嫁仪式音乐进行精心打造后,挪移到民俗旅游村中进行“原形态”舞台化展演,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以及满足游客“猎奇”的心理。因此,一些地方民间艺人、文化部门、民俗旅游村的投资方等必须要对土家族哭嫁仪式音乐进行系列性舞台化艺术改造,其行为本身就是“为他人生产自我”。
四、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在当下的社会意义
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地方民俗旅游文化经济的背景下,一些传统音乐文化资源被作为“民俗”产品打造起来,作为推动地方经济的重要载体。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被民俗学研究者批判地认为,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追求文化政绩,对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进行了改造甚至是造假,因此称之为“伪民俗”。笔者认为,我们反对造假的文化宣传,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建立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创新与改造,只有这样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当然,改造决不是造假,改造是基于历史积淀上的创新,是为了拓展其传播与受众的渠道,最终目的是通过发展地方旅游文化经济进而为当地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注入更多的能源和能量。其次,这是对当地传统音乐文化的“发明”的结果。因为任何传统音乐文化在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中,决不是其源的本真性的传承,而是与周围文化互动、交流融合而成的文化互文。我们很难考究和区分传统音乐文化的“本真性”“纯正性”的基因有哪些?因为,所谓的传统音乐文化就是基于其源的基因基础上的“流变”在当下的历史积淀。同时也是为了“文化持有者”对其拥有的“地方性知识”得到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以及适应其所处的政治、社会、历史语境而自愿做出的改造和创新,这种动机本身是为了长久地传承其文化而做出的一种主动选择。我们知道,很多的民俗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后,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改造与创新,以及长期的艺术实践后形成的文化样态相对较为固定的一种地方传统音乐。所以,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构问题绝不是被民俗学界认为的文化造假行为,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当下社会语境而做出的一种主动选择。当然这种发明的传统音乐一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新的“传统”。比如,当下的某些传统戏曲与器乐音乐中加入的西洋乐器,在若干年之后是不是被视为一种发明的“传统”而存在?很多少数民族民俗仪式(婚俗、丧礼)音乐中加入了流行文化元素,这也可以被视为对民俗音乐文化的一种改造,若从当下反观历史,这种对当下民俗仪式进行改造和创新的做法,难道是一种“伪民俗”现象吗?伪民俗是一种文化造假行为,主要是指某种新发明的“文化”缺少历史积淀(厚重感),完全切断与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主题”之间的血脉联系,而传统的发明则与之完全相反,它是在基于传承某种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主题”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变迁现象,这种文化的涵化现象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积淀之后,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即发明的“传统”。所以,传统的发明完全具备了文化“传承主题”“时间链”“变体链”三个主要条件。总之,“伪民俗”与发明的“传统”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与过去的文化“主题”保持某种密切的历史关联,我们不能把两者之间划为等号。比如,老挝、泰国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发展与变异问题,就是瑶族在经过长期的族群迁徙过程中,受到迁入国家政治、历史、语言、音乐(尤其老龙族乐舞以及泰国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对其传统仪式音乐结构进行的采借与改造,其本身就是对传统音乐的一种“发明”,这种文化的采借、融合、变迁现象也实现了对老、泰瑶族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过程。所以,笔者认为,传统音乐文化在一个历史的短时段中,我们认为是一种改造和创新,而不是一种文化造假行为,同时若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进行观照和审视,它其实就是一种被发明的文化传统。因为,发明的传统必然要经过与过去(历史)建立某种联系。
其次,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利益,致使本土音乐文化在原有传统与历史的基础上出现重建现象。长此以往致使这种被重构的本土文化变成了大众接受的文化传统,进而形成一种“发明的传统”。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为例,当下的“非遗”的申报、少数民族民俗旅游村中的文化表演,等等,都是通过官方、“地方性知识”、民间艺人以及学者的互动参与下建构的一种“发明的传统”。其目的在于最大化地获得经济与社会利益,并在保护与传承地方本土音乐文化方面营造更浓厚的社会氛围。比如,笔者2016年7月考察云南剑川白族“石宝山歌会”得知,作为一种国家级“非遗”项目,为了使这个传统的民俗节日更好地拉动地方经济,主办方挖空心思将原生性的对歌场景进行改造与创新,如将传统对歌形式搬上政府专门为之搭建的对歌台进行表演,同时加入了竞赛环节,还有专门的评委为歌手打分,这种做法也就导致了传统歌会的表演语境与文化象征发生变化。因为,原生性对歌场景主要是在山间树林中进行,更强调其民俗功能(尤其是民歌文化的性俗功能),当下为了强调文化宣传与艺术表演的功用,经过认真改造后搬到舞台上进行展演,更加突出了其对歌的艺术功能、审美功能,当然其民俗功能也基本消失。因为,这些歌手都是作为竞赛与表演目的的一种强强联手,并不是原生语境中的作为一种民俗文化而存在的对歌形式,并且对歌内容也由于用乐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为,早期的原生性对歌场景多带有求偶、性俗心理的暗示与表达,一旦将其搬到舞台进行表演,这些歌唱内容也会受到来自多方语境的影响而改变,歌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反应当下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的考量。尤其是对歌的艺术性将会放到重要的环节来表达。
第三,“传统的发明”旨在通过搜集与挖掘更多、更古老的地方性历史知识,甚至通过“结构性失忆”的行为来重构本土音乐文化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并通过政府、地方学者挖空心思的系列性改造,打造成一种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标签,在发展地方旅游文化经济与追求文化政绩方面营造更多的文化资本。通过运用“地方性知识”以及“结构性失忆”的文化策略建构一种旨在与过去形成历史联系的新的“传统音乐”。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为例,可以看出,一些音乐种类的形成与发展多是由于宋代以来,中原王朝为主的“开边”行为造成的汉族传统文化对其涵化作用的产物。比如西南少数民族戏曲音乐,传统民俗仪式中的乐器以及曲牌的构成,都是明代以来卫所文化移民的产物。在强大的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冲击影响下,致使某些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认同出现变迁。比如,将音乐文化品种的结构运用汉族传统元素进行改革和创新,在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失忆”过程其实也是对其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发明与改造,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其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语境而自愿做出的一种认同的调试过程,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结构性失忆”行为来达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结构的重建行为。
结 语
传统音乐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内,是不同音乐文化之间“濡化”“涵化”的当下结局。 传统的“发明”是建立在其母文化基础上的,对他文化的一种吸收、改造与创新,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应其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审美化需求。传统的发明与彼此的身份认同是本土音乐文化重建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语境中为适应当下社会受众语境而做出的持续性重建。它迫使民间艺人(用乐者)结合“地方性知识”与他文化素材进行发明、改造与创新。当然,这种由传统的发明导致的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过程鲜明地描绘出其文化认同变迁的历史轨迹。所以,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都是为了适应当下多重的社会语境(全球化、城镇化、商业化、流行化等)的冲击下而做出的一种策划性的主客观选择。因为,“任何文化都不是自古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化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物(being),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转换过程(becoming)。……真正的新文化居于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和临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㉞同注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