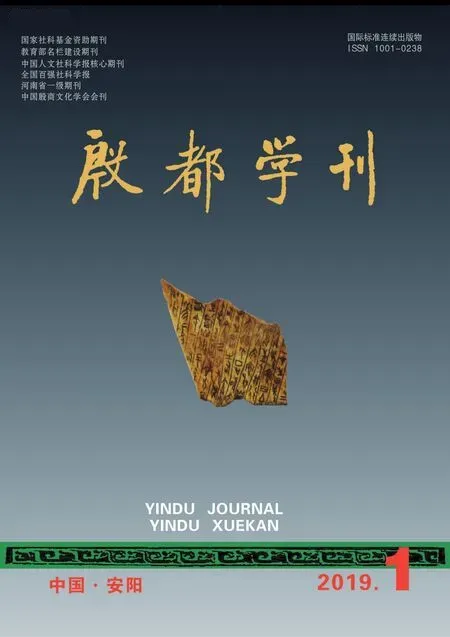汉语能性述补结构句法语义研究述评
周 红,李晨璐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一、引言
能性述补结构,是指由动词或形容词加上“得”或“不”再加上补语或者加上“得/不得”做补语的形式。该结构是具有汉语特色的语法形式,使用频率高,具有“能/会/可以”等能性助动词所代替不了的功能。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是用情态动词来表达能性范畴,汉语则还可用能性述补结构表达,从此将其与情态(modality)挂钩[1]。能性是情态范畴的子范畴,是说话者由于对事件或命题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表达估计或判断的意义。
学界对能性述补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下面从术语变革与理解、句法语义特征、句法语义演变等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功能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另文概述。限于作者学识及篇幅,对能性述补结构研究丰硕成果的梳理与分析难免挂一漏万,望专家学者原宥。
二、能性述补结构的术语变革与理解
(一)术语变革
能性述补结构经历了“可能式”“可能补语”“能性补语”“能性述补结构”的变革。王力(1943)将“V得/不C”结构称为“可能式”,即“凡能愿式之表示可能性,必然性或必要性者”[2](P68-81);范继淹(1963)认为“V得/不X”唯一可能的分析法是V与X先组合,然后和“得、不”组合,就是把“V得/不X”作为“VX”的一种特殊扩展形式[3];丁声树等(1961)[4](P60)、张旺熹(1999)[5](P135-162)等有“补语的可能式”之说;岳俊发(1984)将之概括为“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可能式”[6]。与此同时,杨建国(1959)第一次正式使用“可能补语”[7](P94,109),赵元任(1979)[8](P210-212)、刘月华(1980)[9]、朱德熙(1982)[10](P132-133)等也使用这一术语,如朱德熙认为大部分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都可转换为可能补语。“可能式”“可能补语”这两个术语体现了“得/不”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是否增列补语类型的区别。后来,李晓琪(1985)提出使用“能性补语式”,因为用“可能”来概括不够准确、全面,还可表示“能够”“可以”[11],李剑影(2007)也使用了“能性补语”这一术语[12]。我们赞同“能性”一词的说法。吴福祥(2002a)提出使用“能性述补结构”[1],将“能性”与“述补结构”相结合,既能关照语言类型,将其与述补结构关联,又能关照汉语结构,并将其与情态表达关联。我们认为这一术语突破了传统语法将“可能补语”作为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下位概念的狭隘理解,也突破了“补语的可能式”的观念,开启了对该结构研究的新思路。
(二)能性情态的理解
对于“能性”语义的概念,学界分析不断深入。吕叔湘(1944/1984)认为“得”有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的区分,即“能与不能,以行事者自身之能力而言;可与不可,则取决于外在之势力,如情理之当然,如他人之好恶,而非行事者本人所可左右者也”[13](P127)。在此基础上,刘月华(1980)将“能”的意义分为“主观能力”“客观条件”“有可能”“准许”“情理上的许可”等五种意义,其中“V得/不C”“V得/不了”表示的意义大体上与前三种相当,“V得/不得”与后两种语义相当[9]。这一分类体系得到较多关注。吴福祥(2002a)将能性述补结构与情态(modality)挂钩,进一步阐述了以上五种意义[1]。李剑影(2007)认为能性范畴是情态范畴的子范畴,能性述补结构可表达动力情态、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12]。范晓蕾(2011)则将情态归纳为“内在能力”“条件可能”“条件许可”“道义许可”“认识可能”五类基本能性情态概念和一种边缘性情态概念“估价”,其中“内在能力”和“条件可能”属于动力情态,“条件许可”和“道义许可”属于道义情态,“认识可能”属于认识情态[14]。这些研究为能性述补结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对能性述补结构的理解往往与能性助动词相联系,如丁声树(1961)[4](P60)、赵元任(1979)[8]、朱德熙(1982)[10](P132)等认为表示可能和可能性,如“拿不住”表示“不能拿住”,“回得来”表示“能回来”,然而这种用“能+VR”来解释“V得/不R”的替代观念,不易更好地理解这两种表达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张旺熹(1999)认为典型的“V不C”表示“愿而不能”,“愿”即企望义,指人们主观上企望执行某种动作行为以实现某种结果的意义;“不能”,即不可能,指整个结构表达由于客观原因而使结果不能实现的意义[5](P135-162)。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诸多认可。孙姃爱(2009)认为行为主体的主观意向与影响能否实现某种动作或结果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认知上反映为一种“动力”的对立关系,她运用泰尔米的动力学模式(force dynamics)进行了分析:主体能够克服客观条件的阻碍时,主体就能实现自己的心理趋向,反之,主体不能克服这些阻碍时,主体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心理趋向[15],这一研究更关注语言结构之间的内部语义条件。然而,主客观条件的区分标准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能性情态的判断
对于如何判断能性情态类型,学界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李剑影(2009)认为能性补语认识情态意义的产生是由语用推理引起的,即施事具有进行动作的能力或客观条件,一般就隐含着说话者推测施事有进行某种动作的可能性;当主语由受事充当、主语对补语结果缺乏控制能力、C无法作为主语的目的(包括C的虚化)等句子内部因素下产生认识情态意义[16]。具体须分类别判断:第一,“V得/不C”可表动力情态,其中“V”须是自主动词[12][15];还可表认识情态,这时主语对补语没有控制能力,如“有了这个,在丽江就走不丢了”,可用“怎么V 也 V 不 C(N)”句法检验槽检验;且C相对于主语偏离目的性,多是贬义词,如“吃不好,也肯定吃不坏”;多出现在反问句中,且同现成分具有猜测义,如“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12]。第二,“V得/不了”可表动力情态,其中“V”的语义特征具有[+可控性][12]或者具有[+动态性][15];也可表认识情态,这时“V”为非可控动词或静态形容词[12] [15]。第三,李剑影(2006)认为“V得/不得”表示道义情态,句法条件是不带宾语[12];孙征爱(2009)则认为“V得/不得”可表动力情态,表达主客观条件能否实现某种动作;也可表认识情态,条件是与静态形容词搭配,如“真是一行归一行,错不得”;也可表道义情态,条件是强调叮嘱、警告、劝诫语气时[15]。这些对探究能性述补结构具有促动作用,然而还比较零散。除此之外,范伟(2017)运用Palmer情态系统举例分析了能性述补结构的情态类别,如“V不得dé、V得/不了、V得/不上”“X不得de”“X得/不着zhao”“X不了”等分别表达能力型动力情态、劝谏型道义情态、许可型道义情态和断定型认识情态[17],为今后研究提供了诸多值得关注的研究选题。
三、能性述补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
(一)句法语义类别
根据中缀“得”字的有无和“得/不”后面补语的虚化程度,能性述补结构的句法语义类别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两类说”,即分为“V得/不得”“V+得/不+结果补语/趋向补语”,以朱德熙(1982)[10](P125-126,132-133)、吕叔湘(1980/1999)[18](P165)和黄伯荣、廖序东(2002)[19](P98)为代表。第二种是“三类说”,即分为“V得/不C”“V得/不得”“V得/不了”,以丁声树等(1979)[4](P60-62)、刘月华(1980)[9]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编的《现代汉语》(2004)[20](P325-326)为代表。第三种是“四类说”,即“V得/不得C”“V得/不得”、带傀儡可能补语的“V得/不了”“V得/不来”以及熟语性可能补语,在“三分类”分类上把熟语性可能补语加进来。以赵元任(1979)为代表[8](P211-212)。以上第三种分类最为细致。
(二)句法语义限制
1.“V得/不C”的句法语义限制
学者多从语义特征、语义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如张旺熹(1999)认为“V不C”中“V”和“C”须具有“自主性”和“目标性”[5](P135-162)。不过,张文的分析并不全面,如“轮不到、长不大”等中“V”为非自主性,“吹不倒、吃不腻”等“C”为非目标性。黄晓琴(2005)则认为能否插入“得/不”取决于行为者的主观意愿,即是否愿意使补语的结果发生,如“说了多少次了,这些坏习惯怎么就丢不掉呢?”中的“丢不掉”,并认为“主观意愿”受客观逻辑和社会价值观念限制[21]。郝玲(2006)认为能否构成能性述补结构的条件与说话人主观意愿没有必然关系,而是以说话人认为结果的出现是否需要不太容易实现的条件为前提,如“他写得错这个字”通常不说就是因为“写错”比较容易实现,因此贬义形容词也可进入其中[22]。孙姃爱(2009)认为动结式能否扩展为能性述补结构取决于动作-结果的语义类型,然后根据区分补语类型进行细致分析,如当补语是形容词时,“VC”表达行为者预期的理想结果和中性结果时可构成能性述补结构(如“学不好”“吃得多”),“VC”表示预期结果的偏离时则不能构成能性述补结构;“VC”表示非理想的结果或自然的结果时只表道义“V不C”,如“写不错”“长不大”等[15]。安本真弓(2007)分析了动趋式(V+D)向动可式转换的条件:V(+自主)D(+方向)或(+结果)或(+停止)或(+持续),不可转换条件是V(-自主)或 V(自身运动)D(“上”类、“来”)或 V(+自主)D((+开始)或(+中动)),并提出动可式“V得/不D”是对动趋式“VD”实现可能性的判定,判定条件有两个:确认施事是不是有能力做出“V”这个动作;确认“V”做出以后,能不能出现“D”这种结果[23]。
动词的方向性、语义性质、音节等因素影响“V得/不C”。如骆锤炼(2007)认为形容词能否充当可能补语要受动作方向性的制约,如动词对形容词表达的意义起的制约作用是单向或多向的,可以构成可能式(如“剪得/不短”“染得红”);如果是双向的,也可以构成可能式,但符合自然结果的,可自由地构成可能式,不符合自然结果的,可有条件地构成可能式(如“切得/不薄”“切得/不厚”)等[24]。高增霞(1999)认为“V得A”可能结构的要求是:“V”是动作性强的自由动词,A是性质形容词和动态形容词,V和A之间有控制关系,即V对A产生影响[25]。孙放(2014)认为进入“V得/不C”的双音节动词比单音节动词数量少一些,V一般为动作动词和动态形容词,前者包括活动动词、自身动作动词、部分趋向动词、感受动词、部分心理动词和部分状态动词等[26]。
2.“V得/不了”的句法语义限制
可通过语义分化分析,如李宗江(1994)将其语义分化为“了”实现的可能性和“V”实现的可能性,分别如“没必要点这么多菜,吃不了”“要是找不到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27]。林可(2001)将前种意义细解为“V尽数解决受事或客事的可能性”,必须有数量成分,如“这个体育场容纳不了五万人”[28]。柯理思(2000)认为“形容词+不了”偏于认识情态,这时施事对事件的“可控”特点消失了[29]。
进入其中的动词特征,如郭志良(1980)认为除动词外,静态形容词和动态形容词也可进入其中,前者构成的“A不了”强调性状变化的结果,后者构成的“A不了”强调性状变化的过程[30]。刘月华(2001)认为“V得/不了”主要用于口语,所以口语中不常用的动词或形容词不能构成“V得/不了”[31](P591)。金椿姬(2005)认为能愿动词、离合词、与“得”字结合形成的动词、判断动词、致使动词、表抽象行为的动词(如爱好、抱歉)等不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不能进入“V不了”;能够进入“A不了”中的单音节性质形容词明显高于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且其褒贬色彩也是影响进入“A不了”的主要因素[32]。
3.“V得/不得”的句法语义限制
通过语义分化分析,李宗江(1994)将“V得/不得”语义分化为“客观报道动作实现的可能性”和“期望或不期望动作的实现”,分别如“老人牙齿一颗未掉,肉也吃得,酒也喝得”“这是赚钱的买卖,当然干得”,前者因为表动作可能性的“V得了”的大量出现失去了在系统中存在的价值,正在消失,后者除疑问句外一般只用否定形式[27]。齐春红(2004)将“V不得”分为述事行为和行事行为两类,语义分别为[+客观,+已然,+不能]、[+主观,+情态,+不许],述事行为又分为凸显施事不能做出反应或无行为能力和凸显受事或其他范围,行事行为表温和、委婉地请求、建议或劝阻[33]。
进入其中的动词特征,吕叔湘(1980/1999)认为“V得”中“V”限于单音节,否定式“V不得”中的“V”则不限于单音节[18](P165)。刘月华(1980)认为口语中不常用的,或动作者不能控制动作的动词(非可控动词),或判断动词、能愿动词等不能进入“V不得”中[9]。孙姃爱(2009)则认为非自主动词也可以进入“V得/不得”,如“死不得”“病不得”[15]。
(三)“得/不”的语义与性质
“得/不”是否表示可能或可能性仍存在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表可能或可能性,如吕叔湘(1944/1984)认为“得”表示可能性,“不”表示不可能性[13](P127-138)。王力(1943/1985)认为“得”字放在叙述词后面的时候,和“能”字的意义差不多(如“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即表示“能、能够、可以”等词汇意义;插在叙述词和末品补语中间的时候,表示可能性(如“什么事瞒得过我?”)[2](P69-70)。房玉清(1992)认为“得”和“不”表示有没有能力实现动作的结果[34](P260)。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如岳俊发(1984)认为可能式补语中的“得”表示动作完成所造成的某种结果和趋向,这时“得”本身不再具有“可能”的词汇意义,它已经完全虚化,只起连系补语的作用[6]。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中“得”是助词,已得到共识,但其与状态补语结构中“得”是否同一,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不同一,如朱德熙(1982)认为前者是助词,出现在述语和补语之间,既不属前,也不属后,应该三分(如“看/得/见”);后者是动词后缀,应该二分(如“看得/多”)[10](P125-126)。陆志伟(1964)也持此切分观点[35](P78-79)。第二种观点是同一,如吴福祥(2002b)认为切分不同是因为这两种格式的韵律特征和信息结构有所不同,这不足以证明“得”的语法性质有别,从历史语法来看,认为表实现的“V得C”演化为表可能的“V得C”,“得”性质并无不同,都是结构助词[36]。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得”中“得”是助词还是助动词,还存在一些争议。如吕叔湘(1944/1984)认为“得/不得”古时用于动词之前,后来置于动词之后,由原来的独立语词降为附属字,其情形与英语able转为-able相似[13](P127-138)。力量(1990)认为“V得/不得”来源于“得/不得”置于动词之后,“V得/不得”中“得”表示“能、能够、可以”的词汇意义,与助词“得”语法功能完全不同,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37]。
关于能性述补结构中“不”的语法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助词说,如吕叔湘(1980/1999)认为是助词,它的作用是“放在动结式、动趋式复合动词的两部分中间,表示不可能,跟表示可能的‘得’相对。轻读”[18](P91-92)。第二种是中缀说,如赵元任(1979)把“V不C”中的“不”看作是插在动词和补语中间的中缀[8](P210)。第三种是否定副词说,如陆志韦等(1957)[35](P55-56)、杨建国(1959)[7]视之为否定副词,吴福祥(2002b)从历史语法和方言角度进行了论证:表实现的述补结构“V不C”是通过对主谓结构“V(O)不Vi”重新分析而来的,主谓结构中“不”修饰谓语谓词,是典型的否定词;表实现的述补结构“V不C” 是“VC”的否定形式,“不”修饰补语谓词,也是典型的否定词;“V不C”由表实现变为表可能,“不”的语法性质不变,仍分析为否定词;另外,汕头话对应于普通话“V不C”的格式除“V唔C”外还可以是“V唔得C”,“唔”的语法性质是否定副词[36]。第三种观点获得更多认可。
四、能性述补结构的句法语义演变
(一)能性述补结构的语义来源
1.能性述补结构能性义的来源
关于能性述补结构能性义的来源,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能性意义来源于“得”和“不”。持这一观点的有:黎锦熙(1924/1992)[38](P123-124)、王力(1943/1985)[2](P70)、吕叔湘(1944/1984)[13](P127-138)、赵元任(1979)[8](P210-212)、房玉清(1992)[34](P259-266)、汪国胜(1998)[39]等。第二种是能性义是格式赋予的,即能性意义是整体结构在语境中派生出来的意义。如岳俊发(1984)[6]、杨平(1989)[40]、蒋绍愚(1994)[41](P196-201)、吴福祥(2002)[1]等。
第一种观点建立在“得/不”插入述补结构“V C”构成基础上,如赵元任(1979)认为如果动词和补语都是自由的,就一定能加得进“得/不”[8](P210)。然而,吴福祥(2002b)认为“充其量只能视为一种共时的变换分析,并不反映历时的句法派生过程”[36],并且并不是所有的能性述补结构都是“得/不”加上趋向补语或者结果补语构成的,也正如石毓智(2000)所说:可能式的语法意义并不是V和R与否定标记的简单相加,它有一个外加的结构意义——动作行为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应该把可能式看做一种独立的结构,不是由普通的动补结构通过插入某些成分变换来的[42]。第二种观点获得较多认可。
2.“得”表可能的来源
“得”表可能的来源,目前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后置说,即表可能的“得”从动词前表可能的助动词“得”后置而来,以杨建国(1959)[7]、岳俊发(1984)[6]、李小华(2007)[43]为代表。李认为先秦至中古时期强式助动词“能/可”对“得”的能性助动词功能产生排斥力,迫使它作其他功能的转移,这是“得”字后置的触机;“得”实现弱势功能向强势功能转化是其内在的动力;使成式动补格在汉代的广泛运用又为其提供了条件,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助动词“得”在汉代后移,成为表能性的后置助动词,后引申为表能性的中置助词[41]。第二种是虚化说,即表可能的“得”是从表“获得”义的动词虚化而表实现、结果,再进一步转化为表可能,表示为“得”经历了“获得”义动词→结果补语→动相补语→结构助词的演变过程,以王力(1980)[2](P300)、杨平(1990)[40]、吴福祥(2002a)[1]为代表。第三种是虚化+后置细分说,即“V得”中的“得”是表实现的“得”的虚化,“V不得”中的“不得”可视为助动词否定式“不得”的后置,以太田辰夫(2003)[44](P213-216)、蒋绍愚(1994)[41](P196-201)、李晓琪(1985)[11]为代表。第四种是复合虚化说,即表可能的“得”有两种来源:达成义“得”的虚化和致使义“得”的虚化,以赵长才(2002)为代表[45]。刘子瑜(2003)对赵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很难证明“得”与“使、令、教”等在句法上具有平行表现,因此难以确定是从达成义还是从致使义发展而来[46]。目前第三种观点获得较多认可。
3.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形成
“V得/不C”的语法化与语境、“得/不”的虚化有关。如吕叔湘(1944/1984)最早做出解释:“语其由来,未必为‘得’字之省略,盖旧来自有此种句法,如‘呼之不来,挥之不去’,唯本用以表实际之结果者,今用以表悬想之可能而已”[13](P127-138)。蒋绍愚(1995)认为吕先生这段话说明“V不C”原来是“VC”的否定形式,“V不C”原本表实际之结果,后来才表悬想之可能,蒋认为“V不C”出现早于“V得C”,汉代时述补结构“V(O)不C”是主谓结构经过重新分析而成[47]。在此基础上,吴福祥(2002a)进一步论证了以上观点:(1)“V得C”的语法化与“得”的虚化、语境密切相关。获得义他动词“得”用于非获得义动词后逐渐虚化为表动作实现并有结果的结果补语,唐代时演化成表示动作实现或完成的动相补语,“V得”其后若接谓词性成分构成“V得C”,这时“得”逐渐演变为用作补语标记的结构助词,这是因为“V得C”中补语C已蕴涵了表示动作实现或完成的语义,“得”原有的表示动作实现或完成的语义功能逐渐消失,表结果或状态实现的“V得C”用于叙述未然事件的语境里,就变成了表示具有实现某种结果或状态的可能性。(2)“V不C”的来源跟“V得C”无关。述补结构“VC”的否定形式是“VFC”而非“FVC”,唐代后否定副词F才固定为“不”,用于否定完成体,表实际之结果的“V不C”用于未然语境,就变成表悬想之可能。(3)“V不C”的语法化早于“V得C”。宋代时“V不C”已摆脱对待定语境的依赖,语法化为能性述补结构的专门语法形式;至迟在明代时“V得Vi”已语法化为结果补语结构的可能式,清代时表实现的“V得Vd”已基本消失,至现代汉语“V得A”则仍兼表实现和可能,因此“V得C”仍是一种尚未充分语法化的句法结构[1]。
“V得C”由表现实到表可能,获得较多认可,张汶静(2011)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V得C”来源于动补结构“VC”,“VC”格式的正式确立以及表否定可能的“V不C”的常用化,再加上表肯定的可能式的缺失以及所示音节韵律上的平衡等诸多原因,共同导致了与“V不C”结构对称的、表肯定的可能式“VdeC”的出现,其中“de”由于补语标记“得R”已经出现,于是类推借用这个结构助词,在此基础上,表可能的“V+得+C”(唐代)发展成为表现实的“V+得+C”(宋代)[48]。然而,文中所举历时语料并不能很好地证明这一观点。
“V不C”的形成与“不”的虚化有关。如沈家煊(2006)认为“V不C”的语法化并未体现对语境的依赖,而是其否定含义使它直接发生了主观化,在语用推理的作用下产生了能性含义;否定式早于肯定式出现,也说明演变首先发生在否定式,肯定式在一定程度上由否定式类推而最终确定下来[49](P185-205)。在此基础上,潘晶虹、何亮(2015)认为“不”是促使“V不C”语法化的重要诱因,“不”是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否定词,使用范围广泛,易使表结果的“V不C”发生重新分析,而相应的“没”是对过去、已然的否定,使“没VC”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存在/实现”,不易发生语法化[50]。
(二)能性述补结构的句法演变
1.“V得/不CO”的句法演变
关于近代汉语“V得OC”的产生来源,杨建国(1959)认为能性结构“V得/不C”是由表获得义的“V得O”发展而来的,即在带宾语的“V得O”上直接增加补语C,由于补语C已经蕴含了表动作实现和完成的语义,促使“得”的动作实现和完成义消失,补语C便直接粘着在“V得O”后用以表达动作实现和完成的可能性[7]。
近代汉语“V得OC”到“V得CO”以及“VO不C”到“V不CO”的可能补语宾语位移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
第一种是“得”的虚化。如赵长才(2002)认为中古汉语“V得OC”中动词较受限(多为抽象性较高的动词),随着“得”的虚化,动词不再受限,“得”特定的语法位置使得它朝向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的方向发展,这促使可能补语宾语位置的转移,元明时代“V得CO”用法渐多,并在清代彻底取代了“V得OC”[45]。
第二种是“V不CO”式能性义明显。如杨建国(1959)认为“VO不C”粘合并不紧密,C只能是及物动词,这一结构表动作的状态还是结果区别不太明显,因此转变为“V不CO”结构[7]。张美兰(2003)认为表能性的否定结构产生早于表结果义的结构,能性义明显的“V不CO”结构必然取代“VO不C”[51](P307-315)。
第三种是可能补语的语义指向。如石毓智(2002)认为可能补语是说明动作行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语义指向前面的动词,这使得可能补语C会尽可能地靠近动词,随着C的前移,宾语相应地也发生了位移,由“V得OC”到“V得CO”、“VO不C”到“V不CO”[52]。沈家煊(2006)将其概括为“动词吸引”规律,即负载重要信息的动词核心倾向于将负载次要信息的成分吸引过来[49]。
第四种是“V得/不C”不带宾语结构的大量使用。如郑培煜(2013)认为宋代“V得/不C”结构不带宾语结构大量使用,使得补语C慢慢失去了独立地位,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词尾”的东西,从而动补之间结合越来越紧密,以至不能再插入宾语,宾语也就自然地放在了补语之后,变成“V得CO”“V不CO”[53]。
2.“V得/不得O”的句法演变
能性结构“V+得”与“V+不得”来源不同。如李晓琪(1985)认为“V得”来源于连动式“V得”,它经历了连动式、完成(结果)补语式、能性完成(结果)补语式三个发展阶段;“V不得”来源于动宾式“不得V”,它经历了动宾式、单纯能性补语式两个发展阶段;因此,“V得”和“V不得”中的“得”不是同一的,前者“得”是动词,后者“得”是助词[11],前者可从不少方言中存在能性完成补语式“V得得”得以证实,观点与朱德熙(1982)[10](P133)一致,反驳了吕叔湘(1984)的观点:它们都是助词,表示能性[13](P127-138)。
能性述补结构“V+得+(O)”的来源,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该结构中“得”是由上古汉语动词前的能性助动词“得”后移而来的[3][6][54];另一种认为该结构中“得”与表“达成”的同形格式中“得”同源,区别在于前者用于未然语境,后者用于已然语境[11][40][41][44]。刘子瑜(2003)认同后一观点,认为存在着由“结果→达成→能性”的语义虚化,并认为能性与结果有着共同逻辑语义基础:能性是一种可能的实现,而结果是以可能实现为前提的,二者并不矛盾[55]。
太田辰夫(1993)认为“V不得O”“VO不得”来源不同,前者来源于获得义动词“得”,后者来源于“不得”后置[44](P213-216)。蒋绍愚(1994)认为“V不得O”是受“V得O”的语法类化而存在[41](P197),对此沈家煊(2006)持不同意见,认为存在两个问题:“V不CO”不可能是“VCO”类推而来;“V得O”里的“O”并不限于名词,而“V不得O”里的“O”则限于名词,因此,他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VO不得”中的“不得”前移并依附于V或者是O后移到“不得”后形成“V不得O”,这是“动词吸引”规律的反映[49](P185-205)。在此基础上,李思明(1992)认为晚唐以来发生了“VO不得”到“V不得O”宾语后置的变化,这是语法渐变性的要求[56]。李永(2003)[57]、朱明来(2006)[58]重点考察了郭煌变文、宋人话本“V+得+O”“V+O+不得”“V+不得+O”三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对称性发展,结论与李文基本一致。
(三)能性述补结构的语法化与词汇化
朱景松(1987)认为“V得/不C”可分化为两类语言单位:一是动补结构,补语未虚化,有对应的“VC”式,可单说,如“买得/不来”;一是熟语,补语虚化,没有对应的“VC”式,不可单说,如“合得/不来”等[59]。孙剑(2008)根据意义凝固、功能变化、使用频率高等标准分析了“V得/不上”“V得/不住”“V得/不着”等13种“V得/不C”结构的词汇化程度[60]。崔贵兵(2010)将词汇化的结果分为词汇化为动词、形容词、副词和话题标记4种类型[61]。张爱莉(2011)统计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表可能意义的述补词语[62]。李小军(2011)将“X不得”分为“不能X”和“X不能够”,前者如“说不得”“怪不得”“由不得”等,后者如“恨不得”“巴不得”等[63],往往以不能够实现某事为预设。以上研究多限于对义项和用法的列举。
学界比较关注个案研究。对“V得/不起”的研究,杉村博文(2010)认为“买不起、瞧不起”等结构是汉语的“行为-结果视角”和“事实可能视角”合力作用的结果[64]。彭湃、彭爽(2004)认为“看得/不起”类能性述补结构的固化受“得”变为轻声、“起”语义虚化为“表示够得上、经受得住或够不上、经受不住”、进入动词范围变大、使用频率剧增、“得起/不起”成为构词成分等影响[65]。杨万兵(2006、2012)认为动词的身体动作性强弱与宾语的典型性程度决定了“V得/不起(O)”的搭配,语言的人际功能也是影响肯否使用频率的重要因素[66];他还认为“V得/不起”经历了“VO得/不起”(宋代,VO结合紧密)、“VO得/不起”(明代,VO临时)到“V得/不起O”(清代,O置于“得/不起”后)的演变,其中“得”由获得义转化为达成义进而虚化为动词词尾,“起”由实义动词演变为表动作结果情状的成分[67]。
对“V得/不来”的研究,学者多关注“我们俩还谈得来”之类。宋玉柱(1985、1986)认为“来”是动词后缀,表示“V得/不了(liǎo)”[68][69];徐静茜(1986)认为“来”表示“有无能力完成某事”,在吴方言中普遍存在,由表“能/会/成”的动词“来”语义虚化而来,吸收进普通话中搭配的动词只限于“谈、合、处”等少数几个,表“融洽”义[70]。史有为(1986)认为“得/不来”是表能力的合成助词,“融洽”义只是“能力”的引申[71];刘月华(1998)认为其表达“融洽”“会或习惯做某事”[72](P51-66)。
其他结构研究方面,梅笑寒(1996)[73]、刘芳(2009)[74]、陈勇(2012)[75]分别讨论了“V得/不动”“V得/不定”的语义类别及其语法化,认为“动”由“受事能否发生空间位移”到“受事能否发生状态变化”“施事能否实施某种动作行为”,语义不断虚化[73] [74],“V+不定”包括“结果的未然性”“动向的变换性”“显示人或事物的动态性”“状态的持续性”等意义[75]。孙茂恒(2013)[76]、潘佳琦(2017)[77]分别讨论了“A不了”“V不了”与量的关系,孙文认为“A不了差量比较句”可带不确定大量、小量和具体确切量等量成分,潘文认为“V不了”可带不定指名词、表约量与约量的数量成分和表主观量(包括主观小量和主观大量)的数量成分。何小静(2009)[78]、周敏莉(2010)[79]讨论了“说不定”的词汇化,何文认为“说不定”经历了由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到动补短语再到评注性副词的词汇化过程,周文认为“说不定”作为语气副词,是由同形动补结构固化而来的,其语义特点是事件的低可能性及其提升。范丽芳(2008)认为“禁”的多义性、“不”的未然和已然,再加上刺激主体发生变化的客观或主观因素、条件或环境的制约促进了“禁不住”词汇化的形成[80]。韩启振(2011)认为言者主语、宾语小句是特指问形式、疑问词所在短语表事件发生时间、宾语小句所述事件是将来事件、“说不准”本身的“不确定/主观能动”的语义特点是所在构式语法化的必要条件,而所在小句由前景到背景的变化是语法化的动因[81]。胡斌彬(2016)分析了“搞/弄/闹不好”由假设小句语法化为副词性情态标记的过程:该结构用作二重假设复句“[假设 -[假设-结果]]”的内层假设小句的桥梁语境至为关键,这种语境诱发了其语义的歧解和句法地位的降级;并随着“搞/弄/闹”的语义泛化和虚化,该结构最终虚化为表示可能性揣测的认识情态标记[82]。吴婷燕、赵春利(2018)从认知逻辑、语言事实、形式标记和语义性质角度论证了情态副词“怪不得”所标记的“奇疑-醒悟”因果性话语关联[83]。
五、结语
能性述补结构具有汉语特色,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但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侧重个案研究,缺乏范畴的关照,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零星化和片面化,关联性不足,缺乏对能性述补结构自上而下的总体系统研究。二是能性述补结构的演变来源和途径尚存在分歧。三是描写较多,解释不足。如能性述补结构的不同句法语义限制条件是如何起作用的?能性述补结构表达能性情态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有些能性述补结构没有相应的述补结构?为什么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了”使用频率高?为什么进入能性述补结构的“V”多是单音节动词?为什么“吃不住”这样的结构可以表达两种语言单位,其词汇化的动因是什么?
今后研究的重点:一是尝试立足情态范畴,运用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对能性述补结构的语义来源与语法表现进行系统全面的阐释,共时和历时并重,描写和解释并举,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具有类型学意义;二是加强语义演变研究,概括规律性动因;三是加强对比研究,探索能性述补结构的表达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