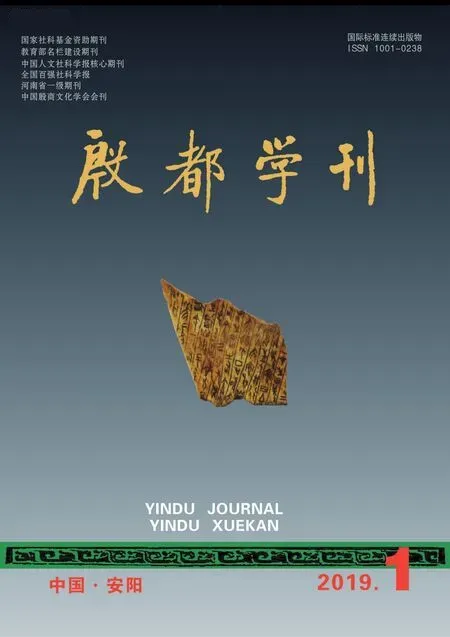社会失范与白朗起义
陈德鹏
(平顶山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平顶山 467099)
关于白朗起义,学界的研究已经不少。但毋庸讳言,既有的研究或仍坚持“起义说”[1],或重蹈“土匪说”的窠臼[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向惯于利用会党,对于白朗,或许正如白水先生所说:革命党人积极联络、支持白朗军,只是想利用这支军队,而不是把它当作同盟军(白水:《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关系述论》,《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并未为白朗“正名”。1936年印行的《甘宁青史略》虽对白朗给予了一定的同情,但仍认为他是“盗”,说:白朗想学王天纵,“其心术同为人所共谅;而王以侠著,白以盗终,盖时机有先后,行动有得失耳!”(杜春和:《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40页)至于河南所修的地方志,更是无一例外地将白朗称为“土寇”或“土匪”。如,民国十八年(1929)的《河南新志》将革命党人段世垣称为烈士,而称白朗为“匪”,说:“(民国)三年(1914)春,白狼猖獗豫南,张(镇芳)遂诬烈士(段世垣)通匪,且以搜去黄兴委任状为证,(段世垣)遂在陕西遇害。”(《河南新志》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46页)民国二十年(1931)刊行的《禹县志》称白朗为“土寇”(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34页),《确山县志》称“巨匪白狼”(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89页);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印的《光山县志约稿》(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40页)和《正阳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374页)都称“白匪”。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海内外一些学者虽称白朗是“农民起义”领袖,却仍把他纳入土匪来研究。如,王天奖的《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略论》(《商丘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修订版)(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近年,有的研究者重提民国时期的观点,认为白朗就是土匪。如,李红光的《白朗研究》(山东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李红光、孙昉、刘平合著的《袁世凯因应白朗起事的军政措施——兼论白朗起事的性质》(《殷都学刊》2013年第3期)等。,尽管有其学术价值,却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持“起义说”者往往只谈白朗军队的反袁而忽略乃至回避其不足,持“土匪说”者则相反,都不免失之偏颇;二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如果仅仅局限于就其某一方面来进行非此即彼的研究,很可能会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基于此,笔者尝试就社会失范与白朗起义的关系进行简要探讨,以拓展研究视野,乞方家批评指正。
一、起义的背景:清末民初的社会失范
民国建元,虽推翻了帝制,但无论是武昌首义的新军还是逼迫清帝退位的北洋军,以及纷纷宣布“独立”肢解大清朝的各省督抚,无不是清朝的遗产,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呈现出社会失范的乱象。
1.官府对民间的强盗式掠夺和荒政的不作为。清末民初,捐税多如牛毛是学界的共识,但不论何种捐税以及每项捐税需要交多少钱,只要按规矩来,同时对灾荒等进行有效救济,形成上下一心共赴时艰的局面,就不会造成社会失范;反之,则会严重破坏既有规范,甚至导致社会失控、“官逼民反”。清末民初的社会属于后一种情况,银与制钱的折价就是例证之一。早在咸丰年间(1850-1861),河南的银钱折算就以1:2700—3000居有统计的各省市之首[注]关于每两白银与制钱的折算,北京在咸丰六年(1856)是1:2000—3000、云南咸丰三年(1853)是1:1800—2000、江苏咸丰六年为1:2000、陕西咸丰四年(1854)为1:2400—2500、湖南咸丰四年为1:2300—2400、浙江咸丰五年(1855)为1:2200—2300、直隶咸丰六年为1:2000、河南咸丰四年为1:2700—300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83页),河南在各省市中折钱最多。;到了清末民初,“以税银论其溢收之处,每两有折钱三千文以上及四千文以上者”[2](P150)。又由于民间实际使用的多是制钱而非银两,战乱之际,灾荒之年,往往都是“钱贵银贱”[注]参见王宏斌《清代社会动荡时期银钱比价变化规律之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第5-14页。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年份外,晚清银钱比都在1:2000以下。如,自道光十二年(1832)至同治元年(1862),每两白银兑换制钱最多的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和咸丰四年(1854)的1:2000,最少的是咸丰七年(1857)的1:1190;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最多的是同治九至十一年的1:1856,最少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1:108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7-578、587-588页)。,所以,同治元年(1862)河南的漕粮“约每石折制钱六千有零,以现时银价计之,将及四两”[注]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倭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4862-044。。这样,官府的赋税以每两银折算三、四千制钱征收,然后再以市场价一千多制钱兑换一两白银交国库,一颠一倒,民众的赋税增加到应缴数额的两三倍。须知,清代的漕粮是所谓的“天庾正供”,是中央政府征收的正式赋税,尚且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民间进行强盗式掠夺,更遑论其他捐税了。
与此同时,官府对民间灾荒的救济则越来越乏力,到了“民国建元,各里粜谷购枪,义仓、社仓遂空”[3](P63),民间失去了自救能力,官府则更指望不上。所以,《河南新志》的编者感叹道:“民国以来,兵凶岁凶,循环未息,例须蠲免赋税,或减缓征收之区,且欲邀帝制时代之滑稽恩典而不可得。盖地方官,视征收为渔利之手术,蠲税缓征,皆足以损失其利润,故于绅民禀报灾荒必竭尽智能以阻其上闻。为之上者,亦不乐闻也。闻之而无以应,则委员查复。凡查灾委员,地方例不供应,故委员咸目查灾为苦差而不肯往,则仍归于地方官查复。而灾区赋税之蠲缓何可冀耶!”[4](P555)简言之,由于赈灾既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减少财政收入,又没有油水,政府官员都不愿作为,导致民国初年政府对民间灾荒的救济还不如清朝。
正是由于官方带头破坏了既有的社会规范,民间也就往往视官府为寇仇,以致官府号召民间组织起来“防匪”的联庄会,还没起到“防匪”作用,就先成为官府的对抗者[5]。
2.社会角色混乱。在规范的社会里,每个或每类社会成员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十分明晰的,互不混淆,各有其责、权、利;反之,则社会角色混乱,责、权、利关系不清。在白朗起义前和起义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社会角色混乱现象。由于前述政府对民间的强盗式掠夺以及后面的许多事例也都可以看作社会角色混乱,此处仅举两例。
(1)官军的土匪角色。军队的职责,是对外抵御侵略,对内剿匪、平叛,维护社会稳定,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民初的一些军队,承袭了晚清军队的陋习,几与土匪无异。如,在河南,“拱卫军……军纪甚坏,强赊硬买,奸淫妇女,迄今怨声载道”[6](P84)。在安徽,听说白朗来攻,六安县知事殷葆森逃跑,其卫队“将狱犯悉释,所有县署公款什物掳掠一空,旋即鸣枪肆掠城内外殷实铺户,如泰丰裕、宝兴、德和、鼎隆、信成、裕泰祥等号,及居民多家”[6](P308-309)。在陕西,“陕军多就地招募,非市井无赖,即会匪党徒。军官多未受军事教育,以鱼肉富室而强夺其资财为快,尝有一陕军语人云:‘我们的希望不在打仗,实在发财。’明目张胆,言之不讳,此可以知陕军之志念矣”[6](P382)。在甘肃,“马营、洛门财物之损失,毅军之搜括,闻较白匪尤甚云”;官军“马忠孝(部)则畏贼不前,未尝接仗,惟至各乡城镇残虐绅民,掳掠财物。曾在伏羌之磐安镇攻堡,已逾一时,幸暴雨猝来,不能上坡而止。然犹将十人捉去,非刑考(拷)掠,搜索各商民金银、烟土,掘地三尺,镇人咸惴惴焉。又至关子镇,将甄姓房屋焚烧,财物付之一炬。进天水城后,声言为马镇报仇,将绅士备极凌辱,又将西和、礼县、西固、盐关、漳县等处富民恣意酷掠,所掠财物无算。其最酷者,则武山县之高楼子,乡民极力支应,(但该军仍)无故将寨堡攻陷,全堡男妇老幼炮毙百有余人,其妇女之幸存者亦受伤甚剧,苟延残喘。而财物之一空,均所不计……来俊臣之狱中流血,惨不如是”[6](P334)。
(2)地方土豪的保护官、民角色。与土匪关系密切或有帮会前科的土豪本是为非作歹的地方害虫,却扮演起了保护官、民安全的角色。1912年4月,宝丰县的卸任知事张礼堂返回开封,要求土豪杨小端保护,后者写信给绿林杜啟(起、其)宾等人,打通关节,要求不要打劫张礼堂,并派保镖十余人带快枪护送[7];白朗军至武功,“地方官与平日以勇自称之团练,皆杳然失踪。县中商民早知官不足恃,曾求计于土豪某氏。是人曾入哥老会,有急智,往时匪乱,全城赖以保全,故今事急,众复往求之。乃议定率人欢迎白狼于郊外,锥牛宰猪羊,以款群匪。群匪大悦,秋毫无犯,信宿而去,临行则馈以现银数千两。武功得以保全,实赖此一人之力也”[6](P373)。
3.社会信任危机。由于大量存在的社会角色混乱,清末民初的贫富之间、官民之间、官府内部、军队内部等,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如军队之间的相互扯皮、攻讦:“陕省军队,因存坐视推诿之意,复有宵小交搆其间,对陆(建章)则谓陕军将有不测之行为,对张(凤翙)则铺张中央待陕之严厉,有意挑衅,冀遂私图。将帅不和,大局益坏,秦人早知有后患矣。及是(白)狼果回窜,重遭浩劫,一误于张,再误于陆,秦民之叹息痛恨也固宜”[6](P391);“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军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首先破议,致被匪逸围而出。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各军事前不肯协力,事后相互怨尤,至为可笑”[6](P406)。再如民间富人对贫民的猜疑:白朗运官盐,“经过鲁山老瓦屋,天色已晚,白朗央求该村大户,请允许牛车暂宿一夜,该村富户坚持不允,白朗说:‘我们穷牛把,(牛把,即赶牛车的)在村头歇一夜,又不是土匪,又不拿你们的东西,何必和我们过不去?’反复交涉,造成口角,被该村富户指使数十人痛打一顿”[7]。
总之,清末民初,由于官府对民间的强盗式掠夺、社会角色混乱以及信任危机等社会失范现象的存在,社会各阶层、群体、成员之间,乃至于官府内部、军队内部,都产生了隔阂;反过来,这种隔阂又会促使社会失范进一步加剧。
二、起义的动机: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
据《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白朗是白家的“单根独苗”,按照中国家庭的常理,他应该是一个很受父母娇惯、比较任性的人,但他同时也肩负着延续家庭“香火”、支撑家族“门面”的责任,在已经有了一子三女、年近不惑的情况下,他是不太容易当“蹚将”的。如白母的再三阻止,白朗自己也说:“我已经三四十岁的人了,还蹚什么?”因之,白朗当“蹚将”虽有其任性的个性因素,但当地官民失范的环境作用则更大也更直接。
《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列出了白朗当“蹚将”的5条“动机”,其中有4条是当地官民失范使白朗产生了“仇恨”。官方失范3条:第二条,白朗在狱中被狱卒李康勒索、毒打、刁难,发誓要“报仇”;第三条,白朗干马队时,自己的大青马被官员项德高逼迫与一匹老马交换,还得再赔上50两银子,回家途中连老马也被梁洼的“小队”抢走;第五条,白朗母亲的包袱被官军抢走,送包的二人被囚禁致死,白朗姐姐家被抄。这三条中,唯有查抄白朗姐姐家或多或少有点合理性,因为在当时人眼中,白朗就是个“蹚将”,但其姐姐家的财物被抄家者洗劫则仍属于失范行为。民间失范一条,即第一条,白家是其庄上的单门独户,经常受大姓王家欺负,因在一次冲突中出了人命,白朗被诬告坐牢。中国农村基本上还是宗法社会,每个村庄的大多数人口都以一、两个姓氏为主,人口占少数的其他姓氏往往受欺负。在社会规范得到严格遵循的情况下,这种矛盾一般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清末民初则不然,它很可能是白朗交结江湖朋友以便对抗王家的直接原因。有了这些“仇恨”,再加上第四条:白朗交结的江湖朋友(也属于民间失范者)或已经或将要当“蹚将”,并极力劝白朗加入,白朗最终踏入绿林。因此,就社会环境而言,白朗当“蹚将”的主因是他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次因则是其失范的江湖朋友的诱导。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豫督张镇芳不顾官方信誉杀害前来投降的土匪,白朗充其量也只是当地的诸多“蹚将”之一,还不至于很快成为大规模起义队伍的首领。
白朗当“蹚将”时,豫西的土匪很多,官方对土匪的态度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应招抚土匪;另一部分人则相反,极力主张剿灭。后者的主要顾虑大致如徐瑞昌在禀报张镇芳时所说:第一,一旦招抚,“愚民闻之,景仰风从”,导致土匪愈多;第二,政府财政支绌,无力收养招抚之众;第三,兵燹灾荒之余,无法增加赋税以养受抚之匪;第四,土匪反复无常,“屡收屡变”,招抚后无法保证其恪守军纪;第五,土匪之中,有人“希图收服后,即以有名之师参与河南政权”,故不可招抚[6](P1-2)。这5个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但都难以令人信服。
第一、五看似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与其说是官方不相信“愚民”,毋宁说是当政者有私心或缺乏足够的自信。历朝历代,中国官方总是实行愚民政策,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到社会出了问题,又归咎于“愚民无知”。进入民国,一切依旧。徐瑞昌的话仍是这样一个看似合理而实则荒谬的逻辑:“愚民”既然无知,当然不能参政;以自己的力量迫使官方同意其参政者,则必然乱政,故宁可灭之。可是,政府不改其愚民政策,百姓何能“有知”?政府不让民众参与政事,民众怎么可能锻炼出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此种论调,要么是视国家政权为私产,要么是缺乏自信不敢接纳更多的人参政议政,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至少从“民国”的角度看,这两个方面都不成立。
第二、三属于财政层面,但并非无法解决。当时的政府财政确实相当困难,民众也确实极其困苦。但是,其一,剿灭土匪就意味着打仗,其破坏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恐怕不一定比养活受抚土匪的花费少。如,商城县,“是役也,匪来两次,兵住月余,总计城乡死伤绅民六百余口,损失一百余万,烧去房屋五千余间,前后用去筹防、兵差、善后各费一万余串,实为三百年来第一大劫。”[6](P306)其二,当时民间的困苦最主要的是由于灾荒,而不是土匪。如,鲁山县由于大旱,“去年(1913)土匪围攻鲁城时,所有粮价,玉米每斗八百文,麦子一串二百文;今则匪患平,玉米一串五百文,麦子二串五百文,价腾过倍,是旱荒较匪患尤为难堪也。”[6](P44)退一步说,土匪也是要吃喝住穿的,也需要花社会的钱,与其让他们靠犯法抢劫生活,不如把他们纳入到体制之内,社会所费不增,又维护了法度的尊严。其三,自清朝中叶以后,河南的各种匪患层出不穷,大者如“白莲教匪”起义、“捻匪”起义,小者多如牛毛,官府的镇压并没有根绝匪患,足以证明匪光靠剿是剿灭不完的。其四,中国古代早有屯田制度,军队并非必须由民众纳粮养活。兵燹灾荒之余,荒地很多,招抚的土匪乃至其他军队都可以用来抗旱、搞军屯以解决粮饷问题,政府不增加财政支出,民众不需要多交捐税,土匪也能得到安置。
剩余的第四倒真是一个问题。在失范的社会里,无论是土匪还是起义者,防止其反复无常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明末的张献忠、太平天国时期的苗沛霖以及其他许多起义者或土匪都是例证。然而,只要政府能够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规范并以身作则,坚决贯彻执行,相信没有几个“愚民”会愚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程度,敢公然“占山为王”当土匪。
但是,袁世凯既然心存私欲,想变民国为自己的“家天下”,其表弟张镇芳自然也不愿意让招抚来的土匪分享河南政权,故采纳了剿灭说,将响应官方招抚号召而来投降的杜起宾、岳东仁、常建福、薛金彪、张应朝、郭义得、薛三、高金宝等土匪头目杀掉,“并捕押其党羽数名”[6](P7)。官方的此次失信,不仅更加坚定了白朗的反抗决心,还使他成了当地最有影响力的“蹚将”,在客观上有利于其日后的发展壮大。
三、起义的性质:对社会失范的反抗与矫正
就与社会失范的关系而言,土匪是利用社会失范来进一步破坏社会规范,以达到获取自身私利的目的。起义者则不同,他们是以破坏社会规范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失范,以期建立新的规范来矫正社会失范。我们认为白朗属于后者,除了其当“蹚将”的主要动机是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之外,还在于他在受到革命党的影响后,曾试图建立一些粗略的规范并加以执行。只是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此处仅以1914年白朗在荆紫关留下的一篇檄文结合其他资料来窥其一二。
1.反对袁世凯篡国的“民主政治”规范[注]关于白朗军发布的许多反袁檄文,应该是出自参加白朗队伍的革命党之手(参见白水《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关系述论》,《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白朗没有接受其民主政治主张,只是对于只读过一年多私塾的白朗来说,其理解的程度应该是很有限的,甚至还有“袁世凯做大清的官,篡大清的位,是一个小人,绝对不能保他”(开封师院历史系、河南科学分院历史所:《白朗起义调查报告》)的因素在内。即使是后面这种“忠君”思想,也反映了白朗是在反抗当时的社会失范。易言之,白朗是在维护传统“忠”的规范。。檄文说:“溯自共和事成,人心望治,岂知邦家不造,祸患相乘,阴霾毒雾,布满政府,妄行威福,摧残民权,借共和之名,实行专制之弊,利人民之弱,遂蓄登极之志。本都督用是痛心疾首,奋起垅亩,召集豪杰,为民请命。”[6](P368)由于军事力量弱,白朗并没有北伐,那么,此檄文是否表明白朗真有反袁之志?回答是肯定的。民国《禹县志》卷二“大事记”说:白朗军攻入禹县县城,“号于众曰:‘此来专仇团防也!’”[3](P234)《白匪陷陇南见闻录》的作者王士蔼记载,白朗军未来之前,“斯时谣言孔多,有谓系干大事,称‘洪汉军’,并不伤害人民者”[6](P328);白军来后,他与白朗部下似乎是一个小头目的还有一段对话。小头目说:“袁世凯干事不公,我们意欲反对。”王问:“既不赞成袁公,即当整军北上,却来甘肃何为?”小头目说:“现在势力不厚,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南方。”[6](P330)《白狼扰蓼记》的作者吕咎予也有类似记载,说白朗军攻入六安后,一名士兵进入一户人家,对居民说:“勿惶恐,俺们此来,系专与狗子为难者(狼匪称官军为狗子,取狼吃狗之意),但防流弹,速令汝全家匍匐墙下,当无碍。”[6](P312)《甘宁青史略》则记载了通渭县在款待白军时白朗对绅民的讲话:“吾所以西来,谋大事耳,事之成败,天也,决不涂炭生灵。”[6](P343)由此可见,无论是白朗自己还是其部下,都在不失时机地宣传其反袁主张,与黄兴给白朗的信中所说“使人人晓然于吾辈之举动,实有吊民伐罪之意”[8]是一致的。公然反对袁世凯独裁、篡国,表明白朗确实有建立“民主政治”规范的图谋,尽管他对民主共和的理解可能极其有限。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认为,白朗起义“皆(袁)世凯一念之私所激而成”[6](P340)。
2.严厉的军队“不扰民”规范。檄文说,“去年义军经此(指荆紫关),秋毫无犯,市厘不惊,商旅安堵。人民亦晓于大义,箪食壶浆,以迎义师,本都督异常欣慰”,“故义军过处,人民不自惊扰”[6](P368、369)。这与黄兴在给白朗的信中所说“师出以律,无伤地方(以免招致)恶感”[8]相近。白朗在与革命党联合后,其军纪、军容确实比以前大有改观。如官方档案记载,1913年,白朗“祭祖回籍,约束甚严。旗上号称‘大汉副都督白’,一切举动,迥与前殊”[6](P20)。亲历者的记述也是如此:“当白狼拔队出城,有往观者,来述余前,称其军律严整,几若节制之师,且不阻挠旁观之人”[6](P316);白狼治军颇严,“在邠县作战时,进城后笔者(乔叙五)在城内西街杨家祠堂前,见有血迹一大片,据本街贡生杨云生说:‘系白狼斩杀违反纪律者所致。’其治军之严可知。”[6](P417)须知,白朗的军队是由土匪、散兵游勇、游民乞丐等构成的,是真正的乌合之众,能够把这些人组织得“几若节制之师”,实非易事;而民众敢于前去“旁观”,则很直观地表明其军队确有“不扰民”的规范。
3.“顺”、“逆”有别的“粮饷供给”规范[注]据说白朗曾提出粮饷的“五征”“五不征”:“做官的征,充衙门差役的征,大商人征,吃租人征,放债人征;苦力人不征,帮工人不征,残废人不征,参加过革命人不征,讨袁人不征。”在鲁山,白朗等又以“中华民国豫南军政府鲁山县代调民军统领”名义张贴告示:“各里殷商生意归该商人管业外,田充军政府助饷;富户田地以三顷为度,两顷归该户管业,外充军政府助饷;花户田地不满两顷者,军政府秋毫不犯;花户田地满三顷,人口仅足自顾者,军政府秋毫不犯”(平顶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顶山市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7-318页)。但白军一直在流动作战,此类“助饷”规章没有执行。。檄文说,“然义军初起,须(需)用孔亟,不得不取之于民。况东征西伐,以讨独夫,而军火无接济之路,寸地有难守之象,其取之于民,实出于不得已,人民亦当谅我苦衷,力为相助”;对于“济以军火,供以粮食,开门投诚者,一律保护,不伤其生命财产”[6](P368、369)。这就意味着不“开门投诚者”的生命财产则不一定保护,与黄兴给白朗的信中所说的“足下饷械两无接济,刍粮所出,不能不稍取给于民间,然必义不苟取”[8]有一定出入。据当时人记载,“凡所过村邑,其有设馔欢待者,匪(指白朗军)辄大嚼嬉笑,掠去少些财物,聊作点缀而去;若十室九空,匪未至而先行藏匿,匪至后必大掠,继之以火,此屡试不爽者”[6](P365)。也就是说,白军在“取之于民”时对地方官民的“顺”、“逆”是区别对待的。一方面,这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另一方面,即使对官民的“劫掠”,也仅限于比较贵重的财物:“白匪搜括财物,烟土为大宗;次则妇女首饰、绸缎衣物,布匹、铜元均所不取”[6](P335);“其掳掠以洋元现银为单位,纸币铜元,概弃之不顾”[6](P365)。一则烟土、金银、绸缎等价值高,易于携带;二则此等财物多非穷人所有,与“打富济贫”不矛盾。所以,白军将“铜元衣物委之于路,或散诸饥人,不劫小镇,不杀行旅”[9],官方也承认白朗军“复假行仁义,见好小民”[6](P56)。而攻下县城后,被“劫掠”最惨的,除了官方之外,就是豪族大户。如在潢川,“巨富被焚之著名而最苦者,为现任许州知事卢某。卢姓为光属望族,其先人曾任某省提督,家中常养健儿百数十人,备置快枪利器”[6](P355)。
此外,还有释放并支持民众公认的好官。如白军在天水抓住向姓道员,逼问军装局所在,向佯为不知,白军将其打昏。“街有许多绅民见之,环跪而请曰:‘此吾父母官向大人,好官也。’求贼勿击。贼又释之。匪酋至前,询知为向道,乃曰:‘百姓皆称君为好官,可仍归署视事,倘有人与君为难,必杀无赦。’”[6](P333)支持教育。如在通渭县,白朗到县城内的高等小学,见“案头国文课本,取而读之,对其党曰:‘此地城小如斗,贫民可怜,不图学生尚堪造就。’捐银二千两交县令收存,以作买书之用。”[6](P343)对自己队伍所犯的错误道歉、赔偿。如在陇县,传教士奈尔逊写道:“据云,匪等并无仇杀外人意,老河口之役则为匪中叛徒所为,言次有抱歉之状。因出银九两,授奈尔逊幼子而去。”[6](P380)善待做劳役者。如“白狼之俘囚,皆须服役(指做后勤服务),所受待遇,固不恶也。”[6](P365)以及白朗的部下帮助百姓家救火[注]马小泉、张朝凤的《白朗起义军在河南淅川境内活动情况调查报告》中也有白朗军救火的例子(《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51页)。等。故有亲历者感叹:“至今思之,尤感其人(指帮其救火的白朗部下)。余所遇之匪,此迨稍有道德者。老氏谓盗亦有道,其斯之谓欤?”[6](P313)
诚然,由“蹚将”班底建立起来的白朗军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甚至有一些土匪习性。如白朗当“蹚将”之初,打劫离任县官张礼堂,还绑架了张的儿子,勒索了10支快枪。尽管这是为了获得武器,壮大自己的队伍,勒索的对象也是官员而非百姓,但打劫、绑架勒索毕竟是土匪行径[注]尽管学界对土匪的定义不同,但多数学者都把抢劫、绑架勒索作为土匪活动的基本特征(参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刘平的论文《论近代会党与土匪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在白军内部存在腐败现象,据当时人记载:白朗队伍开拔时,“前后有大轿十余乘,当系各首领在内,不知孰是白狼?嗣闻人云:‘头戴白狐皮帽,身着反毛皮袍,面长、色黑、无须者是。’”[6](P316)“匪酋有宋老年者,为首领十八人之一,身坐八人大轿,兴高采烈”[6](P337)。在荆紫关,对于挖掘白军士兵坟墓的百姓,白朗实施报复,尽烧民房,还宣称:“天不行雷霆之威,则安知其雨露之恩。汝人民当知孽由自作,非本都督之咎也。”[6](P369)对于被攻下的县城,“劫掠”商铺、当铺等之后,还将其放火烧毁[注]关于白朗军队焚烧房屋的原因,除了在荆紫关是报复当地居民毁坏白军牺牲士兵坟墓外,还有亲历者说:“然白匪讳言伤亡,凡有死者即堆置屋中,覆以柴草,灌以煤油,乘间焚去,故人不见毙匪之尸骸,此次六安房屋被焚之多,此亦一因也。”(杜春和:《白朗起义》,第359页)上海《申报》1914年3月3日所载官军前敌总司令王占元向北京政府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时见该匪所过之处,房屋焚烧一空。匪之中弹而死及伤不能行动者,该匪多半抛入火中,爆尸灭迹,烟焰连天,臭气冲鼻。”如此,白军焚烧商铺、当铺等房屋,似非无因,但仍不免失之暴虐。,已经超出了“筹饷”的范围,以及“劫掠”烟土充军饷等。同时,由于没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白朗及其队伍的文化水平又极为有限,其试图建立的规范既简单粗暴,又不系统,但毕竟不同于到处肆意抢掠、滥杀无辜的土匪[注]李红光在其硕士论文《白朗研究》中引用了不少白朗军队绑票勒索、奸污妇女的资料(见该文第65-67页),但这些资料都来自当时的报纸,而杜春和先生编的《白朗起义》一书所汇集的官方档案和亲历者的见闻似乎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倒是有官军奸污妇女的例子(如陆军守营兵强奸张氏女,见该书第4页)。由于白朗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来自土匪,绑票、奸淫的现象应该会有(如前述白朗绑架离任宝丰县知事张礼堂的儿子),但会不会像当时报纸上说的那么多,尚需进一步研究。如果不是杜春和先生在编辑《白朗起义》一书时对资料进行了选择性的取舍,剔除了与“起义”明显不相符的内容,那就是报纸的内容有失真之处。因为当时《申报》《大公报》等报纸的消息来源既有官方电文等正式文件,也有探报、传教士的见闻等,不乏道听途说之词,其内容未必完全属实。如,该硕士论文引用的《申报》1914年1月29日《豫鄂匪患之可危》一文说,白朗军在光山县,“其最可恶者,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又引用《大公报》1914年2月12日的《光山失守详情再志》一文说,白军攻入光山县城,城内“妇女亦伤亡不少,自尽者三四百人”。上海《申报》所刊文章的题目应该是《光山失陷之警电》,其开头称“罗山县教堂十五号晚电汉口教会云”,表明其所载消息是罗山县传教士听说的,并非亲历亲见;天津《大公报》所刊文章的开头也说“兹又得一访函云”,至于“访”的是谁,也不清楚。据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二“大事记”记载,白朗军队攻下光山县城时,城内绅民“死者二百数十人”;白军破卢家河,“杀该寨男女九百余口”(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40页)。在卷三“列女传”中,没有抗拒白军奸污而自尽者的传记或名单。如此,整个光山县城内才死了二百多人,怎么可能有妇女“自尽者三四百人”?如果这些妇女自尽是发生在卢家河,似乎也不太可能。光山县属于山区和丘陵地带,没有华北平原那样动辄几千人的大村庄,一般一个自然村很少超过200人。因此,卢家河的“九百余口”应该是多个村庄的男女老幼躲避到这一座圩寨中。假定他们当中男女各半,则在包括老幼在内的450余名女性中就有“自尽者三四百人”,如此大的自杀比例,很难令人信服。此外,杀卢家河圩寨“男女九百余口”,似乎与白朗军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不尽一致。如,前述商城县的损失是相当惨重的,是该县“三百年来第一大劫”,其总计城乡“死伤绅民”只有六百余口;光山县城内也只死了200多人。为何一座小小的圩寨会有900余人被杀?由于资料匮乏,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卢家河为何会发生如此惨案。。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的社会失范导致了白朗当“蹚将”,但白朗显然与当时豫西的其他“蹚将”不同,不仅其动机是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且在其接受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之后,还试图建立起一些粗略的规范并加以实行,以反抗和矫正当时的社会失范。因此,白朗是起义者而非土匪。白朗起义失败了,民国初年的社会失范依旧,民间的起义仍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