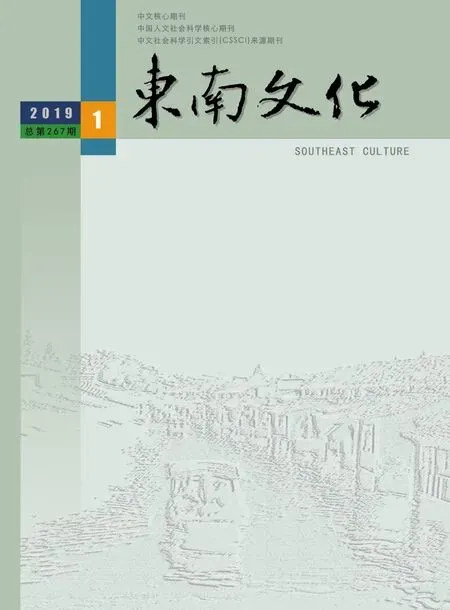郑振铎先生的文物行政学说(上)
孟宪民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北京 100009)
内容提要:郑振铎先生曾领导全国文物工作九年,全力从事,辛勤策划,成绩巨大。先生留下文物行业管理的丰富学说,主要有:文物是当代与未来发展的基础和源泉,要给予其应有地位;文物保护单位体制带有根本性;保护地面地下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为遗产学习推陈出新和进行爱国爱乡教育;考古队伍要壮大,成为有关建设的先遣队;博物馆要加强科研,把握性质、任务及辩证关系;地方要组织专家负责的文物管理委员会。新时代提出新要求,先生的“文物行政学说”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今天的文物工作者急需学习这一理论并以之为基础探求创新之路。
1958年10月18日凌晨,郑振铎先生(1898—195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一年后夏鼐先生的怀念文字写道:先生领导全国保护文物的工作,“九年来全力从事,辛勤策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还引述先生初任文物局长时给他的信:“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1]“行政”即行使国家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文物行政部门”如何。先生是中国首任也是唯有的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夏时为副所长,或有感触:与不少大学者大作家兼官员不同,先生全力从事并辛勤策划了文物行政。
“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可他反对在那个时候挖明陵。”夏去世前一年(1984年)讲话提及往事,可见他对说先生“好大喜功”心存纠结。他时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关注文物行政,“希望大家围绕保护文物来做考古工作”[2];去世后刊出的《夏鼐谈考古发掘》批评有的文物机构“失职”[3]。
先生自己何尝不纠结?罗哲文先生曾回忆1957年,“郑振铎谈到他刚受过‘好大喜功’的批判,现在又将受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批判”[4]。《郑振铎日记全编》(以下简称“日记”)有1958年9月24日:“到沈部长宅,先由我自己检查……下决心不再买书”;但29日记:“到宝禅寺十六号,看房子。”[5]《郑振铎》(以下称“传记”)介绍“足够容纳他的十万册藏书了,郑振铎对他的新居十分满意”[6]。原来先生临走竟喜忧参半。40年后,《郑振铎文博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出版,启功先生“敬题”封面,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作《序》道:他的功绩主要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开拓奠基。笔者认为,先生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丰富经验、基本观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然而世人对他的文物行政仍知者甚少。
作为在国家文物局工作过的后辈,笔者研学先生的文集、日记及传记,获益良多,故试对先生的文物行政学说作一推介,或可期进一步解前辈纠结,补今人积欠。
一、“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
先生早就是文化学术上的名家。“他在五四运动时举起新文化的旗帜反抗旧社会制度”,后还有“南迅北铎”之誉[7]。先生在北京的事迹,尚有一处鲜为人知:1920年,在陶然亭慈悲庵,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领导)、觉悟社(周恩来领导)、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的代表召开会议,共商革命团体的联合与改造,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今天陶然亭展板介绍,先生属曙光社、人道社,还有两幅人道社成员的人物照,先生与瞿秋白的照片并列。先生为政,难得的基础雄厚,五四运动正是其起点。
先生对文物事业的系统思考应始于写作《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出版)。这是最早向国人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希腊史前考古发掘的著述,是中国人著作科学考古史的开端,稍后才有郭沫若译《美术考古一世纪》、卫聚贤著《中国考古小史》。该书发表序文《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以下称“序文”)在先,社会影响应很大。其意义不仅在考古,还在“人类的知识范围,自19世纪以来,差不多较之前扩充了许多倍,无论在空间方面,或在时间方面,在地理上,或在历史上”[8]。这些应是毛泽东主席早就感兴趣的。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说明牌记载,毛泽东曾在此讲授地理。先生后来出任要职,这部著述或也是因由之一。
先生1948年在南京与李济先生(1896—1979年)的交集,可谓是一年后从政的热身。据日记载,先生与李交谈至少六次:“又到济之宅访他,谈了好久”,“至中央研究院晚餐,应济之、作铭约也。谈颇畅”等[9]。一般认为所谈多关先生编著《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事,但也未必尽然。时传“振铎是共产党”,为黄炎培、傅斯年等访问延安后流布:黄问及“南方文物很多,应该怎样保护处理”,毛插话:“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10]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是第一个采用科学方法从事考古发掘的中国人,后为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他时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委,还长期主政博物馆事业,1934—1947年兼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文集》时跨五十多年,多篇涉及行政,为大学者文集少见。如1926年拟《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首条即“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迹遗物;对历史文物的报道应着眼于保护”[11];1934年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提出保存及研究地下古物的基本认识,“不是以见于国家法令为止,应该成为一种一切公民必须有的基本训练”[12]。《古物》1943年刊于《中央日报》,有对古物定义、范围、分类、价值的详解,博物馆产生的交代,更论及收集、收藏[13]。他的最后专著《安阳》提到1923年赴河南新郑发掘的教训:“做这种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现行的政治和社会状况。”[14]
对《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李自是了然在心。1948年底他押运殷墟文物至台湾,再未回来。当年在南京成贤街,两位先生应会谈到“政治和社会”,先后成为文物行政者的学问大家,无意间完成了时代的交接。
二、“防止毁坏与非科学方法”的立场
1950年6月6日,先生以文物局局长名义发表《注意保护古迹文物》,开篇即:“近来有不少古迹文物遭受破坏,这是国家宝贵财富的重大损失,亟应予以有效的制止。”文末呼吁:“希望各地机关、部队、团体和全体人民,对所有古迹、文物迅速采取有效办法,加意保护,防止毁坏与非科学方法的发掘;对已经被毁坏或正在被毁坏者应及时加以清理和坚决制止;并望各级人民政府及文化、新闻机构就保护古代文物之意义加以广泛宣传,使人民自动自觉协助政府共同保护古迹文物。”[15]强调古迹在文物中的地位,防止毁坏,及发掘保护需要科学方法,是先生为政一直秉持的科学立场。此前20年他著《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时,他的这个立场就已形成。
“读者大约总可以见到锹铲的工作,其重要性为如何的了。”先生序文概括了考古发掘“所获”:
第一,发见的是古代生活,将失去的古代重现;
第二,使我们直接与古代史迹面对面地相见,不必依靠传述失真的古代记载;
第三,证明古代的著作、神话、传说,向来以为虚无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的成分在内。有时,且可以知道这种传说、神话的所以构成的原因。
考古发掘与偶然发现,与挖宝,大有不同。先生指出:之前的发见,大都是偶然的机遇凑合,不是“专门家有心”“经了千辛万苦而始得到的结果”,“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时,假定考定了一个遗址,专门的发掘家是等待在那里的”。先生在指出中国古物未经“有意发掘”的弊病后,发出宏愿:“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易的偶然的发见,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
先生指出,之前的发掘大都不是为学问、为艺术、为古史而工作,“不是为个人的财富,便是为了国家的财富”,所以“考古学家看来则为无价之宝的东西,不知被毁弃了多少!这是考古学上的一大劫,倒不如藏宝于地,还可以有复得之时呢……”“有时一片碎陶器所叙述出来的古代的生活和艺术,反较之王宫王墓为更重要”。
先生反对主动发掘帝陵,乃一贯立场使然。立足科学前沿,先生开始了文物行政。
三、“根本性”体制:文物保护单位
法定“文物”与之前“古物”指代范围都极广,但难免与一般仅指器具、碑刻、建筑等的“文物”名词混淆,所以先生还用“古迹文物”来区别。发明“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词组,是汲取国内外保护文物经验,用中国语言进行概括,是对“文物”的进一步定义。而且诚如先生1956年发表《宝爱民族遗产保护文化古物》所言: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16]。从此,法定“文物”一词,包括了文物保护单位。
(一)调查是“了解”的第一阶段
“查我国所有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今后对文化遗产的保管工作,为经常的文化建设工作之一。”这是原政务院所颁首批文物法令1950年《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以下称“1950年法令”)并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的开首之句,颇有价值。于今仍可答疑解惑,例如有观点认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是不久前才提出的,当属谬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文物进行调查登记,始于此。前者第一条即:各地原有或偶然发现的一切具有价值的建筑、文物、图书等,应由各地方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及公安机关妥为保护,严禁破坏、损毁及散佚;并详细登记,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者首先规定:各地调查公共或私人所有之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予以保护并呈报登记。对偶然发现,还规定按照原状保护,“已出土可移动之古物”移往安全地带妥为保管。
“调查是‘了解’的第一阶段”,因此,先生派了多个调查队去调查文物古迹的现状。1950年10月先生发表《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提到,“这种‘了解’是十分重要的。发掘的工作,我们只是附带的做。对于已被盗掘的古陵墓,我们要加以整理、保护。对于已确知遗址,已自身暴露出来的,我们则加以抢救性的发掘。”“一部分是委托各地博物馆去做,只要他们发掘的条件够。一部分是我们派遣了发掘队去工作。”[17]先生的辨析仍可启迪当今。
转年以“重视文物的保护、调查、研究工作”为题,先生提前发表《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序》,对该报告迅速的学术公开大加赞赏:“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的传布于广大的人民之间的。”[18]雁北文物勘查团团长就是发现“北京人”的、先生邀至国家文物局机关的科学家裴文中先生。二位1949年曾同赴“世界和平大会”,行程五十多天,应有深度交流。裴也早就注意“政治和社会”,1949—1954年他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还主持了全国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及培训。他的文物行政也实当加意研究,如迅速公开等或其首倡。
(二)“都列入国家保护”名单
对文物的调查登记,不久后发展为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56年4月2日[国二文习字第六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各地就已知的重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地区和重要革命遗迹、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碑碣等,“提出保护单位名单”,先行公布,加以保护。
《通知》前后情况可见先生日记,如1956年3月29日他在洛阳提到“文物政策法令”即《通知》的修改:“以保护为主,不令其有有意或无意的破坏。地上、地下、建筑物、历史性纪念物的艺术性、考古学术性,有缺点,应补充,现正在修改,成为全面性的。”两天后又记要防止两种思想:(1)漠不关心;(2)要保护的就要大修,已坏了的,且要重修。一年后在兰州“座谈到深夜十一时”,提出甘肃省应该注意的事:(1)古城遗址多,要保护;(2)石窟有七十多处,要保护;(3)注意古墓葬的发掘;(4)普查工作的进行;(5)废铜、废纸如何选拣;(6)修复工作,以保固为主,以不改动原来形式为原则。
“国保”多少为宜?先生的见解,似仅见传记,竟是与毛主席讨论:“在距他牺牲之前不久的日子里,郑振铎还曾专门就在基本建设中如何保护古迹名胜与保护北京的城墙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了详细的陈述。毛主席听后,当即笑着对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表示可以让他在全国列出一千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问他是否满意?他当时并未点头,这表示了他觉得‘一千个’太少了的意思。而当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尽可能不拆北京城墙的意见,并表示,要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将此精神下达给北京市时,他欣然地点了头。”[19]先生日记1958年9月曾三次至中南海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传记应所言不虚。
“一千个”系指大型者。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曾发表要将“全国性的大型文物保护单位”约一千处做到有计划的保护[20]。先生当然不会认可这就是全部。他1957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书面发言写道,全国“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共为六千七百二十六个”[21],精确至个位,说明对此数字的重视。他还调研过国外情况,如曾两次访问的印度的国定古迹遗址约五千处;如日记言及保加利亚“文物单位有6800个。均属于考古、建筑、历史、人文学、艺术等范围。且也将自然风景包含在内。尚有一万多个古坟(托拉基)及居住区土丘未计在内”。先生设想“国保”数量,肯定是要超过他们的。
先生说出“根本性”后,紧接有关键一句:“名单以外的也希望进一步调查研究予以补充,把所有应该保护的文物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22]补充到哪里?当然是名单,包括主要通过“注意”发掘来实现保护的一类,有些国家称“埋藏文化财”。
(三)地区与“人口密聚的城市”
“地区”“名单”等用语,出现于“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先生1953年科普讲座《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以下称“1953年讲座”)已有:先讲有极丰富埋藏的地区。凡是今天人口密聚的城市,往往是古代都邑所在,最容易发现古遗址和古墓葬。再谈地面上的,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名胜古迹,所谓“十景”“八景”几乎到处都有。“最应该注意的地区,首先是北京,那是古代建筑物最多而且最完整、自成体系的一个地方,必须仔仔细细地研究出一个具体的保护、保存的计划出来。”[23]后来我国宪法把“名胜”排于国家保护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之首,前述1950年法令与先生所言或是出处。
1953年讲座还提到,“譬如郑州,过去是不在坚决保护的名单上的”,可见当时已有“名单”,且不止古建筑。我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初动议应在那以后不久。先生195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记有访问其“保护城”;有“武伯纶、罗哲文来谈,把保加利亚带来的那瓶葡萄酒喝光了”。后二人于1958年发表专文,介绍该国一千多城堡在保护之列,“还有 30 个城市作为保护单位”[24]。这之前,我国各地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已有人口密集的城市。湖北襄阳临汉门城墙所嵌保护标志牌,现仍赫然写着:“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阳城 湖北省人民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布 襄樊市人民政府立”。历史丰碑犹在,并将永存。
先生对老城与历史地区保护的认知确处国际和国内前沿。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82年我国决定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对“老城区、古城遗址”“严加保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名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一章。
(四)城市计划“可以千变万化”
1956年《通知》已提到:各级人民委员会在制定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应当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纳入规划,加以保护。
对“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先生早有重视,1956年11月在南京的日记,“到香铺营文化局找朱偰,同去石头城,查看拆去的城垣,形势雄伟极了!不知为何拆之?!”到1957年6月,在《政协会刊》发表《拆除城墙问题》[25],指出:“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最高明的城市计划的专家们是会好好地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组织在整个都市范围之内,只显得其风景美妙,历史长久,激发人民爱国爱乡之念。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善于设计的,不懂得文化、历史、艺术的人,则往往认为有碍建设计划,非加以毁坏不可。”
先生赞同现代建设,但认为“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决不该“操之过急”。他最后道:“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蹋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写作该文不久,先生就去实地调研外国的“保护城”。前述所谓毛主席“支持他尽可能不拆”城墙,可能是因先生提到自己的认识和国内外的做法。
今地面城墙在很多城市已见不到了,但古城遗址还在被“大刀阔斧地加以铲除”。先生的批评仍切中当前城市问题的要害。
(五)单位是“包含”项目的体制
“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乃至上万个项目。像在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像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26]据先生这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解释,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尽管有其主体,但包含项目可很多,且不限时代、类别。
先生日记可证其思考,如“途径阿房宫”,“似佛像的石雕像尚在。其背上似有字(‘嘉’字可认出),应仔细清理一下”。如到甘肃敦煌莫高窟,第二天就去看143号,“有唐墓砖一堆,又有六朝画像砖二堵,色彩已褪,皆夏鼐所发掘者”。
对文物分类,先生曾有研究,希图认识得正确全面,如有种构思:地下的,含未发现;地上的(流传有自的、出土的),可移动、不可移动的[27]。这不以可否移动为据的分类,细究也有道理——地下者属不可移动之类,一旦出土就有了分别。李济的《古物》一文曾介绍古物保管委员会“用概括方法,分古物为十二类”的“名称和定义”,史前遗物、绘画、雕塑等,包括不可移动、可移动的;建筑则含一切遗址。他认为“得将古物分为二类,一类是可以收藏的,一类是不可以收藏的”;“不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收集,或者随便移动古物的位置,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是种罪恶”。
先生了解过去的有关分类,但仍选择了“单位”“项目”等术语来确定复杂的文物保护对象。解释“单位”,词典的第一层意思:“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而“单位制”为“有关基本单位、导出单位等一系列量度单位构成的体制”。科学有效的文物行政体制,正是先生所求。如果说美国保护遗产有“国家公园”体制,我国也不是没有,“文物保护单位”就是,且有意无意间已衍生出若干类别的遗产保护地。
(六)“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之上”
公布名单只是开始,为了建立群众基础,使文物少遭破坏,需要进行实地“宣传与介绍”,有些抢救措施也需加大投入,“运用各种方式”,而不仅仅是博物馆、遗址公园等“较高级者”,从简便易行的先做起来。
(七)“根本性”何在
“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29]先生1956年讲话,最后回答了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何以“带有根本性”。
先生强调“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是唯有这些,包括未发掘的,属于土地——国土乡土。保护和学习大地的文化遗产,而不是别的什么,才能在创新的同时,获得一地一国全体人民和代际的凝聚力。
文物保护单位的“根本性”在于可以使“学习遗产推陈出新”与“爱国爱乡教育”达成最紧密的结合。这是先生着眼全局,将这项工作与他负责的其他文化工作相比较,或是更大范围的比较所得重大结论。这一点,下文还将论及。
四、考古工作者是“建设的先遣队”
先生说出“都列入国家保护”后指出:“在人民群众中加强保护文物政策法令的宣传,普及文物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保护文物工作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之上,单靠文化行政部门和考古工作人员是不够的”。
这个思想,在文化部1963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中还有体现,其中“要进行如下工作”:(一)为防止人为破坏,必须划定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和组织保护人员;(二)为解决和生产建设的矛盾,更好地发挥文物作用,要进行规划工作,纳入城市或农村建设规划;(三)为防止自然力侵害,应逐步开展科技研究和采取措施;(四)广泛地运用各种方式,进行经常的宣传与介绍。其中“(一)”就是现今“四有”基础工作,其余也十分精辟,如规划要解决矛盾。因此,笔者后来再学习时,如获至宝,认为可称文物保护单位的“大四有”[28]。
“考古工作者们的前途是充满了无限的光明的,其任务也是十分的重大艰巨的。他们首先必须迅速地壮大、充实自己的队伍,才能适应日益规模弘大起来的基本建设工程的需要,而成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先遣队之一。”[30]先生1954年首次提到“先遣队”。
(一)为后代保护“公共财产”
文物与基建“关系很大,关系很密切”,先生1953年讲座一开始就强调:盖新房子,免不了要拆除旧房子;修铁路和公路,免不了要发掘地下遗址等。问题就在这里。哪些必须保存,都应经过文物专家的仔细研究。“我们不能重新创造出古代祖先们所遗留下来的东西”,“要为世世代代的子孙们打算,做好保护工作”。为后代保护,是强调文物不可再生的意义所在,是后来文物工作方针的出发点。
同年稍后,政务院以“政文习字24号”发出经先生起草的《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开篇也指出:这些文物不但是研究我国历史与文化的最可靠的实物例证,也是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具体的材料,一旦被毁即为不可弥补的损失。
“凡是地下的古物都是公共的财产。”1953年讲座进一步指出:随处都有发现,有的呈报,有的根本不报。发掘出来的,有的就作为私有,或卖掉分钱。掘墓砖出卖的情况也很严重。“这些属于人民的宝贵财产是不能被私人或某一团体、学校、机关所侵占的;更不能随意加以破坏。”造成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宣传教育不够,1950年法令的精神和力量未能贯彻到广大城乡群众中去。
看来群众转变很快,两年后先生发表:“保护历史文物已成了中国人民自觉的义务,也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要爱护、保护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过去,把偶然出土的历史文物据为己有的风气已经没有了。”政府经常接到各地农民和工人的报告。凡是发现、保护文物有功的都受到奖励[31]。
(二)中国是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这是先生1956年手稿《考古工作与基本建设工程的关系——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讲话》的第一段标题。他写道:如果是没什么历史的国家,简单不过,尽可不顾一切地把工程进行着。“但中国是一个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们的老祖宗把他们一代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几乎可以说是‘无地无宝藏’。情形就要大为不同了。”在列举了全国考古收获后,他进一步指出:“那些一处处的历代物质文化遗存,往往足以当得起‘地下博物馆’之称。有哪个国家有我们那末丰富的东西呢?”[32]
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是先生对“国情”的判断。这令人联想到李济1923年的一段文字:“中国人是最积极的筑城者”,1644年之前“记载中的城垣有4478座”,“所有这些只能靠考古发掘才能重见天日”[33]。有意思的是,两位先生的惊人之语都未再发表,或许是都认为我国地面文化资源及古城也还很多吧。
(三)“结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
先生1953年讲座的一段标题为“结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先生很少使用“配合”一词,强调“结合”,这与他早年主张“有意发掘”一脉相承。
1956年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先生批评“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还很多,首先是,应该走在工程队之前的,却常常落在后边”,“打了很大的折扣”[34]。在几乎同时的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上,他强调:“第一件要事,就是文化部门要参加‘规划’——例如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要走在基建工程队之前,和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水文学家等一同是基建工程的先遣队。”[35]文化部门“第一”要事竟是这件,先生的话于今仍具指导意义。
考古发现规模空前宏大,真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将’少,‘兵’也少,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首先是依靠基本建设人员的力量”。这是先生1953年讲座已提到的:“基本建设人员应该不仅是工程师、建筑人员,同时也应该是考古工作者”。这也是个新颖的提法,而且时隔几年还有下文。
先生自己一定有“规划”,并曾促进有关建设部门建立考古队伍。他空难不久,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正式成立。
(四)何为“重点保护、重点发掘”
关于“两重”方针,先生上述1956年两次讲话都有解析,应最具权威。
在考古会议:任务和力量的距离一天天地大起来。1955年文化部提出“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决定保留不妨碍工程安全与工程不致破坏的古遗址、古墓葬,暂时不加以发掘。这是必要措施,避免力量过于分散,同时也不使发掘因赶工而质量低劣[36]。
在基建会议:在最短时间之内还要用各种各样的培养干部的方法,一方面大量产生新生力量,一方面也大量发掘并使用潜在力量。但这些还不够。文化部制定一个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来,这是必要的,是把干部的力量使用在最必须的地方。如一个工厂,厂基是必须发掘的,空地花园等就可暂时不发掘。这样就可以腾挪出大批考古工作干部从事重点的必要的发掘了[37]。
先生1957年游记有则批评,很说明问题:原来这公园动员了青年在挖“青年湖”,清理队的人员便不得不移到这里,配合挖湖而急急忙忙地发掘。所谓建了公园便会保护好,也便成了“托辞”或“遁辞”[38]。
看来,“两重”为先生力主,本意是“把干部的力量使用在最必须的地方”,毫无放弃“非重点”的意思,倒是很符合现行方针的“抢救第一”。
(五)还要“把这些地区保留下来”
“必须避免在那些古迹和地面文物所在地点兴工动土”,这是1953年讲座已提出的。转年先生进一步指出:有的“是不能有二的极重要的古代和中古的文化遗址,可以提供出不少历史上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必须坚决地加以保存、保护,即使在发掘了之后——需要极精心在意的发掘清理工作——也还需要把这些地区保留下来,像保护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似的保护它们;它们的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就是古代和中古的计划都市的生动的具体的例证”[39]。这就是后来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一类——大大小小的遗产地区与城市,对这些地区与城市的保护,是文物工作者根本性工作。
对此,先生1957年游记有更激愤的表达:殷代人民的居住区,还有窑址,全都在急急忙忙地配合基建的工程里给“平整”掉了。那个地区将建筑一所中学。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而毁坏掉可以作为下一代教育的具体生动的历史、文化资料,这是合理的么?[40]
发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后代长久地保存考古保留地。保住一些重要地区,不再发掘也不建设,也是“保护为主”的意思,与先生反对主动发掘帝陵的主张是相通的。
[1]夏鼐:《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考古》1959年第12期。郑振铎(1898—1958年)于1949年起任中央政府文化部文物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学部常务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2]夏鼐:《文物和考古》,夏鼐著,王世民、林秀贞编《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有注:本文是夏鼐先生1984年3月12日在文化部文物局召开的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上的发言整理稿的节录,全文见《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3]夏鼐:《夏鼐谈考古发掘》,《中国文物报》1985年9月26日。夏先生6月19日去世,此文或为绝笔:“报纸上刊登一条消息,说某单位在基建中发现了许多古物,后来都交到文物机构,受到了表扬”“文物机构和报纸这样在表扬某单位时没有同时指出它的错误,在报纸编辑方面是出于不明白文物法令,但是,在文物机构方面,则是失职”。他用了个老词“古物”,也许又想起前辈的嘱托。
[4]罗哲文:《缅怀周恩来总理对文物建筑保护的关怀和丰功伟绩——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2周年》,《罗哲文建筑文集》,外文出版社1999年。原载《中国文物通讯》1998年第2、3期。罗先生忆及时间可能不准确,据“文集”《郑振铎大事年表》应为1957年8月1日他们同车赴十三陵。
[5]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记6月22日“周总理约我和夏衍同志等同车去”十三陵水库,新房子也许得自上级关照。下文引日记,不再加注。
[6]郑尔康:《郑振铎》,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郑尔康发表先生传记多部,本文选用的是最后一部。第405—406,432页,先生最后寓所今为宝产胡同25号;有先生对称他“藏书家”的看法:“我不是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收藏古书,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需要。”第207—210页,介绍“南迅北铎”是20世纪30年代初先生在北平的大学任教期间“文学青年中流传”的说法,引季羡林说:“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鲁迅先生外,并世无二。”这未必尽然,先生热心和长于编辑,应也是重要原因。第167、168页,有“事情问郑振铎”出处,文集郑尔康《跋》也提到。第377页,介绍与毛主席的讨论。
[7]同[6]。
[8]郑振铎:《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序)》,1928年2月12日,郑振铎著、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以下所引先生文,不另注明者,均见该书)。原载《民铎》1929年11月第10卷第5号。
[9]先生日记1948年3月3、4、5日,6月5、6、7日都记有与李济交谈,晤面则8次以上。先生抗战期间抢救文献,后与时中央图书馆关系密切,到南京住成贤街。现该街有馆址,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10]同[6]。
[11]李济:《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注:本稿底本为英文打印件,是编者1989年在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Freer/Sackler)发现并承该馆复制赠予的。
[12]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原载上海《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7号。
[13]李济:《古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未收入《李济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网站介绍为1943年《中央日报》全国美术展览特约论文。
[14]李济:《安阳》,《李济文集(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该书1977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现中译本有三部。
[15]郑振铎:《注意保护古迹文物》,《光明日报》1950年6月8日。
[16]郑振铎:《宝爱民族遗产保护文化古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1956年12月24日,因某地发生破坏文物事件向《文汇报》记者发表的谈话。
[17]郑振铎:《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0期。
[18]郑振铎:《重视文物的保护、调查、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51年4月5日。
[19]同[6]。
[20]王冶秋:《文物局“务虚”小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21]郑振铎:《党和政府是如何保护文物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22日。
[22]同[16]。
[23]郑振铎:《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原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举办的“基本建设科学知识系统讲座”——《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先于《工人日报》连载,后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后又补充重写,由协会1954年1月出版单行本。
[24]武伯纶、罗哲文:《记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25]郑振铎:《拆除城墙问题》,《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
[26]同[21]。
[27]郑振铎:《祖国文物的科学价值(提纲)》,未见日期,据北京图书馆藏郑振铎手稿排印。
[28]孟宪民:《温故求新:促进大遗址保护的科学发展——大遗址保护思路再探》,《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笔者研读先生文集、传记及日记,是从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并拟该文才开始的。
[29同[16]。
[30]郑振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人民日报》1954年8月31日。
[31]郑振铎:《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发掘》,《人民中国》(半月刊)1955年9月。
[32]郑振铎:《考古工作与基本建设工程的关系——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2月,据北京图书馆藏郑振铎手稿排印。
[33]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1928年首次出版日文版。
[34]郑振铎:《考古事业的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光明日报》1956年2月28日。
[35]同[32]。
[36]同[34]。
[37]同[32]。
[38]郑振铎:《郑州——殷的故城——考古游记之三》,《政协会刊》1957年第3期。
[39]同[30]。
[40]同[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