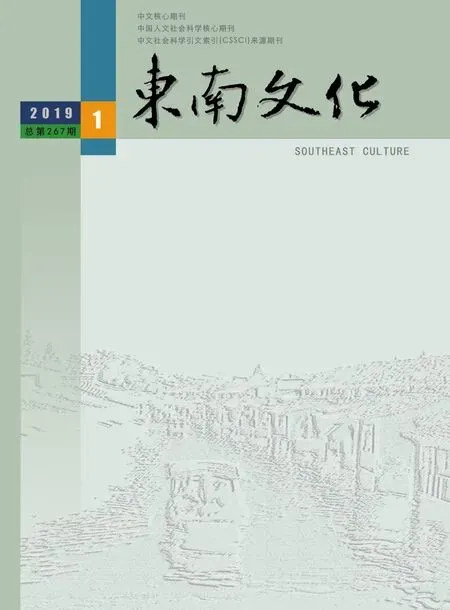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
林留根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从2014年中国大运河(以下简称“大运河”)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国家战略,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重大变化与转折,是中国文化遗产从单体向丛体、从三维向多维、从单元向多元、从点向点线面集成的转折,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完善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一范式可以称之为“中国大运河范式”。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对其价值阐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大运河“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亦将对运河文化遗产的解读和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既要对考古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加以总结和归纳,也要对“后申遗时代”考古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与阐述。
一、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
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以下省略敬称)在推动了长城的申遗之后,就在北京提出大运河申遗的建议,并邀请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在江苏发起响应。1990年,梁白泉提出了“大运河文化”的概念,并指出它是仍在使用的文物[1]。2006年,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整体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项目申遗工作由此拉开帷幕。2009年,由国务院牵头,8个省市和13个部委联合组成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大运河申遗上升为国家行动。到2013年,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隋唐大运河被合并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2013年初,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首批申遗点段,包括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河南到江苏的隋唐大运河以及杭州以东的浙东运河。2014年6月22日,经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Sess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审议,“中国大运河”跨省系列申遗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大运河遗产共包括中国8个省、直辖市的27座城市,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
近二十年来,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主要有文化景观、遗产运河、系列遗产、文化线路等。在这些概念中,与大运河最为相符的是遗产运河和文化线路两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联合编制的《国际运河遗迹名录》(Inter⁃national Canal Monument List)提出了评价运河遗产的四项标准:(1)是人类创造天才的杰作;(2)在技术价值发展方面有重大影响力;(3)是体现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的建筑或特征的突出实例;(4)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据此,这个名录将中国大运河与法国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等世界七条著名运河列入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并称这些运河“是最具影响力的水道,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2]。
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对大运河的价值作了如下概括——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
中国大运河保护学会会长张廷皓认为大运河具有毋庸置疑的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是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是春秋以降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它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重要经济制度漕运的见证;它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它是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它是凸显水利工程和技术价值的文化线路;它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形成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它具有超强的历史活力和适应性,至今在相当区段还保存着运河的初始功能。”[3]
二、大运河遗产价值的考古阐释
在大运河的申遗过程中,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中国水利研究院以及相关省市的考古所联合开展了多项考古工作,充分阐释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为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的考古辨识;(2)大运河遗产构成的考古辨析;(3)大运河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的考古阐释;(4)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的考古阐释。
(一)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的考古辨识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大运河的价值概括,首先就是突出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并随千百年来的环境变化而不断地适应环境。申遗工作首先回答的问题就是大运河的起源、变迁、沿革及其与环境变化对应关系。大运河的开凿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环境复杂、地质地貌多变,从古到今不断变化,且很多河段仍在使用。大运河的这些特点导致学界对其价值的认识不够充分,甚至怀疑其是否具有“文物”身份。这说明长时期以来,人们对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大运河习以为常,仅把它当作一条普通的水路,甚至都没有把它认定为“文物”。大运河从“没有身份”到被认定为文物,继而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大遗址,直至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历时将近三十年。要对几乎覆盖中国东南、长达三千多公里、历时二千五百多年、连接中国四大古都以及上百座历史城镇的大运河的遗产价值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估,就必须开展扎实的考古工作。
大运河河道既是大运河遗产的本体,也是其主体。河道本体历经沧桑,在历史上变迁频繁。各朝代的运河的范围、起止点、关键地点的改道、重要节点的工程遗存等要素中,有相当一部分很难具体落实。这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真实性问题,而解决此问题必须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固然可以在具体的点或小范围的区域内中发挥作用,而面对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大运河则必须利用新技术和新方法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空间信息技术(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006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了“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其中“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课题选择京杭大运河作为示范区,全面应用空间信息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空间信息技术在大型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方法和技术路线。空间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的理论与技术(以下简称“3S技术”),同时结合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进行空间数据的采集、测量、分析、存储、管理、显示、传播和应用等。在针对大运河这类构成复杂、范围广阔的遗产的调查中,空间信息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运河遗产调查主要运用遥感图像技术,为遗产的发现提供线索和勘探定位,解决一些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借助航片与卫片,可以通过各地物在形状、大小、色调、阴影、纹理等方面的光谱差异将其分辨出来。这对于古河道、古堤防等线性运河遗产的发现尤为便利。将几个时期的遥感图像进行空间叠合,就可以直观清晰地看到整个地区运河河道水系与水工设施的现状分布、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等状况,为运河遗产判别提供了线索与重要导引。空间信息技术系统综合应用了嵌入式3S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大大提高了野外数据采集的效率[4]。
大运河自开凿至今,运河路线几经变迁,历史上各时期的运河全貌都不尽相同,甚至直到今天,由于功能的要求和改变,运河线路还在不断地变化。在大运河考古调查中,考古工作者在充分利用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同时,结合历史舆图的判读,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古代运河及其沿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但历史舆图在表达位置、距离、形状等地理空间要素时准确性较差,通过“舆图新绘”的方式可以对区域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复原,从而直观地揭示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为运河遗产判别提供依据[5]。
据此,在大运河河道调查方面,考古专家提出三个一致性的要求,即历史文献和历史舆图的一致性、现存遗址和历史文献的一致性、历史地理信息和现代科学的地理信息系统表述方法的一致性。这些方法与技术的综合运用不仅提高了考古调查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调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大运河数据库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空间信息技术不仅运用于运河调查,还运用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文研院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山东省所”,现更名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综合应用3S技术,率先开展山东济宁汶上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考古发掘工作。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京杭运河著名的水利土程,其筑坝截水、南北分流等因地制宜的治水思想和技术在我国水利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南旺地区古遗址破坏严重,古运河己经干涸并废弃,运河线路模糊不清,曾经用于济运的五大水柜(北五湖)也全部变成农田。2008年3—6月,文研院与山东省所开展了对南旺分水枢纽及龙王庙古建筑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充分应用了精密GPS、航片、卫片、探地雷达、GIS等空间信息技术,参照文献资料,采取“以点带线,沿线追踪”的方法,对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基址、运河三个重要水柜遗迹、开河闸至长沟段运河进行了系统的踏查、定位和测绘,调查行程约100公里。
(二)大运河遗产构成的考古辨析
从时空角度观察,大运河是超大型遗址,是中华版图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自然遗产、运河遗产于一体的复合遗产。大运河属于工程性文化线路性质,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考古、文保和水利专家根据系统调查的大运河资料,对大运河遗产构成进行了科学分类和解析。从宏观角度看,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两大类[6]。如果按照工程系统类别分类,大运河遗产构成则可以分为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设施和运河附属建筑等四大类。水道工程包括河道(主河道、支线河道、城河、月河等),河道航深控制工程(闸、坝),河道水量节制工程(堤防、减河、含闸、坝、涵洞、港口等);水源工程包括水柜(坝、闸、堤防构成蓄供水系统),引水渠;工程管理设施包括浅堡、水志桩、提水机械与机具、过坝绞关等;运河附属建筑包括交通设施(运河上的桥梁、纤道、船与船厂),工程管理建筑及设施(衙署、浅、堡、铺),运输管理建筑及设施(衙署、漕仓、驿站),水神及祭祀建筑(龙王庙、功臣庙、水兽等)[7]。
科学划分与确定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类型与构成,对于把握其特性、深入理解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大运河申遗的价值评估至关重要。全面、客观、系统地研究大运河遗产构成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基础,明晰各类遗产构成的层级关系及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大运河价值判断评估的基础,也为开展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大运河考古调查、发掘明确了方向。
(三)大运河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的考古阐释
如果说米迪运河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标志性工程,那么京杭大运河则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规划和土木工程水平所能达到的顶峰。中国运河是在17世纪前领先世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工程,世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水利方面的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8]。运河遗产极为强调其在科技史上的贡献和成就,《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多次评价了大运河的贡献,将大运河列为“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的首位:大运河“是第一条实现‘穿山越岭’的运河”,“塘式或者箱式船闸是中国人在10世纪时率先发明的,大约在14世纪荷兰人在使用这项技术。”[9]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具有漕粮转输、商业运输、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错综复杂。作为运河遗产,工程技术是其核心价值,而最能体现运河核心技术的则是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例如大运河的河道工程,北京人工河湖水系水源工程、通惠河梯级船闸工程,山东南旺运河分水枢纽工程、中运河规避黄河之险工程,江苏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河洪泽湖大堤和清口的“蓄清刷黄”枢纽工程、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和治黄保运的堤防系统工程等。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往往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均按照不同地点的针对性和需求等,集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诸多技术要素而完成,更具有技术价值[10]。因此必须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解剖工程技术节点。文研院与山东省所、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淮安市博物馆(以下简称“淮安市博”)、镇江博物馆组织了对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对于充分阐释大运河的核心科技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淮安清口枢纽历史上是黄河、淮河、大运河的交汇之处,也是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枢纽工程之一。清口枢纽是一个水利工程遗产区,在其4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53处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如古河道、古堤坝、古涵闸、古寺庙等重要遗迹。明清两朝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对其不断地维护治理,并在极为复杂的水系格局下兴筑不断,保证了大运河工程的运输功能持续畅通。大运河的申遗文本对清口枢纽是这样评述的:“针对黄河夺淮,改变了淮河水系的状况,清口枢纽集成了与水动力学、水静力学、土力学、水文学、机械学等相关的经验型成果,建筑了水流制导、调节、分水、平水、水文观测、防洪排涝等大型工程,成为枢纽工程组群,完整体现了明代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工程意图,是人类伟大创造精神的成果。”为厘清复杂的水系与复杂庞大的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2008—2012年,南博与淮安市博对包括顺黄坝、天妃坝遗址在内的清口水利枢纽工程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天妃坝为明清时期清口治水的最重要实物见证,对于研究明清时期古运河变迁、运口位置、黄淮交汇形势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顺黄坝位于今码头镇御坝村境内,其沿古黄河南岸而建,使黄河水沿堤坝向东北入淮河尾闾进入东海,远离运河河口,从而保证了漕运的畅通和安全,是历史上黄河南侧缕堤的关键工程。历史上由于黄河经常泛滥,此处经常决口。为抵挡黄河的洪水,顺黄坝经不断堆筑而逐年延长和加高。顺黄坝土堤底部宽约72米,另有8~10米的碎石护坡。发掘所揭示出的遗迹体量大、保存完整,对于研究清代土堤坝的堆筑过程,各类水工技术的面貌,黄河侵蚀范围和淤积深度以及与古淮河、运河、洪泽湖等水系的关系等都有重要史料价值[11]。
古运河中段的南旺镇素有运河“水脊”之称,南旺分水枢纽属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修建的“引汶济运”工程,疏浚三湖作水枢,建闸坝,调节水量以保证漕运畅通。南旺分水工程坝址选定合理,因戴村是遏汶河济运较为理想的制高点,符合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至南旺水脊分水,疏浚三湖,蓄泄得宜,运用方便。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考古运用空间信息技术与地面访查相结合,清理发掘了石驳岸、小汶河入运河的石砌分水口设施、海漫石、邢通斗门、砖石堤岸、石砌台阶码头,在河道内清理发现线状分布的木桩挡板遗迹,确定运河南岸大堤的位置与结构。通过测绘和发掘,考古工作者对南旺段运河河道设施、引汶济运工程设施的结构、布局以及大运河河水的平衡调节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明确了通过戴村坝截引小汶河水源和利用石驳岸顶冲与分水口的形状结构相结合来实现南北分流济运的水工技术成就[12]。2013年12月,南旺枢纽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28公顷,包括6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和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2段世界文化遗产河段的部分河道遗产。
复闸工程系统是大运河工程的关键技术,是当时中国水利工程技术领先世界的标志。其通过在运口设置工程措施,使两河平缓衔接,且具有交通调度、水源供给和泥沙防治等综合功能,从而使人工水路与天然河流的边界日益分明。宋代在淮扬和江南运河段创造了具有综合工程效益的复闸设施。复闸是由闸门、引水和退水渠、澳(蓄水破塘)组成的工程体系。除具备季节性水量调节功能外,通过航道上多级闸门与引(退)水设施的运用,形成了类似现代船闸工作原理的工程设施。17世纪意大利米兰船闸与宋真州闸的设施几乎完全相同。江苏镇江段运河跨岗阜丘陵,为江南运河之屋脊,是历代运河治理的重点河段。镇江京口闸位于长江南岸,为大运河穿越长江的复闸水利工程,为历代漕运咽喉,是重要的标志性水工设施。2011年8月—2013年1月,镇江博物馆进行了京口闸遗址的考古工作,发掘揭示出唐至明清时期京口闸东闸体及其附属设施,如码头、石岸、碑亭、道路、河道、河岸等重要遗迹[13]。
(四)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产的考古阐释
大运河功能的发挥和运转需要系统的管理,管理系统则由漕运行政的官僚系统、河道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运河运输管理的制度系统构成,除制度、行政、职官之外,还有一些机构的工程设施。因此,大运河沿线留下诸多的运河附属建筑与设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衙署、钞关、港口、码头、粮仓等。河南浚县的黎阳仓遗址和洛阳的回洛仓遗址、江苏的镇江宋元粮仓遗址和淮安漕运院部遗址等都属于见证大运河繁盛漕运的运河遗产。
为配合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自2011年以来,河南考古工作者首次同时对隋代回洛仓遗址和黎阳仓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取得了极为丰富的考古成果,明确了两处仓储遗址的范围和城墙、城壕、仓窖、道路、漕渠、管理区等总体布局,清理除管理区外的其他所有遗迹类型,一些仓窖内还发现有粮食遗存[14]。对作为代表隋代不同类型的大型国家粮仓——回洛仓和黎阳仓遗址的首次同时发掘,以超前丰富的考古新资料,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完备时期的特大型官仓的概貌以及储粮的种类和技术水平。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黄河和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形制特征。两处仓储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对于研究隋代社会经济、政治、工程技术及俸禄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同时,也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自隋起,朝廷在今淮安地区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明清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以督查、催促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北盐南运等筹运工作。淮安总督漕运部院遗址是明清两代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漕运总督的官署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保存完好。20世纪40年代,总督漕运部院因各种原因被逐渐拆毁。2002年8月,淮安市淮安区在旧城改造中发现了明清时期的总督漕运部院遗址,漕运大堂、二堂及其附属建筑遗迹被相继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建筑石刻。2011年3月,为配合遗址保护,淮安市楚州博物馆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较多的铭文砖,主要有“镇江前军”“镇江中军”“镇江后军”“扬州府”“南昌府”等[15]。2015年淮安板闸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大运河漕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板闸遗址所发现的水闸是全国目前仅见的一座木板衬底的水闸遗址,其位于明清大运河沿线最重要节点之一的淮安,对研究古代漕运、盐运、水利、税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
大运河衍生的运河遗产在各个运河沿岸城市中多有发现。山东聊城七级码头遗址、土桥闸遗址,河南商丘南关码头遗址,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江苏扬州隋炀帝与萧后墓、淮安盱眙泗州城遗址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三、大运河城市与大运河文化的考古解读
在大运河成功申遗之前,考古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申遗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客观实际的科学阐释;在大运河申遗之后,亦即所谓的“大运河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就是对大运河城市及大运河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大运河不仅是技术的集成,也是文化的集成,是一条文化线路。“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作为遗产保护领域的前沿概念,代表了一种影响当前文化遗产演变和扩展的新思路以及对文化遗产背景环境和相关区域的整体价值之重要性的认同趋势,同时也揭示了拥有不同层面的文化遗产的宏观结构。文化线路展示了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要将每个独立存在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来评估其价值。除了其交通运输的道路功能之外,文化线路的存在和意义还能体现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服务于特定目的,并生成与之相关的共同特征的文化价值与遗产资源。
为了充分解读大运河文化,阐释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价值,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江苏而言,徐州、扬州、淮安、镇江、苏州、无锡、常州等运河城市都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早的工作始于2004年由南博主持的南水北调东线的考古调查,结合国家工程项目,对运河沿线的相关文物点作了卓有成效的调查;随后又配合文研院、清华大学、中国水利研究院承担的科技部课题“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对江苏运河沿线文物作了更加深入的调查和考古发掘。
作为线型文化遗产,大运河及其孕育的大运河文化深刻影响了沿线数十座城市的发展。隋唐以降,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所谓运河城市,即指“应运而生”的运河遗产特别丰富的运河节点城市,也是在区域文明中发挥特别重要作用的城市。对这类城市运河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应该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不是各个遗产点的简单叠加。这一类运河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持续地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梳理城市文脉,解读城市的发展与兴衰。
江苏盱眙泗州城遗址地处淮河下游、汴河之口,遗址总面积249万平方米。泗州城为唐宋时期黄河、淮河、长江水道漕运中转站,元统一全国后因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加之汴河逐年淤塞,其漕运地位最终丧失,并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最终沉没于洪泽湖水下。2010—2014年,南博主持泗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城址平面布局、汴河故道及两侧明清建筑遗存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并较为完整地揭露了普照禅寺(大圣寺)、灵瑞塔、观音寺等建筑基址。钻探表明,汴河大致呈西北—东南向贯穿全城。泗州城遗址对研究唐宋汴河漕运及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详实的材料。对泗州城这样一类定格于特定历史时空的古代运河城址,无疑需要长久持续的考古工作,才能充分揭示其价值[17]。
镇江是长江和大运河的“江河交汇”处,是长江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城市。然而,迄今为止镇江没有一处运河遗产点,与长江对岸的扬州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实,镇江具有极为丰富的运河遗产和数量众多的遗存,并形成了运河遗产片区,但是在旧城改造中,整个片区运河遗产损失严重。2009年,镇江市对市区双井路片区进行棚户区改造,该项目位于古运河入江口的东岸地带,是“江河交汇”之处,也是镇江历史文化遗产埋藏较为丰富的区域。2009—2010年,镇江博物馆前后三次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先后发现了元代石拱桥、宋代仓储、宋至清代古运河、宋代房址、明清时期京口驿等遗迹。双井路宋元仓基规模巨大,是目前大运河沿线经考古发现的一座中转仓储遗迹。结合文献记载,此遗址应为南宋时期的转般仓。转般仓是南宋朝廷为供应江淮前线而设置的大型粮仓,自淳熙五年(1178年)创立,至开禧(1205—1207年)“增为五十四廒,约储米六十余万石”[18]。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与之前考古发现的西津渡、大小码头遗址以及后来发现的京口闸遗址,位于江南运河五个入江口之一的小京口附近,背靠长江,与长江、运河共同构成有机整体,具有系统性,可以说是一处天然的运河遗产博物馆,是展示镇江运河城市形态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缺少整体考古计划和系统保护的理念,这些遗产的价值大打折扣,对历史文化名城镇江来说无疑是重大损失。
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漕运的主要物资是粮食、盐、棉花、布匹、瓷器、丝绸等。公元前195—前154年,汉高祖刘邦封刘濞为吴王,都广陵,广陵东有海陵仓。老通扬运河泰州段系刘濞所开,因主要用以运盐,故名运盐河;隋运河开通后,运盐河与运河连接。随着汉代以来海岸线的逐渐稳定,海陵东边的盐场沿着海岸从南向北日益增多,特别是唐宋以来,捍海堰、范公堤与连接盐场的复堆河、串场河形成之后,运盐河就与东边通州盐场及泰州所属的盐场直接连接而专以运盐。通扬运河一线的江苏泰州、南通、扬州等城市的兴衰都与盐运相关,但是除了古称“运盐河”的通扬运河水道外,与漕运、盐运相关的遗迹几乎空白,这就需要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进一步解读盐运文化。2015年,配合川东港拓宽工程,南博、常州博物馆和淮安市博对江苏盐城的大丰、东台和南通等地的古代盐场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发掘了宋代丁溪场盐场以及范公堤遗址,取得了重要收获。从汉唐直至明清,两淮盐课在财力上雄踞全国各大盐区之首,史载“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并有“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以两淮为最”之说,到明清时淮盐盐税已占国库财源的三分之一[19]。在江苏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中,盐运文化不可或缺,要更好地解读大运河文化,还要依靠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以发现更多的实物遗存。
考古工作所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蕴含和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是在特定时代核心文化价值观约束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技术水平”[20]。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不是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简单之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组成、分布以及彼此间的关系等都是核心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产物,凝结和反映的是人类文化。探索运河文化遗产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之上的文化价值,使运河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考古工作任重而道远。
[1]梁白泉:《初论运河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2]张廷皓:《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过程中一些思考》,《华夏文化》2015年第2期。
[3]同[2]。
[4]毛锋、周文生、黄健熙:《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科学出版社2011年。
[5]奚雪松、秦建明、俞孔坚:《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方法在大运河遗产判别中的运用—以大运河江苏淮安段明清清口枢纽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年第5期。
[6]张廷皓、于冰:《京杭运河水运、水利工程及其遗址特性讨论》,《文物》2009年第4期。
[7]谭徐明、于冰、王英华、张念强:《京杭大运河遗产的特性与核心构成》,《水利学报》2009年第10期。
[8]〔英〕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科学出版社2003年。
[9]加拿大渥太华国际运河专家会议编写(1995年):《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国家文物局2008年中译本,第7、9、11页。
[10]同[2]。
[11]淮安市博物馆:《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顺黄坝的发掘与研究》,《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
[12]佟佩华、吴双成、王占琴、李顺华:《南旺运河枢纽工程600年前水工技术至高成就》,《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13]南京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京口闸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
[14]王炬、吕劲松、赵晓军:《洛阳隋代回洛仓遗址2015年度考古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7年第1期;《隋唐大运河考古河南段——永济渠黎阳仓遗址》,《华夏考古》2013年第3期。
[15]淮安市楚州博物馆内部资料。
[16]胡兵、王剑、赵李博、褚亚龙:《江苏淮安板闸遗址》,《大众考古》2016年第4期。
[17]南京博物院内部资料。
[18]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考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
[19]同[17]。
[20]段清波:《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