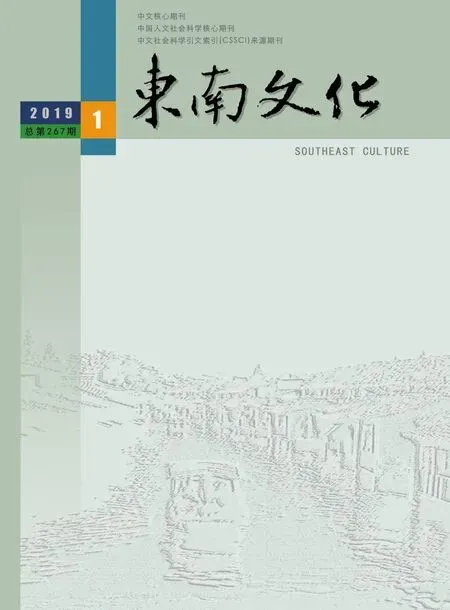当代艺术在后战争记忆空间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
马 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当代艺术全球化语境下战争叙事的表达格外具有优势,它所具备的互动性、普适性、多元性、当代性和自我意识等本质特性都契合了后战争时代具有世界主义内涵的战争创伤记忆的叙事和表征。很多战争题材的博物馆都利用当代艺术展品去实现心灵抚慰和促进战争反思,以此丰富战争历史当代表达,拓展和平教育职能。当代艺术所具备的抽象性特质使其在介入体现普适性价值、为战争博物馆实现心灵抚慰记忆的目标提供了有效路径。当代艺术是推动战争题材博物馆从“仪式性空间”向“反思性空间”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种新方法。
战争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因为战争关乎死亡、毁灭、牺牲,这些记忆既是塑造“民族—国家”自我意象的重要素材,也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权利较量与争夺的记忆源泉。作为一个充满仪式情境的审美场所,战争博物馆的“仪式性”特征尤为突出。战争博物馆是现代国家热衷于构建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国族崇拜的祭坛[1]。
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战争记忆不再仅仅与具体的地域相关,它开始超越地域和文化限制,被抽象为一种历史符号,成为修复人性破损、共筑理想未来的世界主义记忆。如何突破战争博物馆传统意义上的“仪式性”民族国家记忆空间内涵,打造具有“反思性”的世界主义记忆空间;如何在构筑本国观众对国家想象的同时,吸引更多国际观众真正获得跨文化的身份认同——这均需要战争博物馆在展示思路、诠释手段上的创新。本文即主要探讨当代艺术在当代战争博物馆这一后战争记忆空间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当代艺术虽然已经与当代战争博物馆的展示文化之间发生了紧密联系,但它的重要性却并未受到博物馆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往往停留在对其艺术本体论的讨论之中。鉴于此,本文将从记忆学、博物馆学视角去思考这一问题。
一、“世界主义记忆展示理念”内涵分析
战争造成的创伤因其无法被解释,且又往往为历史所拒斥,所以在被书写时,语言符号和叙述结构尤其受到限制。此时,“如何通过营造视觉转换空间,来邀请观众直接面对、感受和体验已消亡的战争世界便显得尤为重要”[2]。战争博物馆是历史的存储器,最直观、最真实、最具象地还原战时情景往往是传统战争博物馆展示战争创伤、并让其创伤解释获得巨大说服力的主要方式。
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化语境下世界主义记忆理念[3]的提倡,战争博物馆的意义不再停留于战争历史的存储器,它更是人们对战争历史进行反思的场所。反思战争责任、肩负文明使命、实践和平教育成为当代战争博物馆的又一使命。美国学者詹姆斯·杨(James E.Young)称:“战争博物馆展示的宗旨不单是将战争记忆予以停泊,并在场于此时此地,让观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使他们对战争事件的再体验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需要将观众的情绪从强调历史观看的方式中抽离出来,唤醒他们对历史的感知和参与感,让他们更为积极地联系自身,培养个体批判性思考的能力。”[4]可见,除最直观、最真实、最具象地再现、营造战争情景之外,当代战争博物馆还需要将世界主义记忆中所蕴含的普适性和道德反思内涵一并注入到这一记忆空间的构建之中。
为此,英国学者沙伦·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为当代战争博物馆提出了一套新的展示思路——世界主义展示理念(Cosmopolitan Mode of Representation)。她称:“世界主义展示理念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个体记忆的形成。它强调叙事的去语境化、普适化和多元观点的赋予,并强调博物馆展示空间不再是一个由权威话语主导性空间,而是一个可以与观众互动、交流的平台。”[5]换言之,它需要邀请观众加入到这一记忆空间的构建中来,通过引导、启发他们展开自主性的思考,来培养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互动、去情景化、多角度、反思、个体”是世界主义展示理念的关键词。
二、后战争记忆空间中当代艺术的价值
美国学者希尔·海德因(Hilde Hein)以独特的学术视角论述了当代博物馆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当代艺术是一种新的博物馆范式,与博物馆开放性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为当代博物馆的复兴提供了契机[6]。美国学者马克·泰勒(Mark C.Taylor)也指出:“后战争叙事依赖于当代艺术的表达,这是因为当代艺术更关注于记忆的过程,它所具备的体验性、当代性和自我意识等特性都契合了后战争语境下创伤、失去和苦难的表征。”[7]海德因和泰勒的理论视角对探讨当代艺术在战争博物馆空间中的价值具有开拓性意义。
何谓当代艺术?按照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分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其中,当我们在阐释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时,唯有把握符号“所指”所体现出来的概念,而不仅仅是“能指”所体现的形式、意象时,才能准确地解读作品内在精神性的表达。因此,后战争记忆空间中当代艺术的价值从本质上看,首先,它与传统艺术集中在作品内容与主题上所表现出的向外“移情”功能与模仿不同,它并不只是对场景的一种直接的还原式呈现,而是更注重于其“内在的抽象性”抽象象征手法的运用。一方面使其在叙事表达时具有去语境化的意涵,当以人类共通的艺术符号、思维逻辑去展开艺术表达时,它所蕴含的普适性意义有效拓展了跨区域和文化的观众对战争历史文化的可读性。另一方面,抽象性特征也使它的内涵往往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一个标准“面向”。有时,即便是同一观众也会在不同情况下对同一艺术作品产生不同的艺术体验。这样一种多元化内涵的属性恰恰契合了“世界主义展示理念”所强调的要通过引入一种更为广阔、多元的视角,有效揭示出战争表象之下复杂的多维面象。
其次,当代艺术本身所追求的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对话性也使得当代艺术的互动性更强。它不致力于提供答案,而是将自身定位为一种索引,引导观众去展开自主性思考。这种对个体关照的强调也无疑与“世界主义展示理念”中具有自主性思考能力个体的培养方式不谋而合。
而从形式上看,与传统艺术相比,由于当代艺术并不在意对作品形式的讨论,因此,相较于战争博物馆以静态实物为主的传统展陈方式而言,当代艺术因造型、材质等的不同而具有复杂性的特征。李鑫根据当前在博物馆展陈中较为常见的当代艺术作品形式,将当代艺术分为概念艺术[8]、新媒体艺术[9]和特定场所艺术[10]三类[11]。
可见,当代艺术“抽象性、互动性、当下性和多面性”的特征恰恰呼应了世界主义展示理念所关照的焦点。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代艺术与当代战争博物馆展示文化之间已然产生了联系。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新建的一系列战争博物馆如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The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and Museum)、英国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德国柏林犹太人纪念馆(Jüdisches Museum Berlin)等,都会在其展览空间中适当运用当代艺术展品去展示、诠释战争记忆。譬如像“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试图记住九月那天天空的颜色”(Trying to Remember the Color of the Sky on That September Morning)就是一件非常著名的当代艺术展品。2016年,该馆又推出了名为“再现难以想象:艺术家回应9·11”(Rendering the Unthinkable:Artists Respond to 9/11)的艺术展,展览运用了不少当代艺术展品,去反思战争创伤所造成的原始情感,以此推动人们理解无辜生命不可预知地被毁灭的灾难性结局。除了“9·11”国家纪念博物馆,2013年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也专门推出了一个以当代艺术与战争为主题的展览“作为催化剂的当代艺术与战争表征”(Catalyster Contemporary Art and War)。该展展出了几十件本馆收藏的当代艺术作品,这些融入了艺术家们个体经验和记忆的作品以一种非再现、复制和写实的艺术形式,试图使观众在当下这个已不再受到地理时空限制的时代,以更为多元和广阔的视角去思考人们对战争的理解。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相关类型的博物馆、纪念馆也开始积极运用当代艺术手法去深化对战争主题的诠释。譬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常设展中的“12秒水滴”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展品,它通过具有抽象意味的诠释手段,创造了一种帮助观众记住历史的方式。2017年,该馆又推出了名为“痛的沉淀与超越”当代艺术展,丰富、拓展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沉重的历史话题,通过超越国界的艺术语言来表达对疼痛和战争的更深邃理解的目的。
三、当代艺术与心灵的抚慰
当今战争记忆已被视为一种可以跨越地域和文化边界,共同修复人性破损,共筑理想未来的资源和素材。那么,如何有效实现更广泛意义上全球化的文化关怀,当代艺术所具备的抽象性特质使其在介入体现普适性价值、为战争博物馆实现成为心灵抚慰记忆场的目标提供了有效路径。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展出了一件名为“展品13”(Exhibit 13)的当代艺术展品,通过一种去叙事化的抽象方式表达了对战争到来时人们最原始情感的反思。该展品是一段4分钟左右的影像,影像画面包含了纸张、信件、商业档案及私人便笺。这些纸张在空中四散飞舞的画面,配合着一段复述纸片记载内容的轻音乐,显得异常空灵,能够触动观众心灵。据创作者蓝人乐团(Blue Man Group)介绍,这件展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灾难发生时从世贸大楼里飘出的纸张。画面中这些书写着不同国家文字的纸张漫天飞舞,反映出这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性的灾难。蓝人乐团希望通过对这一画面的艺术再现,而不是一种基于写实性的完整式绘图方式,让作品本身更加偏向于成为一种提供内心诉求的场域,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从中感受并体会到无辜的生命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毁灭的悲剧性[12]。
再譬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痛的沉淀与超越展”中的“守望相助”展品。这件展品由孟舒创作,属于概念艺术范畴,目的是让观众在“南京大屠杀”这一沉重主题之下找到一个释放悲伤与愤怒的渠道。同样,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展陈设计团队曾在如何展示“恐怖”这一主题时讨论道:“战争的主题本身就已经足够沉重,如果此时我们再过多地以赤裸而直接的方式去简单呈现,那么它在成功渲染出战争惨烈的同时,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历史逃脱感。”[13]如何帮助观众在直面人性黑暗的同时,平复、释放被压抑的悲伤、愤怒情绪,实现心灵抚慰,对于让观众正确理解战争至关重要。
“守望相助”展品之所以选择玻璃这种材料,是因为玻璃的质感可以带给人们一种美好、明亮、轻盈和轻松的感觉。孟舒通过设计色彩的寓意(譬如缠绕在玻璃球中的黑色代表着事件的创伤性、白色象征着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的那个寒冷冬天)和玻璃内形成气泡的形状(如莲花状代表着心灵的释然、眼珠状代表着对历史的见证)等一些抽象艺术符号的融合,来让其成为一个不提供答案但可以引发观众无限想象的展品。玻璃球所蕴含的开放性解读空间在邀请观众积极加入到与历史对话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在这样的可言说之中释放情绪。
除了像“展品13”“守望相助”等希望通过对内心诉求场域的营造来实现普适性的人文关怀的展品外,当代艺术在对个体心灵抚慰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它希望通过展品提醒、督促观众在高情感卷入度的参观体验中,不应仅仅感受到一种泛化的情感共鸣,而更应真正获得一种内化于心或者直击自身心灵的感悟。“南京的悲伤”黏土脸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的另一件当代艺术展品。它由日本学者松冈环组织中日两国的81位学生共同创作完成。松冈环让学生们用黏土自由创作出他们想象中受难者脸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被悬挂在一起的这些黏土脸上所呈现出的痛苦表情各异,有的眼睛紧闭,有的双眉紧锁,有的嘴巴张开。松冈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呼吁人们不仅要记住伤痛,更要用心去体会伤痛。就像詹姆斯·杨所指出的:“传统的历史外化展示方式在记忆某段历史并提醒人们回忆这段历史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这段历史束之高阁,加速了人们忽视、遗忘的过程。”[14]松冈环在展品旁设置了视频装置,其放映的一段纪录片中详细记录了这件展品被制作的过程。她表示这件展品并非只是一件静态的作品,她希望通过对动态性创作过程的再现来提醒每一位观众,残暴的战争所造成的伤痛不是仅通过了解就可以感受到的,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尽管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但只有真正通过我们内化于心、直击心灵的体会,个体心中的纪念才会上升,而这份伤痛战争记忆才可能得到铭记和超越。
四、当代艺术与战争的反思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避免战争再次发生的唯一途径是需要“在任何条件下,教育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15]。他呼吁每一个人都应该建立起对自身批判的思维模式,只有对现代文明内部的阻碍和平的因素进行反思和警醒,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诉求。当代艺术本身内涵的多义性和注重作品与人的对话性特征都使得它可以表现出深层次的调适态度。它如同催化剂、一种索引,督促观众通过与艺术作品的对话展开更为多元化、自主化的思考,形成自我的理解和反思。
纵观当前,当代艺术在战争博物馆中所欲引发的探讨与反思的主题十分多元,以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中的“作为催化剂的当代艺术与战争表征”展(Catalyster Contemporary Art and War)为例,它将几十件当代艺术展品根据主题的不同分为“媒体战争引航”(Navigating the Media War)、“催化剂”(Catalyst)、“记忆的景观”(Landscape of Memory)和“变化的战争前沿”(Shifting Fronts)四个展示单元。从展览单元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展品所欲引发的议题都不是传统的战争叙事题材,它既有像Navigating the Media War单元这样对新闻媒体在战争宣传背后所隐藏的权利机制的反思,进而再衍生出对记忆真实性和历史书写、塑造这一组关系的探讨;也有Landscape of Memory单元致力于对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记忆景观与遗忘的再思考;还有像Shifting Fronts单元侧重于对当代战争中无人机等新武器及根植于本土的恐怖主义等新型战争模式的讨论等等。
譬如在该展览中,菲儿·霍普金斯(Phill Hop⁃kins)创作的“饮食者”(Drinker)艺术品,就通过塑造一个鸟造型的战斗机模型正在饮用一个似鸟食槽的油管概念,去探讨海湾战争爆发的原因。它通过形象的对比,揭示出对石油等经济资源的获取是爆发战争的深层次重要驱动力。再譬如克丽·特赖布(Kerry Tribe)创作的“最后的苏维埃”(The Last Soviet)新媒体影像,它通过对当年苏联解体前电视画面之间的不断切换和画面与声音之间的错配,来影射媒体报道的政治取向,以此向观众抛出历史建构的真实性问题。而马克·奈威尔(Mark Neville)创作的“孩子、夹克衫、屠宰山羊、糖果、彩绘指甲、圣诞节、赫尔曼德”(Child,Jaket,Slaughtered Goat,Sweet, Painted Nails,Xmas day,Helmand)表现出一个头戴圣诞帽、身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分发的夹克衫、手拿英国驻军部队分发的糖果的阿富汗儿童的形象,其背景是正在宰杀一头羊来庆祝圣诞节的阿富汗民兵团这一融合着不同元素的画面,借此揭示出战争给当地人带来的与敌军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奈威尔称他试图通过不同元素之间所造成的违和感去触发观众反思现代战争给战争地区造成的不同价值观和习俗间的碰撞和冲突。毋庸置疑,这些当代艺术展品正是通过提供一种多元的、广阔的诠释视角,不再单纯地展示战争的凄惨场景,更是致力于剖析、揭示出战争表象之下复杂而多维的面象。不仅如此,它的索引特征也让它可以更好地打破长期因话语中心而存在于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那道“隐形的墙”;它意在抛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它通过对话性和互动性方式让博物馆可以真正在知识教化与观众自我体验之间架起一道可逾越的桥梁。
除了像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北方馆这样以特别展览、临时展览的形式将当代艺术融入展览空间之外,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在2005年新开放的常设展览中也大量地使用当代艺术展品深化对战争记忆内涵和意义的诠释和解读。“生活景观”(Living Landscape)和“最后的火车”(The 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是美国学者詹妮·弗汉森-格吕克利希(Jennifer Hansen-Glucklich)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件展品[16]。
“生活景观”展品是一段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犹太社区情况的视频,它由历史老照片和电影片段剪辑而成,滚动播放。但与传统的历史影像幻灯片不同,展品并不旨在通过还原老照片来完整再现历史场景;相反,幻灯片被投影在一个呈三角形的展墙之上。因此,对于观众而言,最终所看到的画面是缺失的。创作者麦克尔·罗夫纳(Michal Rovner)称这件展品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空缺感”。他希望以三角形这一犹太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大卫之星”的一半为视角出发点,以历史画面的缺失去挑战传统战争叙事模式中具有宗教主义救赎意味的复国主义叙事。对空缺的解读无疑会引发观众的联想和思考,即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根本无法弥补,即使今天犹太文明延续下来,但依旧是建立在伤痕和不复回归的过去之上。与“生活景观”展品所欲探讨的要打破对战争等创伤叙事所固定的具有救赎意义的叙事模式不同,“最后的火车”展品却试图再将观众的理解拉回至战争叙事传统模式对于合理、完满的意义解读之中。这两件当代艺术品在展览的物理空间中前后呼应,所引发的关于战争内涵的多维度诠释路径也再一次反映出这种展陈方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催化剂功能。
在传统的战争博物馆展示理念中,大屠杀列车车厢作为毁灭人性的象征是最具有典型性和标志性的文物。譬如像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当初在布展时就特地从欧洲征集了一节旧车厢,并通过声、光、电甚至是气味的调动,试图最大程度地带给观众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和无可辩驳感。然而,“最后的火车”展品的创作者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却突破了传统展示方式,他在最大程度地利用遗物的同时,巧妙地将原本作为物证的元素抽离变成了一个融入周围环境的特定场所的艺术展品。整件作品呈悬空状,向上延伸却戛然而止的铁轨直指远方的霍茨尔山(Hoheisel Hill),铁轨上的一节车厢在与周边环境的融入下,营造出好似要冲破重力束缚、向着远方驶去的意境。萨夫迪称:“作品与周边环境的不可分割性让人们对于大屠杀列车非人道、苦难等传统的想象方式得以超越和发散,它根据不同人的理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乐观的观众会从列车的指向、远方的胜利之山——霍茨尔山中看到重生、自由与延续的希望,而悲观的观众也会从列车好似冲破重力束缚、继续前进的状态中联想到今天甚至是未来都依旧无限循环存在的战争。”[17]
五、结语:作为一种展示新方法的当代艺术发展展望
战争博物馆不仅是展示记忆的地方,而且是记忆生成和重修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之中,历史叙事与个人经验不断交互。尤其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战争博物馆更加追求如何让数量庞大的个体于其中展开创伤书写,也更加关注如何令具有反思深度的个体记忆在这一空间内形成和交流。
如何实现当代战争博物馆从“传统仪式性空间”向“后现代反思性空间”的转型,这不仅需要理论支持,更需要在展示方式、诠释手段上的创新。从上文引用的具体案例可以看出,当代艺术表现形式多样。但无论是概念艺术抑或是新媒体艺术、特定场所艺术,它的抽象性和多元内涵使它抽离于具体的历史信息,拓展了记忆的内涵,并有效地将人性、普适性的维度引入其中。而它对于作品本身与人对话的重视,又使其表现出深层的调适能力。它如同一种索引,在避免给予单一答案并强化某种思维模式时,让观众可以抽离于传统的被灌输方式,在自主性联想和思考中达到对伤痛的抚慰和对历史认知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观众从汇集知识再达到形成自身理解,从而调整自身经验,最终成为自身认识的一部分。而这样的路径恰恰符合了后战争时代当代战争博物馆的教育宗旨。
可见,当代艺术全球化语境下战争叙事的表达格外具有优势,它所具备的互动性、普适性、多元性、当代性和内化性等本质特性都契合了后战争时代具有世界主义内涵的战争创伤记忆的叙事和表征。毋庸置疑,它可作为当代战争博物馆展陈创新中一种不可替代的辅助性元素和手段。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详实的各类历史数据罗列、逻辑清晰的历史事实叙事,是保证观众可以在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认知之上形成对战争更深入思考的前提。因此,本文并不旨在说明当代艺术就可以超越传统的展陈方式、诠释手段,而是希望抛砖引玉,在肯定当代艺术这一媒介所具有的开拓意义的同时,为未来战争博物馆展览空间中当代艺术的创作、运用和实践提供借鉴思路。
[1]范可:《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陈雪云、吴慎慎、陈仲彦、郭文耀:《重返历史、人权与记忆——台湾乌脚病医疗纪念馆的新未来》,《博物馆学季刊》2013年第2期。
[3]世界主义记忆是由丹尼尔·列维(Daniel Levy)和那坦·齐奈德(Natan Sznaider)提出,认为战争、大屠杀等创伤事件超越传统意义上地域、民族、国家经验,而具备一种与人类普遍体验相融合的普适化认同视角,它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承担的、面对的历史。世界主义记忆强调人性和道德责任。
[4]James E.Young.The Texture of Memory: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s.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120-130.
[5]Sharon Macdonald.Difficult Heritage: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Routledge,1998:139.
[6]Hilde Hein.Museums and Public Art:A Feminsit Vision.Harvard Book Store,2014:28.
[7]Mark C.Taylor.Disfiguring:Art,Architecture,Relig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76.
[8]概念艺术又被称为观念艺术,艺术外在的质地、材料、形状等都不是主要衡量因素,最核心的是艺术所表达的观念。考虑到概念本身的抽象性以及观众理解这些概念对于理解艺术作品本身的重要性,因此,在进行展示时,对概念艺术的诠释、说明、引导必不可少。
[9]新媒体艺术主要是指数字化环境下创作的作品,或用非数字方式的新技术、新材料创作的作品。新媒体装置艺术、数字技术、互联网艺术等都属于新媒体艺术的范畴。
[10]特定场所艺术改变了现代艺术作品与场所之间的关系。它强调艺术作品本身不再是可随便改变处所的独立物件;相反,作品与周围环境不可分割,其形式、意义内涵都依赖于其所处环境、位置的互动过程中。
[11]李鑫:《当代艺术的博物馆展陈问题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官网,[EB/OL][2016-12-13]]https://www.911memorial.org/blog/blueman-group-founder-and-fellow-artists-discuss-creating-art-after-911.
[13]〔美〕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著、周怡等译:《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14]同[4],第133页。
[15]〔英〕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著,杨渝东、史健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16]Jennifer Hansen-Glucklich.Holocaust Memory Re⁃framed—Museums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presentati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4:149-172.
[17]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