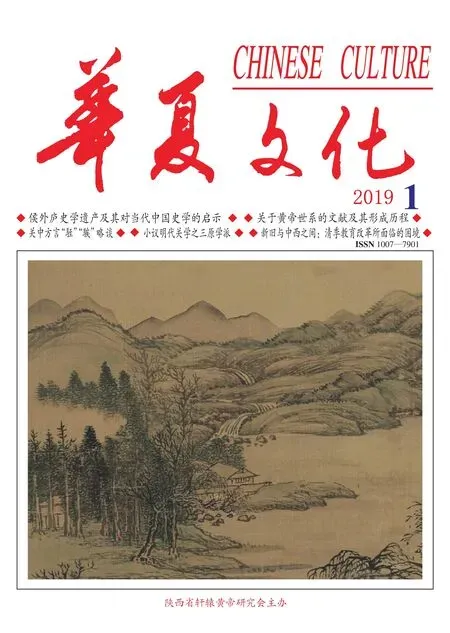论庄子与惠施“天地一体”观的区别
□赵 田
在《庄子·天下篇》中,关于惠施的“道”,可以一言以概之:“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也有类似的言论,《齐物论》一篇中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若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似乎庄子与惠施都秉持“万物一体”的物我观,所不同之处只在于惠施在此处强调了“泛爱万物”,那么庄子对于万物,是否也有这种“泛爱”的情感呢?庄子与惠施所言的“天地一体”的内涵是否一致呢?以《〈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为参考,顾实、高亨、钱基博、马叙伦四位学者对此的注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二者并无差别,一是二者差在“泛爱”。
一、 《〈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一书中的观点
钱基博认为这是“道家者言之究竟义”。老庄对此都有过相关表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老子之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秋水》:“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此庄子之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可见钱基博并不认为老庄与惠施的观点是有所差别的。高亨对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解释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古持有天圆地方之说,或曰:“惠施持天地俱圆之说。以为天如圆盂,而覆于上,地如圆磨,而承于下。天之周涯,地之周垠,本相接连,而成一体,故曰‘天地一体’。或曰:“惠施认为天地为鸡卵,天如鸡卵之白,地如鸡卵之黄,本自成一体,故曰‘天地一体’。”这种解释是基于惠施看待万物的独特方式而作出的,但并未与老庄的相关论述作出比较。马叙伦在这里所采取的是章炳麟和胡适两位学者的注解。章炳麟:“大同而与小同异,此物之所有。万物毕同毕异,此物之所无,皆大同也。故天地一体。一体,故泛爱万物也。惠施之言,无时、无方、无形、无碍。万物几几皆如矣。”胡适:“上说九事,都可证明天地一体之根本观念。以宇宙是一体,故欲泛爱万物。”(张丰乾:《〈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从以上三位学者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们皆认为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观点和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并无差别。
但顾实认为,“泛爱”正是庄子与惠施的不同之处所在。惠施泛爱太过,这一点不可不察。对此,顾实所做的解释如下:“此同心物之异,而为历物之意之结论也。”这是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句话是对惠施“历物十事”中前九个命题的总结,是“合同异”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在《庄子》一书中,相类似的言论还有不少。《秋水篇》曰:“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这是说人只是物中一物,并无任何优越之处。《达生篇》曰:“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则阳篇》曰:“天地者,形之大也。”即便是天地,也是物中一物,只是大小上有所差别罢了。《齐物论篇》亦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接下来,顾实先生以《庄子》一书中的特定篇目为例,说明道家不尚泛爱。例如《天道篇》老子曰:“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在宥篇》曰:“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顾实先生认为惠施所言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与庄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涉及到的,是“泛爱”的问题。惠施“泛爱”太多,而庄周并不尚“泛爱”。这不免涉及到二人的“天地一体”观内涵是否一致的问题。
二、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从《庄子·天下》中所载的“历物十事”可以看出,惠施擅长逻辑分析,注重对事物名相的辨析。其“合同异”命题就是惠施论证“天地一体”的证明:“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按照惠施的看法,同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小同异”一种为“大同异”。“小同异”是从世俗或常识的角度而言的,是说具体的事物之间存在异同之处。此物与彼物,或同或异;“大同异”是说万物毕同毕异。从天地一体来看,万物只是一物,这就是“毕同”,从万物的差别来看,万物各是一物,这就是“毕异”,“毕同”“毕异”意为万物既莫不相同又莫不相异,这就是“大同异”。从惠施“大同异”的观点来看,他是从万物之名上取消了万物之间的同异之别,因此,事物之间的彼此之分都是相对的,所以“天地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泛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到目前为止,关于惠施“泛爱万物”命题的理解存在以下五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该命题具有伦理性质,并且源于墨家的兼爱,如胡适等;第二种:该命题具有伦理性质,但并非源自墨家的兼爱,而是源自黄老,如郭沫若等;第三种:该命题不具有伦理性质,“爱”字只能作 “爱好”、“喜欢”解;第四种:冯友兰认为该命题没有实际意义,可能只是用来加强 “天地一体”的语气;第五种:该命题在惠施那里确实具有伦理性质,但泛爱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惠施这里,“泛爱”只是果,而“天地一体”才是因。惠施通过辨析名理,要达到的,并不是“泛爱万物”,而是“天地一体”。
三、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齐物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从此物看,对方为“彼”;然而从彼物自己一方看,它即是“此”。也就是说,万物之间并无绝对的彼此之分,在未落入对待的情况下,它们实际是“齐同”“齐一”的。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万物之间存在种种差别,是因为人将自己的认知强加给了万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秋水》)但如果人们要是从“道”或“全”的观点看问题,就可以获得“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大智慧,从而不再为“小成”之见所困扰和烦恼。在《齐物论》中,庄子通过“齐是非”“齐同异”“齐物我”“齐生死”,最终达到了“齐万物为一”的境界,这个“一”就是一于“道”。既然万物为一,那么所谓的是非同异问题,当然就归于无形,被消解殆尽了。
除此之外,庄子从生成论的角度说明了“天地一体”何以可能。在《知北游》中有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这是从生成论上肯定了万物皆为一气流行而生,为“万物与我为一”提供了质料保证。
四、二者的区别
从两人论证“天地一体”的思路和方法来看,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是从前面九个命题中得出来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合同异”,万事万物毕同毕异,并无绝对意义上的差别,因此可以说“天地一体”。既然“天地一体”,“泛爱万物”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从对事物名理上无止境的辨析中得出来的,是通过自身的雄辩之才将万物化为一体,至于“泛爱”,则是在“天地一体”的基础上顺势衍化出来的。与惠施不同,庄子是从万物的生成方式上来表述“齐物论”的。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将主体与客体化为一体,取消了主客对立,主客二分。这与惠施通过雄辩之才齐同万物是截然不同的。庄子所说的 “万物”,并不需要“我”这个主体去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探究分析,也就是说,万物无须落入人的对待中来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与天地万物是齐等共处的,而不是外在于它们而存在。从对待万物的方式来看,在惠施那里,是通过自身的雄辩之才来消弭万物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合同异”;而在庄子心中,则是要取消主体的偏执与成心,完全从“道”的立场出发,也就是“以道观物”,在洞察万物表面的性质是有差别的前提之下回归到物质的本性,自始至终所秉承的就是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齐物”状态,这正与惠施的“天地一体”的理论殊途同归。 只不过,庄子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通过“虚静”“坐忘”“吾丧我”等方法,不仅消除物与物之间的界限,也消除了物我之间的界限,从而得到精神的“绝对自由”。而惠施虽然通过论证达到了“天地一体”,却没有将之与自身实践相结合,反而为外物所累,困于名实。 因此也有学者指出,惠施之“合同异”只是在“名”的层次上而言,非实际事物之间差异的同异之“实”。 而庄子所“齐”的不仅仅是“名”,更是齐万物之“实”。(参见赵炎峰:《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的差异》,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由此可见,惠施落脚于“物”,庄子落脚于“道”。庄子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这就表明,惠子聚焦的“物”不及庄子秉承之“道”,因“物”有死生,而“道”则永存,“道”是本,“物”是末。 因此,庄子说“外物不可必”,评价惠施“弱于德,强于物”,“逐万物而不反”,是舍本逐末,误入歧途。
不仅是论证的方法和对待万物的态度有所差别,二者所持的心境也是不一样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所表现出来的,是惠施对于万物之名的辨析之才,而《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体现出来的,则是庄子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篇》)的悟道境界。一个累于物,一个是脱于物,一个是究极物理,一个是超然物外。虽然两人都讲“天地一体”,甚至惠施还提出了“泛爱万物”的说法,但是两人的物我观所体现出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