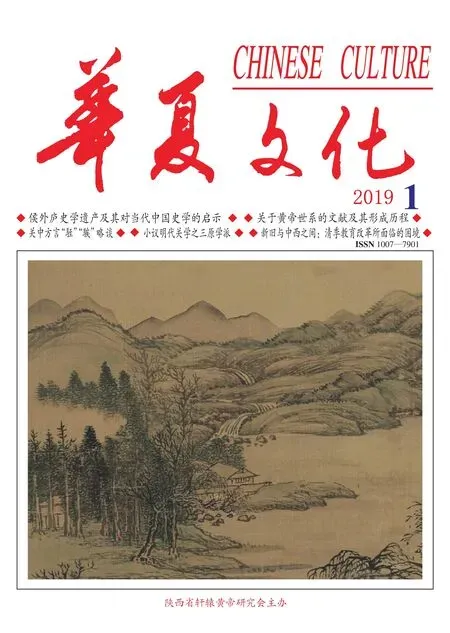朱熹“法者,天下之理”辨析
□白 贤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朱熹不但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为“集诸儒之大成者”,而且在法律思想方面也颇多建树且影响深远,故向来亦为治法史者所重视。
如在礼、法关系上,朱熹认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朱子语类》卷六)而“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晦庵集》卷五九)。他指出:“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晦庵集》卷十四)“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晦庵集》卷四十)“道字、理字、礼字、法字,实理字,日月寒暑往来屈伸之常理,事物当然之理。”(《晦庵集》卷四八)也就是说,所谓天理不过是儒家之伦理纲常而已。因此对于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自然罪无可恕,即“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在量刑标准上,朱熹主张重刑主义。他在《戊申延和奏札》中说:“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晦庵集》卷十四)在司法实践中,朱熹主张以“经术义理”决狱,“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深浅之量可得而测。”(《晦庵集》卷十四)“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晦庵集》卷十四)
也许正是由于朱熹的法律思想主要是通过论述天理体现出来的,致使许多法律思想史著作中多引述“法者,天下之理”一语,并将其视为朱熹对法律的基本看法,至于持此观点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然而这种看法却是出于文本上的误读。
考之典籍可知,“法者,天下之理”一语节录自朱子《晦庵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其原句为:“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文中说得很明白,此处的“法”乃是“家法”,是指先儒“圣贤”的“已成之说”,跟法律之“法”本不相涉。整句话的意思也是在强调遵奉儒家正统思想的重要性。再者,从语句的通顺角度而言,如将“法者,天下之理”从文中抽离,则前后之文根本难以成句。
其实,朱熹此处所言家法,乃是习用汉魏以来的说法。家法一词,在汉代原是经学门派的代称。即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左雄传》时所说:“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载,东汉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即按照门派将经学的各家立为官学,使之沿袭传承。正如清代学者赵春沂《两汉经师家法考》所云:“六籍之学,盛于汉氏,诸儒必从一家之言,以名其学……大抵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有所师乃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夫家法明,则流派著,可以知经学之衍别,可以知经文之同异,可以知众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谊。汉学之盛,盛于家法也。”(载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一)
按照张国刚先生的研究,“家法”观念自身在汉代以后发生了重大改变。要言之,即魏晋以来,家法之意常常被家族礼法取代,乃至后人所理解的家法,就变成了士族人家教授子弟的礼法(参见张国刚:《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如著名的《颜氏家训》综合南北习俗礼法,贯穿儒家孝悌之道,是士大夫立身和处世的行为准则。至于士族礼法传统对唐宋以来政治、社会的影响,张国刚先生亦指出:随着儒家伦理经历了从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经历了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士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于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也成为北宋道学形成的重要土壤(张国刚:《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与唐宋之际的社会演变》,《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期)。对此,两宋时期兴起的诸多士大夫家族的家训、家礼、家规等即为明证。颇具典型意义的是,作为赵宋统治者的“祖宗家法”,成为影响宋代政治与法律的重要依据。有关宋代文献中的“祖宗家法”“祖宗之法”等称谓可谓比比皆是。正如邓小南先生指出:对于“祖宗家法”这种正家治国模式的追求,植根于那一时代的传统之中,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行为、制度乃至社会观念;并且就是在那些行为、制度、观念甚至习俗之中,体现出它的存在(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综上可见,家法一词在宋代至少有两种涵义,一谓学问之师承,一谓家族之法规。朱熹原语中“家法”的含义,正是沿用了汉魏以来的传统说法——尽管这一语义在唐宋时期已较为罕见。所谓“法者,天下之理”的说法虽然暗合了朱子的法律思想,但并非朱子原话本义。然而大多数学者在引用该段文字时不加甄别,以讹传讹,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