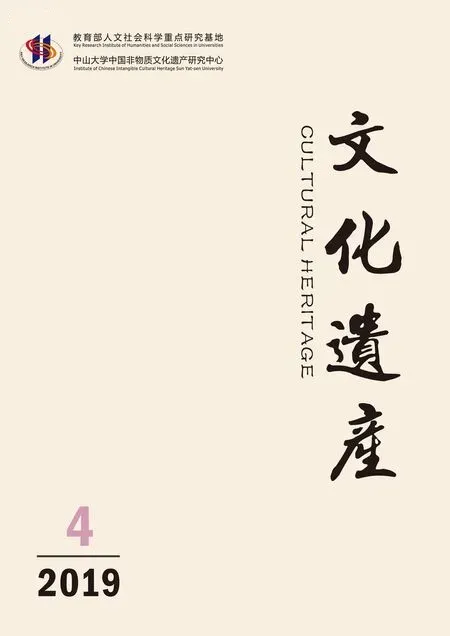国家建设视野下的广州市沙湾镇文化治理研究*
张玲玲 赵 萱
过去的十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不断引起学界的关注。在一系列的讨论中,主要是围绕文化遗产所涉及的众多行动主体和空间层次,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异性的主体关系与权力空间格局展开的, 讨论的重点逐渐由文化遗产本身扩展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从文化遗产作为“民间”(地方)文化的存续扩展到文化遗产作为“国家”(公共)文化的转型。这不仅将文化遗产的内容及其保护过程纳入到了研究视野中,而且将文化遗产的现代形态转化为“提问”而非“结果”,从而呈现文化与政治 之间的关系何以实现。
本文将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广州市沙湾镇的民族志考察,探讨宗族、民间信仰组织以及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进程中逐渐涌现,成为新的主体,促成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国家如何通过全新的“治理技术”实现对多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整合,生成出一种“治理组装”的格局。
一、对文化遗产的批判性反思
以高丙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为非遗)保护带来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认为其在认识取向上实现了从自我否定导向的“文化自省”向自我肯定导向的“文化自觉”的转变。[注]高丙中、赵萱: 《文化自觉的技术路径: 非遗保护的中国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3期;高丙中: 《非遗: 作为整合性的学术概念的成型》,《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高丙中: 《中国的非遗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非遗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非遗实践也例证了根植传统对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注]张举文、周星: 《中国非遗实践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的内在逻辑和传承机制》,王宇琛译,《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张举文:《非遗与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民俗研究》2018年第1期。
因此,如何以整体性、可持续的原则来保护生成于日常生活中的活态文化成为焦点,以往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尚未能有效地实现“整体性保护”。[注]刘朝晖: 《村落社会与非遗保护———兼论遗产主体与遗产保护主体的悖论》,《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4期。随着日常生活中各种仪式及生活实践的遗产化,“日常”正在变成“非日常”,当地方性文化转变为公共性遗产之后,便会与原有生存语境发生断裂,出现选取式的遗产化现象,在遗产遭遇剥离的同时,其原有的意义也将面临解构。[注]刘正爱:《在田野中遭遇“非遗”》,《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周星: 《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随着非遗保护的逐步拓展,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层面的问题开始出现。在新的语境之下,遗产概念被认为受到政治性表述的影响,弱化了地方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和地缘性,使得一套包含了政治、权力、历史形成主体等新的“遗产事实”被再生产出来,这些经过“简化”和再生产的文化遗产,凸显了国家的叙事,却造成了遗产实践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注]魏爱棠、彭兆荣:《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刘朝晖:《“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文化遗产》2016年第6期;刘正爱:《观光场域中历史与文化的重构——以恢复赫图阿拉城为例》,《思想战线》2007年第3期;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和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遗产的制造本身就是一种多主体、多层面的参与过程,不仅包含了遗产部门、政府,还包括了遗产专家、博物馆员工等,除此之外,还有观众对遗产的理解。[注][澳]劳拉简·史密斯: 《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 遗产批判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张煜译,《文化遗产》2018 年第3期。面对当前遗产实践活动中的多主体参与现实,有学者指出关注点应从遗产本身的保护方式转向遗产政治中各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将遗产实践置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分析,尤其是普通人与国家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关系。[注]龚浩群、姚畅:《迈向批判性遗产研究:非遗保护中的知识困惑与范式转型》,《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文化遗产保护逐渐与更广泛的治理问题相联系,例如地方性文化作为现代乡村公共治理的内生资源,只有将这些资源及利用起来,让更多力量加入到地方治理中,才有可能重构多元共治的乡村社会秩序。[注]张翠霞:《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治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正是通过对文化遗产实践的不断反思,保护过程中的主体参与和具体方式逐渐成为分析的重点,国家作为一类重要的行动主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需要新的探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不再是一类单纯的文化与地方事物,而是和更广泛的国家权力实践和社会治理相关联。
这种要求超越单一的地方空间层次以及单纯的文化领域范畴,从“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相互勾连的治理层面去理解文化遗产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一种“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视角。该视角将文化遗产保护视为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关注具体保护和开发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所采用的权力话语以及由此形成的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基于文化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去理解文化与政治关系的不断生成与调整。在此语境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升温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地方文化复兴”或者“市场化”的结果,而是更为复杂的国家治理转型的一部分。
二、多主体共存的沙湾文化遗产实践
要理解当下沙湾镇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上复杂的权力关系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沙湾作为一个文化空间本身所囊括的多元主体。虽然国家建设的视角强调了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国家属性和现代性,但是这一视角的运用更多的是要求分析者将文化遗产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作为问题,去解释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具体形成。沙湾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沿着国家-民众、由上而下的权力关系来展开,但这样一种纵向的、支配性质的管理方式如同民族国家一样,相当晚近才得以形成。在更长的时间内沙湾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其文化的维系并不依赖于国家对于文化遗产的直接保护,而是有赖于地方各种组织和团体日常生活中对多文化符号与仪式的实践与使用。当下沙湾所形成的文化生态并不是由外部施加,而是一些历史中被边缘化的主体通过新的治理技术回到中心的结果。无论是下文中利用“侨胞”这一概念获取非国家主体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合法性,还是以“宗族”之名形成文化遗产开发的另一种路径,甚至是非遗与市场力量在沙湾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快速崛起都需要回到沙湾历史中去找到内生性的解释。这些在历史中维系了沙湾文化空间的主体和力量,虽然在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中被阶段性的边缘化,但是只要现代性的“自反性”逻辑依旧存在,他们就会在恰当的时候再次回到文化空间建构的中心地带,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宗族力量曾在地方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宗族乡绅共同控制着地方社会。[注]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94页。据《沙湾镇志》记载,沙湾的宗族多是在南宋时迁来的,[注]中共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委员会,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人民政府编:《沙湾镇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7页。伴随沙田的开发,形成宗族聚落,沙湾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族都在其聚居的地方建有自己的宗族宗祠。[注]在以往的沙湾研究中,宗族与沙田开发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沙田作为宗族的财产基础是宗族力量的政治和文化资源。刘志伟:《宗族与沙田开发》,《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朱光文:《珠江三角洲乡镇聚落的兴衰与重振》,《广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作为沙湾五大族[注]据《沙湾镇志》记载,沙湾的五大姓指何姓、王姓、黎姓、李姓和赵姓。之一的何族,其宗族祠堂最多时曾达120多座。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力量一度被视为封建残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下逐步式微,宗族祠堂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拆毁或移作他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市场经济的浪潮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解放,也推进了地方非国家力量在社会事务层面的复兴,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宗族复兴”,包括重建祠堂、重修族谱等,宗族文化重归日常生活当中。在此背景下,建于元朝,规模宏大的何氏祠堂——留耕堂被视为当代沙湾宗族文化乃至岭南文化的主要代表,并在1989年留耕堂列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沙湾的宗族文化外,民间信仰也是沙湾地方文化中独具特色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宗族文化相辅相成。因沙湾地区河网纵横,沙湾人便将“水神”——玄天上帝,即北帝,尊称为“村主”,由各村坊轮流供奉,并由此发展出三月三“北帝诞”迎神习俗以及以飘色为代表的娱神仪式。[注]中共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委员会,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人民政府编:《沙湾镇志》,第526页。除此之外,大多数沙湾人相信家中也有神灵,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等,因此,家中各处也都供奉着对应的神灵,形成了以家户为空间的神祗系统。北帝崇拜与家户神祗互不冲突,是一种共存关系,共同构成整体的沙湾民间信仰体系;同时,民间信仰与宗族组织亦存在紧密关联,成为理解沙湾文化空间的重要切入点。
在上述的背景中,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标志性时间点,我们可以切分出沙湾民间文化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文化改造时期(其原有空间不作为文化空间)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复兴时期(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这也与中国民间文化复兴的宏大背景相一致。但这一基于“文化复兴”所进行的历史划分却不免模糊或淡化了文化复兴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将文化空间的塑造过程简化为以国家意志为原点的政府行为;同时沙湾文化依旧停留在单一的“遗产”(包括政治和文化)语境中,而缺少了“活态”的地方性生长过程。在下文中,笔者将聚焦不同历史时期参与主体的变化以及文化概念的转变,尝试厘清沙湾公共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历史经纬。
(一)侨胞:合法性的获取与非国家主体的介入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展开了对民间文物的保护工作。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沙湾镇政府开始计划重新修建何氏大宗祠留耕堂,这一计划在当时得到市、县(现在的番禺区)、镇各级的重视,并于1984年展开了全面的修复,历经两年,留耕堂基本恢复全貌。重修后的留耕堂于1989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注]《沙湾何氏宗族概况》编纂委员会编:《沙湾何氏宗族概况》,何氏联络处内部刊物,2011年,第192-195页。据《沙湾镇文化站评估定级申报工作汇报》记录,这次修复所需资金由主要由政府承担,分别是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各级人民政府共同拨款100万,另有港澳乡亲捐款港币10万。修复后的留耕堂交由当时的文化站管理,只是作为沙湾镇的文化活动场地,以沙湾历史文化陈列馆的形式对外开放。这一显而易见的政府文化工程却隐含着另一条线索。
祠堂的修复往往容易被看作是沙湾宗族文化复兴的起点,但宗族并非文化复兴过程中出现的首要概念。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文化开始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帮助自身取得文化上的复兴。1978年5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侨务办公室,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设立了侨务办公室。特别是随着全国人大及各地华侨工作委员会的相继设立,同胞间的互动机会也因恳请大会、社团联谊大会等活动而逐渐增多。[注]张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侨务实践的政策法规成效》,《侨务工作研究》2012第3期。侨务的兴起使得毗邻港澳的广州地区吸引了大量华侨返乡,20世纪80年代初沙湾部分在港同胞成立了旅港同乡组,每年回村内祠堂组织敬老宴,这一慈善活动甚至登上了香港媒体,传为佳话,并受到了沙湾镇侨办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同乡组的人数逐渐增多,成立了沙湾旅港同乡会,自发筹款修建了沙湾镇养老中心。在此背景下,同乡会以北帝诞可以加强旅港同胞与大陆同胞间的联系为由,向政府提请重铸北帝像。由于是以侨务的名义提出申请,此事很快便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批准,留耕堂东侧的何氏祠堂——申锡堂被政府批给民间供奉北帝。1986年,祠堂修缮完毕,更名为玉虚宫,成为供奉北帝的固定场所,中断已久的北帝信仰正式恢复。
尽管同意了恢复北帝信仰的请求,但镇政府并没有公开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是让侨办出面与侨胞沟通此事。北帝信仰恢复后,沙湾几位何姓族人组建了玉虚宫管委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负责与侨胞沟通的侨办负责人也是何氏族人,从玉虚宫修建至今一直都在参与管理。由此,宗族同样包含在侨胞的实践中从而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对于地方社会而言,他们是何氏族人,继承了本地的文化传统;对于政府而言,他们是侨办的人员,负责侨务工作。在北帝信仰的恢复过程中,内含于中华民族语境之下的侨胞成为了关键的合法性来源,在侨务工作中带动了民间信仰与宗族的文化实践。
(二)宗族:新主体的生成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而言,宗族仍然是一个在合法性上存在缺失、晦暗不明的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一个事件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宗族的文化空间得以全面恢复和重建。
1993年初,沙湾何氏族人听闻位于广州白云山的何氏宋代古墓——“姑嫂坟”原址遭到了破坏,立即赶往白云山“姑嫂坟”处,发现当时的广州市园林管理局要在此修建云台花园。虽然祭祀活动在建国后早已被迫中止,但对于何氏后人来说,何氏古墓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它更象征着何氏先人与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何氏族人阻拦了对“姑嫂坟”的拆移工程,并将此事报请至沙湾镇政府,并申请对这一历史文物进行重修。
1993年12月底,广州市文管办、市园林局、沙湾镇委、镇政府、沙湾群众代表(主要是何氏族人)、同乡会等在沙湾镇政府会议室就重修“姑嫂坟”一事进行集体协商后,一致认为建于南宋时期的“姑嫂坟”是重要的文物单位,应进行重新修复,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对此进行了批复,要求就地保护“姑嫂坟”。[注]《关于保护宋代古墓“姑嫂坟”的批复》,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穗府办函[1993]172号,1993年7月17日。同年8月,“姑嫂坟”被评定为广州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沙湾镇政府组织了“保护古代文物姑嫂坟工作小组”,任命时任镇委副书记为小组组长(何氏族人),其他几位何氏族人为常务组成员,负责向市文物管理部门提供相关历史资料。1994年修建工程得以启动,同年,在镇政府、沙湾镇文化站、何氏族人等多方协同下,“姑嫂坟”的修复工作顺利完成。
在修建姑嫂坟的同时,何氏族人计划重修何氏族谱,以传承传统文化,并希望镇政府能够给予支持。镇政府批准了这一计划,于1994年指定玉虚宫东侧的何氏祠堂——时思堂为何氏族人的办公场所,并将其命名为番禺区沙湾镇何氏留耕堂联络处(简称何氏联络处),何氏宗族组织正式成立。同年,何氏联络处主导并发起了何氏第一次修订族谱活动,在何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下,《庐江沙湾何氏宗谱》于1996年定稿,这也是建国以后第一本完整的何氏宗族族谱,宗族得以出现于官方的公共话语表述之中。
在上述的历史中,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逐步褪去了“司法国家”的色彩而具有了新的特征,但政府尚未改变文化管理者的姿态,一方面是民间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力,允许新的参与主体介入,至始至终决定着整个过程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始终以谨慎、消极的方式参与其中,这一局面直到新世纪的到来,随着新的概念的出现而发生了扭转。
(三)非遗与市场:多元主体的整合与协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积极性开始提高。1999年,沙湾镇政府举办了“沙湾镇十三项工程剪彩庆典活动”,恢复了自解放以后便已中断的迎神赛会——北帝巡游。但与传统的北帝巡游不同,首先,巡游时间不是传统的“三月三”,目的也不是娱神,而是为了庆祝政府的庆典活动;其次,这次巡游活动在形式上由镇政府策划负责,费用也由政府出资;最后,巡游线路也发生了改变,所有巡游队伍的集合与解散都在镇政府大院内完成,巡游路线也以沙湾镇主干道中华大道为主。[注]指沙湾镇的沙湾东村、沙湾西村、沙湾南村和沙湾北村。这次巡游标志着沙湾镇政府对民间文化态度的根本性转变,政府希望成为主导性力量,主动参与和接管民间文化的实践。
2005年,根据国务院的指令,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展非遗保护工作,非遗普查工作开始落实。[注]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沙湾镇政府将这项工作下派给了当地的文化站负责,在第一批非遗的申报项目中,衍生于北帝巡游活动中的飘色名列其中,次年5月,沙湾飘色正式成为省级非遗,但却落选了国家级非遗。据曾经工作于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他们在上级的指导下以民间艺术的门类提交了飘色材料,但被告知申报方向不对,应归为民俗类,最终导致飘色错失了入选国家级非遗的机会。
申报上的失误揭示出地方政府主导文化工作的弊端,这也预示了文化机构需要重大调整。2007年,为响应国家简政放权的政策,沙湾镇政府将文化站与体育中心合并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简称文体中心),负责地方文化及体育事业的发展;2011年,番禺区进行了简政强镇改革,文体中心并入沙湾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挂牌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自1955年便已成立的沙湾文化站完成了历史使命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民间文化事务进入公共文化建设的新时期,从自发逐渐走向自觉,从行政化走向专业化和技术化。
宗族作为明确的参与主体走上前台,随着“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沙湾何氏姑嫂坟崇拜”等项目被列入非遗名单,宗族文化成为沙湾公共文化的一大标签。2009年,何氏联络处为了进一步传承何氏宗族文化,计划重编第二本族谱。与第一本族谱修订的过程迥然不同,这次修族谱活动由宗族组织和镇政府合力完成的,修订费用也是双方共同分担,民间资金是海内外族人自愿捐款,政府资金则通过文体中心以文化经费的形式拨与何氏联络处。2011年底,内容更为完善的《沙湾何氏宗族概况》正式出版。[注]族谱对第二次修族谱的缘由进行了说明:“对于挖掘、承传和利用民间传统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通过一个大家族的成长和发展,我们既可以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透过史实看到民主社会的必然来临;又能从中认识民间文化艺术能以一种特有的形式,让一个氏族成长得富于朝气;更能充分认识到创新及敢为人先已成为一个氏族潜在的发展动力。”宗族组织不再是过去的简单再现,不再被单纯定义为下位于政府、服务于国家的民间力量,而是与国家和社会紧密相关、传承和发扬文化的重要主体。
相较于早期政府对待民间文化时的谨慎或后来的大包大揽,这一阶段政府则希望借助权力分配和专业分工对文化进行重新整理。非遗成为政府“打包”地方文化,对其切割、分类、定级、开发的重要概念,以飘色协会、醒狮协会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民间文化协会陆续成立,成为可调度、借用的文化资源。
与此同时,市场因素同样受到关注。2008年,沙湾镇政府便成立了沙湾镇旅游开发工作办公室,挂靠于镇属房地产公司名下,负责开发当地文化旅游及管理物业。2011年底,旅游办开始转变为独立的镇属企业——沙湾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2012年元旦正式开放“沙湾古镇”第一期历史文化旅游景区。
在镇政府的支持下,旅游公司通过借鉴其他已经成熟的古镇治理模式,于2013年元旦对整个景区进行了围蔽,开始实施新的治理模式。由于沙湾的景区融于村、居民的生活区,围蔽景区相当于围蔽了生活区。围蔽工作开始后,旅游公司在景区入口处安排了工作人员,通过查验身份证的方式来区分沙湾人和非沙湾人,后者需要购票入内。最终,景区的模式遭到区内居民的强烈抗议,在实施了两个月之后宣告结束。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于对留耕堂空间的利用当中。在旅游公司看来,祠堂已经成为可开发的公共空间,在景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依循市场逻辑,何氏族人也不应过多干涉祠堂日常管理事务。2014年曾有影视剧组向旅游公司提出想在何氏大祠堂内取景,旅游公司考虑到这样利于宣传地方文化,于是允许剧组进入留耕堂进行取景。何氏族人发现剧组未经何氏族人的同意将留耕堂第五进[注]留耕堂内摆放何氏祖先牌位的地方。摆放祖先牌位的地方改成了灵堂,立刻进行了制止。随后,何氏联络处介入此事,最终以宗族文化顾问的身份参与到旅游公司的项目开发中。
在这一阶段,民间文化经由非遗实践从地方性语境中抽离,展现了民间文化向公共文化转化的过程,文化从保护、整理、规划的对象进一步迈向多主体开发。政府既作为保护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塑造的参与者,行政官僚体系让位于技术官僚体系,市场成为新的参与主体。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支配性权力关系过渡到生产性的权力关系,政府的管理思维逻辑不再或无需起主导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以多主体参与为根本的文化治理模式。
一种多主体参与的,可命名为“治理组装”的格局逐步生成,地方文化不再拘泥于“地方”,民间文化不再停留在“民间”,而是在公共的宏大语境中解放了文化叙事,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自身的权力的转型以及“双元主体”[注]高丙中:《公共文化的概念及服务体系建设的双元主体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结构的确立与继续发展。
三、讨论
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之下,文化遗产的“现代性”生成而非“本真性”溯源成为关注的重点,文化与政治不再是完全分离的两个领域,抑或一者对另一者实现完全的支配,相反,文化成为了政治的表征,政治同时也需要通过文化进行言说。[注]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在文化遗产领域则体现为“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勾连与循环:文化遗产作为政治的表征,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叙事与不同的参与主体,或被保留或被隐藏,或位于中心或被边缘化;同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不仅反映甚至推动了政治变革,更多的参与主体和方式的出现既是中国政治改革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也是文化领域自身对传统管理方式的突破。正是从“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相互推动与循环的角度出发,文化遗产已经超越了地方文化和遗产保护的范畴而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透过文化遗产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政治在理念、实践和具体方式上的转变与效果。
基于国家建设的视角,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历程和国家治理转型之间具有同构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治理主体先后涌现、治理方式不断发生变革的过程。在此之中,非国家主体通过对合法性概念的挪用使自身成功嵌入到曾被国家垄断的文化遗产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对空间加以丰富;同时,国家则主动改变自身的治理方式,凭借新的文化工程将主权意味下的管辖转化为“治理术”意味下的“引导的引导”[注]Brady, Michelle, “Ethnographies of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ies: From the Neoliberal Apparatus to Neoliberalism and Governmental Assemblages,” Foucault Studies 18 (2014): 11-33.(conduct of conduct),将基于行政和科层关系的管理发展为依靠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治理;而市场力量的介入进一步为社会层面非国家行动者的广泛参与提供了舞台,成为了国家实现治理的重要媒介。
上述过程很难被简单地理解为从“管理”向“治理”的线性变化,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并非一种权力模式对另一种权力模式的替代,而是在出现了更多治理主体和方式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治理组装”(governance assemblage)的形态,即不同管理和治理方式的共存,不同主体相互嵌套,国家本身亦走向了“治理化”[注]Lemke, Thomas, “An Indigestible Mea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State Theory,” Distink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8, no. 2 (2007): 43-64.
(governmentalisation):一种清晰可变的、由上至下的国家结构发展出一种模糊不清的、交互重叠的“国家效果”[注]Mitchell, T,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Steinmetz, G., ed. State/Culture: State-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1996, pp. 76-97.(state effect)。其结果是文化遗产成为一类权力空间,在不同群体、不同空间区域内存在权力关系上的区分、交叉和重叠。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并没有形成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而是在不同主体和差异化的治理策略之下形成了新的依存关系,在社会和市场的主体性得到释放的前提下,国家同样保持了对于文化遗产的控制能力,从而多方之间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是“生产性”的而非“抑制性”的。[注]Hilgers, Mathieu, “The Thre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61, no. 202 (2010): 351-364.反之,借用对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项目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微观案例中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转型,既跳出“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二元化论调 ,也要对诸如主权、权力、治理等概念形成新的理解,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权力观,依循多主体之间的策略实施的角度解释国家转型。[注]Lemke, Thomas, “‘The Birthof Bio-politics’: Michel Foucault's Lecture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on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30, no. 2 (2001): 190-207.
如今,多主体参与、多种方式并行的“治理组装”格局在沙湾社会形成。民间文化由单一、简化、主体清晰的样态转变为复合、复杂、主体交织的治理格局。其中的治理并不是由任意主体决定的,而是在反复博弈中不断被组装。法律、政府、侨胞、宗族、社群、市场等先后加入的主体共同参与并完成了治理格局的搭建,冲突与弥合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进而形成不分彼此的整体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