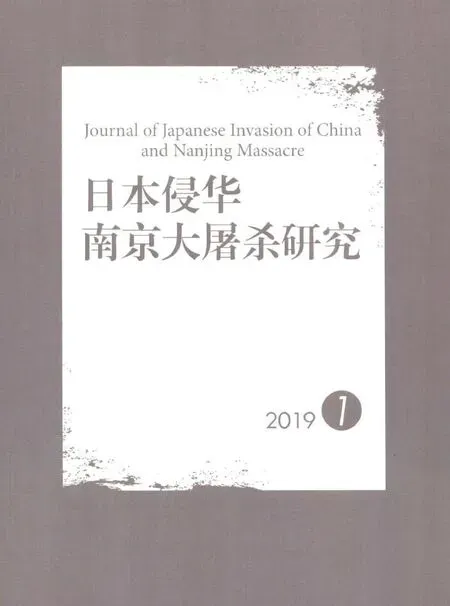汪伪的县政与困境
——以1941—1944年黄陂县为例
杜 强
近些年来,学界有关汪伪政权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从宏观层面考察了汪伪中央政府的外交、舆论宣传和政治经济状况,但对汪伪县级政权却鲜有关注。许多中外学者研究过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如中国学者王建朗等认为日军是通过扶植傀儡政权以“清乡”、经济统制、宣传和推行奴化教育从中国掠夺人力物力资源,变中国人为服从日本的顺民。①王建朗、曾景忠:《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319页。美国学者莱曼·范斯莱克认为日军依靠招募中国人任傀儡政权的警察和保安队员,以恢复占领区的秩序和行政管理。②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9页。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需要县级政权具体执行才能实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拟以1941—1944年伪黄陂县政府(以下简称伪县政府)机关刊物《黄陂月刊》和相关档案史料为依据,试图揭示1941—1944年伪黄陂县政府统治的实态,以期对抗战研究有所裨益。
一、思想控制:宣传“辩解”与奴化教育
武汉沦陷前后,在日军扶持下,湖北沦陷区建立了县级和省级伪政权。③黄陂等地的伪县政府先于伪湖北省政府成立。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黄陂县城,黄陂沦陷。随后,日军进驻县城、大指店、横店、横山集、研子岗、姚家集、邓家湾和聂口等要地,全面控制了黄陂县。不久,日军开始在黄陂筹建县级伪政权。同年11月至翌年5月,在经历了伪县维持会和伪县政筹备处后,伪黄陂县政府于1939年5月下旬正式成立,下设内政、财政、建设等科室,还掌握有保安队和警防团两支武装,全县也被划分为一至六个行政区,每区下设若干乡保,形成一套较完备的统治体系。
日伪在黄陂县的统治范围经历了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起初两年,伪县政府几乎统治了黄陂县全境和全部人口。自1941年始,新四军第五师等逐步收复了部分失地和解放了部分人口,日伪统治范围渐向县城收缩,至1944年底,其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县城及周边区域。
因湖北沦陷区各级伪政权是受日军直接控制或嘱托的傀儡政府,日军多选任曾留学日本、亲日思想浓厚的人担任伪职。吴振汉、谢氏和熊济夫先后受日军嘱托出任伪县长。吴、谢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人均是亲日分子,妄图控制民众思想,全力配合日本侵华。
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中,汪伪中央与地方不得不上下联手宣传日本侵华的“合理性”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1941—1944年间,伪县政府在伪中央授意下,不仅竭力宣传日本侵略的“合理”性和汪伪的“合法”性,还蛊惑宣传和虚构“大东亚战争”的前景“一片光明”。
为应对国共两党黄陂抗日县政府的抗日宣传,伪县政府编织了一套宣传理论,刻意回避世界局势的变化,宣传英美“殖民论”和日本“解放亚洲论”,竭力为日本侵略行径辩解。其刻意强调亚洲曾是英美殖民地的历史,借机宣传英美“殖民论”与日本“解放亚洲论”,还利用近代英美侵华史,宣扬英美罪恶论。如在《南京条约》签订100周年之际,伪县机关报发表社论,斥责英美是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被列强瓜分、使东亚失去本来面目的罪恶源头。①《痛定思痛的南京条约》,《黄陂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年,第1页。同时还宣称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必须发动“大东亚战争”铲除英美暴政,还原东亚的本来面目,②《由大东亚战争说到东亚共荣圈》,《黄陂月刊》第1卷第6期,1942年,第1页。甚至将日本的侵略美化为保卫东亚的“圣战”。③《兴亚纪 念与保卫大东亚纪念》,《黄陂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第1页。
为加大宣传力度,伪县政府还利用县内外有影响力的政要、汉奸文人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1941年3月,在纪念所谓《中日基约》签订一周年,《黄陂月刊》转载了汪伪要人林柏生攻击蒋介石政权的言论:重庆与美苏英等国组成ABCD阵线同盟,威胁、压迫日本与“反共建国”的中国。④林柏生:《中日缔约周年》,《黄陂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第14页。其目的就是替日本推卸侵略中国的责任。1942年,多名汉奸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寻找“合理性”。黄陂文人关堃堂认为,要“解放”“复兴”亚洲,必须与英美一战。⑤关堃堂:《解放东亚运动中之精神建设》,《黄陂月刊》第1卷第6期,1942年,第12页。署名厚德者声称,日本为帮东亚摆脱英美的桎梏,才偷袭珍珠港。⑥厚德:《纪念保卫东亚日与励行新国民运动》,《黄陂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第10页。汉奸文人周毓英认为,日本对英美开战是高举“解放”大东亚民族之旗。⑦周毓英:《论政治的战略》,《黄陂月刊》2卷6期,1942年,第11页。显然,他们均为日本发动战争寻找“合理性”。即使到1944年,替日本“辩解”的宣传还在继续,如在纪念“还都”四周年时,吕光明还赞扬日本是东亚10亿人民解放的先驱。⑧吕光明:《庆祝国府四周年纪念中对大亚洲主义的认识》,《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19页。事实上,汪伪政要与汉奸文人大肆宣传日本侵略的“合理与正义”,实质上是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大环境中,伪政权如果无法证明日本侵略的“合理性”,那么其与日本合作打击抗日力量、为日军征用物资亦难找到“合情理”的借口。
除竭力为日本侵略“辩解”外,伪县政府还协助伪中央塑造汪精卫政权的“合法性”及汪是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汪的叛国不但被绝大多数国人唾弃,即使一些与其亲近的人都为之羞耻。香港学者郑会欣的研究指出:一直视汪为导师和领袖的陈克文在汪精卫投敌后,指责汪是甘当汉奸、自毁光辉历史,必然身败名裂,走上不归路的民族罪人。⑨郑会欣:《从领袖、导师到民族罪人——<陈克文日记>对汪精卫形象的记录》,《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汪对陈有提携之恩,陈还是其妻侄,连陈对汪的投敌都感到不耻,可见汪叛国极不得人心。在举国一致唾骂声中的汪精卫,授意伪中央与地方政权塑造他是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以迷惑国人,并断章取义地解释孙中山的“大东亚主义”是塑造形象的关键,将孙中山实现东亚自强的“大东亚主义”,曲解为继承孙中山实现黄种亚洲人驱逐白种欧美人的遗志。
1941—1944年间,伪县政府不断阐释汪精卫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不二人选,每逢日汪间有大事发生,便趁机宣传汪精卫的“合法”形象。1941年初,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签订所谓《中日基约》不久,一名亲日分子劝导黄陂人要支持继承总理遗教,正努力践行国父“大东亚主义”理想的汪精卫。①儒:《新中国人民今后应有的觉悟和信念》,《黄陂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第6页。1942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逝世时,伪县政府极力传扬汪精卫大赞日本的言论,即日本各界对“大东亚共荣”的贡献,正向国父期望的“大东亚主义”迈进。②汪精卫:《因纪念国父逝世想到大东亚主义》,《黄陂月刊》第1卷第5期,1942年,第4页。1943年11月,在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会议”之际,伪县政府向民众宣称:汪此行是应了国父曾说过的“要完成大东亚主义,中国不能无日本,日本不能无中国”的要求,抱定与日本同生共死的信念与白种人清算百年的血债。③《国家集团主义与大东亚主义之实践》,《黄陂月刊》第4卷第6期,1943年,第13页。1944年3月12日,伪县政府要求黄陂民众要紧随国父唯一的继承者汪精卫“兴华保亚”的坦途前进。④《国父逝世十九周年的感言》,《黄陂月刊》第3卷第3期,1944年,第5页。很显然,上述亲日言行与塑汪宣传皆透露出宣传者的意图,即汪精卫与日本合作是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未尽事业,而且将汪的一切言行都附会于被曲解的“大东亚主义”,无非是突出汪伪政府的“正统”与“合法”。
为进一步凸显汪伪政权的“合法性”,伪县政府还积极配合伪中央开展丑化蒋介石与矮化重庆政府的宣传。1941年3月30日,伪县政府将林柏生攻击蒋介石以党员后辈居高位,目无元老、独裁、叛国父、违背总理遗教等言论在县内广泛传播。⑤林柏生:《中日缔约周年》,《黄陂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第14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大力援华,汪伪借机攻击重庆政府。1942年3月,署名则陈者撰文,攻击重庆政府是替英美残杀东亚人的刽子手,是东亚的叛徒。⑥则陈:《在国府还都二周年纪念中的几点感想》,《黄陂月刊》第1卷第5期,1942年,第7页。伪县政府还在县内大肆宣传汪精卫大骂坚持抗战的蒋介石是一个失掉灵魂拿着英美人武器打亚洲人的东亚“叛逆”等言论。⑦汪兆铭:《今后国民运动的重点》,《黄陂月刊》第3卷第3期,1943年,第6页。
伪县政府的“辩解”宣传不止为日汪合作唱高调,还深入普通民众进行奴化宣传,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控制民众为其服务。伪县政府善于利用节庆纪念活动、集会、放映电影等机会对民众实施迷惑宣传,刻意制造“繁荣”的假象,使民众相信日本必胜,“大东亚战争”前途“一片光明”。伪县政府每年3月下旬都动员全县纪念“还都”,如1944年3月22日,伪黄陂县各界举行大规模的“还都”纪念活动,有伪县政府官员、日军嘱托官、商人、学生、壮丁等万余人参加,内容包括保甲座谈会、民众大会、演唱戏剧、青少年雄辩会、放映电影,自誉为“隆重! 热烈! 愉快! 各界联合庆祝盛况空前”的盛会,⑧《还都四周年:(隆重! 热烈! 愉快)各界联合庆祝盛况空前》,《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7页。以粉饰太平。国庆节亦是其吹捧日本的良机。1943年国庆节,其一面以传单、标语、漫画宣传国共冲突、英美将毁灭、汪管区即将“全面和平”,一面派宣传队深入县城内茶楼、酒肆及附近乡村吹嘘友军的战绩。⑨《国庆三十二周年纪念日告民众书》,《黄陂月刊》第4卷第6期,1943年,第8页。伪县政府还利用电影宣传“大东亚战争”,其内容不是日军“节节胜利,所向披靡”⑩《举行巡回电影轮赴各区宣传》,《黄陂月刊》第1卷第5期,1942年,第22页。和友军获得“赫赫战果”,就是鼓吹“大和民族精神”。
伪中央和地方竭力为日本侵略张本、替汪精卫辩护,鼓吹日军必胜,首先是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其次是迫于日本的压力。四年间,伪县政府每有重要活动,都有日本人参与。1941年1月17日,日本军官10人参加黄陂县警防总团成立大会,并检阅各级警防团阵容。①《警防总团部正式成立》,《黄陂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第9页。徐旭阳:《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20页。1942年5月27日的集会则由伪县长和日本人大林指导官演讲;②《友军海军纪念节黄陂县热烈庆祝》,《黄陂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第22页。再次是应对策反。国共两党的策反宣传导致大量伪军反正。1939—1940年黄陂伪军包括高级将领在内数千人反正,甚至日本兵松原秀雄也从黄陂县城逃出,投奔新四军。③黄宇齐、林滔:《回顾新四军第五师对敌伪工作》,周焕中主编:《特殊的战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伪县政府试图通过洗脑式宣传,以控制民众思想,稳定军心。
然而,由于国内外舆论与客观环境致其宣传难收实效。当时国际国内一致反法西斯的局势使汪伪在与蒋政权的舆论交锋中处于下风。正如中国学者张生所指出的:“重庆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利用特殊的时代背景将政治斗争‘通俗化’——塑造汪伪诸人的‘娼妓’形象,直接毁伤其政治人格,剥夺其附于国民党的资格”。④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同时,抗日力量的壮大也使伪县政府的宣传只能囿于县城及周边有限的空间。以中共抗日根据地发展为例,1941年初,新四军第五师在黄陂县东北部已有较巩固的控制区。1944年底,黄陂县除县城及周边地区外,大部分属于新四军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1943年底,整个武汉已被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包围。更重要的是,沦陷区民众不为日伪的虚假宣传所诱,不仅广大民众支援抗战,连僧侣和帮会人员都积极抗敌御侮。⑤参见慈学民《武汉抗日僧众救护队》,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湖北抗战史料精编》(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79—481页;王一心、蔡松云《民间帮会的抗战》,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湖北抗战史料精编》(上册),第482—486页。
利用教育奴化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是汪伪企图从根本上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四年间,伪县政府创办各类学校实施奴化教育,以提拔重用为名,培养学生的亲日思想和为“大东亚战争”效力的意识。
伪县政府考察青年学生了解日本国情与“大东亚”战争意义的情况,是提拔青年学生的前提。1942年6月,伪县政府为从黄陂“兴亚”学校选拔人才进行考试,大多数试题与欧美侵略史、日本国情与“大东亚战争”相关。⑥《兴亚青年学校严格举行考试》,《黄陂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第22页。日伪同样重视对儿童奴化思想的灌输。县立第一完小,从1942年6月3日起,每天上午8时30分至9时20分加授日语课,以培养儿童所谓的“中日亲善”观念。⑦《完小每日加授日语课,养成儿童亲善观念》,《黄陂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第17页。由此可知,日伪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奴化学生思想,培养学生为侵略战争效力的意识。与课堂教育一样,学生的课余生活亦被打上“大东亚战争”的烙印。课下,中小学生锻炼身体、长知识,是为巩固“大东亚共荣”的基础;到民间做宣传工作,宣传节省消费,是为“友军”作战增添力量。⑧萧国雄:《决战年中小学生应尽的责任》,《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18页。女学生被派往医院向日本伤兵送慰问品,并唱歌、表演游戏,这也是为制造所谓“中日亲善”的气氛。⑨《女职完小师生,慰问友军伤兵》,《黄陂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第12页。由此可见,伪黄陂县管制下的教育全被“绑架”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日伪还要求社会青年要人格高尚、思想纯正、体魄健全,能担起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时代责任。⑩《中国青少年团中总章·纲领》,《黄陂月刊》第3卷第4期,1943年,第6页。然而,沦陷区民众早已识破奴化教育的阴谋,多把孩子送私塾或辗转入国统区就学,并以进敌伪设立的学校为耻,即使被强迫拉入就读,也千方百计退学。⑪《警防总团部正式成立》,《黄陂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第9页。徐旭阳:《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20页。伪县政府为解决师资短缺和生源不足难题,不得不高薪聘请教师,同时还免费为学生提供衣物、伙食、教材等,以招徕学生,还勒令各保派送生源,⑫徐旭阳:《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第501—502页。但效果不佳。
二、援助日军:军需供应与“清乡”
1941—1944年间,伪县长谢氏、熊济夫悉力助日军在黄陂县推行殖民统治。二人分别以实现“和平建国”、完成“圣战”、打造中国的“光明前途”为幌子,勒索民众,镇压抗日力量,助日军侵华。
供应日军所需是伪县政工作的中心。粮食是首要的征用物资,无偿且无度的索粮,使民众不堪重负。以1942年上半年为例,日军储备军粮需搜集小麦、大麦、大豆等42000担,六个区按人口及耕地面积平均分配,然而干旱、麦类黑麦穗病已导致每户减产1至4斗,夏粮共减产6500石,①《六月份农事纪要·农业概况》,《黄陂月刊》第2卷第2期,1942年,第28—29页。《保安队击溃共匪势力,截获大批军需用品,大队部分别给以奖励以资鼓励》,《黄陂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第20页。即使如此,同年秋收后,伪县政府亦征收精米达3500吨。②《黄陂供应需要,厉行征收精米》,《黄陂月刊》第2卷第6期,1942年,第20页。10月,复因日军缺粮,伪县政府派王汉剑等要员赴各区再次征粮,要求每区缴稻谷500吨。③《人民踊跃缴纳谷米,派遣要员催收》,《黄陂月刊》第2卷第6期,1942年,第15页。该年伪县政府的两次征粮数量巨大,民众不堪重负。当时全县约62万人,④《改区设署呈省核示》,《黄陂月刊》第4卷第1期,1943年,第18页。1942年人均毛粮(即大麦、小麦、大豆和稻谷)的负担量约为39斤,⑤按伪县政府的规定:2斤新稻谷可以代替1斤精米,征收3500吨精米即为稻谷7000吨。参见《黄陂供应需要,厉行征收精米》,《黄陂月刊》第2卷第6期,1942年,第20页。其中军粮约占半数,这对本来普遍过着“糠菜半年粮”日子的民众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掠夺。更重要的是,伪县政府无法控制县内全部地盘和所有人口,不可能向中共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口征粮,但征粮总量不变,因而缴粮任务完全由其实际控制的人口承担,因此沦陷区民众实际缴粮负担要比估计的还要沉重。
此外,伪县政府还向民众征收蓖麻、铜铁等军工原料。蓖麻是生产火炸药的原料,1943年伪县政府动员全县种植,员役、保警各学校师生也要种植,执行不力者以犯法论。熊济夫在1944年3月10日的农业增产会上再次强调:“协力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为国民应尽之义务,尤以播种蓖麻,供应军需,更属必要之图。”⑥《本县积极农业增产,农指所开增产会议》,《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16页。严督之下,1944年,伪县政府控制区蓖麻播种面积达3600亩。⑦《本县积极农业增产,农指所开增产会议》,《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16页。战争后期,由于弹药损耗量大、运输不畅,致驻黄陂及周边日军生产弹药所需的铜供应不足。1944年2月,伪县政府派陈邦友、丁文霖下乡强行征铜,羁押收铜不力的区长,直至多方做保并缴足铜后方才作罢。⑧《治乱用重典》,《黄陂月刊》第3卷第1期,1944年,第2—3页。不仅如此,日军的柴禾、猪肉、干草等物资同样要民众供给。由此可知,黄陂民众遭受日伪敲骨吸髓的无度索取,生活陷于困顿,与日伪的矛盾日益加深,所谓的“圣战”“和平建国”“光明前景”等谎言不攻自破。
除了充当日军的后勤供应者外,受日军驱使,协助其“清乡”也是汪伪政权的另一主要职能。由于国共军队的持久抗战使日伪苦不堪言,伪县政府试图通过武力“清乡”和“思想清乡”,倚靠保安队和警防团,协助日军肃清黄陂县境内的抗日武装,强化“反共建国”的政治力量,并从思想上控制乡民,以达到巩固后方、接济日军军需的目的,⑨黄觉:《还都四周年,献给清乡工作的同志》,《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4页。最终使“友邦日本无后顾之忧”。⑩《拥护国府参战确立治安与增加生产》,《黄陂月刊》第3卷第3期,1943年,第11页。
伪县政府大力鼓吹保安队、警防团与新四军等作战的“战果”和伪军的“实力”,按其说辞,武力“清乡”基本是有胜无败。如1942年5月12日,伪保安大队第一中队,截击援渝运输队,抓获王敬折等7人,缴获电话机、粗油线、细油线、电表、子弹、扣眼、细花线等大量物资;⑪同年9月,伪警防团不仅打败了破坏交通的新四军200余人,还协助黄卫大部打死打伤新四军100余人,且抓获新四军1人;①《警防团活动概况》,《黄陂月刊》第2卷第5期,1942年,第22页。《李石L樵关于请S派徐绍阶6、蒋荣中7分别为黄/陂、黄安县1县长的电/及湖北省0政府的电5》(19943年5月1),湖北(省档案馆1藏,)/010/0002。1943年2月25日,伪县保安队在兴集与新四军及国民党孝感游击支队作战,打死新四军24人,俘虏3人,缴获地雷3枚;②《县保安队清乡,收获赫赫战果》,《黄陂月刊》第3卷第4期,1943年,第24页。1944年2月21日,伪县保安队在县东北打死新四军数十人,活捉10余人,缴获连发手枪1枝,步枪弹20发。③《保安队扫荡敌匪,完成任务后安然返防》,《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13页。为了表彰伪保安队、警防团“清乡”的“赫赫战功”,驻黄陂日军司令官表示“深为嘉赏”,伪县政府“大摆筵席用示犒赏”。④《保安队协助剿匪有功,友军司令官特给奖状》,《黄陂月刊》第1卷第2期,1942年,第12—13页。然而在短短数年内,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扩大到30万平方公里,⑤《鄂豫皖赣皖边区扩展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九百万》(1945年1月9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成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主力,伪保安队、警防团连年“清乡”“战果赫赫”的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另外,伪县政府还辅之以“思想清乡”,企图在思想上剿灭民众的抗日意识。伪县政府曾一度重视“思想清乡”,认为“清乡”要先清心,清心是治本,只有支配乡民的思想才能“根绝匪共,使之不能复来”,对新四军武力压迫与攻心战术并举。1944年4月,伪黄陂县清乡局称:新四军不过是一时受人煽动诱惑才走上歧途,随时欢迎新四军投诚,⑥《黄陂县清乡局:告新四军官兵书》,《黄陂月刊》第4卷第4期,1944年,第7—8页。妄图瓦解新四军的抗战意志。伪县政府还张贴“肃正”思想确保治安、保卫“和平区”内根除“英美流毒”、树立“战时体制”、完遂“大东亚战争”等清乡标语,⑦《清乡标语》,《黄陂月刊》第3卷第3期,1944年,第8页。并派“清乡”宣传队下乡,让乡民明了“国府”参战的意义。由于民众的抵制,伪县政府对“思想清乡”的效果不抱多大期望,仅是“思想清乡”的执行者“预料定有一番收获”而已。⑧《清乡宣传队随军出发》,《黄陂月刊》第4卷第4期,1943年,第16页。
三、伪县政权的命运:难以摆脱困境
伪黄陂县政府是武汉外围各伪县政权的缩影。武汉沦陷后,日军在周边扶植建立了一些伪县级政权,以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然而,抗日军民持续的抗日斗争,不仅使汪伪看不到“光明前景”,而且使伪县政权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本文以黄陂县伪政府为考察中心,同时兼顾其周边的鄂东(黄安、麻城、礼山),鄂中(应山、应城、安陆、云梦、汉川)与豫南(信阳)诸县伪政权,探讨其难以摆脱的困境。
黄陂县国、共、伪三方县政权并立,县城沦陷后,国民党县政府即迁址坚持抗战。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也相当重视黄陂县长的遴选。1941年,因县长张凤梧不通舆情,政令不推,改由詹钧代理县长。⑨《黄陂政府关于黄陂县县长张凤梧、詹钧任免事宜的训令》(194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LS31/2/0000030/087/0001。1942年,复因詹钧在禁烟、清查户口、减租、平定物价等县政要务没有一项任务完成规定的10%,考核成绩不佳,⑩《1941年湖北省黄陂县县长詹钧的成绩考核表》,湖北省档案馆藏,LS67/1/0000174/025/0001。因此改陈士敦任县长,1943年又派军事和民众动员能力“较强”的徐绍阶任县长。⑪《警防团活动概况》,《黄陂月刊》第2卷第5期,1942年,第22页。《李石L樵关于请S派徐绍阶6、蒋荣中7分别为黄/陂、黄安县1县长的电/及湖北省0政府的电5》(19943年5月1),湖北(省档案馆1藏,)/010/0002。中共黄陂县政权最迟建立于1941年10月,⑫《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1/0057。到1942年4月,中共黄陂县政府已建立170人、88支枪的抗日武装。⑬《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1/0042。
武汉周边沦陷之县三个政权并立是普遍现象。通常是日军占领县城后扶植建立伪县政权,原国民党县政府被迫转移。1939年,武汉周边县城沦陷的国民党县政府的办公地点为:麻城县驻鬼头河,黄安县驻孟家洼,礼山县驻王家店,应山县驻山河新店,安陆县驻神安寨,汉川县驻江家集,云梦县驻古圣畈(随县境)。信阳县于1938年10月沦陷后,国民党县长李德纯迁黄龙寺办公,并与中共合作,创立信阳挺进队坚持抗日。①龚兴汉、郑冶、严诗学:《抗战时期信阳县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德福主编:《红色四望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黄陂孝感礼山各伪军反正之经过》,湖北省档案馆藏,LS1/1/1091/003/0011。
事实上,中共也在沦陷区建立了抗日县政权(县委或县政府)。1938年10月,信阳县沦陷后,中共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到1939年3月,中共已建有孝感、云梦、汉川、安陆、应城和应山六县民选的县政府。②《艰苦奋斗的三周年》(1941年6月2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39/006/0023—0024。黄安、礼山两县中共县政权最迟成立于1940年10月。③《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1/0057。可见,豫南、鄂东、鄂中县城沦陷的县,除麻城县是国、伪两个县政权外,其余均是国、共、伪三个政权并立,日伪未实现对任何一县的完全统治。
国共县政权的存在使伪县政府受到双重钳制:一是政治压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县政府是县内的合法政府,反之,伪县政府不具备合法性,还背负着汉奸的骂名,政治上处于劣势;二是中共县政权在实际控制区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在实际控制区内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争取各阶级各派别的支持。如1942年中秋节,中共汉川县政府财委会邀请20余位地方中上层名流开茶会吃月饼,并一致通过政权津贴条例。④《鄂豫边政权工作报告》(194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5/0007。再如,1942年,通过改选的汉川县新政府动员220名青年参加新四军,是原征兵计划的22倍。⑤《鄂豫边政权工作报告》(194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5/0005。国共两党县政权对于各县人力物力的争取,加强了抗日力量,制约了伪政权的资日活动。
武汉沦陷后,由于抗日武装的存在与发展,日伪只能以武汉为中心,控制长江、汉江、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及重要城镇。1942年,鄂豫边区驻有国民党军31.7万人,新四军1.8万人及有组织的抗日民众7万人,而日伪军合计不过10.6万人(其中日军8.6万人)。⑥《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1/0045。可见,即使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鄂豫边区的抗日军队对日伪军仍保持着约4:1的数量优势。几十万国共军队迫使日伪军将有限的兵力布防于重点城镇和重要交通线上,而相对偏远的地区被国共军队开辟为游击区或抗日根据地。1943年,中共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已扩展到武汉周边的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人口约1000万(其中基本区约473万)。⑦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第61页。当年中共鄂豫边抗日根据地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主力部队约2.7万人,⑧《鄂豫边五师根据地状况》(1943年),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3/0002—0004。可见日伪无法完全控制点线以外的地区。黄陂县伪官员曾直言,“清乡”的目的是使政府的政治权力“由点与线,扩充到面,以至全面和平的完整实现”。⑨黄觉:《还都四周年,献给清乡的同志》,《黄陂月刊》第3卷第2期,1944年,第4页。此语从侧面透露了日伪的实际控制区域不出“点”与“线”。
伪军、伪官员的反正一直困扰着汪伪。1939年3月至5月,黄陂多次发生伪军反正事件。3月18日,国民党游击司令蒋章骥派员以公谊私情劝导伪军,并晓以民族大义,伪旅长刘梅溪当即反正;3月19日,伪军官胡翼武在沙浦附近枪杀伪师长曾大钧率部反正;4月26日,伪团长郭瑞麟经人触动,率300余人反正;5月28日,伪军李汉鹏部因作战失利而投诚,同日伪旅长率800人反正;⑩《黄陂孝感礼山各伪军反正之经过》,湖北省档案馆藏,LS1/1/1091/003/0006。6月,云梦县伪旅长黄曙晴率部投诚。⑪龚兴汉、郑冶、严诗学:《抗战时期信阳县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德福主编:《红色四望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黄陂孝感礼山各伪军反正之经过》,湖北省档案馆藏,LS1/1/1091/003/0011。1940年,伪军反正之势愈演愈烈。4、5月间,黄陂、孝感、云梦、汉川县等地伪官兵26000余人反正。①《徐育华上报豫鄂一带伪军皇协军26000余人于寒日同时通电反正汉口恐慌异常的电文》(1940年5月2日),湖北省档案馆藏,LS1/4/0570/002/0001。同年,伪黄陂县保安司令田令昌反正②《鄂豫伪军纷纷反正》,《伤兵之友》(江西)第55期,1940年,第8页。,汉口日军亦感到恐慌。
反正或与新四军合作的伪军、伪官员也为数不少。1940年8月,伪应汉孝总队副等千余人,以及府河水上保安队龙登云投靠新四军。一些伪官员、伪军不能立刻反正者也与新四军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伪云梦保安团长杨启发虽对反正持观望态度,但已联络新四军,并请新四军专员常驻其团部。应山保安大队长孙家善参与掩护和保护新四军等人员进出县城,更有铁路保安团长与中共信应军政部长结拜,密助新四军打通信阳至汉口间铁路全线联络站。③《鄂豫边根据地概况》(1942年4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藏,GM3/1/020/001/0028。有些伪军官公开告诫部下:“‘如果和新四军打仗,我不叫开枪就不许打’”。④《十五旅襄南敌伪工作的经过及经验》(1942年4月13日),周焕中主编:《特殊的战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甚至还有伪军希望在战场上被新四军俘虏,因为被俘后不仅不杀头,还能领到优待费。⑤《十五旅襄南敌伪工作的经过及经验》(1942年4月13日),周焕中主编:《特殊的战线》,第240页。上述伪军、保安队的反正及与抗日武装的合作,足以说明伪县政权的统治何等虚弱。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武汉周边的伪政权震动极大。一名伪县长准备“清乡”,其部下居然以“‘这种时局,搞中国人有何意思? 哪个愿意伸出脑壳来挨钉耙敲!’”为由抗命,“清乡”也不了了之。还有一名伪区长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狂饮大醉,状似疯狂,在街上遍寻绅士磕头,连说:‘我没有做坏事,请你们保全我的性命吧’”。⑥刘慈恺:《加紧开展对敌伪、敌区的工作》(1942年3月),周焕中主编:《特殊的战线》,第255页。甚至连一些日军都并非如宣传的那般自信。驻汉口的日军第十一军因三攻长沙不克和多次“扫荡”失败,该军总前卫官竟抱怨说:“‘蒋介石还有三百万保持有战斗力的大军’”,以往“打倒蒋介石,肃清共产党,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自信完全没有了。⑦林涛:《今日的敌军》(1942年10月),周焕中主编:《特殊的战线》,第263页。日军尚且如此,伪县政权更不相信日本会赢得这场战争,所谓开创“光明前景”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托词而已,与日军的合作也难免日趋貌合神离。
四、结语
抗战时期,伪黄陂县政府的舆论宣传、教育、军需征收和“清乡”,使该县成为被日军“绑架”于战争的后勤供应基地。伪县政府试图以宣传“辩解”和奴化教育解决控制民众思想的难题,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下,中国军民一致抗日,压缩了日伪的生存空间,其宣传仅囿于县城及周边地区,奴化教育的效果也不佳。在黄陂民众被“大东亚战争”榨干了血汗,生活陷于困顿的事实面前,伪县政府自诩“治安稳定”“民众安居”,前景一片“光明”的谎言不攻自破。与伪县黄陂政府一样,鄂东、鄂中和豫南的伪县政权,饱受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挤压,也无法摆脱统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