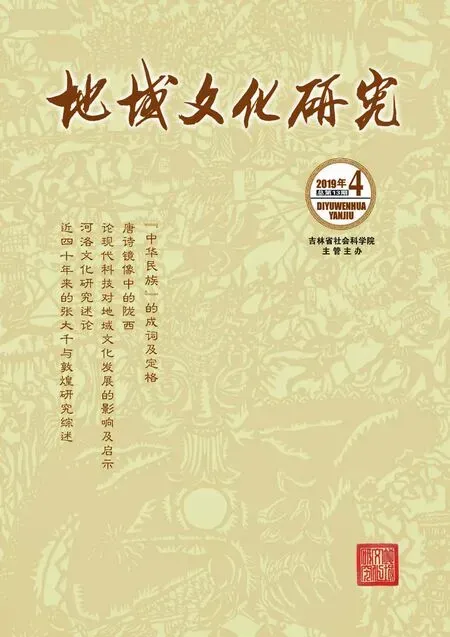彝与夷: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的称谓
李鹏翔
民国时期,四川凉山及云南小凉山彝族尚处在奴隶制发展阶段,①潘先林:《“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其文还论述了其余地区的彝族之社会发展形态,云南滇池周围及滇南彝族处于地主经济发展阶段,滇东北和黔西北即滇川黔边区(主要包括云南省的昭通地区和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彝族处在有浓厚领主制残余的地主经济发展阶段。马长寿:《彝族古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该书提到,四川大小凉山及凉山以西的彝族地区,在凉山边沿改土归流以及交通便利的地方自元明以来便转化为封建社会了,但是大凉山的彝族及由凉山迁到西昌地区的若干彝族直到解放以前奴隶所有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奴隶社会的历史前后保持了两千年以上。杨风江:《彝族氏族部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提到四川凉山彝族的中心区,在1949年之前,还处于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岭光电:《倮情述论》,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川康地区,在外间人心目中,未归化者统曰大小凉山。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该书认为凉山彝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还处于奴隶制社会,而在此时,凉山的摩梭人还保留有原始这回的一些习俗。朱映占、段红云:《民国凉山地区的保头制研究》,《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该文认为:清末及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在一国之内形成独立于国家政权管辖之外,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该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凉山地区实行利用奴隶进行生产的奴隶制度。相对于其周边地区,凉山地区的交通闭塞,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汉文史书中对凉山地区民族的称谓多含贬义。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夷”开始出现,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汉文文献中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民族的称呼。②陇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页。到元代至元十二年(1275),金沙江北岸凉山及安宁河流域的泸沽、姜州、普济州、黎溪州等地建立政权时,以“罗罗新”(即“罗罗”)作为政权机构的名称,即“罗罗斯宣慰使司”,“罗罗”也取代“夷”成为各地彝族的通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称谓,其中也不乏沿用“夷”。在元、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彝族也称为“爨蛮”①《彝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清末宣统年间,官方依旧称凉山地区的部落为“夷”“倮夷”等,记载散见于《清实录》中。②《清实录·宣统政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其中,第2卷第15页有“倮夷介于川滇之间,素不安静,近复勾结匪徒,日肆劫掠”;第14卷第19页有“凉山倮夷介在川滇之交,横亘千有余里,久为政教所不及,与滇之永善、巧家等厅州县接壤,时出劫掠”,“倮夷过江肆掠”;第23卷第7页“凉山倮夷窟穴于川滇两省之中,四出为患……汉夷杂处,夷强汉弱”;第32卷第3页“续办凉山倮夷,扫通夷巢,就交脚地方添设县治”等处均有明显表露“夷”或“倮夷”的称呼。到了民国时期,川滇交界的凉山地区被称为“蛮巢”,外国人称为“独立卢鹿”③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页。“卢鹿”见于《新唐书·南蛮(下)》:乌蛮与南诏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在这里“卢鹿”很可能就是“罗罗”或者“倮倮”的不同写法,因为在该书第34页,作者又写道:“外国人称为独立罗罗”。该书第47页中作者将“独立罗罗”解释为他们既不受中国政治势力所支配,同时并很自由地掳杀汉民,无异一个独立国家。(应即“罗罗”之译音),当地汉人有一首土谚曰:“天见‘蛮子’,日月不明!地见‘蛮子’,草木不生!人见‘蛮子’,九死一生!草见‘蛮子’,叶落又萎根!”④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页。本书第48页中写道,称之为“蛮子”的原因有:一他们喜烧杀抢夺,二他们据高山深林以及衣食住行都与汉族不同,三政府无力量管辖,只能听之任之。除了蛮子以外,文雅些地叫法是“夷教”或“黑夷”。而夷人则是较近汉化的卢鹿,⑤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页。由此可见随汉化程度的不同,称谓也有所变化。对于此种说法,江应樑的记录也提供了佐证:凉山夷人俗呼罗罗,又称蛮子,在边疆民族研究上又给他们一个专名:“独立罗罗”,因其不受政府统治俨然独立状态。⑥江应樑:《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珠海:珠海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7-8页。
由以上称呼可以看出,无论是“夷”“爨蛮”,还是“蛮巢”“蛮子”皆为带有贬义的他称,这其中不仅包含了彼时汉人的自我优越感,还体现了他们对该地区民风的畏惧。在彝族的发展历史中,相比于他称的不断变化,自称的变化则比较小。
从对凉山地区民族文字的称谓上来看,彝文的称呼也经历了多种变化。今天的彝文在先秦时期的六国分封时代被称为“夷文”,魏晋时期被称为“爨文”,南诏时期被称为“韪书”,而元代至民国时期则被称为“倮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跟随族名称为“彝文”。⑦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序言》(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在杨成志的研究中,今天的彝文在民国时的称谓有:“蛮文”“夷文”“散民文”“罗罗文”和“子君文”,散民、罗罗、子君均为罗罗的同族异称。⑧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0页。有不同的异称是因为不同方言的混合和递变而形成。汉语中的“蛮”有时泛称操藏缅语群的人,不过更典型的是用来称呼操苗瑶语的人,再往南则用“彝”来称呼不同的藏缅语群,主要是指彝语支,近期这一名称被用来专门指代彝语支中最大的一组(即倮倮语支)以前称为“纳苏”或“倮倮”。⑨[澳]D·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页。当然,这种说法出现在《彝语支源流》一书中,因为此书英文版初版时间为1979年,所以用“彝”字似乎合情合理,“倮倮”这一称呼可能并非为汉人的贬义称呼,而为自称。对于“罗罗”是否为自称,持有不同看法的是刘小幸,她将“罗罗颇”和“诺苏”这两种称呼做了地域上的分类,她认为“罗罗颇”这一称呼在楚雄地区较为普遍,而凉山地区更多的是用“诺苏”这一自称。①刘小幸:《彝族医疗保健——一个观察巫术与科学的窗口》,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第8页。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解释“㑩㑩”时讲到这个称谓在凉山中不常应用,边区汉人称㑩㑩为蛮子,㑩㑩自称夷家,所以用”夷家”来作为书名,②林耀华:《凉山夷家·序》,上海:上海书店,1947年,第1页。此种说法认为在凉山地区“㑩㑩”这一称呼似乎是带有侮辱性意思的。③巴莫阿依、黄建明编:《外国学者彝学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第6 页。书中还提到,对于凉山的诺苏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类人群,即Nuosu(诺苏)和Hxiemgat(汉人)或者加上Opzzup(俄著),即安宁河以西的西番人和藏人。
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对于各地区各支系的彝族的他称通常是带有贬义的,比如在原先的称呼上加“犭”,除此之外还有“黑罗罗”“白罗罗”“花腰罗罗”“阿者罗罗”“鲁屋罗罗”“妙罗罗”“干罗罗”“海罗罗”等不同的他称。④《彝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页。在地理上,彝族散居很广,所以名称也较为复杂,虽通称罗罗,但却有大罗罗、小罗罗、黑罗罗、白罗罗等的分别。彝族自称也往往会加罗罗称号,如阿者罗罗、鲁屋罗罗、撒弥罗罗之类。⑤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6页。原文中为“弥撒罗罗”,可能为误写,应为“撒弥罗罗”。在《云南通志》中有“滇固西南夷也”的判断,更称彝族为爨蛮、白猡猡、黑猡猡、撒弥猡猡、妙猡猡、阿者猡猡、干猡猡、海猓猡、阿蝎猓猡等,其称呼加“犭”,可断定为他称无疑。⑥《云南通志》卷24《土司种人附》。由此可见,“猡猡”“猓猓”或者“罗罗”均为他人对凉山地区民族的称呼。抗日战争时,因为带“犭”的字含有蔑视意义而被政府废除不用,所以将其改为“倮㑩”或者“倮倮”,“倮夷”和“倮族”也成为通行的他称。在川滇两省,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夷人”和“蛮子”,在这两种称呼中,“蛮子”令当地人民非常反感,但他们对“夷”的接受度则比较高,尤其是懂汉话的人听到被称为“蛮子”时,甚至会以武力相对,这与林耀华的观点相似。当时的政府为去除之前名称中的“蔑视”意味,对他们的官方称呼是“边民”,而当时凉山地区对本民族的自称是Nosu(纳苏),较为高贵的黑夷则自称为No(纳)。⑦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上海:求真社,1947年,第92-93页。
从图腾信仰的角度来说,彝族内有崇尚龙、虎图腾的部族。彝族以龙虎为图腾的信仰由来已久,除了有关的文字记载以外,还体现在对本民族的称谓之中。在彝族关于氏族部落的歌谣中有:“日暮高山寒,天寒地贫瘠,布与尼之地,位于洛尼山。”⑧杨风江译注:《彝族氏族部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这里的洛尼山是古代彝族地名,意为“青虎山”,彝族有黑即青的认知习惯,所以洛尼山也被称为“黑虎山”,今彝族尚以虎自诩。⑨杨风江译注:《彝族氏族部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洛之意为虎,尼之意为青色。“罗罗”为虎的最早记载是在《山海经》中:“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有注曰:吴任臣云:“《骈雅》曰:‘青虎谓之罗罗,近云南蛮人呼虎亦为罗罗’见《天中记》”。⑩《山海经·海外北经》。刘尧汉记录的凉山彝州德昌县城南欣东拉打村今尚在世的两位彝老甲巴比古、甲巴里尼说:“我们阿姆金古家(氏族),从古以来都认为自己是老虎的后代,谚语说:‘阿达拉莫乌都茨基’,意为都是虎的骨头(血统),又说‘骨是虎造,血是虎生’”。⑪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页。对虎的图腾崇拜还有虎是万物本源的说法,虎尸变万物:虎毛变草木,虎肉变大地,虎骨变岩石,虎血变江河,虎的五脏六腑变日月星辰。①刘尧汉整理:《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2-173页。
从龙虎的发音上来看,“罗罗”的自称与龙虎的发音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彝语中,龙音为lu,虎音为luT,所以有学者认为彝族自称“罗罗”即龙虎译音的说法。②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自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另外,还有学者的研究证明,彝语中“罗”的意思为“虎”,“罗罗”即“虎人”“虎氏族人”或“老虎的后代”的意思。③杨继林、申甫廉:《中国彝族虎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页。彝族自称“罗罗”,意为“虎族”,与彝族崇拜黑虎图腾有关。④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页。四川省大渡河之南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其东北邻乐山地区峨边、马边两彝族自治县和西南邻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永兴乡、元谋县凉山乡这些地区的凉山彝族则自称“诺苏”,其意为黑族,但他们也曾自称“罗罗”,意为虎族,因彝族尚黑,又有黑虎族的称法。目前云南尚有100 多万自称“罗罗”的彝族,而四川省的彝族曾全自称“罗罗”,其意与前同,为虎族。⑤曲木约质:《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见刘尧汉《巴且、曲木两书合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由此可见虎无疑是彝族的原始图腾。
从色彩偏好的角度来说,彝族尚黑,这也体现在他们的称谓之中。在凉山北部方言中,将自己称为“尼”或“诺苏”,“尼”即“黑”意。⑥朱文旭:《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彝族古谚语中有“天白为父,地黑为母”,自炎黄时代开始,就有母系氏族文化特征的部族以黑自称。⑦朱文旭:《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39页。
从时间上来说,1949年以前,彝族大约有30多种不同的自称或者他称,四川全部、贵州大部以及云南昭通地区、曲靖市、玉溪地区、思茅地区、丽江地区、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及宁蒗县小凉山等大部分或部分彝族都采用“诺苏泼”或“诺苏”这个自称。⑧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页。书中指出,“诺苏泼”在彝语中有特定含义,“诺”有“主体”的意思,也有“黑”的意思,“苏”意为“族”,“泼”意为“男人”,由此可知“诺苏泼”为“主体的族群”或者“尚黑之族”之意。大、小凉山当地的官员也是用“夷患”“夷巢”“夷人”“倮倮”“黑夷”“白夷”等来称呼当地土著居民。⑨任映沧:《大小凉山倮族通考》,成都:西南夷务丛书社铅印本,1947年。在当时彝族内有一位名望很高的土司后裔:岭光电先生,他有一本专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方面的著作,叫作《倮情述论》。⑩岭光电:《倮情述论》,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从书名中可以看出“倮”为自称,且书中也均用“倮”来称呼1949年之前在凉山地区生活的人民。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书中也大量出现了用“夷”来称呼凉山彝族的情况。⑪岭光电:《倮情述论》,1943年。从目录页中便可窥出端倪,目录中有“倮民”“倮族”“夷胞”“汉夷通婚”“夷民”“边民”等字样,书中内容仍是如此称呼凉山地区的人民。这可能与其个人经历有关,作为彝族人岭光电具有深厚的彝族情感,但他亦倾慕汉族文化,还曾兴办学校,聘任汉族教师。⑫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页。可见其受到过一定的教育,相较凉山地区其他文化较低的人民而言,其思想更为开明,也更能接受“夷”的称呼。但这并不能证明“夷”为自称的说法,岭光电在书中用“夷”来称呼凉山地区的人民,只是借用他称而已。另有一种说法是,在1957年以前,彝族大约有18种自称,如“那苏濮”“罗罗濮”“俚濮”“米切濮”等等。①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第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1页。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很可能没有“彝族”这一称谓,但是有人提出“彝”字作为族称最早见于清道光《沾益州志》,此说不妥。②马锦卫:《彝文起源及其发展考论》,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页。《沾益州志》只有乾隆三十四年刻本和光绪十一年抄本,道光年间的《沾益州志》不知从何而来。“彝族”这一族称很可能是人为构建的,而在这之前则普遍用“倮倮”,或者外延更宽的“夷”。“彝”的字义是一种祭祀用的酒器,20世纪50年代末期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开始用“彝”代替“夷”。③[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综上所述,在彝族的发展历史中,他称和自称皆在不断变化,但是“夷”的称呼却总是伴随,许多民国时期到凉山地区去考察过的民族学家,在当时撰写民族调查报告时,也用“夷”这一说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进行民族识别后,鉴于之前的他称中多含有贬义,且采用之前官方的“边民”更是不恰当,因此官方为了可以更准确的称呼该地区的民族,才用“彝”字替代“夷”字。而在之后有关该地区民族的著作之中开始渐渐采用“彝”字,这也导致后期在对民国时期有关彝族的民族志再版过程中,出现了“彝”“夷”互用的问题。在“彝”与“夷”的使用上面,必须要考虑到作者所处的大环境。马长寿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于1940年完成初稿,2006年正式出版,书名为“罗彝”④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整理前言》,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7页。,而本书书稿完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书名写作“罗夷”。由以上分析可知,民国时期并没有使用今天的“彝”来称呼大、小凉山地区的人民。这个问题在李绍明的《马长寿对藏彝民族走廊研究》一文中有明确的记录,马长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撰成此书时,书名是《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在此之前马长寿还有《凉山罗夷族谱》一文的问世,⑤李绍明:《马长寿对藏彝民族走廊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2008年,第78页。王建民在评价此书时也使用了《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这一书名,⑥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但是在2006年整理出版时,“彝”这一称呼已经代替具有民族歧视意味的“夷”,书名的改动,不仅结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凉山地区民族有着“罗罗”的自称,也深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名称用词不同的意蕴。
(特别感谢导师周伟洲先生对本文的指导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