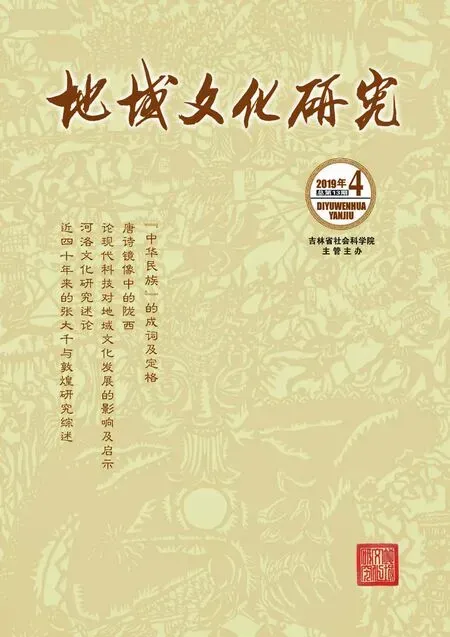梵净山区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特征及启示
张 永 曹 勇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在一个文化系统内,“文化核心是指那些和生计活动与经济安排有密切关联的特征集合。”①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法国哲学家科尔纽指出,“环境对人和人对环境的不断作用与反作用,决定了人的活动的本质。”②[法]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5页。张岱年先生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化”“对象化”“人化自然”的启发,认为“凡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文化。”③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在农耕时代尤为明显,生态环境决定了一切生计活动与经济安排,千百万的重复形成了人的行为、思维与意识的特征。反过来,又反映在人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活动。
梵净山是铜仁的文化命脉,其良好的生态孕育文化,吸引了文化,净化、融合了文化。良好的文化促进生态的平衡。铜仁境内呈现东西部不同文化区块现象,是梵净山自然“边墙”形成的。而梵净山作为地球同纬度仅存的原始绿洲,又得益于文化区块相互制衡。梵净山位于铜仁、松桃、思州、石阡诸府厅交界之地,雍正十二年(1734)于梵净山山麓东南面置四十八溪主簿于堡脚(今松桃普觉),管理边界争议、制止任何单方面越界与其他破坏行为。区划历史演化下的文化意识,使这座独特、神奇的山全身心地投进铜仁市的怀抱。这是梵净山之幸,也是铜仁之福。梵净山作为当下地球同纬度保护最完好的原始生态,本身就是奇迹。这奇迹背后隐藏着生态与文化和谐的必然关系。2018年7月,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声名远播,游客如潮。梵净山的兴衰关乎铜仁的兴衰。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是以依赖自然为前提条件,在扩大梵净山旅游市场、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必须坚守发展底线、协调发展与生态的关系。
一、梵净山的地理分水岭与其文化区块的“边墙”
梵净山被认为中国黄河以南最古老的台地,巍然耸立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地带,为贵州第一山、武陵山脉的主峰,自北向南纵贯铜仁地区东北部,成为沅江、乌江水系的分水岭。因山体绵延庞大、山势险峻高耸,以船、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东西山麓人们老死难以往来,成了阻隔两坡面人们交流交往的天然屏障,也因此将梵净山区生态环境受人的活动的破坏性降到了最低。即使如今公路蜿蜒盘旋山势相对平缓的苗王坡,从东面山麓到西面山麓车行也需一小时左右。这道屏障将铜仁市十个区县分隔为东5县(区)与西5县,唯有河流衔通,以山为界、以江为带,构成了两个文化区块。东5县区主要通过沅水支流锦江与湖南衔接,形成荆楚文化的边区;而西5县主要通过乌江与蜀地相连,形成巴蜀文化的际区。梵净山也因此从地理上的分水岭演变成文化区块的自然“边墙”。这是贵州文化因大山阻隔与河流衔接构成文化区块的典型特征。尽管边缘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扩张力相对较弱,但是它具有吸纳、兼容的强大功能,这两种不同的区块文化虽然相隔一山,但由于都具有边缘性特征,所以能相互包容兼收。
有学者从人类遗址发现、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世居的少数民族以及人类从山上到山下迁徙规律的角度分析认为,梵净山、乌江区域“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人类文明、中华人文始祖和古帝文明、中华古老民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①黎斌:《〈山海经〉中的“梵净山”与“乌江”》,《贵州民族报》2014年9月12日,第A03理论版。若此结论成立,理应呈现以梵净山为核心向四周扩展的同类文化区域,也就不存在以梵净山为界分的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区块现象。
另外,从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来看,梵净山脉铁矿丰富,是雷电重灾区,云雾较重,空气湿度大,岩穴潮湿阴冷,不太适合古人类的居住。梵净山山脉为长江支流之源头、缺乏大型的江河湖泊冲积或自然形成大片平坦肥沃土地来孕育文明。即使诞生史前人类生命,也难以产生文明。
此外,与从沅江、乌江下游逆流而上的迁徙规律的史志记载以及沿着江河延伸与辐射至梵净山山脉两种文化现象也不符。清诗人查慎行《铜仁庚申秋日有感和刘丙孙原韵》云“风物移黔境,关城接楚邦。”②(清)徐宏主修:《松桃厅志·风俗》,龙云清校注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人多好巫而信鬼”“颇有楚风”③(清)徐宏主修:《松桃厅志·风俗》,龙云清校注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梵净山区西坡面,“风俗同黔中。在荒缴(郊)之外,蛮夷杂居,言语各异。”④《嘉庆·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点校本内部发行),1991年,第8页。因此,梵净山区作为区域文明发源地的观点很难成立。
二、梵净山东西坡面的气候环境与生存意识
据钟有萍等气象学者利用梵净山周围6个基本气象站1971—2010年相关数据以及梵净山自然风景区自动气象站2005—2010年相关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发现,“梵净山的东、西坡气候差异与海拔高度、坡向有关,高大的山脉造成它的东西两侧丘陵地的气温和降水的差别较大,形成不同的气候类型,东南坡多雨,冬温低而夏季炎热,西北坡少雨,冬温高而夏季炎热”①钟有萍等:《梵净山对局地气候的影响分析》,《贵州气象》2011年第6期。。山地海拔气温变化,导致气温、土壤等条件的明显垂直差异,使梵净山区形成了30多种森林类型,5个比较典型、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②张锦林主编:《.贵州古树名木》,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4年,第9页。海拔在700 米至900 米的坝干、快场、黄家坝、冷家坝等区域分布大量的楠竹,处于东侧的松桃、江口的年降水量高达1,300mm以上,但在西侧的沿河、思南、印江的降水量只有1,100mm 左右③钟有萍等:《梵净山对局地气候的影响分析》,《贵州气象》2011年第6期。,东坡区要比西坡区多130—210mm;东坡面的太平河一带年平均降雨量可达1,700mm④钟有萍等:《梵净山对局地气候的影响分析》,《贵州气象》2011年第6期。以上。梵净山脉对东北方入侵贵州的冷空气的阻挡作用,可使梵净山东西两侧温差达4℃以上,西侧降温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滞后时间达8天以上。“这种差别使得西北坡在农事活动上,要比东南坡早10天左右。”⑤钟有萍等:《梵净山对局地气候的影响分析》,《贵州气象》2011年第6期。由于东南面为迎风坡、西北面为背风坡,东南坡多雨、西北坡少雨,形成东南面生态植被要好于西北坡面,且修复能力强。
由于梵净山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带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高耸、庞大的山体,使得南北空对流骤然降温带来充沛的雨量,空气上升过程中温差持续变化,在山体描上了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多雨、潮湿与云雾缭绕,有利于植物生长和爬行动物繁殖,而厚厚苔藓的铺盖山体、包裹灌木的树干,有益于水土的涵养。梵净山的自然防御体系与自我修复体系,成了同纬度的绿宝石现象的重要因素。
梵净山的东西坡面生态植被的差异主要受气候影响,继而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生产意识。东南坡面的人们因生态环境良好,在生产中团结协作抗击自然灾害的机会少,而单打独斗能完成生产活动的机会多,独立意识强于协作意识。西北坡面石漠化程度较重,少雨容易干旱,暴雨又容易导致山体滑坡、塌方。生活在此处的居民一方面在生活生产中形成忧患意识、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等意识要强于东南坡面的居民。西北坡面冬季温度高于东南坡面4℃以上,在夏天高温一致的前提下,西北部坡面冬夏温差小于东南坡面4℃以上,西北坡面在农事上早于东南坡10天左右,农耕生产更具有超前谋划意识。
三、梵净山的生态环境与佛教传播
梵净山的奇诡幽净、云雾缭绕,是佛教得以传入的环境基础。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梵净山大概始于东汉年间。随着佛教的兴盛,寺庙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唐贞观二十年(646)、宋建炎三年(1129)分别建天庆寺、护国禅寺(原天池寺),后来又相继建立承恩寺、镇国寺、坝梅寺,这就是后获敕封的“五大皇庵”。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梵净山区的庙宇总数近百余座,僧尼道首人数近千,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胜境。
佛教传入后,随着大规模修建庙宇活动的增加,梵净山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尤其开矿、积薪烧炭等行为破坏尤甚。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为节省资金开销,往往就地取材,于梵净山的山麓修建庙宇。从修建庙宇用材来看,首选大而直的杉木,而梵净山杉木、马尾松主要分布在海拔300 米—500 米区间,砍伐树木从山麓运往山顶,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钱财,也使梵净山区植被破坏严重。梵净山麓人烟稀少,寺庙僧人难以维持生计,出现了圈占地盘,订立界碑,大兴庙产等行为。到乾隆时期,庙地已达四万亩,年收佃租大豆数万担。清乾隆七年(1742)楚人私开梵净山北坡金矿,侵害天庆寺庙产。道光三年(1823)坝梅寺僧普禅与地方奸商与不法分子勾结,私卖梵净山树木,掘窑烧炭。游客、香客对环境也造成污染与破坏。据清代徐訚《梵净山记》,“溯自有朋迄今三百年来朝谒者,趾错踵接,前呼后应,靡有止息。”①《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点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51页。佛教的兴盛也吸引了大量佃农入山居住,使梵净山古生带原始植被逐渐缩小。庙宇建设、僧侣生计与佛教活动等客观上破坏梵净山生态环境,但佛教教义又强化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四、古代梵净山生态保护意识及举措
据《铜仁史志》记载,道光十二年(1832),贵州巡抚麟庆、贵州布政使司按察使李文耕,撰文勒碑禁止破坏梵净山生态的行为。两碑文阐述的观点基本一致,“有外来炭商勾串本地刁劣绅民及坝梅寺僧私卖山树,掘窑烧炭,只图牟利,不顾损伤风脉”。②喻帮林:《梵净山碑文述略》,《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6期。出于“思铜数郡保障,其四至附近山场树木,自应永远培护,不容擅自伤毁。”③喻帮林:《梵净山碑文述略》,《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6期。所以有胆敢破坏、损害生态环境者,“进行查勘封禁”“从重究办”“倘差役乡保得规包庇及籍端滋扰,一并严惩。”④喻帮林:《梵净山碑文述略》,《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6期。梵净山区积薪烧炭破坏生态恶行,在道光三年(1823),知府敬文就撰文勒碑禁止,但道光三年到十二年,这十年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却屡禁不止。这与铜仁府、思南府发生旱涝灾害以及官府苛捐杂税的过重盘剥有关,梵净山区百姓穷苦,寺庙香火寂寥,致使寺庙、绅民卖林烧炭。
道光三年(1823),铜仁知府敬文撰写《梵净山禁树碑记》,文章才情文理并茂,阐述了保护梵净山区生态的缘由。其文要点有五:一是阐述佛教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梵净山成为仙佛胜境,乃因崇山茂林、山奇水净、雾幻烟影、晴雨佛光,如此独特的清缈梵境,营造物质与意识完美统一的佛缘境界。梵净山佛光胜景召唤、吸引修佛之人,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栖落高山之巅峰或藏于山麓,寒浸雾染、餐风饮露、息气养神,得缘修佛。二是阐述了山与草木的关系。“草木者,山川之精华。”“自兹以往,峨峨而岩岩者,其山也;郁郁而葱葱者,其树也。”⑤《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点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草木调节气候、吸炭释氧、涵养水土与优化土壤等,若失去草木荫蔽,必将导致水土流失、河流干涸、气候干燥、山体坍塌,有机生命或逃或亡,生态断链。三是阐述是梵净山区与水源的关系。水乃生命之源,有水才有生命及文明。铜仁大小二江汇聚城南,“斯二水发源于梵净山之分水岭下。”梵净山是铜仁的“水之源,山之祖”。“山川者,一郡之气脉”。草木植被遭到破坏,不仅失去梵净山涵养水分的源头作用,江河干涸,铜仁将失去气脉而不存。第四表达了自己对梵净山自然风光的向往之情。“余至郡,值岁暮,冰雪,未及一识山灵。今春于役松桃,曾于车中望见,写诗以记,亟思公暇登临,所谓千里风烟一览而尽者,俾得骋壮护而舒远眸。”①《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点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五是阐述自己与老百姓守护梵净山的共同责任。“且因以省吾民焉,亦守土事也。”“适邦人以无知民某某,近于斯山积薪炭,具状来白。”②《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点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自古不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祖山、水源与草木的关系、生态与社会关系、生态与佛教文化关系等方面来阐述保护梵净山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知府敬文的远见卓识可鉴、可敬与可赞。
据田野调查,梵净山区广泛流行自然宗教,神化物有土地公、古树、巨兽、巨石、井、鸟雀等,人们通过祭拜这种仪式来强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契约,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意识,遵循适度获取自然资源的自觉与认知,从而符合自然规律性。如砍伐古木老树、捕获大鱼大蛇、毁灭性的掠夺自然资源等行为必遭惩罚的警诫广为流传,客观起着约束、纠正、规范人们失范行为。
五、启示与建议
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民族民俗文化在此汇聚交融,梵净山以其刚健而又柔润的情怀吸纳、包容、润泽。文化以其独特方式沉淀了梵净山区生态保护共识。我们继承这种文化心理,积极推进生态文明与五大发展理念,增强区域文化自觉、自信,积极开拓两个空间、培育开拓性意识,创新文化旅游方式、突出文化区块特征的开发,推进绿色减贫、加强梵净山生态环境的保护,深度融合乡村战略与文化旅游发展,推进生态、文化与社会治理的高度融合。
(一)始终把生态环境放在首位,推进绿色减贫,结合东西山麓文化旅游资源的差异性适度开发,推进文化旅游创新
禁止山体开发,以梵净山环山麓村寨为重点。西面坡由于石漠化程度较深、雨水相对少、生态植被脆弱且修复能力弱化等因素,加强环境生态监测与保护工作。修复西部五县生态,促进绿色减贫,加大退耕还林与异地搬迁的力度,协调乡村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的关系。进一步限制东坡面开发的同时,加强人居环境治理,尤其加强河流的源头监管,治理两岸生活污水排放、垃圾投放与处理,限制酒店、餐馆、寺庙污水无处理排放,修建以防洪与景观为一体的太平河河堤,保护梵净山区湿地。
梵净山东西山麓文化旅游景点要体现差异性。东面以荆楚文化、苗族民俗为主,西面以巴蜀文化、土家族民俗文化为主,在佛教文化基本成型的前提下,主要提升品位与品牌效应。大力开发山麓村落、结合民族民俗、红色资源、历史传统进行,推进乡村振兴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重点建设历史文化著称的乌罗镇、红色资源丰富的木黄镇、以手工艺加工文化旅游产品出名的德旺乡,以观光休闲现代化农业条件好的闵孝镇,改善乡村公共设施服务,积极推进文化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成立与规划梵净山区乡村战略的创新区。
推进文化旅游创新,从盲从市场到引领市场发展。理顺创新型人才的引进与培育机制,统筹内外两个市场,挖掘文化特质,立足优势资源,做好前沿性高端规划,提升文化形式与时代内涵的融合度,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尤其注重无法复制的、独特的、新颖的、具有精神内涵的审美产品。加强文化旅游推介文本创新,以文化形式与内涵高度统一为追求目标,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优势,提高互动度、发挥自媒体效应,注重小投入、大产出的效益。发挥生态环境的优势,结合奇险峻峭、多元民俗、厚重的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以心灵冲击与视觉震撼的方式,诠释并展现民族民俗、历史、红色等精神内涵,抗拒推介的单一性、平面性与模式化。从理念、制度与市场层面引导与规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摒弃经济发展焦虑,突出质量、效益、协调、绿色与共享,始终遵循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积极引导资本推动文化发展。加强文化旅游市场的管理与整治,对于低俗、庸俗的形式进行取缔、教育与惩治,推进文化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积极构建两个空间,培育开拓进取的文化意识
铜仁交织着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融夜郎文化,交汇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呈现多元性。就文化生境而言,荆楚文化的生境为丘陵,而巴蜀文化的生境是山地,铜仁处在这种文化两种生境过渡区,相对倾向于山地。从文化与生境关系来论,尽管这种两种文化生境与山有关,具有生态意识,而巴蜀文化或许更加强烈。从性格、行为而言,荆楚文化于丘陵可纵目远眺而易俯瞰,关注远方而不虚空。山地文化侧重于务实重行、吃苦耐劳与团结协作,但生活在山区往往缺乏极目远眺的自然条件,即使偶有纵目远望的开阔空间,视下层峦叠嶂的山峦,也显闭塞、郁闷与狭隘
铜仁山峦起伏,从区县主城区而言,铜仁市十县区除玉屏、松桃、德江相对平坦开阔外,其余四周大山围堵或盘踞陡峭狭窄的江边。城镇化形成高楼大厦的水泥森林,使得城市视野更加狭窄。一是从物理空间进行改造。山峰聚合,大厦林立,需要登高望远,开阔心胸。这种意识行自古存在,城市建设以古塔、楼阁作为地标建筑,既为城市防御、瞭望敌情而设,也为市民登高望远开拓心胸之用。梵净山区不少区县的城区有古塔、楼阁,随着现代化高耸的建筑增多,起不到当初设立的功能。因此,选择主城区理想的山体,精心建设集健身休闲、观光养性、文化道德建设于一体山地公园,山巅修建极目远眺的仿古建筑物,从空间的开拓来培育人们的文化意识与行为意识。
(三)增强文化自信与加强文化区块的融合
推进文化治理实践,构筑精神高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聚集内生动力。“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打破了一切凝固的生活方式。文化要想富有生气,就必须从批判和断裂中获取自我转化的力量。”①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继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坚持文化的主体性,以批判与创新的方式,获取自我转化力量。文化自信在于结合时代进行创新,文化旅游的开发,实为塑造民族价值、展现民族精神的文化生产。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
有学者认为,人类一切冲突源于文化差异。消除文化的“边墙”,加快文化的融合,是我们文化学者的使命与责任。既要整合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又要突出铜仁地理、自然与历史文化特征。铜仁一切文化现象与梵净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梵净山脉孕育锦江、松江,也为乌江注入千溪万水。山之都、水之源。文化与山水相连,山为江之源,水为文化之命脉。
文化融合的过程是长期的,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但只要一代代文化学者具有文化融合的自觉意识、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这个过程也就不会太长。
(四)推进生态、文化与社会的融合
生态文明是基于反思工业文明的先进文明,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相存与相荣,是建设性的后现代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世界进入文明转型期。文明转型意味着兴衰起落,淘汰落后文明,兴起先进文明,促使抢占先机的地区从弱变强。积极发挥区域文化的治理功用,抓住文明转型的契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铜仁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生态安全保护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建设推进低碳县(区)示范建设点、水源保护区试点、重要生态功能区,逐步恢复石漠化地区生态功能,森林覆盖率63.49%。铜仁生态林保护与建设取得重大成效,成为抢抓机遇的独特优势,必将带来经济社会良性发展。近年来铜仁文化治理实践与创新不断推进,“梵天净土·桃源铜仁”,指出了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的统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武陵人视角描述的世外桃源,正是人们追求向往文化、生态、社会高度融合的乌托邦。历史沉淀的集体意识在现实中凸显,赋予“武陵”更宽泛的功能、责任与意义。而“武陵之都·仁义之城”彰显区域中心与道德建设,“厚德铸铜·仁义致远”涵盖历史文化与道德建设。这表达了文化、自然与社会的融合指向。铜仁区域文化展现的人文情怀、精神价值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使得文化结构趋于平衡。以全域游为契机,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开发与保护民族文化,加强社会综合治理,促进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