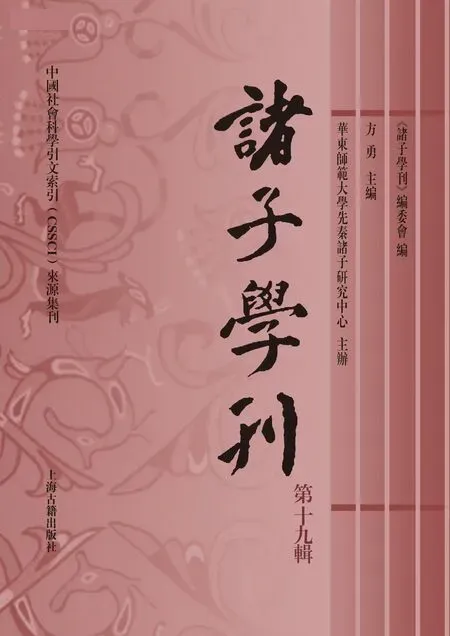“道 生 法”
——《黄帝四經》法思想的理路邏輯
向 達
内容提要 《黄帝四經》是黄老學的奠基之作。其思想主旨是“案(按)法而治”。在闡述此思想主旨時,《黄帝四經》運用了比較特出的理路邏輯,彰顯了黄老學獨具魅力的特徵。這種特色表現在它以道爲理論基礎,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邏輯基礎上,借助“一”“二”“多”“名”“分”“無爲而治”等範疇,演繹了“道法”的創生、執法、司法、保障及監督等一套較爲完整的法度體系。雖然《黄帝四經》的法治主旨比較明確,但畢竟爲時代所限,相關的理論闡釋並不系統,但其在“道法”基礎上演繹凝練的“隆禮重法”思想對後世治道精神和治道模式産生了奠基性影響,故有必要對其道法思想的理路邏輯進行梳理。
關鍵詞 道生法 《黄帝四經》 無爲而治 隆禮重法
《黄帝四經》是戰國中後期黄老學的經典之作。對《黄帝四經》的學術主旨可總結爲以下三派: 第一,以陳鼓應先生爲代表的“主道派”,認爲《黄帝四經》屬於道家的著作,主要從“道”的哲學角度解讀《黄帝四經》;第二,以唐蘭先生爲代表的“主法派”,他們認爲《黄帝四經》屬於法家著作,從法的角度解讀《黄帝四經》;第三,以裘錫圭先生爲代表的“道法派”,主張不能簡單地把《黄帝四經》歸屬於道家或法家,而是視爲道家和法家智慧的綜合。這派影響最大,在日本的代表爲金谷治和池田知久,我亦遵從此説。
《黄帝四經》洋洋灑灑一萬餘言,歸其宗即一個“法”字,這是符合黄老應時精神的。難能可貴的是,在衆多黄老著作中,唯有《黄帝四經》將“法”作爲宗旨來思考論證,從而創立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道法”思想體系。整本書以“道法”爲中心建構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度體系,提煉出“隆禮重法”的治理精神,對中國治理精神産生了奠基性影響。就禮與法而言,《黄帝四經》傾向於“法主禮輔”。雖然《黄帝四經》的法治主旨比較明確,但畢竟爲時代所限,相關的理論闡釋並不系統,學界對其法思想也缺乏系統而細緻的研究,所以有必要對其道法思想的理路邏輯進行梳理。本文旨在通覽研磨全著的基礎上,梳理其法思想建構的理路邏輯。
一、 道 生 法
司馬遷言,黄老之學皆源於老子之意,在各自的歷史背景、階級、學術立場發揮其道意。那麽作爲黄老之學最早最完整的經典之作——《黄帝四經》的道意發揮在於“道法”。“道法”概念的提出,顯然是黄老學用老子意修正原始法家,避其法出無根、嚴苛少恩的弊端。當然在這種修正中,《黄帝四經》也吸收了儒、墨、名、陰陽等家思想,形成一個豐滿的具有立體感的法治理論系統,這也是黄老之學“道術將爲天下合”的時代背景和理論特徵之體現。
《黄帝四經》原老子之意,提出“道生法”的命題,但其重心在法不在道,“道”只是將法帶入道的世界的鑰匙,整部書基本是論證法是怎樣發揮道意的。《經法·道法》開篇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1)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頁。首先從謀篇佈局看,作者在點出“道生法”的立場後,接下來並没有對道進行贅述,而是接續“法”字展開論述,通篇觀之,我們可串意爲: 法爲道所生,法是明是非曲直的繩墨,所以統治者制定法後所有的人都不能違犯,也不能隨意廢棄之。統治者更是要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帶頭遵守法律,如此則“一天下”就不難了。以此觀之,此段話核心是言法的,也是整部書的主旨所在,《黄帝四經》援道言法之用意已昭然若揭。
道爲何物?《黄帝四經》爲何要援道言法?在《黄帝四經》的作者看來,道是天地萬物之源泉,萬物流化的規律,法生於道,因而也藴含了道的神聖性和必然性。《黄帝四經》雖只對道進行兩次正面定義,但道的影子充盈於整部書之中。陳鼓應先生説:“‘道’指宇宙實體、萬物本原和普遍規律,爲老子首創的哲學專用名詞,並成爲中國哲學的最高範疇。”(2)同上,第2~3頁。老子之前,古籍中有“道”字出現,但不具有深刻的哲學寓意,老子創立道家學派,將“道”發展成一個神秘莫測、包攬萬象的哲學範疇,並成爲中國哲學最高的範疇。這是東周之際,華夏民族思維理性化的歷史結晶。
《黄帝四經》以道言法的用意大概可概括爲以下幾點: 首先,以道言法可加深法的神聖性,從而提高法的權威性和執行力;其次,法的客觀性、正義性、規律性、必然性源於道,並且只有源於道的法才是“良法”,才值得人們遵守。所以作者雖然提出“道生法”的命題,但後面又强調“執道者生法”,用意在於只有道的理念深入人們尤其統治者的内心,才能確保所生之法爲良法;如果失去了“道”的原則,統治者所定之法難免偏頗,民衆也無所措手足了。
道生之法即道法,它不是道與法的簡單疊加,二者具有内在的邏輯因果關係: 道是法的因,法是道的果,是道的具化,同時是道的表現。這裏的法是法度的意思,是治理社會國家的規範體系。《黄帝四經》中“道”“法”同文共有四處: 其一,《十大經·觀》及《十大經·姓争》:“其明者以爲法而微道是行。”其二,《稱》:“馳欲傷法,無隨傷道。”其三,《道原》:“抱道執度(法)。”第一句話説明了法與道是現象與本質的關係,緊密聯繫。第二句認爲人若放縱自我,將違犯法律,若盲目迷亂會違背道,可見二者是一體的。第三句强調在執法過程中要遵循道的原則。這四處的道法同文,再一次强調了道與法的緊密關係。
道法同文在其他文獻中也有,這些思想與《黄帝四經》有一定的關聯。如《管子·法法》曰:“憲律制度必法道。……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3)管子《管子》,齊魯書社2006年版,第136頁。這裏不僅道法同文,而且連言,顯然沿襲了《黄帝四經·經法·道法》的用語。《鶡冠子·兵政》言:“賢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此句話,從因果遞進推理看,仿佛賢最高,依次遞減爲聖、道、法、神,這種理解其實是錯誤的。其本意是由賢者産生統治者,統治者明達通道,依道制法執法,以法度治理天下。這句話之所以易讓人産生歧義,主要是因爲身爲楚國人的鶡冠子,像莊子那樣放達狂野,文風迷離。
《荀子·致士》也有道法連用之例:“無道法則人不至。……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4)荀況《荀子》,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349頁。荀子認爲道法能招徠人們,但只有明道的君子才能正確地理解道而制定良法,因此君子是制定和執行道法的基礎。這句話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荀子作爲稷下學宫三爲祭酒的儒家集大成者,居然提倡道法,説明稷下學宫學術融合是相當成功的;第二,荀子提倡道法,説明黄老道家乃至《黄帝四經》對其影響是很大的,二者皆爲戰國中後期“道術將爲天下合”的典範。荀子道法觀是對《黄帝四經》道法的發展。
道法體現了《黄帝四經》的本質特徵,是其建構法度的理論基礎。當然道法的制定和執行,需要執道者(君子、統治者)在充分悟道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期間還有一座“名”的橋梁,此邏輯路徑可概括爲: 道—名—法。
二、 握一以知多: 守道成法的功效
“道生法”,道爲法之母,二者的邏輯推衍體現了一與多的特徵,是道生法的具象。關於此,有幾個問題: 第一,一爲何物?第二,多爲何物?第三,何以守道?最後,守道何以成法?本部分即以此四個問題爲中心,進一步解析《黄帝四經》道法的理論邏輯。
(一) 一與多的問題
“一”字在《道德經》中合共出現5次,區區五千餘言,字字珠璣,老子竟捨得5個字的篇幅,説明在他心目中“一”字何其重要。爲何重要呢?因爲“一”是“道”的化身,也是道從無到有化生萬物的突破口,這看起來比較抽象、神秘,常被王夫之在《老子衍》中大加諷刺,但從邏輯上看,體現了老子邏輯之精妙、寓意之深刻,難免讓唯物的王夫子有諷意。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5)王孝魚《老子衍疏證》,中華書局2014版,第148頁。老子在此構建了一幅道生萬物的生動畫面。這段話包含了以下幾個意思: 第一,此處的“一”,是道之子,是道從無到有的過渡,是化生萬物、從抽象到具化的窗口;第二,陰陽是創生萬物的動力,萬物既生,仍懷抱陰陽,二者的辯證互動衍生萬物,即“和”;第三,雖然説萬物繁多,但其原在道、在一,因此要認識和改造世界尤其以法度治理天下,首先要把握道,以達“握一以知多”之效。王夫之認爲陰陽是道生萬物的動力和原理,是道的内在屬性,所以道生萬物也是陰陽生萬物。
老子通過精心的邏輯建構,提出“一”的範疇,而且不惜在短短五千餘言的著作中五次對“一”展開論述,從而建構了道創生萬物的邏輯體系。如果没有具體而又可把握的“一”,混沌之道只能停留於虚無。老子創生“道”,目的是想“合天下”,爲宇宙人生尋找終極的解決之途。所以才有接下來的“一”“二”“三”的創生。作爲宗老子的《黄帝四經》當然不會放棄老子這一根本宗旨,而且它更傾向實用,所以在《黄帝四經》中,“一”的出現次數不亞於“道”,目的就是“握一以知多”,爲其法度體系的建構作邏輯鋪墊。下面看看《黄帝四經》是怎樣用“一”作邏輯鋪墊的。
“一”在《黄帝四經》中出現的情況如下: 《經法·論》2次,《十大經·成法》19次,《十大經·順道》1次,《十大經·名刑(形)》1次,《道原》6次,合計29次,遠遠高於《老子》的5次。這個數字與黄老之學的實用傾向是相契的。下面看看這些“一”在《黄帝四經》中的具體涵義。
首先看《經法·論》中的“一”多問題。此篇論述天道和人道,天道即“八政”“七法”,人道即“六柄”“三名”(6)八政: 春、夏、秋、冬、外、内、動、静。七法: 明以正、適、信、極而反、必、順正、有常。六柄: 一曰觀,二曰論,三曰動,四曰槫(轉),五曰變,六曰化。三名: 一曰正名立而偃(安),二曰倚名法而亂,三曰强主滅而無名。,統治者應推天道以明人事。此篇對名實關係也作了一定論述,概念較多,哲理性較强,這也是其用“一”較多的原因之一。
《經法·論》曰:“天執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7)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26頁。此句話的意思是: 上天依靠道的力量,生成日、月、星辰,建構陰陽法則,然後建構和運行八政、七法。這裏的“一”,很顯然是道的意思。爲何不直接用“道”而以“一”代之呢?原因是,相比於道,“一”更顯明具體,是道的具化,同時“一”與後面的“三”“二”形成呼應,是道運化的邏輯軌迹。道運化的總體邏輯是由一到多,所以後面的“三”“二”“八”“七”便順理成章了。緊接着《經法·論》曰:“岐(蚑,多足動物。——筆者注)行喙息,扇飛蠕動,無□□□□□□□□□□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8)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26頁。《新語·道基》和《淮南子·原道》皆引用此句,證明《黄帝四經》在戰國、秦漢之際是很有影響的。此句話是對第一句話的申衍,是對“道”或“一”的具體論證描述,天下之所以這樣和諧,就是因爲萬物遵循了普遍之一(道)。《經法·論》中所見“一”,僅此兩處,此兩處的“一”,是《黄帝四經》“推天道以明人事”邏輯過渡的典型,也是由握道之“一”以知人類社會法度之多的典型。
其次看《十大經·成法》中的“一”多問題。《十大經》是《黄帝四經》的第二部分,此部分共計15篇,其中大部分是黄帝與其大臣的對話,可以看出此部分的主旨是緊續《經法》對道法的論證後對其具體執行的問題。《十大經·成法》“一”字出現19次,其中作道解者計13次,出現之多當屬《黄帝四經》諸篇之冠。一篇400餘字的小文,同一個字出現這麽多次,足見此字的特殊意義。篇首黄帝便問其大臣力黑(力牧)説,自己以一人之力怎樣對付奸猾之徒。力黑説:“循名復一,民無亂紀。”由此可知“名”與“一”皆爲道通向法的中介,不過“一”比“名”的層次更高,二者是一與多的關係,要使道幻化爲具體之道,首先必須給事物定名,定名的依據是“一”,所以曰“循名復一”,名定之後,又成了法度的依據。此段點出了“成法”即“循名復一”,復一守道。
黄帝進一步問道: 請問天下真的有道嗎?力黑肯定地回答: 有的。黄帝又問:“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長乎?”意思是“一難道只能以‘循名復一’一言而解釋,没有更多的涵義嗎”?力黑於是對“一”展開了一番解釋:“一者,道其本也……握一以知多……抱凡守一,與天地同極,乃可以知天地之禍福。”(9)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291頁。一是道的具化,它無所不在,無時不有,所以要守一,握一以知多,那麽天下的法度就不會偏頗了。《十大經·成法》用如此多的“一”,所要表達的無非是要勸人守道,爲民立極,遵循道來治理天下。以“一”言“法”,此篇尤其突出,表現了非凡的推衍智慧。
《十大經·順道》裏,“一”僅出現一次,因爲此篇主要目的是强調雌節問題,這裏“一”幻化爲雌節問題,成爲“一”中之多的一極,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法度之一。爲此作者從正、反、合三個維度論證了雌節的重要性。但雌節之根即在一。力黑説:“中請(静)不(流),執一毋求。”(10)同上,第330頁。意思是堅守道意,心静如水,毋馳於外。雌節的卑下柔弱,需以心静毋躁爲基礎,而堅守道方能毋躁,所以最終又歸屬“執一”。
《十大經·名刑(形)》主要解析名形、無爲,因此“一”在此篇幻化爲名形和無爲。文章開頭即强調:“欲知得失請(情),必審名察刑(形)。”(11)同上,第336頁。這裏顯然把名形相合作爲治理效驗的標準,在此,名是法的抽象表達。作者認爲只要名形分定、名副其實,那麽萬物將自化,社會自安定,統治者可收“無爲而天下治”之效。無爲之境的基礎是什麽呢?那就是“一”。“能一乎?能止乎?”只要做到一,就能用心專一、虚壹而静(12)《莊子·庚桑楚》言:“老子曰: 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止乎?”《管子·心術下》也言:“能專乎?能一乎?……能止乎?”此兩處與《十大經·名形》的“能一乎?能止乎”雷同,顯然是二者引《黄帝四經》之意的結果,再一次證明了《黄帝四經》在戰國中後期學界的重要地位。。
從題名和實際内容看,《道原》是論述道體與道用之本質的。道要從其原始點出發流化萬物,就得尋找中介和過渡,這個中介和過渡就是“一”,“一”就像“道”穿越到自己幽深隧道的大門,出了這個大門,道就幻化爲萬物了,包括有形的物質和無形的精神及法度。如此則過渡到道用了。道用在人類社會的最大表現就是法度。它的工作機制是: 推天道以明人事,握一以知多,審分定名,如此則萬物自定、萬民不争,可收無爲而治之效。因此《黄帝四經》的法度與純法家的法度不同,它是通過道來發揮作用的,把一切都拉到道的軌道上來,有一套特定的運行邏輯和機制,比較抽象,而且主要借助於人對道的了悟。
因爲《道原》主要是原道,因此“一”字出現的也比較多,共計6次,僅次於《十大經·成法》的19次,在整部《黄帝四經》中居第二。《道原》主要論證道體道用,落腳點放在“一”上,“一”在有無的關口,既是道體又是道用,是整部《黄帝四經》乃至整個道家學派僅次於“道”的最關鍵範疇,也是理解道家思想的一把智慧之鑰。《道原》開篇即言:“恒無之初,迵同大(太)虚。虚同爲一,恒一而止。”(13)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399頁。這裏的“恒無之初”“太虚”“一”,對道體進行了多方位的展現。第二自然段的開頭,作者對道作了總結:“一者其號也,虚其舍也,無爲其素也,和其用也。”(14)同上,第402頁。“一”是道的稱呼,虚爲道的居舍,無爲爲道之本質,和諧天下爲其用。這裏的“和”在人類社會中的應用便是道法,因此可以説道法的特性即在和。《道原》認爲只有聖人能洞悟道,“抱道執度,天下可一”(15)同上,第409頁。。統治者了悟道、抱道執度(法度)便可和天下。
綜上所述,“一”既是道的稱號,又是道從道體到道用的過渡和關卡,是理解道的一把智慧之鑰,也是聖王治理天下的妙法。
(二) 守道成法問題
守道成法是“握一知多”的結果,是“一”應用於人類社會治理的具體表現,二者存在着遞進的邏輯關係。《黄帝四經》對守道成法有一定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篇中: 《經法·名理》《十大經·正亂》《十大經·行守》《道原》。分述之如下。
《經法·名理》是《經法》的末篇,與首篇《道法》相呼應,邏輯意涵上也頗多應合。《名理》首先强調了道的神妙、循名究理的重要性,然後正話反説,用反面例子强調守道成法的重要性。但是整篇只提一次“守道”,講的是逆例,即君主如果守道不徹底,就會招致禍亂,反襯守道之重要。《經法·名理》言:“重逆(16)這裏的“重逆”是指内憂外患,《周書·謚法》稱這種狀態爲“荒”。□□,守道是行,國危有央(殃)。”(17)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92頁。國内積重難返之際又發兵攻打外國,即使再守道,都有亡國的危險。因此不論何時都應該“處於度之内”,堅持守道成法,才能和諧天下。
《十大經·正亂》是《黄帝四經》討論“王術”尤其是戰争的文章,黄老道認爲“治國以正、用兵以奇”,但反對不義之戰,反對陰謀,主張“寢兵”“銷兵”,這一點與老子之術似相契合。但是比老子走得更遠的是,《黄帝四經》不廢仁義,提倡隆禮重法,這一點與老莊之南方道家截然不同,當然也體現了戰國中後期稷下黄老道“合天下”的旨趣。本篇主要是黄帝與其大臣力牧及太山之稽(18)在此要説明一點,即陳鼓應先生認爲太山之稽就是黄帝,此説應該是不確切的,理由是《淮南子·覽冥訓》言:“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高誘注:“力牧、太山稽,黄帝師。”高誘説太山之稽是黄帝師,結合《黄帝四經》他們之間説話的語氣看,太山之稽要麽是黄帝老師,要麽是軍師,反正年齡比黄帝大、智慧比黄帝高是無疑的。討論戰争尤其是攻打蚩尤的經驗總結。黄帝最後總結發言:“謹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視(示)後人。”(19)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261頁。這裏守名即是守道。名是《黄帝四經》概念體系中僅次於“道”“一”的範疇,是道體向道用過渡的中介之一,是聖人立法的依據,所以黄帝才説“守吾正名,毋失恒刑”,守名在先,恒刑(法)在後。
《十大經·行守》雖無明文“守道”字眼,但從其文章的主旨看就是探討守道問題的。《行守》認爲治國、爲人都不應“刑於雄節”,而應守雌節,講信用,“言之壹,行之壹”。即爲國之謀、爲人之守最終應落腳於道,這個道無形無名,是天地之母,無時無刻不在創生運化萬物。因此行守就是守道。
《道原》是專門論述道體與道用的,前半部分論道體,後半部分論道用,强調統治者要“察無形,聽無聲”,定名形,“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最後總結道:“抱道執度,天下可一。”(20)同上,第406、409、409頁。《道原》是比較集中地論述道體的篇章,其他篇章只是把道體夾雜在行文中,缺乏系統的專門論述。作者欲以《道原》對整個《黄帝四經》作總結,所以後半部分不忘道用的論述,道體與道用合一,這正是《黄帝四經》的主旨所在,概之曰“守道成法”。
三、 得道以審分定名
道、一、二、名、法是黄老道家獨具特色的範疇,道—一—二—名—法是其獨具特色的邏輯鏈條,當然戰國、秦漢之際的儒家(如荀子、董子等)受這種邏輯影響頗深,其於中國封建主流統治模式——“隆禮重法”的形成有參驗合力之功。除了儒家,戰國、秦漢之際的法家和名家受黄老道家影響也頗大,如申不害、慎到、韓非子、鄒衍等,以至於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介紹這些人時常以“其本歸於黄老”作總結。在道—一—二—名—法的邏輯鏈條中,道爲宗,一、二、名、法爲繼嗣,把道的精神意涵像血液一樣傳遞給下位階的範疇,因而也是一個實用性逐漸遞增的過程。以上分析了道、一這兩個範疇,接下來看“名”。
從題目“得道以審分定名”看,有幾個問題需説明: 第一,名比分重要,理由是: ① 從《黄帝四經》相關語境看,名的内涵與外延都要比分大;② 從《老子》開篇即言“名可名,非常名”看,名這個範疇的地位遠比“分”高;③ 從黄老道家的邏輯鏈條看,名與道、一、二、法的邏輯相關性更强;④ 一般情況下,名的内涵中的名分義涵括了“分”的意義,因此此節棄“分”而留“名”,僅對名作細緻地梳理。第二,名是道的演化之物,其存在的本質取決於道,“道正”或曰“守道”則有正名,不守道則有奇名甚至無名;名是道建立天地秩序規則的直接依據,是道生法的具體基礎。第三,道是法之宗,名是法之父,因此名在《黄帝四經》中非常重要。第四,名在黄老道家中的含義較多,要之有: 道名、規律、本質、秩序、名稱、稱呼、稱號、稱謂、名分、名位、法度等。第五,這樣的意義定格,其源在《老子》,其流在《黄帝四經》《管子》《韓非子》等其他著作中,下面就相關問題分述之。
(一) 名之源泉: 《老子》
名之重要,其源在《老子》。《老子》有“名”的篇章共計10章,除了第一章的“名”哲學意味較强外,其餘多表示稱謂、名稱等,哲學意味不强。《老子》開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句話共有5個“名”,其中第一和第三個“名”意思是道,但又不完全是道,是道的衍生物,可稱之爲“道名”。因爲可以稱謂的名“非常名”,也即不是像道那樣具有恒常意義的名,所以這兩個“名”的意思是道名。其餘三個“名”皆爲稱謂之意,但在有無之間,意思又稍有差異。這裏的“無名”實指道,即道爲無名的存在,是天地之始元。這裏的“有名”,實指“一”,是道化生萬物的開端,“一”是可認識的,所以是有名的。有名的“一”,也是法度之原。總觀《老子》之“名”,可明白以下幾點: 首先,“名”在《老子》中雖應用較多(泛見於10章),但相比於《黄帝四經》,其哲學意味不强、内涵不多、外延不大,可見《黄帝四經》宗於老子,以敏感的思想嗅覺捕捉到了《老子》“名”之精義,並發展之。第二,作爲以“道術將爲天下合”爲己任的《黄帝四經》對《老子》“名”作了充分發展,豐富了其内涵,拓展了其外延,但主要在法度,包括法度的内涵、外延、建構、執行等意義。這其實是《黄帝四經》“道生法”“案法而治”内在邏輯的應有之義。
(二) 《黄帝四經》對老子之名的發展
“名”在《黄帝四經》中合計出現15次,這給我們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名”在《黄帝四經》乃至黄老道家中很重要。《黄帝四經》的《經法》計9篇,《十大經》15篇,《稱》和《道原》獨立成篇,合計26篇,在26篇中有15篇言及“名”,這遠遠高於《老子》的10∶81的比率,而且更重要的是,《黄帝四經》還有專門論述“名”的《經法·名理》,可見“名”在《黄帝四經》中的重要性。“名”在《黄帝四經》中這樣頻繁出現,其用意何在?愚以爲其最大的目的是爲“道生法”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邏輯路徑,以此契合其“道生法”“案法而治”的寫作宗旨。
《經法·道法》主要講的是道生法的問題,但是作者兩次提到名形問題,分别是第三自然段和倒數第二自然段。倒數第二自然段是對第三自然段的重複和强調。第三自然段的名形是作者在對道進行了一番描述後自然過渡而來的,即道雖虚無縹緲,但“虚無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刑(形)名”,即只要我們心在虚無有的狀態,那麽就可洞察秋毫,明白事物的形名及其關係。接着作者説明了刑(形)名的意義:“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刑(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迹匿正矣。”(21)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0頁。這裏名指名稱、名號、概念,形即事物的形狀、外貌、形體,形名即事物的形態與概念,也可理解爲名實。道在創生萬物之後,人類應該要對這些事物進行認知,給它們分門别類,爲了不混淆,所以有必要給不同的事物取不同的名字,標準即是名實相符。所以這個“名”是内涵和外延非常廣泛的概念,因爲它與事物是對等的關係。以此觀之,“名”比“法”要高一個位階,要抽象些,“法”懲罰已犯,名理重在預防,與禮相類。但是作爲道的演化者,“名”具有理和秩序之意,所謂“循名究理”,是法制定和執行的依據。本段所説的聲號即爲法度,是顯明的“名”,追其源爲道。所以本段的邏輯是只要心虚無有,歸於道,那麽就可以洞察道所創生的世界之奧妙,依形立名,依名立法,則天下萬物無所逃匿道,則天下是非分明,黑白有度,自然和諧了。最後作者强調説:“名(刑)形已定,物自爲正。”(22)同上,第25頁。如此則統治者可收無爲而治之效了。
《經法·論》中提及“名”者有4處。主要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是法度之名;第二層是把“名”作了正名、奇名、無名的劃分。從第二種意思看,“名”有正名,即天定的順道之名;有奇名和亂名,即人定的亂道之名。奇名是中性詞,褒貶視其語境而定,例如本篇曰“倚(奇)名,法而亂”,認爲奇名會導致法度的紊亂。但是在戰争中未必爲壞事,老子便主張“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兵法》也認爲“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主張“出奇制勝”。可見在和平的守成社會,要用正名,在戰争中要用奇名。《黄帝四經》將“名”作了三種劃分,顯然是拓展了“名”的内涵和外延,是對老子之名的發展。《經法·論》曰:“七法各當其名,胃(謂)之物。”七法即明以正、順正、信、適、必、極而反、有常,這七種法應當與其名稱、本質相符合,才能算是達到了事物的本然狀態,意即順道。這裏所言“名”爲天然名,即道名、正名。接着作者提出審“三名”的問題:“審三名,……達於名實(相)應,盡知請(情)僞而不惑,然後帝王之道成。”如果大家都“循名復一”走正道就没有壞人壞事了,但是人是自主和自我的動物,所以難免會出現偏離道的情況,看來三名的劃分實出無奈。所以帝王要對人的言行進行觀察,哪些是符合名的、哪些不符合,然後獎賞正名者、懲罰和禁止無名及非戰争的奇名,如此社會才會日趨向好,霸業指日可待。接着作者對“三名”進行了描述:“三名: 一曰正名,立而偃(安);二曰倚(奇)名,法而亂;三曰强主烕(滅)而無名。三名察則事有應矣。”正名則國安,奇名則法亂,無名則强主滅。勸導人們要分清“三名”,多用正名,戰用奇名,不用無名。最後作者總結道:“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静(争)。勿(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三名察則盡知請(情)僞而[不]惑矣。”(23)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30~142頁。此點出了作者的寫作目的,就是要統治者“名實相應”,以取“物自正、名自命、事自定”的無爲而治之功,大大降低統治成本。
《經法·論約》有兩個地方提到“名”,第一個地方曰:“功不及天,退而無名。功合於天,名乃大成。……逆則死,失□□名。”這裏有三個“名”,前兩個當作名聲、建樹解,最後的“名”可作正名或名聲解。第二個地方曰:“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之謂有道。”(24)同上,第169~173頁。此處之“名”作本質、名稱解。《論約》之“名”是對《論》之“名”的補充,没有新的意義突破。
《經法·名理》是《黄帝四經·經法》的末篇,唯一以“名”爲篇名,但“名”僅在一處出現,提出了一個新概念: 循名究理。循名究理是其論證的主題,所以《名理》的篇名當作“循名究理”解較爲貼切。《經法·名理》曰:“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名□□循名廄(究)理之所之,……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虚静謹聽,以法爲符。”(25)同上,第187頁。天下之事,必有其名,循名究理以定法,是非紛争以法斷之,虚静謹聽能入道境,法度是道境之顯像。此段話最大的特點是道出了道、名、法的邏輯關係,循名究理的目的是爲了法治。此篇與首篇《道法》首尾呼應,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 首篇提出“道生法”“案(按)法而治”的主題,經過一系列的邏輯論證,尾篇點出了道生法的邏輯,强調了“是非有分、以法斷之”的法治主旨。以此看來,邏輯這樣緊密,風格如此相似,可以推斷至少《經法》的九篇係出自一人之手。
下面看看《十大經》15篇中的“名”。《十大經》大多是黄帝與其大臣(軍師)的對話,是黄帝踐行道法的經驗之談。15篇占了總篇幅26篇的一半多,彰顯了《黄帝四經》黄學(26)戰國初年,田齊代替姜齊後祀崇黄帝爲祖,以與姜齊祖炎帝區别開來,所以齊國出現了一系列以黄帝命名的學術著作,尤其稷下學宮存續的150年間更是如此。這就是黄學,重法强兵,崇仁尚義,與老子道合流,遂成黄老道,隆禮重法,重功用,崇道名,與南方的老莊原始道有一定的區别。的實用特色。當初班固將此書取名《黄帝四經》,其主要依據可能在此。如果説《黄帝四經》是黄老之學的代表作,那麽《經法》《十大經》是黄學集中部分,《稱》《道原》是老學集中部分,合之爲黄老之學,隆禮重法,重仁尚義,崇道法,尚功用,是典型的南北文化合流的産物。《十大經》以黄學爲主,因此理論色彩稍遜於其他三部,但是在交談的言語間也流露出道法的邏輯張力。“名”的字眼有出現,但很少有大段的相關論述,多爲一句帶過。這種結構布局可能與談話體的文風邏輯有關,語言的靈活性和互動性讓深入某個概念或理論不太可能。
《十大經·立命》曰:“吾(黄帝)受命於天,定立(位)於地,成名於人。”(27)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96頁。從語境和語言邏輯結構看,此處之“名”應爲名位、名望的意思,即我黄帝最終征服了百姓,獲得了帝王的名位。這裏的“名”,與道相去甚遠。《十大經·觀》中“名”出現了兩次,都未作深入論證。第一個“名”是力黑要布制建極,以改變“静作無時,先後無名”的混亂狀態。第二個“名”上接自然秩序下續人倫日常,與法度相關,彰顯了《黄帝四經》道生法之邏輯。《十大經·觀》曰:“其時贏(盈)而事絀(縮),陰節復次,地尤(炁)復收。正名修刑,執(蟄)蟲不出。”(28)同上,第223頁。贏指春夏,爲生發,當賞,絀指秋冬,爲收藏,當刑殺,此乃順天時。意指春夏之際,陽氣勃發不應行肅殺嚴苛之政,否則陰氣就會乘機搗亂,陽氣得不到升華,如果違背天時布德施賞決獄刑罰,蟄蟲將春眠……以此觀之,名法是建立在順應天時的基礎上的,而天時是順應道的,所以名法應遵道而行,否則將適得其反,塗亂天下。《十大經·果童》中“名”只出現一處二次,黄帝曰:“地俗(育)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兩若有名,相與則成。”(29)同上,第241頁。這兩個“名”都可作名分、秩序解,意即地以静養德,天以動正名……天地陰陽若都按規矩運行、相互配合則萬物生、萬事成。此篇之“名”與《觀》相似,都是把“名”作爲道法的過渡來論證。《十大經·正亂》中提到“名”者有三次,其中第二次是説戰勝蚩尤後,割下其頭髮裝飾旗杆並高高懸掛,“名曰之(蚩)尤之(旌)”,此處“名”顯然是“稱”的意思,第一、第三個“名”則是名位、秩序之意。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個“名”,黄帝曰:“謹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30)同上,第258~261頁。“名”和“刑”連用且“名”在前,這種句式在《黄帝四經》中多次出現,説明“名”是“刑”的基礎,其内涵外延皆大於“刑”,其意義之張力要遠勝法,也可以説,“名”是法制定和執行的原理和基礎,是其自然法淵源。
《十大經·姓争》説:“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其事若易成。”(31)同上,第269頁。這是《姓争》中唯一提及“名”的地方,其意當爲名分、規則。這裏將“法”與“名”連用,但是一反其常,將“法”放在“名”前面。乍看好像使“法”的意義位階高於“名”,實際此處的邏輯是遞進關係,是綜合法而非演繹法,因爲顯然動作比静居要複雜得多,因此需循名,僅有法尚不足以成事。這兩句話的含義很微妙,稍不留心就會産生錯覺或誤解。
《十大經·成法》中雖只三次提及“名”,但意義非凡,因爲作者在此篇中將“名”與道、法作了比較完整的邏輯論證,這在《黄帝四經》中是比較難見的。從邏輯上看,此篇是《經法·道法》的邏輯解析,二者遥相呼應,共同述説着《黄帝四經》“道生法”的旨趣,形成比較完整的邏輯鏈條。這一點再一次成爲整部《黄帝四經》乃同一人所作的佐證。此篇對道生法的邏輯解析,主要是通過新概念——“循名復一”來進行的。《成法》是黄帝問其大臣是否有成法來治理天下的對話。力牧認爲成法即“循名復一”。他説:“吾聞天下成法,……循名復一,民無亂紀。”(32)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286頁。從整篇文章的語境看,“成法”的意思是現成、先天之法,顯然是探討道法的原理與基礎或曰自然法淵源的,所以本文没有提及具體之法,其是中國古代少有的一篇法哲學論文。有自然法的追求和論證正是《黄帝四經》的可貴之處。自然法具有普遍性、永恒性,是能跨越時空的宇宙法則,是人定法的基礎。梅因在其《古代法》中對自然法進行了高度評價:“受法律和習慣統治的一切國家,部分是受其固有的特定法律支配,部分是受全人類共有的法律支配。……由自然理性指定給全人類的法律則稱爲‘國際法’,因爲所有的國家都采用它。”(33)[英] 梅因《古代法》,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7頁。在自然理性指導下所制定的法律具有普遍性,所以受到所有國家的尊重,成爲國際法的法哲學基礎。梅因認爲一個民族所制定的法律是“民事法律”,是特定法律,只在一國之内遵行。我倒覺得,不管是一國之法還是國際法,甚至習慣法,都有共同的法理基礎,那就是自然法。難能可貴的是,在幾千年前的戰國時期,居然有專門論證法律原理的法哲學著作,表明先秦之際中國先祖的思維之發達、邏輯之嚴密、理性之高超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尤其《成法》篇,更是其精華。
《十大經·前道》中兩次提及“名”。第一次言:“天下名軒執□士於是虚。”軒,本義爲士大夫所乘車輛,引申爲士大夫;虚作聚集解,這都没有異議。名,陳鼓應先生作“大”解,我以爲值得商榷,軒在此是用其引申義,即士大夫,如果真如陳老師所説作“大”解,那麽名軒連用意爲大士大夫,這顯然不通順,我以爲作“著名”解更妥帖,那麽名軒即爲名士。再有,□裏缺字陳老師認爲應該是“國”,理由是下文有“國士也”的用語,然而連用爲“執國士”不太通順,我認爲缺字爲“道”較妥,連用爲“執道士”,執道士即執道者,這個稱謂《黄帝四經》多處使用,符合其用語習慣。因此這裏的“名”與道、法關聯不大。第二個“名”即:“□[名]正者治,名奇者亂。正名不奇,奇名不立。”(34)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314頁。這裏的“名”意爲刑名,正名即正定刑名、名副其實。其涉及了名法問題,認爲正定刑名是天下治的前提條件。
《十大經·行守》目的是勸人守道。作者最後總結道:“無刑(形)無名,先天地生,至今未成。”(35)同上,第323頁。這句話是對全文的總結,也是對道的描述,此“名”當理解爲“名稱”“名狀”,無形無名,即道是無可名狀的,此句與《老子》“名可名,非常名”相呼應。
《十大經·名刑》提及“名”者僅一處,即“欲知得失請(情),必審名察刑(形)”(36)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336頁。。這裏提出了個新概念——審名察刑(形),是“名”邏輯走向的下滑綫,上滑綫爲“循名復一”,通道境,下滑綫通萬事萬物,即刑(形),力求上要“循名復一”,下要“名副其實”。當然法度屬於刑(形)中的一種形態。“名”在此與法度相連了。
《稱》爲《黄帝四經》的第三篇,没有分章,獨立成文。主要論證的是陰陽、動静、正奇、内外等矛盾雙方對立轉化中的平衡。全文爲格言集萃,缺乏整體的連貫邏輯,但所選之言,皆屬黄老無疑。此篇“名”字在兩處出現。第一處:“建以其刑(形),名以其名。”(37)同上,第345頁。即依據其形體而用之,依據其名稱而稱之。第一個“名”爲動詞,即稱謂,第二個“名”爲名詞,即名稱。此處與道、法相關性不大。第二處“名”言:“帝者臣,名臣,其實師也。王者臣,名臣,其實友也。”(38)同上,第352~353頁。此處論述五種臣名義與實質的差别。如帝者臣,名義上爲臣,實質是帝之導師。這裏的“名”顯然作“名義”解,與道、法關聯不大。
《道原》是《黄帝四經》的收官之作,其中“名”字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曰:“人皆以之,莫知其名。”(39)同上,第399頁。這裏“名”爲其本意——名稱。第二個“名”意義稍微複雜些。《道原》曰:“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40)同上,第409頁。根據事物各自的名稱而給予正確的界定,使各歸其位,則萬物自定。這裏的“名”我以爲不僅僅是名稱,而且有名分的含義(41)谷斌、張慧姝、鄭開所注《黄帝四經注譯·道德經注譯》認爲此處之“名”爲名稱之意,我以爲這種含義只是此處“名”之意義的一半,除了名稱,還有名分、等級秩序的含義,這樣才足以在邏輯上與下句“而萬物自定”銜接,因爲僅僅作“名稱”意缺乏萬物自定的驅動力。參見谷斌、張慧姝、鄭開《黄帝四經注譯·道德經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9頁。。
值得一提的是作爲黄老學派最早最完整的法哲學著作,其重“名”思想對《管子》《尸子》《尹文子》《韓非子》(42)見《管子·七臣七主》《尸子·發蒙》《尹文子·大道上》及《韓非子·主道》《揚權》《詭使》等篇。等黄老其他著作産生了較大影響。在維繫黄老學體系中,“名”這個範疇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作爲法哲學專著,《黄帝四經》論述“名”主要是銜接人類社會的法度,而以上所説的其他著作未必都能實踐如此的邏輯圓融。
綜上所述,《黄帝四經》中的“名”是其法哲學邏輯體系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上承道、一、二,下啓法,是作者精心建構的一個法哲學範疇。應該説“名”和其上位的道、一、二構成了人定法度的自然法基礎,爲良法的創生與執行提供了强有力的道義支援,這種嚴謹的邏輯思維是《黄帝四經》的特出之處,是其能擔當“道術將爲天下合”歷史大任的智識基礎,也是其與商鞅、吴起等純法家的區别之所在。
四、 審分定名以萬民不争
審分與定名雖然具有先後的邏輯差異,但是兩者的意義很接近。從某種程度而言,審分即定名,定名即審分。因爲審分的過程和結果必須以不同的名來進行界定,而定名的過程和結果本身就是分判的過程。
標題“審分定名以萬民不争”可以“定分止争”概括。“定分止争”首出《管子·七臣七主》。各家之言,其旨必在止争,但路數有别。法家以法分止争,儒家以禮分止争,原始道家以道合止争,墨家以博愛止争,兵家以兵戰權謀止争,名家以名分止争,黄老道兼提名分和法分止争。與《老子》一樣,《黄帝四經》鮮提“分”,通覽全書,提及“分”者僅2處。這是因爲“分”與“名”意義相當,所以多以“名”字代替“分”字,以定名止争代替定分止争。應該注意的是,從語言學角度看,“分”字的抽象性比名字低,在意義指涉上要比“名”清晰,所以也可把“分”看成是“名”的具化過渡關口,此關係頗類道與一的關係。道即一,但一的指涉更具體,二者能指一樣但所指有一定差别。正因爲此,所以《管子》提出了定分止争的範疇,是對《黄帝四經》“定名止分”的繼承和發展,以此將道法逐漸明朗化,形成一條“道—一—二—名—分—法”的清晰的邏輯鏈條。下面看看《黄帝四經》止争的路數。
前面我們對“名”已經進行了詳盡的析述,此部分將“名”與“分”、止争聯繫起來,深入挖掘“名”在《黄帝四經》中的意義,也只有與“分”、止争聯繫起來,才能使“名”在《黄帝四經》中的意義變得圓融起來。正如以上所述,“名”是《黄帝四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原因在於它是道通達法的橋梁,没有名,道要實踐它的法意,完成接地氣的化生之旅很難。所以“名”在《黄帝四經》中頻繁出現,26篇中15篇都涉及“名”。下面看《黄帝四經》是怎樣通過名分來止争的。
從邏輯上看,不管其具體涵義如何,“名”本身内在地具有“分”的屬性。如公孫龍所言“白馬非馬”“離堅白”,其依據即在白馬、馬、堅和白是不同的概念,即不同的“名”,分别代表不同的事物。因此每個“名”都代表某個或某類特定的事物,這些不同的事物及其名之間是有區别的,反之正是根據這些差别才判定事物的特性並給予其特定的名稱,這就是“分”。從大的方面看,有時“名”代表規律、規則、秩序,不同的規則就是“分”。因此從邏輯上看,名分止争是貫通一氣的。這就是爲何《黄帝四經》大談特談“名”的原因,其目的在“分”,在法,在止争。
雖説“名”内在地隱含“分”之意,但《黄帝四經》直接談名分者僅四篇,即《道法》《大分》《名理》和《道原》。《大分》是直接以“分”命名的專門談及“分”的,其餘三篇僅是提及。但是在《黄帝四經》有限的26篇中能有一篇專論“分”,説明它對“分”還是很重視的,或曰特意以此篇説明“分”的意義,綜述“名”之“分”之意。《經法·道法》曰:“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迹匿正矣。”(43)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0頁。前一句論證的是刑(形)名已定,是是非非就有明確的標準了。後一句説的更具體,即刑(形)名立,法制建,天下萬物皆按照刑名、法度運行,違背了刑名、法度就要遭到懲罰。這裏的物自爲正,當然包含了萬民不争。這裏面也藴含着無爲而治的意涵,當然這種無爲是建立在“執道者生法”的有爲基礎上的。
《經法·大分》,陳鼓應先生作“六分”,作“大分”是李學勤和余明光先生的觀點。陳鼓應先生作“六分”解,恐是看文章裏有“六逆”“六順”的論述。至於“分”字,陳鼓應先生作“分際、界綫”解,而谷斌、張慧姝、鄭開注釋爲“大義、要領”,我以爲這些解釋都符合“分”的廣義,但具體意義則要視其語境而定。從全文的邏輯結構看,作者首先提出“六逆、六順”,然後對這些現象進行哲理分析,宗旨是論證治國的方略。所以在文章的後部作者提出了“道”,將思維的觸角深入到最高深的範疇。如此看來,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分”之義,得將其放在“道—一—二—名—分—法”這一黄老特有的邏輯體系中進行,從這個角度看,似乎題名定爲《大分》更貼切。《經法·大分》言:“六順六逆□存亡[興壞]之分也。主上者執大分以生殺,以賞[罰],以必伐。……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又[有]人焉。參[三]者參用之,□□而有天下矣。”(44)同上,第86~87頁。從此段行文看,作者完全是從道的整體邏輯來論證治道的,因此“分”也必須放在這個整體邏輯體系中進行理解。第一個“分”可理解爲“分際、界綫、大義、要領”,第二個“分”外延更廣,除了包含了第一個“分”的意義外,還可理解爲“規則、法則、名分”等,總之是僅低於“名”的邏輯範疇,比“名”要具體但比法又抽象些,是統治者治理天下時應切實注意分辨的一些帶有原則性的問題。
“分”要達到的最終目的就是分清是非好壞、等級名分、職責分工,以便“是非有分,以法斷之”(《經法·名理》)。《經法·名理》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從整體角度看,《經法·名理》還是對道作接地氣的解析,其中“道”“名形”“分”“法”“剛柔”等《黄帝四經》的基礎範疇都出現了,再一次彰顯了《黄帝四經》邏輯的嚴密性。整篇《名理》中,“分”僅出現一次,即“是非有分,以法斷之”。這裏的“分”是是非之分,與具體的人定法接近,是人定法遵循的準則,這好比是道派遣的使者,專門管理、引領人定法。
《道原》中的“分”也是在道法的整體邏輯系統中展開的,是道生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對道進行一番描述後,作者言:“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不爲治勸,不爲亂解(懈)。”(45)此段話可與《尸子·發蒙》《尹文子·大道上》等篇相關表述比對,可見後二者相關文句和文意顯然引述了《道原》。《尸子·發蒙》曰:“若夫名分,聖人之所審也……審名分,群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辯,名定也。”《尹文子·大道上》言:“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參見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409頁。第一個“分”爲動詞,意爲使之分明,第二個“分”爲名詞,意爲名分、職分、分界(46)名分、職分主要用於人,分界主要用於事物。,只要以名分、分界將萬物分判清楚,則萬物自定,萬民不争。下一句的“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與第一句是雙關語,兩句文義互見,所以第一句也包含了“萬物自定”的意思。第三句是總結,即只要授之以名、分之以分,則萬物自定、萬民不争,人們不會只在國家安定時努力謹守本分,在國家混亂時也不會懈怠,這就臻於無爲而治之境了;《黄帝四經》所要探討的就是道法的這種最高的治理境界。這裏的無爲不是絶對的無爲,而是相對的,包含着必然的有爲成分,比如“執道者生法”“抱道執度”“案法而治”、國人對道法的遵守等等。因此道法存乎有無之間。
綜上所述,不管儒家、法家還是黄老家,都有審分定名的表述,其目的皆在“止争”。但不同的是正如以上所述,儒、法審分定名的邏輯性、深刻性、體系性、哲理性都不如《黄帝四經》。在止争方面,《黄帝四經》的止争已臻於無爲之境,存乎有無之間,既有高大上的理論,又不乏接地氣的法度,充分彰顯了其自然法的根蒂,爲有根之法,因此更具有生命力、説服力。
五、 無爲而治: 法之迵(洞)同太虚的妙用
《黄帝四經》道法之無爲妙用當然是延續老子無爲而治的範疇。所以先從老子處挖掘無爲之根。
無爲是老子創生的範疇,與有爲是對立,且具有辯證一體性,是老子思想體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作爲“君人南面之術”的《老子》,其“南面之術”的核心即“無爲”,無爲是道的本質,也是道運化天下的方式。老子運用其高超的哲學智慧將一個普通詞彙——無——賦予了迵(洞)同太虚的本質和智慧,成爲中華民族和合文化辯證的化身,其智不可謂不高,其功不可謂不大。
《老子》八十一章中,有“無”字出現者計35章,可見“無”在老子心目中的地位。概之這35處“無”字意義主要有三: 第一,爲無的本意,與“没有”同;第二,爲道的代名詞或描述;第三,無爲而治。作無爲而治解者多以“無爲”字眼出現,有的雖無“無爲”字眼,但意義與無爲同。以上三種意義,第三種與本節主題相切,特分解如下。
老子對無爲十分重視,對其進行了多方解説,其認爲無爲的本質是道的存在和運化萬物的方式,最終上升到自然。老子創生無爲的理論,目的是展開其“君人南面之術”,奉勸世人尤其統治者要尊重事物的發展規律,順其自然,不妄爲,尤其對於社會人世的治理更是要遵循無爲之道,“以無事取天下”,才能收無不爲之功。《黄帝四經》正是接續了老子無爲之意進行政治言説的。
作爲黄老學最早最完整的經典著作和稷下學宫最完整最深刻的法哲學著作,《黄帝四經》以黄帝、老子爲宗,這一點以其整部著作的結構佈局爲證,即其整部著作中充滿了老子和黄帝思想觀點的交織,其中黄帝思想主要集中在《十大經》的15篇中,當然這15篇處處也充斥着老子的道意,老子思想在《經法》9篇、《稱》《道原》中比較集中。當然《黄帝四經》提出“道法”的主旨思想,與黄帝及齊文化重兵戰有一定關係,可以説《黄帝四經》思想是以黄帝、老子、齊法家爲主的整個戰國文化的綜合,其胸懷與氣魄體現了“道術將爲天下合”的精神。因爲黄帝太久遠,其思想難考,所以在理論基礎方面《黄帝四經》以老子爲宗是自然的事,這就是爲何在專論黄帝思想的《十大經》15篇中充斥着老子思想的原因。而重事功的齊文化内在要求《黄帝四經》在吸取老子智慧時應重在應用,所以《黄帝四經》創生了“道法”理論,着重論述道生法的邏輯及其功用,因此無爲而治便赫然於《黄帝四經》的邏輯鏈條中。
如果説《老子》的無爲太抽象太理想化,那麽《黄帝四經》對其作了具體化的發揮,即將無爲運用於“道生法”的邏輯鏈條中,對具體法度的生成及應用從無爲角度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如果説《老子》之旨在“無爲而治”,那麽《黄帝四經》之旨在“道法之治”,從這個立場看,無爲而治僅是論證和升華“道法之治”的工具。所以整部《黄帝四經》有無爲而治之意者6篇(47)即《道法》《論》《五正》《名形》《稱》《道原》。,其中直接涉及無爲者僅3篇。文墨雖少,但並不代表無爲不重要,其集中體現了“道法”之道的精神内涵,是解析《黄帝四經》“道法”無爲之妙用的鑰匙。
《經法·道法》言:“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無執也,無處也,無爲也,無私也。”(48)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10頁。從此段可看出《黄帝四經》的一個特點,即論證無爲時多與刑(形)名之論夾雜在一起,這説明其重心在形名,因爲形名與人定法關聯緊密,因此在提到形名聲號的功用時才提及無爲,認爲只要“循名復一”“名符其實”、行無爲之道,則“無不自爲刑(形)名聲號”,收無爲而無不爲之功效。
《經法·論》没有直接提及無爲,也是在論述刑(形)名時闡述了關於無爲而治的理論。《論》曰:“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静(争)。勿(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49)同上,第141頁。《論》的作者認爲只要名實相應則物自正、事自定,可收無爲而無不爲之效。在此“物自正”“事自定”即物事順應了道,無需人爲的作爲,否則反而會擾亂事物的正常運行和發展。所以無爲的前提是一切人、物、事都回歸道,回到自然本身,即如胡塞爾所言的“回到事物本身”。
《十大經·五正》也無直接提及無爲者,但無爲之意可從其中推斷出來。例如黄帝在與蚩尤決一雌雄之前在博望山上“談(恬)卧三年以自求”,修煉内功,將治理之事交給大臣,以無爲治理天下,結果終於戰勝蚩尤,統一天下。這是作者用實例説明無爲而治的功效。《十大經》最後一篇《名刑》言:“刑(形)恒自定,是我俞(愈)静。事恒自施,是我無爲。”(50)同上,第336頁。此處論證無爲的邏輯與以上各篇同,是在刑(形)名自定基礎上確定事恒自施,然後提出無爲之功效。《稱》也没有直接提及無爲,但能從其文意中推斷出來。例如“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辟其户牖而各取其昭焉。天無事焉”(51)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381頁。《淮南子·詮言訓》引述了這段話。。此段話是借天之明比喻道無爲之功,道創生萬物後,將道的精神灌注其中,成爲事物之本質,讓事物按其本質自行運行,道無事了,這個無事就是無爲。
《道原》是《黄帝四經》的最後一篇,也是提及無爲思想的最後一篇。作者把《道原》放在最後,無疑是以之作爲整部《黄帝四經》的總結(52)由此再一次證明整部《黄帝四經》具有邏輯連貫性,係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可能性很大。。因爲是總結,所以本篇幾乎囊括了整部《黄帝四經》所有重要的範疇,如道、太虚、一、陰陽、刑(形)名、無爲、稽、極、分、抱道執度(法)等,《黄帝四經》所言之要即是由這些重要的範疇構成的邏輯體系。作爲總結之篇,相較於其他各篇,本篇無爲思想更具有體系性和邏輯性。《道原》曰:“一者其號也,虚其舍也,無爲其素也,和其用也……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53)陳鼓應《〈黄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第402~409頁。第一句中的四個分句都是從不同角度對道描述和界定,第四句道出了其和用之功。和即和諧,包括自然内部、社會内部及自然和社會之間的和諧。爲何道能實現這些和諧?是因爲道清虚守静、無爲無欲,定名刑(形)、建聲號,以道創生萬物,創生後又使事物回到自身,回歸自然,所以萬物自定,天下和諧。值得一提的是此章還是將無爲而治放在道、刑(形)名、名分的整體邏輯中探討,沿襲了其一貫重邏輯的文習。最後作者總結道“抱道執度,天下可一”,度即法,所以又可表述爲“抱道執法,天下可一”,這句話既點出了《道原》的主題,又是整部《黄帝四經》的思想總結,與首篇《道法》的“道生法。法者……[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54)同上,第1頁。之言遥相呼應,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
結 語
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以來,《黄帝四經》備受關注,其爲黄老學之經典也漸爲學界肯定。在“道術將爲天下合”(55)向達《〈黄帝四經〉“法主德輔”的治道精神及其意義》,《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的歷史背景下,《黄帝四經》“援道言法”“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凝塑成獨具特色的“隆禮重法”治道精神,“是理性和智慧的化身,爲中國‘隆禮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56)向達《〈黄帝四經〉的“案(按)法而治”三題》,《理論導刊》,2016年第6期。。通過道、一、二、名、分、法等範疇,《黄帝四經》“推天道以明人事”,證成自己“無爲而治”之功,形成一套具有嚴密理路邏輯的法度體系。《黄帝四經》“隆禮重法”的道法之治對六國時齊國及漢初的政治實踐具有直接影響,在理論方面對荀子、陸賈、賈誼、韓嬰、董仲舒等儒家産生了重大影響,尤其荀子、董子的“隆禮重法”思想的基本框架即建基於《黄帝四經》,不過他們傾向於“德主法輔”而已。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黄老道法之治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爲儒家的“德主法輔”所替代。《黄帝四經》“隆禮重法”“法主德輔”的法治思想“適合現當代中國社會,應對其歷史和現代價值進行應有的肯定”(57)向達《〈黄帝四經〉的“案(按)法而治”三題》,《理論導刊》,2016年第6期。。筆者水準有限,相關研究難免不足,不求文章千古,但祈抛磚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