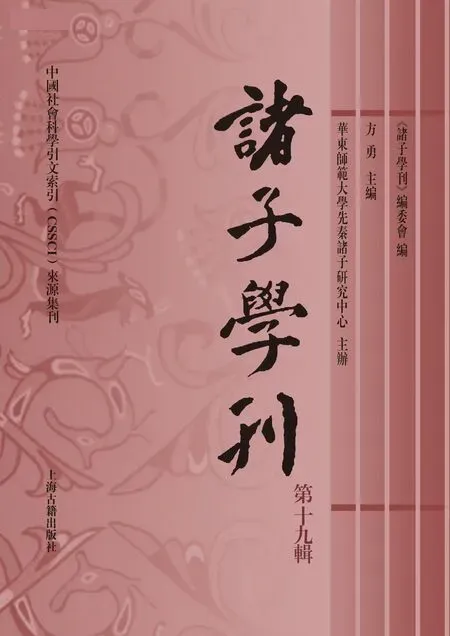老學早期學者對老子無爲思想的拓展
李秀華
内容提要 老學早期學者,是指春秋戰國之際接受和弘揚老子思想的一批學者,大多是老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以關尹子、文子、列子、楊朱爲代表。他們沿着“内聖”與“外王”的思路,對老子無爲思想作了富有個性的拓展。關尹子談無爲,着重於内在精神的寂清,主張消泯一切自主意識和行爲,完全被動地回應外界,但反對“聚塊”“積塵”式的無爲。這對莊子“至人無己”的説法無疑具有直接影響。文子談無爲,注重由内而外的實際功用,主張王者“執一無爲”,“見小”“守静”,融道、德與仁、義、禮於一爐,以期成大功,立大業。文子可謂黄老學者之初祖。列子談無爲,立足於修心養神,主張泯内忘外,彼我不分,以臻至虚静玄妙之境。莊子學派的“坐忘”“心齋”理論即來源於此。楊朱談無爲,與列子正相反,主張彼我分明,不相侵越,個人應“貴己”“全生”,保證自我齊整,以達致整個社會的大治。他們的拓展,在無爲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
關鍵詞 老學 老子 無爲 内外
導 言
老子雖爲隱士,但曾任周代守藏室之史,聲名頗大。顯然,他不會是獨行者,身邊也會有許多人向他問學,從他遊學,還有一些人作爲他的朋友與其交往。老學憑藉自身的魅力,再經過這些人的傳承和發展,在春秋末與戰國初就産生了巨大影響,衍生出多種學問流派。
《莊子》一書雖然“寓言十九”,有的荒誕不經,但是很多寓言故事中的歷史人物並非虚構,不可一概否決。據其記載,向老子問學的有孔子(見《天地》《天道》《天運》《田子方》《知北遊》),有子貢(見《天運》),有崔瞿(見《在宥》),有士成綺(見《天道》)(1)其他典籍記載問學老子的還有尹文先生、楊氏之父(見《列子·周穆王》)、南榮疇(見《淮南子·修務訓》,賈誼《新書·勸學》作“南榮跦”)。;從老子遊學的有庚桑楚(見《庚桑楚》),有柏矩(見《則陽》),有陽子居(見《應帝王》《寓言》)(2)庚桑楚,《列子·仲尼》作“亢倉子”;陽子居,《列子·黄帝》作“楊朱”。;與老子相友善的有秦失(見《養生主》),有叔山無趾(見《德充符》)。除此之外,班固《漢書·藝文志》載録“《文子》九篇”,自注:“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載録“《蜎子》十三篇”,自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載録“《關尹子》九篇”,自注:“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另據《列子·説符》,列禦寇曾求學於關尹喜,所以與老子也有師承關係。
可見,老子學説自誕生以後就不斷得到傳播,尤其是老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如關尹喜、文子、庚桑楚、蜎淵、楊朱、列子等人,將其發揚光大。這些人可稱爲老學的早期學者。他們是道家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承上啓下式的人物,莊子學派、黄老學派、法家學派就是在他們的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發展的。很可惜,這些老學早期學者的著作大都散佚不存,有關他們的文獻記載也非常稀少,留存至今的一部分著作又被後人定作僞書,争議不斷。因此,要確切、具體地討論這些學者的思想是非常困難的。鑒於這些學者的重要性,我們在討論老子無爲思想的發展這個問題時,就不應忽視他們,因爲他們是驅動老子無爲思想演變的最初力量。
一、 向内收斂: 關尹子“貴清”的無爲主張
司馬遷説:“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若太史公所言屬實,那麽關令尹喜便是學習和研究《老子》的第一人。我們知道,關尹喜並非關尹子的真實姓名。現存《關尹子》一書,至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最早質疑,已基本被認定爲僞書。此書皆以“關尹子曰”起句,是純語録體,無任何寓言説理,確與先秦典籍不類,其内容多談五行之變,談儒家仁義禮智信,亦不近於老子思想,僞書的可能性很大。
如今要討論關尹子的無爲思想,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借助其他文獻的相關引述。《莊子·天下》云: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悦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虚不毁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顯然,莊子學派是把老子和關尹子歸作同一種思想流派。《莊子》引用關尹子的這段文字,在《列子·仲尼》有更爲詳細的引述,可作參考: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虚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3)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44~146頁。
與老子相比,關尹子的無爲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其意含更加向内收斂,更加注重精神上的清寂。“在己無居,形物自著”,郭象注曰:“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4)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094頁。物來就作出反應,不來就不作出反應,作出反應就無所藏匿,不自以爲主,只是任物去留,而物各自明。這種行爲,就像浮物於水面,隨其而動。這種行爲,就像鏡子,自身虚静,卻能將萬物情態原原本本地照映出來;這種行爲,就像聲音的回響,從不先唱,唯有後和。可見,關尹子主張的無爲,是要求泯滅一切自主的意識和感覺,即“不用耳”,“不用目”,“不用力”,“不用心”,做到絶對的無己,所有與外界發生的行爲都只是被動、消極回應的結果。這與老子“損之又損之”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帶有積極意義的無爲,明顯具有本質上的不同。此外,老子雖然講“不敢爲天下先”,但並未講“常隨人”,關尹子則把老子無爲思想中的不争不先,變成了隨波逐流。顯然,這也不符合老氏無爲思想的宗旨。
但在關尹子看來,他所主張的無爲並不是“聚塊”“積塵”。宋代江遹説:“聚塊則不爲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爲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爲矣。雖無爲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爲哉?聖人之無爲,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虚,無心於物,未嘗有爲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真無爲者也。”(5)江遹《沖虚至德真經解》,《中華道藏》第15册,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頁。聚塊、積塵,無非僵死不化,了無生氣,這樣的無爲不合於道。顯然,關尹子也意識到了“僵死不化”式無爲的危險性,他主張“在己無居”,其目的就是爲了排除自我的固執,以及由自我固執而造成與外界的生澀。只有如此,内心才能保持澄明,精神才能達致寂清。這正符合《吕氏春秋·不二》“關尹貴清”的説法。
《吕氏春秋·審己》還記載了列子與關尹子關於射箭的一段對話:“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6)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頁。所謂“守而勿失”之“守”,實際上就是《莊子》中提到的“純氣之守”(7)《莊子·達生》和《列子·黄帝》都記載了列子和關尹子的一段對話:“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莊子》作‘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當作吾)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莊子》作‘形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莊子》作‘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深(《莊子》作‘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所謂純氣之守、神全、得全於天,都是指保持精神上的純一。。純氣之守,本質上還是要讓内心保持澄明,精神保持寂清,没有自主意識與感覺的預先安排,没有外界聲色形貌的妨礙干擾。關尹子的這些思想,直接啓發了莊子學派“至人無己”“虚己遊世”的學説。
二、 由内而外: 文子“執一無爲”的主張
文子,班固説他與孔子同時,其真實姓名和生平事迹難以確考,但文子爲老子弟子這一點,自古及今學者並無疑義。今傳《文子》一書,被大多數古今學者定爲僞書。從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前55年)墓中出土的竹簡《文子》(殘本)徹底否定了《文子》是僞書的論斷。關於竹簡《文子》的成書年代,目前學術界尚在争論中。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今本《文子》雖然有些内容與竹簡《文子》相對應,但在古本《文子》的基礎上作了大規模的竄改,已失古本原貌。因此,竹簡《文子》就成了反映文子思想比較可靠的文獻。鑒於竹簡《文子》的嚴重殘損,我們討論文子的無爲思想,是建立在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大致對應的文本之上。
從竹簡《文子》保留的全部内容看,可以説《文子》與《老子》就是傳與經的關係。竹簡《文子》主要反映了文子的治國思想,對老子的無爲之治思想作了更加貼近社會現實的闡述和發揮。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執一無爲”説法的提出:
2262王曰:“吾聞古聖立天下,以道立天下……0564□何?”文子曰:“執一無爲。”平王曰:“……2360”文子曰:“……0870[天]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爲,爲者販(敗),執者失……0593是以聖王執一者,見小也;無爲者,……0775下正。”平王曰:“見小守静奈何?”文子曰:“……0908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0806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長守□;0864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長守民。2327[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富貴不離其身。”(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年第12期,第29頁。
這段文字,今本《文子》有大致對應的記述: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静也,守静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禄及子孫,古之王道,俱於此矣。”(9)王利器《文子疏義》,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1~232頁。
今本《老子》無“執一”一詞,然帛書《老子》、竹書《老子》均出現過1次(10)如帛書甲本:“曲則金(全),枉則定(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聲(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竹書本:“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或。是以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今本作“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在《老子》書中,“執”有四義: 一是捕捉罪人,如七十四章:“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二是依憑、持守,如三十五章:“執大象,天下往。”三是把持、占有,如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四是手拿、手握,如七十九章:“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只有這樣細分出來,我們才能解釋《老子》中“執”與“無執”説法的矛盾。老子講“執”時,取依憑、持守之義,其對象是道、大象、一;講“無執”時,取把持、占有之義,其對象是天下、萬物。
《文子》並没有改變老子對“執”的這些用法,但把“執一”與“無爲”連在一起使用尚屬首次。文子認爲,聖王執一就是見小,無爲就是守静。天地萬物乃大器,所以不能執爲,只能因循。文子這裏説的“一”正與“大器”相對。竹簡《文子》云:“2246文子曰:‘一者,萬物之始也。’平王曰:‘[何]……’。”(11)《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第29頁。又云:“‘0607萬物?’文子曰:‘萬物者,天地之謂也。’”(12)同上,第32頁。可知,天地是萬物的總稱,一即是天地之始。按照老子的説法,“無名,天地之始”,“道恒無名”,因此,“一”可以代稱“道”,聖王執一即是依憑和持守道的原理。在文子看來,“以道立天下”的規律,便是“0581産於有,始於弱而成於强,始於柔而……2331於短而成於長,始於寡而成於衆,始……”(13)《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第27頁。,便是“0899[高始於]下,先始於後,大始於小,多始於少”(14)同上,第30頁。。那麽,聖王執一,就是要持守弱、柔、短、寡、下、後、小、少,要“0595觀之難事,道於易也;大事,道於細也”(15)同上,第31頁。。這也就是文子所説的“見小故能成其大功”。文子提出的“執一無爲”,顯然是對老子正反相隨、正反互轉理論的運用,也是對帛書《老子》乙本中“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觀點的進一步發揮,體現了無爲而無不爲的原則。文子將執一與無爲連用,無疑遵循了老子思想的理路。至於守静無爲的觀點,亦是源自老子,並無新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子的執一無爲,完全是針對統治者而提出。他認爲,能做到見小守静,就能大而不衰、高而不危,能大而不衰、高而不危,就能富有天下,貴爲天子,長守富貴。這明顯具有世俗功利的目的,與老子不同。竹簡《文子》出現“帝王”3次,“天子”5次,“王侯”1次,“聖王”4次,“王者”6次。此足以證明文子提出的執一無爲,正在逐漸演變成帝王之術。文子説:“2419王者[一道]。”又説:“2385故王道唯德乎!臣故曰一道。”王者一道,即是執一御多,以易馭難,以小成大,而一道唯在於“德”。“以道王者,德也”(16)王利器《文子疏義》,第235頁。,道與德已合二爲一。可見,文子消除了老子之道的形而上色彩,將其實化。在此基礎上,他明確提出以道德治天下的主張:
0885平王曰:“爲正(政)奈何?”文[子曰:“御之以道,□]0707之以德,勿視以賢,勿加以力,□以□□2205□[言。”平王曰:“御]……2324□□以賢則民自足,毋加以力則民自……0876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離散不養。……0826則民倍(背)反(叛);視之賢,則民疾諍;加之以□,0898則民苛兆(逃)。民離散,則國執(勢)衰,民倍(背)……0886[上位危。”平王曰:“行此四者何如?”文子](17)《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第30頁。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不敢也。下以聚之,略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争,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叛則上無威,人争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18)王利器《文子疏義》,第242~243頁。
以道德治天下,就要排斥智巧、武力這些導致統治者妄作妄爲的因素。只要統治者以道御民,以德養民,不用智巧,勿尚武力,民衆自然會依附、臣服,自然會自足、自樸。否則,統治者就要權位不保,國家就要衰微。這些觀點無疑是承自於老子,是對老子無爲之治更加具體,更加實際的闡述。
爲使自己的主張更有吸引力,文子對待仁、義、禮等儒家教義,並没有像老子那樣采取貶斥的態度。相反,他把這三者都納入到了自己的治國思想中,使道、德、仁、義、禮並行而不悖。竹簡《文子》存有大量肯定仁義的殘言斷語,其云:“……0591踰節謂之無禮。毋德者則下怨,0895無[仁]0960則下諍,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0811[者不]立,謂之無道,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19)《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第29頁。無德、無仁、無義、無禮,則國將不國。可見,文子把老子對仁、義、禮的反感轉變成了親近,有意折衷老子與孔子的主張,使之成爲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的一般思想。從這個方面説,文子所主張的無爲之治,已有融合道、儒之趨向。
三、 内外俱泯: 列子“貴虚”的無爲主張
列子,即列禦寇,與鄭子陽(死於公元前398年)同時(20)《莊子·讓王》《吕氏春秋·先識覽·觀世》《列子·説符》等篇皆載列子與鄭子陽之事:“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據《史記·鄭世家》,(鄭繻公)二十五年(前398年),鄭君殺其相子陽。由此可知,列子生活在公元前398年前後,爲戰國初期人。列禦寇當時被稱作有道之士,年齡應該在60歲上下,所以列子當生於公元前458年前後。,隱姓埋名在鄭國生活了四十年,後入衛國,曾師事關尹喜、壺丘子林和老商氏,亦可謂老子的再傳弟子。司馬遷未爲列子作傳,其生平事迹不詳。據《漢書·藝文志》,有《列子》八篇傳於世。書中多稱“子列子”,可知此書是由列子弟子主要追記其師言行編撰而成,但並非全是列子思想的體現。今傳《列子》一書,自柳宗元質疑開始,逐漸被許多學者認定爲僞書,但仍有不少學者認爲是真書,遂形成針鋒相對的兩派觀點。
作爲僞書,《列子》有時被斷定爲漢時作品(21)見劉汝霖《周秦諸子考》,文化學社民國十八年版,第70~72頁。,有時被認爲是魏晉人士所造(22)見張心澂《僞書通考》,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825頁。,有時又被直接認爲是東晉張湛所造(23)見梁啓超《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48~49頁。。然而,《列子·周穆王》所描述的穆王“駕八駿之乘”,與西晉太康二年(281)出土的戰國魏襄王之前(公元前296年)的古書《穆天子傳》中的叙述一樣,這就基本否定了《列子》是漢魏時人僞造的觀點。此外,《淮南子·繆稱訓》所謂“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其寓言故事僅見於《列子·説符》;皇甫謐(215—282)《高士傳》記壺丘子林與列子談好遊之事、列子與尹生的對話也分别僅見於《列子·仲尼》和《列子·黄帝》;張華(232—300)《博物志》卷八《史補》記“二小兒辯日”事亦自稱出於《列子》。這些材料又相當於否定了《列子》是東晉人張湛僞造的觀點。持僞書觀點的學者,大都犯了以局部否定整體的錯誤。今本《列子》應是在古殘本《列子》的基礎上改動、增益、拼湊出來的,其中保留了古本的部分内容殆無可疑。
我們或許可以借助其他文獻的記載來分辨出古本的一些内容,從而瞭解列子的無爲思想。《吕氏春秋·審分覽·不二》:“子列子貴虚。”關於“貴虚”,《列子·天瑞》的記述更爲詳細: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虚?”列子曰:“虚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静,莫如虚。静也虚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24)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8~29頁。
去名之害,莫如虚静。保持虚静,方能使心有所安。向外界不停地索取贈與,只會導致心無所處,即使舞弄仁義,也不能補救這種心無所安的混亂狀態。顯然,列子反對世俗的取與之爲,强調内心的虚静與安穩。這是對老子虚静無爲思想的繼承。
又《莊子·逍遥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關於列子御風,《列子·黄帝》也有相關記述: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 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虚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25)同上,第46~48頁。
列子的這番長篇大論,是對虚静無爲觀點的進一步闡述,描繪了自己從不敢言是非利害,到率性而言是非利害,再到分辨不清彼我之是非利害,再到人我、物我兩忘的修心過程。可見,他所主張的無爲,要求完全消泯個人的主觀意志和情感,甚至自身感官的感覺差别,就像乾枯的樹葉皮殼一樣,以此達到一個彼我不分、内外俱泯的玄妙之境。莊子學派的“心齋”“坐忘”理論,即是來源於此。列子將虚静無爲引向一種極端的彼我不分、内外俱泯的精神境界,這顯然是老子無爲思想中所不包含的新觀點。
又《淮南子·繆稱訓》:“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列子·説符》亦有更爲詳細的記述: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 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26)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39頁。
形是實,影爲虚;形是主,影爲客;影隨形變。把自我置於影(虚像)的這面,不取實而取虚,不爲主而爲客,不執於自我而順應萬物之自然。這就是持後論的内涵(27)唐代盧重玄解釋説:“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僞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高守元《沖虚至德真經四解》)此引入“神”一詞,不符合列子原意。,用之於修身處世,則常常能獲得“處先”的效果。顯然,列子的持後論是對老子不争不先、外身身存、後身身先觀點的形象化闡述,並無有實質性的突破。
以上討論的都是列子以無爲來修身處世的思想,《戰國策》則有一段文字反映了他以之治國的理念: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28)劉向集録《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92頁。
史疾研習列子言論,這説明列子的學説曾經受到重視,也可以作爲《列子》一書在先秦時期即已形成的一個證據。“烏不爲烏,鵲不爲鵲”,説明的是名不副實,所以“正”就是正名。列子重視正名,這可能與他接受早期名家和黄老學派的學説有關,但與孔子的正名思想還是有區别的。孔子之正名主要强調身份等級的不可僭越,列子之正名則强調循名責實,百官各司其職,各行其是,必須名實相副。正名做好了,君主就可以無爲而治了。可見,列子“貴正”的觀點,與老子主張無名的説法相距甚遠,是對老子無爲之治的改造。
四、 内外分明: 楊朱“貴己”“全生”的無爲主張
《孟子》《莊子》《韓非子》等典籍,皆將楊朱、墨翟並稱,並記載了楊、墨的學説盛行一時的歷史事實(29)如《孟子·滕文公》:“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莊子·胠篋》:“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由此可知,楊朱的生活年代當與墨子很接近,或許比列子要更早一些。楊朱學説雖盛行一時,但很快被邊緣化,隨即沉寂、失傳。導致這一情況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受到了同時代及後來一些學者的激烈批判和排斥。如今,記載楊朱及其思想的可靠文獻屈指可數,而且大都只是隻言片語。《列子》被視作僞書後,其《楊朱》篇也變得不可靠了。很多疑古者時有主觀臆測,其結論自然難以服衆人之心。《列子》張湛序説:“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説符》《目録》三卷。”(30)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79頁。遭遇世亂,書籍散失是很正常的事情,張湛没有理由爲了作僞而編造這樣的經歷。《楊朱》篇極有可能就是今本《列子》所保存的古本内容之一。爲謹慎起見,筆者討論楊朱的無爲思想也將以其他文獻所記爲主,以《列子·楊朱》的相關内容爲輔。
對於楊朱思想,朱熹有一段評論:“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個逍遥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要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3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321頁。認爲楊朱的學説全部來自老子,楊朱本人是一個逃避俗務、明哲保身的人,非儒家眼中的義士。但朱熹所總結的“自要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可以説是對楊朱思想的精凖把握,爲我們理解楊朱的無爲主張提供了極好的注腳。所謂“界限齊整”,就是要内外分明,即“我”與“天下”界限分明;所謂“不相侵越”,就是要各守其界,即“我”不利“天下”,“天下”亦不爲“我”。“我”不利“天下”,即是“貴己”;“天下”不爲“我”,即是“全生”。只要社會中每個個體都能“貴己”“全生”,即“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那麽社會就會不治而治,終得大治。此便是楊朱無爲之治思想的精髓。
“貴己”是取於《吕氏春秋·不二》“陽子貴己”之説。但孟子卻用“爲我”一詞來批判楊朱,他説:“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盡心》)又説:“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的説法,又詳見於《列子·楊朱》: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32)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30頁。
從這段文字看,孟子以“爲我”來批判楊朱,顯然不够妥當。孟子只看到了“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的這一面,卻没有注意到“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另一面。韓非子批評楊朱,也犯了與孟子同樣的錯誤。他説:“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韓非子·顯學》)在楊朱看來,傷害自己去爲天下謀求好處,或者征服天下以滿足自己,都是不足取的。因此,用“爲我”或者“輕物重生”來解釋楊朱“拔一毛”之説都是片面的。尤其是孟子的説法,容易使人誤解爲楊朱只是個自私主義者。楊朱“不與”“不取”的説辭,顯示出他慎重於有爲的態度,此與老子的無爲是相通的,只是老子立足於道,而楊朱立足於個人本身。
楊朱認爲,如果社會的每個個體都能管理好自身,不越過自然的、法定的或約定俗成的界限,去侵犯其他個體,不自負地以社會爲己任,那麽整個社會就能不治而治。很顯然,這是對老子無爲自化思想的改造和應用。老子的無爲之治,僅對統治者提出了要求,並未對社會個體提出要求。在老子的眼中,只要統治者不違背道的性質和原理,守持無爲、好静、無事、無欲的原則,社會個體自然可以自化、自正、自富、自樸,整個社會自然可以不治而治。楊朱則罕言天道,將思考的着力點放在了個人之本身。他深刻地洞悉了人性,把無爲之治建立在對社會個體的規範之上,自律則是規範社會個體最重要的手段。這不能不説是楊朱對老子無爲思想的一種發展。
雖然楊朱提出了一種嶄新的無爲而治的社會治理模式,但他没有深入討論下去,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花費在思考個人的生命與價值等問題上。《淮南子·氾論訓》云:“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33)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7頁。楊朱非議墨子,應該是基於墨子不顧自身而自負地以天下爲己任的主張和行爲(34)《莊子·天下》説:“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從莊子學派對墨子的這些批評中,我們也能大致瞭解楊朱的意見。。與墨子相反,在社會與個體的權衡上,楊朱顯然更注重於後者,同時更明白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道理。所以,他强調個體生命的重要和自得,提倡社會個體的全生保真。《淮南子》“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之説,在《列子·楊朱》闡述得很詳細:
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御,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之物者,其唯聖人乎!(35)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34~235頁。五常之性,張湛注曰:“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其中“五常”,非董仲舒所指的仁、義、禮、智、信。這段引文從開頭至“任智而不恃力”,班固《漢書·刑法志》作:“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當是襲用《列子》而來,由此更可證明《列子·楊朱》的真實性。
楊朱講“全生”,但同時也講“身非我有”,故與貪生不同;楊朱講“存我”,但同時也講不侵占外物,故與自私不同。可見,楊朱關於全生的思考是非常理性的,與老子隨順自然、反對厚身益生的無爲修身思想是一致的。楊朱與孟孫陽的一段對話,進一步體現了這些主張:
孟孫陽問楊朱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36)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29~230頁。
貴生非能存生,愛身非能厚身,生命與身體都是自然所賦予的,人之有意作爲都不能增益其間。以不死和長壽爲目的的貴生愛身行爲,皆非楊朱所主張的全生。“廢而任之”是其全生的根本方法。廢,即無意於樂生惡死;任,即不壓制自然的欲望和行爲;廢而任之,即是無條件順應人自然的生死過程和原始欲望。與老子相比,楊朱不再强調道的根據,不再强調“鎮之以無名之樸”。因此,他所主張的全生容易帶來縱欲的危險。
當然,楊朱也看到了這一點,對老子“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的觀點作了詳細闡發。他説:“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 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民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37)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35~236頁。順民與遁民的差别,就在於能否抑制不顧自身而向外逐物的行爲,能否做到不逆命、不矜貴、不要勢、不貪富。即使是社會所認同的善行、善名,在楊朱看來也需要慎重爲之(38)《韓非子·説林》記載:“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最後一句,《列子·黄帝》作:“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列子·楊朱》載楊朱之語:“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争期,而争及之: 故君子必慎爲善。”皆能表明這一點。。這説明楊朱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求控制欲望的,反映了他以無爲而全生、順自然而養生的思想主張。
劉笑敢先生説:“對於老子來説,無爲可以導致一個更好的人類社會,引導一個更加自然而平和的發展。而楊朱的無爲則在於全身,没有任何社會性的目的。這是無爲理論的第一次轉變。”(39)劉笑敢《無爲思想的發展——從〈老子〉到〈淮南子〉》,《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2期,第95頁。認爲楊朱的無爲思想没有任何社會性的目的,似乎不合於事實。依筆者看,楊朱無爲而全身的主張,正是爲了造就適應其無爲之治模式的理想的社會個體。全生保真就是人人不損一毫,不以物累形就是人人不利天下,由此達到天下大治的社會效果。所以,楊朱並未割裂其全生理論與社會治理的關聯。以每個個體的全生保真來實現整個社會的無爲而治,儘管理想色彩依然濃厚,但確是老子無爲思想的一次大轉變。
結 語
總之,以關尹子、文子、列子、楊朱爲代表的老學早期學者,基本上是沿着内以修身、外以治國的方向,對老子無爲思想作了富有個性的拓展。關尹子談無爲,着重於内在精神的寂清,主張“在己無居”,消除一切自主意識和行爲,完全被動地與外界回應,做到絶對的無己,以保持内心的澄明,但並不是“聚塊”“積塵”式的僵死不化的無爲。這些主張直接啓發了莊子“至人無己”的觀點。文子談無爲,注重由“内聖”達到“外王”的實際功用,主張王者應“執一無爲”,“見小”“守静”,以期成大功,立大業,並主張把道、德與仁、義、禮融於一爐,用以治國。從這個方面説,文子可謂黄老學者之初祖,其無爲思想已有融合孔、老的趨向,具有明顯的用世精神。列子談無爲,則立足於修心養神,主張漸泯於内而終忘於外,彼我不分,物我同一,以臻至虚静玄妙之境。列子的無爲主張,與關尹較爲接近,都是要達到精神上的虚静之境,但列子更加强調物我的相通合一。他的這些主張直接影響到了莊子學派“坐忘”“心齋”的理論。楊朱談無爲,正與列子相反,要求分清彼我,不要相互侵越各自的界限,主張個人應“貴己”“全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以保證每個個體的自我齊整,從而達到整個社會的大治。可以説,楊朱“貴己”的無爲而治思想,是對老子思想的全新改造,是一次理論上的大轉變,可惜未能爲世人所認同。這些老學早期學者對老子無爲思想的拓展,都是有益的探索,極大豐富了它的内涵,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承前啓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