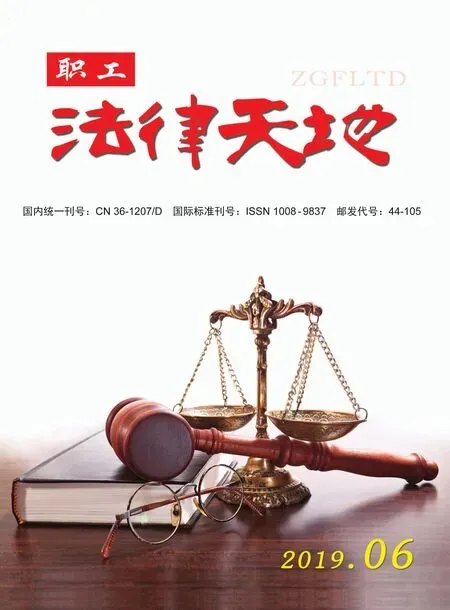浅析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
蒲 悦
(710063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一、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基本共识
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问题是实践中、学者间争议较多的热点问题。在民法学界和劳动法学界针对这二者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多次理论交锋。到目前,学者就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也达成了部分共识,即劳动关系发端于雇佣关系、劳动关系是对雇佣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法学者就二者的关系问题达成了相近甚至一致的结论。谢增毅认为:“劳动契约源于雇佣契约,但超越劳动契约”。郑尚元教授认为:“一般意义上,先有雇佣关系的民法调整,后有劳动关系的劳动法规制”。两位学者十分精准认识到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二者间的紧密联系,郑尚元教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更是理顺了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立法先后问题,事实上,域外多数国家亦是如此。
二、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关于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不同的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同观点,其中有人认为,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有着本质的不同。“劳动合同已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合同,而是一种在契约自由原则基础上渗透了国家公权力必要干预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合同。这种干预是国家基于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在对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实力对比和各自社会地位、身份等情形经过具体考察后,在劳动法的劳动者权利本位、用人单位义务本位的思想指导下所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关系的具体平等、结果平等和实质平等,使双方的利益格局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这二者在本质上亦是相同的,其中又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并无实性质差别。劳动合同就是一个“特种之雇佣契约”,史尚宽先生是这样认为的,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从属关系”,而劳动者的行为需要高度服从雇主的要求与标准,同时,劳动者“系提供其职业上之劳动力”。不过,现如今大多数的雇佣契约,都已属于劳动法意义范畴内的劳动关系。许建宇的观点是:“劳动法当属公私兼顾、以私法为主的法律劳动关系自主化、合同化是私法性质的主要体现,制定劳动基准和强行规范则是公法性质的集中展现,尽管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在劳动立法中相互交融,有时很难进行截然明确的划分,但就整体而言,合同化是第一位的,公法规范对合同关系的渗透程度必须以维护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为前提,只有当这种合意行为有可能损害到双方利益关系的均衡格局或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时,法律才通过预设劳动基准和强行规范进行必要的干预。”第二种观点认为,雇佣关系并不是民事关系,而应当是与劳动关系同性质的一种社会关系。其实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雇佣关系所具有的隶属性特征实际上并非民事法律关系所能够包容的一般性内容。除此之外,通过劳动法的发展由来及过程看,劳动法的相关内容已经从民法范畴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民法不同本位的社会法所调整的内容。故此,一些民法学者所主张的包容说只不过是大民法观念下的一种体现而已。所以,雇佣关系可以被理解为只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
事实上,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在原生状态下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它们都源自双方之间实施或接受劳动与得到或支付金钱报酬的交换关系,二者只是从不同的视角与维度来进行观察与思考。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的成立,都需要依赖于双方当事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意志之选择,即其发端于流通领域;而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的实现则需要依靠提供劳动的本人之付出,即其产生在劳动进行的过程中,实现在生产领域。因此,这两种关系在原生的状态下本质上是相同的关系。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法律的不同调整机制与不同立法背景下,这二者开始出现了区别。现代劳动同题,自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借出卖劳动力来谋生的工人,这个问题才日益受到重视。近现代社会中有关雇佣关系的领域,有相当大比例是出自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如1964年瑞士颁行的《工商实业劳工法》,从其名称上即可得出劳工之雇佣关系是出自工业和商业领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产业之外的第三产业在社会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其存在价值,世界各国劳动法大多将第三产业中的雇佣关系也纳入其调整范畴。非产业领域的雇佣关系则不定受劳动法规制。同时,这类雇佣契约规定适用债法,而家庭雇佣是否适能够用劳工法则依照受雇方是否为职业受雇者而决定。职业性是雇佣契约与劳动合同区别的又一重要标志。自工人产生后,职业受雇者或以被雇佣为生者为职业雇佣,因此,衡量雇佣契约与劳动合同的又标志是受雇佣者是否是以被雇佣为生的工人或劳动者。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在其适用范围中直接以各类产业为前提,将范畴内的产业领域的用人单位与个人都覆其中。此时,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开始有了区别。
三、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完善与思考
在我国,法律并未对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作出理论上的总括性规定。目前,我国对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实行双轨制的调整模式,即劳务关系由民法调整和劳动关系由社会法即劳动法调整。其中,并不能将劳务关系等同于雇佣关系来做理解,而劳动法列举式的规定又会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形,因而在实践中被《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所“遗漏”的这部分雇工与雇主之间因一方提供劳动力与一方给付报酬所发生的这种关系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实际生活中常见的这类雇佣形式有:家庭所雇保姆,私人之间的雇佣(如车主雇开车司机),雇请钟点工、私人保镖,聘用离退休人员,以及不具有招工资格的单位(如法人内部机构)招用临时工等等。遗憾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较差,雇佣关系目前尚未实现法典化,在合同法中的规定亦不明晰。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又有一定局限,时常出现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错位调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现存的制度困惑,以相互独立说为理论指导,提供制度性建议。在承认传统雇佣契约和劳动合同差异的基础上,我国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其民法典中关于雇佣契约的相关规定。在未来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或合同法的修改中,适当增加有关雇佣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弥补在劳动法之外大量不属于劳动关系且又无法为传统的有名合同所调整的这种雇佣关系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只能依靠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来决定如何适用。
同时,劳动关系理论的快速发展也给雇佣关系带来反向的借鉴意义,使雇佣关系更好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劳动关系在坚持国家管制与劳企自治并重,而雇佣关系则应当坚持意思自治基础上的适当强制。并且,该种强制应当并不具有普遍性和社会福利性。简而言之,劳动和雇佣应当“守好自己的边界和底线”。
四、结语
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法律调整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一直是热点研究对象和焦点问题,直至目前也尚未形成通说。对于雇佣关系的准确界定,可以给劳动法理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它可以作为民法和劳动法的桥梁与纽带,为两类法律关系架起了“平台”。
实践中,雇佣关系立法处于空白,仅有极少数的司法解释和法院的裁判指引是远远不够的,雇佣法律关系中的实践问题越来越多。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清楚界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关于雇佣关系的立法漏洞所带来的遗憾,更能为雇佣合同的民事立法提供理论依据与价值参考。同时,二者关系的准确界定,亦能够给劳动关系借鉴雇佣关系理论带来便利。
——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