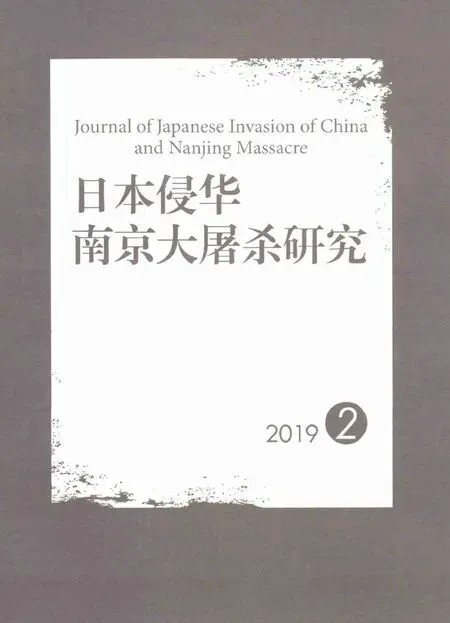田村泰次郎战争小说中的反思与局限*
李 敏 王振平
日本小说家田村泰次郎(1911—1983),出生于日本三重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法文科,大学期间就开始创办杂志,进行文学创作,曾多次到中国旅行。他于1940年4月应征入伍,同年11月被派遣到中国山西省辽县,后被分配到阳泉的旅团司令部宣抚班[注]日军在占领区从事“宣传”“抚慰”以笼络民心的部门。。日本投降后,田村及其部队在保定市被解除武装,随后被押送到北京丰台的日军战俘营,1946年2月被遣返日本。回国后,田村重拾文学创作,其以“肉体文学”享誉文坛。战后,田村历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日本笔会副会长等职。1952年,他代表日本赴法国尼斯参加国际作家笔会;1956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28届国际笔会;1965年,以文艺家协会代表身份访问苏联,一直活跃在文坛。
田村的小说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也几乎被文学界遗忘,因为人们认为他的作品是无稽之谈,而他本人也被视为风俗作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池田浩士曾替他鸣不平,认为他“受到了不该有的轻视”。[注]池田浩士『文化の顔をした天皇制』、社会評論社、1986年、90頁。近年来,为田村重振名声的潮流已经涌现。2008年,研究田村作品的第一部专著《田村泰次郎的战争文学》在日本问世。[注]作者为尾西康充,他还著有『戦争を描くリアリズム——石川達三·丹羽文雄·田村泰次郎を中心に』、大月書店、2014年。中国也有人研究过其小说《蝗》。[注]于长敏:《“蝗军”和“女人”的证明——评田村泰次郎的战地小说〈蝗〉》,《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年第1期,其主要对小说《蝗》进行探讨,对其他个别小说也有概括介绍。另外于长敏指导的吉林大学耿启艳的硕士论文《肉体文学中的性与欲望》(2014)从“女性”的角度分析了田村的多部小说。有日本学者认为,田村“刮起了一个时代的旋风,他不只是在写风俗小说,他是向掌握时代话语权的人果敢地投以飞镖的作家。”[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5』、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年、220頁。还有日本史学家“直接将田村的战争小说作为‘史料’来引用”。[注]濱川勝彦「田村泰次郎の戦場小説——「肉体の悪魔」を中心に」、『丹羽文雄と田村泰次郎』、学術出版会、2006年、201頁。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盛赞田村的《春妇传》《肉体的恶魔》等战争小说,直言“他的一系列著作与贫血的战后文学不同,十分准确地描写了那个时代。”[注]鈴木昌司「田村泰次郎文庫の日記と書簡」、『丹羽文雄と田村泰次郎』、346頁。近年来,田村的战争小说在日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专著、论文等不断涌现。
田村的思想轨迹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变迁。青年时代,他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撰写小说,经办左翼杂志《人民文库》,入伍前撰写过为日本侵略战争歌功颂德的文章,战后集中创作小说。田村的战争小说虽不及其通俗小说数量多,却是他文学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战争文学创作沿着战争亲历者、见证者、反思者的轨迹,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历时30多年。田村通过小说揭露了日军森严的等级制度、军国主义的虚伪、日军的恶行和荒淫无度。但他也难免受到民族传统、时代观念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在作品中暴露出其认识的局限性。
亲历者的告白:“真情”流露
田村在中国大陆度过了5年多时光,重返故土后百感交集,于日本战败初期创作了大量战争小说。他返回日本的第一年即1946年,创作了《肉体的恶魔》《饥渴的日子》《回故国》[注]这部小说本应发表在《小说》创刊号(1946年11月)上,但因未通过检查,没能发表。《女人的诉说》,翌年发表了《死于冲绳》《春妇传》《太行山之画》《栏》《雾》,随后又推出了《现代诗》(1948)、《苍白的胳膊》(1948)、《雁归来》(1948)、《将军》(1949)、《途上》(1949)、《大岛》(1949)、《鸟瞰图》(1950)、《夜晚队长》(1950)等小说。这些小说多是他根据在中国的实际经历创作,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有的甚至被认为是真实故事而被当成史料。小说将其执着恋情、悼念战友、痛恨军官、怒叱军国主义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执着恋情 对恋情执着的代表作是《肉体的恶魔》,讲述了佐田(田村的化身)与中国八路军女战俘张泽民的恋情。张泽民的思想在灵与肉的挣扎中输给了肉体。《肉体的恶魔》是田村战后第一部作品,颇受赞誉,成功打响了复出的第一枪。《栏》为《肉体的恶魔》的前奏,通过一对冒充夫妇的抗日大学学生被俘后的经历,描写了自己与张泽民关系的进展。田村泰次郎第一部“慰安妇”小说《春妇传》是日本战后最早的“慰安妇”小说。故事中的朝鲜女性春美,为忘掉恋人对自己的背叛,自愿投身慰安所,在那里她受尽欺辱,后爱上一个传令兵,最终两人双双殒命。战后,田村多以“肉体文学”表达其文学观和战争观,而他肉体文学的表现形式多是对男女性关系的赤裸描写。刚刚回国的田村,依旧带着战场上的性体验,他借中国女战俘和朝鲜“慰安妇”表现自己的爱恨纠葛,扭曲女性的道德与理性,发泄自己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委屈,却没有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自责与反省。
悼念战友 田村在《饥渴的日子》《回故国》《女人的诉说》《死于冲绳》《太行山之画》等多部作品中描写了对战友感怀之情。田村悼念战友的原因,一是出于对战场上士兵的同情。士兵在军官盲目指挥下,在力量悬殊之际还继续出击,做无谓牺牲。在战场上,生病的人被随便放在土炕上,无人照顾,生命垂危,“连轰走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年、215頁。士兵还被灌输“不但要歧视敌人的生命,还要歧视自己的生命,否则就无法赢得战斗”[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304頁。的思想,以致许多重伤者都被自己人杀死。二是对自己苟活的事实感到歉疚。战死士兵的家属向他咨询士兵死前情形,他觉得对方的眼神里充满了“你们竟然活着出来了啊”[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134頁。的憎恨,而且为了逃命,他们甚至顾不上处理死者的尸体,“遗弃了包括队长在内的多名士兵的尸体”。[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93頁。回国后,他每每想到此处,都会产生“自我厌恶”[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92頁。的心理。战争后期,田村所属的第六十二师团被派往冲绳,几乎全军覆灭,而兵役期满的他被编入第十二野战补充队,阴差阳错地保全了性命。从中国遣返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和母亲去给亡父扫墓时说,“如果我去了冲绳的话,也得进这里(墓地)了”[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126頁。,“还不如死了呢”[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127頁。。没有去送死,本该庆幸,然而却成了他的心病。这也体现了战后以田村为代表的日军士兵的受害者心理。
痛恨军官 日本军队等级森严,暴力和私刑屡见不鲜。士兵不仅要绝对服从,而且要承受各种虐待,军官不把士兵当人看,随意打骂。田村指出,日本军队的缺点之一就是“军官拥有特权,士兵没有,等级差异悬殊”[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23頁。。《春妇传》中的三上就是底层士兵的鲜活写照,他受尽中尉虐待,却决不肯违逆上级,以服从为天职,将日本士兵的耿直和愚忠发挥到了极致,而虐待他的中尉则花天酒地、残忍暴虐。在《将军》中,本田中将家世显赫,虽生于武家,但跟其他粗鲁的军官不同,有贵公子姿态。陪他“切磋”俳句的上等兵小西跟他交情看似很深,但一旦小西穿着邋遢去见他,他便原形毕露,摆出将军架子,狠狠“教训”小西,甚至小西战死他也毫无所动,揭露了高级军官自以为是、虐待下属、毫无人性的丑恶嘴脸。对于军官的变态心理,正如《夜晚队长》中高级军官向其他军官训话时所言,“如果担心部下的生命就没法打仗,士兵只要花上一钱五厘,要多少就能买多少。”而这“一钱五厘在战前只是一张明信片的价格”,[注]田村泰次郎「夜の部隊長」、『小説新潮』1950年7月号、179—180頁。士兵生命被视为草芥。在《现代诗》中,一个官至参谋曾经趾高气扬的军官复员回国后,为了推销保险,对自己战争期间的情妇奴颜婢膝,甚至学狗叫。对军官在战争中和战后两副嘴脸的形象刻画,田村无情地嘲弄了特权阶级,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对战争的眷恋和对自己战后境遇的失落感。
怒叱军国主义 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在《春妇传》中多有体现。小说中两个慰安所的名字分别为“日出馆”(日の出館)和“君之屋”(君のや),看上去很容易联想到日本国旗“日之丸”和国歌“君之代”。[注]于长敏:《“蝗军”和“女人”的证明——评田村泰次郎的战地小说〈蝗〉》,《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年第1期。用慰安所的名字隐含代表国家的“国旗”和“国歌”,田村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暗喻的方式,表达了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上等兵三上真吉死于自杀,然而军医开具的死亡报告却是“因伤口化脓导致急性肺炎”。[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10頁。这些细节无一不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虚伪本质。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这次战争日本凭借武力获得胜利,也无法以和平的手段维持下去”。[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21頁。战败回国,看到曾经大肆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和亚洲解放论的人翻弄股掌,转而批判战争的罪恶,使他觉得“受到欺骗”[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23頁。,感慨万千。
日本战败初期,田村大肆宣泄情感,真切地执着恋情、悼念战友、痛恨军官、怒叱军国主义,这四大特征成为田村战争文学的主旋律,贯穿其一生。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有男女情事,多部小说一边揭露战争的罪恶,一边感怀战友,对军官、军国主义的批判更是俯拾皆是。他说要将战争期间的事情“坦白出来,等待法律的审判”。[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23頁。话虽如此,但他很少揭露日军暴行,一直在执迷不悟地感怀战友的献身精神。他认为,“虽然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从热爱和平的国际道义来看,是决不能原谅的。但被卷入战争,为国家和民族勇敢地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难道应该同战争目的一起被否定吗?”[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136頁。可见,田村否认战争,是因为他看到了日军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毫无人性的军纪、战友的惨状和战后初期日本的积贫积弱,他并没有从被侵略国家的角度反省战争。其实,这种思维不独属于田村,“终战时的日本人,当然是指大多数日本男人,无人不对帝国军队的劫掠暴行有所了解”,但“日本人首先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痛和内疚所压倒。”[注][美]约翰.W.道尔著,胡博译:《拥抱战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71页。因为悲痛和内疚,田村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军国主义和军官,然而他同时却试图用扭曲的男女恋情掩盖战争的残酷,美化战争。
见证者的揭露:良心发现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实施军事占领,直至1952年4月。田村曾提到,“在被占领的时期,我感到头顶上被东西遮着”,“呼吸困难”。[注]田村泰次郎『蝗』、新潮社、1965年、228—229頁。占领期结束后,日本人从被奴役的心态中解放,加之朝鲜战争的“特需”带来经济复苏,日本人生活状况逐渐好转,田村对战争的认识也渐趋全面和客观,开始思考“加害者”的责任。此时,他的战争小说风格有了重大转变,从战败初期主要执着恋情、悼念战友、痛恨军官、怒叱军国主义,转至大胆揭露日军对中国人的罪行,尤其着重书写对女性、老百姓、年轻人的伤害。
女性的灾难 在《有裸女的部队》(1954)中,主人公“我”于二战结束后第十个年头的某一天,说服妻子去电影院看一部拍摄于中国山西省的名为《将军、参谋和士兵》的电影。 电影里的场景勾起了“我”对战场的回忆。山胁队长率领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无度,甚至强迫父女相奸,兽行累累。在一次扫荡后的行军时,“我”受命去联络山胁部队。时值寒冬,日军冻伤患者频出,“我”惊奇地看到山胁部队行军队伍中的每个小队中间都夹着一个一丝不挂、浑身鸡皮疙瘩,冻得如同蜡像般的中国姑娘。一个下士吼叫着:“要是想抱姑娘就别磨蹭,看着光溜溜的姑娘,向前冲!”[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4』、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年、24—25頁。像是姑娘母亲的老太婆扑上来哭喊着恳求放过女儿。一个军官一脚把她踢翻在路边,只见山胁队长弯腰抱起一块西瓜大小的石头向大声哭喊的老太婆砸去,一声惨叫撕裂了山里的空气,“老太婆的头被砸得粉碎”,“乳白色脑浆缓缓流在冰冻的土地上”。[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4』、25頁。田村的这段描写令人毛骨悚然,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却并非虚构。据与田村同属一个部队的日本老兵近藤一所述,他们所在的部队确实有在部队中带有裸体女人以激励士气的事情。“近藤一部队的前川中队长是从士兵升为大尉,并有希望进一步升职的男人。在讨伐所到的村庄,他让被轮奸的女性只穿着鞋子,全身赤裸着和士兵们一起行军在山道上。女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但士兵们将脆弱的孩子扔下了山崖,女人立刻追了上去,自己也从山崖上跳下去了。”[注][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主编,赵金贵译:《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可见,田村笔下的日军兽行并非空穴来风。战争带给女性的灾难罄竹难书,这些灾难在田村笔下陆续出现,如《一种死》(1955)中的士兵伊势田大肆奸淫,《红帆下》(1955)中的新兵新海,“进了村子就到处追女人”,[注]田村泰次郎『戦場の顔』、講談社、1958年、136頁。《青鬼》(1956)中的八木岗准尉也是强奸狂人,“好多姑娘都遭了他的毒手”。[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313頁。写实性描写将日军对中国女性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
老百姓的灾难 在《有裸女的部队》中,田村指出,在中国战场上,“老百姓这个词对日军而言没有任何人格的意义,他们和野狗、蚂蚁毫无区别。在长期战争中,被日军杀死的老百姓,估计要比战死的中国士兵还多”,甚至还有“公然杀戮老百姓的军令”[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4』、20頁。,而且前线士兵们传说,“战区范围内所有的村落要统统烧光,连一条狗也不许留下。日本军队成了嗜血成性的魔鬼军队”。[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4』、21頁。《一种死》(1955)中的一等兵伊势田忤逆军官、怠慢军务、无视军规,得不到晋升,他在一次突袭中被射杀,部分骨灰被随便放在一个士兵的饭盒里。骨灰到了铁路沿线的县城后受到日本居民的隆重“接待”,摇身变成被追悼的“英雄”。实际上,这位战死的“英雄”却无恶不作,他残害无辜百姓、强奸妇女、掠夺财物,干尽坏事。《青鬼》中被誉为“鬼神”的八木岗准尉将日本军官两面三刀、八面玲珑、凶残至极的特征暴露无遗。他作恶的方式十分残忍,变着花样砍人、杀人,不用说俘虏,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一次他非常残忍地踩死了一名俘虏,还让狼狗咬死了两名俘虏。日军把他奉为“超人”和“神秘的英雄”,对他十分敬畏,而当地居民把他视为恶魔,十分恐惧。除了残忍,他还拼命讨好上级军官,献尽媚态。他的下属别府军曹向“我们”透露,他其实是个胆小鬼,真正突击的时候,不见他踪影,突击结束了,他才从后方冒出来,“他杀的不是俘虏就是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313頁。《战场的面孔》(1951)中,一个日本兵看似好人,可就是这个“好人”,却能心安理得地将被日军强征的生病苦力杀死。这些描写充分暴露了日军官兵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犯下的滔天罪孽,可谓残忍至极。
年轻人的灾难 《年轻人》(1955)讲述的是战友冲绳人普天间忠义(在军队里当翻译)的孩子普天间正夫偷渡到日本本土学习,遭到女朋友父母歧视的故事。普天间正夫的经历使作者联想到被日军俘获的一个十八九岁的中国青年。这个青年是河北保定人,要偷渡黄河,跑到非日占区求学,因此被视为有“强烈抗日思想”,受到日军的折磨,但年轻人毫无屈服之意,正义凛然。“日军不分中国士兵还是普通民众,只要对他们表示反感的人都是敌人。”[注]田村泰次郎『蝗』、231頁。青年多次逃跑未遂,终被日军斩首示众,斩断他头颅的,正是蹩脚翻译普天间忠义。田村感慨道,这个青年冒着生命危险渡过黄河,不过是想在民族之魂未被扭曲的地方勤奋学习而已。在喝咖啡时,田村甚至认为浓浓的咖啡就像中国年轻人体内流出的红色血液,令他久久不能释怀。这些描写,都表现出田村人性的善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遭受残害的他都同情;不管是他的战友还是敌人,无恶不作的他都痛恨。
这一阶段,田村大胆揭露日军官兵在战场上的兽行,尤其是日军对中国女性、老百姓、年轻人的戕害。这些揭露之作,虽不及武田泰淳的《审判》(1947)、堀田善卫《时间》(1953)、远藤周作《架着双拐的人》(1958)等战争小说广为人知,却是日本侵华罪行证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盟军占领期结束及朝鲜战争给日本的经济复苏带来了机会,战争的阴霾似乎已经散去,但曾经的事实、一幕幕人间悲剧,在田村的头脑中始终挥之不去,成为他心中无法逾越的藩篱。于是,田村一边揭露,一边找寻救赎之法,并为曾经的罪行辩解。
反思者的救赎:兽性本能
战败初期田村就有所反思,认为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罪恶的”。[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223頁。在《途上》(1949)中,他描写了战争带给一个士兵的心理创伤,战场上的残虐行为如影随形,使他复员后无法融入都市生活,以致入室抢劫,成了一个通缉犯。在《远征幻想》(1954)中,一个复员老兵无法回归社会,成为流浪汉,居住在墓地,腰间还藏匿了一枚手榴弹。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觅食”,幻想自己踏上了征途。田村还在多部小说(包括风俗小说)中,将复员老兵描绘成罪犯,甚至是杀人犯。他在这些作品中对复原士兵种种恶行的原因仅轻描淡写、浅尝辄止,并未深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一边揭露日军暴行,一边真正反思战争。据说,这是因为“田村于1962年与阿川弘之一起巡游东南亚各地,去了曾经的战场越南,他头脑中在和平年代渐渐淡去的‘战场’又开始复苏。”[注]秦昌弘「肉体文学新論」、『丹羽文雄と田村泰次郎』、298頁。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一边揭露,一边寻求疗伤之法,最终认定了救赎之道,即兽性本能。
“知识分子”化“雄鹿” 在《男鹿》(1964)中,大木户登是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士兵。战争期间他非常残忍地用石头砸死了一名日军掳来的生病的中国苦力(同前述《战场的面孔》中的事件),后在冲绳战役中死里逃生,回到日本后心理变态,无法正常生活,还犯下杀人罪行。他在逃亡中受了伤,在潜逃疗伤期间遇到了一头雌鹿,最终他变成一头雄鹿,随雌鹿归隐。在这个故事中,田村强调在战争期间心理变态的大木户登回国后也无法生存,最终他拒绝为人,化身野兽。可能田村认为,大木户登更适合与兽类为伍。
“皇军”乃“蝗军” 在《蝗》(1964)中,分队长原田带领两名士兵运送五名朝鲜“慰安妇”和一卡车骨灰盒去前线,途经每一个日军驻地时,“慰安妇”都被当作“通行税”,遭到日军轮番施暴。在运输过程中,原田一行人遭到袭击,一名“慰安妇”被炸断一条腿后,被视为“废品”遭到遗弃,另两名“慰安妇”在另一次袭击中遇难。最终运送到的两名“慰安妇”要受到上万名日军的强暴,原田也加入了排队的士兵中,轮到他时,他被“慰安妇”下体内的蝗虫刺痛。整篇作品充斥着“蝗虫”,寓意“皇军”如同虫兽,毫无人性。
“士兵”是“耕牛” 在《地雷原》(1964)中,“我”时任宣抚班长,受同一大学毕业的对共产主义有共鸣的“中尉”之命,“解决”原为日军的一名八路军俘虏。“我”试图努力劝说对方自杀,没有奏效,在门外偷听的“中尉”破门而入,将俘虏击毙。内心不服输的劲头迫使“我”跟中尉一同走在踏雷牛群队伍的前列。日军进入雷区时,让强掳来的耕牛、俘虏以及管理俘虏的部分士兵走在前面,为日军开路。在这个“人牛混杂的奇特敢死队”[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4』、263頁。中,不论牛、俘虏还是士兵都被视为草芥,成为牺牲品。田村利用被掳来充当炮灰的耕牛,暗寓日军士兵的危险与无奈处境。
“强兵”等同“淫兽” 在《黑色乌鸦》(1965)中,吉见节三就职于日本商社,长期处理越南方面的业务,此时恰逢越南战争,他又拒绝了女儿的好友清水京子的主动投怀送抱,这些事情的发生使他开始回想二战期间在中国大陆和在越南战场上,日本士兵为了度过所谓漫长、孤独和倦怠的生活,侵犯当地女性以取乐的经历。田村强调,士兵根本没把这些女人当作母亲或妻子,她们只是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田村不断辩解,只有让自己加入动物集团,才能让自己生存下来,他甚至觉得自己比禽兽更加低劣,而且觉得要想抹杀自己的良心,就必须侵犯她们。然而,所谓的强悍,源于深重的罪孽。最终,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伤及了无辜,并用和歌“受到炮弹伤害的小鸟,在湿地上悄无声息地拍打着翅膀”[注]田村泰次郎「黒い鴉」、『群像』1965年8月、76頁。来表达对受伤害女性的同情。
“勇士”变“恶狗” 在《失去的男人》(1966)中,伊丹忠平和战友太田安次在战场上是完美搭档,他们狼狈为奸,还阴差阳错地受到过表彰。战后,伊丹经营公司成了暴发户,而太田回到村里,成了“瘟神”。两人将战场上的恶习带回家乡,伊丹包养小妾,还跟自己公司的打字员和女事务员发生关系,太田则侵犯村里的女性。曾经的战场“勇士”,回到日本变成了“出轨者”、“强奸犯”。太田向伊丹索要了一只牧羊犬,它不断配种、杂交,最终形成牧羊犬杂种狗群,惹是生非,四处作恶。和平年代的这些恶狗和战争中日军的军犬一样,都是带来恐慌、残害人类的危险因素,暗示了战争中丧失人性的日军,如同恶狗一般,无恶不作。田村大胆描写了士兵在战地强奸妇女的丑恶行径,并通过露骨的讽刺手法,刻画了部分士兵重返故土、回归生活后的生活与病态心理,暗指一朝有了野兽本性,便终生兽性难泯。
对于日军在战场上的暴行,田村一直在找寻原因,他回国后不久就指出,“故乡和战场不在同一个世界,如果战场是现世的话,内地(指日本国内——译者注)就是彼世”,“不论哪个人,在某个瞬间都可能变成非人类。”[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2』、135—136頁。后来田村在《肉体即是人类》一文中坦言:“我见证了拥有正经‘思想’、不可一世思想的人变成野兽的过程。我自己也是野兽中的一员。”[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5』、188頁。田村坚持“兽性”理念,认为“不论多么正常的士兵,在战场上都会变。战场使人如此,战场不是人生活的地方。那里跟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在同一空间”,极端地说,那里是一个“为了活下去,人不被允许是人,也不能是人”[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5』、201頁。的地方。在战场上,士兵会“轻易变身野兽”。[注]田村泰次郎『蝗』、239頁。
田村在战争期间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战场上不允许思考后行动,马上就得行动。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在伦理上意味着什么。”“同敌人战斗,同时也跟自己战斗。杀死自己,也是必要的。”[注]尾西康充『田村泰次郎の戦争文学——中国山西省での従軍体験から』、笠間書院、2008年、44頁。他认为自己“不得已”而形成了分裂的自我、杀人的机器。殊不知,“服从和消极的习性就像利己心的伪装烟幕,起着强化利己心的作用”。[注][日]南博著,刘延州译:《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田村有意遮掩自己成为杀人机器的事实,虽然心有不忍,但良知被军国主义的狂热遮掩,终难避免成为军国主义走狗的命运。田村最终通过“兽性理论”为日军在战场上的行为辩解。在战场上,士兵犹如“蝗军”,类似“耕牛”,等同“淫兽”,人性泯灭。回到家乡,他们变身“恶狗”,无恶不作。他们无法融入社会,最终化身“雄鹿”,彻底归隐,这是田村所能为他们找到的最好结局,甚至是一个让人感到“神圣”[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4』、169頁。的结局。这是田村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日军兽行的认可和美化。
虽说田村找到了救赎之法,但他依旧无法释怀。他在辩解、认可和美化的过程中,强调自己“与众不同”。《在包围中》(1967),主人公河野班长拼命阻拦日军屠杀从通“敌”村落中强掳来的村民,极力“保护”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国女俘虏李玉华不受其他日军的私刑与强暴,怒斥奸淫无度的日军为“野兽”,但这只是源于他抱有女俘虏对他说了“我爱你”的错觉,非常“想展示日军人性的一面”。[注]田村泰次郎「包囲の中で」、『オール読物』1967年8月、193—194頁。田村不同意强奸后杀死对方,认为已经施暴了,“就没有必要杀死”。[注]田村泰次郎『田村泰次郎選集4』、22頁。他走的只是温情主义路线,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田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内消解战争创伤。他的救赎方式是拒绝为人,化身野兽。他带着无处安放的伤痛感叹道:“谁都犯过罪,都背负着深深的伤痛”,[注]田村泰次郎「深い傷の中で」、『オール読物』1967年1月、205頁。坦然接纳了过去的罪行。
1966年,田村在巴黎遭遇交通事故,1967年患了脑血栓,之后他的战争小说数量大幅减少,仅发表了《我快乐的阵地生活》(1973)、《充满爱的远方战场》(1976)等少量作品。小说中虽然不时出现“扫荡”“强征”“强奸”等场景,但主要描写了战场上的逸事、士兵与中国女俘虏的爱欲纠葛等,没有实质性的思想延伸和对战争更为深刻的反思与剖析。
结 语
通过田村的文学轨迹可知,战败后他没有从战争困境中走出,倾心于描写战争、战场。他既想描写战争的真相和纾解心中的战争情结,更想揭露战争的残酷和为日军在战时成为恶魔寻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战败初期他品味恋情、怀念战友、痛恨军官、怒叱军国主义,之后开始揭露和批判日军的残忍和暴虐,表达了对遭日本侵略、残害和屠杀的中国人的同情与反省,也表达了对朝鲜“慰安妇”和日本“慰安妇”的同情,在文学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他反思为何日军会在战场上如此荒淫无度、惨无人道?最终依托兽性本能理论,将责任归结为战争和战场,认为他们在战争中作恶是因为善良的人性受到了天然的兽性驱使,而这样的解释和理解更容易让他心安理得。虽然田村也意识到了自己“将责任归咎为战争的狡辩”的虚伪本质,但他强调那是“在战场上学到的”,[注]田村泰次郎「最低の自画像」、『小説現代』1965年10月、371頁。没有从个体角度真正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没有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剖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之源,日军荒淫残暴的不仁之根。
相比那些坚持否认日军暴行的人,田村可谓良心作家,但也必须承认,他对于战争和日军暴行的认识具有局限性。他为日军的残暴行为找到的,只是他认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并没有找到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受“肉体文学”观念的影响,他在战争小说中加入了过多的肉欲和恋情,这些肉欲和恋情,扭曲、偏离了女性正常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污蔑了女性的人格与人性。对日军的暴虐行为,田村竭力强调战争、战场这些客观因素,为其暴行减罪。他把战场理解为“兽性”培养所,目的就是想让自己对日本兵的兽行心安理得,让读者接受和理解他们的兽行,对侵略者的战争暴行少一丝罪恶感。
这种兽性、本能的理论并非田村独创,翻阅战后日本文学就会发现,根据战争使人性扭曲、战争使人变成魔鬼的理念创作出来的作品比比皆是。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性不受兽性驱使并战胜了兽性。正如聂珍钊所言,从伦理意义上说,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它们共存于每个人身上。“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一旦人身上失去了人性因子,自由意志没有了引导和约束,就会造成灵肉背离。肉体一旦失去灵魂,就会失去人的本质,只留下没有灵魂的人的空壳。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依靠本能生存,没有伦理,不辨善恶,与野兽无异。”[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坛在主流上没有站在世界人道主义立场对他国受害群体进行及时的文学观照”,[注]周异夫:《战后初期日本文坛的战争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甚至“在战后二十一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层出不穷,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注]李德纯:《战后日本文学史论》,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田村文学虽不乏侵略者的加害视角,但局限性亦极其明显。田村文学作为“证言”,既揭露了日军对中国民众的蹂躏,又表现了日本人的错误认知。因此,通过田村文学再次认识侵华战争,认识日本的战争反思文学,了解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田村改造“解压”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