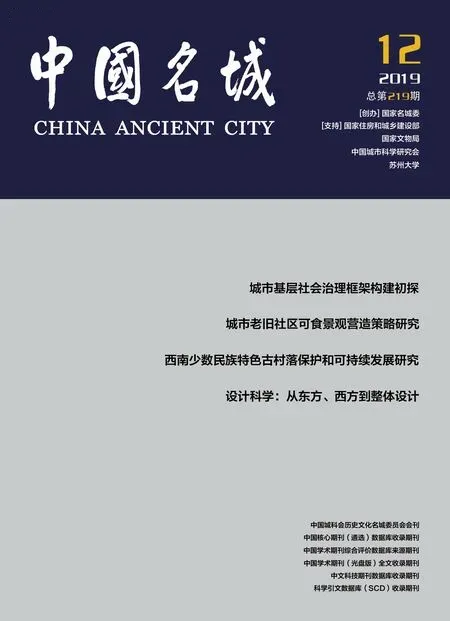淮安城的城墙、城门与空间结构*
王聪明
导 语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城”与“市”结合的存在形态。《说文》中载:“城,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即“城”具有容纳居民的功能,“市”为物品交易的场所。对于中国早期城市来说,“城”的意义明显大于或早于“市”,这种意义主要通过城墙的修筑得以彰显。城墙将居民围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范围内,带有强烈的军事防御需要,这种修筑城墙的观念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人说:“在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或者说,不筑城墙的城市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算不上正统的城市。[1]不过近年学者经过举例论证,得出从唐宋元直至明初,“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圮状态可能是城市城墙常态”的观点,对既有的“高度强调城墙在城市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其象征意义”加以反思。[2]即便如此,似难忽视城墙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城墙将城市围合成封闭的空间,而城门的设置则提供了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通道和窗口,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重要层面。淮安城(今淮安区),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长期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历代均较重视对其修筑,并且形成了三城鼎峙的独特空间结构。本文尝试对城墙的修筑与兴废、城门的设置及其名称等问题进行考辨。
1 东晋山阳城的始建
淮安城的修筑开始于东晋时期。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记载:淮安城“初无城郭,东晋安帝义熙中,始分广陵立山阳郡,乃于此地筑城”。此处仅说东晋义熙年间,并未具体到某一年。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楚州总论”引《宋书》载:“安帝义熙元年,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三县,为山阳郡”。此处说义熙元年(405),射阳县废置,改立山阳郡,并立山阳县。不过清代淮安地方学者范以煦对此辨析说:“今宋书无此文,惟领县及安帝立县,合其云省射阳及元年并误”,他认为义熙元年,设置山阳郡、县记载有误,并援引义熙二年(406)诸葛长民自山阳“还镇京口”之事加以佐证。史载:“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城池崩毁,不闻鸡犬”,范以煦据此认为“假令元年筑城,何至二年遂崩毁,且亦不得为坚矣”。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关于山阳郡、县设置的时间,另有义熙九年(413)的说法,这一说法源自《太平寰宇记》:“晋义熙九年省射阳县,置山阳郡,属徐州,又立山阳县以隶焉”,[3]同书记载互有龃龉,必有错讹之处。其校注者王文楚引《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地理志书,记山阳郡、县初设于义熙七年(411),认为义熙元年之“元”当为“九”或“七”之误。由此仍很难断定,是义熙七年或九年,初设山阳郡、县。又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海陵、山阳二郡”,可知山阳郡、县始置于东晋义熙七年。
无论是义熙元年、七年或九年,我们只见到设置山阳郡、县,并未见及修筑城墙的表述,不过设置郡、县,同时兴筑城墙,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淮安城的修筑时间尚可向前推移。前述范以煦认为义熙元年(405)为筑城之始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城墙可能先于郡、县而建。彼时的山阳,与“鲜卑接境”,“此番十载,衅故相袭”,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战状态下,山阳城的崩毁亦属正常。《宋书》中载:义熙年间,“鲜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阳、淮阴诸戍,并不复立”。既然有山阳戍的说法,证明当时山阳可能已筑有城垣或类似城垣的防御设施。只是这些城防设施处于废隳的状态,因此诸葛长民才从山阳退至京口据守。又据《晋书》卷八《哀帝纪》,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载:北中郎将“庾希自下邳退镇山阳”,《水经注》亦谓山阳“城本北中郎将庾希所镇”,[4]所镇之地当有凭险可守之法,因此,可能在东晋隆和元年之前山阳已经筑城。
2 唐代楚州城的城墙与城门
隋唐时期,淮安地区的最高行政单位为楚州,治所位于淮安城。白居易盛赞楚州曰:“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5]可见唐代楚州已筑有城垣。而且,唐代淮安城有重修之举,此由范昭撰、郑萼正书的《唐楚州修城记》碑文可见,为宋人赵明诚所得,其文字被收入其所著《金石录》之中,且由此文可知,重修淮安城的时间为唐上元元年(760)七月。大中十四年(860),楚州刺史李荀对城南门予以局部重修,时人郑吉撰文曰:“楚州新作内城之南门,何以言新?因旧之云也。何以言作?更从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诸侯台门也。何称内城?别于外郭也”。[6]可知,从外观上说,至迟到唐代中后期,楚州城即有内城、外郭的建置。李荀之所以重修淮安城南门,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文中曰:“溯淮而上达于颍,而州兵之益团练者,纚联五郡焉,楚最东,为名郡。疆土绵远,带甲四千人,征赋二万,计屯田五千顷,凡兵、赋、食三者相通也”。从淮河上游直至下游,形成了五处州郡一级的城防重镇,楚州位于最东,对楚州城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而楚州城南门的建设尤为重要,因“南门者,法门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因此,重修城南门寓有为唐朝政权兴兵固邦之意。
虽然原来的南门设置了可供瞭望、御敌的谯门,不过属于简单草创,所设的谯门“卑且陋,但阖两扇,为露棚于前,振军旅焉。露棚不能蔽风雨,亟理而亟坏”。这不符合楚州作为淮东大郡的军事地位,因此李荀对此加以重修。具体来看,“巉然而楼,增以旧五之二焉,划为双门,出者由左,入者由右,夹筑高阜,类观阙而非者九”。由此可知,经过重建,楚州城南门成为双向两道,出城门的人从左面行走,进城门的人从右面行走,既增强了南门的规格与形制,又突出了南门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另外,从“楼增以旧五之二焉”可知,楚州城南门原来就有门楼,此次重修同时对其加以扩建。关于南门城楼的名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乾隆《淮安府志》等文献中,均记载为宴花楼。唐朝赵嘏有《楚州宴花楼》诗曰:“门外烟横载酒船,谢公携客醉华筵。寻花偶坐将军树,饮酒方重刺史天。”[7]这首诗在赵嘏《渭南集》中题作《陪韦中丞宴扈都头花园》。据清代吴玉搢考证说:“宴花楼之名仅见于此,韦中丞即楚州刺史韦瓘,扈都头不知何人”,他认为宴花楼应该是扈都头花园中的楼阁。吴玉搢还引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对宴花楼为南门楼的说法提出异议:
大中之末去会昌不二十年,岂有会昌中有楼屹然,可以宴会,而大中中即止存露棚之理?即或圮坏,郑记宁无一语及之?此以知宴花楼必不为南城楼也。[8]
这一观点当属的论。其实,郑吉记文中已经述及南门楼的名称,即“命之曰却敌”,并且在城楼中“卷斾援枹”,以求达到“以谨击柝,以严教令,以壮都鄙,以张军声”的目的。郑吉记文中还说到,大历年间,将作少监李阳冰曾经客游楚州,“因大署州门,昔人措之于西偏,至是公易之于南门,以表揭远近”。可见,大中年间,李荀将原来书于城西门上的题额,改易到南门之上,至于南门名称并未记载。另外,关于唐楚州城门的名称,见于对北阊门的记载,张祜曾两度陪韦舍人游宴于此,[9]恐北门即名为阊门,城门附近为楚州城的形胜之地。
3 南宋边防战事与楚州城的修筑
南宋时期,楚州与金元诸族交壤,动辄兵锋相向,遂成军事重镇,故地方官员和守将屡次主持修城事宜。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三《代抚州陈守奏事》中记载:“淮东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有城与无城异耳。国家南渡以后,大筑襄阳、楚州两城,方其经画之初,岂能无劳民伤财之患?设使两城不筑,前者虏人得以据吾之要害。”可见,宋室南渡之初,即着力兴修楚州城,将之作为边防重镇加以建设。建炎四年(1130),赵立担任楚州知事,其间遭遇金军的猛烈进攻,史载:
会金左监军昌亲率数万人围城,攻其南壁,立自为旗头,引众出战,相持四十余日。至是,敌以炮击三敌楼,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为鹿角,以槎其破处。而下修月城以里之,月城之中实以柴薪城之,内为熔炉。敌自月城中入,立命以金汁浇之,死者以百数,敌不能入,遂退守孙村大寨。[10]
宋、金交战相持达四十余日,足见楚州城的坚固难攻。金兵以楚州城南壁为突破口,“以炮击三敌楼”,可见城南门上当有三座门楼。知州赵立又兴修月城,即瓮城,以加强守备,月城为粮草储存之地,并以此作为抗御金兵的第二道防线,成效益著。然而金人并未就此罢兵,建炎四年夏四月,完颜挞懒“围楚州急。赵立命撤废屋,城下燃火池,壮士持长矛以待金人登城,钩取投入火中。”时值“兀术将北归,以辎重假道于楚,立斩其使。兀术怒,设南、北两屯绝楚饷道”。[11]金兵既“绝楚饷道”,楚州城开始出现粮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戊辰条云:“初有野豆野麦可以为粮,后皆无生物,有凫茈芦根,男女无贵贱斸之。后为水所没,城中绝粮,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楚州城最终陷于金人。
绍兴元年(1131),宣抚使刘光世收复楚州。绍兴五年(1135),都督张浚抵达镇江,召见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亲谕上旨,使移屯楚州”。[12]楚州城“屡经兵革,地皆榛棘”,[13]世忠锐意振兴军务,“抚集流散,通商惠工”,楚州再次成为重镇”。[14]世忠守淮期间,当亦增修淮安城。宋孝宗年间,有改筑之议,时李大性任楚州通判,他认为“楚城实晋义熙间所筑,最坚,奈何以脆薄易坚厚乎?持不可”。[15]李大性所谓晋时所筑之城,为淮安旧城。南宋时期,楚州城最大的变化为乾道七年(1171)新城的修筑,周孚撰修城记文曰:
光州观察使陈侯敏自高邮往代之,侯既至郡,览视河山,知天子所以防患之意。而又知役之大费之巨,而人不可久劳也,乃计工庸差物宜,裁其费之冗者,谪其卒之不中程者。……。而城以成,其长四千二十有三步,其高二丈有七尺,濠之广如城高之数。而杀其一为门,六水门、二楼橹,机械之用毕具,沈沈翼翼,视旧之功盖有加焉。时某适从事此邦,而侯求文为记,某尝从侯而登周览四向矣,盖淮东诸郡,其视以为喉襟者,莫逾楚也。[16]
所谓“楚州新城”,并非指旧城翻新,而是在旧城之北另筑一城,楚州新城设有一旱门、六水门、两座城门楼。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材料还涉及新城的规模,城墙高2丈7尺,周长4023步,另外设有濠沟,其宽为2丈7尺,可见楚州新城开始重视对周遭水域的利用,增强作战防御能力。陈敏所筑的新城,“北使过者,观其雉堞坚新,号‘银铸城’”,足见其城墙之坚实。至此,楚州形成了旧城、新城并峙的“双城”格局。元人王恽有《淮安州》诗曰:“平野围淮甸,双城入楚州。喉襟开重地,鼓角动边楼”,[17]此“双城”即指淮安旧城与新城。南宋后期,应纯之、赵仲等地方官员又曾修缮城池,以御外侮。
关于南宋时期楚州旧城城门的设置与名称,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舆地纪胜》中记载:满浦闸,在朝宗门外西北四里,可以推断朝宗门为西门或北门。南宋楚州太守应纯之曾开凿管家湖“以教舟师”,[18]并在管家湖上筑水教亭。而管家湖又称为西湖,水教亭位于望云门外,则知望云门必为楚州城西门,朝宗门为城北门。临运河处有北津亭,位于朝宗门外,亦可证明朝宗门为北门。又有南津亭在观风门外一里,可知观风门为旧城城门之一。根据正德《淮安府志》记载,观风门应为东门,南门名为迎远门。元代楚州城的基址方位、城壁楼橹、空间结构等基本未变,仍为旧城、新城组合的双城格局。
4 明清淮安城墙的修筑与演变
4.1 旧城
元至正年间,江淮地区战乱频繁,作为各方军事力量角逐的据点,淮安城受到驻守将领的重视,曾对城墙加以修筑,但由于驻将变更,仅对原来的土城进行局部的修整,以加强军事防御的能力。明朝建立之后,淮安城成为府级治所,行政衙署相继设立,城墙的修筑亦随之展开。正德《淮安府志》卷五《规制一·城池》载:旧城“国朝累增修筑,包以砖甓,周置楼橹”。可见明朝前期淮安旧城经历多次重修,并且通过设置城楼等建筑使得城防体系逐渐完备,更重要的是,淮安城在原来土质城墙的外面,用方砖加以包砌,实现了由土城向砖城的转变,此为淮安城墙修筑史上的重要阶段。就旧城墙规模而言,其城墙高30尺,周长11里,东西510丈,南北525丈,这是目前获知关于淮安城墙高度与长度较早且精确的数据,另外东西、南北长度相当,接近于方形。明清时期,淮安旧城的城垣与城楼虽历经维修,不过其城郭形态在总体上并无改变。
4.2 新城
淮安新城,位于旧城北一里许,即古代的北辰镇。前文已述,淮安新城的修筑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不过元代可能处于废隳不修的状态,直至元末,张士诚的属将史文炳驻守淮安,对新城再次加以整修,当时仍为土质城墙。洪武十年(1377)大河卫指挥使时禹复增筑城墙,并且“运宝应城甓甃砌坚完”,[19]新城防御功能愈益增强。新城高28尺,周长7里20丈,东西326丈,南北334丈,可见无论是高度、长度还是周长,比旧城均相差不少。明清时期,新城曾经多次修葺。不过明末以后,新城呈现出衰败景况,这与明末清初的藩镇形势有较大关系,其时刘泽清屯驻于新城,他开府新城期间,连年混战,对淮安地方完全是强盗式的掠夺,在经济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举措与建树,这帮割据势力撤出后,造成了新城的急遽衰败。清顺治十年(1653),谈迁旅经淮安时记曰:“新城如野”[20]。又据流寓淮安的吴江人蒋楛诗曰:
沧桑递变谁与期,蟪蛄朝菌夫何知。我来淮阴逾二纪,乡殊物换星屡移。
卜居新城类村野,垝垣旷土连洿池。东邻父老向余道,此城全盛今非时。
岂无城南韦与杜,锵金鸣玉声华垂。一朝渠师立藩镇,飞扬跋扈生疮痍。
革命迄今遂瓦解,蜃楼海市安可追。更闻黄河咆哮西北郭,于今迁去涟水湄。
废兴消长各有数,旷观身世归希夷。登陴翘首一长啸,吾欲乘风飞上扶桑枝。[21]
此处蒋楛表达出刘泽清屯驻前后新城反差强烈的城市景观,本来是人烟辐辏、商贾鳞集、风气奢华,自四镇骚乱之后,新城则退变成乡村野落、城垣颓圮、市井萧条。嘉、道年间,郭瑗有诗曰:“南介长江北介河,淮阴市上近如何。旧城新了新城旧,旧日新城蒲叶多”,[22]借用旧城、新城名称之对照,较为巧妙地点出了淮安新城日趋颓败的事实。
4.3 夹城
明初,运道行于旧城、新城之间,诸如陆家池、马路池、纸坊头等处,均为粮船屯集之地,后世仍留存屯船坞的遗迹。自运道改由城西,其地多涸为平地。嘉靖年间,倭氛愈紧,淮安地方遂有筑城之议,史载:
欲将西湖嘴另筑一城,又虑财力地势俱有未便,聊将夹城中间联筑为道,一自新城东南角楼起,抵旧城桃花营,一自新城西南角楼,抵旧城北水关,共计四百余丈,比之扬外城之功,不及十之一二,如此则两城相通,粮草兼济,攻守有备矣。[23]
负责夹城修筑工程的为漕运都御史章焕,不过修筑联城提议初始,知府范槚力言不可,曰:“淮安故两城,新城者,南宋时筑也。时乱后,漕院以多备也,议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遄举之,身为植工,竣,命曰玉带,绘联城图”。[24]可知联城又名玉带城,且绘有城市舆图,惜未传世。所谓联城,即筑东、西城垣,将新、旧城连贯而成,其中东城垣自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西城垣自旧城西北隅接新城西南隅,分别长256丈3 尺、225丈5尺。至于高程,初建时“因砖土骤高,虑不经久”,仅有一丈四五尺左右。万历二十一年(1593),“倭奴愈横,乡官胡效谟等议请加高”,“始与新、旧城平”。[25]
夹城的修筑,对于抵御倭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也造成城市景观的衰败。明代张尔调《远心园怀古》诗曰:“东北隅通万斛舟,居人鳞集纸坊头。筑城改运成荒圃,辟地为园得倚楼。伍相祠连水月寺,射阳湖接菊花沟。无边陈迹俱难问,惟有听莺载酒游。”[26]可见至清代前期,不仅伍相祠、水月寺等古迹悉数湮废,夹城内的张氏远心园亦已隳坏良久,可见彼时夹城景观之一斑。
按照官方追根溯源的说法,巴塞尔表展可从1917年第一届MUBA展览算起,不过,最开始的MUBA并不是钟表珠宝行业展,而是一个各行各业的博览会。
5 明清淮安城的城门
5.1 旱门的设置与变迁
一般来说,城门可分为旱门和水门。根据正德《淮安府志》记载,明代以前,淮安旧城建有五座旱门,分别为西门望云、北门朝宗、东门观风、南门迎远,另在西门稍北处原有清风门,宋元之际被南宋守将孙虎臣堵塞而废弃,因此明代旧城建有四座旱门。这四座城门各有子城与门楼,各门楼最初俱无名称,隆庆六年(1572)改原“城楼”名为“通漕”。后来王宗沐又建举远楼于西门子城上。另置三座角楼,分别为北、西、东南角楼,其中东南角楼“下临龙王庙闸”,后世名之曰瞰虹楼。[27]万历二十三年(1595),倭寇作乱,曹于汴着力措置防御工事,添设四座敌台。其后城门形制与名称基本未变,仅至咸、同年间,四门名称俱改,分别改为东门瞻岱、南门迎薰、西门庆成、北门承恩。
新城共有五座旱门,东、西、南三个方位各有一座城门,北面城墙除设置北门外,另在其西侧建有小北门,各城门初时均无名称。成化十四年(1478),南门城楼毁坏,正德二年,漕运总兵官郭鋐加以重建,同时对各城门命名,分别是东门望洋、西门览运、南门迎薰、北门拱极、小北门戴辰。“门各有楼,惟小北门无”。[28]城上除建门楼外,亦有角楼之设,凡四座,另有“窝铺四十八,雉堞一千二百垛”,东、西门建有子城。清代前期,新城衰败,各城门楼均逐渐毁坏。乾隆十一年(1746),政府拨款重修,较以前更加巩固。此后,新城再次衰败。与旧城更名形成对照的是,新城的名称保持不变。
关于夹城旱门的记载,历史文献多有歧异之处。据天启《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城池》记载,夹城的旱门共有四座,分别是东南门天衢、东北门阜成、西南门成平、西北门天衢。又据吴玉搢《山阳志遗》卷一《遗迹》援引明代淮安人冯一蛟《闲园志遗》记载,夹城四座旱门名称,分别为东北阜成门、西南平成门、东南、西北均为顺成门。乾隆《淮安府志》卷五记载,东南天衢门、东北阜城门、西南平成门、西北天衢门。此后晚清方志文献的记载与乾隆《淮安府志》一致。总体看来,对于东北门与西南门,虽然在个别字眼和顺序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名称基本一致。而对于东南门与西北门,这两门名称相同,不过文献记载有较大差异,即有天衢门与顺成门两种说法。至于为何有两种说法?可能是文献记载本身的舛误,亦有可能是城门名称一度更改所致等其他原因,置此存疑。
5.2 水门的设置与变迁
淮安三城除了设置旱门之外,还设置了不少水门,体现了运河城市的典型特色。淮安旧城建有三座水门,或称水关,分别位于城西南隅、西北隅、东南隅,是为西、北水关以及巽关。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中曰:“西水关旧制可行船入西湖”,亦可“由西水关引湖水入城”,这一旧制延续至明代初年。明永乐年间,这一引湖入城的格局发生变化。十三年,陈瑄依循宋故沙河旧道,“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以免淮河风涛之患,就管家湖筑堤亘十里,以便引舟”。[29]由此漕运水道经由城南而沿城西行,管家湖成为供给漕船航行的主要水源,所以自管家湖中筑堤后,“改建一小闸进水,其制甚狭,由旧城西门稍南数十步穿城下入”,[30]这一形制狭小的水闸称为响水闸,又名上兴文闸,与之相对的则为运河东岸下一铺之南的下兴文闸。
在旧城北门西另有北水关,其设置甚早,北宋欧阳修宦游楚州时,曾“与元均小饮仓北门舟中,夜宿仓亭”,[31]似可推知当时城西北隅的北门已为水关,可通行舟楫。至明代前期,仍可乘坐小舟通于城中。不过因其形制较窄,仅能通行小舟,本来御驾龙舟的正德帝南游至山阳时,“却侍卫,步入城”,[32]这一点在清乾隆帝南巡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六次巡幸江浙,皆过山阳境,每次御舟驻北角楼登岸,乘马入北门,由西门出登舟”。[33]可见北水关仍在使用,而且是城内通往萧湖的主要水行通道,只是御舟体型甚阔,无法通行而已。
明天启年间,在淮安旧城东南隅疏凿巽水关。鉴于南门外的宝带河水“东去之无情”,在“东南巽方凿渠引水入城”,[34]是为巽关或巽洞。其实东南巽关的开凿,更重要的是风水堪舆层面的考量。天启三年(1623)冬天,知府宋祖舜、知县孙肇兴采纳士民公议,疏凿巽关,引宝带河水入城。城东南巽关的修造及与宝带河的连通,不仅形成了淮安城巽亥合秀的水关格局,同时对城市供水体系及水域景观的呈现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宝带河下达涧河,与城市泄洪及东南乡村聚落的农田灌溉均关系匪浅,这也成为地方官府与社会精英主要关注的水利问题。
新城南、北门侧开设水门或水关,据正德《淮安府志》卷首图所示,新城南门稍西处为南水关,北水关则位于大、小北门之间,其中北门水关虽不行舟,但城内河道仍经此注入外围城河。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中说:
北水关在未筑城前为石闸,古邗沟由射阳至末口入淮,石闸即古末口。自北辰堰筑而末口变为石闸,自新城筑而石闸变为北水关矣。
可见,明初重筑新城时,将石闸改置为北水关。这一说法如若不虚,则北水关即为古末口、北辰堰所在,古运道由此达淮。明永乐年间又于新城外西北、东北方向修筑淮安五坝,每遇清江口淤塞,漕运粮船及其他官民商船均经此盘坝入淮,所以在明万历年间黄河北徙之前,新城北门外形成了较为繁盛的城外商业街区。
由于夹城曾有运道经过,多有面积不等的水域分布其间,所以其水关即水门的设置相当重要。夹城修筑工程完竣时,漕运都御史章焕撰写记文,并勒于碑石,至清末碑石仍存于北门子城茶济庵内,内称:“门四,水关称之,关桥二”,[35]可见夹城旱、水门配对而置,各有四座,如东北门曰阜成,旁置水关曰阜成关,西南门名平成,水门亦名平成。不过,东南、西北的天衢门亦为水门,史载:既筑联城,“乃悬空二水门,以便船桅出入,故号其门曰天衢”。[36]必须强调的是,清代前期夹城四座水门中,东南天衢门水关亦称巽关,久已闭塞,不通行舟,而夹城东北、西北方向的两处水关,分别为通向东北涧河、西北关厢的主要关口,由此勾连起城市水利渠道的交通网络。
6 结语
淮安,处于运河与淮河交汇之处,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较早地发育、发展成为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至封建社会晚期,其城市经济更加繁荣。淮安城的空间结构较具特色,为旧城、新城、联城三城鼎峙格局。其中,旧城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南宋时期边防战事吃紧,淮安新城初步修建,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侵扰,将旧城、新城相连修筑为联城,俗称夹城。在政治、军事、交通等因素的作用之下,淮安城的城墙与城门屡经修葺,除旱门设置外,淮安城的水门或水关相当重要,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水利系统。由此可知,早期的淮安城具有浓厚的军事属性,后期这种属性虽仍存在,但明显减轻,更多的呈现为以治水、用水、排水为核心的水利型城市。同时,清代淮安的城墙与城门也处于衰颓、破败的处境,其中以新城、夹城较为严重,旧城的衰败相对较轻,诚如黄钧宰记:“今新、夹二城皆圮,官民商贾全集于旧城”。[37]直至晚清,淮安旧城仍是当地城市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民国以后,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互相融合下,淮安城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城市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