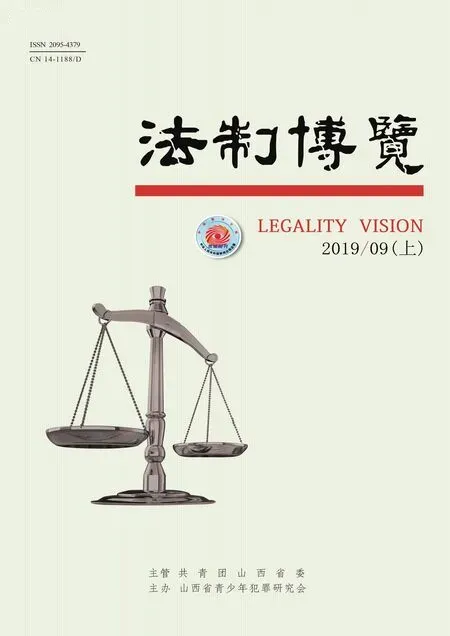宪政编查馆与修订法律馆关系考
戴馥鸿 杨 波
成都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在清末的法制改革中,最为人所知的机构即为修订法律馆了。修订法律馆的存在时间从光绪三十年直至宣统三年清廷覆亡。在这一段时间里,修订法律馆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的率领下,邀请日本法律学者冈田朝太郎、志田甲太郎、松冈正义等参与清末法典的修改和起草。后来,清末修律的主要成果《大清现行刑律》、《民事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法院编制法》等都是由修订法律馆主要负责完成的,这些法典至今在我国部分地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修订法律馆展开修律工作的第三年,清廷发布上谕仿行立宪筹备宪政,接着即设立宪政编查馆统筹一切与宪政有关的编制法规、统计政要诸事宜。从此,宪政编查馆成为清朝末年一切政治法律活动的管理机构,修订法律馆也开始在宪政编查馆的统率下开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修订法律馆和宪政编查馆必然会发生很多职能和工作中的联系。这里,笔者不会太过注意修订法律馆和宪政编查馆在人员和机构的交叉,而主要是着眼于在清末法制改革中,宪政编查馆设立以后修订法律馆地位发生的变化。
一、修订法律馆的开设
根据陈煜博士的考证,修订法律馆源于刑部下设的律例馆。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清廷发布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这一上谕宣布了清末修律的开始。当时“沈家本为刑部左侍郎,伍廷芳也刚刚从出使美国任上召回,以四品卿衔道员赏四品京堂候补”,“尚无具体官名”。此时的修律,根据前文的研究,是以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基础的。从这个时候开始,至修订法律馆正式开设,沈家本和伍廷芳由于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在修律方案上自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沈家本意在改造旧律,伍廷芳想要创造新律”。于是,沈家本着手开始将大清律例内“全部条例反复讲求,复查历届修例章程应分别删除、修改、修并、移改、续纂”等,一俟编订。而由于清廷急需发展工商,设立商部,“兹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定商律,作为则例。”伍廷芳作为谙习东西洋各国通商状况的新式人才,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被派去修订商律,同年,则起草并颁布《商人通则》和《公司律》,并以《钦定大清商律》颁行。而伍廷芳也于该年七月十六日被任命为清廷新设商部左侍郎,筹办一切通商事宜。可见,修律伊始,两位修律大臣都是根据清廷“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的变法原则分别工作,并没有设立独立的修律机构,也没有制定系统的修律计划。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此时修订法律事宜没有专门负责的机构或独立的身份与名义,仅仅是由两名分属不同机构的大臣负责其事。
这一状况在光绪三十年发生了初步的变化。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日,沈家本、伍廷芳“酌拟大概办法,遴选谙习中西律例司员分任纂辑,延聘东西各国精通法律之博士、律师以备顾问,复调取留学外国卒业生从事翻译,请拨专款以资办公,刊刻关防以昭信守”,并以修订法律馆的名义开始办事。根据沈家本、伍廷芳奏设修订法律馆的意图,修订法律馆的职责一为修订律例,一为翻译东西洋各国法律书籍。
然而,这一阶段的修订法律事宜在人事和职权上仍然存在三个大的问题。第一,修订法律虽然正式以修订法律馆的名义办事,但是却依然是在刑部之下,主要以原属刑部律例馆的人员具体办事,修订法律馆并没有自己专门的办事章程、办事人员和机构设置。第二,修律大臣沈家本为刑部侍郎,伍廷芳为外务部侍郎,而且伍廷芳光绪三十二年又被派驻美墨秘大使,两位修律大臣分属不同机构,难以统一办事。第三,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发布仿行立宪上谕,著改定官制,改革官制之后,刑部改为法部责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以使司法和审判大权分立,取司法独立之效。原修律大臣、刑部侍郎沈家本则迁任新设大理寺正卿,这使得修订法律的人事关系更为复杂和混乱。这三个问题导致修订法律馆的修律工作难以统一行使,再加上官制改革以后,中央部院的调整导致修订法律馆的身份和权属更加受到争议,使该馆无法独立完整地展开修律工作。
二、宪政编查馆与修订法律馆的独立
如前所述,修订法律馆源于早年设于刑部之下的律例馆,至修订法律观开馆修律以后,由于修律大臣沈家本仍然为刑部侍郎,所以,该馆依然为刑部附属机构,缺乏独立性。至官制改革以后,沈家本授任新设大理院正卿,大理院掌管审判事宜,刑部掌管司法事宜,取权力分立之效。然而在整个中央官制的改定过程中,修订法律馆的地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在法部与大理院就司法权限的划分引发部院之争之后,虽然争论并非因修订法律的权限引起,但是随着部院之争扩大,再加上人事归属不清,修订法律馆的地位以及修律权的归属也受到了法部和大理院之间争论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改任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就修订法律的组织机关、修律宗旨等问题首先发难,同一日两次上奏,指出:“臣愚以为修订法律,以之颁布中外,垂则万世,若仅委诸一二人之手,天下臣民,或谓朝廷有轻视法律之意。甚且谓某某氏之法律,非出自朝廷之制作,殊非所以郑重立法之道也。”将矛头直指修律大臣、刑部侍郎沈家本,认为沈家本有借修律侵夺皇权之嫌疑。张仁黼认为:“请钦派各部院堂官,一律参与修订法律事务,而以法部大理院专司其事”。其意图很明显,即要共同执掌修律权。对此,法部侍郎、修律大臣沈家本答复到:“原奏所成修订法律事体重大,拟请钦派部院大臣会订,而以法部、大理院专司其事”等,“均属切要之言”。后来,法部尚书戴鸿慈针对此事也上折指出:“若夫编纂之事,委诸一二人之手,固觉精神不能专著。”戴鸿慈赞同张仁黼由法部和大理院专司修律事宜的意见,并对该意见做了补充,认为应该“钦派王大臣为总裁”,管领修律事宜。针对张仁黼批评的“某某氏之法律”,沈家本深感惶恐,在历数修订法律馆近几年来在翻译各国法律,编订古律,改定旧律方面的实绩之后,提出:“臣学士浅薄,本未能胜此重任,加以进来精力日逊,每与官员讨论过久,及削稿稍多,即觉心思涣散,不能凝聚,深惧审定未当,贻误非轻。再四筹思,惟有仰恳天恩,开去臣修订法律差使,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广集众思,较有把握”。沈家本的奏折既有辩解的意思,又有宣战的意图。如此,关于修订法律馆的归属以及修律权的归属,瞬时成为清末法制改革过程中急需明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央官制改革刚刚完成不久,各部院权限尚在厘定阶段,而清末立宪又面临一个权力分立的问题,修律权的归属即为立法权的归属。如此,对修律权的归属和修订法律馆地位的明确界定就非常的必要。而这个结果最终由宪政编查馆做出。
关于修订法律馆的地位及修律权的争论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至六月。而该问题的解决直至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五日宪政编查馆成立以后才由宪政编查馆做出最后定论并得以解决。前面我们数次提到,宪政编查馆负责筹备立宪期间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诸事宜,而且在《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第二条第三款明确指出:该馆“负责考核修订法律馆所定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所订各项单行法及行政法规。”其中法典草案就是指“由修订法律馆所编订的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诸法而言”。修订法律馆应该以独立于法部和大理院的身份负责修律事宜,并直接向宪政编查馆负责。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草拟修订法律办法,就之前法部和大理院关于修律权及修订法律馆的地位问题给出最终的结论:
各国编纂法典,大都设立专所,不与行政官署相混,遴选国中法律专家,相与讨论,研究其范围,率以法典为限,而不及各种单行法。诚以编纂法典,事务浩繁,故不能不专一办理。原奏所谓特开修订法律馆,无论何种法律,均归编纂一节,范围太广,拟请饬照各国办法,除刑法一门,业由现在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明草案不日告成外,应以编纂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诸法典及附属法为主,以三年为限,所有上列各项草案,一律告成。其所请钦派王大臣为总裁一节,查修订法律馆之设,专为编纂法典草案起见,将来尚须由臣馆核定,该馆似无庸再由王大臣管理,免致重复。又所请以法部、大理院专司其事一节,查立宪各国,以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分立为第一要义。今若以修订法律馆归该部院管理,是以立法机关混入行政及司法机关之内,殊背三权分立之义。
根据此修律办法,各部院及修订法律馆所编订的法律法规尽归宪政编查馆核议,修订法律馆得以在身份上与各部院平行,脱离了刑部和大理院的束缚,得以独立负责修律事宜。基于对之前身份和地位不明确而得到的教训,根据宪政编查馆制定的修律办法,修订法律馆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即奏请正式开馆办事,制定《修订法律馆办事章程》十三条,馆内设“提调、纂修等员及延聘东西法律名家”,由提调“奏调任用各员陆续到馆”办事,馆内“设二科,分任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之调查起草,设译书处,任编译各国法律书籍,设编案处,任删定旧有律例及编纂各项章程,设庶务处,任文牍、会计及一切杂物。”
至此,修订法律馆真正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根据《修订法律馆办事章程》该馆负责“拟定奉旨交议各项法律;拟定民商诉讼各项法典草案及其附属法,并奏定刑律草案之附属法;删定旧有律例及编纂各项章程。”并根据《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将所编订律例法典及各项章程交付宪政编查馆核议。至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制定九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并命中央各部院将该机构根据筹备清单所应负责事宜开单胪列报宪政编查馆负责,修订法律馆遂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将该馆所应负责事宜奏报宪政编查馆审议,开始在宪政编查馆的统率下负责修律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