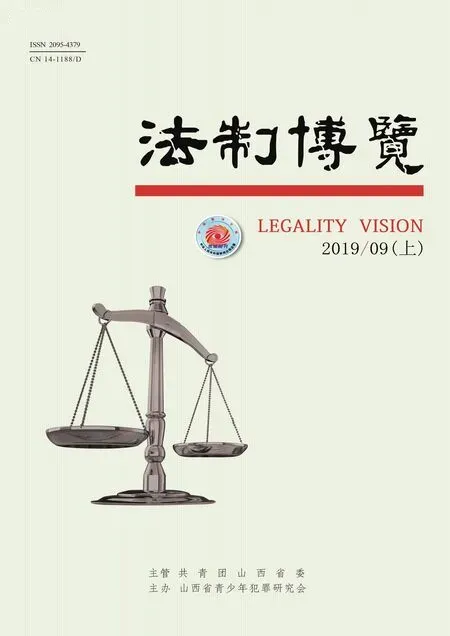高额彩礼的司法规制路径
贾 伟 李鹏飞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在我国,婚姻的缔结走着两条线路,一条是形成于古老民间传统的婚约。一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民政登记。与民政登记这个“新生儿”相比,婚约在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受宗法制影响,基本的婚姻制度就已形成,其中婚姻成立的要件便包括“一夫一妻多妾”、“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个主要原则和“婚姻六礼”这个程序性事项。此处的“婚姻六礼”依次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与民政登记相比六礼有着更多的程序、仪式与讲究,也更能体现婚姻的神圣性和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夫家对妻家的感激,因此婚约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后曾受到批判,一度废止)。“六礼”中的纳征便是民间的彩礼,又称财礼、聘礼、身价钱,男方在婚约初定时赠送财物,他作为婚姻缔结的一种前置程序与实质要件更作为一种民间习惯存在着。在法律世界里,通说认为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其解除条件就是婚约的解除,他具有极高的现实目的性,那就是确保婚姻的最终缔结。
近些年,一些学者因为高额彩礼的问题,对彩礼这个问题颇有偏见,社会生活中甚至偶尔会出现几个不要彩礼的婚姻来做这个彩礼社会的一股“清流”。其实我们欠缺的是对彩礼的一个正确认识。通过对婚姻史的追溯,不难发现财婚较之之前的掠夺婚是婚俗方面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掠夺婚又称抢婚,尤其盛行在以男子为中心的游牧时代,男子通过掠夺其他氏族部落妇女的方式来缔结婚姻,女子往往成为部落战争中抢掠的重要对象,是“战利品”。掠夺婚标志着母系社会的解体和父系社会的成长当今社会我们仍然可以洞察到抢婚的点点迹象,如新娘头上罩着盖头、往往在夜间凌晨接亲等都往是“抢”这个行为的体现,最能体现娘家对新娘离家的不舍和新郎得到新娘的不易。财婚的出现及对掠夺婚和“假结真婚”的胜利是女性地位上升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他使得婚姻的缔方式更加合乎情理。但由于婚姻彩礼作为生活习俗缺少监管,往往肆虐失控,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
首先,必须要认识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彩礼沉重的国家,婚姻尚财,形同买卖,因贫困而终身莫娶者甚多。曾有学者将中国古代的婚姻形态分为政治型、门第型、重婚与世婚型、财婚、侈婚、冥婚、收继型。纵观这些婚姻形式无不与财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财婚其实已经成为婚姻缔结的主要方式。在肆虐的财婚习惯下出现了各种畸形的手段作为婚姻的弥补。了解这些弥补手段,对我们准确把握高额财婚给社会带来的严重问题极为必要。其中童养媳制度特点尤为鲜明,童养媳就是将幼女养于婿家,年长后成婚,因为成年女子的财礼非一般人家所能承受。如此看来养育一个女性的成本总和低于婚姻成本,或者是一种变相的储蓄。类似的还有“未生子先抱媳”,这也是古代婚龄极低、女性的婚姻自由根本无从谈起的重要原因。封建社会的礼、法向来严禁亲属为婚,而在清代兄收弟媳、弟娶兄嫂在多地成为习俗,美其名曰升房、转亲,高额财婚带来的无奈足以突破良善风俗和形成已旧的秩序,突破礼、法规制。入赘与通常情况下的女入男家恰恰相反,一方面解决了无力娶妻的问题,一方面解决了有女无儿,宗祧难以承继的问题。相似的还有先到女家工作些许年份,再以劳工折抵彩礼。除了以上列举的外还有租妻(多为抵押婚,主要是用于生子,生完孩子便分道扬镳)、孝堂成亲、换亲。当妇女亡夫之后,夫家和母家将其视为货物一样抢夺,为的就是争夺她的再嫁主婚权,因为主婚权的背后便是财礼接收权,而再嫁的彩礼价值同样不可小觑。而后在清代,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夫家主持再婚权,理由便是此女子出阁时母家已经接受过一次财礼,母家无权二次获利。从古代文艺作品中,我们也足以发现民间往往将“嫁得好”与财婚划等号,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便可见一斑。通过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一旦财礼畸重,就会滋生各种特殊婚姻形式,并且突破当时条件下政府的规制手段,与良善风俗背道而驰。当我们再将视角投入当前社会生活中时,不难发现当代人依旧面临着高额彩礼的困境。
笔者绝不否认彩礼作为婚姻习俗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就像我们的春节习俗一样更多的是在表达人们对婚姻的理解。笔者也不打算给他扣上封建糟粕和买卖婚姻的帽子,相反,他是延续千年的民众传统,值得尊重和引导。另一方面司法对于当前彩礼乱象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持“沉默”态度。苏力教授在他《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曾言法律不能统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否则就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突破着法律的。我们确实应积极发挥法律对民风民俗的规制、导向作用,高额彩礼问题已经越过其社会底线,而法律应当既居庙堂之高也思江湖之远。我们有必要在国家法律层面对彩礼金额问题表明基本态度和立场,引导婚礼习俗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体现法制关怀。因为事实证明彩礼不是短暂的历史现象,不可能在短期消亡,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和建国初期都曾将之视为封建糟粕而予以废除,但他却延续至今,并在生活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兴风作浪”,与仪式效能、情感因素渐行渐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起点,新家庭应当诞生于良好的家风之中,而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严重的乱象。
有人戏谑道:“爷爷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牛,而我们娶媳妇却要了父母半条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婚姻缔结观念与建国初期相比是退步的或者说是腐化的。虽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我们的经济水平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与彩礼支付能力是非协调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婚姻观念变得更加物质化了。当今,中国人对彩礼的要法也呈现多样化态势,例如“万紫千红一片绿”,而鲁西南地区则用秤称量,河南吕楼村按女方学历要价。不论何种方式,也不论显得多么标新立异,都不过是索要彩礼的变相手段而已。
彩礼问题深深的影响着社会安定,一旦因彩礼问题导致单身男性过多必将滋生社会问题。2018年,江苏高邮37岁男子因彩礼问题与女友分手进而演化为绑架母亲,并将母亲虐待致死。近日,湖南凤阳县一16岁少女被囚禁地下室,遭55岁男子龙某合多次性侵,而地下室的墙上挂了些许的婚姻饰物。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犯罪分子对婚姻的极度向往以至发展出变态心理。家庭是社会的稳定器,多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必将少一份邪恶的罪孽。为了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司法有必要对彩礼进行规则确保中国有着良性的婚姻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婚姻彩礼是家庭致贫的重要因素,在当下脱贫攻坚中轻减彩礼也应列为重要一项,2017年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主任就指出一部分人因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而致贫。当我们过分的将目光投放到财物上时就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财婚”,进而忽略了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使得社会风气浮躁,婚姻目的不纯。当前我国的离婚率一路飙升,闪婚闪离早已见怪不怪,这绝对与过于看重物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在法律方面有如下几点努力方向。
一、《婚姻法》对买卖婚姻的定义不精准
我国倡导和尊重婚姻自由,为了最大减少外部干预并没有对婚姻的缔结、彩礼做细致的规定,甚至没进行专门的司法解释。另一方面,我们将婚姻立法的重头放在了婚姻的存废之上而忽略了婚姻的起始。《婚姻法》第三条规定了“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在司法解释中,只是规定了要对要求返还彩礼给予认可和支持的几种情况,对彩礼多少的问题避而不谈,当然彩礼准确数额在法条中也确实无法规定。就法条而言,他将买卖婚姻的行为同包办婚姻一样归入了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一类。而就通常理解而言,买卖婚姻属于财产性行为,是“求财”应具有独立的价值,求财并不必然干涉婚姻自由,两者不能划等号。而干涉婚姻自由涉及的是人身和身份关系,是限制自主选择,同时根据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我们知道人身权利高于财产性利益,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位阶,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应当两分,不应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法条的抽象性也弱化了“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功能,法条理解起来就如同是只要不干涉婚姻自由就可以进行包办和买卖,当然如此理解必然是片面的,但笔者在此只是想说明具有独立价值的财产性规制是被忽略了的。按照上面的思路,“索取”也显得实用性极差,联系到日常生活中彩礼的索取多是“暗地里”进行的冷暴力,这种索取是极为隐秘的,可以说女方很少直接索取或留下证据,整个“索取”的过程处在看似平等的协商之中,至于是否按照女方的彩礼意思都是让男方自己去思量的。所以“索取”二字与我国的国情并不充分吻合,我们陷入了以具体规制过于抽象的泥淖。最后便是没有对额彩礼和干涉婚姻自由的“冷暴力”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予以法律制裁。时至今日在我国特定地区仍存在因婚姻自由受到严重干涉而导致的严重的自伤、自残、自杀案件。而“造成”此后果的家长却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没有制裁等不利法律后果,就使得本条款单单成为宣誓性条款,在具备假设条件、行为模式后就应当完善其法律后果。
或许从刑法判断因果关系的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我们只能得出当事人自残与自杀与婚姻干涉无直接因果关系或者介入因素过于偶然。从社会心理与社会关系维系的角度考虑,也不宜使家长再受司法打击。但我们无法否认家庭的过分干涉与严重结果的内在的事实的联系。在过程的角度而非结果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家庭影响是逐步根深蒂固直至不可撼动的。司法关于婚姻问题的特点就是注重行为和结果而忽略起因与过程,着重打击实害犯而严格控制对危险犯的制裁。
因此,笔者主张首先对我国的婚姻法进行完善,对彩礼这个婚姻的起点进行规制,明确区分求财行为与干涉婚姻自由行为,以便建立起求财婚姻与买卖婚姻和买卖人口的适当联系。一方面减少对三者的模糊认识,一方面有效避免以彩礼为幌子变相的买卖婚姻乃至买卖人口而使司法正义受到破坏。其中,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彩礼究竟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度,多大数额是彩礼,而多大数额又是买卖婚姻。当然,这本来就是难以确定的东西,从古至今我国的彩礼就存在着极大的地域差异、阶层差异并且没有规律可循,经济落后的地方彩礼不一定低,经济发达的地方彩礼也不一定高,对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人口大国来说实属必然。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将彩礼与当地年收入挂钩,以百分比的方式确定彩礼的合理区间,实现彩礼的确定与当地经济水平的联动,突出彩礼作为程序的作用,减弱彩礼的求财效能。大多时候高额彩礼只是目的性的,此目的往往通过干涉婚姻自由的手段来实现,这样,对干涉婚姻自由造成的恶果为的惩处更显得极为必要了。对于干涉婚姻自由行为,我国只是将带有暴力的干涉纳入其中,而现实中存在的更大量的来自于家庭的冷暴力,多数家庭成员通过威胁、谩骂、侮辱等非暴力方式来达到干涉婚姻自由的目的。我们之所以忽略这些方式是因为认定此类行为与自杀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可如果此类行为没有达到一定的恶劣程度,当事人又怎会自杀呢。所以笔者认为,此类行为有惩罚的必要性。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是亲告罪,基于当然解释那些非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更是无法提起公诉。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行政处罚,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
二、着重规制公众人物的大操大办
彩礼在本质上是一个民风民俗问题,而社会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豪门”等主流群体的影响。这一方面源自他们自身具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跟风惯性。只是这种跟风在婚姻彩礼方面显得更为凸出。从2013年,北京朝阳的马某在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宴会厅连摆三天婚宴并请当红明星演出,再到江苏南通摆阔婚礼,将500万人民币拼成羊肉卷作聘礼等等,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况下,彩礼已经失去了其原本意义,也超越了“热闹”、“喜庆”的边界而成了炫富、作秀的手段,极尽低俗。其恶劣影响不仅仅对我国彩礼居高不下推波助澜,更是加深社会矛盾的帮凶,无疑是仇富心理的重要诱因,严重干扰了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扰乱了我国的婚姻秩序。
笔者认为,应从其传播途径上进行有效隔断,巨额彩礼,大操大办者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作秀心理,企图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信息管制,对社会大众心理进行良性引导,在网络安全管理条例中增加适当条款,限制或禁止高额彩礼婚姻在主流媒体和搜索引擎上出现在,相应的加大简约朴素婚礼的宣传。对于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在当地形成一定影响的当事人实行报告制度,对其造成的交通、环境影响进行管制并设定收费制度,这种收费制度可以采用类似于税收的超额累进制度。婚礼车辆超过一定数量了需向交通部门报批。对未形成特定影响或私下给付彩礼的行为则不予追究。其法理便是在维护社会良善风俗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凭自己资金实力进行彩礼给付的个人意愿。
三、加强对骗婚的打击力度
与普通的民间婚姻彩礼问题不同,骗婚在我国尤其是边远地区大行其道,由于赤裸裸的强调彩礼条件,使得索要彩礼常态化,这可谓是真正的买卖婚姻。
比较而言骗婚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婚姻“市场”。骗婚案件的增多更是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婚姻秩序。我国近年来非法边境婚姻持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中越、中缅、中泰,边境婚姻数量大幅增长,户籍管理混乱,边境管理困难。同时这也使得骗婚、骗彩礼的情况多了起来。例如购买越南新娘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虽然购买越南新娘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的彩礼,但这种婚姻往往难以长久,越南新娘婚后“逃跑率”极高,形成短期婚姻,而且其性质正是买卖婚姻。因此也属于骗婚的一种。国内的骗婚案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由于国内的彩礼较高,法律规制不健全,很多犯罪分子走上了彩礼诈骗取财的路子。骗婚一方面源于我国民间畸高的彩礼,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彩礼的严峻形势,对其进行规制实属必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很难把已经领取结婚证,只是因为女方婚姻家庭意识不强,对婚姻不负责任而导致婚姻持续短暂的情况认定为骗婚。这就给了骗婚很大的操作空间,形成了该方面的法律漏洞,骗婚者往往假戏真做,有的甚至直接跑路,男方不仅没有娶到妻子,还使得家庭更加贫困。
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婚姻登记的落实,加强境外婚姻监管,并打造婚姻登记记录网上查询平台,将进行过多次婚姻登记的女性的情况告知男方当事人,甚至对超过一定登记次数的女性不予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在法律上进一步细化对骗婚定性,并将之与诈骗形成合理联系,在实务中进一步加强对骗婚赃款的追缴力度,其相关措施向我国打击“老赖”的措施借鉴。对买卖婚姻和买卖婚姻的中介进行民事处罚,禁止公开的婚姻买卖。
本文以乡土中国的人文风俗为视角结合当前婚姻彩礼的主要问题,呼吁我国完善彩礼立法,强化婚姻管理与司法规制,保护并完善我国的婚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