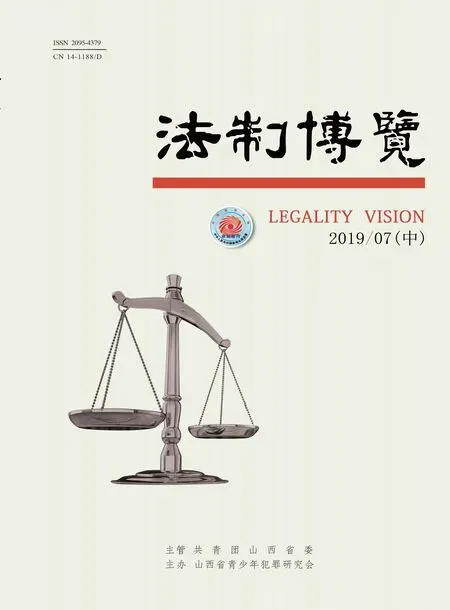学术与政治:印度尼西亚①民族学人类学的命运*
唐 欢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的话题之一,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在其“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中,论述了其对学者(尤其是教师)与政治家身份的定位。他认为学术不涉及终极关怀,教师在课堂上应该传授客观知识,不能带有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偏向;而以政治为业者应该有终极关怀,但需要道德伦理与责任感指导行为。[1]因此,在韦伯看来,学术不应该卷入政治因素。然而,学术发展与知识生产,不论有心无心,都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及其之后的研究写作中,构建出“权力-知识”体系,认为权力制造知识,而知识又为权力所用,维护现有知识或创造新的知识。[2]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类似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但政治超出“权力”范畴。
本文以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萌芽、建立、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主线,通过对不同时期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生产与政治环境的关系的论述,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即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与国际关系形势、国家统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尤其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探讨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命运。
一、殖民统治: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肇始(1945年之前)
印尼位于亚洲、大洋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的交界之处,自古是欧亚大陆海上贸易的咽喉要地。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香料、黄金、石油、煤、天然气)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汇聚世界各地的旅行家和贸易商,先后受印度、阿拉伯、欧洲和中国文化影响,与其原始文化融合,形成其文化多样性现状;也使其成为欧洲殖民扩张争夺的重要对象。自葡萄牙人15世纪末取代穆斯林商人向欧洲供应香料,印尼先后受葡萄牙-荷兰-英国-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尤其受荷兰近三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可从三方面了解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是欧洲尤其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产物。
其一,欧洲人对印尼的早期记录,是当地较早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是后期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关于印尼地理生态及其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多为欧洲殖民扩张时期的西欧人所述。包括旅行家的日记、基督教传教士的记载、语言学家的作品、自然博物学家的写作以及殖民官员的报告等。[3]这些早期的记录和写作量很大,但并非专业的研究写作而质量不高,当今学界对这些成果多有批评——如多为作者自身经历印象的罗列,信息零碎、偶然和片面;带有作者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标准,文化描述具有主观性和偏见等。[4]
其二,对印尼人及其文化的专业研究,源于19世纪末荷兰政府为殖民统治而发展的“印度学”,是后期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了更好地统治印尼殖民地,需要了解印尼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荷兰政府开设了印尼文化培训课程,包括爪哇语、马来语、印尼地理、民族学、民俗学、阿拉伯学、印尼习惯法及印尼经济等课程,形成一门区域学科——印度学(Indologie),到二战时期被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科学”(Ilmu bangsa-bangsa Indonesia)。开设三个一级研究领域:暨印尼历史与文献、社会政治、社会经济。接受培训学习的人除了殖民官员,还包括教师、传教士以及荷兰印尼企业职员。殖民官员被发送到印尼后,不仅实践着他们所学到的,而且也进行教学。每一个殖民官员都是印尼民族学人类学专家,他们在印尼各地任职,将自己了解的材料写成报告,这些工作报告就像民族志,又促进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有些殖民官员回国后,更是成为专门的印尼民族学人类学教授。荷兰的印度学家还尝试用规范方法理解印尼人文,包括找寻基本规则建立文化体系模型,用归纳演绎等方法开展比较研究。荷兰对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多围绕语言、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和“原始思维”、社会经济生活、习惯法、古代社会结构、文化适应等主题展开。[3]殖民官也从当地收集大量数据资料,以待回国做比较研究。其他学者借助这些资料展开比较研究理论构建,还把他们的关注需求反馈给身在实地的学者以补充资料收集。荷兰语言学家也对印尼兴趣深厚,并且印尼民俗、爪哇考古学、前殖民史、印尼伊斯兰教和教法研究领域推广语言学方法。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殖民政府对印尼青年的教育,及其对印尼人与文化的研究,是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萌芽的基础。随着19世纪末“分而治之”思想的出现,殖民政府开始培养地方精英以促进更好地治理殖民地。之前印尼青年高中毕业后只能到荷兰高校留学,20世纪初,荷兰政府新的“民族政策”颁布,给予印尼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20年代后,荷兰政府在印尼建立高校,培养印尼本土青年。这些接受国内外高等教育的青年,多学习法律、经济和农业科学,多进入公务员体系以壮大殖民政府行政管理,而少有从事学术工作者,因为荷兰学界对这些印尼学者并不很认同。也有荷兰著名人类学家如乔赛林·德·荣格(J.P.B.de Josselin de Jong),鼓励印尼学生研究自己的文化,希望他们可以建立印尼本土的民族学人类学。少数学生学习“印度学”,主要是语言、历史和习惯法的学习,毕业后从事学术工作,在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侯赛因·贾佳迪宁格拉特(Hoesein Djajadiningrat)、博尔巴迦纳戛(R.Ng.Poerbatjaraka)、苏波莫(R.Soepomo)、佐佐迪古诺(M.M.Djojodiguno)等。
二、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挑战与学科建立(1945-1957)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挑战
20世纪初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已萌芽,但民族学人类学的殖民性质与研究特色,也造成二战后印尼独立之初,印尼政府与学界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存在意义的质疑。这种质疑可从去殖民化思想和现代化国家发展建设两方面来解释。
其一,去殖民化思想对民族学人类学的排斥。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立即征战东南亚;1942年3月8日迫使荷兰投降退出,日本全面占领印度尼西亚。日本占领印尼的三年半时间里,关闭欧洲的公司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为了战争的胜利,推动自身的发展,对印尼残酷剥削,引发印尼人对殖民的深刻的仇恨,促进了印尼民族主义的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于8月17日宣布独立,在民族主义去殖民化思想下,民族学人类学的存在遭受各方的质疑和批判,其发展前景陷入政治僵局。一方面,民族学人类学被视为殖民科学。战后印尼宣布独立,但荷兰政府不愿放弃殖民印尼的利益,印尼经历了四年半的独立战争,印尼民族主义者仇视殖民统治,连带也反感民族学人类学。印尼青年学生对这个学科持怀疑态度,而印尼学者将民族学人类学视为荷兰殖民印度学的嵌入。另一方面,民族学人类学首先是“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研究”,在社会进化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下,非欧洲民族被视为“原始的部落”、“野蛮人”。印尼等新独立的国家,拒绝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不愿被视为“原始的”、“野蛮的”、“落后的”。因此,虽然战后荷兰学者在印尼开设民族学人类学课程,但很少有印尼学生对此感兴趣。荷兰民族学人类学家也被起诉,很难继续在印尼做研究。
其二,对民族学人类学适应印尼现代化发展建设的否定,主张用社会学取代人类学。学界对民族学人类学存在意义的态度有分歧。1950年印尼建国后不久,印度尼西亚大学的法律学院和文学学院关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开展了一场学术讨论。这场讨论源于“现代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与主张取消种族隔离构建印尼身份认同的人之间的辩论。部分人偏向社会学,认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应该由社会学取代而取缔;部分人认为民族学人类学对印尼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者以印尼社会学家莫利亚(T.S.G.Moelia,1896-1966)为代表。莫利亚是民族主义者,他1951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印尼的社会学”(Indonesische Sociologie)。[5]在这篇文章中,莫利亚控诉了荷兰民族学人类学的殖民性质,指出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基本上是对“原始的”和“静态的”社会感兴趣,不适合当下印尼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他认为新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需要新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为了研究和促进印尼社会的发展,建议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用社会学取代民族学人类学。其他支持社会学的人也认为人类学不适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家需要看向未来,而不是关注过去的、原始的和静态的方面。[6]
(二)本土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立
尽管对民族学人类学存在诸多批判与质疑,最终,印尼政府基于政治需要,支持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印度尼西亚特殊的地理生态和历史进程,形成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现状,不同地域、民族、语言、宗教的人组成不同的政治党派。早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各阶层党派之间便有冲突,为了摆脱荷兰殖民统治,各方势力暂时妥协,一致对外,但并未完全一心;印尼独立建国后,这些冲突又爆发。1950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持续动荡,不同地区、民族、宗教精英摩擦不断。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印度尼西亚要发展建设,首先需要建构印尼的“国家文化”,促进不同群体的国家身份认同与整合。不同地域、民族、宗教人民的团结,首先需要相互理解和认同。支持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人认为,因为民族学人类学可以洞察和获取多民族地区的知识,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文化的有效方法,因此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实现“多元的统一”。基于此,印尼政府教育部并没有取缔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并支持本土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设。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的建设受命“去荷兰殖民化”。
在去荷兰殖民化政治意识的主导下,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受政治权力影响,高举“去荷兰殖民化”的旗帜,研究主题、术语必须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然而,因为师资与教材的缺乏,荷兰学者仍在印尼高校任教,使用荷兰人编写的教材,印尼先驱学者也多有荷兰教育背景,深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为了去荷兰殖民化,印尼派遣印尼青年学者和学生到外国留学,然后回国促进本土学术的发展。如科恩贾兰宁格罗特(Koentjaraningrat,1923-1999)1954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195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印度尼西亚大学,1957年建立第一个印尼的民族学人类学系,撰写印尼语教材,并受命帮助各地方高校建立民族学人类学专业。
三、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1957年至今)
(一)国际关系形势影响下的研究与教学
国际关系形势对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印尼独立建国后,在美国与苏联阵营的冷战中采取不结盟政策。但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其他大国都想争取与印尼的国际合作。西伊里安岛的黄金矿,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印尼独立建国,荷兰政府为了黄金储藏,不愿归还西伊里安地区。1956年,两国因该地区的纷争关系破裂,荷兰学者被迫离开印尼,荷兰民族学人类学家转战西伊里安地区做研究。二战后,美国因为印尼的战略地位与经济资源,对印尼的兴趣提升,将之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在印尼独立战争时期压迫荷兰承认印尼的独立,之后又因西伊里安的利益,积极压迫荷兰归还西伊里安地区。美国还开始关注印尼的社会与文化,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马萨诸塞州的技术研究中心是研究印尼文化的中心,支持印尼青年学者到美国留学,印尼“人类学之父”科恩贾兰宁格罗特便在1954年于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1963年,荷兰政府归还西伊里安地区成为印尼的一个省,荷兰与印尼两国时关系缓和,逐渐有荷兰学者到印尼做研究。为了了解和治理西伊里安地区,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在科恩特的引导下,兴起一股西伊里安研究热。
1966年后,苏哈托担任印尼第二任总统,开始偏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印尼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合作日益扩大,也促进了两国学术的交流与合作。1967年2月20日,美国发起和主导了IGGI(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n Indonesia)项目,项目成员包括美国、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瑞士,促进了印尼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日本等国在70年代大量进入印尼投资,荷兰与印尼的关系也日益升温。印尼派送学生到这些国家留学,民族学人类学青年教师与学生多到美国或荷兰进修。1975年,印尼实施美国的教学机制,本科教育从原本荷兰教学机制的五年变为四年。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加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在印尼高校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大学的人类学课堂上纷纷涌现。
(二)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发展与应用人类学倾向
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建立与发展,深受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尤其在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社会科学研究被政府意识主导而倾向于应用与发展。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因建国之初的质疑与争论,使之建立之初就偏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建设。苏哈托“新秩序”政权取代苏加诺政权后,印尼民族学人类学更是倾向于应用人类学与发展人类学。苏哈托上台后,基于印尼社会贫穷的现实,致力于经济发展建设,1969年,印尼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意识导向下,与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农村发展建设、民族国家的整合、教育、人口动态、社会文化变迁、贫困、工业、计划生育、移民、城市化、健康、生态和环保等主题的研究。[7]
印尼民族学人类学核心人物如科恩贾兰宁格罗特、马斯里·辛加里姆本(Masri Singarimbun)、帕苏迪·苏帕兰(Parsudi Suparlan)等均受政府的影响开展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8]这三位人类学家不仅引领了印尼的人类学,而且参与政策的制定,影响印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科恩特受命在印尼各省高校创办和发展人类学系,将人类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派往美国、荷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学习各种人类学分支学科理论,以期他们回国后任教于各地方高校人类学系,发展印尼本土的民族学人类学。马斯里从澳大利亚学习回国后,建立了人口研究中心,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印尼政府的人口政策。②他1977年关于贫困的研究,改变了政府认定贫困和人口的政策方向。帕苏迪关于民族的研究影响了印尼民族政策的制定,也研究农村地区、贫困和多样的文化的相关方面。
80年代初,苏哈托政府命令社会科学学科培养学生参与和促进国家的发展建设。文化与教育部着手将人类学系从原本的文学院,转移到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学院。因科恩特等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先驱和中心人物,认为印尼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使命在于参与和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建设,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偏向“社会人类学”,因此积极主导人类学系的转院。在科恩特的推动下,印度尼西亚大学的人类学系于1983-1984年转到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学院,改名为“社会人类学”(Antropologi sosial)。其他多数高校的人类学系也转到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学院。只有少数高校,以日惹特别行政区的加查马达大学为首,坚持人类学系留在文化科学学院。在国家政府权力的意识形态和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先驱核心人物的推动下,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偏重“社会人类学”,偏向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将文化视为人类学研究本身的一部分,重视结构与功能,致力于社区、社会的各种属性与社会问题的研究。
另外,80年代,苏哈托“新秩序”政权限制言论和学术研究,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与研究机构和高校合作,开展研究项目,高校学者少有研究的自由;另通过武力,禁止学界探讨民族、种族、宗教、族群间等政治问题,质疑国家政策和政府官员,否则将遭到拘禁与打压。直到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尼民主改革,学术界有更多研究和言论的自由,可以探讨如民族自治等政治问题。这也体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学术知识生产的控制。
(三)民主改革后的反思
苏哈托“新秩序”的军政极权,导致腐败与贫富差距,尤其苏哈托家族腐败严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印尼经济动荡,引发各种社会运动与学潮,苏哈托1998年辞职。印尼结束了历经32年的“新秩序”政权,发起民主改革运动,也促使学术自由得以发展。印尼的民族学人类学也重新反思自身的角色。1998年后各地的地域、民族、语言、性别、宗教等“原生情感”的爆发,使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等问题成为急需解释的问题,人类学开展大量的地方、民族、种族、宗教和族群间乃至国家的文化认同、跨境文化等主题的研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也在印尼兴起。
“新秩序”时期的人类学多受政治权力的影响,自上而下做发展项目,提供政策建议,解决社会问题,而较少从底层、边缘出发,满足底边人民的真正需求。“后新秩序”时期“地方分权”政策下,学术的解放与反思,促使印尼人类学家可以更多地按照学者自身的兴趣做研究,更多地与地方机关和公司合作,更多地关注地方、底层和边缘人民被压抑的“声音”,也可以更多地参与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9]
印尼民族学人类学更加多元,“文化人类学”与“政治人类学”两派的纷争,也反映出对“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观点的区分。前者认为人类学更倾向于研究社会属性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即“学术”服务于“政治”;而后者倾向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与解释,更倾向于“学术”的自由,而不涉及终极关怀,提供知识让政治家更好的治理国家。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知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建立、发展及其知识生产,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具体而言,深受印尼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国际关系形势、国家政治需求与统治权力的影响。其实,更广而言之,知识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又影响社会生活,这里的“社会生活”即“社会存在”、“文化生态根基”。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基于其文化生态根基,即印尼独特的历史情境、民族文化心理、时代精神、文化制度、权力结构等生活文化,上述的“权力”,只是文化生态根基的一部分。本文仅限于探讨权力对印尼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建立、发展与知识生产方向的影响,关于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具体问题与成果,将另外呈现。
[ 注 释 ]
①印度尼西亚全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文使用简称“印尼”.
②这个人口研究中心改了几次名字,现在是加查马达大学的人口与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