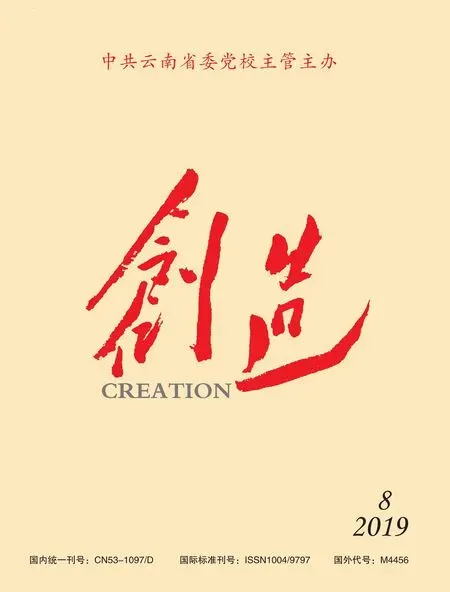从点苍会盟看道教在南诏的地位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南诏异牟寻与唐使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史称“点苍会盟”。点苍会盟是唐与南诏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会盟后,南诏重新臣属于唐,双方结束了对抗战争的状态,维持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点苍会盟的重要特征是南诏采用了“以道证盟”的宗教形式,即以道教的神仙作为盟约的证盟神、监盟神和执法神。点苍会盟中的道教,已有很多学者研究[1],但大都停留在解释南诏道教的状况。吴棠虽对道教在南诏前期的地位有过论断,但只停留在表层。[2]道教在点苍会盟中的影响和地位,以及其反映的南诏宗教文化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一、点苍会盟的历史背景
点苍会盟的双方是唐与南诏,却涉及唐、南诏和吐蕃三方势力。三方关系复杂,时而唐支持南诏打击吐蕃,时而南诏依附吐蕃对抗唐朝。点苍会盟是唐与南诏互相需要的情况下,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努力推动中完成的。
(一)唐打击吐蕃的需要
唐与吐蕃的关系在三方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南诏只是依附双方以求自安。武德元年(618),李渊在长安称帝,都长安,国号唐。唐朝建立后,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3]贞观二年(628),松赞干布(581-650)继赞普位。赞普,即吐蕃王,吐蕃风俗称“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4]。松赞干布在其叔叔的辅佐下,对内清除旧贵族势力,对外进行征伐,完成了西藏的统一,吐蕃崛起。吐蕃的崛起,对唐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唐在处理与吐蕃的关系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先后入藏,唐与吐蕃结成了“舅甥关系”,保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不顾“舅甥关系”,趁火打劫,夺取陇右、河西走廊。其后,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边境,成为唐朝大患。
唐德宗即位之初,锐意改革,因急功近利,处置失当,民怨沸腾。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推朱泚为帝,占据长安。唐德宗仓皇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叛军包围一个月,史称“奉天之难”。奉天之时,唐与吐蕃约定吐蕃助唐平叛,收复长安,唐将安西、北庭之地给吐蕃。吐蕃发兵长安,但因长安城瘟疫横行,引兵退出长安。唐德宗在敕尚览铄的文书中说:“朕以宗庙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阙戎,岂惜酬赏,遂许四镇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属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马,便自抽归”[5],对其进行谴责。朱泚之乱平定后,吐蕃派使者讨要安西、北庭之地。唐德宗因吐蕃背信弃义,无收复之功,拒绝吐蕃的要求。吐蕃以助唐平叛却没有得到恩赏为由,不顾清水之盟的誓约,不断侵扰唐朝边境。贞元二年(786)十一月,吐蕃攻陷盐州,十二月攻破夏州。后吐蕃屡以请和为由,诱唐与其重新定盟。贞元三年(787),吐蕃尚结赞与唐使浑瑊盟于平凉川。吐蕃趁机埋伏,会盟之时攻击唐军,企图劫持浑瑊,直攻长安。浑瑊夺马逃回,监军宋凤朝、判官韩弇被杀,崔汉衡等六十余官员被俘,“余将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驱掠者千余人,咸被解夺其衣”[6],史称“平凉劫盟”。唐朝再次被吐蕃算计,德宗深感自责,下罪己诏曰:
乃者吐蕃犯塞,毒我生灵,俶扰陇东,深入河曲。朕以兵戈粗定,伤夷未瘳,务息战伐之谋,遂从通和之请。亦知戎丑,志在贪婪,重违修睦之辞,乃允寻盟之会。果为隐匿,变发壝宫,纵犬羊凶狡之群,乘文武信诚之众,苍黄沦陷,深用恻然。此皆由朕之不明,致其至此。”[7]
平凉劫盟后,唐与吐蕃关系恶化,德宗为防止吐蕃的入侵,加紧军事布防。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北庭都护府,唐失去北庭地区,后几年唐又失去安西地区。至此,安西、北庭在安史之乱后与唐隔绝,坚守近三十年后,失陷。唐彻底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
德宗即位之初,深陷兵乱之苦,又面临吐蕃的威胁,内忧外患不断,疲于应付。平凉劫盟之后,唐与吐蕃关系恶化,攻伐不断,边境战乱频繁。唐需要一个能合力打击吐蕃的同盟,南诏无疑是最佳的对象。
(二)南诏摆脱吐蕃的需要
南诏(738-902),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于开元二十九年(738)建立。南诏的前身为蒙舍诏,蒙氏高祖细奴逻于649年所建。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白子国首领张乐进求以国让细奴逻,细奴逻遂于蒙舍川建国,号蒙舍诏,自称奇王。当时,云南洱海地区共有六诏,即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蒙舍诏位于最南端,故又称南诏。永徽三年(652),细奴逻始遣子入朝。开元二十六年(738)春,皮逻阁入朝,玄宗皇帝封其为越国公、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后皮逻阁逐河蛮,唐朝因功册封其为云南王。皮逻阁为蒙舍诏第四位首领,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灭掉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旧唐书》载:“归义渐强盛,余五诏浸弱。先是,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归义赂,奏六诏合为一诏。”[8]天宝七年(748),蒙归义死,子阁罗凤袭云南王,后叛唐。
阁罗凤叛唐的直接原因是唐朝用人不当。姚州都督张虔陀作为云南守官,不仅未能稳定边疆,反因横征暴敛,欺压少数民族,激起西南民怨。张虔陀经常辱骂阁罗凤,又征求财务,激起阁罗凤的怨恨。天宝九年(750),阁罗凤携妻子去成都,路过姚州,张虔陀侮辱阁罗凤的妻子,又向朝廷诬告阁罗凤谋反,导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杀张虔陀。事后,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未能妥善处理此事,出兵讨伐阁罗凤。阁罗凤遣使谢罪,鲜于仲通不许,继续进攻南诏,被南诏所败。阁罗凤叛唐,臣属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东帝。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恶化,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因发生在天宝年间,故称“唐天宝战争”。
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位之初,连合吐蕃进攻唐朝,遭到惨败,为吐蕃所责。《滇考》载:
异牟寻为人有智数,善抚其众,颇知书,师事郑回。大历十四年嗣,居史城,连吐蕃入寇,为王师所败。吐蕃怒,杀诱道使来者,异牟寻始惧,改城苴哶。[9]
此事发生在建中元年,吐蕃因这次军事进攻失利,迁怒南诏。异牟寻因此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防备吐蕃。南诏臣属吐蕃后,受到吐蕃的剥削与压迫,不仅要向吐蕃缴纳大量的贡赋,还要为吐蕃提供兵源。《滇云历年传》引《通鉴纲目》载:“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为先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地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10]异牟寻迁都羊苴咩城以后,吐蕃与南诏之间的猜疑日益加深。吐蕃降异牟寻为日东王,并要求异牟寻将大臣之子送到吐蕃作质子,异牟寻怨恨更深。南诏清平官郑回趁机劝异牟寻归唐,说:“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11]异牟寻接受了郑回的建议,开始谋求归唐。
南诏苦于吐蕃的统治,需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既能保护自己,又能摆脱吐蕃的统治。此时,与吐蕃对战的唐朝无疑是最佳的归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采取招抚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坚定了异牟寻归唐的决心。
二、点苍会盟的经过
点苍会盟的顺利进行,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工作。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促成点苍会盟的关键人物。清代倪蜕认为“边将不得人,则蛮夷叛;边将得人,则蛮夷朝。”[12]南诏能够归唐,正是德宗用人得当,韦皋功不可没。贞元元年(785),韦皋官居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代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出镇成都。韦皋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多达数十万之众,与吐蕃交好,如果吐蕃攻打蜀中,“必以蛮为前锋”[13]。因此,韦皋认为“计得云南则斩虏右支”[14],于是采取招徕政策。韦皋的政策,得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拥护,西南少数民族陆续归附唐朝,缓解了唐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矛盾。
点苍会盟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南诏清平官郑回。天宝年间,郑回为西泸(今四川西昌)县令,后为南诏所俘。郑回因儒学精湛,为阁罗凤所重,教异牟寻。异牟寻即位后,任命郑回为清平官,推行汉化政策。异牟寻苦于吐蕃的压榨,郑回趁机劝说异牟寻归唐。在郑回的劝说下,异牟寻开始谋求归唐。
贞元三年(787),异牟寻派使者去拜见韦皋,传达其内附之意。韦皋在招徕西南少数民族的同时,尤其注重改善与南诏的关系,争取南诏归唐。韦皋得知异牟寻内附之意,即上奏德宗皇帝“宜招纳之”[15]。此时,李宓也在劝德宗招抚云南,切断吐蕃的右臂。德宗采纳了二人的意见,命韦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16]。贞元四年(788),韦皋派间者入见南诏王异牟寻,传达唐天子的招抚政策。贞元七年,韦皋为坚定异牟寻归唐的决心,“遣使段忠义等招谕,兼送皇帝敕书。”[17]段忠义是南诏人,曾为阁罗凤的使者,后为韦皋讨击副使。段忠义的回归引起吐蕃的怀疑,吐蕃遂发兵二万屯守会川(今四川会理西),企图阻断滇、蜀之间的交通道路。韦皋为了维持唐与南诏道路的畅通,争取南诏归唐,出兵攻打会川,吐蕃大败。韦皋占领会川,控制了滇、蜀交通要道。贞元九年(793)四月,异牟寻派三个使者带着帛书,从三路去成都拜见韦皋,并献生金与丹砂。韦皋派人护送使者到长安,“使者奏异牟寻请归天子,为唐藩辅。献金,示顺革;丹,赤心也。”[18]德宗下诏慰抚,并命韦皋处理此事。韦皋派判官崔佐时入羊苴咩城,见异牟寻。贞元十年(794)正月,异牟寻与其子寻阁劝及清平官等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点苍会盟结束后,崔佐时带着誓文回成都复命。同年,唐德宗遣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节册封南诏。十月,袁滋在羊苴咩城宣读德宗敕书,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授贞元十年历。十一月,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等七人随袁滋入朝,奉表谢恩,进纳吐蕃赞普钟印一面,并献铎鞘、浪川剑、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等物品。至此,南诏正式回归唐朝,点苍会盟取得圆满成功。
三、点苍会盟中的道教
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末年,张道陵在四川创造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其中蒙秦治和稠粳治横跨滇川二省,成为道教传入云南的桥梁。南诏统治集团——蒙氏家族,据龙腾研究认为其祖先是生活在蒙秦治下的蒙人,是早期五斗米道的信徒。[19]唐代,南诏还接受了中原道教,《南诏德化碑》的碑文中就有“阐三教,宾四门”的记载。一般学者认为“阐三教”,即阐扬儒、释、道三教。而温玉成认为异牟寻的礼制建设中,“把阐扬儒、佛、梵三教定为国策。而五斗米道早已融入巫鬼教之中,在南诏王看来,似乎是不必特加阐扬的。”[20]假若温玉成的推断正确,则说明五斗米道在南诏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已深入南诏文化。无论“阐三教”中是否有道教,都可以说明南诏道教确实存在。五斗米道融入巫鬼道,是道教在南诏的发展逐渐本土化和南诏化的必然趋势。
道教南诏化最明显的表征是天、地、水三官信仰与本地山川信仰的结合,并运用在政治盟誓中。《云南志》载: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判官崔佐时谒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21]
点苍会盟中的天、地、水三官为五斗米道的最高神灵,也是道教的重要神灵。三官,又称三元,三官大帝,三官帝君。唐代是三官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三官诞辰日——三元节成为道教界的重大节庆日。
点苍会盟中的道教,是南诏的宗教信仰,还是南诏用以博取唐王朝政治好感的策略呢?其关键之处在于唐德宗与道教的关系;会盟仪式是以唐为主,还是以南诏为主。
(一)德宗与道教
唐初,李唐皇室尊老子为祖,而老子又是道教教祖。这样一来,道教就与李唐皇室攀上了关系,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唐玄宗天宝年间,道教的发展达到鼎盛,成为唐朝国教。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唐后期,藩镇割据、宦官干政困扰着李唐皇室,帝王权力衰落。道教虽仍为李唐皇室尊崇,但地位和影响不似从前。
唐德宗(742-805),唐朝第10位皇帝,代宗李豫长子,大历十四年年(779)登基,在位26年。德宗在遗诏中说:“朕常奉圣祖玄元清静之教,励精至道,保合太和,每忘己以爱人,岂嘉生而恶死。”[22]遗诏中貌似德宗崇奉道教,其实不然。纵观德宗的帝王人生,急功近利、贪婪自私、猜忌大臣、重用宦官,无一与老子清静之教符合。德宗之所以在遗诏中强调“圣祖玄元清静之教”,只是唐初尊奉老子为祖政策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德宗尊崇道教。
德宗尊祖而不崇道,对佛、道教二教施行严格的管理和限制政策。即位之初,德宗深感佛、道教二教弊端严重,下达“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23]、“罢献祥瑞”[24]等政令。德宗对佛道二教的认识是一致的,并没有抬道抑佛的理念和举措。其在《修葺寺观诏》中说:“释道二教,福利群生,馆宇经行,必资严洁。自今州府寺观,不得客宿居住。”[25]德宗下诏不许寺观留宿外客,在法律层面禁止僧侣、道士与世俗之人交往,防止双方互相利用以谋求政治权益。贞元四年(788),德宗罢崇玄馆大学士,从制度上废除了宰相兼领道教教学事务的惯例,降低了道教的地位。因而,英国学者巴瑞特总结说:“德宗统治时期有着对任何宗教都特别吝啬资助的特点。”[26]
德宗崇尚儒家礼制,不盲听道教术士之言。贞元十五年,术士匡彭祖对德宗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27]德宗诏礼官和大儒讨论此事。归崇敬以现有的郊祀制度,每年六月土王之日,在南郊祭祀黄帝,以后土皇地祇配,正是符合国家土德之运,“彭祖今请用四季祠,多凭纬候之说,且据阴阳书,事涉不经,恐难行焉。”[28]德宗听取归崇敬的意见,遂罢此事。这说明德宗对待儒家礼制和道教术士学说的态度不同,德宗更倾向于儒家礼制。这也表明了德宗对道教的态度——不盲从,不迷信。
德宗尊祖而不崇道,节而有制,对道教没有太多的热情。德宗从统治的角度出发,对佛道教的发展进行限制,虽没有玄宗初期限佛的力度,但也没有玄宗后期崇道的狂热。德宗不崇道,南诏也就没有理由在点苍会盟中用道教的神灵做监盟神,以博取德宗的好感。
(二)会盟仪式
南诏道教资料留存较少,需要结合当时唐王朝与其他民族订立盟约的情况。点苍会盟前,唐曾多次与吐蕃结盟,其盟约仪式反映了吐蕃主流文化发展变化的情形。佛教成为吐蕃统治文化前,吐蕃按古羌族习俗,即刑牲歃血,作为盟约仪式。佛教文化占统治地位后,佛教因素逐渐出现在盟约仪式中。南诏国前期和后期与唐结盟的形式与吐蕃颇为相似。点苍会盟中,道教因素参与盟约。南诏世隆时,则出现僧人景仙与世隆定盟的情况。这与南诏统治文化的转变有关。
汉人盟誓常采用筑坛、刑牲歃血的盟约仪式。建中四年(783),韦皋与士兵盟誓的形式,反映了汉人盟誓的特点。时年,朱泚叛乱,德宗被困奉天。韦皋为抵御朱泚叛军,誓死保卫陇州,与将士盟誓。《旧唐书》载:
皋乃筑坛于廷,血牲与将士盟曰:“上天不吊,国家多难,逆臣乘间,盗据宫闱。……言诚则志合,义感则心齐;粉骨糜躯,决无所顾。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于子孙,亦罔遗类。皇天后土,当兆斯言。”[29]
韦皋与将士盟誓的流程是是筑坛场,在坛场上举行刑牲歃血的盟誓仪式。监盟之神为皇天后土,这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最高神灵。此次盟誓的双方均为汉人,不掺杂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是典型的汉人盟约仪式。这说明汉人的盟约仪式通常具备三个条件:坛场、刑牲歃血、皇天后土监盟。
唐朝在与吐蕃、南诏会盟的仪式中不仅有汉人的盟约仪式,同样夹杂了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唐与吐蕃的会盟仪式最为典型。肃宗元年,吐蕃遣使请和。因吐蕃佛教兴盛,肃宗命宰相郭子仪等与吐蕃使者盟于光宇寺。吐蕃使者却说:“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须于鸿胪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礼。”[30]此时,佛教还没有参与吐蕃盟誓的活动中。
建中四年(783),唐与吐蕃清水会盟时,佛教在其中发挥了盟誓的作用,并成为吐蕃盟誓的重要环节。《册府元龟》载:
德宗建中四年正月,诏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相尚结赞等盟于清水,……时塞外无豕,结赞请出羝,镒出犬、白羊,乃于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文曰:“……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斋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无得愆坠。其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结赞亦出盟文,不加于坎,但埋牲而已。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礼,各用其物,以将厚意而归。”[31]
清水会盟首先采取的是唐与吐蕃都能接受的坛场“刑牲歃血”盟约仪式,请天地山川之神监盟。其后,又因佛教在吐蕃政治和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出现了向佛盟誓的现象。
两次会盟反映了唐朝在与吐蕃会盟时,都会考虑吐蕃的宗教习俗,以对方的宗教习俗为主。清水会盟中出现神、佛共同证盟的形式,以佛监盟非汉人习俗。唐王朝为了保障誓文的履行,不仅采用自己的神灵加以约束,还采用了“以彼之神,监彼之盟誓”的形式,借此达到约束对方行为的目的。德宗在《赐吐蕃尚结赞书》中提到:“契约至明,誓词至重,告于皇天后土、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国。”[32]敕书特别强调誓约的神圣性,皇天后土是约制双方的,诸佛主要是用来制约吐蕃的。然诸佛并未能约制吐蕃,唐王朝“以彼之神,监彼之盟誓”的意图随着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边境而破产。
唐与吐蕃会盟仪式的变化,体现了吐蕃文化的转变及其约制吐蕃的目的。唐与南诏会盟仪式的变化,同样体现了南诏文化的变化及唐希望其神约制南诏的意图。点苍会盟的盟约仪式中未出现筑坛、刑牲歃血的盟约仪式,盟神也以道教神灵为主,仅仅在崔佐时的誓文中夹杂了儒家文化的天地尊神。这说明点苍会盟中运用道教证盟的方式是南诏的意愿,体现了南诏的宗教文化。
点苍会盟是由唐王朝主动发起,希望结束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对立关系,争取南诏的归复,以抵抗吐蕃的侵扰。南诏虽然也需要唐王朝的支持,但其处于在吐蕃与唐之间的摇摆状态。这表明点苍会盟的双方关系中,唐王朝处于积极主动争取南诏归附的状态。为争取其归附,甚至动用军事力量为南诏归唐扫清障碍。所以,唐王朝更需要通过盟约的形式来约束南诏,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南诏后期世隆叛唐,攻打安南。安南经略使蔡袭让樊绰收集南诏资料。点苍会盟的誓书就是众多资料之一。唐军用箭将誓书射进南诏军营,企图让南诏遵守盟约,停止战争。
点苍会盟的誓文突出体现了唐王朝约束南诏的意愿。誓文中的监盟神是西洱河神、点苍山神。西洱河、点苍山也是盟书的存放之处。会盟虽然请三官神及五岳四渎神莅临,但实际发挥监管作用的是西洱河神和点苍山神。这两个神祇都是南诏的本土信仰。誓文对南诏破坏盟约的惩罚尤为严重,《云南志》载:“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33]而对唐王朝破坏盟约,崔佐时、韦皋不守约定的惩罚,则只是“神祇共罚”[34],而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这说明誓文最重要的意图是唐王朝约束南诏,防止南诏与吐蕃再次结盟,侵扰唐朝的边疆。利用南诏的神祇对南诏进行约束,实为唐王朝对南诏的重大策略,也是其“以彼之神,监彼之盟誓”政策的延续。
四、道教为南诏前期的国教
点苍会盟是唐和南诏冲破种种阻隔,历时10年,才达成盟约,重新确立友好关系。所以,点苍会盟的胜利完成,在唐与南诏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双方在点苍山确立盟约,扭转了二者与吐蕃的战争局势,成功遏制了吐蕃的扩张,夺回失地。点苍会盟意义重大,道教神灵作为点苍会盟监盟者,则凸显了道教在南诏的地位,是南诏前期的国教。
道教在大理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重要影响,吴棠以“蒙段佞佛好道”的文献记载,断定道教的影响力不亚于佛教,进而得出道教在南诏立国初期占有主导地位的观点。[35]吴棠对南诏道教发展的论断是确切的,点苍会盟中的道教就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反映。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佛教占据南诏后期的宗教话语权,道教在历史上的记载寥寥无几,因而无法断定道教在南诏的真实情况,只能靠一些碎片化的历史记载,去推断一个大致的南诏道教。而点苍会盟誓文的留存成为我们破解南诏道教历史地位的重要材料。
(一)盟约的证盟神
南诏道教经历了本土化和南诏化的过程,在继承道教神灵的同时,将南诏本土信仰融入道教,形成了具有南诏特色的道教。点苍会盟开篇即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神及管川谷诸神灵降临盟场,见证神圣的盟誓时刻。神灵的降临使得点苍会盟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成为约束双方行为的重要力量。三官神是南诏道教的最高神灵。五岳四渎神则是异牟寻所封的南诏地域神。三官神高不可攀,五岳四渎神分处不同的区域,只是见证盟约的订立,很难形成执行力。真正具有执行力的神祇是当地的神祇,即点苍山神和西洱河神。点苍山神是五岳中的中岳神。三官神、五岳四渎神和山川神构成了南诏道教的基本神灵系统。
南诏道教神灵莅临盟场,是唐王朝与南诏盟约的见证者和监督者,同时也是违背盟约的执行者。道教神祇构成的约束力主要针对的是南诏。因为南诏是道教的虔诚信仰者,这些神灵能够对南诏形成强大的约束力。
异牟寻时期,儒学、佛教、婆罗门教在南诏都有发展,而且为南诏统治者阐扬。在众多文化中竞相发展的时期,道教在点苍会盟中的出现,凸显了道教在南诏的地位。道教在南诏文化构成中居于主导地位,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
(二)南诏的守护神
在誓文中,虽然神灵对南诏的监控力和影响力更为突出,但是南诏也通过神灵加强了对唐王朝的约束。道教神祇成为南诏的守护神。誓文说:
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及节度使不为奏闻牟寻赤心归国之意,亦愿神祇降罚。[36]
南诏道教神祇同样惩罚不守盟约的唐王朝。这是南诏以自己的神灵监管唐王朝的重要表现。在发现违约的情况下,南诏的道教神灵会对唐王朝降下灾难,惩罚唐王朝,守护南诏。作为南诏的守护神,有义务守护南诏的安全。
南诏道教神祇是南诏能够成功归唐的重要守护力量。受天宝战争的影响,异牟寻对于唐王朝的地方官员持有怀疑的态度,并不能十分肯定崔佐时和韦皋能够将自己的赤心和誓文带给德宗。如若崔佐时和韦皋违背盟约,则由神祇降灾于二人。神祇对于崔佐时、韦皋的监督,成为安抚异牟寻的一颗定心丸,同时也是南诏顺利归唐的重要保证。为了回赠神灵的恩佑,异牟寻准备了丰厚的祭品,“奏请山川土地灵祇”[37]。
南诏前期与南诏后期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情势不同,道教在南诏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道教在南诏政治中出现,是南诏道教深入南诏社会的重要体现,突出了道教在南诏的社会影响力。
(三)南诏后期废道教
南诏王劝丰佑时期,南诏道教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走下了南诏的政治舞台。太和二年(829),南诏王劝丰佑宣布“废道教”[38]。劝丰祐(?-859),异牟寻之孙,寻阁劝之子,劝利晟之弟,823年至859年在位。贞元十年(794),道教在点苍会盟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至太和二年(829),劝丰祐废除道教。时隔35年,南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重大变化,道教与佛教的斗争日趋激烈化。
劝丰佑废道教之举,再次说明道教在南诏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劝丰佑废道教的初衷,是扶持佛教,将佛教的地位抬升至国家的主导文化。其扶佛废道之举,说明南诏佛教已有长足的发展,但道教仍然占据优势,佛教还不能与南诏道教相抗衡,只能通过国家的政治力量去扭转二者的地位。国家以政治的强力改变宗教信仰,是佛道二教冲突激烈的表现。
劝丰佑的母亲出家为尼是是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太和元年(828),“王母出家,法号惠海。”[39]太和二年(829),劝丰佑“用银五千,铸佛一堂”。[40]在一个家庭之中,母亲的职责是教育子女。所以,母亲对子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劝丰佑废除国家的官方信仰,将佛教定为国家宗教很显然是受其母亲的影响。劝丰佑的这一政策,使得佛教在南诏走向兴盛,成为大理地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之后的南诏帝王以及大理皇帝都以崇佛著称,大兴佛寺,推行佛学教育,甚至退位出家,在寺院度过晚年生活。大理国因佛教昌盛而享有妙香国之美誉。
废道教事件虽然使道教走下政治神坛,但是道教对大理地区的社会影响力依然存在。继南诏之后的大长和国国王郑旻有“服丹药躁怒杀人”[41]的记载。王崧本《南诏野史》载:“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以僧道为官属。”以僧道为官,说明大理国时期道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综合上述,点苍会盟对于唐王朝和南诏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奠定了唐王朝与南诏结盟抵抗吐蕃的基础。点苍会盟后,唐王朝与南诏相互配合,不仅抵挡了吐蕃的攻势,还收复了被吐蕃侵占的领土。双方维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时期,有利于南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西南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而道教是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者。道教神灵在点苍会盟中充当了盟约的见证者,是点苍会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道教神灵不仅充当见证者,还是对违约方进行处罚的执行者,是唐王朝惩罚南诏的执法神,是南诏监督和惩罚唐王朝的守护神。这表明道教神灵对于南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是南诏的主导文化。劝丰祐废道教事件,更好地证明了道教在南诏前期拥有着其他宗教不可比拟的地位,是南诏国教。南诏后期,道教虽然失去政治地位,但其在社会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注释:
[1]持此观点的学者:向达.南诏史略论——南诏史上若干问题的试论[A].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张泽洪.南诏大理时期的道教探微[J].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06.
[2]吴棠.道教在大理的传播和影响[A].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南诏史论丛[C].1986:206-207.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6]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7·南诏蛮)[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冯苏.滇考(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三).
[10]倪蜕著,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倪蜕著,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13]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倪蜕著,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16]倪蜕著,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17]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龙腾.天师道“蒙秦治”考[J].四川文物,1997(03).
[20]温玉成.<南诏图传>文字卷考释——南诏国宗教史上的几个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2001(01).
[21]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十一·遗诏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3]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5]全唐文(卷五二·德宗皇帝).
[26]巴瑞特著,曾维加译.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M].山东:齐鲁书社,2012.
[27]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8]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9]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0]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1]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2]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33]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4]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5]吴棠.道教在大理的传播和影响[A].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南诏史论丛[C].1986.
[36]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7]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8]南诏野史.云南图书馆藏版.
[39]南诏野史.云南图书馆藏版.
[40]南诏野史.云南图书馆藏版.
[41]尤中校注.僰古通纪浅述[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