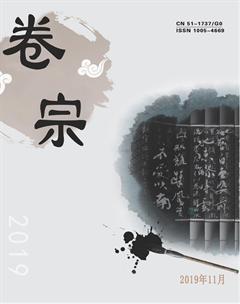认知符号学视角下中华文化的音译探析
摘 要:语言是一种符号,翻译是符号转换和分析的过程,涉及译者对符号及符号所处文化、社会、历史等的认知和心理过程。本文将从认知符号学视角,探究其在中华文化音译过程中发挥的相应作用。
关键词:认知符号学;语言;中华文化;音译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政府明确作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决定,将文化输出作为展现中国软实力的一种形式。翻译作为语际交流的媒介,是文化传播的一项主要途径,而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之一便是音译的使用。英语是拼音文字,可较为方便地同其他英美语言拼音文字相互借用词汇。而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之间,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给汉译外带来不小的挑战。使用音译虽然能更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一些特有概念和词汇(如 qi,kongfu 和yin yang等),而滥用音译则会影响读者理解,不利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因此本文拟从一门认知角度研究意义的科学,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音译研究,期望寻求到恰当译法。
2 认知符号学
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是一门从认知角度研究意义的科学,它试图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寻求对人类意义生成的理解。(苏晓军,2007: 121) 认知符号学为基于符号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得益于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发展与融合。皮尔斯全面提出符号学概念和研究范围,认为符号不仅包括语言符号,还包括非语言符号,并给予它们相等的认识论地位(卢巧丹、卢燕飞,2005: 49-51) 。他的这一观点突破索绪尔基于语言的符号学认识,丰富人们对意义的理解,即意义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符形、符指与符释的动态关系中获得解读和发展。由此,在翻译活动中,意义不局限于字面意义,而需要译者通过洞悉符号背后的认知、心理、社会等关系,结合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等,从而获得其在译文中的意义。
而翻译是一个意义与文化、心理、社会等因素交互影响的过程,翻译的载体和翻译的产物——文本体现出符号与外界的有机联系,同时翻译的产生也涉及符号的理解、编码、操作与接受。对于翻译而言,符号的意指和能指连接起符号产生的环境和主体。翻译不再是符号之间的孤立转换,而是文化与认知的交流。
3 认知符号学与中华文化的音译
很多学者认为,音译是专名翻译的最好途径且是必然的选择。如项东、王蒙提出:“中国传统文本英译时离不开音译,最主要原因是文化的异质性”。(项东、王蒙,2013: 104) 然而很少有学者怀疑音译存在的历时性和局限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果在翻译中默认差异的存在,那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共通就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当我们遇到文化负载量大的专名时,音译究竟带来了哪些惊喜和教训呢?
3.1 译名不一
译名不一在直观上表现为译语符形变化不一。这是由于翻译过程中符形与符指的不相关和符形与符释的偏离,以及译文符形音译过程中由于译者对读音的感受不同而造成的。译名不一,一方面不能完好地再现原文符指和符释的关系,另一方面给译语的纯度造成干扰。
例如:“阴阳”的英译。
目前国内外使用比较广泛的“阴阳”英译有“Yinyang”、“Yin and Yang”、“yinyang”、“yin and yang”、“yin-yang”等。“阴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负载词,是中国古代较具代表性的传统符号。在中华文化里,阴,古作“侌”,或加表示虚拟实体的“阜”作“阴”;阳,古作“昜”,或加表示虚拟实体的“阜”作“阳”。“侌”字从今从云,意为“正在旋转团聚的雾气”。“昜”意为“发散气体”。汉字,作为传统的象形文字,其一撇一捺都蕴含着深刻寓意。“阴阳”二字的唯一独特性承载了汉语的符指和符释。
众所周知,音译的产生是文化差异所致,以音赋形的方式比意译更能确保译文形式的一致。但从目前所通用的音译“阴阳”来看,音译没能使译文统一: “Yinyang”和“Yin and Yang”译文都将首字母大写,Yinyang作为一个整体,“Yin and Yang”强调其区分于单独的Yin和Yang,表达特指性; “yinyang”、“yin and yang”、“yin-yang”译文使用小写和连字符形式,表示音节的拼读和音节数。众多译法和符形不一给英语读者造成很大的麻烦,而且也不利于读者在符形与符指和符释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联系。
3.2 专名翻譯
音译是用译入语的文字符号来表现原语的发音,从而引入新词的一种翻译方法,主要用于专有名词的翻译上。中国古代已有音译方面的探索,如唐朝著名的翻译家玄藏在翻译佛典时就大量使用了音译词,他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翻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不译”的翻译理论,即: 秘密故不翻;多义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然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速,“五不翻”的范围也在缩小。如今,翻译的种类、范围更多更广,音译在翻译中的作用也更大,但是很多译者奉“五不翻”为圭臬,将译文中能承载原文符指和符释的符形的语码弃之不用,而使音译泛滥,导致译文的可读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
音译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之于另一种文化的神秘感、权力、可译度,然而这些都没有提及翻译的本体,即该专名在两种文化中存在的原由。音译也没有从符号的组成、重新建构及其在异质文化中的认知找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有必要重新从认知符号的角度对专名翻译做出本体论上的合理解释: 一种文化独有的专名对另一种文化并不是不可译的神秘之物,而是可以交流的符号。译者可以通过符形替换、移植借用、编码重构等方式获得符号的再生,从而实现文化交流。
4 结论
借用赵彦春教授的一句话:“音译不是唯一的方法,基于认知符号学,准确融入符形、符指、符释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做好专名翻译是当务之急。” 音译词汇虽然简洁,但如果读者没有预设文化,则很难理解音译词所表达的涵义。因此,中华文化音译的范围是随着时间和文化交流频度、深度而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恒量。
参考文献
[1]苏晓军.《复活节的翅膀》的认知符号学分析[J].外语学刊,2007(1).
[2]卢巧丹,卢燕飞.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对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3).
[3]项东,王蒙.中国传统文化文本英译的音译规范刍议[J].中国翻译,2013(4).
作者简介
王振(1993-),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在读研究生,沈阳化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